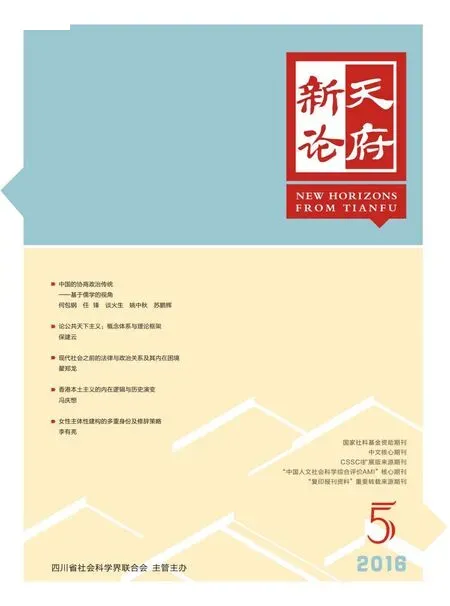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家庭
——以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妇女自杀为例
赵刘洋
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家庭
——以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妇女自杀为例
赵刘洋
本文聚焦于“道德的法律实践”两种类型即“滞后道德”的法律实践与“超前道德”的法律实践对妇女自杀的影响。前者将对妇女贞节道德的要求纳入到法律中,具体包含三种机制:法律鼓励妇女贞节道德受到侵犯时选择自杀;法律对妇女的保护与贞节道德联系起来;法律惩罚违犯贞节道德的行为,妇女因选择受限而趋于自杀。后者则关于法律对妇女超前性别道德的追求,具体包括法律对激进性别平等和离婚的鼓励、道德从法律退出后道德约束力的弱化、法律对权利的强调导致妇女对权利的片面理解。两种类型的实践与具体社会实际存在诸多冲突,都造成妇女自杀,因此,法律对妇女不切合社会实际的道德规定促使妇女趋于自杀。法律实践应根据社会实际以实用的方式调整权利与道德的关系,现代法律尤其要处理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关系。
道德法律社会家庭主义现代性妇女自杀
缘 起
笔者曾于2013年在某村陆续从事一项田野调查,调查的目的是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改革时期中国基层乡村家庭道德的转变与延续,①笔者最初的调查更多的是从记忆的角度进行分析即被访谈者如何认知改革时代的家庭道德,而基于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又是如何表述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家庭道德。在调查过程中,搜集到近30年来该村的自杀案例。当回到书斋与档案馆中研究十八世纪时期的诉讼档案时,发现基层社会中妇女自杀现象普遍,且多与道德伦理有关。而田野调查的经验使笔者在阅读清代档案时至少有三点启示:一是在当代基层社会中,自杀与公共秩序发生关系时才会进入官方的话语体系中,而实际上基层自杀案例往往与家庭秩序或伦理道德有关②吴飞关于华北某县自杀的调查统计简表中,总共搜集58份案例,除1例原因不详外,其中有41例是与家庭秩序相关的。参见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二是中国基层社会自杀行为者往往是女性,这与她们所处时代的法律构造是否存在某种内在关系;三是自杀者本身的“声音”已无法“听到”,但能从田野调查和档案中透视自杀者的行为逻辑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由此将关注点集中于基层社会中的女性自杀行为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将历史与现实彼此参照,既反思历史也批判现实,希望明晰历史与现实中妇女自杀行为逻辑的变迁与延续,以此亦尝试超越比附历史的研究路径。
本文希望融合经验与理论、历史与现实、档案研读与实践调查,对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妇女自杀现象提出一己之见。当然本研究不可能解决这一复杂问题,只是希望能对此有所回应。
过去:“滞后道德”的法律实践与妇女自杀
对中国社会的自杀现象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诸多成果。*See 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 — China, 1990-2002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Vol. 53, No. 22 (June11,2004), pp. 481-484;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Michael Philips,Are ‘Killing’ and ‘Letting Die’ Adequately Specified Moral Categories? Philosophical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 Vol. 47, No. 1 (Jan., 1985), pp. 151-158;Suicide Rate in China:1995—1999.与之相比,关于清代社会的自杀现象,对其进行系统、专门研究的相对较少。*郭松义、布迪和莫里斯、戴真兰(JanetM.Theiss)、滋贺秀三等学者都曾注意到,其中后两者也关注到妇女自杀。戴真兰以性别研究的视角着重于十八世纪的“贞洁政治”,滋贺秀三则是从妇女在家庭中的结构性不公的地位解释自杀的。郭松义:《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8卷;See Janet M.Theiss,“Femininity in Flux:Gendered Virtue and Social Conflict in theMid-Qing Courtroom,” in Susan Brownelland JeffreyN.Wasserstrom, eds. Chinese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47-66.尤其是JanetM.Theiss.Disgraceful Matters:The Polities of Chas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滋贺秀三注意到除了明清律斗殴.威逼人致死条之外,围绕自杀的规定,散见于条例之中的各处,其判例也很丰富,参见〔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92、513页;博迪和莫里斯认为自杀的盛行能够反映出人们在儒家社会中的紧张心态和受压抑心理,《刑案汇览》最为常见的犯罪中,“威逼人致死”罪在数量上位居第二,“威逼人致死”只是一种概括性表述,实际上此类犯罪的具体情形多种多样。参见:D.布迪 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5页;有意思的是马克斯.韦伯认为“自杀”在中国具有“巫术”意义,如“在中国,债权人会以自杀来相威胁,有时候甚至抱着死后仍将追索其债务人的期望而真的自杀”以及“受冤者的哭号会引来鬼神的报复。这在受害者是由于自杀、悲怨和绝望而死时,尤其如此。最晚起于汉代,这种坚定的信仰是从官僚制与诉之于天的权利的理想化投射萌芽的。我们也已看到伴随着真正的被冤曲者的大众的呼号,对于官吏的约束有多大的力量。”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也涉及到妇女自杀,如T’ien Ju-k’ang, Male Anxiety and Female Chast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thical Values in Ming-Ch’ing Times, Leiden: E. J. Brill, 1988;Paul Stanley Ropp,Paola Zamperini,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Passionate Women: Female Su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rill, 2001;赖惠敏:《法律与社会:论清代的犯奸案》以及〔美〕苏成捷:《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均收于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本文先着重探讨清代法律对妇女不切实际的道德主义要求如何使妇女趋于自杀。
既有的研究表明清代(18世纪)中国人口激增,土地压力日益增大,生存压力加剧,社会流民增多。“摊丁入亩”的推行和“贱民制”的废除放松了对民众的身份限制,伴随着中国商品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雇工、佣工、合伙谋生的民众增加。以上两种变化,加上性别比例的失调导致:基层社会出现没有娶妻的“光棍”现象,底层妇女的实际生活缺乏遵守贞节道德的环境*关于十八世纪的“流民”,可参阅〔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49-58页;关于十八世纪的“佣工”,可参阅〔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五章;关于十八世纪的“光棍”,可参阅Matthew H.Sommer,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另一方面,面对底层民众的实际生活状态,清代法律*传统法律的范畴并不限于《大清律例》,关于此点,具体参见马小红:《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辨正——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本应采取实用性的一面,但为加强社会控制却选择了道德主义的一面,清代法律强化对妇女遵守/违背贞洁道德的奖励/惩罚,顽固坚持与社会实际相矛盾的道德主义,易驱使妇女选择自杀。
底层社会的贫穷、妇女易受侵犯以及法律对贞节的强调,是清代中国底层妇女面对的三个互为相连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尽管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是“内卷”还是“发展”一直存有争议,*参见〔美〕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美〕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但法律档案中有诸多案例反映出底层民众仍然没有脱离“糊口经济”的生存状态,底层妇女面对贫困的生活境遇,为了生存而做出不符清代法律的行为;那些家庭中的男子为了生活而外出佣工的以及守寡的妇女,容易受到底层社会中的男性的骚扰和侵犯;妇女的贞节在18世纪的中国社会进一步被强调,无论官府还是社会都非常重视妇女的贞节道德。
清代法律关于妇女自杀的具体规定主要是在“威逼人致死”例中,尤其要指出的是,“威逼人致死”律中总共包括25种情形,其中涉及奸情的就有17种,包括“犯奸”及“杀死奸夫”等纷繁复杂、轻重各异的条文。*(清)薛允升:《读例存疑》,第三十四卷,人命之三,“威逼人致死”。另外,清代法律还规定妇女自杀案件涉及到地方官员的责任,比如:“凡调奸图奸未成者,经本妇告知亲族乡保,即时稟明该地方官审讯。如果有据,即酌其情罪之重轻分别枷号杖责,报明上司存案。如本家已经投明乡保,该乡保不即稟官,及稟官不即审理,致本妇怀忿自尽者,将乡保照甲长不行转报窃盗例杖八十,地方官照例议处。”*《大清律例》第二十六卷。总之,可以看到清代法律对妇女自杀案件非常重视。
妇女在清代法律表达中被预设为两种形象,一种是“舍生取义”的“贞节烈女”。比如,“孀妇自愿守志而母家夫家抢夺强嫁者,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其娶主不知情不坐,知情同抢照强娶律加三等,未成婚妇女听回守志,已成婚而妇女不愿合者听如孀妇不甘失节因而自尽者,照威逼例”。*《大清律例》第十卷。还有因强奸导致的各类羞愤自杀者,比如,“强奸内外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未成本妇羞忿自尽者,俱拟斩监候,其强奸已成本妇羞忿自尽者,俱拟斩立決”等。另一种则与此相反,是“犯奸”和“不孝”的妇女形象。若妇女犯奸引起父母等家人“羞愧自尽”的,妇女此种情形自尽,则“已死不议”,否则妇女就要遭受严重的惩罚,“妇女通奸致父母羞愤自尽者,无论已嫁、在室之女,俱著问拟绞立决”,“因奸因盗以致父母忧忿自尽者,照子孙过失杀父母例,拟绞立决”。
清代社会关于妇女的行为设有一整套的法律规范,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关于妇女的家内伦理和婚姻中的“性道德”。与此相关,清代法律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归为遵守贞节伦理的妇女(贞妇、节妇、孝妇、烈女)以及违背贞洁伦理的“犯奸”妇女,还有作为弱势的妇女形象,如遭到拐卖和抢夺等。清代法律对妇女有明显的道德要求,即应该遵守贞节伦理,国家奖励和保护那些遵守贞节的妇女,惩罚或不保护那些不守贞节的妇女。
本文依据的资料主要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的230件刑科题本,因为这些案件都是作为“命案”上报和处理的,因此在判决时都详细比照清代律例。这些资料涉及到妇女因遭到调戏而自杀、孀妇因遭到逼嫁而自杀,另外还有妇女因为诸种“奸情”败露而自杀,这些类型的妇女自杀占中央司法档案中妇女自杀案件的主要部分。
1.法律对妇女守贞极端行为的鼓励
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所藏的清代妇女自杀的法律案件中,妇女因遭调戏而自尽的案例数量众多,在这一类案件中,妇女若遭到调戏因而自杀的话,那么调戏者将被依照律例被处以绞监候,妇女将会得到政府的旌表。
清代法律详细规定了旌表妇女的类别,〔1〕清代政府对旌表妇女非常重视,希望通过大规模旌表妇女的行为来使社会形成极为注重妇女贞节道德的风气。
尽管康熙曾专门下诏反对女子轻易自尽的做法,*康熙曾下诏:“人命至重大,而死丧者恻然之事也。夫修短寿夭当听其自然,何为自殒其身耶?不宁惟是,轻生纵死,反常之事也。若更从而旌异之,则死亡者益众矣,其何益焉!”转引自〔美〕卢苇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2页。雍正皇帝也曾要求地方官员严格依照谕旨向民众告知朝廷爱惜民众生命的本意,不要让民众误解了旌表的目的,特意强调旌表原本的目的并不是鼓励民众自杀,并表示对那些不珍惜生命而轻生纵死的妇女,并非全部旌表。*雍正曾降旨:“嗣后若概予旌表,恐转相则效,易致戕生,深可悯恻。著地方有司,将朕前旨广为宣布,家喻户晓,倘宣布之后,有不顾躯命,轻生纵死者,不概予旌表,以长闾阎激愤之风。”转引自陈惠馨:《清代法制新探》,五南图书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第262页。但是,到乾隆的时候则出现了大规模旌表妇女的现象。卢苇菁曾以旌表的妇女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突出明清贞女现象之普遍。她根据《实录》的记载,发现清军入关第六年表彰的不到十位妇女,此后逐渐以惊人的规模上升,1644-1850年间大约有217336人因堪为楷模的道德伦理行为而获得旌表,其中女性则为214784人,而妇女主要表现是在“节”和“烈”上,很少是因为“孝“和”“义”。〔2〕
在这样的一种极端强调妇女贞节道德的社会中,弥漫着一种轻生的风气,诸多妇女遭受到调戏即选择自杀,贞节对这些妇女而言,比生命还要重要。 江苏高邮州的靳赵氏嫁与靳雄为妻,离她的娘家赵陈氏家不远,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初四日下午,靳赵氏哭到赵陈氏家。原来她丈夫靳雄出门去了,与他丈夫一起撑船的同村人景三春见赵氏正敞着怀喂孩子,看四下无人后,假装引孩子玩,走到赵氏身边调戏,赵氏就大声喊骂起来: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把我调戏!邻居听到哭喊声赶到赵氏家中问其情由,赵氏也不言语,哭到娘家,赵陈氏劝她先回家,因为家里还有孩子。赵陈氏把这事告诉女婿靳雄,两人去找景三春,后者已经躲起来了,没有找到。“下晚回家,不想已经服卤死了”。清代官员认为应旌表该妇女,“赵氏一经调戏,即矢志捐躯轻生重节,贞烈可嘉,旌表以维风化。”*《题为审理高邮州民景三春调戏靳赵氏致羞忿自尽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初四日,档号:02-01-07-307-071-0682。
由于当时社会性别失衡,家中男子因生活压力外出佣工等时,妇女缺乏外在的安全环境,容易遭受侵犯。清代法律鼓励妇女遭到调戏即轻生自尽,“重节轻生”的妇女会受到官府旌表,那些因调戏妇女而致命案的男子则会受到严惩。董有成赴琉璃镇卖炭外出,有本村鹿万忠前赴伊家,推门入室,用言语向伊妻杨氏调戏,伊妻羞忿难堪,于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夜间乘伊睡熟,在鹿万忠门首树上自缢身死。据董有成的兄弟口供称:到傍晚时候哥子卖炭回家,嫂子向他说了,哥子说这是丑事,不要声张罢。嫂子只是啼哭,饭也不吃,不料到二十三日夜里嫂子就到鹿万忠家门首树上吊死了。最后鹿万忠依例“但经调戏本夫羞忿自尽者”被判“绞监候,秋后处决”,而杨氏“因被鹿万忠调奸不从,捐躯名志,洵属节烈可嘉奖,应请旌表以维风化,以慰幽魂。”*《题为审理磁州民人鹿万忠调戏董有成之妻致其羞忿自尽身死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三十日,档号:02-01-07-307-081-2582。
可以看到,杨氏在这一案件中并非直接选择自杀,她告诉了她的丈夫,但他的丈夫因为觉得自己的妻子遭到调戏毕竟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丑事”,如果传出去,自己也会觉得丢失脸面,因此他选择隐忍。杨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能选择自杀来证明自己的贞节。妇女自杀后,调戏者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而妇女的贞节则获得了证明。
这样的案例在18世纪很常见,在当时的环境下,被羞辱的妇女选择十分有限。遭到调戏在妇女看来是一种羞辱的事情,由此心生的怨气,但无法释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直接选择自杀。除直接选择自杀外,也可以采取其他的选择,比如告诉丈夫、家人等,希望家人去找调戏者以还清白,但家人碍于“丑事”不可外扬的担忧,往往很少去找调戏者,对妇女不要声张,或者即使去找了调戏者,但调戏者并不承认;妇女也可以报官,但又因缺乏证据,也很难奏效。心生“羞忿”的妇女为证明自身清白最终只能选择自尽。
而妇女自杀,不仅证明了自己的贞节和清白,自杀事迹也会被地方政府广泛宣扬,目的是维持社会风化。妇女获得旌表,对地方官而言,亦可显示“教养”成绩,这在社会中却造成了妇女激烈轻生的风气,妇女甚至可能会因为一句调戏的话就采取自杀行为。
与之相比,即使是守节数十年也未必能获得清代官府的旌表,这在社会上无疑强化了对妇女自杀的鼓励。“吴氏于顺治十三年嫁与文沅为妻,至康熙十九年文沅身故,吴氏至康熙五十四年始亡,计其守节之年虽有三十余载,而文沅故时吴氏之年已逾三十之外,实与旌表之例不符。”*《题为安徽省休宁县故民汪文沅之妻吴氏守节年例未符毋庸旌表事》,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微缩号:02-01-03-07-061-0456。吴氏即使是守节三十余年,但因为她的丈夫死时她已经三十余岁了,因此无法获得旌表,由此也可以看到清朝对旌表规定的严苛。
因此,妇女遭到调戏时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调戏成奸”,一旦奸情泄露就将遭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一种即是反抗不从,这又可分为自杀和不自杀。若妇女不自杀,为证明其清白,妇女求助家庭,但家庭往往碍于“丑事”不可外扬的担忧,妇女因“羞”生“忿”,当“忿”无法释怀而自尽(这类情形很多);若求助法律,不仅难以达到清代法律的证据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方式也不能完全证明妇女的清白,反倒容易“丑声外扬”,遭到戏辱的妇女的“忿”仍然无法消除。笔者搜集到的档案显示很少有妇女曾专门因遭到调戏而求助于法律的。相反,妇女若遭调戏即“羞忿自尽”,即可达到以下“效果”:一是可以证明妇女的清白;二是获得政府的旌表,妇女家庭获得奖赏,自杀妇女得以建祠设位,地方政府官员为显示“教养”成绩,也以此作为地方荣誉;三是“调戏者”会依照清代法律判处“绞监候”,达到惩罚的目的,只不过代价却是遭调戏妇女失去了生命。
2.法律对妇女守贞的保护
清代规定对守节达到一定年限的孀妇进行旌表,这对清代社会的妇女而言,当然是莫大的荣誉。《大清会典》载:“各府、州县建节孝祠,祠外建大坊,应旌表者,题名其上。身后设位祠中,由督、抚、学政会题,取具册结送部。其在部呈请者,由部行查,督、抚覆咨,题准令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建坊。如奉有御赐诗章、匾额、缎匹,由内阁交部发齐督、抚,行地方官给领。节妇不论妻妾,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身故,其守节已及十五年,俱准旌表。”〔3〕那些妇女的姓名和事迹,由地方政府一直上报到中央,之后作为维护风化的典型进行旌表。
旌表在传统时代则具有重要地位,代表皇帝的荣典,无论对妇女而言,还是对她的家人以及地方政府而言,都是极为荣耀之事。“此类牌坊或牌楼乃由帝王之旌表而建立者,中国素以旌表为维持社会风教上极重要者,为皇帝荣典之一者,不只为历代所重,即于民间,亦以受旌建坊为无上之荣焉。”〔4〕妇女旌表在当时的基层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直到民国时期,游历中国的日本学者小竹文夫曾因见清代旌表遗迹,心生感慨而写道:“旅行中国者,于各处城邑乡村或郊外墓表之前,见其遍立前代遗物之旌表之牌坊及牌楼。其年久者,石柱或倾倒于碧草间,使旅人兴沧海桑田之感。亦有虽已黝黑而俨然如故者。尤于较新者,于中国市镇乡村生活中,现出其不调和,似夸其华美之石材,壮丽之雕刻而矗立道周。”〔5〕在当时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极端重视贞节的风气。
清代法律并不干涉寡妇改嫁,但寡妇若改嫁后就失去了其在夫家的财产处理权,*关于妇女的财产,可参阅白凯(Kathryn Bernhardt):《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苏成捷(Matthew H.Sommer),“The Uses of Chastity:Sex,Law,and the Property of Windows in Qing China,”in Late Imperial China,Vol.17,No.2,December 1996.同时清代法律鼓励寡妇自愿守节,任何违背寡妇意愿强逼改嫁的应遭受惩罚,这使得妇女极为重视贞节;但寡妇自愿守节,贫穷的夫家人就要承担提供寡妇生活物资的经济负担,加上当时社会性别严重失衡,未娶妻者不一定都特别贫困(比如有诸多案件提到交付的彩礼钱已达到数十两,想必一个处于糊口的男子难以拿出这些银两),于是在财礼的诱惑下,夫家更容易采取威逼寡妇改嫁的抉择,而寡妇自尽不仅能够守节,而且能够获得政府的旌表,那些“逼迫孀妇改嫁者”也会因此而遭到惩罚。在贞节道德和严峻现实夹缝中的妇女容易采取自杀,因为在她们看来,贞节比生命更重要,在无法实现守节的心志下,只能选择自杀。
比如,詹人璧胞侄詹伯章病故,遗妻刘氏孀守。詹人璧每月给钱,贴补用度。后因詹人璧家中日渐困难,无力资助,刘氏渐出怨言。詹人璧考虑刘氏难以终守,就劝刘氏改嫁,刘氏剪发不从。詹人璧因贫难养赡,立意将刘氏改嫁,捏称刘氏自愿改嫁,托陈鸣岐媒合,觅得娶主孙万贵,抬轿往娶。后尚未成婚,刘氏不甘失节,乘间投缳殒命。〔6〕
再如,陈玉隆长子陈富于乾隆三十一年身故,遗媳彭氏年甫十八,并无生育。陈玉隆以彭氏年轻,恐难终志,与彭氏表兄王起义商议遣嫁,王起义希图媒金,兼可分润财礼,从中怂恿。陈玉隆即托王起义代觅人户,后陈氏不甘失节,十九日乘李氏归家,投缳殒命。〔7〕
尽管清代法律规定“孀妇自愿守志而母家夫家抢夺强嫁者,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其娶主不知情不坐,知情同抢照强娶律加三等,未成婚妇女听回守志,已成婚而妇女不愿合者听如孀妇不甘失节因而自尽者,照威逼例”*《大清律例》第十卷。,但法律档案中显示这些妇女在自杀之前并未曾求助于法律。即使求助于法律,清代政府因此保护孀妇的守节心志,但处于糊口经济的现实境遇下,妇女守节仍会面临诸多关涉生存的现实问题,我们能从法律档案中看到许多处于底层社会中的孀妇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加上法律的一再鼓励,许多孀妇为守节最终选择自杀,如黄氏因刘泽远强嫁不从,自刎身死,黄氏死后获得旌表,“该抚转行该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自行建坊,其该县节孝祠内设牌之处照恩诏定例遵行。”〔8〕
3.法律对违背贞节道德行为的惩罚
在注重贞节伦理的社会中,妇女的犯奸行为对其家人而言,是一件“没法见人”的事情,容易造成其家人自杀。“震泽县沈维城遇无服族叔沈灿文之妻凌氏在场乘凉,彼此闻谈遂诱成奸,后凌氏因奸败露,羞愧自缢。沈灿文控县差拘候讯,沈维城母纽氏以伊子犯奸酿命,恐干重罪,又见与其有讼嫌沈氏私自谈论,生气即于二十二日夜潜至沈氏家猪屋投缳毙命。沈维城‘合依子孙因奸因盗以致父母忧忿自尽者,照子孙过失杀父母例’,拟绞立决”。*《题报苏州府震泽县民沈维城与沈凌氏通奸败露致氏自尽拟绞立决事》,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档号:02-01-07-1467-001.这里有两位妇女选择自杀,凌氏与沈维城之间的奸情败露,在当时一种极端重视贞节道德的社会环境中,前者因为觉得羞愧,也要面对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压力,因此选择自杀。沈维城的母亲得知儿子犯奸,又看到别人在谈论此事,一方面觉得非常羞愧,另一方面也担心自己因为儿子的行为要承担重罪,在羞愧与恐惧中选择自杀。
在这一类妇女自杀的情形中,多数是一些“通奸”案件。如前所述,妇女的犯奸行为如果被告到官府,就将遭到惩罚,妇女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又“惧”又“愧”,不仅会遭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将背负着“污名”生活,妇女就有可能采取自杀的行为。王成学同儿子王铎在望都县佣工,王铎母亲王丁氏听其侄子丁全孝说二十八日晚上他撞见了丁青山从她儿媳刘氏家里走出,丁全孝喝问了一声,丁青山就跑了。第二天王丁氏问过儿媳刘氏,后者并没有言语。等到王成学父子都回来,王丁氏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父子,王铎走去向刘氏查问,刘氏说是丁青山们走来轮奸她(后查清事实是刘氏与丁青山通奸),王铎把这件事情告到县衙,不料刘氏就上吊死了。*《题为直隶束鹿县民丁青山与王刘氏通奸败露致氏自尽并奸夫之祖畏累自缢议准绞立决事》,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档号:02-01-07-1177-003.刘氏见其夫要去报官,这就意味着刘氏的“奸情”有可能暴露,如果确实属实,刘氏就将遭受严厉惩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刘氏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而选择自杀,这样的她犯奸的行为因此就不会追究了,只不过这样的代价是付出生命。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犯奸的妇女被发现后首先要面对丈夫的压力。广东归善县民陈亚扁与骆亚受邻村熟识,长相往来,陈亚扁之妻邱氏与骆亚受素不避忌。乾隆四十九年陈亚扁自外佣工回家撞遇,骆亚受在房内搂抱伊妻邱氏调笑,随即上前捉拿骆亚受,骆由窗门跳出,陈亚扁向邱氏诘出奸情,叱骂欲殴,邻人谢煌训、魏廷俊劝止,邱氏因奸情败露服毒身死。*《题为广东归善民陈亚扁妻与骆亚受通奸败露致氏自尽砍伤骆亚受身死议准绞监候事》,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档号:02-01-07-1739-007。
清代对犯奸案很重视,妇女犯奸即使“羞愧自尽”,也应该按照法律上报官府,否则的话妇女的夫家人也会受到政府的惩罚。徐荣祥系徐荣发胞兄,徐荣发娶妻王氏,徐荣祥向在徐荣发前间楼上住歇。嘉庆四年六月初九日徐荣祥与王氏调戏成奸后,遇便宣淫。有一次王氏与徐荣祥行奸被徐荣发看破,于是斥訾王氏的不是。徐王氏用刮布小刀自抹咽喉身死,徐荣祥畏惧赤身跑避。徐荣发顾惜颜面,诡称徐王氏因夫妇口角轻生自尽,买棺殓埋。经县访获犯,详审,供认不讳。徐荣发被严厉惩罚。*《题报孝感县人徐荣祥与弟媳通奸败露致氏自尽拟绞立决事》,嘉庆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档号:02-01-07-2135-01。
妇女因为奸情自杀,这一类案件也“不准私和”,因为在地方官员看来,因奸酿命是严重的案件。比如一份来自四川巴县的档案:宋友章的妻子冯氏与周绍基通奸,周绍基的妻子张氏与冯氏争吵,冯氏因此自杀。宋友章的母亲因为家里贫苦,而且年纪超过了六十岁了,“不愿拖累,愿具悔结”,冯氏的娘家人也是希望如此。但地方官员当堂驳斥:因奸酿命,岂容私和请息。因此堂批:“不准结,掷还!”他认为这样的行为“殊属冒昧可恶!”〔9〕可以看到该地方官对于犯奸的行为极为厌恶,更何况由此还引发命案,因此这样的行为坚决不能悔结。
正如一位刑部官员所认为的那样,犯奸的行为应该遭受惩罚,“盖名节乃举世所重,奸淫为恶之首”,因此要“惩邪淫而维风化!”〔10〕在他看来,法律应该通过惩罚这些犯奸者,在社会中造成一种压力,才能有效维持社会的风化。
总体来看,清代法律惩罚犯奸的妇女,使妇女犯奸的行为暴露后,要面临法律的惩罚,还有夫家人以及习俗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犯奸妇女因又“羞”又“愧”又“惧”,便趋于采取自杀行为。
从以上可以看到,清代将对妇女的贞节道德限制纳入法律中,法律鼓励妇女在贞节道德遭到侵犯时应极力反抗,以证明清白;法律将对妇女的利益保护与贞节道德密切联系起来,那些遵守贞节道德的妇女可以获得法律的保护,反之,若没有遵守法律所鼓励的贞节道德,法律则不保护;法律对违犯贞节道德的行为进行惩罚,使得那些妇女面临诸多压力。道德法律化使妇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选择极为受限,诸多趋于自杀。
法律对妇女的“滞后的道德要求”对妇女自杀造成诸多影响:当妇女遭到侮辱就会由“羞”致“忿”,无论侮辱轻重,“忿”无法从内心释泻,同时也为了“清白”而舍弃生命;即使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也应该追求忠贞,这是底层社会孀妇的生存动力之一,当这样的追求遭到威胁而无路可走,则选择以死明志;“犯奸”对妇女和她的家人而言是一件耻辱和丢人的丑事,妇女犯奸被发现,由“羞”生“愧”,因为“内心羞愧没法见人”而选择自杀。
现在:“超前道德”的法律实践与妇女自杀
随着传统社会的制度理念和意识形态全面崩溃和解体,以父系家庭为基本构造的中国传统法律转变为以“权利人”为中心的现代法律;作为“礼”的重要内容的道德主义和身份差别从现代法律中退出,传统社会中的身份、家族和团体的支配亦被摧毁;传统社会中道德教化作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方式的一套保证体系如乡约和旌表制度以及士绅和地保等阶层群体,因无法应对西方的强烈冲击和全面的社会变迁而渐被抛弃。*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萧公权:《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英文版),《萧公权文集》(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尤其是第十五章以及第312-317页。但是,传统的对妇女贞节道德严格限制的法律被废除后,并不意味着妇女自杀问题就能获得解决。
民国时期,尽管在法典层面妇女比以往获得了更多的权利,但乡村基层社会中,过去的一套规则和习俗仍然延续着,在一些情形下,新的法律因为没有考虑到社会实际,在法律实践中,与以往相比,反倒损害了妇女的利益。比如在继承法方面,正如白凯(Kathryn Bernhardt)所指出的,清代法律确定了孀妇可在侄子中选择“爱继”侄子,且优于“应继”侄子;国民党法律则完全废除承祧制度,确定妇女与男子同样的继承权,但在农村实际生活中,新法律的作用十分有限,新的法律看似保护妇女的权利,实际上则是对妇女原有权利的损害。〔11〕
更多的情形是,新的法律在诸多方面并未对乡村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妇女在乡村社会中的处境并未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善,民国的法律变革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与城市相比则是很缓慢的。乡村社会激烈的变化要等到中国共产党进入后才发生,革命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改变了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主张男女平等,努力改变妇女被压迫的境遇。但是,悖论的恰恰是,法律对妇女超前的道德追求带来了一个未能预料的后果:妇女自杀比以往更为普遍。
1.法律对“激进性别平等”的追求与对离婚的鼓励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动员过程中就认识到妇女的重要地位,注意发挥妇女作为“半边天”的作用。最为有名的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专门提到推翻“夫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即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2〕
中国共产党重视通过制定法律以动员妇女参加革命,激进的性别平等理论在中共争取政权的过程中有明显的体现,并通过法律的方式将其确认,尤其是在婚姻法方面。黄宗智曾指出此种激进的性别平等法律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早在“江西苏维埃根据地时期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九条就宣布‘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样的法律远较西方国家激进,西方国家直到60年代才开始实行无过错离婚。”〔13〕
正如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注意到的法律制定与法律在社会中的效果之间的复杂关系,脱离社会实际的激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诸多问题,法律制定的目的会与法律实际效果产生严重的背离。尽管他是以民国政府的继承法为例,“在亲属组织中,目前法律对财产继承问题的规定似已成为两性不平等的实例。一旦男女平等的思想被接受,这样的规定将产生一种修改单方亲属原则的行动。正如我要说明的,财产的继承是两代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部分。供养老人的义务,落在子女身上的社会里。在目前父居家庭的婚姻制度下,女儿和儿子不能分担同等的义务。因此,双系继承与单方立嗣相结合将形成两性的不平等。从这一点来看,立法的后果显然与期望是背道而驰的。”〔14〕这样的问题同样发生在同时期江西苏维埃时期中共激进的婚姻法实践中。
此种激进性别平等的法律因与社会实际冲突明显,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问题。首先是对于农民而言,“婚姻方面的花费相对于农民的收入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生只负担起一次,允许妇女自由而言,对于农民家庭而言是很严重的打击。”其次,对于红军战士而言,因为长期在外,妻子更容易离婚,“这显然威胁到当时红军战士对妻子的主张权,这将进而威胁到中共的政权基础。”另外,因为离婚过于自由,“会使得一方面男性党员借口妻子政治的落后,实际想与来自城市的女同志结婚”。〔15〕而且妇女也可以借婚姻自由,实际上想与干部结婚。正是在诸种现实尤其是从中共革命政权的稳定性方面的考虑,要获得红军士兵和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中共的激进的性别法律很快从激进的立场中撤退”。〔16〕
但是,这种激进平等性别的思维因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宣传的“废除封建婚姻”的口号具有一致性,后者不会根本背离其政治诉求,所以在取得政权后进行的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得到更为直接的体现,但是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大量的妇女(1950-1953年每年约有7-8万名)遭到杀害或自杀。〔17〕
1950年新的《婚姻法》目标是“废除封建婚姻”,在原则部分首先指出,新的婚姻法要“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而且也专门强调“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新的婚姻法促进了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离婚案件激增,妇女纷纷要求废除封建婚姻,主动要求离婚。如北京市人民法院374件判决离婚的案件中,女方单独提出的有222件;〔18〕河南省仅商丘地区,“据1951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共发生婚姻案件达1854起,1953年贯彻《婚姻法》过程中, 商丘市一个市即发生各种家庭纠纷案件104起, 婚姻案件123起,离婚案件108起。”〔19〕笔者在苏北邳州县档案馆也发现这一时期离婚案件占法院处理案件的绝大比重。
新《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在乡村社会则遭到广泛的抵制和反抗,妇女提出离婚的主张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新的《婚姻法》鼓励妇女选择离婚,但在实践层面并未建立起保护妇女权利的常规机制,这一方面使妇女的离婚诉求无法达成。比如,“苏北有一个童养媳遭到婆家的毒打后去找乡指导员诉说,但这位乡指导员却敷衍道,自己也并没有什么办法”;〔20〕“河南省洛阳县被杀、自杀妇女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因为乡(村)干部不给她们开离婚或结婚的介绍信而死的。绥远省固阳县五区妇女王凤英因受虐待要求离婚,村干部不给开介绍信,她要求保护,干部也不理,结果在回家途中即被她丈夫王拴虎杀害。”〔21〕
当时干部并未积极执行新的婚姻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新的《婚姻法》因为废除的旧式婚姻范围过广,在基层社会遭到广泛的抵制。可以想见,多数农民的婚姻都属于“封建婚姻”,而且如前所述,在婚姻方面的花费对于他们而言是很大的支出,若是村干部轻易批准离婚,肯定会遇到乡村民众的诸多压力和抵制。
另一方面,妇女受新婚姻法的影响,提出离婚主张,导致家庭矛盾进一步激化,可能在家庭中会遭受更为严重的压迫,不少妇女因此选择自杀。比如,“福建省惠安县在婚姻法实施后一年半的时间120多位妇女因不堪家庭的虐待而被逼自杀,妇女陈康约了同样遭受家庭虐待的妇女陈尾娘、陈哭吓等集体投河自杀。所幸被人及时发现只溺死了陈哭吓一人,但陈尾娘仍在1950年9月间上吊自杀。”〔22〕
激进的性别平等法律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法律对妇女的超前道德追求,与社会实际不一致,因此遭到了诸多抵制,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唤起了妇女强烈的性别平等的意识,在妇女强烈的性别平等意识与极为有限的现实选择之间的冲突中,妇女大量趋于自杀。
2.道德制约力的弱化与变动的家庭结构
当代中国与以往相比,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带来了家庭关系结构的变化,但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老人在家庭中逐渐居于弱势,而且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遗弃、不赡养老人的问题。甚至,1980年《婚姻法》2001年修正时特意增订“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23〕而法律中强调对老人群体的保护,恰也说明社会中关于老年人的保护已成社会问题,老年妇女显然也包含其中。由于被遗老、子女不养老或婆媳矛盾等,老人尤其老年女性自杀现象增多。
关于当代中国自杀问题的调查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使我们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基层社会中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引起的自杀案件的严重程度。陈柏峰对湖北六个村落的调查显示出老人自杀现象的严重性,比如,他提到最初当向村民们询问是否存在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村民们的回答居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24〕景军、张杰等学者也提到类似的事实,“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往往与家庭矛盾缠绕在一起,而家庭矛盾的焦点之一即是婆媳关系,家庭矛盾中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例如夫妻间的从属地位以及婆媳关系等。”〔25〕刘燕舞则通过对7省34村的质性访谈而获得的1980年-2009年间604例农民自杀的死亡案例数据分析,质疑景军等学者主张的农村人口迁移引起的自杀率下降的观点,刘认为当前农村的自杀率仍呈显著上升的趋势,青年人自杀率的下降与老年人自杀率的上升并行不悖的存在于当前乡村社会,青年女性自杀率的下降拉低了青年人整体自杀率,但老年人自杀率的上升则拉升了农村的整体自杀率,他认为决定此种面貌的主要因素并非女性迁移,而是代际变动与农村离婚的加速。〔26〕
在当代基层社会,与父母提前分家成为解决家庭问题的普遍方式,家庭主义进一步弱化。阎云翔根据在下岬村的经验,从分家的习俗中讨论家庭政治中道义与经济的关系,在他看来,经济改革使得农村家庭重新作为生产单位的同时也鼓励了个人财产观念的发展,促使年轻人要求提前分家。〔27〕但是,分家之后并不意味着家庭问题就能获得解决。笔者自己关于基层的调查发现,即使分家之后,母家庭与子家庭之间也会存在着诸多联系。一方面,对独立人格价值的强调使得年轻的夫妇更容易分家,在他们看来,自己过日子会比较顺心,经济方面也可以免于纠葛,尤其是多数年轻妇女都表达出自己希望分家单过的想法,在她们看来,平时接触多了总会容易产生矛盾。但另一方面,无论在法律义务、情感纽带还是共同财产等方面又使得与母家庭有各种联系,在二者的拉锯中就容易产生冲突。
代际冲突与老人在现代家庭结构中的弱势地位越来越突出。黄宗智20世纪80年代于华阳桥镇的调查研究中就已经指出家庭结构的变化,“解放前当媳妇的在村内处于最底层,在婆婆的摆布下生活,不少村民说,过去媳妇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做饭,现在这些都由婆婆来做了,年轻妇女不会像以前的媳妇那样容易被摆布。”〔28〕而且老人年纪越大,就越有可能受到已婚的儿子或者儿媳的虐待,阎云翔曾举出了一个案例:“儿媳妇在与老人的一次冲突中,从后面一把抓住公公,将公公的头往家具上撞了好几下,老人头上身上到处都是伤,最后只好将儿子告上法庭,法庭很快判儿子媳妇虐待老人,但正如村里人预言的一样,法庭上的胜利并没有带给老人几天好过的生活,因为还是几个儿子互相推诿或宣布断绝父子关系,老人被安排住在一个破房子里。”〔29〕笔者自己关于基层的访谈也注意到了老人自杀现象。一例是因婆媳之间的争吵,婆婆因而自杀;一例是女儿把母亲的房子卖了却不养老,母亲因而自杀。
此外,尽管法律规定禁止干涉婚姻自由,但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实际干涉婚姻自由的案例并不少见,尤其是对老年人再婚的干涉。阎云翔在下岬村的调查就曾遇到这样的案例,一位64岁的寡妇为了避免儿子不孝顺以致老来无依靠的悲惨命运,决定不顾社会舆论再婚,反对最厉害的就是她的儿子和儿媳,因为他们觉得这非常丢脸,尽管寡妇最终再婚了,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儿子动员亲友强迫她按照旧习俗举行了侮辱性的寡妇再嫁仪式,实际上村里人都知道其实只是为了惩罚这位寡妇,奇怪的是村干部和当地政府根本没有制止虐待老人的行为,哪怕是听到村里人提意见,村干部也是装聋作哑。〔30〕如果反观历史的话,则恰好相反,“1949年之前都是婆婆欺负媳妇,如果媳妇守寡想再嫁,婆婆就会用那些习俗来侮辱她。”〔31〕
与城市民众相比,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主要依赖于子女的赡养,他们也因此更为重视与子女的关系,如果子女不孝顺,带给他们的伤害也会更严重,加上选择受到诸多限制,因此容易趋于选择自杀。
在传统时代,“道德法律化”使得违背道德的行为要面临诸多压力,道德约束有一套相应的保证机制,而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对青年的约束力日益衰弱,道德渐从法律中退出,道德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缺乏外在保证,尤其是由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获得前所未有的合法性,道德的约束功能进一步弱化。这与西方不同,道德从法律中退出后,宗教很大程度上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中国实际的情形是,子女若不孝顺,在实践中也不会遭受到法律上的惩罚,道德约束缺乏外在保证。
可以看到,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家庭关系处于变动中。一方面,传统的孝道在延续着,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家庭情感具有相当的韧性;但另一方面,道德约束力也在日益消弱,老人渐成为弱势群体,在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纠葛中,中国的家庭伦理也随着法律与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3.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与妇女对权利的片面理解
当代中国法律打破了传统社会父权夫权统治、男尊女卑的思想。如宪法规定男女平等、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的原则,使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当代婚姻法律宣示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原则,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前者是婚姻自由的主要内涵,后者是对婚姻自由的重要补充。此原则主要是为破除中国传统社会余留的“婚姻乃父母之命”思想,防止发生“对于离婚者、丧偶者或老年人再婚,子女或家属亦多有阻挠之例。此外还特别重申禁止包办、买卖婚姻或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结婚索取财物,以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32〕
新近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中涉及房产的解释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主义的原则,如“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父母双方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额按份共有,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婚后购房的归属),2011年7月4日通过,自2011年8月13日起执行。
但这并非就意味着传统稳定机制的解体带来的都是幸福生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家庭中的稳定关系反倒因为父权的解体而变得脆弱,“父权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中的权力机构和稳定机制被改变之后,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成为家庭中最核心的关系,伴随着自由爱情的强调,人们也更强调人格的独立性,这样就有可能使诸多本来并不激烈的冲突变得十分敏感,过去维护家庭基本稳定结构的父权制度打破之后,并不是家庭地位的消弱,也没有使今天中国人可以在家庭之外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正相反,家庭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和不可预期。”〔33〕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婚姻亦出现诸多问题。首先是如阎云翔指出的,基层社会的年轻人费尽了心思提高彩礼与陪嫁的数量,目的是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使得结婚费用越来越高,〔34〕甚至已经开始超出了大部分基层家庭的承受程度。
其次,无论城镇还是乡村的离婚率都呈上升趋势,1978年每二十对夫妻中只有一对夫妻离婚而且法庭也能处理其中半数,但30年后的2008年,每五对夫妻中就有一对离婚,法庭处理的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三十。戴慧思(Deborah Davis)将当代的婚姻出现的诸种新变化(婚姻趋于自愿订立的合同关系、婚姻共同财产保护以及两性关系严密监控的弱化,高离婚率、高再婚率以及高结婚率是此“三大转变”的结果)称为“婚姻的私有化”。〔35〕这样的趋势在冲击着既有的关于婚姻的诸多道德观念,二者在交汇过程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婚姻观念。一方面,妇女在婚姻家庭中面对纠纷具有了多种选择性,妇女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意识,但另一方面,婚姻与家庭的不稳定也同样带了诸多问题,比如,对当事人及其子女身心健康的消极影响等。〔36〕
此外,忽略家庭本身的亲密关系,过分追求家庭中的“个人期望”,当未达到时,就容易采取过激的非理性行为,典型事例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中因为家庭关系中的琐事导致的相当数量的自杀案件。吴飞在田野调查中就遇到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例:“一位刚结婚没两年的少妇,和丈夫非常恩爱,几乎从不吵嘴,在她的陪嫁中,有一台录音机。有一天家里失盗,录音机被小偷偷走了。这位少妇当时就在家中,却没有看到小偷进来,她的丈夫知道后,狠狠数落了她一番,责怪她看管不严。她觉得非常委屈,因为丈夫从未这样对待过自己,于是一气之下,喝下一瓶农药死了。”〔37〕
笔者自己关于基层的访谈也注意到因家庭琐事争吵导致的妇女自杀较为明显。比如,一位母亲和女儿争吵,女儿认为母亲在嘲笑自己的长相,选择自杀;另外一个案例是妻子因家庭琐事与丈夫争吵后,妻子选择了自杀。
涂尔干提出“集体情感”以解释家庭中的自杀现象。他认为影响家庭成员自杀倾向的关键在“集体情感”,此种情感的强度取决于共同感受到这种情感的个人意识的数量,而家庭运转的方式随着人口的多少而变化,所以家庭成员的数量影响自杀的倾向,涂尔干的结论是家庭是避免自杀的强大因素,家庭的构成越牢固就越能避免自杀。〔38〕将“集体情感”的强度归为人口数量,则并不能解释传统时代因受家庭压迫自杀的现象,在人口多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出现自杀倾向的程度并不必然就会低。
但是,“集体情感”的解释力,在于突出家庭的稳固性对避免自杀的重要意义。现代法律废除了对妇女的道德压迫,强调妇女权利和家庭成员地位平等,这使得妇女更为看重的是家庭中的“幸福”,正因如此,家庭关系变得不可预期,家庭缺乏稳固性。核心家庭中,妇女处理的是夫妻之间以及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悖论的是,往往越是与亲近的人反倒越容易产生矛盾,这亦可以理解,矛盾总是在接触中产生,而越是亲近意味着接触得多。对于当代社会的妇女来说,令她们在意的是,家庭成员所做所言是否与自己期许的一致,当二者产生冲突时,就容易对家庭的稳固性产生消极影响。
可以看到,与传统时代的法律相比,当代中国法律保护妇女的权利,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地位,妇女在遇到家庭冲突时的选择也具有多样性,比如在“感情破裂”时可以选择离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家庭秩序中的妇女选择自杀,感情往往并未“破裂”,一方面,她们极为重视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另一方面,她们又对权利片面强调,在二者的纠葛中就容易趋于选择自杀。
结 论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形式相对实体、理性相对非理性的方式构建出四种理想类型即形式理性、形式非理性、实体理性、实体非理性,并通过分析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等层面的关系及其与三种政治支配(家族和宗教、宗主父权封建制、现代法律官僚制)和权威类型(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之间的互动,试图证明西方法律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作用并暗示整个社会“理性化”的趋势。他认为形式理性类型法律具有系统性、逻辑一贯性及普适性的特点,因此,只有此类型的法律可以独立于统治者意志及反复无常的环境与情形,而与之伴随的具有形式化、职业化、专门化特征的近代理性官僚制与形式理性法律的统合则对整个社会理性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39〕
在他看来,基于演绎逻辑的“形式理性”理想类型具有两方面的特点, 即通则化和体系化:从最初步的思维运作开始,把决定个案的各种典型理由化约成一个或数个原则即“法命题”;其次将所有透过分析而得的法命题整合,使之成为相互间逻辑清晰而非自相矛盾,尤其是原则上没有漏洞的规则体系,使所有可以想见的事实状况全都合乎逻辑地摄于体系的某一规范之下,以免事实的秩序缺乏法律保障。〔40〕韦伯强调形式主义理性法律,目的在于追求法律的“确定性”,使其外在于宗教、道德伦理、情感意志等因素,不受权力的干涉。
但本文通过以上对妇女自杀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道德法律化还是法律的去道德化都会造成妇女自杀。本文一方面反思与此相关的当代中国大规模的移植形式主义法律的整体趋向,强调道德从法律中退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追求法律形式主义,结合田野调查经验说明此种法律类型同样存在问题,当代中国基层仍是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长期拉锯,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法律构造与现实并非完全契合。*阎云翔称此变化趋向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但实际上情形并非“个体化”所能概括,黄宗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拉锯。参见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而权力和道德完全从法律中退出,家庭秩序中的公正将以何种形式寻求保证成为新的困境;另一方面,也着重批判“道德法律化”的做法,认为这实际上造成了妇女过度的道德压力。因此,本文主张对道德进行具体区分。
首先,根据社会维度,区分“道德的法律实践”的两种类型,即“滞后的道德”与“超前的道德”,实际上,二者都会造成妇女趋于自杀。前者将对妇女的贞节道德要求通过法律的方式确立,具体包含三种机制:法律鼓励妇女贞节道德受到侵犯和怀疑时选择自杀;法律积极保护守节的妇女;法律同时惩罚违犯贞节道德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妇女因选择受限而趋于自杀。后者则追求超前的道德,包括法律对激进性别平等的鼓励;道德从法律退出后,道德失去外在保证,道德约束力的弱化;法律对权利的强调导致实践中妇女对权利的片面理解,“超前的道德”与社会实际也存在诸多冲突,同样造成妇女自杀。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法律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实际调整对民众的道德规定,融合权利与道德。
其次,应该区分“善的道德”与“恶的道德”,并将后者从法律中排除,依据的原则可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黄金准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传统时代的妇女自杀是因为妇女受到法律的道德压迫,比如,妇女在家庭中的结构性不公地位,以及对妇女行为进行的诸多道德限制和约束,而对妇女的道德压迫显然违背了儒家自身所提倡的准则。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道德约束力衰弱后导致老年人的弱势地位、对个人权利的片面理解导致对家庭亲密关系的忽略亦同样违背了这一准则。而实际上此准则对于基层社会民众而言,具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如果别人这样对你,你会怎么样?”另一种是“如果我这样做了,别人会怎么看我?”
最后,中国的妇女自杀多发生在家庭领域中,现代法律应重视处理与这一独特领域的关系。如前所述,对自杀者不惩罚,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应积极从外部帮助民众实现“家庭幸福”。家庭关系的特征在于亲密关系,但它亦存在着不同于公共领域的竞争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去道德化显然都无法重构法与家庭价值的关系,也恰因如此,在实践中也造成了诸多问题。黄宗智已经指出,目前理论资源和意识形态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误区,那就是“于现代主要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伴随现代经济发展,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小农生产将被个体的产业工人所取代,其三代家庭也将会被核心家庭所取代。”但实际上,无论在社会生活方面还是伦理情感方面,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一直在拉锯和纠葛中,“也恰是因为中国的实际与西方的差异,因此亟需建立另一种社会科学”。〔41〕本文着重指出的是,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社会的长期延续的基本单位,忽略这一给定现实会造成诸多问题,而现代法律应重视重构家庭价值,而这亦需要更加艰苦的论证。
〔1〕〔3〕(清)陈培桂.淡水厅志〔Z〕.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清代台湾方志丛刊(第二十八册)〔Z〕.台北远流出版社,2006.389,389.
〔2〕〔美〕卢苇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72.
〔4〕〔5〕〔日〕小竹文夫.清代旌表考〔J〕.人文月刊,1936,3(1).
〔6〕(清)祝庆祺.刑案汇览(第七卷)〔Z〕. 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249.
〔7〕〔8〕〔10〕(清)全士潮,张道源,等.驳案汇编〔Z〕.何勤华等点校.法律出版社,2009.55-56,63-64,686.
〔9〕四川省档案馆.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Z〕.档案出版社,1991.88.
〔11〕〔美〕黄宗智,尤陈俊.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M〕.法律出版社,2009. 前言6;〔美〕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1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C〕.人民出版社,1991.31.
〔13〕〔15〕〔16〕〔17〕〔美〕黄宗智.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与现实〔A〕.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89-290,290,289,292.
〔14〕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
〔18〕李方甜.对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贯彻与实施情况的再探讨〔D〕.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5.
〔19〕商丘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商丘市志〔Z〕.三联书店,1994. 427.
〔20〕许德珩.正确执行婚姻法,消灭封建的婚姻制度〔J〕.新华月报,1951,(5).
〔21〕中国青年报,1953-01-23.
〔22〕福建惠安县第九区怎样宣传婚姻法〔J〕.新华月报,1951,(10).
〔23〕〔32〕王泰铨.中国法律通论(上册)〔M〕.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624,623-624.
〔24〕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六村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4).
〔25〕景军,张杰,等.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5).
〔26〕刘燕舞.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1980-2009)——兼与景军先生等商榷〔J〕.青年研究,2011,(6).
〔27〕〔美〕阎云翔.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1998,(6).
〔28〕〔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中华书局,2000.301-303.
〔29〕〔30〕〔31〕〔34〕〔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 龚晓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90,190-191,191,168.
〔33〕〔37〕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7,45.
〔35〕Deborah S.Davis , Privation of Marriag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odernChina,2014,Vol.40 (6), p.551;Who Gets the House? Renegotiation Property Rights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ModernChina,Vol.36 (5),pp.463-492.
〔36〕李凌江,杨德森.离婚对当事人及子女心身健康的影响与心理干预〔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1,(5).
〔38〕〔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206.
〔39〕〔40〕〔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7-29,28-29.
〔41〕〔美〕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1,(5).
(责任编辑:邝彩云)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编号:16XNH017)。
2016-08-16
赵刘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