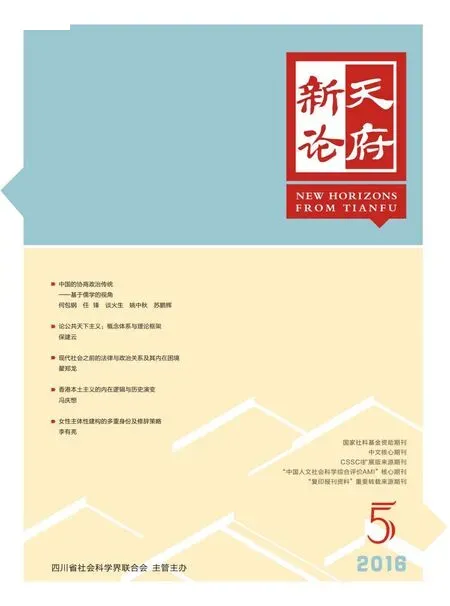倒错:齐泽克的法罪辩证观
陈 剑
倒错:齐泽克的法罪辩证观
陈剑
在齐泽克理论中,常规的法罪辩证观是“倒错”的逻辑,即符号秩序与逾越罪欲的反转关系,齐泽克以圣保罗和巴塔耶笔下的“法罪互生”或“法罪统一”为例论及,律法不仅激生犯罪,其本身就是犯罪。另外,齐泽克所说的法与罪的“辩证反转”或绝对同一恰是超越倒错的途径,接近拉康的实在界伦理学或“独一的新型倒错”。
齐泽克拉康圣保罗倒错超我
“Perversion”这一概念在汉语学界通常被译为“变态”“倒错”“反转”①“反转”这一译名,可见杨慧林教授的相关论文《“反向”的神学与文学研究——齐泽克“神学”的文学读解》、《反向的观念和反转的逻辑:对齐泽克神学的一种解读》等。。它源自拉丁文,最早是一个有军事内涵的概念,然后演化为神学的概念,指涉罪欲和色情。在这一基础上,它又从心理学和性科学中获得了性倒错的内涵。克拉弗特-厄宾(Kraft-Ebing)将性倒错分为两类:一类是性欲对象的倒错,诸如同性恋、恋老癖、恋童癖、恋兽癖、自体性欲;另一类是性欲行为的倒错,诸如施虐狂、受虐狂、恋物癖和暴露狂。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1905年)中继承厄宾的观点,用“sexual aberrations”统称一切反常的性行为,而用“inversion”称呼同性恋等性欲对象的倒错,用“perversion”(德语perversione)表示性欲行为的倒错。而在拉康精神分析学中,它是精神病、性倒错、神经症三大心理结构之一,原指“否认”阉割(disavowal of castration),将自己视为“大他者”(Other,即母他:mOther)的欲望客体,即想象菲勒斯以保存幼年时母性原乐(jouissance)的主体。他陷入渴望融入父法阉割却不能如愿的恶性循环中,只能以变态行径重复原乐和阉割的双向仪式,其表现症状主要是施虐癖、受虐癖、恋物癖。另外,拉康认为,许多正常人,即神经症者也具有与倒错狂相似的症状,他们在性行为和幻象(fantasy)中有强烈的恋物或性虐倾向。②拉康以上观点可参见《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客体关系》(1956)、《康德同萨德》(1962)等。
齐泽克将拉康的“Perversion”嫁接到社会体制中,其文本中的“Perversion/ Pervert”大多指自以为知道“社会大他者”的欲望,甘愿成为其获取快感的客体工具的变态主体和心理,这就延伸向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并在执法过程中享受施虐——受虐快感的规训式傀儡,如法西斯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以历史崇高使命为旨归、完全受制于集团意志和淫秽原乐。简单说,“Perversion”是支撑体制的欲望和享乐,是律法要统治人心必须借助的超我、幻象及其力比多投入,因此,它是法中之罪、体制之过度。在这一角度,人人皆倒错!*通俗说来,倒错是对荷尔德林那句老话的验证:“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正是努力使之变成天堂的那种努力。”然而,齐泽克的倒错不止于直接酿造人间苦海的心理或政治极端,他使用倒错及恋物癖、幻象等相关概念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暗指所有安于现状,屈服、受诱于资本主义的主体都是倒错狂,他们麻痹在五光十色的物质消费和庸常幸福的人际规范中,无视资本主义机器高速运转的危机以及人类自我超越的可能。
在齐泽克的论说中,“Perversion”有两种辩证模式:法罪互生和法罪统一。前者即系统的自反,秩序生产自身的逾越、犯罪和享乐,其生产物又反过来支撑、发展秩序;后者即系统自有的过度,秩序自身就是逾越、犯罪和享乐。
简言之,不仅人们心中隐蔽执着的享乐、欲求总是律法中介和异化的结果,而且为人心掌控的人间诸法总是被其“罪欲之反面”调和、玷污,正如齐泽克所说:
“我们服从于律法并不是‘自然的’、自发的,而总已经被那些(压抑的)触犯律法的欲望所中介。当我们服从律法时,那不过为了与那些触犯它的欲望做斗争而采取的绝望策略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越是严格地遵守律法,也就越是表示在内心深处,我们感受到沉迷于罪欲的压力。”〔1〕“这不仅是禁忌之果的逻辑(律法通过禁止某物而制造对其的欲望),更根本的是,人类对法的坚持已经是罪——是伪装成法,将热情投入法中的罪欲自身。”*Slavoj Žižek and John Milbank, 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 Paradox Or Dialectic? London: The Mit Press, 2011, p.272. 齐泽克据此认为,西方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或穆斯林恐怖分子是“伪装的罪犯”,通过打击别人打击自身的诱惑。他们之所以妒恨他者并深感威胁,是因为他者有罪的生活深深干扰、触动并诱惑着他们(这自然是“无意识没有否定”的例子)。他们远不如佛教、孟诺教派等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后者根本就对他者的邪恶生活漠不关心,甚至心怀慈悲。
可见,齐泽克不仅论说了人们熟知的“禁忌增生逾越”的法罪互生逻辑,而且论述了投入病态力比多(施虐-受虐)的法罪统一逻辑。这两种模式可借圣保罗神学和巴塔耶(George Bataille)的“消费-色情”理论为例。齐泽克开拓了“倒错”这一概念在神学中的内涵,以此探讨法罪辩证及超越倒错之可能。
一、从康德的法罪对立到圣保罗的法罪辩证
法与罪的关系只是简单的对立吗?只有在强大明晰的法律面前,人类才能免于犯罪的诱惑和沉沦吗?就像人们常说的,法律不像宗教修行或崇高理想,它只要求人们遵从行为底线,不去触犯社会禁忌、从事不见天日的勾当。无论人类是否认同它,它严格而强力执行着,惩罚和阻止一切犯罪。
法罪对立的逻辑可参看康德的一个例子。他曾为论证先验道德律的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讲了一个非常实在的事:如果有个好色的人遇到了行淫的大好机会,其自身断不能克制,但倘若在他偷欢情妇的家门口树立一个绞刑架,警告他一旦宣泄完淫欲,明晨便将其绞死,一般人即便色胆包天也定会理智抵挡诱惑。康德意在表明道德律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即使难以做到,但在特殊状态下我们总能自觉并遵守道德或法律。
真如康德所示,主体的内心(内化)律法和外在的法律强制是犯罪的阻止力量吗?在《幻象的瘟疫》(ThePlagueofFantasies)中,齐泽克举了一出学校霸王闹剧中常见的课堂场景:上课之前学生们打着哈欠,仰望天花板,无精打采,直到一个门口张望的学生大叫“老师来了!”一下子所有的学生活跃起来,大吵大闹,互相扔纸团,推搡桌椅,制造噪音。他们故意制造出让老师发火的骚乱,期待看老师如何应对。这骚动远非严酷的学校纪律压迫下的能量爆发或反抗,而是纪律自身促成的力比多享乐。法律不一定禁止了犯罪,也有可能吊起了犯罪的胃口。
以此思路看来,在绞刑架的例子中,康德无视犯罪的心理动机,许多人正是因为有断头的危险才犯险淫乐,一个需要用性命去引诱的女人才激起男人无限的勇气和兴趣,这也是保守禁欲的时代才有轰动激烈的偷情和爱情的原因。在这一角度,法律、禁忌远非犯罪的阻止力量,而是因为有了禁忌我们才能享受逾越的快乐。
法律激发犯罪。换个角度看,犯罪也支撑着法律。社会上无法杜绝的偷情恰是婚姻法实施的保障。法律和逾越是互为条件的,法律的合法性建立在对违法的解决之上。在课堂骚乱的例子中,齐泽克亦表示学生们并非真正反叛,而是为了让老师责备以维持纪律,他将这一逻辑串联于福柯所说的“服务于权力的抵抗”“权力产生制衡又为制衡所界定”的观点,〔2〕以及巴塔耶所说的“为了享有反叛,一个人不得不安置禁令”〔3〕的思想。——此类法和罪反向支撑、生成的观点,笔者称其为“法罪互生”,而齐泽克将其追溯到圣保罗的“法唤醒了罪,罪又确立、强化了法”的辩证观。
保罗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和《加拉太书》中,反复论及法与罪的相互促生关系。在其眼中,律法虽是圣洁的,却始终是和罪、死靠在一边,而与信、义、生隔岸相对。究其原因,乃是律法唤醒我们的负罪感,罪因律法活了,占据了我们的肉体,并反过来支撑着法律的统治,我们内心和肉体的分裂永不会停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哥林多前书 15:56》)“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加拉太书 3:9-12》
齐泽克在《神经质主体》中引述了《罗马书 7:7-18》和《罗马书 3:5-8》这两段阐发圣保罗的法罪辩证观:
“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它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
齐泽克指出,第一段表示倒错是“众生之道”(the way of all flesh),法和罪并非对立,罪并不外于先于律法而存在——屈服于血肉之躯的诱惑,并非简单地无视道德禁忌的律法,放纵地沉溺于现世罪欲的追逐中。先于律法的只能是简单天真、堕落之前的生命。——罪是处于律法中的凡人无法逃脱的宿命,它恰恰由禁止之法所造就:“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众生之道’,是一个罪与法、欲望与禁忌紧紧交织在一起的世界;禁制这个行为本身引起了逾越禁忌的欲望,也就是说,将我们的欲望锁定在被禁止的对象之上”。〔4〕
而在第二段中,“我们可以做恶以成善”这句话定义了何谓倒错。律法需要须借助人的犯罪来成就自身。齐泽克由此追问:神是否是隐蔽的倒错狂(pervert),他是否必须造成我们的堕落才能施以救赎呢?那么,“我们应该继续犯罪,以让恩典充足起来吗?”(《罗马书 6:1》)如若答案是肯定的,那神的救赎就依赖于人的犯罪,唯有我们沉溺于罪中,才可以让神扮演救主的角色。由此想来,律法不仅暗暗滋生犯罪,其自身就属于怂人犯罪的神圣计划。
不过齐泽克强调,圣保罗的问题并不是要认同律法领域不可消解的倒错,也不是单纯遵从律法的统治,消除逾矩的冲动,而是要打破律法和罪欲的恶性循环。“罗马书的这整个部分中,圣保罗所苦思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去避开倒错(perversion)的陷阱,亦即‘律法本身造成了违法,因为律法必须借此来标举自己是律法’的陷阱。……圣保罗念念在兹的,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5〕
因此,齐泽克借助圣保罗并非要发明一种鼓励犯罪的“变态神学”。*齐泽克甚至鼓励读者去批判圣保罗,去详细阅读《罗马书》、《哥多林前书》、《哥多林后书》,做一通拉康式的《神学笔记》,数以百计地批注 “(拉康的)原文如此”与“这个句子前半部分蕴含拉康伦理学的深刻洞见,后半部分全是神学胡扯!”他的要点和圣保罗一样,是要以法罪辩证观超越“遵法净罪”(或可称“以法战肉”)的传统道德训诫,并开拓一条打破法罪辩证、禁制与逾越恶性循环的出路。
首先,他以精神分析理论重述、概括了《罗马书 7:7-18》中的论点:由于律法的介入,主体分裂成两部分:遵从律法的意识部分和渴望逾越律法的无意识部分。逾越律法的并不是作为主体的我,而是非主体化(nonsubjectivized)的罪本身,我无法在那不可遏制的罪的冲动中识别自身,只能感受自我的死亡,丧失了活的动力。“生命”于是属于了逾越法律的罪的冲动,我的生命力、热情、欲望都成为一种外来的自动作用(automatism),坚持它那病态的沉沦。我向善的意志、意愿从此弱小不堪。
接着,齐泽克从两个角度谈论律法与罪欲相生一体的恶性循环:
1、律法开启并维持了罪的领域、挑起了逾越律法的冲动。人的罪欲早已是被律法介入、调停的结果,律法是不被承认的罪的同谋;
2、律法统治的终极后果便是超我(superego)。这不仅是律法激起了非法的、罪恶的欲望,而且律法本身“死”的文字扭曲了我对生命的享受。当我因怀有罪恶的思想而惩罚自己时,我却从中能获得满足。律法让我们感到罪恶而寻得自己那倒错而病态的满足。因此,律法不仅带来倒错,其本身就是倒错。
“在这个倒错的世界中,相较于那些在世俗的乐趣中天真享受的人,那些代表律法发言的禁欲主义者反倒更能获得更强烈的满足——其实就是圣保罗所称的‘众生之道’,对应于‘精神之道’:众生并不对立于律法,众生实际上是由律法引起的过剩、自虐、苦行的病态着迷(见罗马书5:20:‘律法进入后,使过错倍增’)。〔6〕
可见,齐泽克叙说了两种倒错模式,一种是抵御律法的罪欲,一种是和律法统一的虐待欲(这重合于萨德式的施虐狂机制或法西斯主义的超我法则),后一种也是他在《幻象的瘟疫》中阐发的“法罪统一”:律法不仅激发犯罪,其本身(一旦内化为欲望)就是犯罪,是具有病态力比多的“超我法”,它加诸在主体和他者身上,以病态的快感实施统治。这也可见证于卫道士、原教旨派的道德攻击,支撑他们在大他者指令下诛除异己、异端的正是超我快感,即执行意识形态法令的形式快感。
要补充的是,法罪互生和法罪统一是超我的两个(异化)功能。超我作为内心权威操控着主体的欲望和享乐。当超我呈现为“禁令-逾越”的恶性循环时,享乐是由禁令压抑反向生成的,这好比最早的超我(父亲的禁令)通过压抑孩童对母亲的欲望从而形成了主体的欲望幻象,这是法罪互生的逻辑;而在欲望幻象或超我绝对指令的层面,超我同样支配着主体,此时的它无异于大他者,主体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主体自认为是大他者原乐、意志的工具,在满足大他者原乐的同时大肆享乐。享乐是由禁令压抑正向生成的。这是法罪统一的逻辑。
最后,齐泽克指出,圣保罗以“超越律法的爱”瓦解了生命在律法领域的病态享乐,打破了律法及其逾越的困境,并将自己敞开向有爱无罪的永恒生命。而拉康同样以欲望伦理学或死亡驱力实现了这一点。这是“超越倒错”之路。
笔者认为,倘若主体毫无犯罪或病态享乐的可能,他就和内心、外界的法权系统无一点关系了。律法之所以存在,正因为我们的力比多黏着正向或反向地支撑着它。换言之,从人性、俗欲、超我的角度来看,法罪是一体难分的,倒错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圣保罗神学的杰出洞见。
二、齐泽克的法罪统一
在《幻象的瘟疫》中,齐泽克概括了法律与犯罪的四种关系:(一)法与罪直接对立,犯罪对法权造成威胁;(二)罪依赖法而确立,没有法也无所谓罪,犯罪外在地依存于法律;(三)法律内在地产生了违法,违法又反过来促成法权,这是圣保罗发现的法罪互生逻辑;(四)法律或权力为了实现自身控制他者,就必须凭借犯罪。齐泽克试图阐释的是第四种关系。*参见《幻想的瘟疫》,第33页。按黑格尔术语,这四种关系或可视为直观的常识、知性的逻辑、辩证的自我否定和思辨的对立统一。
他指出,这并非是福柯所谓的抵抗对于权力的绝对内在关联,“权力产生抵制,直至对后者失去控制”。而是权力大厦必须“一分为二”,权力要发挥效应就必须依赖“自身奠基性的内在过量”,某种卑劣增补——潜规则。用黑格尔的思辨统一(speculative identity)的术语来说:“权力一直是,也已经(always-already)是自己的违越”〔7〕。因此,法权即犯罪:法罪统一。
齐泽克的意思是,公开的法律总是和阴暗的不成文法、潜规则相伴而生,齐泽克有时也称之为夜间法、超我法。表面上,潜规则总爱与公法唱对台戏,对公法具有绝对的僭越性:一方面对于公法明文禁止的东西它敢于嚣张违犯;另一方面,对于公法允许的东西它敢于严格禁止。齐泽克举例说18世纪晚期普遍人权的宣扬虽表示人人享有人权,但实际执行、未敢公开承认的却是对白人有产者的利益庇护,而将有色人种、妇女、儿童等排斥在外。*同理,我们也可以说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公开宣扬的是自由民主和繁荣富强,其不敢承认的潜规则却是发达国家后殖民时代的开拓发展,如原料和劳动力的廉价掠夺、先进技术的经济战略。法律并不以公法为最高准则,而总偏向潜规则这边。当两者对抗时,潜规则比公法有更高的权威性、强制性和禁忌性。潜规则是公法不愿承认却委身屈服的强大对手。然而,理解潜规则的关键却在于明白其表面上的违越实际上是一种必要。齐泽克敏锐地发现,公法总有虚假含糊不实际或失败的一面,恰恰需要潜规则的补充才能具体执行,或者说才能主体化。潜规则一方面与公法对立,另一方面却是公法所必需的卑劣补充。这就让犯罪和法律有了本体论一致的可能。
齐泽克强调,为超我快感所浸淫的潜规则绝非是法律、权力加诸客体之后的副产物(法罪互生),而是其自身不敢承认的情欲基础,是其“原罪”。公法要作用于主体,正常运转,必然要依靠潜规则。因此,犯罪是法权之必需,法权实施着犯罪。
笔者以一部电影为例,2014年的科幻片《新机械战警》(RoboCop)大胆地设想要彻底地杜绝犯罪,必须依靠一个毫无人性的机械执法系统。改造为机器的警察墨菲正是这一系统的重大尝试。但人类的执法系统岂能是非人性、无私欲的!设计这一系统的OmniCorp公司只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幕后主脑最终沦为最大罪犯。而主角墨菲的人性觉醒更是直接的犯罪:报私仇、爽快施虐和滥用极刑。诚如齐泽克所说,中性的公法一诞生就已被卑劣的潜规则所玷污。〔8〕没有犯罪的执法系统是根本不存在。——人即是罪,法亦是罪。*更有意思的是,在《机械战警3》中,执法者墨菲最终摆脱OCP公司的操控,逆转了自己的警察身份,加入了被压迫的反抗组织。这难道没有指出超越律法及其倒错的途径?那是抹除实证身份的自我回撤(self-withdraw),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要注意的是,齐泽克所说的法权总是一种关乎主体的律法。而对于那些坚持法律和犯罪截然对立的人,我们可以反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你确定你的法律和犯罪没有关系,那你为何让它统治你?”这正如齐泽克借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观点所指出,即便是起草反色情法的赫尔姆斯(Jesse Helms)也在条文中流露着变态性欲望的幻象轮廓,征讨色情的圣战同样有着下流的性欲基础。
三、巴塔耶的法罪互生
在齐泽克的视野中,另一个阐发了圣保罗的法罪辩证观、还大胆支持“禁忌激生逾越欲望”的哲学家是巴塔耶:
“他仍坚持律法及其逾越的辩证法:禁忌激生逾越欲望,这导致他得出了虚弱的反转结论(debilitating perverse conclusion):一个人为了享受反叛,不得不安置禁令……这难道不是被圣保罗在罗马书的有关法罪关系——律法如何激生罪恶,即触犯自身的欲望——的著名段落中进行了充分的辩证拓展?”〔9〕
齐泽克在《视差之见》、《木偶和侏儒》(ThePuppetandtheDwarf)*该书的标题源自齐泽克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开卷典故的反用。本雅明声称唯物主义木偶内藏神学侏儒因而立于棋局的不败之地,齐泽克反其意用之,声称神学木偶需要招募日益退潮的唯物主义侏儒方能百战百胜。要注意的是,齐泽克是站在神学的立场探讨基督教的唯物主义经验,所以可称为唯物主义神学或无神论神学。Slavoj Žižek, The Puppet and the Dwarf, p3。中将巴塔耶称为对“对‘实在界充满激情’(passion for the Real)的哲学家”,这里的实在界应指超我领域由禁制激发的逾越和享乐。巴塔耶充分意识到,那种违反律令的激情本身依赖于律令和禁制,因此,他明确反对性解放、性自由。“我认为,性紊乱是该死的。……我并不是那种把情色禁令当儿戏以求解脱的人,人的潜能依仗于这些禁令,没有它们,人将一无所能。”〔10〕笔者认为,这可视为法罪互生的逻辑。巴塔耶并不是单纯支撑逾越,而是“需要制度,也需要过度”〔11〕。
齐泽克还认为,巴塔耶将同质性(homogeneous)的交换秩序(order of exchanges)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无限消费之秩序(order of limitless expenditure)对立起来,这呼应(echo)了拉康将符号交换秩序与遭遇实在界的创伤性过度(excess)相对立的做法。“异质性现实是强力或打击(force or shock)之现实。”〔12〕这使他接近了拉康的“坚持到底、绝不妥协”的欲望伦理,具有追求不可能实在界体验的勇气,无怪乎他反对资本主义民主,认为民主是“掉光了牙齿的老人的表象世界”。
但无论如何,巴塔耶对过度激情的沉溺不等同于拉康的实在界伦理学,他既痴迷共产主义,也醉心法西斯主义。齐泽克指出,巴塔耶赞成革命却不支持苏联:革命是反抗政府之过度消费(excessive expenditure),但他担忧这种过度消费的革命精神会在新秩序中被遏制,甚至变得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同质性”。以此看来,巴塔耶的逻辑仍属于秩序与逾越反向互生之关系,他只能在法律、禁忌的反叛中确立过度,而无能在新秩序本身中确立过度并将其视为伦理欲望。齐泽克亦得出同样的结论:
“或许,这就是巴塔耶严格说来排在前现代行列的原因。……巴塔耶不能构想的只是康德哲学革命的后果,即绝对过度是律法自身之过度这一事实——律法作为绝对去稳定化的‘异质性’之粉碎力量,干预我们以快乐为本位的生活的‘同质’稳定性。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伦理学讲座中,他……走向了康德有关绝对命令(即道德法)的正确公式,把绝对命令直接等同于纯粹欲望(pure desire)。”〔13〕
在这里,区别于巴塔耶,齐泽克从拉康伦理学中探索出另一种异质性的过度以及律法和过度(罪欲)的同一,道德法等于纯粹欲望。笔者认为,这正是他借基督教神学阐发的“辩证反转”(dialectical reversal):对立面的绝对同一。〔14〕在此,可用安提戈涅式的无条件法令与萨德式的“终极犯罪”*萨德在其作品《茱莉埃特》(Juliette)中,宣称有一种根本、绝对、终极的犯罪,释放大自然的创造力量。他的观念是从蒲柏(Pope)在《伊利亚特》第五卷出版时所作的长篇演讲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是普通的犯罪、自然的死亡,那是“创生和腐败的自然循环的一部分,是自然连续转换的一部分”;另一种却是终极犯罪、绝对死亡,是毁灭大自然固有的循环规律,解救它,创造新的生命形态。之重合为例,两者都为毁灭符号界、开创新时代的死亡驱力所支撑,它们超越了圣保罗所发现的法罪辩证之倒错。但必须注意,这不是超我法则的法罪统一(为了区分两者,本文分别将“identity”译为“同一”和“统一”)。*这两种辩证逻辑的区分或可参考《南华经·齐物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只有离弃对立面的调和(彼是相因),认识和遵从对立面的同一(彼是无偶),才能接近道的枢纽。齐泽克曾在《基督之畸形》(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中将生与死的辩证同一视为“辩证反转”的最高例子,也视为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奥秘。
比较而言,“法罪统一”虽具有实在界不可遏制的激情(比如恐怖主义袭击、施虐-受虐狂),但它仍是符号界对立面相互调停和包含的结果,抹除法罪的差异从而巩固两者;而“法罪同一”源自纯粹的实在界,它中止了对立面的相互调停,绝对的法不再包含俗罪,绝对的罪也不再受制凡法,对立面同一但差异、矛盾、斗争保留,道德法是罪欲的矛盾,终极犯罪是符号法则的矛盾,它们由此升华到另一个圣灵的、本体的层面,一个不可能主体化、符号化的层面,一种绝对的爱和自由意志中,它是奋斗中的激进普遍性,是主体本身,是新秩序之起点,也是不断颠覆符号界的否定力量。
四、法罪互生或统一的原因
倒错或变态的根源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归根结底在于人间的律法是属人之物,它必须一定程度内化、主体化和凡人的爱欲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统治人心。而一旦落入人类这种低劣的血肉之躯中,它也就堕落了。千百年来,法律支撑了地球上无数大小共同体的繁荣发展,人类却无法杜绝分裂、冲突和战乱,更不可能寻找统一秩序营造绝对的和平团结。人间的法律有其天生缺陷,它并非一套永动机或计算机编程般的完美秩序,让每个人心悦诚服,视为理想的家园。在宇宙深处璀璨星空的映照下,人法总是黯然失色。这难道不也是柏拉图要追随本体理念、康德要发明无条件道德法和拉康要从实在界论说神法(摩西十诫)的原因?
正如布鲁斯·芬克(Bruce Fink)说,像康德这样的学者倾向于相信道德法是客观而圣洁的,人类之所以能够理性生活是因为它们是真理和绝对之物。然而,弗洛伊德却认为“任何法律必须借助一定分量的力比多的黏着和融合,才能形成我们的心理现实”〔15〕。如果不计较“性”这个词的狭隘,可以说人的法则本身都是性欲化的,其集中代表是“超我”。
在《自我和本我》中,弗洛伊德论述了儿童的父亲认同(identity)是人生的第一个认同,它是超我的起源,也形成了父法的内化。它包含了父亲与孩子间的敌对、禁忌关系、力量借贷、专制压迫以及孩子的无意识罪恶感,*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的无意识罪恶感导向犯罪,不是犯罪的结果,而是动机,是一种自我(向父亲)证明罪恶的宽慰。其本质是同性性欲(对于男孩)的升华、去性化。这也就释放了性欲的破坏潜力,引出超我归罪的无限攻击:内向攻击譬如“你必须”的自我归罪批评;外向攻击譬如狂躁症。
正如弗洛伊德所教导的那样,超我对于自我的批评并非简单的是将(父亲)法律加诸于自我,而是在斥责自我的无能中感到兴奋刺激,从而享受一种法律的淫荡表达。从享乐的角度,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超我,在《康德同萨德》(KantavecSade)、《再来一次》(Encore)中,他指出超我的本质是大他者的欲望或意志,其命令是“去爽吧!(Enjoy!)”*可参考Jacques Lacan,Encore 1972-1973,eds.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Bruce Fink ,London and New York: W.W.Norton, 1993, p.3:“只有超我才能强制一个人去享乐(jouir),超我是原乐的命令——去爽吧!”他还将超我与萨德的虐待狂机制及康德的道德法相勾连。
芬克指出,*参见Bruce Fink, A Clinical Introduction to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Theory and Techniqu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9.超我最早来自我们父母命令的内化,但它并不仅是父母传达给我们的道德规则的内容存储,同样也是我们在他们教育、训斥、惩罚我们的声音中体会到的某种严厉冷酷。道德法起源于父母的声音,尤其是父亲的声音,在声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父母的欲望。法则的表达是通过一种他者欲望的方式实现的,对孩子下达法律的父亲总是宣布他对事物的欲望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喜欢的孩子要铺床、要洗手。因此,孩童是通过体验大他者的欲望来学习法则的,我们不可能将父母强加给我们的命令和他们传达命令时的声音、语调相分离,同样,在我们也不可能将力比多或原乐和道德法的内容相分离。或许我们可以说:“当大他者(父亲)的法则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他者的欲望也偷偷地潜入。没有欲望和享乐,法则就无法内化。”
根据拉康的《菲勒斯的意义》(TheSignificationofthePhallus)、《主体的颠覆和在弗洛伊德无意识中欲望的辩证法》(TheSubversionoftheSubjectandtheDialecticofDesireintheFreudianUnconscious),我们知道,父亲(或母亲)作为法律的原初代理也就高于法律,总有一部分作为法律的例外(非法)而存在,这一部分也就是大他者之欠缺、大他者之欲望。*这难道不就是最简单的权威高于法律的道理?当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区分了西方法律体系中严格规范(norm)的权力(potestas)和无规范(anomie)的权威(auctoritas),说的难道不是同一回事?父母的欲望在符号界总是缺失的,这一缺失引发了小孩无终止的焦虑,*布鲁斯·芬克曾为说明这种焦虑举过一个妙绝的例子,假若我是一只螳螂,参加一个螳螂舞会,我知道在这个舞会上母螳螂会吃掉公螳螂,并且有一个母螳螂已经靠近我向我表示出强烈的兴趣,但我不清楚我是公还是母,对方的欲望是团结我还是要吃掉我,再也没有比这种被不明不白的大他者欲望钳制更令人焦虑的了,这种焦虑的折磨甚至强过自己即将被吃的那种恐惧。小孩只能从父母的声音或凝视中,抑或借助自身和父母之间某些中介物如母亲的乳房、自己的粪便中去揣测他们的欲望,构建一个法则之外“欲望着的父母形象”,并按父母的欲望来自我塑型、自我欲望。这在拉康的欲望图表中,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能指“S(A/)”和大他者的法则所指“s(A)”及自我理想“I(A)”的关系:主体必须将大他者的欲望“A/”纳入能指系统并以幻象的方式($◇a)内化,同时才能内化譬如穿衣叠被等相互关联的大他者的法则所指“s(A)”,形成主体的法律和自我理想“I(A)”。因此,自我理想总要凭借阴暗压抑的超我才能生成,内心法则的执行总包含了权力的贪淫、超我的施虐和力比多的享乐。
据此看来,主体的法律必然具有齐泽克视野下倒错狂所瞄准青睐的特性,即法律不为任何客观法则本身,而只为了满足大他者的原乐而建立,这种满足同时也是主体的享乐。这好比受虐狂在大他者的发号施令下,在鞭子的抽打下道道红肿又兴奋无比。因此,法律的超我面也可按齐泽克的说法称为意识形态的“倒错内核”。任何法律要执行,要与人发生关系,就必须借助一个力比多化的内化空间,一种渗透了超我快感的潜规则。对于正常人和标准的道德伦常,这样的快感享乐是隐蔽在公法的表层文本之下的,始终与之保持距离,甚至可能造就了禁制-逾越的恶性循环(法罪互生)。然而,对于倒错者或极端的社会体制,由于大他者法则具有鲜明的超我施虐本质,在法律的位置,执法者直接上演大他者的欲望和快感,以大他者的意志代替法律,公开展演隐蔽的幻象结构(法罪统一)。这就和虐待狂萨德如出一辙:主体既是凌辱他人的施虐者,也是作为大他者原乐工具的受虐者。
五、巴塔耶的法罪统一
齐泽克在讨论巴塔耶“法罪互生”的前现代主义思想时,他忽略了巴塔耶的逻辑深层:秩序和色情、占有和消费的统一性。婚姻不仅激发色情,本身就是色情的一种。从”乱伦禁忌”发展而来的婚姻是对族内通婚秩序或自然(动物)规则的反抗。可以说,它是一种“吃腻了碗里的觊觎锅里的”、“一家淫乐不如众家淫乐”的色情或偷情。这一思想见诸《色情史》。
在书中,巴塔耶借列维·斯特劳斯在《亲缘关系的基本结构》中的观点指出,族外通婚的法则,亦即父女兄妹的乱伦禁忌是人类早期的符号交换秩序,但它并不(仅)是狭隘的利益算计(女性经济价值之交易),而是超越算计、否定个人意识、拒绝吝啬、进行排泄的赠礼法则,具有鲜明的节日性质和色情结构。它最初是反自然的激烈革命,是由禁忌所指定的令人垂涎的对象,只是在历史发展中转变成激发逾越色欲的新禁忌。巴塔耶说:
“倘若没有发生放弃近亲的反自然的运动?……一种隐蔽的革命,这种革命的激烈超乎寻常,……无疑,就是这种运动,是妇女交换节日(异族通婚)的根源,……我觉得很难想像,如果一种制约没有涉及到生殖的力量,这种制约,禁忌的制约,能如此强硬地——且处处——推行。”〔16〕
“禁忌就是规则——婚姻是一种违反。……在最初的情形中,近亲对他们的女儿、姐妹、侄女和表姐妹拥有特权。……那些对女人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认可那些对女人没有任何权利的人违反禁忌(如同我们所见,以对等的条件作为回报)。”〔17〕
“通常,我们丝毫不理解婚姻的色情特征,因为,最终,我们在婚姻上看到的不是状态,我们忘记了转化。……状态的合法特征战胜了转化所常见的不规则特征。”〔18〕
婚姻是人类最早的色情禁忌,但同时也是对禁忌的违反,是不规则的色情。巴塔耶将族外通婚制类比于献祭仪式中的谋杀,那是“被规则认可的与规则的决裂”的悖论式统一。当近亲们放弃乱伦欲望,将“使用这些妇女的权利被赋予、转让给通过互赠惯常的礼物与一个小圈子相连的男人”,这种消费相当于“供奉物的毁灭、破坏、燃烧”,那是“违反的最惊人形式”,它违反了世俗秩序的功利性交换法则。——在这种论说中,婚姻法不仅是激发婚外情的禁制,而且也是充溢逾越享乐的放纵过度(让我们想想封建夫权)。如作者所说“违反的权力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在所涉权利之外的规则的存在”〔19〕,法与罪达成了思辨统一,敞露了其中的超我属性,亦即齐泽克所谓的潜规则,因此是法罪统一的逻辑。
色情推翻了规则又形成新的规则并以快感实施统治,这是法罪互生或法罪统一的反转圈套。它被巴塔耶称为“色情变迁的历史”、暂时性规则的“永不休止的颠覆”。
那么,这是否是人类的永恒宿命?欲望解放是否注定依赖于秩序禁锢,爱情是否注定源自压迫和禁忌,抑或新秩序的建立注定要沉溺于罪欲的享乐中?这如同拉康在伦理学讲座中感叹,自然主义的理念注定失败,欲望只有在挑衅上帝时才能熠熠生辉,人们再也不能获得萨德、米拉波(Mirabeau)和狄德罗笔下那种空前绝后的激情,挑衅者早已在倾尽全力的颓唐中断了出路。
幸运的是,拉康开设伦理学讲座就是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他阐述康德同萨德之关系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有一种纯粹欲望、道德法则、死亡驱力、女性原乐位于法罪的倒错领域之外,它是最本真的爱欲,是人类和属天之物(实在界)发生感应、联系的唯一通道。他在讲座的绪论中称其为“独一的新型倒错”(a single new perversion)。
〔1〕Slavoj Žižek,TheFragileAbsolute-or,WhyIstheChristianLegacyWorthFightingFo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0),142.
〔2〕〔9〕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塘,叶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7,33.
〔3〕Slavoj Žižek,ThePuppetandtheDwarf:thePerverseCoreofChristianity(London: The Mit Press, 2004), 56.
〔4〕〔5〕〔6〕斯拉维·纪杰克.神经质主体〔M〕.万毓泽译.台北:桂冠出版社,2004.205,206,210.
〔7〕〔8〕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塘,叶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3,13.
〔10〕〔11〕George Bataille,OeuvresCompletes(Paris: Gallimard, 1971-1988), vol.3, 512,vol.12,296.
〔12〕George Bataille,VisionofExcess(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4.
〔13〕Slavoj Žižek,TheParallaxView,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6, paperback edition, 2009), 95.
〔14〕Slavoj Žižek,TheMonstrosityofChrist:ParadoxOrDialectic?, 43, 252-253, 291.
〔15〕Bruce Fink,AClinicalIntroductiontoLacanianPsychoanalysis:TheoryandTechnique(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8.
〔16〕〔17〕〔18〕〔19〕乔治·巴塔耶.色情史〔M〕.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3.35,104-105,106,105.
(责任编辑:谢莲碧)
2016-06-14
陈剑,博士,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西方文论及西方哲学。广东湛江524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