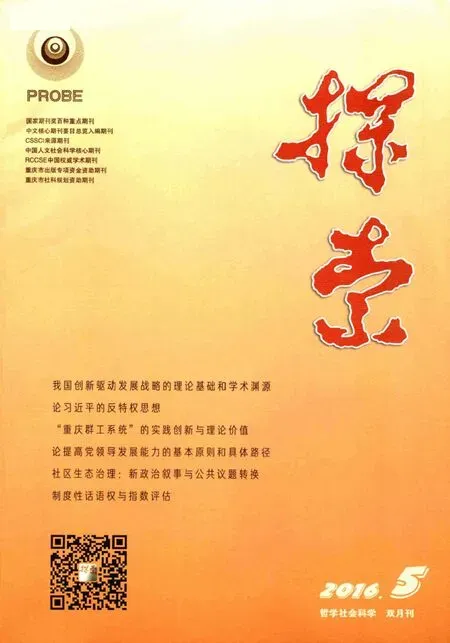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协商民主路径研究
钱再见
(南京师范大学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23)
所谓公共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由政府行政官员及相关公共部门掌握并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目标、增进公共利益的强制力。从本源上讲,公共权力是全体公民共同所有的权力,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共权力不可能由全体公民来共同行使,而只能由其代表(或被委托人)来代为行使。为此,人们必然关注公共权力的实际行使和运行情况:公共权力是如何行使的,公共权力的行使是否致力于实现公共目标和增进公共利益,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行过程何以公开、透明,等等。在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诸多方案和路径中,协商民主是其中的一种民主化和制度化的路径。在协商民主体制下,通过有序化的公民参与、制度化的信息公开和常态化的公共讨论,实现协商主体交往权力的包容性、信息权力的共享性和话语权力的平等性,从而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
1 协商民主条件下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内涵
从根本上说,民主就是指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掌握在人民手中,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依法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监督公共权力行使和运行的过程与结果。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曾解释:“民主就是公民对领袖或政策的一种有效的、正式的控制:‘有效的'是指排除那种例行公事式的参与形式;‘正式的'是指排除将叛乱作为一种控制手段。”[1]98确实,民主作为对公共权力的有效控制手段,就在于其是一种制度化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公民参与,是一种有序的而不是无序的公民参与。人民行使民主权力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人民通过常态化的公开讨论以达成共识来行使权力的方式,就是协商民主。具体而言,协商民主是指人民通过广泛参与、信息共享和公开讨论的途径行使权力并达成共识的公共决策方式[2]、公共组织形态[3]3和公共治理形式。美国学者艾丽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认为,协商民主包括四个要素:一是“包容性”,所有受到影响的公民都应当被包括在决策过程中;二是“政治平等性”,所有受到影响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利益;三是“合理性”,参与者要有开放的胸怀和认真倾听的态度,愿意在深思熟虑后改变个人不合理的偏好;四是“公开性”,参与者应当公开说明自己的利益和偏好[4]22-24。协商民主的这些要素和特质可以有效改变公共权力运行方式,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相较于选举民主而言,协商民主具有很多优势,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公共权力运行模式,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机会,使社会政治生活变得更加健全和健康。协商民主条件下公共权力运行有很多新的特点,同时也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1.1 协商主体交往权力的包容性
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只有在相互交往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汉娜·阿伦特在“行动理论”中认为,任何权力都是人们交往行动的结果,也是政治生活的本质体现,而行动是在公共领域中展开的。她认为:“行动,是唯一无需物或物质作为媒介而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它对应于人的复杂性境况,即对应于这样一个事实,是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并居于世界之中。尽管人的境况的一切方面都以某种方式与政治相关,但这一复多性尤其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条件——不仅是先决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5]7人们的权力只有在交往行动中才能产生、实现和保有。在阿伦特看来,“当且仅当人们为了行动的目的而组织起来,权力就出现了;而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当人们互相疏离和抛弃的时候,它就会消失”[6]174。在福柯看来,权力就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关系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7]29。在开放式的、未发生畸变的公共领域中,人们不仅能够相互看见和听见,而且能够在言谈中阐释和展现自己,在交往、沟通和商谈中劝说他人。按照哈贝马斯对于民主法治国的构想,狭义的政治权力如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等应该是从交往权力转化而来的结果。具体来说,政治权力源自公民交往所产生的交往权力,而行政权力则是由交往权力通过法律媒介转化而来的。哈贝马斯指出:“非正式的公共性意见形成产生的是‘影响',通过政治选举途径,影响转化为‘交往性权力',而通过立法,交往性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8]协商民主理论认为,由于政治过程的复杂性,间接的代议民主与简单多数原则实际上是在替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作决策,难以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只有通过自由、平等、公开而理性的对话、辩论、商谈、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才能赋予立法和公共决策以合法性。协商的基础是协商主体交往权力的包容性、理性化和公开化,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是,立法和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必须来自于公民公共的、开放的、包容的、自由而平等的交往、沟通和讨论。
1.2 协商主体信息权力的共享性
所谓信息权力是指基于对别人所需信息的控制而实现对其施加影响力并使其服从的一种能力和控制力。1959年,约翰·R.P.弗伦奇(John R.P.French)和伯特伦·H.雷文(Bertram H.Raven)提出了法定权力、奖赏权力、专家权力、参照性权力及惩罚权力等五种权力类型的模型。在后续研究中,雷文进一步讨论了专家权力和信息权力之间的差异,并认为拥有信息权力的人没有严格要求“看起来比较专业”,但他们必须具备说服能力和影响力,能够导致目标对象的认知改变和接受信息影响的结果[9]。其实,我们在信息化和民主化的背景下分析协商主体的信息权力时必须明确的是,公民知情权是目的,信息公开是关键。弗朗西斯·E.洛尔克(Frances E.Rourke)指出:“政府过程公开并接受公众的批评和监督的原则,是民主不证自明的公理。”[10]公民知情权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根本要求,其实质是对政治权力和公共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监督,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在艾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等协商论者看来,公开是协商的核心。这是因为,只有在协商过程切切实实地公开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民主的责任。在理想型的协商模式下,公民之间是相互负责的,而协商的公开性则要求协商过程的参与者负有说明其提出某项立法或政策动议的道德合理性的责任与义务[11]3-7。协商民主具有突出的公开性特征:首先,协商过程是公开透明的,与协商相关的公共信息是可以公开获取的,整个协商程序是公众所知晓的;其次,协商参与者在交往、讨论和对话过程中必须公开自己支持某项立法或政策的理由与偏好;再次,协商主体各方的立法或政策建议也都是公开的,公众能够清晰获知一项立法或政策的具体形成过程。协商主体信息权力的公开性强化了人人都有知晓、参与并评判立法和政策的平等权利,同时,这种信息权力的公开性还具有阻止公共权力暗箱操作的功能,因为协商过程的参与者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公开自己的主张、理由和动机以影响他人的态度,寻求公众的支持。
1.3 协商主体话语权力的平等性
话语权力的平等性是协商民主的基本要素和基础性条件之一。菲利普·N.佩蒂特(Philip Noel Pettit)指出,任何民主的做事方式,都应该是包容性的、理性判断的和对话的……它必须是开放的,是指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必须是非强制性的,是指人们不必担心说出自己的想法;它必须近似于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理想的言论条件[12]。也就是说,只有在平等、公开的基础上,民主商谈和理性讨论才有空间和可能。梅维·A.库克(Maeve A.Cooke)则直截了当地说道:“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3]其实,话语本身也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在福柯看来,话语绝对不是透明的,也不是绝对中性的,话语即权力。话语里面关乎权力和欲望,话语实际上是某些强制力量得以膨胀扩张的良好场所。话语里面不仅隐藏了不平等关系和权力的运作方式,而且也暗含了欲望的语言。“在要言说这‘真实'话语的意志中,如果牵涉的不是欲望和权力,又能是什么?”[14]7权力与欲望都借助话语实现自身的存在和诉求,同时又必须在通往目的和目标的过程中依靠话语奇妙地掩盖自身的真实存在。在协商民主中,我们首先需要承认话语权力的客观存在,同时必须明确协商过程中的话语权力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基于平等参与者之间的理性与公开的讨论,并且使理性超越权力的私欲性和自利性,才能实现合法决策的目标。卡罗琳·M.亨德里克斯(Carolyn M.Hendriks)认为:“协商民主更像是公共论坛而不是竞争性的市场,其中,政治讨论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审慎的公共讨论的结果。正是通过追求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选项,并作出合法化的决策。”[15]协商民主中的话语权力运行的场域和空间之所以具有公开性的特质,还因为“一般而言,听众的效用在于以理性的话语取代利益的话语,以热情的动机代替无动于衷的动机。公众的在场使得协商代表很难表现出自己是纯粹受个人利益驱动的……公开性不能排除低劣的动机,但是可以迫使或诱使言说者们将其隐藏起来”[16]111。早在19世纪,密尔就提倡“讨论的政体”,并且认为公开的协商讨论可以纠正错误的判断。确实,话语权力的公开化和平等性以及公共协商过程的开放性能够限制和约束公共权力的扩张性,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和规范化,从而提高公共决策的质量并且充实民主。克里斯蒂安·胡诺尔德(Christian Hunold)认为,“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17]。协商民主促进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基础就在于其通过协商过程以民主的方式约束公共权力的扩张性,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约翰·S.德雷泽克(John S.Dryzek)指出,对协商民主而言,政治决策的合法性依赖于受到该决策影响的那部分人参与协商决策内容的权利与能力。这些受影响的人不仅仅只是去投票、去表决,或去登记其偏好[18]。诚然,协商民主不一定非得抛弃偏好聚合及表决方式不可,但其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通过协商过程中包容性的交往权力、共享性的信息权力和平等性的话语权力提升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促成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
2 协商民主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现实限度
基于协商民主的权力生成机缘、权力构成机理及其权力运行逻辑,我们认为,协商民主具有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基本功能。然而,协商民主在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方面也是有现实限度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协商民主运作过程中协商主体中存在着交往权力的边缘化、信息权力的垄断化、话语权力的精英化的倾向。
2.1 交往权力的边缘化
权力制衡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民主的制度性保障。在协商民主条件下,交往权力能够有效规制行政权力吗?哈贝马斯说:“从权力的视角出发……行政部门把控选民公众集体的行为,为执行机构和立法机构预编制纲领,把司法部门功能化,从而行政部门本身就成了一种自我编制纲领的机构。”[19]482西方协商民主论者主张最大范围的包容,即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公民都应当包括到协商过程之中,但是实际上由于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所拥有的权力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而生成于社会中的交往权力则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处于边缘地带的交往权力往往很难有效规制作为政治权力中心的行政权力。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精辟地阐述道:资本通过对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即民主共和制的掌握,可以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20]120。难以撼动的行政权力往往是在政治权力中心地带自我运行,或者至多是内部博弈。正如哈贝马斯所看到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权力的中心脱离了权力的边缘而自我编程、自我运行[21]。社会中交往权力的边缘化必然导致行政权力的扩张性、自利性和非理性。尽管艾丽斯·杨认为,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它致力于使理性凌驾于权力之上,但是她同时也承认,社会具有的自发性、去中心化等特征恰恰不利于社会成员积极组织起来进行合作。“事实上,社会的许多活动可能会加剧和恶化诸如不平等、边缘化、妨碍各种可行性能力的发展的问题。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各种具有更多物质资源和组织资源的人和群体更容易借助其社团活动来维持甚至扩大他们的社会优势。”[4]186交往权力的边缘化还会不断弱化协商主体的协商能力,甚至弱化其协商意愿。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社会公共领域中交往权力弱化的现象。虽然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承诺通过协商的平台,以协商的方法,公平、公正、公开地解决社会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普通百姓却往往并不具备足够的意识、能力和办法借助这些协商平台进行有效的协商。一些公共问题常常无法透过现有的协商平台和管道得到有效的解决,久而久之,就会影响人们对于公共协商的信心。
2.2 信息权力的垄断化
按照自然法理论,权利是权力的来源与基础。民主政治的理想就是要使政治权力服从于人民的权利,并使人民的权利有效地制约政治权力。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信息权利是原发的,而信息权力是派生于它的一种控制力。斯蒂格利茨认为,民主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要求参与者必须获知充分的相关信息,而保密则减少了公众可获得信息的质与量,使公众参与陷入步履蹒跚的困境……问题就在于许多情况下,政府官员掌握的信息是即时性的最为重要的核心信息[22]。共享性的信息权力意味着公共信息资源公开的制度化、法治化以及获取信息资源的平等性。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过度的公开必然损害在协商过程中进行思想的真实交流,比如戴维·斯塔萨维格(David Stasavage)发现:当参与协商的代表公开决策时,他们面临着利用其行动向选民暗示忠诚的激励,潜意识里会忽略关于不同政策真实价值的个人信息。这一点如果被预先估计到,那么即使是公开辩论,人们也不会改变其原初的政策偏好;相反,当协商代表们私下决策时,他们更愿意利用个人的信息去思考能够更好解决问题的政策[23]。这就是说,协商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和立场不同都会影响到协商的过程和结果。目前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公众参与协商过程以及信息公开的具体程序或方式,即使有一些法规性的规定,其可操作性也并不是很强。现实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公共协商仍然处于无序状态,甚至流于形式,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陷入了“想协商就协商,没意愿就不协商”“有时间可多协商,没时间就少协商”的困境。
2.3 话语权力的精英化
众所周知,协商实际上就是一个话语过程。迪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认为:“实际上,沉默的民主几乎是不存在的。民主通常是一项话语事业……协商民主得益于一种科学讨论式的争论。就像默顿、波普以及其他许多人已经指出的,科学和民主共有或者是获益于许多类似的优点,如试验性。无论是科学还是民主都通过公开辩论而获得合法性。”[24]19协商民主不仅是基于包容性的参与、共享性的信息,而且也是建立在平等协商、理性商谈和公开辩论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正如艾丽斯·杨在讨论激进分子对协商民主的挑战时所说的:结构性的不平等是造成严重不公平或社会危害的基础因素,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官员们没有动机与他们坐在一起协商[25]。实际上,即使他们能够坐下来一起协商,也会由于话语霸权的存在而无法实现平等协商。所谓“话语霸权”,就是强势群体特别是权力精英在表达特定观点时,以居高临下的官僚姿态、说一不二的官腔官调、绝对权威的官方结论,强行向其他协商主体灌输某种思想、观点或主张。协商论者倾向于认为,只要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悬置起来,就能够确保对话者之间的平等。然而,这种观点未能注意到,妨碍人们成为平等对话者的社会权力不仅仅源于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和政治上的支配关系,而且还源于人们对自己是否有权发言的内在感觉和主观判断。交往民主理论关注社会差异以及权力对言谈本身的渗透方式,即常常表现为以“话语霸权”的方式压制或贬低某些人的言论,从而形成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公共协商似乎只能是属于精英的,而不是一般大众的。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目前的协商同样也主要是一种精英式与咨询式的协商,更多地具有政策咨询的特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条件限制,相当多的社会成员还不完全熟悉民主协商的程序和规则,不完全掌握民主协商的手段,不完全拥有民主协商的相关信息,也不完全具备民主协商的必备技能。所以,话语权力的精英化也就是目前这种历史阶段性的必然。
3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协商民主路径选择
一些西方学者提出,如果中国能够逐步建立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具有各种形式社团的社会和允许个人根据其基本权利诉诸正义的司法制度,那么对于具有庞大政治体系的中国民主化而言,协商民主将是一种可行的模式。实际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和独特优势。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说到底就是要通过协商的途径规制公共权力,使其运行过程更加规范化、公开化。
3.1 扩大公民参与,以交往权力规范公共权力运行方式
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公共权力具有相关性、依附性等特点,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域中,公共权力作为实施公共管理和民主治理的基础,具有强制性的基本特质,但是民主体制中的强制不能同“暴力”相联系。协商论者简·J.曼斯布里奇(Jane J.Mansbridge)认为,在任何运作良好的民主体制中,“在利用强制的时候,民主必须找到其自身所需要的对抗强制的方法”[26]46,协商就是一种对抗强制性权力的方法。当然,规范和制约公共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必须通过始终在场的交往权力才能实现。在协商民主理论中,协商主体已经从政治精英扩展到广大公民,不仅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人都应该参与到协商过程中,而且他们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去公开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以及他们对所关注问题的意见,并拥有同等有效机会相互询问以及回应不同的主张与论证。在理想的协商中,“参与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平等的……旨在达成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共识”[27]178。通过理性的协商民主途径,交往权力以“理性说服的民主潜能”打破公共权力垄断,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当然,公民要想有效地参与公共协商与理性对话,许多“自主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如理解力、想象力、评估力、欲求力、讲述力,以及对修辞和辩论的运用能力,等等。在协商民主论者看来,通过志愿团体、基层组织、协商小组以及网络论坛等形式,公民具有了切实可行的公共参与方式。诚然,依法选举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要通过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将公众参与的主体从社会精英扩大为广大公民,从而拓展协商民主的基础,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实现对间接民主的超越和完善。过去我国的民主协商主要是执政党、参政党和党外各界之间的协商和通过人民政协渠道进行的政治协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主要任务作出部署,拓宽五个协商渠道。2015年2月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更是对拓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七个方面的协商渠道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同时,协商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了,包括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多种形式。在此基础上,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民主协商氛围,从而在公共治理和公共决策的各个环节中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
3.2 推进信息公开,以信息权力防止公共权力暗箱操作
公民的信息获取权利是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的法理基础,马克·波文斯(Mark Bovens)甚至认为它是与马歇尔(T.H.Marshall)所讲的公民权、政治权、社会权同等重要的第四种权利[28]。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的封闭性和信息权力的垄断化其实是政府行政权对公民信息获取权和民主监督权的漠视,是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障碍。要实现从公民知情权利到信息权力的过渡,关键是要切实推行信息公开制度,以信息权力防止公共权力暗箱操作。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是以对公共事务的知情为前提和基础的,如果不能获取政府的信息,人民就无法选择、参与和监督政府。只有在拥有知情权的基础上,人民才能实现对政府职责的真正监督,才能防止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从本质上看,协商民主的公开性特征应该是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协商过程的。在协商之前,协商的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必须是公开的;在协商过程中,协商的程序和形式也必须是公开的;在协商之后,作为协商的结果也必须面向公民和社会公开。在立法和决策时,协商民主鼓励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公共协商,公开自己的偏好和理由,同时也尊重他人的意见,尊重他人的种种利益关切。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法治的基本理念就是一切公共权力都要受到监督;从治理的法治特征来看,法治发展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对公共权力有效监督和控制的过程。民众只有通过对公共事务的了解、参与和讨论,才能全面获取政府运作过程各方面的信息,才能对政府行为作出正确的评判,人民才可以选择和监督政府,才能有效行使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力,也才能有真正的协商民主。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必须基于信息公开制度的逐步落实,坚持“以信息公开为原则,以信息不公开为例外”的准则。只有在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的基础上,公众信息权力和权利的获得与分享才有可能,进而以信息权力防止公共权力暗箱操作,促进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
3.3 借力公开讨论,以话语权力消解公共权力话语霸权
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协商民主不仅是指公民的参与权、选举权和知情权,而且包括公民在协商过程中平等的话语权。实际上,协商民主就是一种以讨论为基础的民主理想。同包容性的交往权、共享性的信息权一样,平等性的话语权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特质,也是通过公民参与、民主治理和公共问责等途径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政治讨论不能等同于权力,它却能传播着、产生着权力。当然,讨论需要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并且能够辨认、区分公共利益和其他各种利益的关系。戴维·米勒(David Miller)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29]201这种决策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先前的利益和观点,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在思考各方观点之后作出的判断,以及应该用来解决分歧的原则和程序。这种公开讨论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在私人信息分布不对称的背景下,它在集中这些信息方面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开讨论与自由交往及信息共享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公共权力的制约力量。公共领域中公众的公开讨论可以形成公共舆论,其对公共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作用正是协商民主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重要路径。在民主协商过程中,公民及其代表在作出集体决定之前,必须通过公共讨论来检验他们的利益和理性,证明其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协商民主将理性参与、信息共享、公开讨论和平等话语看作是政治民主化的核心,致力于实现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讨论和协商以达成和增进共识,而增进共识则是以协商沟通为前提的,以知情权和参与权为基础的。没有理性化的公民参与、制度化的信息公开和常态化的公开讨论,共识就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那样的话,以协商民主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也就难以实现。
4 结论
协商民主作为人民通过有序化公民参与、制度化信息公开和常态化公共讨论的途径行使权力,进而达成共识的公共决策方式、公共组织形态和公共治理模式,是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重要路径。与传统民主理论不同的是,协商民主强调法律和政策合法性的来源是真正的协商与审议,而不是单纯的投票。协商民主条件下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主要是指协商主体交往权力的包容性、协商主体信息权力的共享性、协商主体话语权力的平等性。推进协商民主,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需要扩大公民参与,以交往权力规范公共权力运行方式;推进信息公开,以信息权力防止公共权力暗箱操作;借力公共讨论,以话语权力消解公共权力话语霸权。
参考文献:
[1]ELSTER J.Deliberative Democrac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2]MANIN B.On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Deliberation[J].Political Theory,1987(3):338-368.
[3]GUTMANN A,DENNIS T.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4]YOUNG M.Inclusion and Democrac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5]ARENDT H.The Human Conditi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6]ARENDT H.On Revolution[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5.
[7]FOUCAULT M.“Society Must Be Defended”: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5-76[M].New York:Picador,2003.
[8]HABERMAS J.Three Normative Models of Democracy[J].Constellation.1994(1):1-10.
[9]RAVEN H.A power Interaction Model on Interpersonal Influence:French and Raven Thirty Years Later[J].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1992(2):217-244.
[10]ROURKE E.Administrative Secrecy:A Congressional Dilemma[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0(3):684-694.
[11]GUTMANN A,THOMPSON D.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12]PETTIT P.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Discursive Dilemma[J].Noûs,2001(1):268-299.
[13]MAEVE C.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J].Political Studies,2000(5):947-969.
[14]福柯.话语的秩序[G]∥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5]HENDRIKS M.The Ambiguous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C],Refere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Jubilee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October 2002.
[16]JON E.Deliberative Democrac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7]CHRISTIAN C.Pluralism and Democracy:Toward a Deliberative Theory of 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J].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2001(2):151-167.
[18]JOHN D,王大林.不同领域的协商民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32-40.
[19]HABERMAS J.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M].Cambridge:MIT Press,1996.
[20]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王晓升.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哈贝马斯对于民主国家中的权力结构的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6-11.
[22]STIGLITZ E.On Liberty,the Right to Know,and Public Discourse: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in Public Life[A].Oxford Amnesty Lecture,January 27,1999.
[23]STASAVAGE D.Polarization and Publicity:Rethinking the Benefit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J].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07(1):59-72.
[24]GAMBETTA D.Deliberative Democrac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25]YOUNG M.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J].Political Theory,2001(5):670-690.
[26]MANSBRIDGE J.Democracy and Differenc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27]谈火生.审议民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8]BOVENS M.Information Rights:Citizenship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2002(3):324-355.
[29]MILLER L.“I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Unfair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Democracy as Public Deliberation:New Perspectives[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