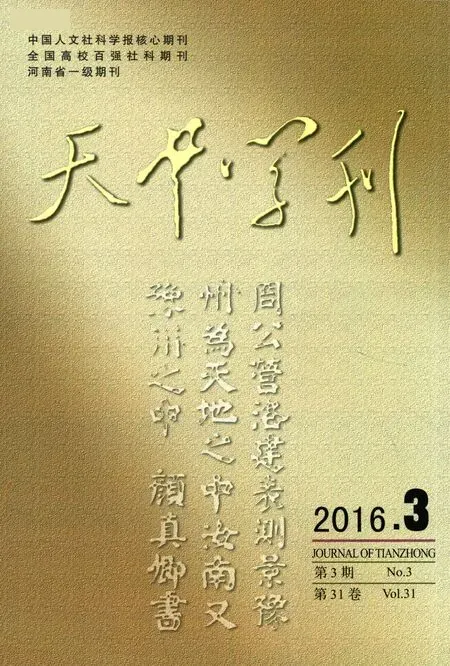谈晚清新小说的趣味叙事
管冠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谈晚清新小说的趣味叙事
管冠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晚清新小说在其文学地位得到绝大提高的同时发展出了一套趣味叙事。这与晚清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及读者意识、小说的开放性和报刊业的繁荣有很大关系。趣味叙事包括游评的故事模式和审丑的喜剧叙事,选择人们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物进行命名以及评点都可以增加新小说的趣味感。晚清趣味叙事呈现了新的叙事风貌,促进了短篇小说的繁荣。五四时期,主义代替了趣味,完成了一次文学话语的大转型。但是,趣味叙事仍然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新小说;趣味叙事;叙事模式;晚清
一、新小说追求趣味叙事蔚成风气
谈晚清新小说,莫有不谈《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者。如果我们把它与钟嵘《〈诗品〉序》的两篇文献——一篇提倡五言新诗,一篇为新小说鼓呼一一对读,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并感叹大家之心思神想能超越时空而相通契合:(1) 钟嵘与梁启超各推崇诗与小说的功用,无以复加。钟嵘认为,“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而梁启超则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上中下三界都难逃文学法网。(2) 钟嵘倡五言诗,因为它“会于流俗”且能“感荡心灵”,“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梁启超亦认为小说会于流俗之外,能“导人游于他境界”,并深具情感力量,“感人之深,莫此为甚”。(3) 钟嵘标举“滋味”,而梁启超则发扬“趣味”。虽然此文并未明确提出,但他把小说的性质喻为“空气”和“菽粟”,已隐含“味”意。梁启超在把新小说外用功能提高到关乎国运兴衰的同时,又发扬了一种趣味叙事。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里,他自认此作“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实乃谦辞。因为在《新小说》第七号的《小说丛话》中,他认为“谈话体之文学尚矣。此体今二三百年来日益发达,即最干燥之考据学金石学,往往用此体出之,趣味转增焉”[1]81。专欲发表政见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是一部以谈话出议论的小说。小说中的孔老先生说:“横滨新小说报社主人要将我这讲义充他的篇幅,再三谆嘱演成小说体裁,我若将这书做成龙门《史记》涑水《通鉴》一般,岂不令看小说报的人恹恹欲睡,不能终卷吗?满堂听众拍掌大笑。”[2]梁启超具有明确的追求趣味叙事的意识,其游评的故事模式为其他新小说家普遍采用。
或许是任公一呼,从者云集;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新小说家们谈“趣味”蔚为风气,在趣味中展开叙事,在叙事中追求趣味。打开当时的文学刊物,翻开当时的小说,于眉批、回批、总批之中,于《小说丛话》《说小说》《评林》《小说小话》等论说性栏目之中,于各种叙言、弁言、后记之中,我们会不断与“趣味”及其多样的表述见面。限于篇幅,本文仅提供几个例证而已。《小说林》是晚清具有纯文学意识的刊物,主编徐念慈视“事迹繁,格局变”为中国小说特有的“兴味”。被称为“小说界巨子”的吴趼人“向以滑稽自喜”,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趣味”:“小说家言,兴味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3]86以他为主撰述的《月月小说》成为“趣味”的大本营。在《评林》所展示的同人报刊的贺词中,几乎都有“趣味深厚”“趣味深长”的论语。当时更热闹的翻译界也是“趣味”横生。周桂笙的《知新室新译丛》乃摘译泰西“小品之有味者而拉杂成书:《顽童》写顽童之调皮,《鱼溺》写鱼被训为陆地动物,一日入水竟至溺死,可发一噱。周自称“仅仅为翻译界小说家之一马前卒”,林纾则就是老帅了,他在《〈冰雪因缘〉序》中说道:“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得,法文之高者曰仲马,吾则皆译之矣,然司氏之文绵褫,仲氏之文疏阔,读后无复余味。独迭更司先生临文如善奕之著子,闲闲一置,殆千旋万绕,一至旧著之地,则此著实先敌人,盖以未脱胎之前已伏线矣。”[4]374林纾大概对这个比喻非常欣赏,在《块肉余生述序》中再次使用。其时,侦探小说最流行,亦因它最得趣味。《上海侦探案》的作者承认“外国的侦探小说,差不多十分之九是从理想上来的,所以布置得整整齐齐……作得很有意味,足令读者惊心怵目,称奇道怪”[5]。
以上种种足以说明以叙事见趣味乃是新小说家自觉的艺术追求。所谓趣味叙事,即指叙事既要引人入胜,又要提供某些东西长人见识、开人心智,使人受到教育,以达到改良社会文明进化的目的。趣味叙事讲求故事性与通俗性,适应民众的审美口味与接受能力,多认同与发扬民间传统的文化思想。民初,苏曼殊与徐枕亚的写情小说既迎合读者的趣味,情感起落缠绵,浓得化不开,却又呈现文人化的形态。因此,本文不把它作为论述的主要对象,只在适当时候提及。
二、新小说追求趣味叙事的三个原因
新小说家们对趣味叙事的重视与追求,可从三个方面找到原因。
首先,与晚清新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和小说的开放本性有关。晚清新小说家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诗文教育,以致陈平原做出以下推测:“推前一百年,吴趼人、李伯元可能还会写小说,而梁启超、刘鹗、林纾、苏曼殊则可能是诗文家而不是小说家。”[6]150这个推测是极有问题的。小说虽被视为小道,但其作者群自唐宋以后就越来越文人化了,且不说四大名著的作者,单是专家考证的《金瓶梅》的可能作者,哪一个不是诗文家?推前一百年,这些人的身份最有可能还是双重的,如现在的吴李两人以小说名世,却也都有诗文留世。新小说家从诗文中借用“味”这个审美范畴来规范小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并且,这恐怕也是他们不自觉而最佳的选择。因为“味”这个包容性巨大的民族化的审美范畴,与小说的开放本性和新小说呈现的混沌性天然地契合。中国小说本孕育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与诗歌多类母体之中,最具包容性与开放性,能吸收其他文学样式的营养质素,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真可谓“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新小说家们也充分认识到了小说文体的开放优势。梁启超就说《新中国未来记》:“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7]55周桂笙在《神女再世奇缘》自序中也说:“此篇以小说为体,而淹有众长,盖实兼探险、游记、理想、科学、地理诸门而组织一气者也。”[8]164黄摩西则把小说与时文相比,认为:“小说中非但不拒时文,即一切谣俗之猥琐、闺房之诟谇、樵夫牧竖之歌谚,亦与四部三藏鸿文秘典同收笔端,以供馔箸之资料,而宇宙万有之运用于炉锤者,更无论矣。”[9]这种“淹有众长”、包备“宇宙万有”的“四不像”形态正是新小说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又一次呈现出孕育于母体时的混沌特征。当然,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古典小说形成章回体的模式以后,四平八稳,食欲不足;而新小说则非常“饥饿”、格外“贪婪”,举报纸新闻、法律条文、组织章程等非文学性的文字也照录不误,呈现出混沌的特质,仿佛黎明前的黑暗,是大创造之前的积极摸索。唤醒小说吸收潜能和开放欲望的,一是灌输文明、灌输新知的宗旨,二是西洋文化和文学新鲜的刺激与召唤。新小说之新也就在于在前两种合力的驱使下因着小说的本性而全面突破传统的故事模式与套路去寻找小说新的趣味。我认为,这是对陈平原“两个移动”说的必要补充和修订。因为“两个移动”发生的平台正是开放的小说文体本身。再者,我认为,不要在文学内部区分什么边缘与中心。即使说小说进入中心,也无非是指由小道而登大雅之堂,成为最流行的创作文体和欣赏对象。可是,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文学流行,诗歌一直被认为是文学的最高典范,时至今日,我们赞誉一本小说或一篇散文,仍然说它们“像一首诗,具有诗情画意”。当然,如何借用典范,自然古今有别:古典小说直接借用诗歌的形式,以诗录入小说;而现代小说则重视在文本中构筑诗的意境和意味,以诗融入小说。
其次,趣味叙事也显现了新小说家启蒙背后的读者意识。小说要发挥启蒙作用,就须“会于流俗”,投人所好。“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10]205吴趼人因《笑林广记》“无甚新意识新趣味”,所以他要改良为《新笑林广记》。《新新小说》颇多侠气与血气,主编冷血(陈景韩)在《侠客谈·叙言》中自称“命意浅近”,立局“甚率直,无趣味”,实则,要领略它的趣味需要一定的资格。他期待的读者是有着感时忧国之热血心肠的十四五岁少年。像这样明确的读者划分和想象,其时罕见。
最后,最根本的,是在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写作受到了报刊销行与稿酬制度的制约与驱动。毫无疑问,新小说的兴起与现代报刊和稿酬制度的出现密不可分。新小说既从中受益,又为其所制。包天笑回忆说:“一种出版物的发行,非常重要,在推广销路上,也正大有技术,他们商业上所称的‘生意眼’,未可厚非。”[11]376这些“技术”包括给刊物起个响亮的名字,封面要活泼,内附美人像、插图,等等。而小说趣味与否也至关重要,因为“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11]318。“读小说如听说书一般,要继续读下去,方有兴味”[11]378。意思再明白不过,报刊需要有趣味的小说,若登载的小说没趣味,就可能办不下去。《新闻报》就曾大力改革原本“不活泼”的副刊,而请李涵秋、向恺然做小说,很能吸引人,激增了该报的销量。
1907年,《小说林》正式以千字若干元的方式募集小说,被视为现代稿酬制度建立的标志。稿酬制度为晚清作家的创作自由提供了必备条件。当然,也不乏有人仅仅拿小说的趣味来紧紧地追逐金钱的铜臭味,从而在五四时期招来了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郭沫若等人的猛烈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与金钱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而标志着五四成长起来的文学家、批评家们正在奋起争夺文学的权力和利益。
三、新小说趣味叙事的数种方式
新小说分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在这百花齐放的根处,却有着一种共通的写作模式:“将现在时势局面人情风俗一切种种实在坏处一一演说出来,叫人家看得可耻可笑;又将我脑中见得到的道理,比现在时局高尚点子的,敷衍出来,叫人家看得可羡可慕;中间又要设出许多奇奇怪怪、变化出没的局面叫人家看得可惊可喜。”[12]即新小说的趣味叙事采取了游评(睹游+议论)的故事模式和审丑的喜剧叙事。
“游的趣味,无论甚么,都及他不来”[13],新小说的作者(他们不管自己叫“作者”,而是“记者”)总是叫人物不断地游历,不停地变换地点,并常去茶馆酒肆旅店这些人多的地方,打听民间疾苦和世间奇闻。山寨和闺阁已无法容纳新小说的想象视域。20世纪初,整个民族的想象疆域是由新小说大力开拓的。《老残游记》和《邻女语》面向中国的北方,吴趼人的小说提供了对于南方的想象风貌,《新石头记》《新纪元》《月球殖民地小说》和《新法螺先生谭》则扩展到全球并深入宇宙。在不停地想象旅途上,歇脚之地往往成为议论风生之处:或是两三人辩论,或是听人做时髦的演讲,虽然现在看来陈腐枯燥,但在作者本意却是不吐不快。更何况他们还力求使之别开生面,发人所未发,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关于做善事的议论,《新石头记》里关于专制胜于共和、立宪的议论,《老残游记》里关于清官能吏的议论……这些有新意的议论恐怕是新小说家对读者最主要的阅读期待。可以说,没有议论,也就没有新小说。这种粗糙却也独特的写作方式乃是士大夫文化的精神传承,是新小说家们感时忧国的重要途径和国民意识的重要体现。
如果说在另两个叙事空间——家和官场——进行审丑观照是正常,那么该如何看待新小说对新事物的黑色叙事呢?这里面反映的政治和道德取向非常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审丑叙事是为了增加趣味,无论对新对旧,嘲世的嬉笑怒骂精神晚清小说家整体上表现得最痛快淋漓。在这场有着考据之风的世纪旅行中,上海成了一个不可不去的新兴都市。夏仰西初次来到上海,看见“一路有些机器厂等类,局面比之杭州更是恢张……很有些三层高的洋房,街上的外国人,来来往往不绝,马车东洋车更是热闹……更奇的是那中国人改洋装的更多了,觉得自己在杭州的时候很厌恶这种人,叫他是汉奸,如今看他们的模样,倒觉得入目,并不是什么汉奸,颇像有些读书人的秀气”[14]。上海就这样成了一个化中化西具有魔法的城市。可是,在更多的新小说那里,上海却是一个审丑叙事的大空间。吴趼人对上海的体验在当时的知识群体中颇有代表性:上海是“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但“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所以“不是好地方”[15]1。在新小说当中,往往会写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体验文明风景,但最后的结局不是逃避,就是灭亡,再就是投入都市之丑之恶的怀抱,迷失了本性,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九死一生”,《文明小史》里的贾氏兄弟和姚氏父子,《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新石头记》里的宝玉,《上海游骖录》里的辜望延,《恨海》里的陈伯和,《海上繁华梦》里的谢幼安和杜少牧,等等。另外,演讲和叫局在当时是大上海的象征,但叫局被后世指摘为颓废的享乐,而代表新事物新面孔的新派演讲也常被描述为闹剧,如宝玉在张园参加的演说成了妓女、马夫、和尚与暴徒的无声戏,而王济川在民权学社看到的演讲也成了听者与姘头的窃窃私语。
此外,新小说至少还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追求叙事的趣味感
首先,从小说题材来说,新小说家特别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尤其热衷于官场题材,几乎可以说是无官场不成小说。官场仿佛就是最具吸引力的磁场,它可以连接江湖、市民、妓院、茶馆、酒肆、报馆、洋人等形形色色的组织与人物,不断地更新与变换,提供了一幅幅饶有趣味的关于国家和民族想象的图景。同时,官场还和上海这座新兴的都市相互叠加,就更加令人眼花缭乱了。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别感兴趣于写情。所谓人类之“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16]。写情小说泛滥一时,整体上看,比政治小说取得的艺术成就更高。1906年,因吴趼人《恨海》和符霖《禽海石》的出版,可被称为“写情小说年”。《恨海》写情不离道德,《禽海石》要传写“意中人和我两相恋爱、两相乖违、可喜可愕、可歌可泣的情节”,都追求叙事的趣味。而辛亥革命后徐枕亚的写情小说虽承趣味叙事余绪,却又躲入闺阁,呈现出书面化和文人化的形态。这其实是给五四作家出了一道题目:如何在文学中既关注家国命运,又保持艺术品位;既是宏大叙事的,又是个人体验的?
其次,对人物进行谐谑化和寓言化命名。伊恩.P.瓦特曾说:“一个在小说写作中虽小却并非不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取的名字应该是巧妙得恰如其分,又意有所指,而且听起来还要象日常生活实际那样。”[17]13以此来判断新小说对人物的命名,可以发现他们牺牲掉了“日常生活”,不怕承担概念化和类型化的风险,而特别凸显人物名字的意指。大致说来,有两种人物形象和名称是作者和读者都感兴趣的:一类是小人形象,尤其是那些穿了外国衣服的中国人——十里洋场的买办们,往往被分配给一个好看却不好听、一说就露馅的名字,如《官场现形记》里的魏翩仞谐音“骗人”,刘瞻光谐音“沾光”,《恨海》里的辛述坏是“心术坏”,《新石头记》里的柏耀廉是“不要脸”,《中国现在记》里的武官“卫得胜”实是“未得胜”,《活地狱》里的差役莫是仁实是“不是人”,此类谐音人名比比皆是,无须赘举。另一类就是君子形象。自《新中国未来记》诞生了黄群黄克强父子,新小说就多了黄姓一族。《黄绣球》里的黄绣球自谓“我黄绣球,要绣成一个全地球”。《新石头记》文明境界里的东方一族与之遥相呼应。记住他们不是因为丰富可感的形象,而是这些带着国家和民族寓言的名字。“民族若无这等人物,如何立国?”[18]他们有实学本领,根本上却是克己修身的儒家传人,体现的是以君子立国的政治理念。这类命名方式在五四以后罕有继承者。
最后,眉批和回批也是使小说趣味发扬的一种叙事手段。眉批和回批也是一种创作,它们确立了作者、批者和读者的对话关系,使经过评点的文本变成多声部的交响乐,使意义的指涉、趣味的辐射更加丰富遥远。当我们看到“我也这样说”“我看了也一辈子忘不掉”“某某听者”这样的评语时,是不是也激发了我们阅读的兴趣?
四、新小说趣味叙事的历史贡献
新小说的趣味叙事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说五四小说的主要任务和功绩是建立了现代叙事规范,那么新小说则要突破传统的叙事模式。正像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所充分论述的那样,在游评的故事模式中,传统的全知叙事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海游骖录》《老残游记》等小说中被第一人称甚至是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所(部分)取代,而且在《老残游记》中则体现了把人物置入具体环境的倾向和努力。新小说还提供了新的时间经验。在新小说中,时间可以不再是外在客观的,可以不再是宏大遥远的,可以不必再托之于梦,而是可以以身体验、以心变幻的。倒叙自《新中国未来记》之后已经屡见不鲜①。某些新小说还表现出抓住一个又一个“瞬间”的倾向与努力,对人物心理进行繁复曲折的描写。需要说明的是,新小说家对人物心理进行繁复曲折的描写是因为他们有“穷形尽相”的艺术追求,而这也是趣味之所在。钟嵘《〈诗品〉序》认为五言诗之有滋味:“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新小说家也持此观念。狄葆贤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里列举了小说的五对“对待之性质”:简与繁,古与今,蓄与泻,雅与俗,实与虚。“而所谓良小说者,即禀后五者之菁英以鸣于文坛者也。”小说之能事就在于“穷其形”“尽其神”。陶曾佑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认为小说导人以“兴味津津”,而其源泉“不外穷形尽相,引人入胜而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我”探察会党时进退两难的内心活动,《恨海》写张棣华在八百户小店一灯相对时的思念,《九命奇冤》写凌贵兴盼望发榜的焦急心情,《老残游记》写老残月夜在黄河岸边的家国之忧,《月球殖民地小说》写李安武看到龙孟华落魄的样子而想及自身,都不只是一个念头,而是用一大段三四百字的篇幅来写人物的绵绵欲念。而到了苏曼殊和徐枕亚,时间更加主观化和日常化。《玉梨魂》引筠倩病中日记,从六月五日到十四日,叙其病中的感念心绪颇有动人处,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可谓头一回。对趣味的追求,使新小说家们不仅仅注意到“外面之生活”,也能在恰当的时机深入挖掘人的“内面之事情”。唯有如此,人物的丰富个性才能展现。现代科学知识视野中的“人”形象正在中国文学中步步成长。
同时,对趣味叙事的追求促进了短篇小说的兴起。胡适从先秦寓言唐宋韵散中都找到了短篇小说,唯独丢下了晚清时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清末之谴责小说”结构多与《儒林外史》同,其实却有很大不同。因为晚清长篇(不独谴责小说)“颇同短制”的结构是作家追求趣味叙事和叙事趣味的结果。“……做书的人到了此时,不能不将他这一段公案先行结束,免得阅者生厌”[19]166,因为有“免得阅者生厌”的追求,新小说有越写越短之势。《爱芩小传》《中国兴亡梦》《侠客谈》等小说有章而无回,每章不过一二千字,叙事具有现代节奏风味。《月月小说》14号“特别征文”,“征求短篇小说每篇约二三千字及这西丛谈逸事等稿”。《小说林》第六期有新年大增刊的告白,征求的小说“最长以五千字为限”且能鼓吹兴味。此外,短篇的兴起与立宪运动的政治刺激有关。1906年7月,清廷下诏预备仿行立宪,《月月小说》第一号(1906年9月)即在“短篇小说”栏发表了吴趼人的《庆祝立宪》,此后又发《预备立宪》《立宪万岁》等。显而易见,短篇比长篇能更及时、更灵活地反映和干预社会现实。所以,短篇的兴起是报刊发行的现代节奏、趣味叙事与时代刺激合力的结果。吴趼人的短篇小说尤其值得重视:《平步青云》中第一人称叙事运用自如;《大改革》里的人物关系及对话使人想起了鲁迅的《在酒楼上》,“我”和朋友各自发出不同的声音,具有复调性;《黑籍冤魂》前一部分叙传说与演说,后一部分乃吸毒者自叙,充满叙事的张力;《查功课》的文字跳跃与流动却呈现了现代品性。短篇小说在第一人称的运用、限制视角的使用、抒情性和心理化的描写以及叙述的现代节奏等方面取得了不应被忽略的成就。王德威说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用在此处,最为恰切。
五、趣味叙事的长久生命力
1922年6月10日,《小说月报》刊登了《批评创作的三封信》。第一封信认为周作人的《西山小品》“平平淡淡,没什么趣味”,但沈雁冰则称许为“艺术品”,因为“那个卖汽水人是个可爱的人,是一个‘人’,有一个‘朴质’的心”,平淡事情下面是“跳跃的情绪”。第二封信对叶绍钧的《旅路的伴侣》颇有微词,认为“既然不能引起读者的趣味,亦不过有之若无罢了”,沈雁冰对于后者没作有力的答复,却说“《旅路的伴侣》简直就是杰作”,因为“珠儿父母的灰色生活至少也是一段值得研究的灰色人生”。这两封信清楚地表明了趣味在当时的读者群中尚有不小的影响,但五四成长起来的作家和批评家对之不屑一顾直至嗤之以鼻。西方的“主义”取代了东方的“趣味”:《新青年》的写实主义,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沈雁冰的自然主义,创作社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此后,评价作家作品看其有无某种主义思想,用的是何种主义方法。这次话语的转变之所以完成,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小说在辛亥革命之后日趋窄化和封闭,堕入黑幕躲进闺阁,在西方文学修养深厚的五四作家看来,趣味叙事流于表面,毫无现代性的深度和艺术表现力可言,甚至成了享乐消遣和拜金主义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新青年》和北京大学联手,掌握了在现代知识传播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学院权力,以自己为分界线确立了新的新旧概念,迅速控制了文学史的叙述权力。
从此,趣味、趣味叙事和低级庸俗缀在了一起。朱光潜认为“文学本身上的最大毛病是低级趣味”[20]22,并就作品内容和作者态度两方面各列了五种低级趣味。以朱先生的学识和修养,自然能够“把第一眼看去是平淡无奇的东西玩味出隐藏的妙蕴来”[21]37,可是,讲求通俗性和故事性的趣味叙事显然也拥有广大的市场。当时在解放区,赵树理就重新拾起文学上的说书行当,以趣味叙事的方式——具有喜剧色彩的中间人物,有矛盾斗争却又显得简单化的故事以及大团圆的结局——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的启蒙与灌输。虽然学界对赵树理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毕竟文学功利性和审美性的纠缠永远不会结束,但比起后来单纯图解政策的高大全式的作品,赵树理的趣味叙事无疑是成功的。总的来说,按解放区模式培养起来的作家越来越失去了晚清小说家自由的身份、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嬉笑怒骂的精神气质,显得僵化而单薄。更大规模的趣味叙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学刊物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纷纷变脸,从封面到内容,变得活泼通俗,富有趣味。
回想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以趣味叙事开始又以趣味叙事结束,其间的起伏消长回环曲折岂有不令人深思玩味之处?不由想起了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小说君子不为而亦不灭的生命力何在?趣味叙事是也。
注释:
① 就《新中国未来记》而言,倒叙手法可能受到了古典文学名著《桃花扇》的影响,但就整体而言,晚清小说家是在中西小说比较时才发现了外国小说倒叙的趣味,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模仿之,一时蔚然成风。可以参考管冠生《 “小说”的诞生——论晚清以来的小说知识话语》,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 饮冰,等.小说丛话(节录)[G]//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 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J].新小说,1902(1).
[3] 吴趼人.历史小说总序[G]//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林纾.《冰雪因缘》序[G]//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 吉.上海侦探案·金戒指案[J].月月小说,1907(7).
[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G]//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 周树奎.《神女再世奇缘》自序[G]//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 黄摩西.评林[J].小说林,1907(1).
[10]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c]//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12] 中原浪子.京华艳史[J].新新小说,1905(5).
[13] 萧然郁生.乌托邦游记[J].月月小说,1906(1).
[14] 吴蒙.学究新谈[J].绣像小说,1905(49).
[15]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济南:齐鲁书社,1998.
[16] 定一.小说丛话[J].新小说,1903(15).
[17] 伊恩. P . 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董红钧,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
[18] 嗟予.新党现形记[J].新新小说,1904(2).
[19]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0] 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M]//朱光潜.谈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21] 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M]//朱光潜.谈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杨宁〕
On the Interesting Narration of the New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GUAN Guan-sheng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271021, china)
The new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developed an interesting narration with the rising status of literature,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writer's double identities, the openness of the novel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modern newspaper industry. The interesting narration includes the narration mode of “travel- comment”, ugliness's appreciation, selecting the interesting subject, etc. It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short story. The interesting narration keeps long vitality, although it was replaced by the “theme” in“May Forth” times.
new novels; interesting narration; narration mode; late Qing Dynasty
I206.5
A
1006-5261(2016)03-0098-06
2015-11-19
泰山学院科研项目(Y-02-2014002)
管冠生(1977—),男,山东诸城人,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