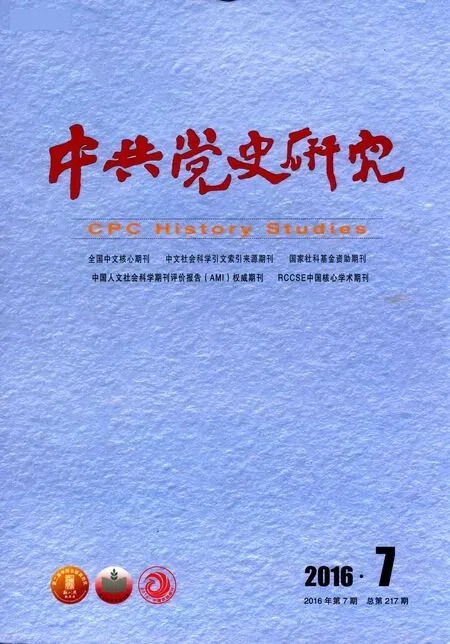从美国档案看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内战调停问题
姚 昱
从美国档案看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内战调停问题
姚 昱
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向四大国提出调停照会之后,中苏两党领导人毛泽东与斯大林围绕此事展开了一次重要而又微妙的协商。这一协商引发了学术界有关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革命态度究竟如何的长久争论。本文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为基础,并与已有俄文和中文资料进行比较互证,通过系统论述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尝试说明斯大林无论是在时局的认识还是策略的设定方面都存在着问题,而毛泽东的认识与策略则更有成效,而且其事后对此事的评价也相当客观公正。
调停;斯大林;毛泽东;美国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苏联领导人是否曾阻碍中国革命的深入和完成,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尤其是中俄两国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最早的学术讨论源于中文资料披露的毛泽东、周恩来有关1949年上半年斯大林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过长江”、想要在中国建立“南北朝”的说法①参见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3页。,此后随着一些内容相互矛盾的回忆录出现,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争议②支持毛泽东、周恩来这一说法的相关资料有斯大林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司徒雷登的记述、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对杨尚昆的访谈以及米高扬儿子的回忆记录等。师哲的回忆录和当时斯大林派驻延安的联络员N.B.科瓦廖夫回忆的米高扬访华却呈现出斯大林并未阻止过中国共产党“过长江”,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72—373页;〔俄〕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俄〕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安·梅·列多夫斯基等著,彭卓吾译:《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67—169页。相关学术争论见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陈广相:《对斯大林干预我军过江问题的探讨》,《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王庭科:《“雅尔塔格局”对苏联、斯大林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刘志青:《斯大林没有劝阻过人民解放军过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陈广相:《对斯大林劝阻解放军过江问题的再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由于这些回忆录内容较为模糊,所以在相关学术争论中毛泽东、周恩来究竟所指何事这一关键性内容始终不能厘清。但俄国学者齐赫文斯基和列多夫斯基先后于1994年、1995年公布了两组苏联政府解密档案——1949年1月初斯大林与毛泽东就国民党政府调停照会一事的往来电报和米高扬关于其1949年1月底、2月初秘密访问西柏坡的回忆报告,*这些苏联档案汉译版见〔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俄〕安·列多夫斯基著,李玉贞译:《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上、中、下),《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第3期。英译版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6/7 (Winter 1995), pp.27-29.毛泽东、周恩来提到的苏联人曾阻止中共“过长江”、要中共建立“南北朝”这一问题的具体缘由得以清晰化,即1949年1月初在处理中国国民党提出的请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大国调停中国内战问题上,中苏两党领导人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接受他提出的有条件和谈,但毛泽东认为会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加以拒绝。*但学界对“过长江”“南北朝”说及“划江而治”的缘起,有不同认识。参见〔德〕迪特·海因茨希著,张文武、李丹琳等译:《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94—301页。薛衔天:《“划江而治”的风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
这两位俄国学者对两组档案的解读以及作为当事人(齐赫文斯基为当时苏联驻北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为当时苏联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一些回忆*〔俄〕齐赫文斯基:《1948—1949年的苏中关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的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22页。并未让相关讨论画上句号,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论。齐赫文斯基和列多夫斯基都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在国民党政府提出调停照会后建议毛泽东接受有条件的和谈,是担心美国借口中国共产党不接受和平而趁机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而斯大林的这一建议颇为英明——既不给美国军事干涉的借口,又让中国共产党接过了和平的旗帜;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有关苏联领导人阻止人民解放军“过长江”的看法实际上是误解了苏联领导人的真实意图。尽管许多学者接受了这两位俄国学者的看法*如迪特·海因茨希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也认为斯大林建议和谈并非要阻碍中国革命,而可能是出于以下三个考虑:不让国民党政府和美国获得希望和平的美名、向毛泽东展示其作为国际领袖的视野、提醒中共领导人其不得不依靠苏联外交和政治支持的现实。Odd Arne Westad, “Rivals and Allies: Stalin, Mao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January 1949, Introduction by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6/7 (Winter 1995), p.7.国内持类似看法的有王真:《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评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沈济时:《关于斯大林劝阻人民解放军过长江问题的探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但仍有学者质疑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接受和谈的真实动机,不赞同中共领导人误解了斯大林的说法。*如李良明、黄雅丽:《关于斯大林是否主张“划江而治”的再探讨》,《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另有学者认为这些档案说明了斯大林的确有调停中国内战的想法,见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57; 〔韩〕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沈志华:《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争论虽然激烈,但对于斯大林在相关电报中为证明自己建议正确而反复提及此次国民党调停照会实为美国政府的“阴谋”这一说法的研究尚不系统。笔者通过查阅美国政府相关解密档案发现,美国方面的资料不仅可以证伪斯大林的说法,而且还提供一些有关这一事件的重要佐证,可以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国民政府的调停照会与中苏两党领导人的分歧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内战中颓势日益明显。为了挽回局面,国民政府于1月8日同时向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驻华公使递交了请求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此时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的斯大林收到这一照会后,于1月10日给毛泽东发电报,通知中共领导人国民政府提出了调停照会一事,并希望中共领导人能接受莫斯科为中共设计的有条件接受和谈这一策略。为了论证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明显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提出这一策略的正确性,斯大林在电报的一开始就判定国民党政府的调停照会实质上是美国政府主导的一个大阴谋——“从各个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的建议是由美国授意提出的,目的在于宣告南京政府主张停战和建立和平,而中共如果直接拒绝同南京进行和平的谈判,则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在1月11日补发的电报中,斯大林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判断,认为国民党要求调停并非是真的为了在中国实现和平,而是美国想让中共背上“和平破坏者”罪名故意设计的一个阴谋。而苏联领导人提出拒绝美国调停和拒绝蒋介石等战犯参加和谈这两个条件来迫使国民党拒绝和谈的策略,既可击破美国这一阴谋,又可保证中国革命的继续。*斯大林相关原文如下:“因此,我们预计,国民党将拒绝在中共提出的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结果是,中共是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因而不能够指责它希望继续进行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将成为阻挠进行和平谈判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所玩弄的和平花招就将被戳穿,您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
尽管毛泽东1月13日未看到斯大林1月11日补发的电报,但当时他对斯大林第一封电报的回电说明其已经确认斯大林所建议的是一种“迂回策略”,并认为这一策略并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有利国际局势:
我们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特别是美国,虽然非常愿意参加调停工作,进而达到保住国民党政权的目的,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当中已经失去威信,加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它们是否愿意继续援助南京政府,继续欺负人民解放军,好像也是个问题。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享有极高威信,因此,如果苏联在对南京政府照会的答复中,采取您1月10日电报中阐述的立场,美英法就可能认为,参加调解工作是应该的,国民党就会得到侮蔑我们的借口,说我们是好战分子……不过现在我们想据理拒绝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考虑到中国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也不利,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季就可以渡江进攻南京。
好像我们无需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在目前形势下,再次实行这种策略,弊多利少。*〔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
上述电文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对当时国际环境的判断与斯大林有着根本的不同,不赞成斯大林的策略。他认为在西方国家已不愿干涉中国事务的情况下,即使苏联只是做个姿态而表示愿意调停国共内战,也将会导致西方三国趁机干涉中国革命。
毛泽东的不同意见迫使斯大林在1月14日第三次就此问题致电毛泽东,证明自己有关世界局势的看法与相关策略是正确的。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将美国的阴谋进一步升级——美国不仅是要“帮助你们国内外的敌人来污蔑共产党和赞扬国民党,把共产党说成是主张继续内战的好战份子”,更是要寻机干涉中国革命:
这意味着您使美国有可能朝着这样的方向改变欧美社会舆论,认为同共产党媾和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要和平。在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组织大国进行武装干涉,就象从1918到1921年这四年间对俄国所进行的武装干涉那样。*〔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斯大林的确一直担心美国可能干涉中国革命,他甚至在中共要发起渡江作战前夕专门致电毛泽东,强调人民解放军要保留足够的预备队防止美国军队可能从解放军后方登陆干涉中国革命。〔俄〕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安·梅·列多夫斯基等著,彭卓吾译:《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69页
斯大林提出美国是幕后黑手的判断很快被证明是误判——1月13日美国政府第一个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调停。尽管毛泽东1月14日公布了同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八项条件、斯大林于15日回电说中苏双方“问题已经解决”、苏联政府也将于17日正式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调停请求,但斯大林却不得不向毛泽东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他认定的幕后黑手美国政府会第一个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调停要求?1949年1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就此问题指责中共方面向美国方面泄密,导致杜鲁门政府了解到苏联对调停持否定态度而抢先拒绝了国民党的调停。尽管这一说法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否认,但米高扬仍然坚持己见。*师哲的回忆说明苏联领导人是真的认为中共方面出现了泄密:1949年1月底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甚至怀疑中共方面会泄露其行踪或者是中共保密工作做得很差。当时前去接他的师哲发现,米高扬一方面要求保密,但另一方面则不断走访当地群众,不注意保密。当师哲向他提出这一点时,米高扬却讽刺说中共方面无法保密:“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但米高扬此次秘密访问一直未被西方觉察,为此50年代初米高扬专门就此事向师哲致歉。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72—373页;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1—42页。
那么,国民党政府调停照会是否是美国政府主导的一个重大阴谋?是否存在中共向杜鲁门政府泄密的可能?美国政府解密档案证明苏联的看法是错误的。
二、杜鲁门政府拒绝调停的决策过程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1月8日下午收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亲自提交的调停照会后,将这一照会立刻发给华盛顿,同时与英国、法国驻华大使进行了紧急磋商,以探究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1月9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美、英、法三国大使的猜测。司徒雷登和英、法大使一致认为,由于苏联不太可能参加调停或即使参加也不抱善意,因此西方的调停不会对目前战场上的胜利者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国民政府也并非真要和谈,而只是借机拖延时间和挽回面子。司徒雷登言下之意很明白,是建议美国政府拒绝调停。*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以下简写为FRUS), 1949, Vol.8, GPO, 1978, pp.22,25.因此,如果国民党政府调停照会一事为美国指使的阴谋,则司徒雷登根本无需与英、法两国大使进行紧急磋商。
有趣的是,1月10日司徒雷登又推翻了自己前一天有关苏联不太可能参加调停的猜测,反而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猜测——苏联政府极有可能是国民党政府调停照会一事的怂恿者。司徒雷登认为,当前只有苏联能对目前占据优势的中共产生影响,因此唯有苏联表示愿意进行调停,国民政府才会向四大国提出调停请求。司徒雷登还提请美国国务院注意这一点:国民党政府的调停照会并未要求四大国进行“联合调停”,因此非常有可能国民政府已经与苏联达成了由后者进行单独调停的某种默契。为此,司徒雷登建议国务院指令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立刻假借联合调停的名义接触苏联外交部,以探听苏联对美、苏、英、法四大国联合调停的反应,并以联合调停之名阻止苏联进行单独调停,来避免因其单独调停成功而获得和平调解者的声望。*FRUS, 1949, Vol.8, p.26.很明显,无论是司徒雷登认为国民党调停照会是苏联幕后操作的看法,还是建议美国政府为破坏苏联可能进行的单独调停而向苏联提出联合调停,都说明国民政府提出照会一事与美国无关。*台湾学者注意到司徒雷登怀疑苏联可能进行单独调停这一点,但未做深入研究,参见Yu-ming 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pp.243-244。
而华盛顿的相关决策过程也说明美国政府并未策划国民党政府的调停请求。在接到司徒雷登1月8日来电两天后的1月10日,杜鲁门政府决定拒绝调停。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乔治·凯南(George Kenan)从现实主义出发,认为西方国家虽然应当进行调停,但他们的调停根本不会得到目前取得优势的中共的重视和同意,因此美国应当拒绝调停。负责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远东事务司司长威廉·沃尔顿·巴特沃斯(William Walton Butterworth)也基于此时美国正在进行的全球冷战战略的考虑而建议拒绝调停。巴特沃斯认为美国如进行调停则会产生下列负面影响:首先,美国调停中国内战不利于美国此时的全球冷战战略。因为美国如进行调停,就要负责组建一个有中共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这会在已将本国共产党人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的法国、意大利、日本和远东各地引起不利的反弹,也会影响此时正在进行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和西方联盟(Western Union),还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不利的反响。其次,国民党政府的调停要求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替罪羊,美国介入只会重蹈马歇尔调停的覆辙。再次,在调停问题上苏联掌握了主动权,但苏联不太可能与西方三国一起行动。巴特沃斯虽然不排除司徒雷登猜测的苏联单独调停的可能性,但他在权衡利弊后建议美国政府拒绝调停,并正好借此机会澄清马歇尔调停的历史,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撇清关系。*FRUS, 1949, Vol.8, pp.26-29.
由于巴特沃斯和凯南意见一致,因此巴特沃斯拟定了一份美国拒绝国民党政府调停照会的答复草稿。这份草稿经凯南修改后于当天上午呈给总统杜鲁门,后者略作删减后批准了这一草案。同时,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NSC 34/1号文件明确了美国政府当前对华基本政策是避免卷入中国内战。在了解到英国完全拒绝调停、态度稍显暧昧的法国也愿意与美国一致行动后,美国政府于12日向司徒雷登发出了拒绝调停的答复声明,后者又于13日晚正式递交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FRUS, 1949, Vol.8, pp.29-30,41,47—48;FRUS, 1949, Vol.9, p.475.
实际上,国民政府也对美国进行调停不抱希望。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未向国民政府表明其态度,为此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专门于1月13日约见美国代理国务卿罗伯特·A.洛维特(Robert A.Lovett)并询问美国政府的立场。顾维钧的表现说明国民党政府已经预料到美国不会进行调停——当洛维特答复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后,顾维钧特意询问洛维特,美国如不能调停,是否可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真诚希望和平解决等?但这一要求被洛维特当场驳回。*FRUS, 1949, Vol.8, pp.44-45.而司徒雷登在递交美国政府正式答复时,也观察到国民政府外长和副外长对美国的拒绝已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两人的反应是感到失望但并不意外*FRUS, 1949, Vol.8, pp.47-48.。与此类似,蒋介石在听闻这一消息后也做出了“此在意料之中”的评价*林秋敏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8卷,(台湾)国史馆,2013年,第500页。。
杜鲁门政府上述决策过程不仅表明美国不是国民政府调停照会一事的幕后主使,而且证明了米高扬提出的、后来为列多夫斯基所坚持的中共向美国“泄密”这一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首先,杜鲁门政府上述决策过程表明其不仅未从中共方面得到任何信息,而且考虑的重点是美国冷战战略的进行,与国民党撇清关系。其次,杜鲁门政府的迅速决策过程说明中共领导人也不可能向美国方面泄密。美国领导人做出拒绝调停决定的1月10日,斯大林才从莫斯科向毛泽东发出了有关此事的、内容颇为简略模糊的第一封电报,第二天又发出了对自己意图进行明确解释的第二封电报,此后斯大林与毛泽东经过交换意见,到14日才出现“问题已经解决”的局面。中共根本无法将14日苏方才确定的“拒绝调停”决定在1月10日美国政府正式决定拒绝调停之前就泄漏给美国人!
而列多夫斯基在其研究中列举的一些支持所谓“泄密说”的证据也难以成立。为说明调停一事为美国牵头的阴谋,列多夫斯基以时任苏联驻南京大使馆一秘的历史当事人身份提到有关美、英、法三国故意提出联合调停以刺探苏联态度。但列多夫斯基的这种说法被美国解密档案所证伪。美国政府解密档案表明,杜鲁门政府为防苏联人侦知美国政府在此事上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司徒雷登曾建议的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刺探苏联外交部对联合调停的反应,反而训令美国在华和在苏外交人员避免与苏联人接触。同时,美国政府还向英、法两国再三强调就拒绝调停一事要向苏联保密。*法国因为出于维护其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需要而对进行调停抱有一丝期望,曾于1月11日想要接触苏联外交部未果。FRUS, 1949, Vol.8, pp.36,40-42.虽然法国态度略有摇摆,但英国拒绝调停的态度十分坚决,并未与苏联人有接触。因此列多夫斯基的“刺探”一说至少与美、英两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不符。特别有问题的是列多夫斯基对《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RelationsofUnitedStates)中相关重要档案的处理态度。列多夫斯基为了证明米高扬提出的“西方大国是在明确知道有关我们态度的确切消息后,才急于拒绝进行调停的”这一说法,特别援引了此份文件集中收录的1月9日司徒雷登猜测苏联不可能调停国共内战的第一封电报。但此份电报并不能证明司徒雷登得出此判断是因为中共“泄密”,因为1月9日苏联大使馆才正式接受南京政府照会,而中共更是迟至1月10日由斯大林的电报才得知此事。同时列多夫斯基还罔顾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与1月9日电报仅一页之隔的1月10日司徒雷登第二份相关电报。在这封电报中司徒雷登本人已经推翻前论,认为苏联极有可能与国民政府达成某种默契、意欲进行单独调停,这更证伪了美国反对调停是因为中共“泄密”的说法。*〔俄〕安·列多夫斯基著、李玉贞译:《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三、杜鲁门政府眼中莫斯科的奇怪反应
既然国民党政府调停照会一事并不是如斯大林所说的是美国政府策划的阴谋,那么毛泽东认为苏联有意单独调停、而且司徒雷登也猜测国民党调停照会与苏联有关的这两个不约而同的看法是否成立?美国解密档案中也有非常重要的相关信息。
杜鲁门政府发现,苏联政府最为奇怪的行为是,相比美、英、法三国驻华大使都于1月8日接受了国民党政府调停照会,无论是苏联驻华大使还是苏联外交部却都于1月8日同时回避接受这一照会。在莫斯科,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受命向苏联外交部提出请苏联进行单独调停的口头请求,但一直被拒见,直到1月12日才得以向莫洛托夫提出这一请求。*FRUS, 1949, Vol.8, p.85.在南京,因为苏联大使罗申故意称病不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直到1月9日才向其提交了调停照会*罗申甚至也以生病为借口,未出席约定好的当晚与美、英、法三国驻华大使的会晤。参见〔俄〕安·列多夫斯基著,李玉贞译:《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也记述了苏联大使缺席1月8日国民政府递交调停照会的会:“外交部长吴铁城邀晤美英法三使,商请斡旋和平。并正式照会美苏英法四使,征询对于中国和平意见,是否准备协助。”参见FRUS, 1949, Vol.8, p.43;斯大林在1月10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也称苏联大使是在1月9日接到的国民政府调停照会。参见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民国二十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38—194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823页。。按照时任苏联大使馆一秘的列多夫斯基的说法,罗申之所以在1月8日避而不见,是因为他一直到2月初都得不到莫斯科的指示。但列多夫斯基的这一回忆和苏联外交部的表现恰恰说明,不同于被蒙在鼓里的美、英、法三国政府,苏联外交部和驻华大使馆很有可能已知道国民政府将会在1月8日提出调停照会。这反过来说明国民政府极有可能已经就调停一事接触过苏联大使或苏联外交部,当然后者的反应也表明苏联对此立场仍不明确,否则罗申和莫洛托夫不会采取“躲”的方式对待国民政府的调停照会。
而此后美国驻南京和莫斯科大使馆陆续向杜鲁门政府报告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和苏联政府一系列颇为怪异的行为。1月13日司徒雷登再次向华盛顿报告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奇怪表现:1月12日,法国大使曾就中国调停要求一事咨询罗申,但罗申未进行表态*FRUS, 1949, Vol.8, p.43.。司徒雷登随后还发现,甚至请求在苏联政府1月17日公开拒绝了国民政府调停请求之后,罗申还与1月21日上台的李宗仁就调停问题进行接触。*1月23日司徒雷登就甘介侯与苏联大使、美国大使的相关接洽给美国国务院发去一封电报,说李宗仁已经与罗申就签订一项中国保持中立的条约达成了草案。参见FRUS, 1949, Vol.8, p.78.司徒雷登这一电报在《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中被公布出来后,8月23日甘介侯专门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说明。甘介侯说李宗仁的确曾想接触罗申,讨论中国与苏联签订一项在未来国际冲突中保持中立的条约,以换取苏联对中共施压、在国共和谈中做出让步。不过罗申抬高价码、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尽最大可能在中国排除美国的影响、与苏联建立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但罗申并未完全拒绝甘介侯的这一提议。按照甘介侯的说法,直到数日后苏联大使才采取了彻底敌对的态度。不过甘介侯并未否认曾与罗申秘密接触。参见FRUS, 1949, Vol.9.The Far East: China, GPO, 1978, pp.1401-1403.
与此同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福伊·D.科勒(Foy D.Kohler)也发现莫斯科在中国内战和调停问题上有许多颇值得注意的表现,并为此推翻了自己于1月12日提出的苏联不会调停中国内战的初步判定*在1月12日就国民党政府调停照会一事发给美国国务院的分析电报中,科勒认为“大使馆并不预计苏联会对中国的调停要求作出有利的答复”。参见FRUS, 1949, Vol.8, p.38.,转而认为苏联政府不仅确有可能事先与国民党政府有所接触,而且未尝没有调停中国内战的打算。1月20日科勒向国务卿马歇尔汇报了莫斯科一些很值得关注的行为。首先,在各种流言和新闻报道流行了几个星期后,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正式于1月2日否认了国民党政府曾接近苏联或苏联正在考虑调停中国冲突的流言。但此后不久的1月8日国民党政府却在南京向四国提交了调停照会。*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民国二十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38—1949)》,第823页。其次,虽然毛泽东在1月14日宣布了国共和谈八项条件,但莫斯科直到1月19日才公布了中共提出的条件。再次,法国驻莫斯科大使于1月11日就提出与苏联副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商谈国民党调停照会一事,但直到1月18日维辛斯基才接见法国大使,并声称直到前一天深夜苏联领导人才决定拒绝调停,但事实是前一天下午维辛斯基就已将苏联的答复交给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FRUS, 1949, Vol.8, p.60.科勒还从傅秉常那里得知,后者曾于1月12日向莫洛托夫当面表达了国民政府希望苏联进行单独调停的愿望,但莫洛托夫既未表示拒绝,也未表示同意*FRUS, 1949, Vol.8, p.85.。
对苏联政府这些看起来颇为怪异的行为,科勒做出了如下猜测:
我们认为中国局势的快速发展超出了苏联政策范围,并迫使克里姆林宫——很可能是在征询了中共意见后——对其当前有关中国冲突的政策进行迅速的反思和决策。虽然去年苏联——特别是苏联驻南京大使罗申——向南京暗示希望进行调停,这可能是烟雾弹,但更可能是克里姆林宫错估了中共的军事能力和国民党政府的弱点,并相信当时政治解决(中国局势)是有利的。但中共军队夺取沈阳并取得瞩目的胜利,加上毛泽东针对国民党政府公开发表了不让步态度,这必定令克里姆林宫要重新进行思考……本大使馆认为,无论是苏联方面想要就国民党政府调停要求进行决策,还是毛担心苏联会赞同国民党政府这一提议,双方领导人可能已经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议来决定和协调政策。*FRUS, 1949, Vol.8, p.60.
科勒上述判断颇为精准,中苏两党领袖的确就此问题展开了最高级别的协调,只不过双方是通过电报的方式来进行沟通。此后科勒又发现了证明自己这一判断的新证据。2月初苏联两份重要报纸《文学报》和《新时代》终于刊登了有关中国局势的评论文章——这是几个月来苏联媒体第一次对中国局势发表看法。由于这两份评论文章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用词上都与中共刊发的文章保持一致,科勒判定到1949年2月初,苏联领导人才终于确定了其有关中国局势的政策路线——支持中国共产党,此时克里姆林宫已经与中共建立起了牢固的联盟关系。*FRUS, 1949, Vol.8, p.105.
其他相关材料都佐证了科勒对苏联政府直到1949年2月初才最终明确了其对中国的政策这一看法是相当准确的。正在莫斯科采访、十分关心中国局势的美国左翼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也发现,“当时在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和外国外交人士,都对自1948年秋天以来苏联报纸一直对中共取得的胜利闭口不谈这一点感到十分疑惑”,直到1949年1月下旬,“苏联报纸打破了长期以来对中共胜利的沉默,对于中国内战,发表了长篇社论,而中共的胜利这时已经继续了三个多月了”。而一位苏共老干部就此事对斯特朗的解释与科勒的判断几乎完全相同:“我想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正在高级领导层中重新审议,所以在此期间,报纸保持沉默。”*参见〔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陈裕年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俄国人1949年为什么逮捕我?它可能与中国的关系》,三联书店,1982年,第29、31页。自1月下旬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秘密接触的李宗仁的私人代表——甘介侯后来也承认,罗申一开始仍与其保持接触并且态度暧昧,但在数日后突然采取了彻底敌对的态度*FRUS, 1949, Vol.9, pp.1401-1403.。列多夫斯基也承认,大约在2月初苏联驻华大使馆才接到莫斯科有关调停一事的明确指示。此后罗申态度不再暧昧,于2月20日和21日两次明确拒绝了国民党政权的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与代总统李宗仁提出的希望苏联能介入国共和谈的请求。作为进一步佐证的是,斯大林在再三拒绝毛泽东访问苏联以讨论中苏两党合作问题之后,终于于1月底派出了苏共代表、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明确表示要与中共展开密切合作,并就一系列具体合作问题展开了讨论。*沈志华:《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最新公布的苏联政府档案证明了毛泽东和司徒雷登的看法恰恰更贴近事实。1月12日,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傅秉常根据行政院长孙科和外交部代理部长在此问题上的指示,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交若干重要事项的秘密通报。其中第三项就是“上述4个国家(美、英、法、苏)政府为恢复中国和平所作的真诚援助不一定采取共同行动的形式。如果苏联政府愿意单独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谈问题上做出友善的帮助的话,中国政府将不胜感激。”*《莫洛托夫与傅秉常会谈纪要》(1949年1月12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351页。而此前南京政府已经充分考虑了苏联方面的可能态度——1月4日蒋介石在与行政院院长孙科讨论邀请四大国调停内战时,曾特别强调:“应研究苏俄与共匪之政策有无和平诚意,以及此事之利害究竟如何?方可决定也。”*林秋敏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8卷,第374—75页。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南京政府之所以在1月8日就试图向苏联提交单独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当是与苏联有所接触,而苏联的态度至少是没有明确拒绝。
总而言之,上述来自中国、美国和苏联的多方资料表明,由于当时中国内战局势尚不明朗和担心美国对中国革命进行军事干涉,苏联曾对中国内战的态度较为暧昧,并在单独调停国共内战这一问题上应该事先与南京政府有所接触并达成了某种默契。只是因为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和中国内战趋势的快速明朗化,斯大林才最终确定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实现全国胜利的基本对华政策和拒绝国民党调停要求的立场。
四、结 论
既然美国政府解密档案说明了杜鲁门政府并不是国民党政府提出调停请求的幕后推手、中共也未向其“泄密”,那么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围绕此事展开的争论来看,毛泽东当时对与中国内战有关的国际局势的认识比斯大林的认识准确得多。而美国的相关文件和后来事实发展更说明,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策略中存在着一些致命的漏洞是颇有道理的。首先,毛泽东在1月13日电报中就指出,苏联政府若表态愿意调停,则极易为西方大国提供干涉口实。而司徒雷登为破坏苏联单独调停,的确于1月10日建议美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四大国联合调停,而法国当时也一直对苏联进行调停抱有一定幻想并试图就此与苏联沟通。其次,毛泽东在1月14日回电中委婉批评斯大林拟定的进行重开国共和谈两项前提——不准美国调停和不准国民党战犯参加——不足以阻止国民党回到谈判桌前,这一点也被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蒋介石下台后李宗仁政府甚至初步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更为全面和严苛的八项和谈条件。
基于上述事实,笔者以为,毛泽东未事先通知苏联领导人就于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文并公布了国共和谈八项条件这一举动,与其说是毛泽东全盘接受了斯大林的策略,不如说是毛泽东坚持自己策略为主、辅之以斯大林策略中优点的表现。毛泽东通过中共单方面抢先发布要求国民党直接与中共交涉的声明,彻底杜绝了苏联发表原拟定答复而对解放战争产生的不利影响(当然也堵上了西方国家调停中国内战的借口),同时也补上了斯大林建议的仅包括拒绝美国调停和禁止战犯参加和谈这两项而可能令中共陷于被动的漏洞,更接过了“和平的旗帜”*〔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毛泽东的这一单方面举动实际上是否决了苏联的提议,所以斯大林在1月15日回电中才不得不说两党之间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解决。
从以上两点重新审视周恩来与毛泽东1955年、1957年有关“过长江”“南北朝”的谈话,笔者以为他们的说法是相当客观的。两位中国领导人都不是指斯大林主观上要在中国建立“南北朝”而不让解放军“过长江”,而强调的是斯大林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担心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极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干涉,为此建议人民解放军不“过长江”。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如果当时中国领导人盲目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客观上反而会出现“南北朝”。*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3页。简言之,毛泽东与周恩来认为斯大林的主观动机并非想要阻碍中国革命,只是因为其误判了形势,所以其所提出的策略在客观影响上不利于中国革命。而周恩来提到的此时苏联对华政策仍然摇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当时同苏联是有分歧的”这一判断,甚至得到了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苏联政府观察的佐证,也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及其根源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但中共领导
人对苏联领导人的动机仍然进行了非常善意的理解。周恩来认为在当时冷战已经兴起,在国共内战中的三大战役尚未彻底结束的背景下,“斯大林总的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时期”,而“中共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学术界也公认在这次争论中,斯大林以较为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共产党人,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事先征求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较为平等的地位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苏两党最终较为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件。就此而言,中国学者过去认为毛泽东、周恩来的说法证明了苏联故意干涉中国革命的各种看法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原意有所曲解,但俄国学者仅以苏联档案为基础、无视苏联领导人认识与策略上的错误的看法也略为偏颇。当然,要对这一问题本身及其国内外历史背景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仍需要以多边相关历史资料为基础,以更为全面、客观的态度来加以审视。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兼职教授 上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广州 510630)
(责任编辑 张 政)
On the Mediation for the KMT-CPC Civil War in January 1949 on the Basis of the U.S.Decoded Archives
Yao Yu
After January 8, 1949, the KMT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mediation note to the four countries, and the leaders of the two parties, Mao Zedong and Stalin launched an important and delicate negotiation on the issue. The negotiation leads to a lasting debate about Stalin’s attitude on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academic. On the basis of the U.S. government decoded archives, and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ussian and Chinese dat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on this issue, and tries to explain that Stalin had some problems, whether in the situation understanding or strategy setting, but Mao Zedong was more effective in understanding and strategy, and later his evaluation was quite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on the issue.
K266;D822.3
A
1003-3815(2016)-07-00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