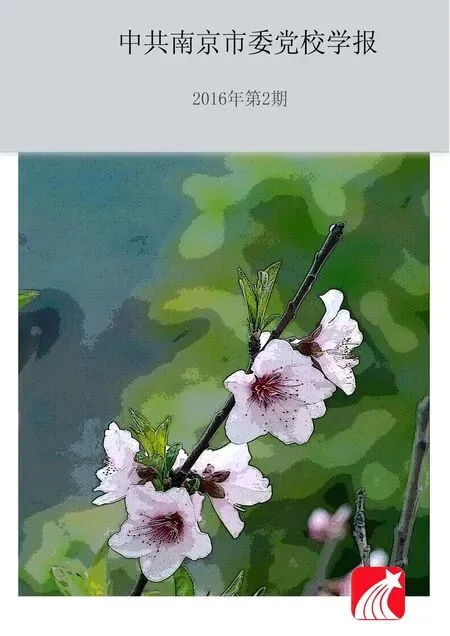集中力量办大事
——县域中的整合式治理模式
曾 森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湖北 430072)
集中力量办大事
——县域中的整合式治理模式
曾 森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湖北 430072)
县级政府连接着中国各级政府,因此,县域治理是中国复杂而多重国家治理体制的中间环节。在各级政府治理结构同构的同时,县域治理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本文在“行政吸纳”和“运动式治理”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县域内存在的整合式治理模式。笔者先厘清了整合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区别,然后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整合式治理模式的存在根源,并列举了该治理模式的特点。最后,笔者认为,这一模式的存在折射出中国政治中深刻的矛盾,即党政之间、党与法之间的关系长期没有理顺。这也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县域治理;整合;结构;吸纳
县级政府是中国最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一级政府,长期承担着赋税征收、秩序稳定、信息沟通与政治教化的重要功能。在当代中国,县级治理依然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杨雪冬等认为,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框架中,县是最全面的微观单位,不仅能够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集中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徐勇提出了“接点”的概念,认为县域是国家与地方基层、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权力运作与权力监控的“接点”单位。 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县级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与治理压力,并形成了县域范围内的整合式治理模式。本文试图分析在县域中,党委领导下的整合式治理这一模式的运用及其影响。
一、吸纳与整合
本文的整合式治理,得益于“行政吸纳”理论。行政吸纳模式最初由金耀基提出并用来解释香港的治理行为,它“是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3]金耀基认为通过英国统治者与非英国的(绝大部分为中国人)精英共同分担决策角色的共治体系与咨询,香港构建了与韦伯的“科层组织”不同的行政体系,即政治的行政化。康晓光利用行政吸纳政治模式,试图解释1989年中国在合法性受损与国际局势不利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腾飞的原因,并据此提出“行政吸纳社会”的观点。他的行政吸纳模式强调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联盟这一特点。[4]综上可知,行政吸纳模式主要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占主导型的行政机构吸纳社会精英力量,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和政治稳定的统治策略。
与行政吸纳理论不同,整合式治理主要不在于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而是对政治精英内部分化的政治机构和职能的整合。因此,所谓的整合式模式就是指政府的分支机构,即县人大、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等在党委领导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临时的或阶段性的组织,以改进治理工作,提升治理绩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治理方式是以党委与政府为核心吸纳其他政治机构和政治行为的方式展开的。
二、整合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
在理论构建上,整合式治理还受到运动式治理的影响。但是,两者从形式、主导力量与内在根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运动式治理的最大特点在于暂时打断、叫停纵向的科层体制,自上而下进行非常规化的治理,而整合式治理则致力于整合与集中横向政府结构,以达到治理行为中的一致与有效性。换句话说,前者重点在于打通“条条”关系的障碍,而后者更重视“块块”关系的协调。因此,这就导致了两者的治理主导力量是迥异的。对于运动式治理来说,上级政府,有时甚至是中央政府,是这一行为的发动者与主导者,而整合式治理一般以同级的党委与政府为核心。如果说,县域中的运动式治理的主要决策由遥远的上级政府的地方工作会议作出的,那么整合式治理的决策则主要是在本县县委常委的会议上作出。
更为重要的是,运动式与整合式这两种治理模式所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不同的。正如周雪光所揭示的那样:“在中国大一统体制中,存在着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运动式治理则是针对这一矛盾及其组织失败和危机而发展起来的应对机制之一,反映了国家治理的深层制度逻辑。” 对于整合式治理来说,其产生及延续是政治结构分化与有效治理之间内在矛盾,这在像中国一样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权威体制国家中尤其明显。结构分化是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一大特征。正如亨廷顿所说: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等三个方面。亨廷顿认为, 在现代化过程中, 政治稳定依赖于具有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的制度。 在政治结构分化过程中, 政治结构分化程度和广度与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比值是衡量一个政治系统整合程度和稳定程度的标准。但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又会带来政治结构有效性的问题,这就要求各政治结构之间进行某种形式的整合。这种整合在世界各国都有各自的形式。 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之下,是在保持君主制的情况下,将政府结构整合在某个民选的机构手中,一开始是议会,之后逐渐集中于内阁;在法国等半总统制下,整合是以总统为核心而展开的,总统充当国家的拱心石的作用;在美国,分权制衡的传统和松散的政党体制导致政治机构的整合水平非常低;在中国,这种整合更为彻底与全面。在中央政府层面,以党的班子为核心,通过分口管理和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的形式组建了强大的整合体制。
在县域层面中,由于所处的“接点”位置,县级政府处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中央政策与地方利益的中间环节,既要面临来自压力型体制的科层压力,又直面日益崛起的社会利益与民众诉求。近些年,县级政府一方面要进行“招商引资”以加速本县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需维护本县的社会稳定。在晋升“锦标赛”的模式下,本县的治理绩效与县“一把手”的升迁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对于县级政府与县级官员来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整合本县资源与政府各机构成为迅速提升治理绩效的方法之一。
三、何以可能?
那么,在县域内,为何这种整合式治理能够广泛而经常地发生呢?根本上说,这归因于县域政治权力分布的特殊结构,也就是在党政一体化制度下强化的“大同心圆”结构。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实施党政分开的改革,并初步在制度上确立集体领导体制。的确,按照党章的规定,重大问题由县委员会及其常委会通过表决决定,各委员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但是,县级政治的制度发展滞后,县委书记作为县党委常委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一般处于主导性地位,常委们一般要围着“一把手”的思路转。[9]通过人际关系的运作与权威的潜在性影响,县委书记在县的党组织内部独揽大权的现象非常普遍。
同时,由于党政分开不彻底,党政一体化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相互渗透、同化的现象。因此,县委书记不但在县的党组织中拥有主导的权力,还实际拥有人事任免与经济社会文化的最终拍板权,也最终领导着政府与法院检察院。因此,这种在党委领导下的权力结构可以称之为“大同心圆”结构。县委书记就是县政治权力这一同心圆的圆心,是无可置疑的党政“一把手”。
县级政权的人事制度也在强化这种“大同心圆”。近几年,虽然四川、湖北等地开始试点县党委书记不再兼任人大主任,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两个职务的兼任仍然很普遍。同时,县委书记这一职位本身的升迁经历也有利于这种结构的形成及维持。升迁到县委书记的途径主要有两个:少数是从上级空降,更为普遍的情况从基层扎扎实实做起,台阶式上升,最终任职县委书记。这一台阶的过程是一般干部——副乡长—乡党委委员——乡副书记——乡长——书记——副县长——县常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1]因此,很多县委书记在一县之中任职多年,并多曾任职过处于县的“同心圆”权力结构内的职务,积累了很多人脉,甚至在社会文化氛围下,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集团。
在权力渗透与人事制度的影响下,县委书记作为县级政权“大同心圆”的圆心,在治理压力与政绩推动下,往往试图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动员“同心圆”外围结构进行县域整合式治理,以在任期内提升政绩与治理绩效。
四、整合式治理的特点
总的来说,县域内的整合式治理,主要针对县域内重大问题和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例如维稳,招商引资以拉动GDP和环境治理等等,其主要特点有政府再结构化、政治行政化与治理行动动员化。
(一)政府再结构化
县域政府作为最低一级的完备政府,本已存在一套完整而程序化的的政治机构体系,所有政府结构都有其特有的政治功能。县级党委、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组成了县域治理中的主要机构。在制度设计上,县党委主要对县域内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是县域内实际的“一把手”。另外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人民代表大会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是最高权力机构,在人大闭会期间设置了常设机构——县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着一县之内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与人事任免权;县政协发挥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体现了多党合作的机制。县政府是地方国家执行机关,也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县法院与县检察院也由县人大产生,并履行司法、监察功能。近些年,县级政府也开始根据《公务员法》在辖区内建立公务员制度。这明显体现了现代政治中结构的区分化、科层的分工化、专业化以及制度运作的非人格化的特点。
但是,在县域治理中,核心行动者经常弱化这些机构的作用而试图建立囊括这些机构于一体的新的机构。正如樊红敏认为的,在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核心行动者的行动以及策略来看,县域治理秩序超越了嵌入县域科层组织的制度化文本,是一个再结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常见的策略是成立各种各样的非常规的领导小组、指挥部等等,而这些领导小组的成员一般都包括本县的四大班子的领导。
(二)政治行政化
在现代政治学概念中,政治与行政的功能是不同的。政治意为自下而上系统地履行表达功能的机构和行为;而行政则意味着履行自上而下的贯彻功能的机构和行为。政治行政化是指从功能视角分析,政治中履行自下而上表达功能的机构和行为都被整合进了行政过程之中。
在县域政治框架内,县人大、县政协、政党(主要是民主党派)和社团组织是履行着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的“政治”组织。理论上,这些组织的存在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体现,并不断通过民众政治授权与利益吸纳而降低了执政的成本,维持着社会的稳定。但是,在县域治理的实际过程中,这些组织经常在“服从大局”的方针下参与到行政过程中,如维稳和大的项目建设等。 除了上文提到的成立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统合各种“政治”机构以从事行政事务之外,有些县级政府甚至通过包村包案的方式,使人大、政协的领导干部直接参与到行政工作中。
在这种治理逻辑下,甚至县法院、县检察院等司法机构也被行政化了。司法案件的审理更多考虑的是其社会效果而不是法律效果。长期存在的党委审查案件的制度及维稳的治理目标导向,使这种情况愈加明显。
(三)治理行动动员化
县域中整合治理还表现出很强的动员化的特征,这点与运动式治理颇为相似。如果说政府的再结构化是横向的整合,那么,动员式的治理就是突破韦伯式纵向科层制,通过开展活动的形式达到治理效果。在制度化薄弱并且政治空间狭窄的县级政府中,动员化治理仍然在继续使用。
根据樊红敏对A市的研究,该市2009年就开展了11项重大活动动员。其动员过程可以概括为确定阶段性核心目标——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动员大会——活动开展——检查反馈——观摩评比——总结表彰——活动告一段落。以A市的“清洁家园、美化乡村”百日行动活动为例,动员治理具有以下特点:①高度整合性。所有重要的政府组织和领导都被整合在一个行动领导小组之中;②军事化动员。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是铺天盖地的军事化语言,例如该市L书记讲话一再宣布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各地、各部门还要“立军令状”。③权力运作的剧场化,主要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开大会”和精挑细选的“树典型”。
对于县级政治来说,整合式治理对于调动有限的财政与政治资源,集中精力与力量暂时提升治理绩效与政绩,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其带来的弊端也很明显。首先,整合式治理方式的过多使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治理效果的递减;其次,县人大、县法院、县检察院等“政治”机构的过度行政化将导致其本位职能的缺位与错位,堵塞政治表达与吸纳的渠道,长远来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最后,整合式治理折射出中国政治中深刻的矛盾,即党政之间、党与法之间的关系长期没有理顺。国家治理,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治理经常依靠一种非常态化的模式以解决迫切的暂时性的问题。整合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一样,都根植于系统性的组织失效,也都是政治现代化缺失的产物。
[1]杨雪冬. 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2]徐勇.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以若干个案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6).
[3]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A],见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C].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21.
[4]康晓光.再论行政吸纳政治——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J],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8).
[5]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
[6]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9]樊红敏.转型中的县域治理:结构、行为与变革——基于中部地区5个县的个案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7.
[10]樊红敏.县域政治:权力实践与日常秩序——河南省南河市的体验观察与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77.
[11]樊红敏.政治行政化:县域治理的结构化逻辑——一把手日常行为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1).
(责任编辑:悠 然)
2016-01-19
曾森(1990-),男,江西吉安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
D035.5
A
1672-1071(2016)02-00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