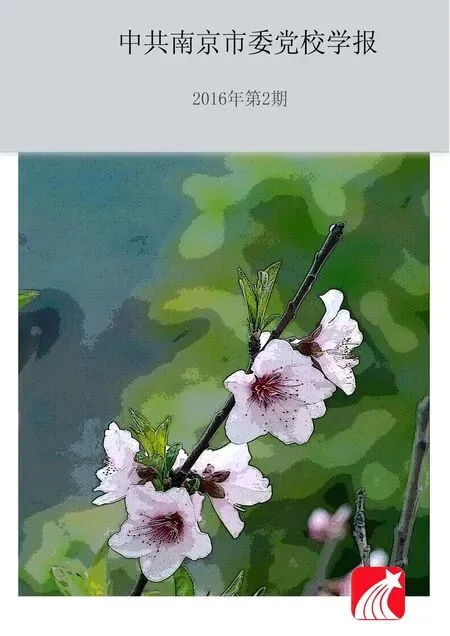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浪漫”情结及其革命性的文化内涵
温 权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浪漫”情结及其革命性的文化内涵
温 权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以资本主义的反人道主义性为批判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创立伊始,就天然具有改造现实的普世情结。后者可被视为,变革世界的“红色浪漫”。正是基于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追求,它才为共产主义运动增添了浪漫的因素。对该浪漫因素的历史意义重新予以揭示,正是在文化内涵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再理解。这同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维度上自我转向新的开端,即构筑于文化背景下的一次宏大叙事般的精神变革。
红色浪漫;宏大叙事;共产主义;自由;文化
一、作为现实革命动因的“红色浪漫”及其文化含义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意义之上,始终有一种无法抹去的情愫贯穿于其中。它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所倡导的建立人间天国的宏大愿望。暂时撇开带有实证色彩的具体操作方案,以及在革命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林林总总需要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单就马克思主义运动本身进行考量,作为对现实的实践性变革的运动,它本身就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并直接指向人类命运的理想化构建图景。
激发这场伟大变革的动因,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制度不合理性所导致人道主义缺失这一耳熟能详的原因之外;一种夹杂有部分“乌托邦”色彩的历史性文化因子,在共产主义运动发轫之初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蕴含在人类向往进步并期望获得自身解放的强烈诉求。该诉求正是通过对蕴含在各个时代对于不合理现实,进行能动批判并经历史沉淀而逐渐形成的强大文化力量。即一种强大的并带有美感的浪漫情怀。对此,马克思认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们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服务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意义上具有这一强烈的文化诉求。后者希冀在历史的维度当中,以一种合理的现实表达出来。从而完成这一文化从隐性向显性的转向,进而使现实在不断的合理性进程中,于历史维度彰显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
正是基于建立人间天国的强大信念,马克思主义才在其现实性上有可能指向具体的社会环节,并以现实的“社会——人”的关系为蓝本,从而演绎出一整套关于人类解放的可行性方案。当然,马克思的立脚点是现实的以物质生产为前提的整个人类社会,他的全部问题域都集中在,以人类的现世解放为基本前提的历史维度之下。因此,他的世界图景是历史现实演进过程中,对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合理性现状所做的惊鸿一瞥。但是,这一瞥不可能逾越马克思本人对现实的物质性变革。这就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落入宗教的语言框架中去。对此,马克思反复强调,“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绝非仅限于批判宗教这一浅显的指向。在现实的意义上,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透过现实变革世界的运动,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一项隐含在革命过程当中的深层因素。即用以指导并激励革命进程的强大意识。这种意识毋宁是,被历史当中的不合理形式所激发,并投射于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文化因子。
对此,马克思指出:“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类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须的,这种变化只是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为,革命之所以必须,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3]在马克思看来,在历史的客观演进过程当中,始终有一种否定现实不合理性的现实革命运动。后者以其特有的否定性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存在状态。若将这种运动本身加以提炼,我们很容易透过马克思的话语系统,获得一种潜藏在人类发展过程当中的强烈诉求,即基于自由意义上的解放。
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作为一种基于人类历史的文化积淀,若想在现实层面得以实现,它就必然经历一种革命性的转向。鉴于此,马克思指出,“首先必须重新唤醒这些人心中的自信心,即自由。这种自信心已经和希腊人一同离开了世界,并同基督教一起消失在天国的苍茫云雾之中。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4]。毫无疑问,马克思强调的是一种根植于人内心的、对于解放的终极诉求。作为这种诉求的载体,人类本身正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有机统一。当历史的维度加入其中,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里,作为革命动因且关于解放的诉求,就演化为一条揭示人类进步历程的精神性线索。它的典型外化,便是为反抗资本主义制度,而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彻底变革的人类运动本身。其内在核心毋宁是,一种基于现实意义、且相对独立于物质存在的文化存在。这一文化存在通过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人类活动,就展现为一种极富浪漫气息的红色情愫。
作为一种理论样态,该浪漫情怀更多的表现为,对于物质世界变革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5]正是如同闪电般具有冲击力的思想,表征着浪漫的革命性文化情愫,才在无产阶级变革世界何以可能的前提下,为革命的上层意义找到了可实现的前提性可能。即作为红色浪漫的革命自由文化,通过历史的大幕为暗哑的物质实践找到了自觉的指向。从此,无产阶级作为自在自为的力量,才在唯物史观的蓝图下找到了面向未来的可靠途径。
这种文化以其所承载的历史性情愫,为人类憧憬未来的自由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于是,暗哑的现实因为获得了浪漫的情怀,从而在无产阶级先行者的指引下,开创出一个普遍自由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崇拜任何东西,所有的现实都将作为关于未来的现实,而在历史的意义上予以批判,并演化成扬弃就制度的社会变革。所以说,“马克思的批判是文化的批判,不是社会的批判,它的依据不是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而是劳动和文化创造活动的实践。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不是批判资本主义这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形式,而是批判政治、经济本身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和解释理论。”[6]无疑,以上论断之所以具备充足的合理性,正是由于,以文化作为背景支援的革命浪漫情愫,弥散于社会批判的各个层面的结果。以此为前提,真正意义上革命运动才能自觉地展开,而这场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弥漫着红色浪漫气息的文化革命。
二、作为宏大叙事表征的“红色浪漫”及其现实意义的达成
诚然,我们通过考量马克思思想的概念框架,初步认定了作为文化表征的浪漫情愫在实际变革运动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在历史的维度下重拾了马克思本人对于“红色浪漫”的描述性界定。而现在亟待探讨的问题,就是作为文化表征的浪漫情结,如何在历史的现实性演进过程中,逐步完成它的终极诉求。即由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及其所伴随的由浪漫向真实的跃迁。
毋庸置疑,构架于现代性意义上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场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现实的不断批判的史诗式的巨作。艰辛而磅礴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人类最为高尚的普世情怀,共同构建了一幅绚烂但几近悲壮的历史画卷。而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背后,潜藏着一场更为深刻的现代性文化革命浪潮。并且,其内容远非单纯的政治诉求亦或是经济诉求所能囊括。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它向我们展现了一条几近曲折但又至关重要的革命道路:寓于文化层次上的、对于人本身在历史当中存在标识的重新确认。即人的价值与解放问题。
对该问题的回答,实则是在革命的语境当中,关于人类自身历史性的史诗性重释。它亦可以理解为以解放为初衷的“红色浪漫”,在现实领域的人的达成。其实质,可视为在文化意义上的人本质的达成。但是这一目的的实现与其说是直接性的、完全的,不如说是继续性的、不断扬弃的。对此,马克思指出:“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有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7]正是在与敌对势力的不断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才能逐渐彰显启示性质的革命理想,以及它所具备的浪漫情愫在整个运动中的积极意义。
“红色浪漫”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必然依附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性活动,才能具备最终向现实飞跃的可能性。于是,原先关于“红色浪漫”的达成就转变为人对于其本质的达成。即人关于人本身解放的最终实现。而这样一种解放同样是历史层面上,作为文化存在的人的本质如何获得自由问题。该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又转变为“人——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问题。故而,这又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意义上的问题:“并不是因为这里没有类似于人的本质的问题,而是因为所有关于人的本性与社会关系思考所得出的机制模型都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人的本性与社会关系并非相互外在且区分为不同层次和方面的”[8]通过社会来理解人的本质,毋宁是将社会这一大课题集中于人的有限存在之上,从而在社会的历史维度使人的本质获得历史意义的进路。它赋予人类追寻自身自由这一诉求以永恒的展望。
若将这一展望牢牢的扎根于最为现实的人类物质生产生活当中,就能在可能性上为人类解放的最终归属找到了合理的起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起点本身就是作为蕴含在其中的浪漫情愫得以现实化的真正开端:它的达成是革命本身的进程,而它所反对的不仅仅是之前所有不合理制度这一静态意义上标的。更重要的是,它要重申对于不合理制度的批判与能动性变革。所以马克思才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9]至此,为马克思主义所孕育的“红色浪漫”情愫,到现在为止终于结出现实的花蕾了。它所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现实与现存的状况。它要摆脱现实当中不合理性的坚固枷锁,从而在人间确立一种运动状态的革命机制。它向一切不合理性开火,并打破所有坚不可摧的顽固力量,进而在人的意义上使人本身在不断的精神革命过程中,获得最为现实的解放。难怪马克思热情澎湃的宣布“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0]
摆脱现实的锁链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极诉求。而获得人类的解放亦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归旨。立足于现实的历史文化土壤,当以反对一切不合理性为内核的文化结晶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大放异彩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情怀就获得了最为现实的表征。后者直接体现为,“共产主义明确的预设了共同体和现实以及‘交流’的重要性…当然交流和协作在这层意义上代表了人类高端需要的满足;共同体不仅仅意味着另一种终结更是对于其自身的最终终结。”[11]以及“这并不是向一些既定的点亦或是终极观念接近的过程。事实上所有关于人类最终终结的观念都是被否定的。”[12]马克思主义及其所引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活的文化性指向。它在人类的交往环节中,不但以物质的革命为前提,而且在展望未来的远大视野上,又同样关注人类精神层面的解放。马克思所要反对的不仅仅是物质对人的奴役,更是以物的奴役所衍生出的人自身的奴役。庸俗的唯物主义除了无法厘清人在历史当中的积极作用以外,更在人类本质的精神层面,无法认识到孕育在其中的真正力量到底为何物。
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浪漫情结,无疑将一切庸俗的思想残渣彻底地清除出人们的头脑。而人类真正摆脱异化的关键,除了摈弃掉对物的依赖之外,更在于从宏观的视野中找到人类未来历史发展的进路。即还要拥有批判当下所谓的“合理性”中,潜藏的不合理性的智慧和勇气。而只有充分领会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我们才能在不断扬弃的过程中,时刻保持对于终极合理性的无限追求。当然这里所说的终极的合理性,本身仍旧是一种过程性、革命性的存在状态。
“红色浪漫”的最终达成,实际上是人以社会现实为基础,进而对现存的一切不合理性进行不断反抗的过程,在历史维度当中的实现。在关于未来的开放视野之下,它是不断追逐和理性的诉求;在关于过去的收敛层面中,它是不断批判不合理性的范式。正是以历史积淀的文化土壤为发轫的起点,马克思主义所孕育的红色浪漫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情愫。在历史的不断进步过程中,它更是一种人类为了追求自由而自觉打造的强大的现实武器。我们把这样一种红色浪漫的激情注入到现实的物质生活中,就使得现实的人类获得了改造自身的真正自觉,从而为自觉的实践力量的迸发找到自明的起点。对此,我们无疑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该问题问题。即“人只是渴望救赎会导致人自身的灭亡。但人有另一个出路,人的本性就是创造着、自己生命建设者,因而对创造的渴望不会导致人自身的消亡。”[13]创造的渴望毋宁就是浪漫的情结,正是在这种情结的指引下,自觉的革命运动才将自由变为现实的存在。
三、作为终极价值取向的“红色浪漫”及其指向人类的关怀
毫无疑问,贯穿马克思主义始终的红色浪漫情愫,因其在历史当中通过人对自身自由本质的不断追寻,从而获得了最为真实的现实意义。于是,它作为人类自觉改造自身的先导和精神自由的必然,就天然在人类最终价值诉求的意义上,具备当然的终极关怀作用。不难看出,由于马克思的立脚点始终是现实的人类存在,所以作为终极关怀的浪漫情怀就以非虚幻的形式,在可实现的层面上相对于人类历史徐徐的展开。基于这一前提,该关怀绝非囿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价值、亦或是其它单一维度上的人类存在方式。换言之,我们所指认的浪漫情怀,它所蕴含的终极关怀,毋宁是囊括人类发展总体的一种全面的生存性关注。马克思预想这样一种情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对于人类生存的最终指向,马克思在他的预设当中用到了“自由”作为总结性的陈述。可以想象,无论是基于解放而不断进行的对于现实不合理性的革命运动本身,还是立足于人类历史在文化的层面上针对人的本质所作出的扬弃性批判,在人的现实存在—社会性存在的层面下,它们都不约而同的指向同一个目标,即自由对于人类生存境遇的指引。
我们一直提到的浪漫情愫无疑在可行性层面上,成为了这种全面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的渲染。它不仅给予我们改造世界及自身的自觉性,更给予我们在这一过程当中所必不可少的信念性。而它强大的信念性之所以由来的根源,除了理论上的完备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历史性和可实现性。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为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5]由此,马克思在现实性的层面上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通往自由的可行性路径。正是基于自由意识的引导,我们才能形成对于现实性批判的自觉,而这样的自觉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于现实不合理性的革命性批判。只有立足于现实并将之自觉贯彻于唯物主义原则之下的批判,才是抓住事物根本的批判。以此为前提,后者才能被社会性的人所接纳,并由此迸发出真正的物质力量。从而在现实的维度上提供达成自由的原动力。讲到这里,我们不禁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正是信仰般的浪漫情愫所彰显的自由诉求,通过人的历史激发了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自觉,并借由这种自觉完成了人类对于自身价值和终极关怀的最终目标。可以这样认为,人类自由的最终实现就是“红色浪漫”这一革命情愫在历史进程中的逐步达成,它是一种趋向更是一种亟待现实化的文化转向。它所挣脱的不仅是可能性的束缚,而且还有现实的不合理性带给它的沉重枷锁,因此,对于“红色浪漫”信念性的渲染,就是人类试图挣脱现实枷锁的强烈渴望。而这一渴望在马克思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都抱定这样的信念,并且问题就在于弥合它与未来革命必胜的更远的信念。”[16]
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浪漫”情结不仅仅作为一种实现自由的自觉,而在现实当中突显其难以估量的价值。对于它的重新解读,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当中,同样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在改革的风潮当中,如果将“红色浪漫”的情愫提高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环节当中来,并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自觉性信念。这对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路和基本方向上,势必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它的全面性价值诉求,所以才能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阶段有机的结合起来,并在精神层面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向共产主义的发展前景找到新的理论自觉。而“红色浪漫”本身对于未来性的渴求,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理想逐渐靠拢的集中体现和自觉遵循的道路。
[1][2][3][5][9][10][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9-10、91、15-16、87、307、294、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7.
[6]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31.
[9][12]Sean Sayers Marxism and Human Nature Routle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153~154.163.
[12]R.N.Berki The Genesis of Marxism Everyman’s University Library London 1988.14.
[13]Бердяев Cпасение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два пониман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http://vehi2.by.ru/berdyyaev/spasenie.html.
[16]G.A.Cohen History,Labour,and Freedo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2003.52.
(责任编辑:木 杉)
2016-01-19
温权(1987-)男,山西太原人,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哲学基础理论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A8
A
1672-1071(2016)02-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