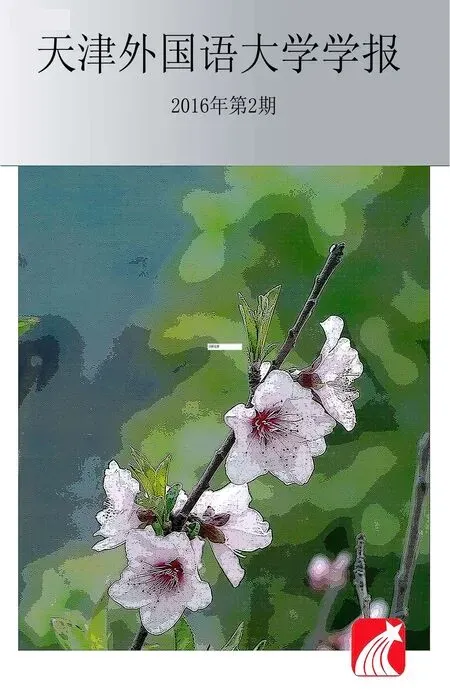《性别理论视阈下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评介
王占斌
(天津商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134;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刘永杰. 2014.《 性别理论视阈下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32页.
《性别理论视阈下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评介
王占斌
(天津商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134;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刘永杰. 2014.《 性别理论视阈下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32页.
《性别理论视阈下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是郑州大学刘永杰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这部专著洋洋洒洒46万字,作者在详细阅读奥尼尔的50部剧本的基础上,借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和研究了奥尼尔的性别伦理意识。国内外奥尼尔研究可谓非常成熟,大家辈出,论著丰硕,几乎可以见到从各种文学批评角度对奥尼尔剧本所作的研究,(汪义群,2006)而从性别理论视角进行的研究恐怕还是首次。阅读这本专著感觉耳目一新,还有点相见恨晚之感,故不得不写上几笔,与专家学者共飨。
本书的独到之处概括起来有三:文本细读、判断客观、观点创新。作者不迷信权威,对奥尼尔的 50部剧本进行重新解读;不受男权与女权思想的困扰,身处其中,得出不偏不倚的判断,在解读剧本的基础上提出新颖独到且合情合理的观点。正如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刘永杰在对奥尼尔剧本痴迷之时,我们也对他的著作心醉神往。
专著分为五章,第一、二章重点探讨了奥尼尔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和创作实践。奥尼尔的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其作品主题和现实生活密切关联,剧中的角色都是来自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尤其是剧中的女性人物往往是按照现实生活的原型刻画的。奥尼尔剧中的很多人物就是奥尼尔本人、家庭成员、朋友和知己,有时他甚至连剧中人物的名字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名相同,这也使他的剧本折射出平凡的意义,流露出朴实的真理。正当人们普遍认为生活就是戏剧时,奥尼尔却认为“戏剧是生活”(Cargill,1970:107),是对生活的解释和对生活实质的真实反映。
第三章揭示了奥尼尔剧作中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心理。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女性都被刻上了传统女性的烙印,只有严格遵守性别社会传统,拥有属于自己的性别特质,才能为社会所接受。这些都是男权中心主义社会杜撰出来的美丽神话,其目的是将女性牢牢地固置在第二性的位置上(波伏瓦,2014),最大限度地维护男性群体的既得利益。久而久之处于第二性的女性便会认同这样的社会身份,而且由认同发展到习惯,女性会完全走向了集体无意识,她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男尊女卑的事实,满足男性群体的需求。她们在行动上依附男性,把她们对未来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男性,尤其是她们的丈夫和情人身上,认为男性可以保证她们拥有幸福稳定的生活。
第四章研究了奥尼尔剧作中男性对依赖于自己的女性的无能。奥尼尔剧作中的大多数男性背离了男权中心主义社会对男性的性别规约,他们不再像传统男性那样处处表现得积极主动、勇敢果断、独立坚强、冷静理性等,却变得和女性一样,失去了传统男性的阳刚和彪悍,不能成为女性的依靠,不能胜任女性保护者的角色。奥尼尔剧中的男性普遍患有两种疾病,一种是俄狄浦斯情结症,另一种是诗人的气质症,前者会把对母亲的依恋转移到妻子身上,生活不能独立,反而依赖女性;后者则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逃避现实,盲目自大,生活在白日梦中。这些男性不能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暴露出软弱无能的一面。
第五章研究了奥尼尔剧中女性的反抗和斗争。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剧作家,奥尼尔对受压迫女性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对她们简单的同情上,他敏锐地捕捉到受压迫女性痛苦的声音,希望通过戏剧帮助妇女探索一条解放自我的道路。在他创作的早期阶段的剧本中,妇女的反抗和斗争的力量比较弱小,但是已经造成夫妻一方的死亡。在创作的中期阶段,她们的斗争再也不是徒劳的死亡,而是变得成熟,并开始讲究斗争的策略,以此实现自己的目标。与第二阶段相比,第三创作阶段的剧本中女性人物的反抗变得迅猛、顽强、无畏。女性意识到男性力量的强大,尤其是意识到男性让她们沦为第二性,她们设法让男性饱尝自己种下的苦果。
专著整体而言可谓浑然一体,用性别理论把五章上勾下连在一起。性别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女性运动中提出的概念,80年代以后被学界广泛接受。性别理论继承了女权运动的精髓,但又自身超越,社会性别理论由单性转向两性视角(Newton,Ryan & Walkowitz,1983)。奥尼尔是悲剧大师,不管是个人悲剧还是社会悲剧,悲剧的肇始者都是具体的人。因此,追溯悲剧的起因就得从人入手,具体说来就得从男女两性的关系中找到答案。男女两性关系是最基本的人类关系,也是人类社会其他诸多关系的基础,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都必然会从两性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只从单性视角研究奥尼尔戏剧总是显得单薄和片面,这也是作者刘永杰运用性别理论代替女性主义理论的原因吧。事实证明,单性视角有时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到奥尼尔剧本中女性悲剧的本质原由。苏泽尼·布尔(Burr,1989:37-47)的《奥尼尔剧中的魔鬼女性》就是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最典型的论文。但这类论文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女性痛苦的表象,忽略了给女性带来痛苦的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本书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作者从性别角度出发给予奥尼尔剧中两性同样的关注,适时地把男权中心主义社会中的男性拽了出来,把男女两性都纳入研究的视野,从男女两性的关系上寻找悲剧之源。作者开拓性地用性别理论解释隐藏在文化基因之中造成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旨在解构存在于两性关系中的男权中心逻各斯,建构和谐平等的多元文化社会。
本书的另一个突出点是作者撕掉了一直以来贴在奥尼尔身上厌女的标签。奥尼尔传记作者路易斯·谢弗(Sheaffer,1973:500)认为,奥尼尔塑造的女性多数是“淫荡凶悍的恶女”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灾难的坏女人。乔治·纽金特(Nugent,1991:60)断言道,奥尼尔剧中的女性“飞扬跋扈”,“充满危险”。奥斯丁等诸多女性批评家也认为奥尼尔是男性话语的代言人,他的叙事是男性的叙事。奥斯丁(Austin,1990:26-28)在其著作《女权主义视角下的戏剧批评》中就对奥尼尔的男性霸权话语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国内著名学者杨永丽、时晓英、刘琛、沈建青、夏雪也同样认为奥尼尔是男权社会的代表,他在歌颂男权社会男性对女性主宰的合理性。他们认为,这些主要是因为奥尼尔深受瑞典著名戏剧家斯特林堡的女性观的影响,具有深度的厌女情结,从而导致在奥尼尔的剧中女性不是完全不在场,就是变成失语群。有的被肆意折磨和残酷虐袭,有的被随意描黑和诋毁。奥尼尔总是把女性书写成蛮狠跋扈、残忍无道、放荡不羁的泼妇(杨永丽,1990;时晓英,2003;刘琛,2004;沈建青,2003;夏雪,2015)。而本书作者刘永杰则持相反的观点。奥尼尔剧中的女性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她们往往是母亲、妻子和女儿,也有的是情人和妓女,她们确实经常被描写成泼妇一般的罗兰太太(《早餐之前》)、淫荡不堪的尼娜(《奇异的插曲》)、吸毒成性的母亲玛丽(《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读者和观众一定会斥责这些女性,因为她们的恶行破坏了家庭的和谐和婚姻的幸福。观众在鄙视和责骂的时候,奥尼尔难免也会被扣上厌女的帽子。奥尼尔只是照单上菜,如实叙事,何罪之有?要说剧本有厌女情绪,那也只能说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在剧本的镜子中被映射出来。
我们认为,奥尼尔展示给我们的女性是真实的女性。奥尼尔生活在一个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从头到尾不在场,完全是男性在定义她们和建构她们的身份。男性根据自身性别的需要对女性提出诸多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并美其名曰女性气质或女性美德,女性失去给自己命名,解释自身经历和表述自身的权力,就连自身的存在也不得不依赖男性才能实现。久而久之女性自己也不知不觉地以男性的视角观察和认识自身,不仅在生物形态上沦为第二性,在精神上沦为第二性。女性们也许会不经意间意识到她们正在遭受不幸或不公平对待,却最终没有发现给她们造成痛苦的原因。《早餐之前》中的罗兰太太除了抱怨还是抱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母亲玛丽的回忆不过是恍惚间的瞬间醒悟而已。男权社会强大的话语网络很快会使她们的低声细语变得彻底失语。
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妇女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他者身份,开始奋起反抗,从此逐渐走向了前台。但是在奥尼尔生活的时代,女性的权力还只是一个美丽的词汇,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奢侈的理想罢了。奥尼尔是一位严肃的剧作家,他用严肃的戏剧形式把女性生活遭遇展现在观众面前。他相信大家在为母亲玛丽、安娜、爱丽丝等女性的悲剧悲戚的同时更应该获得心灵的触动和震撼,并能够严肃认真地对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进行反思。假如她们是你的母亲、你的妹妹、你的妻子,你还会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吗?奥尼尔期待观众观剧的同时能够透过舞台上这些无助的女性的故事,引导大家去质疑和思索那些早已内化为我们意识的集体无意识,拨动人们对社会中男女不公的事实早已麻木不仁的神经,使人们静下心来仔细地审视我们人类自己,尤其是男女两性伦理关系错位的问题。
刘永杰专著中专门另辟一章论证女性权力意识的觉醒和为权力斗争的行为,这也许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他认为,奥尼尔中后期剧中的女性已经不屈命运,向男权中心猛烈开火,让男性付出代价。然而,事实是《安娜·克里斯蒂》中的安娜不是在争取个人权利,而是在寻找男性的庇护,到头来只是一个悲观的结局;《榆树下的欲望》中的爱碧不过是老凯勃特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凯勃特儿子伊本报复和发泄性欲的对象;《奇异的插曲》中的尼娜看似占有了六个男性,实际上她的命运完全被六个男性暗中操纵;《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玛丽依赖男人不得,便开始依赖毒品度日。对于女性的处境和痛苦,奥尼尔表示极大的同情,他盼想女性早日从男性编织的谎言中觉醒。他希望《苦役》中温柔体贴、相夫教子的爱丽丝别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走出家门拯救自我便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他希望《鲸油》中的肯尼太太别再百依百顺,忍气吞声,虚伪自私的肯尼船长只能逼得妻子肯尼太太发疯;他希望《送冰的人来了》中的伊夫琳忘掉道德沦丧的丈夫希基,别指望一个女子能够救赎男人肮脏的灵魂,殊不知为了建构男性自我优秀而将女性建构成他者的男性如何能够允许女性比自己还宽容?奥尼尔在剧中残忍地安排伊夫琳被丈夫施以私刑,他期盼这个悲剧结局能够惊醒一点女性意识的初醒。
奥尼尔通过戏剧暗示观众依赖男性建设美丽家园和幸福生活对女性是个遥远而美丽的神话,可望而不可即。女性只有通过找回失去的自我,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才能赢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对于家庭和婚姻比较失败的奥尼尔通过反思自我,审视社会,探索性别问题的症结所在。就如法国萨特用文学诠释他的哲学思想,奥尼尔用戏剧诠释了他的性别伦理思想,揭示了性别伦理的扭曲和女性悲剧的渊源,唤起全人类对男女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具有强烈的性别伦理意识。
专著的缺陷是在探究婚姻、家庭、爱情和性别时,作者不自觉地用中国人的伦理取向理解和判断剧中的人物行为和心理,用中国式的术语描写奥尼尔剧本中的西方现象,忽略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社会形成的婚姻伦理、家庭伦理和性别伦理价值体系。全书一再贯穿的关键词就是和谐婚姻和幸福家庭,其实西方的文明发展史就是追求自由、平等和爱情的伦理发展史,完全用中国的关键词分析和解释奥尼尔剧中人物的行为道德和伦理价值并非不可取,有时可以增进中国读者的吸收和消化,但过度的归化解读也在一定程度上显得牵强附会,甚至有些不可信服。
[1] Austin, G. 1990. Feminist Theory for Dramatic Criticism[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 Burr, S. 1989. O’Neill’s Ghostly Women[A]. In J. Schlueter (ed.) Feminist Readings of Modern American Drama[C].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3] Cargill, O. 1970. O’Neill and His Play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4] Newton, J. , M. Ryan & J. Walkowitz. 1983. Sex and Class in Women’s History:Essays from Feminist Studies[M]. London: Rutledge.
[5] Nugent, G. 1991.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A]. In R. Morton Jr. (ed.) Eugene O’Neill’s Century: Centennial Views on America’s Foremost Tragic Dramatist[C].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6] Sheaffer, L. 1973. O’Neill: Son and Artist[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7] 刘琛. 2004. 论奥尼尔戏剧中男权中心主义下的女性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5): 59-63.
[8] 刘永杰. 2014. 性别理论视阈下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 时晓英. 2003. 极端状况下的女性——奥尼尔女主角的生存状态[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4): 36-40.
[10] 沈建青. 2003. 疯癫中的挣扎和抵抗:谈《长日入夜行》里的玛丽[J].外国文学研究, (5): 62-67.
[11] 汪义群. 2006. 奥尼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2] 西蒙娜·德·波伏瓦. 2014. 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3] 夏雪. 2015. 尼娜:男性世界中的囚鸟——对《奇异的插曲》的女性主义解读[J].社会科学论坛, (2): 85-90.
[14] 杨永丽. 1990.“恶女人”的提示——论《奥瑞斯提亚》与《悲悼》[J].外国文学评论, (1): 105-111.
(责任编辑:于 涛)
2015-11-17;
2016-02-27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项目“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研究”(131025);天津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多维视角下的奥尼尔研究”(TJWW15-020)
王占斌,男,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美国戏剧研究、文学翻译研究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