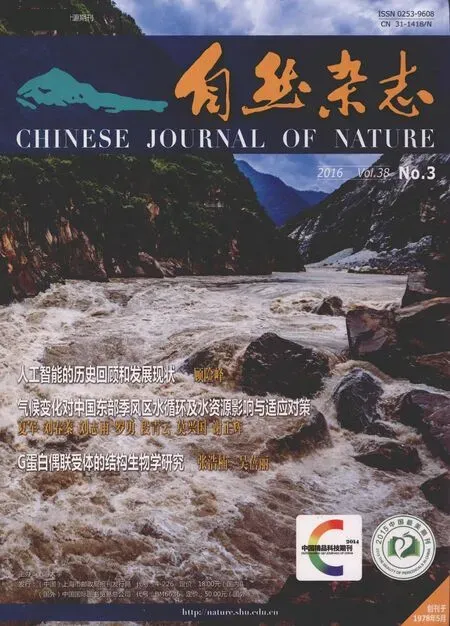地质微生物
——地球环境中的“协调员”*
蒋宏忱,黄柳琴,冯灿,杨渐,董海良
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②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地质微生物
——地球环境中的“协调员”*
蒋宏忱①†,黄柳琴①,冯灿①,杨渐①,董海良②
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②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简单介绍了微生物-地球环境的相互作用,并从微生物矿物相互作用、微生物环境修复、极端环境地质微生物学和古微生物生态重建等四个方面介绍了微生物-地球环境协调发展的意义。
微生物作用;地球环境-微生物矿物相互作用;微生物环境修复;极端环境微生物;古微生物
微生物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是全部原核细菌、原核古菌、部分真菌和单细胞真核藻类等生物的总称。它们分布广泛、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功能多样[1]。微生物处于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底端,在维持基本的生态系统功能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微生物代谢活动几乎参与地球上所有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地球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循环[2-3]。微生物是地球环境演化的重要推手和协调员:微生物通过参与地球系统生源元素物质循环,促进了地球环境的改变(即微生物对环境的反馈),这种环境改变反过来也会影响微生物居群构成及功能(即微生物对环境的响应)。这种微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促进环境生态良性发展(地球环境生态协调发展),也可以造成地球环境生态恶化、甚至地球生物物种大绝灭。因此,理解地球环境中的微生物-环境相互作用,对于我们正确认知地球环境生态协调演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本文就几类与地球环境演化发展密切相关的较为常见微生物作用进行阐述。
1 微生物-矿物相互作用
微生物-矿物相互作用是地球上广泛存在的一种地质作用,对于岩石风化和土壤形成不可或缺[4],其作用类型主要包括微生物成矿作用和微生物溶解改造矿物作用。
微生物成矿是指微生物及其代谢作用所产生的有机质参与成矿或分异聚集元素形成矿床或矿化菌体自身直接堆积形成有用矿床的作用。按作用机理,可分为微生物控制成矿和微生物诱导成矿。前者是指通过微生物吸收、富集环境中的元素等作用直接形成矿物,例如一类可以感应地球磁场的微生物——趋磁细菌,通过吸收环境中的铁元素进入细胞体内合成有序排列的自生磁铁矿,有特定晶形,被称为“磁小体”,作为自己“指南针”引导活动的方向[5];后者是指通过微生物的代谢活动改变微生物周围的微环境营造出适合矿物形成的条件,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长期困扰科学家的“白云石问题”。几十亿年前地球上形成了大量白云石,导致现代厚达上千米的白云石岩层。然而,理论上达到白云石沉淀条件的现代自然环境和实验室模拟实验中都难以沉淀出白云石[6]。有科学家发现,硫酸盐还原菌的代谢活动可以提高细胞周围溶液的pH值和碳酸盐碱度,同时有效地去除或降低抑制白云石成核的硫酸盐浓度,从而诱导白云石的沉淀析出[7]。因此,微生物诱导作用在白云石形成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此外,蓝藻等低等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所引起的周期性矿物沉淀、沉积物的捕获和胶结作用而形成的叠层石(Stromatolite,在前寒武地层中大规模存在)是另一种微生物诱导成矿作用的体现[8]。
微生物生命代谢活动可以促进矿物溶解、也可以改造矿物。在有氧环境中,微生物直接氧化矿物中的元素(如硫、铁等),从而获得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例如,微生物通过氧化黄铁矿,促进其溶解并形成酸性很强的酸性尾矿水,大量伴生重金属元素(如Cu2+,Pb2+,Zn2+等)随之被释放。这一过程会对自然环境产生酸化和重金属污染,也可被用于开发利用低品位重金属矿和回收利用矿山废渣,从而增加经济效益[9]。
在无氧环境中,微生物可以还原矿物中可变价态的金属元素,同时氧化降解有机质来获得能量和营养,从而形成新的矿物[10]。例如,异化铁还原菌Shewanella能够在常温常压下经两周的时间还原蒙脱石矿物中的结构铁、造成蒙脱石结构崩塌,从而形成伊利石,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学术界早前对于蒙脱石—伊利石转化为高温(300~350℃)和高压(100个大气压)地质过程的固有认识[11]。
此外,微生物代谢产物中含有有机酸和胞外聚合物等物质,可以改变环境的pH值和氧化还原电位,从而造成矿物溶解和微量元素释放。例如,土壤中的解钾细菌,可以通过分泌胞外物质作用于含钾矿物(如钾长石等),使矿物中的钾释放出来,微生物得到了其生长所必须的钾元素;同时这一过程也为土壤提供了重要的钾源,改善土壤肥力。另外也有一类能够溶解碳酸盐岩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通过产生碳酸酐酶溶蚀灰岩和白云岩,从而促进碳酸盐岩溶地区土壤形成[6]。
微生物矿物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很多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其中包括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土壤、沉积物以及地下水的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污染对人类和环境危害巨大,微生物和矿物相结合是去除该类污染的有效方法。首先,微生物和矿物本身巨大的比表面积可以吸附一部分污染物;其次,微生物对矿物的改造带来的晶体缺陷、负电荷等特征使金属元素可以通过元素替代、静电引力等进一步固定在矿物上得以去除;最后,对于变价的重金属和放射性核素污染,如铀、铬、砷等,这些元素不同的价态迁移能力和毒性差别巨大,例如,六价铀在水中溶解度很高,而四价铀形成沥青铀矿(UO2)以固体形式存在。因此,通过加入营养物质等方法刺激具有金属氧化还原功能的微生物活性,将重金属或放射性核素转变为不溶价态沉淀析出得以去除,是修复重金属污染和放射性核素污染的经济有效的方法[12]。例如,为了防止固态的污染物被微生物再次氧化或还原释放造成二次污染,可以采用微生物―黏土―重金属(或放射性核素)的三元体系。简而言之,黏土结构中的铁元素被微生物氧化还原后能够促进部分重金属的氧化还原反应,加快污染去除效果;另一方面,黏土层间结构及剩余电荷能够有力的吸附金属污染物,使污染物被包裹在不透水的黏土颗粒中,从而防止了污染物的二次释放[13]。
2 有机质降解及有机污染修复
由于工业发展,大量人工合成的有机物(如有机农药、增塑剂及塑料用品、除污剂、洗涤剂、芳香剂、染料、涂料、医用药物、表面活性剂、食品添加剂等)被广泛投入使用,尽管对工农业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但其对自然环境生态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这些人工合成有机物原先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因此有效降解循环路径缺乏,导致其在自然环境中大量积累,甚至进入食物链,危害动植物和人类的健康。例如,部分有机农药和增塑剂等具有内分泌激素活性,导致人类和野生动物雄性雌性化、生殖能力低下、生殖行为异常等。通常来说人工有机物的降解方式主要分为生物降解、光化学降解、化学降解和热降解等。所谓生物降解是通过生物的作用将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无毒或低毒化合物,并最终降解为水、CO2和矿物质的过程,相对于物理、化学降解技术,生物降解具有高效、彻底、无二次污染的优势。微生物由于生存能力强,易发生突变和具有强大的代谢多样性,对层出不穷的各类合成有机物的降解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微生物对合成有机物的降解方式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微生物直接作用于有机物,其实质是酶促反应,包括水解、脱卤、氧化、硝基还原、甲基化、去甲基化、去氨基等作用,主要是微生物本身含有或因基因重组、改变产生可降解该有机物的酶系基因。例如多数有机氯农药为卤代有机物,残留时间长,毒性危害大,脱卤往往会降低卤代脂肪族化合物的毒性,并且脱卤反应通常是卤代有机物矿化过程中的起始步骤和关键步骤。微生物可以分泌脱氯化氢酶、水解酶和脱氢酶等,催化卤代有机物脱卤[14]。另一类是微生物的活动改变了微环境功能从而间接促使有机物降解,包括:①以有机物作为生长基质将其分解;②在有可利用碳源存在时分解代谢其原来不能利用的有机物;③在同一环境中的微生物联合代谢某种有机物。例如多环芳烃(PAHs)的微生物降解。多环芳烃是指2个或者2个以上的苯环稠合在一起的一类化合物,是有机质不完全燃烧或高温裂解的副产品,多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有些PAHs具有强烈的毒性,对微生物生长有强抑制作用。然而有些微生物可以在PAHs的诱导下分泌单加氧酶和双加氧酶,将PAHs氧化为能被微生物用于合成细胞蛋白的中间物质[15-16]。
3 极端环境微生物
自然环境中的普通生命体对环境的适应具有一定范围,这个范围的上限或者下限就是生命的极限。超过生命极限条件的环境就被称之为极端环境,如:盐湖(盐度)、热泉(高温)、冰川及冻土(低温)、酸性尾矿水(极酸)、碱湖(强碱)、深海(高压、贫营养、缺氧、少光等)、地下深部(无光、缺氧、高压、高温、高盐、高辐射、贫营养等)、沙漠(缺水、紫外辐射强烈、贫营养等)等环境。尽管这些环境对普通生物来说无法承受,在这些极端环境中却栖息着许多微生物[17],这些微生物就被称为“极端环境微生物”。地质历史早期地球上以及地外星球上具有很多高温、高盐或冰冻环境,因此研究这些现代极端地质环境中的微生物生命活动过程对于揭示地球早期生命、生命起源以及探索地外星系生命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本文将简要说明盐湖、热泉、冻土和地下深部等典型极端环境的微生物分布、生理特征及潜在应用。
盐湖是典型的高盐极端环境。这些高盐湖泊环境栖息着大量嗜盐微生物,目前发现的嗜盐微生物主要有以下几类[18]:非嗜盐微生物:最适生长盐度即氯化钠浓度<0.2 mol/L;弱嗜盐微生物:0.2~0.5 mol/L;中等嗜盐微生物:最适生长盐度0.5~2.5 mol/L;极端嗜盐微生物:最适生长盐度2.5~5.2 mol/L;耐盐微生物:最适生长盐度0.2~2.5 mol/L。嗜盐微生物和耐盐微生物适应盐度的机制主要有两种机制[19]:①通过胞内积累高浓度钾离子来对抗胞外的高渗环境;②通过细胞内累积小分子有机物(如甘油、甜菜碱等)来抵御高渗透压。大部分微生物采用第二种抗盐方式,只有部分极端嗜盐古菌和少数耐盐细菌采用第一种适盐机制。因此,微生物在高盐湖泊生存,能量代谢非常关键。因为微生物需要足够的能量合成有机小分子抵御盐度渗透压[20]。在食品行业、医药与化妆品、生物电子、生物材料、高盐废水处理和生物能源方面,嗜盐微生物具有广阔和现实的应用价值[21]。
热泉是典型的陆地高温环境。在热泉环境栖息大量嗜热微生物。根据最适生长温度可将嗜热微生物划分为三大类[19]: ①兼性嗜热微生物:最适生长温度可在55 ℃以上或者在常温生长;②极端嗜热菌:最适生长温度在65 ℃以上,而且最高生长温度超过75 ℃及最低生长温度超过40 ℃;③专性嗜热菌:最高生长温度超过55 ℃,最低生长温度在40 ℃左右。微生物适应高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22]:①细胞膜高温适应机制:细菌主要通过增加磷脂分子中磷脂酰烷基链的长度,磷脂分子中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和异构化支链的比例来提高细胞膜热稳定性;古菌则依靠增加环戊烷结构的数量提高细胞膜的机械强度,降低细胞膜的流动性来提高热稳定性;②核酸分子高温适应机制:通过胞内的DNA反解旋酶、一些带正电荷的蛋白质、聚胺类物质以及高浓度的钾盐来维持胞内DNA分子维持热稳定性;③蛋白质分子高温适应机制:通过稳定蛋白质非保守结构来提高整个分子的稳定性;④代谢产物和辅酶高温适应机制:通过快速合成或替换热稳定性较差的代谢产物(或辅酶)来维持细胞高温生理代谢。热泉是嗜热微生物资源宝库,这些微生物可以应用于生物能源,医疗、冶金以及环境修复等方面。因此,开发嗜热微生物资源具有重要工业应用价值。
冻土环境是典型的低温环境,主要分布于地球两极、高山、高原、冰川等地区。生活在这种冷环境的微生物被之为低温微生物。根据其温度生长范围,我们可以将低温微生物划分为四大类[23-24]:①专性嗜冷菌:最适生长温度<15 ℃,上限生长温度<20 ℃和下限生长温度<0 ℃;②兼性嗜冷微生物:能在<5 ℃的温度条件下生长;③极端嗜冷微生物:最适生长温度>-2 ℃,在>10 ℃的温度条件下不能生长;4)耐冷微生物:最适生长温度>15 ℃,且能在0~5 ℃条件下生长。嗜冷微生物适应低温环境的方式主要是增加细胞膜的流动性[24]。例如:增加不饱和脂肪酸比例、缩短酰基链长度、增加脂肪酸支链的比例和减少环状脂肪酸的比例等。嗜冷微生物产生多种嗜冷酶,这些酶在低温条件下仍能保持较高的催化活性。嗜冷酶目前已经广泛地应用于食品、纺织和医药等行业,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大陆地下深部具有多种极端条件(如无光、缺氧、高压、高温、高盐、高辐射、贫营养等)。尽管环境极端恶劣,但是仍存在多种多样的微生物。这些地下微生物仍在发生生命代谢活动。比如:金属还原微生物存在于沉积盆地和陆地热液的深层岩石环境中,由于地下深部厌氧、贫营养环境,金属还原微生物只能通过氧化或还原深部地下岩石中的金属元素(比如铁、锰等)获得能量,从而维持生命[25]。另外,在浅层地下还生存着一些异养微生物,主要通过发酵获得能量。在沉积盆地地下水含水层,由于流体迁移带来大量的有机质,致使大量异养型细菌存在,如硫酸盐还原菌、产甲烷菌、常温和嗜热的发酵微生物和异养铁还原菌等[26-27]。此外,地层中的氢气也可以作为能源物质保障岩石空隙的微生物生存,如硝酸盐还原菌、锰和铁还原菌、硫酸盐还原菌和产甲烷菌等[28]。
4 地质记录中的微生物-地质环境协同作用
较于宏体生物,微生物更能敏锐地响应气候―环境条件变化[29-30]。在地质记录中,微生物有机大分子可以记录微生物―气候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通过研究微生物有机微生物大分子构成及分布,可以重建地质记录中的古环境气候变化的信息。其中,微生物细胞膜类脂化合物和脱氧核糖核酸分子(DNA)较为常用的用于古环境气候变化研究的生物有机大分子。
研究较多的微生物细胞膜类脂化合物是甘油二烷基甘油四醚类化合物(Glycerol dialkyl glycerol tetraethers,简称GDGTs)。GDGTs是一类比较稳定的微生物有机生物大分子,易于保存在沉积地质记录中。不同微生物物种具有不同的GDGTs构成;随着环境变化,同一微生物物种会调节自身细胞膜GDGTs的构成。因此,由微生物产生的GDGTs构成分布能够很好地指示气候环境变化。通过对保存在地质体中这些大分子化合物的分析,可以定性乃至定量重建古气候和古环境变化的历史。目前,研究学者已建立了一系列的基于GDGTs组成的古气候代用指标,成功地用于重建海(湖)古水温和pH、古海拔、古土壤湿度、古盐度等研究[31]。
DNA记录着生物的遗传信息,通过分析地质记录古微生物DNA遗传进化信息,恢复古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构成,进而根据古生物群落变化特征,可以重建地区性的古环境生态演化。近年来通过研究地质环境记录中的古生物群落,大大提高了我们对古生物生态环境(尤其是那些没有大化石留存的地质环境)的认知水平[32-33]。在以古微生物DNA分子手段研究古气候环境变化方面,营光和严格需氧生长的微生物功能群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真核微生物和单细胞藻类为营光生长的微生物,它们生存依赖光能。在没有光的深部沉积物中发现它们的DNA信息,说明这些DNA片段来自历史时期的藻类残体。国内外学者根据真核生物和藻类这一生理特点,用真核微生物或单细胞藻类的古DNA信息,成功地获悉黑海古盐度和冷、干气候变化[34-35]和库赛湖古盐度、温度和营养状况[36]。氨氧化古菌是需氧古菌。它们不能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下生存。如果在深部沉积物中发现氨氧化古菌的DNA信息,可能说明它来自历史时期的微生物残体。依据这一特点,有学者成功地恢复了青海历史时期的湖泊营养状况[37]。因此,结合使用沉积记录中的微生物有机大分子指标,可以有效地恢复古气候环境变化和微生物生态信息。
5 总结
微生物虽然个体微小,却是地球环境演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协调员”,在地球生源元素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微生物科学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和应用,将会使地质微生物交叉科学研究更具生命力,为用微生物学技术手段解决地球科学问题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6年2月19日收稿)
[1] WHITMAN W B, COLEMAN D C, WIEBE W J. Prokaryotes: The unseen majority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8, 95(12): 6578-6583.
[2] BARDGETT R D, FREEMAN C, OSTLE N J. Microbial contrib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through carbon cycle feedbacks [J]. ISME Journal, 2008, 2(8): 805-814.
[3] SINGH B K, BARDGETT R D, SMITH P, et al. Microorganisms and climate change: terrestrial feedbacks and mitigation options [J].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2010, 8(11): 779-790.
[4] DONG H, LU A. Mineral-microbe intera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mediation [J]. Elements, 2012, 8(2): 95-100.
[5] 林巍, 田兰香, 潘永信. 趋磁细菌磁小体研究进展 [J]. 微生物学通报, 2006, 33(3): 133-137.
[6] 连宾. 矿物—微生物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地质微生物专栏文章评述[J].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2014, 6: 759-763.
[7] DENG S, DONG H, LV G, et al. Microbial dolomite precipitation using sulfate reducing and halophilic bacteria: Results from Qinghai Lake, Tibetan Plateau, NW China [J]. Chemical Geology, 2010, 278(3/4): 151-159.
[8] STAL L. Cyanobacterial mats and stromatolites [M]//WHITTON B, AND POTTS M. The Ecology of Cyanobacteria. Berlin: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2: 61-120.
[9] RAWLINGS D E. Heavy metal mining using microbes [J]. Annual Review of Microbiology, 2002, 56(1): 65-91.
[10] MYERS C R, NEALSON K H. Bacterial manganese reduction and growth with manganese oxide as the sole electron acceptor [J]. Science, 1988, 240(4857): 1319-1321.
[11] KIM J, DONG H, SEABAUGH J, et al. Role of microbes in the smectite-to-illite reaction [J]. Science, 2004, 303(5659): 830-832.
[12] 董海良, 于炳松, 吕国. 地质微生物学中几项最新研究进展[J]. 地质论评, 2009, 4:552-580.
[13] BISHOP M E, GLASSER P, DONG H, et al. Reduction and immobilization of hexavalent chromium by microbially reduced Febearing clay mineral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4, 133: 186-203.
[14] 李安章, 邵宗泽. 微生物卤代烷烃脱卤酶研究进展 [J]. 微生物学报, 2015, 55(4): 381-388.
[15] 刘世亮, 骆永明. 多环芳烃污染土壤的微生物与植物联合修复研究进展 [J]. 土壤, 2002, 34: 257-265.
[16] 张银萍, 王芳, 杨兴伦, 等. 土壤中高环多环芳烃微生物降解的研究进展 [J]. 微生物学通报, 2010, 37: 280-288.
[17] ROTHSCHILD L J, MANCINELLI R L. Life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J]. Nature, 2001, 409 (6823): 1092-1101.
[18] 宁卓, 张波. 嗜盐菌的研究进展及应用 [J]. 苏盐科技, 2007, 1: 31-32.
[19] 陈骏, 连宾, 王斌. 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及其生物地球化学作用 [J].地学前缘, 2006, 13(6): 199-207.
[20] OREN A. Thermodynamic limits to microbial life at high salt concentrations [J].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1, 13(8): 1908-1923.
[21] OREN A. Industrial and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of halophilic microorganisms [J].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2010, 31(8-9): 825-834.
[22] 曾静, 郭建军, 邱小忠, 等. 极端嗜热微生物及其高温适应机制的研究进展 [J]. 生物学技术通报, 2015, 31(9): 30-37.
[23] 王红梅, 吴晓萍, 邱轩, 等. 微生物成因的碳酸盐矿物研究进展[J].微生物学通报, 2013, 40(1): 180-189.
[24] 周璟, 盛红梅, 安黎哲. 极端微生物的多样性及应用 [J]. 冰川冻土, 2007, 29(2): 286-291.
[25] SLOBODKIN A I. Thermophilic microbial metal reduction [J]. Microbiology, 2005, 74(5): 501-514.
[26] MAGOT M, BASSO O, TARDY-JACQUENOD C, et al. Desulfovibrio bastinii sp. nov. and Desulfovibrio gracilis sp. nov., moderately halophilic,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isolated from deep subsurface oil fi eld wate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2004, 54(5): 1693-1697.
[27] VAN HAMME J D, SINGH A, WARD O P. Recent advances in petroleum microbiology [J]. Microbi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Reviews, 2003, 67(4): 503-549.
[28] AMEND J P, TESKE A. Expanding frontiers in deep subsurface microbiology [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05, 219(1/2): 131-155.
[29] 谢树成, 黄咸雨, 杨欢, 等. 示踪全球环境变化的微生物代用指标[J]. 第四纪研究, 2013, 33(1): 1-18.
[30] DONG H, JIANG H, YU B, et al.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 on microbial ecosystem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NW China [J]. GSA Today, 2010, 20(6): 4-10.
[31] 王欢业, 刘卫国. 青藏高原微生物甘油二烷基甘油四醚类化合物古气候指标研究进展 [J]. 盐湖研究, 2016: 待刊.
[32] WILLERSLEV E, CAPPELLINI E, BOOMSMA W, et al. Ancient biomolecules from deep ice cores reveal a forested southern Greenland [J]. Science, 2007, 317(5834): 111-114.
[33] WILLERSLEV E, DAVISON J, MOORA M, et al. Fifty thousand years of Arctic vegetation and megafaunal diet [J]. Nature, 2014, 506(7486): 47-51.
[34] COOLEN M J L, SAENZ J P, GIOSAN L, et al. DNA and lipid molecular stratigraphic records of haptophyte succession in the Black Sea during the Holocene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09, 284(3/4): 610-621.
[35] COOLEN M J L, ORSI W D, BALKEMA C, et al. Evolution of the plankton paleome in the Black Sea from the Deglacial to Anthropocene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3, 110(21): 8609-8614.
[36] HOU W, DONG H, LI G,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hotosynthetic plankton communities using sedimentary ancient DNA and their response to late-Holocene climate chang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J]. Scienti fi c Reports, 2014, 4: 6648.
[37] YANG J, JIANG H, DONG H, et al. Sedimentary archaeal amoA gene abundance reflects historic nutrient level and salinity fluctuations in Qinghai Lake, Tibetan Plateau [J]. Scienti fi c Reports, 2015, 5: 18071.
(编辑:段艳芳)
Microbes—Coordinators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s
JIANG Hongchen①, HUANG Liuqin①, FENG Can①, YANG Jian①, DONG Hailiang②
①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②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Interactions between microbes and environment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which focuses on the coordinations between microbes and Earth environments including microbe-mineral interaction, microbial bioremediation, microbes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 microbial ecology.
microbial function, Earth environment, microbe-mineral interaction, microbial bioremediation, microbe in extreme environment, ancient microbe
10.3969/j.issn.0253-9608.2016.03.008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2CB82200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422208)资助
†通信作者,E-mail: jiangh@cug.edu.cn
- 自然杂志的其它文章
- 科学家合成“最小”生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