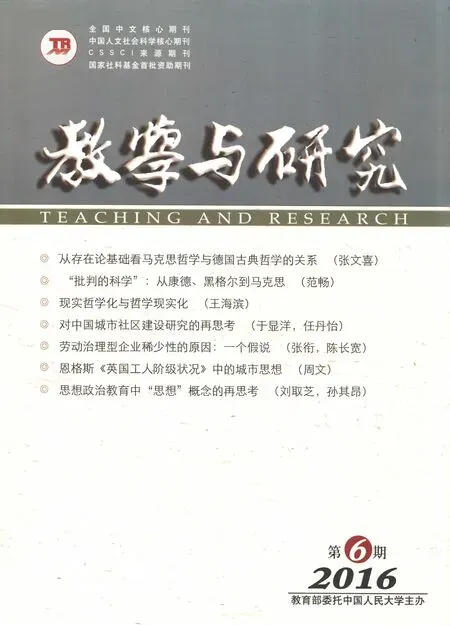从权利到正义:社会价值体系的“阿基米德点”及其旨归*
赵 威
从权利到正义:社会价值体系的“阿基米德点”及其旨归*
赵 威
社会价值体系;阿基米德点;权利;正义
在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中,权利是一个能撬动其他价值观的“阿基米德点”。权利能逻辑地推导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转化为民主、法治的制度安排,落实为人道、正义的社会目标。考察西方权利—正义观的历史生成及其价值旨归,从中西文化比较中加深对权利—正义价值的认识,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阿基米德曾有过这样的豪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对构建一个社会价值体系来说,也需要确定这样一个“阿基米德点”,它就是指能够逻辑地推演出其他价值观并把整条价值链贯穿起来的关键点或起始环节。中国政府曾庄严宣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1]如果我们要从这条价值链中确定一个“阿基米德点”的话,那么它就是人的“权利”(rights)。习近平在给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中指出:“实现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中国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推动各国人权事业更好发展。”[2]无论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还是马克思强调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权利”显然都是基础概念,以此为支点,可以撬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推进自由、平等的价值认同;落实民主、法治的制度安排;并最终指向正义、人道的社会目标。也就是说,肯定权利只是实现“人是目的”的前提条件,只有使权利符合正义所包含的公道、正确、合理、应得等规范,并辅以相应的制度保障才是实现“人是目的”的充分条件。本文将以权利这个“阿基米德点”为中心,考察西方权利—正义观的历史生成及其价值旨归。
一、古代西方在超验视野下 对权利与正义的探索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文明关于权利与正义的思想,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古希腊早期哲学思想的残本“都是关于正义、非正义及人权的”。[3](P24)在希腊文中,dikaion的意思是权利,dikaiosyne表示正义,可见正义内在地包含了权利;在拉丁文中,jus代表法律,justitia表示正义,“属于正义的东西我们称之为jus”。[3](P49)这说明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三者的顺序是:权利—正义—法律。柏拉图的《理想国》记载了苏格拉底反对“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之论,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做符合自己天性的事。柏拉图承袭了其师的观点,指出正义应该是正当地享有自己的东西和做自己的事情。[4](P3)这就把“正义”与人的正当“权利”联结起来。他还认为,正义与权利的实现既符合人的德性,又是国家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则明确指出,“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政治制度就是“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5](P109)他声称凡自然而平等的人,“应该分配给同等的权利……这才合乎正义。”[5](P167)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5](P138)为此,他称赞雅典民主政制“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指出“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5](P312)随后,罗马思想家西塞罗也指出,人人生而平等,都有资格享有某些基本权利;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利,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福利;国家之所以能把人们集合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就在于拥有法律,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可见,在“古典时期,法律与权利的含义是一致的,而正义是权利的另一表达词。”[3](P77)
然而,权利、法律和正义从哪里来呢?既然“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那么,以权利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正义就不能来自有政权私利的世俗统治者,只有超然独立的赐律者(Law Giver)——神或自然法,才能成为关照公共利益的正义之源。在荷马时代之前,神是希腊社会的价值权威。早期的希腊诗人赫西阿德借助神话表达了他的权利与正义思想,认为维护弱者的权利是宙斯正义的本质。随着“轴心时代”思想的觉醒,自然的发现成为权利、正义理论的来源。而所谓自然的发现,就是把人的自然权利追溯到社会的原初状态中,即对自然状态作出符合社会理性的解读。一般认为自然法思想源于希腊的斯多亚学派,但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已有自然法思想的萌芽,他认为,一切法律都是以神圣的、足以支持一切的唯一的自然法则为基础,它们最终都只是人类为了实现这一神圣法则而作出的努力。[6](P25)这已包含着人法应该符合自然法的思想。所以,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罗门说:“经由赫拉克利特……自然法作为一种自然的不变的法则,而所有人法均由其获得力量的观念,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7](P6)亚里士多德也说:“宇宙法则是自然法则,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现:自然正义与非正义确实是存在着的。”[8](P784)他还把权利定义为正义的标准,声称“作为正义标准的权利是调节政治交往的准绳。”[9](P192)现代学者弗雷德·米勒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自然、正义和权利》一文即揭示了亚氏的正义理论与自然、权利的关系。其后,西塞罗更明确主张“法是一种自然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认为国家的存在需依赖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它追求公共的目标,如果丧失了这个目标,国家就与强盗无异。他还强调,国家本身和它的法律永远要服从上帝的法律,或道德的或自然的法律——即超越人的选择和人的制度的更高一级的正义统治。也就是说,权利、正义皆被追溯到超验的上帝法律或自然法律那里去。
即使到了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神学家们仍然坚决主张权利、正义要符合公众利益就必须来自超验的神法或自然法。早期的神甫在评论《圣经》时,开始用jus来代表神的旨意,用自然法代表基本的戒律。“最终到14世纪,jus就指个人权利和主体权利了。”[3](P55)奥古斯丁认为,民众“是由对权利的共同承认,由利益的一致性联系起来的群体……没有真正的正义,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利。”[8](P802)正义具有彼岸世界的神性,对神之正义来说,世俗正义经常出错。[3](P56)因此,真正的正义应是完全超验的合乎逻辑的宗教推断的结果。[4](P9)托马斯·阿奎那则宣称:“实在的正义从属于自然的正义”,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假定“一件事本身违反自然权的,那么,人的意志就不可能使这桩事合乎正义。”他又说:“法律的首要的和主要的目的是公共幸福的安排”,[10](P105)如果“当权者把苛刻的法律强加在老百姓的头上……这样的法律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强盗逻辑!”[8](P786)可以说,这样的论断是发人深省的。
综观古代西方哲人的价值探索,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权利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起始环节,权利受理性和法律约束才能成为正义;正义既要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又要以超验的神法或自然法为依据,因为只有超然独立的神法或自然法才能摆脱统治者的私利而关照公共利益;自然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是上帝法与人定法的中介;国家是(为公共利益)达成社会契约的产物,违反神法和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这些思想曾构建了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法治制度,即使在封建的中世纪,人们仍坚持这样的政治理念:“封建主义是建立在有所限制的君主权这一思想上的。不管谁是统治者,封建主义反对绝对权威。封建政府被认为是法律统治的政府,不是人统治的政府。任何统治者,无论他的地位多高,无权随心所欲地把他的个人意志强加于他的臣民。”[11](P10)显然,这些深刻的观点是从来不懂质疑“王法”正当性的中国古人所没有的。也可以说,主张人民权利、追求社会正义,正是近代西方走向民主的理论资源和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
二、近现代西方在世俗化进程中 对权利—正义理论的拓展
近代以来,随着人的全面觉醒和世俗化进程的启动,哲人们对权利、正义的探索也与民主宪政理论及其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从深度与广度两方面拓展了对权利、正义的追求。
就深度而言,由于文艺复兴已吹响了人道主义的号角,思想家们也在摆脱神学羁绊的过程中推进了价值探索。英国的阿尔色修斯提出“共生”的概念,认为国家是“组织起来彼此合作以达致共同目标”的综合性的社会共同体,构成社会共同体的人类是共生的。他将正义定义为“共生的善德”。这就引出一种几乎是实证主义的正义观念,它根源于自然主义者对人的迫切需求的承认,[4](P58)承认迫切需要就要把它转化为权利。荷兰的格劳修斯亦企图把自然法世俗化,他说自然法即正义本身,是正当的理性准则。“自然法是固定不变的,甚至神本身也不能加以更改。”[12](P583)“格劳修斯的意思是,即使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假设:‘从自然人及社会需求考虑,推导出这些原则也是合理的。’”[13](P33)这就把自然法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了。
英国是经验主义哲学的故乡。霍布斯和洛克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虽说他们均以自然法作为其权利—正义思想的前提,但其主张却颇为不同。霍布斯虽然承认自然权利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的自由,但又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人对人像狼一样”的状态,人如果不放弃这种天赋的权利就不能和平地相处下去,因此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只好放弃自然权利,达成社会“契约”,建立有强制力的国家。于是在他那里,“权利渊源或基础不再是服从一些自然关系以及对‘最优政体’的哲学思辨或对神的戒律的解释,而是制约人的自然性。”[3](P77)他一方面承认人民是主权者每一行为的授权人,“所以他除开自己是上帝的臣民,因而必须服从自然律(自然法)以外,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决不缺乏权利。”[14](P165)另一方面又认为,正义意味着“必须有某种强制的权力存在。”[11](P109)君主国一旦按约建立,就永远将继承者的问题交给在位的国王根据其判断与意志处理了。洛克则反对霍布斯这种观点,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正义就是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和结合全社会的契约。他虽然仍把上帝作为正义的终极依据,但还是把重心放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在其名著《政府论》中,他也从权利与正义的关系来论述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及其宪政理论。这就是以个人权利本位为其宪政论的逻辑起点,主张人的权利先于政府权力。因此,他对政府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基于权利问题而依次展开的,正是缘于人们为了保障权利才需要建立授权政府、分权政府、限权政府。这样的限权政府只拥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无权侵入个人权利的领域。为了使正义能够实现,人必须在政治上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只有在宪政秩序中才是可能的。这就使超验的正义依据在经验的宪政中得以实现。洛克的契约论与分权说对卢梭和孟德斯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康德是“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倡导者。在卢梭所谓“道德良心”的影响下,康德坚持“一切道德的概念所有的中心和起源都在于理性,完全无待于经验。”[15](P28)由于他看到了纯粹理性的局限,故强调实践理性领域人有意志自由,并把他的政治学与法学理论建立在道德学说上。康德以罗马法关于自然、理性与正义三合一的原则作为法理论的起点,依据每个人的自由及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共存这一点来定义正义,认为正义是内在立法与外在立法据以联系的观念,其核心是内在的自由权利,它是一种(且是一种)依据人的理性属于每个人的原始权利。[4](P86)权利有自然的和取得的之分,自然权利首先是自由,即个人不受他人的专横意志的控制。为此,他把正义定义为“一个人的意志能够与他人的意志相协调的条件的集合。”[16](P167)而这样的正义只有在宪政秩序中才能实现,他既不像霍布斯那样美化国家,也不像洛克那样美化自然。他认为,自然状态是有个人权利但无分配正义的状态,与此相对的则是建立在有公民权利及分配正义之上的文明状态,在文明状态中人们通过法律共同执行正义的原则。在这种状态中,尽管人们牺牲了部分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但却获得了安全,实现了正义。所以桑德尔认为,近代道义论的自由主义中,“正义、公平和个人权利的概念占有一种核心地位,而其哲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康德”。[17](P1)
就广度而言,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自由、平等、权利、正义的价值观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广泛的传播。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率先肯定了公民享有请愿权、自卫权、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等权利。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政府。”[18](P66)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再次重申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人权,并宣称国家“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权的权力。”[18](P86)在这些思想的激励下,民主革命先后在欧美国家取得胜利,并日益向亚、非、拉国家与地区扩展。二战后,1945年《联合国宪章》“重伸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强调要“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促进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18](P177)随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又指出:“对人类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18](P218)这些宣言标志着以权利为轴心、以自由为基础、以正义为诉求的价值观已从学术走向社会并迈向全世界,这个进程至今仍未结束。
应该看到,西方古今权利思想虽然是一脉相承的,但其演进也包含着意义深远的转向:它从古代的自然权利推进到现代的公民权利,颠倒了个人与社会传统的先后关系。传统与中世纪的自然法表达了宇宙和其中的群体的权利秩序;而现代性解放了人的个性,将他从公民转化为个体。当思想家的社会理想通过民主革命从思想探索转化为政治实践后,框架性的奠基基本结束,现实正义又进入学术论争的视阈。其中,既有“分配正义”与“持有正义”的争锋,也有“承认正义”对“分配正义”的诘难,还有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较量。然而,除了侧重点不同和差异性解读外,各派在承认权利,崇尚自由、平等,宣扬民主、法治,坚持正义等原则方面并没有分歧。《认真对待权利》的作者德沃金就声称他与罗尔斯、诺齐克“行进在同一条路上。”[19](P317)
三、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加深对 权利—正义价值的认识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20](P1)中国政府也曾宣布:“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21]从“正义”被认可为“首要价值”这个意义上说,正义被称之为“诸价值的价值”和“权衡和估量各种价值的定律”是当之无愧的。[17](P20)源自西方的权利、正义、民主、法治价值观之所以能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同与它的文化“软实力”是分不开的。如果把它放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可以加深对其合理元素的认识。
首先,对“权利”的肯定是撬动整个价值体系的支点。因为如果不坚决肯定人的权利的正当性和优先性,人民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但如果不把权利追溯到自然赋予那里,它就成为统治者的“恩赐”;如果权利的定义与限度由政权界定,它就会被用来为自身的统治利益服务。尽管自然法在经验上无法证实,但人的理性可以推断: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即享有自然权利,如生存权、自由权、自卫权、财产权等。即使这些权利在自然状态下不完美或无保障,但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发展这些权利,人们才组成契约政府,保护自身利益,使自然权利在社会状态(国家)下转化为公民权利。由于自然权利先于公民权利,可见它并非来自政府的恩赐,所以政府也无权把它从人民那里夺走。这种源自自然法与契约论的权利观和国家观显然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盲区。从文献上看,人民应该享有权利这种主张从未进入古代政治精英、思想精英的视野,无论是个人权利、社会权利或政治权利尽皆阙如。孔子声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2](P2487)“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2](P2521)人民既无知情权亦无议政权。《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23](P1463)子妇既无经济自主权也无爱情自主权。从社会的角度看,“三纲”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父、夫被视为臣、子、妻之“天”,天下之臣子、妇女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没有任何个人尊严和权利。汉代御用学者董仲舒公然宣称:“尊压卑也,固其义也。”[24](P789)不仅尊者视为当然,卑者亦不知抗议。直到清末民初,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学贯中西的严复才指出:“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25](P442)他还看到国人没有权利与古人不知“国”为何物直接相关,他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耳!”[25](P401)由于没有以捍卫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国家,没有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奴婢不管如何“易主”仍然没有权利。所以,马克思抨击专制主义“使人不成其为人。”[26](P65)没有权利确实“不成其为人”。
其次,对正义作出超验的假设是古代西方价值探索的闪光点。如同权利不能来自政权那样,正义的坐标也必须超然独立,这是西方从古至今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因为当权力高地被王权占据时,如果终极价值再由统治者定义,社会正义就会被扭曲为“权力正义”。如果以上帝的名义代表道义,神学正义便可超然独立地拷问鞭挞俗世,对抗王权,于是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上帝就成了古代的“无知之幕”。但是,当权力高地已被民权占有时,神学正义便不再是绝对必要的假设,社会理性、人民意志就是正义的坐标。现实中的正义虽不完美(上帝正义由于是假设的,所以才能尽善尽美),但它可以在理想与现实的互动中逐步靠拢理想。借助罗尔斯所谓“无知之幕”,社会正义也可以超然独立于任何特定对象。其实,中国古人也有“义自天出”的思想,但自从五帝时代“绝地天通”后,统治者便垄断了神权,实现了真正意义的政教合一。《易·观》明确指出,“圣人以神道设教”是为了使“天下服”。虽说中国古人也把上天看作最高正义的象征,由于中国缺乏西方教会那样独立的实体机构来代表天意,而是使政权与神权皆由帝王一手掌控。当天意的诠释权掌握在君主手中时,他便可以“口含天宪”、“伪假天威”,把自己的统治利益包装为上天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正义也就沦为帝王自我定义和谋利的“已知之幕”。当董仲舒鼓吹“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时,[24](P784)谁都知道只有“屈民伸君”才是真的,而“屈君伸天”根本就是假的。因此,不打破权力垄断与真理垄断的胶结,古人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
再次,对政权合法性与法律合理性的追问是西方走向民主的动力。古希腊时代已有“僭主”统治非法的主张,《雅典政制》指出:“任何人为了达到僭主统治的目的而起来作乱者,或任何人建立僭主政治者,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都应被剥夺公民权利。”[27](P20)否定僭主统治的依据便是主权在民的理论。西塞罗曾针对那种认为“一切风俗和国法都是天然合乎正义”的观点,反驳道:“独裁者的法令也是天然合乎正义的吗?”[8](P795)可见掌握权力不等于代表正义,颁布法令不等于其法合法(因为“恶法非法”)。即使在中世纪,思想家们仍坚称法律的合法性必须来自神法和自然法。阿奎那认为,一切权力均来自上帝,各种法律都应该来自上帝的永恒法。可见,未得到上帝授权的政权是不合法的,不符合永恒法的人为法是不合理的。中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西利更明确主张,唯一合法的主权者是人民,人类立法者就是人民,全体公民。[28](P304)这种主张便是近代西方立法权属于人民、立法机构来自民选的理论渊源。相比之下,中国古人几乎不懂质疑“王法”的合法性和“胜者为王”的正当性,古人对开国之君虽然有过“君权神授”“天命有德”这种政权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认可,对继体之君也以“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礼制作为继位合法性的依据。《慎子·逸文》曰:“法虽不善,犹逾于无法。”即使这种立贵不立贤的制度并不合理,它终究是一种规矩方圆。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也是可以戏弄践踏的,理论上它有“子以母贵”的礼制规定,现实上又有“母以子贵”的灵活变通,更有“成王败寇”的强权逻辑,任何人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夺权成功,马上他就变为“天子”“圣上”。这使中国古代的权力斗争只问成败不认是非。法律也是这样,古人虽然没有立法权属于人民的主张,但对法律的来源与性质也有过理性的探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道家。《文子·上义》指出:“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乎人心。”《鶡冠子·环流》又曰:“是者,法之所与亲也;非者,法之所与离也。”可见法的价值尺度就是“义”与“是”,它来源于“众适”、“人心”。《管子·心术上》又提出:“法出于权,权出于道。”它看到法固然是由掌权者制定的,但它必须来自“道”。这与西方关于人为法必须以永恒法为终极依据的主张是相似的。但是,在帝王专制的历史条件下,“法出于权”是实,“权出于道”是虚,所以“人为法”最终还是沦为“帝王法”。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是“一家之法”,因此是“非法之法。”但除他之外,偌大中国鲜有人有此见识。
最后,对社会系统的建设是落实权利推进正义的实质步骤。马克斯·韦伯曾经认为,儒家的道德理性缺乏实现的技术手段。可见,价值要转化为事实还需要社会系统的协同推进。它要靠政治贯彻、法律捍卫、道德内化、经济落实,它们均是保障权利、实现自由、维护正义、完善人性、促进发展的工具,而贯穿其中的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人道(humanity)。赫尔德说:“没有一个比‘人道’这个词更高贵的词可以来证明人的使命”。[29](P78)在他看来,人道就是对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尊重,一切事物的价值都是根据它们与人道的关系而确定的。人道就是价值体系的开展和社会系统的落实。然而在古代中国,由于“天下为公”的理想与“天下为家”的现实无法协调,人道、正义的价值理想也服从于帝王政治的需要。《礼记·大传》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这个“圣人”是指帝王;这个“人道”则是“序尊卑,别贵贱”的礼制。《礼记·丧服小记》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礼记·丧服四制》则曰:“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所以,孔子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30](P2124)荀子声称“维齐非齐”,均在强调要使统治秩序整齐就必须名分不齐,因为“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31](P401)而对于尊贵对卑贱的统治是不问是非的:“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彩,必践于地。”[32](P505)君主再坏也应尊于上,臣下再好也要踩于下。“故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32](P466)这种非理性的主张是以整个社会系统为依托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都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虑。马克思本人虽然对资本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但是当他把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放在历史理性的天秤中衡量时,还是肯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然而,即便我们看到西方权利—正义思想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仍要充分认识其实践上的弊端,因为它们实行的正义终究属于“弥补性正义”,而不是“制度性正义”、“结构性正义”。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所以由私有制带来的权利在现实中必定是有差别的,贫富悬殊带来的不公平非正义也不可能靠自身的改良来克服,因此,“制度性正义”、“结构性正义”只有在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但这并不等于在这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即使不完美的西方权利—正义思想及实践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其实,马克思并不泛泛地批评人权,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洛赫在评论这一点时说:“他(指马克思)也许对非现实的人权感到失望,但绝不会对人权的目标失望。”“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自然法的一些长处……社会主义可以举起古代基本权利的旗帜。”[3](P174)
[1] 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N].人民日报,2007-03-17.
[2] 习近平致信祝贺“2015北京人权论坛”开幕[N].人民日报,2015-09-17.
[3] 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M].郭春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4] 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6] 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和哲学[M].姚中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7]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 莫德玛·阿德勒.西方思想宝库[M].周汉林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9] 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M].蔡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0]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1]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M].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2]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C].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3] 道格拉斯·F·凯利.自由的崛起[M].王怡等译.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14] 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5]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M].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6] 康德著作全集[M].第6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7] 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8] 辛向阳主编.千世箴言——影响人类的十大宣言与宪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19] 布莱恩·麦基编.思想家:与十五位杰出哲学家的对话[C].周惠明,翁寒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20]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1] 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首要价值——温家宝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N].新华日报,2009-02-03.
[22] 论语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3] 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4] 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5] 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8] 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9] 卡岑巴赫.赫尔德传[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0] 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1] 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2] 韩非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敖 华]
From Rights to Justice:The “Archimedes Point” in the Social Value System and Its Purpose
Zhao We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social value system; Archimedes Point; right; justice
Right is an “Archimedes Point” which can leverage other values in the value system of human society. The right can logically deduce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transform into the system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s well as implementing the social goal of humanity and justice.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view of right and justice and its the value purpose, and to reflect the deficiency in such field in Chinese histo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in China.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资助项目·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项目“罗尼·佩弗的社会正义论研究”(项目号:15SKGC-QG01)的阶段性成果。
赵威,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福建 泉州 36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