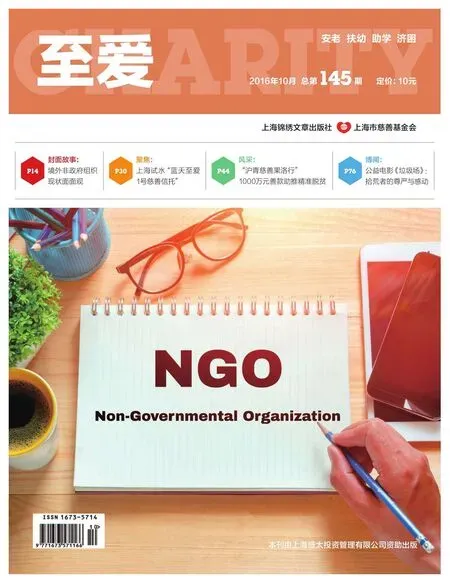走出误区—慈善不只是“一腔热血”
文|熊颖琪
走出误区—慈善不只是“一腔热血”
文|熊颖琪
伴随着中国社会财富的逐步积累,公益与慈善事业的话题正进入寻常百姓家。
然而,目前慈善事业在中国属于起步阶段,由于自身发展的不健全,以及观念传播的滞后,百姓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存在不少误区。
一个郭美美,让红十字会“受尽委屈”;一个王杰,打着助学的旗号,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性侵多名未成年女学生;一场网络“逼捐”,让马云发出“不能愚蠢地捐了”的感慨。
让我们和学者与行业专家一起为您破解重重认知误区,畅想慈善发展的良性轨迹。
误区一:做慈善就该是活雷锋?资金是慈善的前提与保障
在人们过往的认知中,与做慈善相对应的说法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甚至“倾囊相助”。财产似乎与捐助者走向了对立面。
北京大学社会责任研究所所长崔志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定数额的财富是捐赠人与捐赠机构确保慈善行为良性运转的基石。他解释道:“社会个体往往在‘心有余,力够足’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到慈善捐助行为中来,这也是一种良性的社会生 态。”
对于慈善机构,其内部人员属于专业化的工作人员,必要的薪酬保障不仅能给他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更能保证专业化慈善行为的延续。
误区二:只要有热情就能参与?专业性是慈善的根本依托
中国的志愿者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短暂的时间内吸引了大批人加入。青年人乐于参与到重大事件中,奉献自己极大的热诚,并以此为荣耀。但由于缺乏预见性和专业性,近年来,在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救援或者骨髓移植等生命接力的志愿行动中选择“中途退场”的志愿者时有出现。最终,不仅延误了救助的时机,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中心儿童事业部主任姚世洪对记者说:“热情是做慈善项目的必要条件,但慈善行为本身更需要专业性做依托。慈善机构应当培养并引导个体学习必要的专业知识,并能以机构内部专业化的操作流程来扶持一项慈善项目的顺利进行。”
误区三:多捐钱就能办好慈善?算清流水账才是慈善关键
募捐,在人们的意识里,是做慈善最为重要的事情。然而,专家告诉我们,比“怎么捐钱”更难的其实是“怎么花钱”。
姚世洪向记者介绍,社会捐助行为往往包括定向捐赠和非定向捐赠,来自社会更广泛的捐赠往往属于后者。这就对慈善组织的“花钱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崔志如表示,在发达国家,慈善机构往往分为仅提供慈善项目筛选和募款的支持性机构、仅完成后续项目落实的执行性机构和慈善基金托管机构。在中国,目前这三块内容往往涵盖在一个组织内。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任晓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慈善组织财务运作大致包括内部人员机构的运作成本以及善款的去向、效益。慈善组织财务并非国家机密,属于可以公开的信息,只有让全部的数据能够被公众可获得、易获得、能质询,才是实现了个人与机构的平等,有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
崔志如补充道:“现代慈善比起善款的堆砌,更讲究运转效率。国际慈善项目的评估指标包括资金的使用效率、减贫效果和项目的可持续性。高效的资金运转不仅可以加快扶贫进程,更能提高再筹款的速度,实现整体良性的新陈代谢。”
误区四:慈善宣传不低调即炒作?善用媒介才能够效益倍增
中国的传统观念讲究“做好事不留名”“润物细无声”,对于过于高调的慈善行为往往充满了争 议。
崔志如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案例,2011年由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在运行初期通过微博、自媒体的宣传,从民间获得了几千万的捐助。随着其传播渠道的迅速扩张,又迅速拿到了政府103亿元的支持资金,如果没有信息的传播,这是很难想象的。崔志如表示,现代化的慈善行为必须善用媒体善用传播,在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捐助总额远远高于知名人士,这其中,媒介传播的力量功不可没。
姚世洪还提到了“郭美美案”。他表示,唯有慈善组织自身和社会媒体客观、冷静,并真正公开地还原事件真相,才能重塑一项社会事业的形象。新时期,媒体的运用,机遇与风险并存,这同样对慈善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
误区五:公众为慈善设衡量标尺?少些猜忌将评判诉诸专业
在如今的中国,慈善正成为名人圈里的时髦事儿。不少艺人、企业家、运动员、文化名人参与其中,他们的慈善动机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出现了不少的负面猜忌。
崔志如表示,从国际研究成果来看,个人参与慈善的心理因素异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能排除部分名人参与慈善是受社会舆论施压或者从众心理使然,但应该更专注人们行善的结果,而非过于追究其动机。
任晓兰补充道,“慈善的行为是否涉及动机不纯或者真的存在法律与道义的问题,应当交由公正的裁判机构进行鉴定,如果涉及违法行为,自有法律论处。例如广西百色助学网一案中,涉嫌假借慈善外衣行不法之事的负责人王杰已经受到了法律的追究。”
针对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名人被“逼捐”现象,崔志如表示,这是公众对于慈善行为实施者和慈善定位的误读造成的。他解释道,慈善行为分为两种,以宗庆后和马云为代表的属于发展式慈善,它在于挖掘潜能;还有一部分热点事件中参与的慈善行为属于救助式慈善。每一个慈善家和慈善组织都有着自己的专业定位和救助方向,专业化的发展也有利于一个慈善组织的长期行为。公众非专业眼光的道德审判,不仅破坏了舆论氛围,更是对慈善事业的伤 害。
(转载自《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