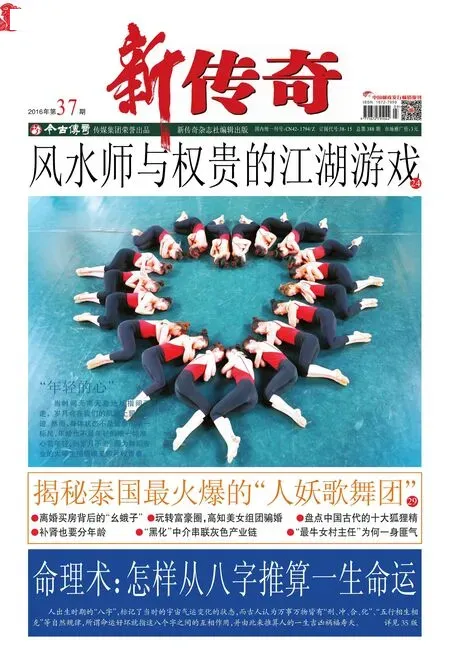用中国“柔力量”取代西方软实力
用中国“柔力量”取代西方软实力
从边缘迈向“全球治理”中心舞台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G8一再邀请中国参与,但是中国始终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一直到2003年,G8把原来仅邀请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与,提升为邀请最高首脑参与,胡锦涛主席也是从那时开始出席峰会的。
实事求是地说,即使参与了G8的有关会议,对于参加全球治理实践,中国还是一个后来者。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他的《战略对话》这本新书中证实,中国是在2005年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的时候,才“比较公开地讲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也比较放松地和美国人讨论国际体系问题,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这之前,我们不大用‘国际体系’这个词。”
当时,西方急于要求中国等新兴国家参与G20,有着各种动因。除了世界经济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美不得不通过吸纳发展势头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决策,推动分担风险之外,在面临气候变化等一类新挑战时,西方也急于想通过这类新体制,把当时最大的排放国——中国拉进来,以成制约之势。后来,经过了西方大国之间的密切磋商,也征得了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同意,最终形成了G20峰会机制。
在杭州峰会前,中国的自身定位是“积极的合作者”,中国逐步了解全球经济治理,并尝试做出贡献。此次杭州峰会成果渗透着中国秉持的原则和理念,这将有可能让中国成为“规则制定的引领者”。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使各国协商合作。习近平明确警告,重回以邻为壑的老路,不仅无法摆脱自身危机和衰退,而且会收窄世界经济共同空间,导致“双输”局面。
其次,中国坚持世界平衡包容发展。中国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本届峰会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中国还明确表示不愿G20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小圈子,G20要属于全世界,关注全人类共同发展。
可见,中国能够走向全球治理中心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维护国际秩序公正,维护各国的共同利益,负责任,有担当。
本次峰会前期所达成的很多共识,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二,每年所达成的承诺数量有了不小的增长,虽然G20的决定还不是非常严厉的刚性约束,但是即使是“承诺”和指导性意见,依然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第三,G20实行轮值主席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律有资格轮流担任。这已经远不像当年,仅是在G8首脑达成协议之后,才向新兴国家领导人传达。对此中国领导人严肃地提出过意见,才形成今天这样的平等交往的格局。
由G20取代G7是历史的必然
G20到底与曾经最能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G8有何可比性,可以由一个例子来佐证。
两年前,“G8变G7”的故事与俄罗斯密切相关。
2014年,正值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在俄罗斯索契召开的发达国家俱乐部非正式峰会,七国集团均未派领导人出席;随后,七国领导人在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又齐聚布鲁塞尔开会。在此背景下,曾经的“八国集团”就变成了“七国集团”。
自此之后,俄罗斯被西方世界打入“冷宫”,在经济上遭受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气愤地表示,莫斯科已与“七国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今的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8月31日,德国外长施坦因迈尔接受本国网络媒体采访,在被问及“俄罗斯如回归G8需要何种条件”时,他表示,叙利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都可以表明,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几大经济体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小范围谈判,“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施坦因迈尔强调,如果乌克兰东部问题及叙利亚停战谈判能够出现实质性进展,七国集团愿与莫斯科商讨俄罗斯回归G8。施坦因迈尔同时表示,回归G8的钥匙在莫斯科手中。
德国外长的话,至少代表了部分西方国家在目前情势下的某种期待。对此,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在G7或G8范围内商讨全球问题“不会产生良好效果”,相比G7,普京总统更愿意与更加有效的国际模式进行合作。佩斯科夫进一步表示,在是否回归“八国集团”这个问题上,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或许在于莫斯科对G20模式已相当满意。俄罗斯相信,在G20模式下,俄已可以获得最完整的世界前沿经济剖面,能够充分挖掘俄罗斯的自身潜力。
对于施坦因迈尔的希望俄罗斯回归G8的表态,俄外长拉夫罗夫也明确回应,莫斯科不会再与G8“纠缠”。事实上,除了自身处境和诉求的考量,俄罗斯对G20“相当满意”也有充足理由。时至今日,G20已走过了17个春秋,如今的20国集团成员国的GDP已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G20已经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在多数国际问题分析家看来,从G7到G20是历史的进步,由G20取代G7则更是历史的必然。
但人们普遍担心的是,西方国家并不情愿与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分享权力,更不愿新兴经济体参与规则制定。因此,G20自身建设也存在挑战。
用自身的方法论来阐释世界外交
从被排除在外,一步步到平等交往,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外交方式有关。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智慧的文明大国,擅长用自身的方法论来阐释世界外交。
韩国庆熙大学朱宰佑教授说,自古以来中国都把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应用于外交,在以前的亚洲所有的中心点都是围绕中国而演进的,中国也有能力用和平手段去维护这种格局。但现在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变化,中国陷入一种结构性限制,面临着如何保证在自身发展中不威胁他国,并在发展中如何影响他国的问题。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栾建章认为,传统的中庸思想不能照搬到现实中来,新形势下的中庸是包容性的增长,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结伴发展而不是结盟,不是要梦回唐朝,回到朝贡体系,而是要用自身的方法论来阐释世界外交。
对于“软实力”这个词语,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提出建议用中国传统的“柔力量”来取代西方的“软实力”,中国柔力量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体现。他认为在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必须“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日本法政大学赵宏伟教授从习近平的有关论述中分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中心,而中国外交战略的最高目标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改善国际秩序,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这种外交战略是全球大战略,中国外交不是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外交,是以文治武功数千年之中华文明为底蕴为底气为理念为智慧为软硬实力的立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球大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