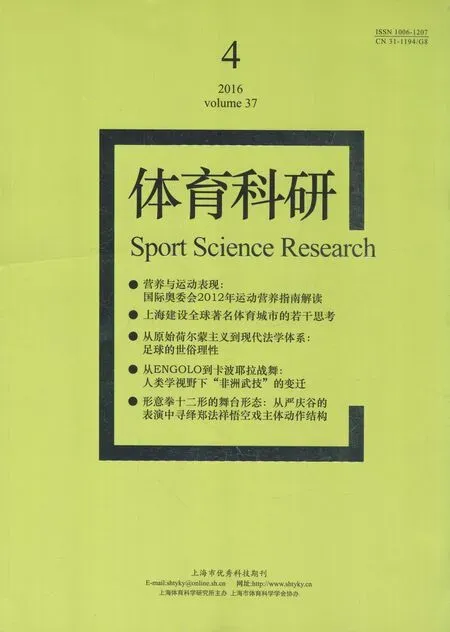古代巫风的现代延续:武术基本功马步之“马”的探源及启示
蒋德龙,谭广鑫
古代巫风的现代延续:武术基本功马步之“马”的探源及启示
蒋德龙1,谭广鑫2
从语音、考古、历史、民俗等方面,以武术人类学视角,梳理、比较与分析了马步之“马”的原始名称、原始意蕴及其重要启示。结论:(1)“巫”的上古及残存的读音为“ma”,“巫”的上古及残存的形象为“蹲踞”式,“巫”的上古及残存的活动为“下马”,进而初步判断马步之“马”的原始名称是“巫”;(2)“马步”之“马”的原型是战神、原旨是附体、原生是律动、原附是焚香,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各种宗教(大如道教、佛教,小如清水教、白莲教、天理教、八卦教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夹带着浓浓的巫风。启示:为传播武术,马步英译应该是“magic squatting”;武术基本功习练可以“感性的神秘”,武术基本功研究则要“理性的神秘”。
武术;马步;巫风
武谚“未学打先扎马”、“要习打,先站马”、“练拳先蹲马,马功到家、不怕刀枪”[1]等,道出了武术基本功马步的地位及重要作用。各拳种的“马”也有不同说法,如峨眉拳有“子午马、二字马、三角马、丁八马等”[2],蔡家拳有“三角马、拖步弓马、高四平马、跪马、插步马”等,台山洪拳有“四平大马、子午马、吊马、麒麟马、八分马”[3]。而“马”的本义或者原始意义是什么,极少见到这方面的资料。也有学者将马步之“马”翻译成“horse”,显然是不准确的。本文主要从语音、考古、历史、民俗等方面,以体育人类学视角对马步之“马”的原始名称与意蕴进行探源。
1 “巫”:马步之“马”的原始名称
1.1 “ma”:“巫”的上古读音及残存
许慎(汉代)在《说文》中,认为“马,武也”。钱大昕(清代)认为上古无轻唇音,“巫”作为明母字读“m”[4]。郑张尚芳(1996)在《上古音系》中,认为“巫”的上古读音为“ma”,并认为“巫、无在上古同音为‘ma’”[5]。向熹教授在《诗经词典》中明确指出:上古音“马”、“武”都是“鱼部、明母”;原本读音相同,以后才分属不同声母。小丁(2006)认为取自汉字草书“武”字的日文“む”的声母是“m”,故“む”读作“mu”,并认为韩语“武”读作“Mu”[6]。可见,“巫”的上古读音为“ma”。而且,现在我国各地的方言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巫”的读音(称呼),也是“ma”或者“ma”的音变“mu”、“mo”、“me”等。比如湖北方言称巫婆为“马子”,湖南娄底方言将能降神并代神立言的人称为“脚马”,湖南长沙方言将祭祀活动中的神差称为“马脚”,江西于都方言称巫师为“马脚师傅”,河北邯郸任县和保定唐县方言称巫婆为“马工”[4]。
东北满族的巫师,满语称为“萨满”、“沙曼”、“叉玛”、“萨玛”、“沙玛”、“撒麻”、“萨瞒”、“珊蛮”,且民间沿用“叉玛”。满族巫师萨满祭祀时候,附体之神的神名有一个统称,满语一般为“玛玛”、“瞒尼”或者“玛发”。比如有满族诸氏族尽崇奉的女神“佛朵玛玛”、女战神“敖都玛发”、“山因玛发”、满族石克特里家族独祭的“巴图鲁瞒尼”(还有“按巴瞒尼”)、“玛克己瞒尼”、“多豁洛瞒尼”、“朱禄瞒尼”、“胡亚气瞒尼”、“查罕布瞒尼”等[7]。以上可以发现满语对“巫”(神)的称呼读音一般为“ma”——“玛、麻”、“man”——“满、蛮、瞒、曼”(祭祀仪式中萨满巫师就是神的代言人)。
纳西族巫师东巴的典籍,纳西语读音为“2tso,1mu”被体育专家称为“最古老的拳谱”,发音被翻译为“蹉模”[8]、“磋姆”[9]或者“蹉姆”[10],而被音乐家称其为“最古的舞谱”,发音被翻译为“蹉磨”[11]、“磋模”[12]。东巴典籍中的神的名字最后一个纳西语读音是“ma”或者“mu”,比如巴哇优麻纳西语为“2paə2uə2iə1ma”,楚里拉姆纳西语为“3ts’i2lw2la2mu”,端格优麻纳西语为“2duæ2kə2iə1ma”,达依拉姆纳西语为“2tæ2i1la2mv”,米佐优麻纳西语为“2mi2ts’o2T ə1ma”[12]。以上我们也可以发现纳西语对“巫”(神)的称呼读音一般为“ma”——“麻”或者“mu”——“姆、模、磨”。
广西壮族自治区花山岩画附近的龙州县方言中,有把消灾减难的巫婆的“巫”发音为“麽”——“ma”,与“马步”的“马”发音相同。同样,与龙州不远的那坡县,则有把消灾减难的巫婆的“巫”发音为“蔓”——“man”[13]。
另外,还有土家族巫师称为“梯玛”(国际标音“thi55ma53”),康巴藏族巫师古称为“莫玛”,哈尼族巫师称为“贝玛”、“贝牟”,彝族巫师称为“毕摩”、“兵母”或“必磨”,维吾尔族巫师称呼为“喀木”(皮尔洪的先驱),云南苗族巫师称为“背马”,傣族巫师称为“咩莫”或“雅莫”,水城仡佬族称“巴磨”,傈僳族巫师称为“尼玛”,布朗族巫师称为“白摩”,门巴族巫师称为“觉母”,墨脱珞巴族巫师称为“巴目”等等。这些少数民族巫师的地方读音都是“ma”或者其音变。
综上所述,马步之“马”的读音为“ma”,而“巫”的上古读音也是“ma”及“巫”在流变的文化残存中同样是读音为“ma”或者其音变“mu”、“man”、“me”等。
1.2 “蹲踞”:“巫”的上古形象及残存
马步典型形象是“蹲踞”或“曲膝”,也即“脚尖内扣,蹲居如平,气沉丹田,挺胸收腹”。这种“蹲踞”形象在上古时期可以从岩画中寻找。在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以及世界各地都有这种典型的“蹲踞式”马步形象。这些典型的马步形象被学者称为“蹲踞式人形”,基本被认为是祭祀中的巫师形象。比如中国的岩画图(图1~3)。

图1 左江宁明花山岩画蹲踞式巫师Figure 1 Squatting Wizard in the Rock Paintings of Hua Mountain in Ningming County along the Zuo River

图2 嘉峪关黑山岩画蹲踞式巫师Figure 2 Squatting Wizard in the Rock Paintings of Black Mountain in Jiayug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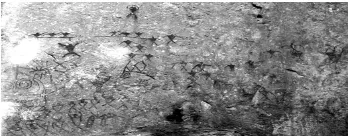
图3 云南沧源岩画蹲踞式巫师Figure 3 Squatting Wizard in the Rock Paintings of Cangyuan,Yunnan Province
胡小明认为图1这幅岩画中,“双手高举曲膝跺步,踏地为节”的蹲踞式人形,就是史前时期的巫师,也就是现代所谓的潜体育中的带有鬼气的武术形象,当地巫师“麽”驱鬼赶鬼的“拉屎马”[14]。汤明伟、王辉认为左江花山“大都呈马步、半马步架势”的岩画中的蹲踞式人形,彰显的就是青铜时代骆越人的武舞的形象[15]。董必凯、何卫东认为花山岩画蹲踞式人形与壮拳的基本功“七步铁线桩功”非常相似[16]。著名壮医专家覃保霖将花山岩画典型的蹲踞式人形(人物正面站桩形,双膝微弯成平马步,双肘微屈上举成莲花掌),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夫动作形象——“壮医乾坤掌子午功”,是中国三大气功文物之一[17]。
黑山岩画中的蹲踞式人形(图2),习云太认为是一种练武状[18]。崔乐泉认为黑山岩画中“曲臂、双腿半蹲”的蹲踞式人形,是仪式中“象以习舞娱乐的方式练武”的形象[19]。
刘锡诚把沧源岩画中“蹲踞”式人形称为“骑马蹲裆”(图3),是典型巫师形象[20]。王俊奇认为云南沧源岩画蹲踞式人形是武舞形象,属于一种先秦时期的原始巫术活动[21]。
另外在中国其他地区以及世界各地还有一些岩画、陶罐、画像中都有蹲踞式人形,一般被认为是祭祀中的祈祷者或者萨满巫师[22,23]。如福建华安仙字潭岩画、云南墨江岩画、仰韶文化陶器和甘青地区半山文化的彩陶罐、日本北海道的小搏市地区的富勾贝洞穴岩画、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加雅岛(IiranaJya)岩画、意大利卡莫诺山谷岩画、墨西哥Guanajuato地区的岩画等等。
现代拳种里的马步之“马”这种典型的“蹲踞”式形象有许多。比如峨眉拳有“子午马、二字马、三角马、丁八马”等,蔡家拳有“三角马、拖步弓马、高四平马、跪马、插步马”等,台山洪拳“四平大马、子午马、吊马、麒麟马、八分马”,咏春拳有“外钳阳马、内钳阳马、二趾钳阳,三角(藏三脚)钳阳马、吊提马、单蝶马、双蝶马以及追马、四平马、三字马等”。
可见,马步之“马”的典型形象(姿势)是“蹲踞”式,而“巫”在上古的典型形象(姿势)也是“蹲踞”式,及在其文化残存中的典型形象(姿势)同样是“蹲踞”式或者类似的形象(姿势),而且现代许多拳种里面有大量的“蹲踞”式的“马”的形象(姿势)。
1.3 “下马”:“巫”的上古活动及残存
在上古以及残存的祭祀性质的巫术活动称为“下马”也称为“发马脚”、“关马脚”、“擂马子”等。马步的上古活动在前面的岩画中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以下我们看看各地方言记载、小说记载、历史事件以及现代民俗中举行巫事活动时的“下马”。
湖北省民俗方言中的“下马”,是巫师在巫事活动中开始部分,声称某位大仙(白鹤大仙)仙魂附体,或者称自己是某位菩萨(观音、如来大师)下凡,还有另外一种称为“收兵”的形式——巫师“马脚”将小兵小将收归其麾下遣用。
栾星校注李绿园(清代)《歧路灯》第四十七回中的一段话是关于“擂马子”的——逢天旱或其他特大灾害,神社祈雨禳灾,击鼓打锣日以继夜,叫做擂马子。马子被擂下来之后,声称某某神祗显灵附体,可表演各种武术技艺。
义和团练武前也有“下马”活动,可称为“发马脚”。据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记录,义和团民在练武前置神案设关圣、恒侯、赵子龙等牌位,拜神后肃立,则忽然“发马脚”,而能够“飞拳踢足,七八岁者亦一跃数尺”[24]。义和团这些年轻的练武者被称为“马匹”[25],练武者的“下马”活动被描述成“作揖通城,施走数转,即能舞拳”[26]。另外,历史上类似义和团还有很多练拳中的“下马”活动,被称为“神打”、“神兵”等,往往相信“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的刀枪不入本事。
陕西省户县大良村建国后还举行过一种叫做“伐马角”的祈雨活动。活动开始时“马角”坐在长凳上被黄裱纸在前额转圈烘烤,直烤到灵魂出壳时,“哦”的一声——山神成功附体。尔后“围坛”期间,被“伐”下的“马角”有绝技活动,包括耍棍、轮刀、甩鞭、舞剑(平时不会)[27]。类似的活动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还有残存。如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尕则敦村的“插口钎”,山西临绮的屈村、南赵、北赵、安昌、蔡村以及山西万荣的邱家村等称为“扎马角”,湘中称为“发马脚”。湖北武汉黄陂区茅店村“元宵节狮子灯”的“下马”活动开始部分称为“试将(僵)”,其时“马角”要经过燃香、转圈点黄裱纸、燃炮、锣鼓齐鸣,当“马角”手脚颤抖身体后仰,说明“试将(僵)成功”,进而能够使出“扑”、“盖”等类似武术动作驱除村里年轻人身上的晦气[28]。
可见,马步之“马”的武术活动叫“下马”或者“扎马”和“蹲马”,而“巫”在上古的武术活动也叫“下马”或者“扎马”及其文化传承中同样是“下马”、“扎马”或者类似的“发马”、“伐马”、“关马”、“擂马”等相关武术活动。
2 “巫风”:马步之“马”的原始意蕴
以上从语音、考古、历史、民俗等角度,对马步之“马”的读音、典型形象及其活动名称,进行了探源与梳理、比较与分析,初步判断马步之“马”的原始名称是“巫”。那么,马步之“马”的原始意蕴是什么呢?也即我们要认识武术基本功马步除了从其名称上,还应该进一步对马步之“马”的原型、原旨、原生、原辅等方面探溯其原始意蕴。
2.1 战神:“马步”之“马”的原型
原始初民认为万物有灵,给予其益处的视为神,危害其生存的则为鬼。当原始初民遇到难以排解的危机(久旱、山洪、战争、疑难病症等)时,往往认为是鬼在作祟,而要举行仪式以求得神的智慧和力量,来战胜危害其生存的妖魔鬼怪(现代很多地方存有)。仪式(傩仪)的主持者就是巫师(部落首领)。巫师所求的神的智慧和力量得足以能够打败妖魔鬼怪,其有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神话故事),所以这神属于战神,也即马步之“马”的原型。成为巫师崇拜和接通的战神,有太阳、高山、大海、动植物等自然之神灵的战神,以及祖先和英雄人物转化的战神。我们可以在典籍、民俗傩戏、历史事件以及现代武术中都可以发现。战神为自然之神的,如《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古岳渎经》中记载,大禹治水施行巫术时,所求得的是战神日神的智慧和力量[29,30]。《周礼·夏宫·方相氏》载有经典的方相氏驱鬼傩仪[31]:“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殴疫”,其中方相氏求得的是战神“熊”神的智慧和力量[32]。西藏的巫师拉巴、古郭在为民众驱邪傩仪式中,所求得的是战神被称为灵希达的山神的智慧和力量[33]。青海黄南土族有“跳於菟”仪式[30]傩仪,云南双柏彝族有种“老虎笙”的傩仪,其参与的巫师及信众求得的是战神“虎”神的智慧和力量[3]。这种以动物为战神原型的“巫”(马),现代中国武术拳种里比比皆是的要数象形拳,正是程大力在《论图腾崇拜对象形武术的影响》中说到的“象形武术是模仿动物——是为了馅媚图腾物,以取得图腾物的神性和力量”[34]。
王芗斋在技击桩法中“神意之应用”里写道“神犹雾豹,意若灵犀”,具有“烈马奔放,神龙嘶噬”之势,以及动则如“怒虎搜山,山林欲崩之状,全体若灵蛇惊变之态”,“神机微动雀难飞,颇似有神助之勇焉”[35],其战神原型可见一斑(至少12个)。王芗斋的战神原型除了这些应该有其崇敬的师傅郭云深,对待这些战神原型要“拳拳服膺”——铭记在心。
战神为祖先及英雄人物转化而来的神,如下。
满族巫师萨满战神“查罕布瞒尼”和“按巴瞒尼”都是武功极高的英雄好汉。前者兵器是“铁榔头”,兵器技术表现为:萨满双手各执一柄铁榔头拼命地轮打着,指东打西,挥北击南,浮上翻下,飘忽无踪。后者兵器是“托力”,则兵器技术表现为:萨满手执两面托力,前后左右翻转,四面八方照射,意似三角四处搜查[7]。
1765年浙江虾县吴家山神拳练武活动中“发马脚”,其“马匹、马子”求得的是战神“关圣、桓侯、赵子龙”等的智慧和力量[36]。1899年山东朱红灯的义和拳,其“马匹、马子”在练武活动中,所求得的是战神杨戢、孙膑、刘备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的智慧和力量[37],甚至还有神话小说中的孙悟空。
1774年清水教王伦的义和拳的练武活动中,“马匹、马子”所求得的是战神“青龙、白虎、朱雀、元武”等四方神的智慧和力量,而李翠的义和拳练武活动中所求得的是战神如来佛释迦牟尼的智慧和力量。1823年李芳春练武活动中“马匹、马子”所求得的战神是《封神演义》小说中的哪咤、姜子牙、土行孙等的智慧和力量[38]。
20世纪初的中国西南义和团拳民练武活动中“马匹、马子”所求得的也是战神如“观音、关帝圣君、沙僧、唐僧、八戒、悟空等的智慧和力量[39]”。
梅花拳大师杨炳《习武序》中记载所拜的祖师,第一是“收元老祖”,第二是“均天教主”,第三是“东都护法”,都可以认为是梅花拳的战神。
按照荣格的原型理论来说,武术各门派拳种的种种神话传说与传人的传奇武林故事的战神原型,就是该门派拳种的集体无意识,是根植于该拳传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代代相传。
可见,武术基本功马步之“马”(巫)的原型是战神,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能够驱除危害人的妖魔鬼怪,并且武术基本功马步之“马”(巫)这个战神原型经历了自然神战神到祖先英雄战神的发展,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战神体系(故而形成了不同武术拳种)。
2.2 附体:“马步”之“马”的原旨
巫术活动以及“下马”、“擂马”、“发马”、“扎马”等民俗仪式活动中的武术活动,从前面的描述中可知,其原旨在于“附体”。附体指战神“下”到、“擂”进、“扎”入巫师体内,使得巫师与战神合而为一,具有战神的智慧和力量,成为战神的代言人而能够驱除妖魔鬼怪。附体,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不同称呼,有称为“出神”,有称为“上将”,有称为“发神”,有称为“上杠”等。如满族巫师叉玛,附体称为“出神”,其时“全身出现抽搐,四肢震颤或者僵直,两眼翻白,甚至口吐白沫”。湖北武汉黄陂区茅店村在元宵节狮子灯时候,“马甲”被神明附体称为“上将”,其时“手脚颤抖,慢慢地全身颤抖,最后他起身,一个劲地要抓住某物,身体向后仰”。苗族巫师巴岱,称为“迷征”,其时“眼神空洞,身体激烈摇荡,接着双眼翻白,口吐白沫,手脚乱颤起来”[40]。
能够附体成功往往就成为巫师或者检验真假巫师的标志,或者说能否战胜妖魔鬼怪的条件。比如满族巫师叉玛成为叉玛的仪式叫“落乌云”,其时学员必有附体上身才能通过。土族巫师法拉那里称为“插口钎”,其时附体上身“双脚同时离地,围绕会场狂奔”。在义和团拳民练武时,能够附体的“马匹”才可以学武,即念咒后要“喘大气、瞪眼睛、跺脚”,“翻身仆地上者,教之;不然者,谓不可教,斥之”[41]。
附体,在现代武术中大概就是许多学者所说的武术基本功的练习要达到的功夫“上身”。据说,梅花拳的桩功“拉架子”练习,因为拳理朴实,功夫“上身”快,能引发一定的灵感思维,开发灵性[42]。如太极拳功夫“上身”重视身体的习练,探究的是思想的感知和身体体验图式[43],也只有功夫“上身”以后武术技术体系才进入第三层[44]。有学者认为高校武术教学改革中“动作组合的目的是让学生在不断的重复练习中,去感受和领悟武术的真正内涵与精要”进而达到功夫“上身”目的[45]。少林武术神话故事“僧稠乞力金刚神”,实际就是“在殿中,闭户抱金刚”修行而达到到功夫“上身”,使得劲力暴增[46]。
附体,也就是许多学者说的是人的一种意识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ASC)代名词,是专门研究萨满巫师的关键术语。荣格的原型理论认为只要曾经帮助储存和建立原型的特殊场域出现时,潜藏在人们心理结构深处的原型就会被重新激活和显现出来,此时已经改变原来的意识状态,进入到或者接通其集体无意识——人神合一。
王芗斋桩功里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是“精神假借”,其在“习拳述要”里说“按拳道之由来,原系采禽兽搏斗之长,相其形,会其意,逐渐演进,合精神假借一切法则,始汇成斯技”[35]。“中国行——中医健康管理工程”首席健康指导专家王开俊用“激活潜意识”解释王芗斋站桩功的精神假借[47]。笔者认为,王芗斋的“精神假借”有根源于“附体”的含义。
李仲轩在《逝去的武林》中提到的形意拳有“入象”的古说。“入象”是“化脑子”,有“恍然”的感觉,也即“走火入魔”,并说“练拳一定得走火入魔,先入了魔境再说。有了恍然,处理恍然,是习武的关口,要凭个人聪明了。处理好,就鲤鱼跳了龙门。恍然来了,让它傻傻地过去,练武便难有进展”[48]。笔者认为,“入象”与“附体”异曲同工,“化脑子”应该就是意识改变了的意思(ASC)。
可见,武术基本功马步之马(巫)的原旨在于附体——原型进入到巫师体内,使得巫师与原型合而为一,具有战神的智慧和力量,成为战神的代言人而能够驱除妖魔鬼怪。并且在现代武术基本功中仍然存在另外一些概念来表示附体(上身)这个要求。
2.3 律动:马步之“马”的原生
巫师能否有幸得到战神附体于身,与战神合而为一,成为战神的代言人,而具有战神的智慧和力量,在荣格所说的出现“曾经帮助储存和建立原型(战神)的特殊场域”中,得有其独到条件是身体重复性运动——身体律动。也即马步之“马”的原生性的身体运动是律动。如满族萨满巫师为达到战神附体——进入意识改变状态,会重复地做一个同样的运动——踏地旋转,正如白翠英老师说到的“疯狂激荡地踏地旋转是将科尔沁博(萨满巫师)导向昏迷境地的真正咒力和魔法”。彝族巫师苏尼(“专事击鼓颤抖舞蹈之仪式活动的人,苏尼类似萨满”[49])驱鬼仪式中,有些苏尼是反复地单脚跳、双脚跳等节律性运动进入附体状态,有些苏尼是身体不停地反复转圈进入以及维持附体状态。壮族巫师“麽”进入附体状态时,会“直立上跳,不断晃动双腿”[13]。达斡尔族未来萨满想进入附体时,被人拽着其腰带按照顺时针方向不停地转圈,或者被托着胳膊转圈,或者在师傅引导下握着师傅萨满服上的皮绳不停地跳跃(配合鼓声)[50]。苗族巫师未来巴岱在“过法”仪式中要进入附体状态,双手与师傅相扣在胸前上下摇晃,其后背被同伴不停起伏推攘而使得身体摇摆。前面我们说到的“扎马角”和狮子灯“马甲”都有在额前不停地转圈燃烧黄裱纸,而进入附体状态。如罗伯特·莱顿对仪式中都具备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重复行为的身体律动的解释那样,“创造重复舞蹈和音乐韵律的一种可选择的原因是在参加者身上产生催眠作用”[51]。也即身体律动情况下方可附体——接通战神原型、原型战神沟通,具有战神的智慧和力量。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熊学鹏奏折中记载了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宁波、温州、瑞安等地的神拳活动,谓“作揖通诚,施走数转,即能舞拳”[26],施走即反复走之意。
王芗斋意拳桩功练习中有“小腿发生轻轻地颤动,继而颤动到大腿、腰、腹、胸等部,任其发展,将会颤动越来越大,以致全身大抖动,甚至脚跟时起时落地打击着地面”[52]。
李仲轩在《逝去的武林》中提到唐师维禄所传的桩功中以及李存义的桩功都有类似的“律动”。前者的要点是“时常浑身抖一抖”,属于“很细致很轻微地抖抖”,据说仿象于熊冬眠中时而要出来抖一抖[53]。后者的标志是“浑身细胞突突——高密度高深度的颤抖,由突突到不突突再突突,反复多次,这就出了功夫,站桩能站得虎口指缝里都是腱子肉,这是突突出来的”[54]。
李一道长认为站桩要有“颤抖”意识。“颤抖”是人体在极度放松状态下引发的一种生理节律,可以修复人体内部的紊乱和无序化,使人感觉全身非常舒畅[55]。
可见,马步之“马”的原生性身体运动是身体反复性、重复性的律动,是马步之“马”的标志性特征,如果没有身体律动,战神不能附体,也即功夫难以上身。
2.4 焚香:马步之“马”的原辅
马步之“马”战神原型要附体(上身),除了原生性的身体律动以外,通常要有一定的环境支持或者说要处在特定的场域中。在这个特定的场域里有辅助性的手段。也即,需要一定的辅助手段来帮助达到附体(上身)目的。其中明显标志就是在特定的场域中焚香(还有制度性音声[56])。比如,东北萨满关氏家族萨满在每年的七月初七前就要到山上采摘年息花(杜鹃、金达莱),制作成举行萨满仪式时候通神御鬼用的香[57]。此香具有开窍、辟秽、活血的功效。特别是认为清香的烟雾能使萨满飞凌天穹请神,神灵也能在烟雾中踏着星光降临神堂。
义和团的“马匹”每欲打拳,要“烧香上表”,然后将焚香后的香灰点在额头上,或者用水将香灰调和后饮用。
回族武术家胡云祥先生在介绍他习武经历的时候,说他马步可以蹲三炷香[58]。通臂名师郭长生曾讲起他的师傅武术技击家刘玉春站桩之前要先点一炷香,然后纹丝不动地开始站桩,并且要等到这炷香烧完为止[59]。郭长生要求儿子郭瑞祥(武术九段)练“高吊腿”(高吊马)时候,也要在旁边点上一炷香,香不燃完搁在墙上的腿不准下来。
王芗斋站桩是早上天不亮就在庙里站马步。共要站两炷香,先是点上一炷香,然后给达摩磕头,再给他的师傅郭云深磕头,然后站食指挑眉桩,头炷香站完,再点上一炷,再按顺序给达摩和郭云深磕头,再站食指挑眉桩。如此站了9年。
咏春大师叶准的徒弟李坦亿20世纪70年代练武的时候,说非常辛苦,“屁股下点一炷香,开始扎马步练基本功”[60]。
据调查,在今天对冀南广宗县前魏村、北杨庄与杜家庄等地,“梅花拳会”是一种“信仰”,其文场主要是看香,与洪拳的差异是“梅花拳烧香”。进入拳会的标志是立“架”——要“求香礼”测神意,据“香谱”定资格[61]。据《梅花拳谱》所载,三才“人、天、地”对应为“香、香灰、香烟”,“金木水火土”对应“香盘、香、茶、灯、香灰”。
可见,马步之“马”的原附(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是焚香。现代武术基本功的马步练习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见到“香烟袅袅”,但是这种焚香的最初的目的已经被遗忘了。很多人认为传统武术基本功马步练习的“一炷香”是为了计算蹲马步的时间长度,是不完全正确的。其实际点燃的是一条“香路”,营造一种仪式氛围,为了与战神原型沟通达到人神合一。
3 对武术基本功的启示
以上探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武术基本功马步之“马”的原始名称是“巫”,其蕴涵着一阵“巫风”——原型是战神、原旨是附体、原生是律动、原附是焚香,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各种宗教(大如道教、佛教,小如清水教、白莲教、天理教、八卦教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现代则主要从生物力学、工学之类的科学方面来解释。一方面,这正如人类学家费雷泽说到的人类认识、解释、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的发展进程,是巫术——宗教——科学一样[62],对马步之“马”的认识、解释、实践恰好与之相一致。另外一方面,仅仅从力学、工学之类的科学上来认识、解释、实践马步之“马”,显然已经割断了马步之“马”的深远的历史人文基因,使得马步之“马”的本真名称与丰富的意蕴逐渐地被蒙蔽和遗忘。
恐怕这就是邱丕相对当代武术的管窥和思考时说的那样,“武术的内功、内劲、内气,以及由此引申的传奇是否在没有充分揭示之前,还得保留一定的神秘性”[63,64],也认为“由于武术本身所具有的东方文化的神秘色彩,且能够帮助人们拓展属于人类生存层面的基本自由,二者的结合让以任何方式塑造武术形象成为可能”[65]。也有学者为了回归与敬畏经典套路,提出学校武术教学要“一校一拳”,变“祛魅”到“附魅”[66]。
所以,从以上对马步之“马”的原始名称与原始意蕴以及发展流变的探源中,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3.1 “magic”:马步之“马”的英译
目前对马步之“马”的英译,一种情况是从其字面意思直译为“Horse”,马步则译为“Horse Stance”[67]、“Horse-riding Stance”[68]、“Horse Step”[69]。另外一种情况则是不直接翻译“马”,将马步意译为“seated position”[70]、“squatting stances”[71]。显然,这两种翻译已经割断了马步之“马”的“巫”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基因,使中国武术在国际传播上浅薄化(动物意义的“马”)、冰冷化(一种僵硬的姿势)。为此,笔者认为将马步之“马”翻译为“magic”,马步则译为“magic squatting”。因为“magic”,英文可以做名词,翻译为“巫术”、“魔法”、“不可思议的魔力”等,可以做动词,翻译为“用魔法变出”、“用魔法摆脱”、“用魔法得到”、“使中邪”等,可以做形容词,翻译为“魔术的”、“幻术的”、“不可思议的”、“有奇异魔力的”等。这样,马步英译为“magic squatting”就可以很大程度地保持了马步之“马”的“巫”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基因。再有,据记载,1930年王芗斋弟子赵道新与宋子文保镖安德森比武时,使安德森像断线风筝摔出丈外,而安德森高呼“magic!magic!”[35]。最近有一种全球热词“Asian squat”,实际乃中国特色,据说历史渊源流长,“Asian squat”可以能够拉升大腿、锻炼腿部肌肉、促进消化和排便等等[72]。
3.2 感性与理性:武术基本功的神秘
探源出马步之“马”的战神原型、附体原旨、律动原生以及焚香原附,并不是现代武术基本功训练也必须回到“巫”的原点上的神秘莫测。学界对武术基本功之类的神秘,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祛魅”,一种是“附魅”。“祛魅”观从科学理性出发认为所谓的武术的神秘有迷信、虚假,是武术的负面形象,而要褪去这层神秘面纱。“附魅”观从人文出发认为武术的神秘是习武人最深邃、最美丽的情感,是武术的“真科学与真艺术的真源泉”,是武术传承的内在动力[73]。
我们认为武术中的神秘而是要进行区分的:武术基本功习练可以“感性的神秘”,武术基本功研究则要“理性的神秘”。“感性的神秘”指李泽厚所说的“是‘启示’、‘灵魂游走’之类的,人们在心里确实体验过的那种不可言说的奇异现象”。比如中医中的经络、针灸,以及苦修中,长时间的饥饿使得身体很疲劳出现的幻象[74]。这种奇异现象在将来的科学中是可以认识并解释清楚的。那么,武术基本功习练的“感性的神秘”,比如“蹲马”中就是习练者在反复的身体律动中,心里确实体验过的战神附体(上身)后的不可言说的奇异现象。这种奇异现象往往与自己的祖师(战神)的忧国忧民、嫉恶如仇、除暴安良、所向无敌的英雄豪迈气概紧密相通。这种气概已然入驻己身,好比自己已经成为了祖师(战神)一样的人,让自己陡然高大、英勇。正如李仲轩说的“入象”后的“恍然”和“走火入魔”。王芗斋桩功中论述“精神假借”“试力”时,说“身体均整,筋肉空灵,思全体毛孔无不有穿堂风往还之感。然骨骼毛发毛发都要支撑遒放,争敛互为”,并且这种毛发穿堂风与骨骼遒放之感实乃“非豪端所能形容”,“言之繁难之极”[35]。
李泽厚“理性的神秘”,张文初解释为“是那种虽然没有实在的感性体验,却是依据理性的推理可以认定的存在;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不可知之,但可思之的东西”,也即是可以用理性推导出来的神秘[75]。那么,武术基本功研究的理性神秘,就属于这种理性推导的神秘。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邱丕相、虞定海、赵光圣、王林、郭玉成等学者所论说的武术的“附魅”之类的理性推导的神秘,以及本文对马步之“马”的理性推导的关于“马”的“巫风”的神秘(战神、附体、律动、焚香)。这种理性的推导的神秘,虽然不是直接领有的心理奇异感,但仍然是由情感性心理来“直接领有”的。这种由理性推导的神秘存在于来自于武术基本功习练的历史上和现实里的实际战斗的情感体验之中。
[1]梁绍灿.浙东南拳技法[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83,7(1):57-58.
[2]邹德发.峨眉派拳术十八种概说[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3 (3):32-41.
[3]陈永香.对双柏县老虎笙的文化阐释[J].青海民族研究,2007, 18(3):37-40.
[4]邵则遂.“下马”、“马脚”探源[J].长江学术,2008(3):172-173.
[5]郑张尚芳.古越语地名人名解义[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8-13.
[6]小丁.“武”与moo(wu)[J].文史杂谈,2006(1):79.
[7]张寒冰,石继顺,石光华.满族石克特里家族萨满文化诠释[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
[8]和力民.纳西族东巴舞蹈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体育学刊,2013,23(3):15-19.
[9]万义,王健,龙佩林,等.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文化生态学分析——东巴跳与达巴跳的田野调查报告[J].体育科学,2014,34(3):54-61.
[10]杜长亮,王慧勇,李晓华.东巴跳源考与属性辨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8(5):123-125.
[11]黎华.“东巴跳”与《磋磨》跳谱的定位[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1999(1):72-73.
[12]申明淑.中国纳西族东巴舞谱研究——兼论巫与舞、舞蹈与舞谱[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13]萧梅,孙航,魏育鲲,等.中国民间信仰仪式中的音乐与迷幻[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14]胡小明.从左江岩画看民族体育的起源和传播[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2,18(2):29-33.
[15]汤明伟,王辉.论少数民族武术的本源与区域特征[J].体育与科学,2013,34(1):67-70.
[16]董必凯,何卫东.广西花山岩画蕴涵的壮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现代传承发展[J].广西社会科学,2015(4):51-54.
[17]庞宇舟.花山岩画壮医学内涵探析[J].光明中医,2008,23(12):1873.
[18]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33.转引自汤明伟,王辉.论少数民族武术的本源与区域特征[J].体育与科学,2013,34(1):67-70.
[19]崔乐泉.史前乐舞祭仪与原始的体育娱乐——原始体育形态的考古学分析[J].南方文物,2008(2):74-80.
[20]刘锡城.舞法及其象征[J].民族艺术,2001(4):113-134.
[21]王俊奇.先秦绘画雕刻中的体育及其意蕴[J].体育文化导刊, 2014(1):161-164.
[22]汤惠生.原始艺术中的“蹲踞式人形”研究[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1):3-18.
[23]张嘉馨,孙晓勇.美洲地区“蹲踞式人形”岩画的分类与内涵阐释[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4,11(4):89-95.
[24]佐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事杂记[M]//中国史学会.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52.
[25]路云亭.论义和团仪式的民间杂艺元素[J].民俗研究,2009(1): 72-85.
[26]周伟良.传统武术中的一缕神光[J].体育文史,1992(2):47-48.
[27]刘高明,孙立新,贾芝茂.户县大良村“伐马角”祈雨的原始崇拜文化考察[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27(1):72-82.
[28]童旭.变与不变:他们心中的神明——武汉市黄陂区茅店村“元宵节狮子灯”现象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3):74-85.
[29]向柏松.水神巫术神话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关键性仪式——神话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再发现[J].中南民族学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5(1):146-150.
[30]秦永章.江河源头话“於菟”青海同仁年都乎土族“於菟”舞考析[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0(1):52-55.
[31]孙治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59)[M].中华书局,1987:2493-2495.
[32]张紫晨.中国摊文化的流布与变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1(2):19-27.
[33]孙林.西藏民间宗教中的“山神”——希达、念神、赞神关系考析[J].中国藏学,2009(3):164-170.
[34]程大力.论图腾崇拜对象形武术的影响[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3,19(2):6-10.
[35]王芗斋.“意”无止境[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
[36]左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事杂记[M]//中国史学会.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52.
[37]1965年12月《在平义和团调查资料》,转引自陆景琪.山东义和拳的兴起、性质与特点[J].文史哲,1982(4):72-79.
[38]路遥.“义和拳教”钩沉[J].近代史研究,1991(2):101-126.
[39]左瑞成.试论西南地区义和团运动的源流和特点[J].贵州文史丛刊,2001(2):9-12.
[40]陆群.苗族宗教仪式中的迷征现象考察———以巴岱“过法”仪式为例[J].宗教学研究,2014(1):137-144.
[41]周伟良.义和团武术活动简论——义和团活动研究的一个新视域[J].学术界(月刊),2011(8):163-177.
[42]张士闪.从梅花桩拳派看义和拳运动中的民俗因素[J].民俗研究,1994(4):54-62,67.
[43]张杰.基于文化符号圈理论的太极拳文化符号结构研究[J].体育科学,2012,32(12):85-91.
[44]杨建营.武术分层技术体系的构建[J].体育学刊,2011,18(2): 121-128.
[45]李光全,张元河.方法、现状与中国意识:高校武术教学改革新探——基于武术原初素质和精要的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11):81-85.
[46]于均刚.如何对待国粹——兼驳“武术封建糟粕”论[J].体育文化导刊,2006(1):26-28.
[47]王开俊.站桩功的精神假借[EB/OL].蒋德龙的博客,http://blog. sina.com.cn/s/blog_ec9a2eab0102vfk6.htm l.
[48]李仲轩,口述;徐浩峰,整理.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28-133.
[49]巴莫阿依.彝人的信仰世界——凉山彝族宗教生活田野报告[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52.
[50]萨敏娜,吴凤玲.达斡尔族斡米南文化的观察与思考——以沃菊芬的仪式为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14-119.
[51]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M].靳大成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150.转引自王静.消弭与重构中的“喳玛”——一项宗教仪式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200.
[52]姚承光.姚宗勋拳学思想文集[M].香港:北京图书出版社,2013:62.
[53]李仲轩,口述;徐浩峰,整理.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13-117.
[54]李仲轩,口述;徐浩峰,整理.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69-186.
[55]李一.李一道长养生有良方[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76.
[56]萧梅.仪式中的制度性音声属性[J].民族艺术,2013(01):32-43.
[57]纪录片《探秘萨满》第2集[EB/OL].华数TV广电宽频,http: //www.wasu.cn/Play/show/id/1689571.
[58]刘汉杰.沧州回族武术文化的内聚与外衍——以八极拳的传承、传播为例[J].回族研究,2005(2):186-190.
[59]牛增华武学研习会.浅谈通背合一门拳的源流[EB/OL].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d8dcddf0100u2h5.htm l.
[60]刘小利.李坦亿:一名写作老师文能书法武会咏春[N].东莞日报,2014-12-11.
[61]张士闪.民间武术的“礼治”传统及神圣运作——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梅花拳文场考察[J].民俗研究,2015(06):38-47.
[62]费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上)[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12-13.
[63]邱丕相.对当代武术的管窥和思考[J].搏击·武术科学,2007,4 (8):1-3.
[64]邱丕相,马文友.武术的当代发展与历史使命[J].体育学刊, 2011,18(2):117-120.
[65]王伟,邱丕相.武术休闲:基于供应链理论的市场开拓[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3,30(1):82-86.
[66]王晓晨,赵光圣,张峰.回归原点的反思:中小学武术教育务实推进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4,29(3):197-202.
[67]王冬梅.旋风脚720°接马步动作落地时致膝关节损伤的运动生物力学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3):139-144.
[68]王森.武术套路旋风脚900°接马步可行性试验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4,29(2):177-181.
[69]武术套路中旋风脚转体720°接马步动作踏跳阶段的生物力学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5,29(5):66-69.
[70]赵勇,刘显东,王小兵.不同屈膝角度的马步桩在髌骨骨折术后康复训练中的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骨伤2015,28(4):327-329.
[71]DING Yu,YANG Mei-yi.Electroacupuncture assisted by squatting stances for lumbar disc herniation[J].World Journa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WJAM),2015(1):47-50.
[72]李雪萌.严肃地来谈谈蹲的事儿[N].济南日报,2016-03-03.
[73]王林,虞定海.传统武术传承场域嬗变论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2(6):149-155.
[74]李泽厚,刘悦笛.关于“情本体”的中国哲学对话录[J].文史哲,2014(3):18-29.
[75]张文初.本体之情与生存的诗性言说——论李泽厚的“情本体”[J].文艺研究,2011(5):90-97.
(责任编辑:陈建萍)
Modern Continuity of the Ancient Magic Wind:the Origin and Enlightenment of"Ma"of the Magic Squatting in Martial Arts
JIANG Delong1,TAN Guangxin2
(1.College of Athletics and Kinesiology,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421008,China;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voice,archaeology,history and folklor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tial arts anthropology,the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original name,original meaning and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of"Ma"in squatting stance.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1)The pronunciation of"magic"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remnant pronunciation is"Ma".The image of"magic"in the ancient times and the remnant image is"squatting".The activity of"magic"in the ancient times and the remnant activity is"dismount".And then we can determine the original name of"Ma Bu"is magic squatting.(2)The prototype of"magic"in the word "magic squatting"means the God of War,which has countless ties with the various religions such as Taoism, Buddhism,Waterism,White Lotus Society,Tenrikyo,Eight Diagrams Society,etc.),and the deep"magic"flavor can be tasted.The enlightenment to us is that"Ma Bu"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magic squatting"in order to popularize wushu.The basic skills of martial arts can be practiced with"mystery of sensibility"and the researches of the basic skills of martial arts depend on"mystery of rationality".
wushu;magic squatting;magic wind
G80-05
A
1006-1207(2016)04-0042-07
2016-06-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C890019);国家社会科学课题(15CTY020);湖南省体育科学学会课题(2015HN050)。
蒋德龙,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学术史,体育人类学。E-mail:jdl741124@126.com。
1.衡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衡阳421008;2.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广州2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