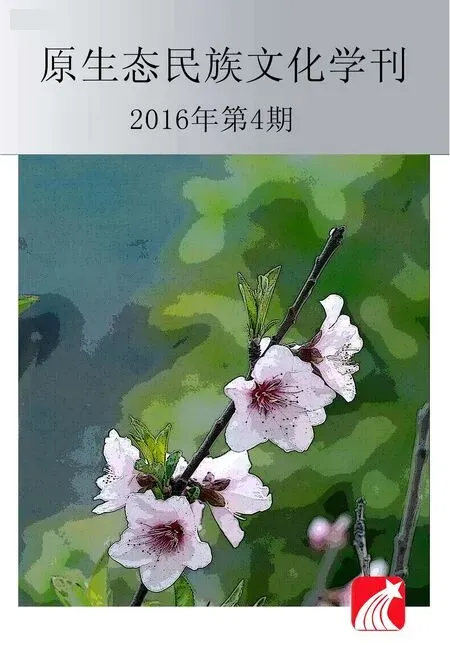民艺的“中国隐喻”
——建立具有本土化实践和运用的民艺再生路径
王小梅
(贵州日报社, 贵州 贵阳 550001)
民艺的“中国隐喻”
——建立具有本土化实践和运用的民艺再生路径
王小梅
(贵州日报社, 贵州 贵阳 550001)
参照日本民艺运动的实践案例,试图在案例解读中阐释中国的民艺运动,这需要在文化性和精神层面认知民艺的中国价值,梳理民艺的内涵和外延,从主流工艺美术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传习和发展等,逐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模式;发展民艺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并在手工制造的时间投入和情感附着中,发现民艺在快速消费时尚蕴藏的文化价值,建立民艺在中国快速发展中的现代性审美价值体系;倡导民艺手作者内生性自我发展体系,从价值倡导到精神共享的层面建立民艺的主体性文化认同,建立具有本土化实践和运用的民艺再生路径。
民艺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土化实践
“民艺”已是约定俗成的词语,有其独立的内容和涵义,研究的对象是“以实用为主导、以服务于民众的生活为目的而制作的器物”。而作为“民艺学”理论,所涉及的方面是很广泛的,对此,“民艺”一词首创者日本柳宗悦先生的《民艺学概论》已作过全面的构想。
被称为“民艺之父”的柳宗悦,七十多年前在日本发起的民艺运动,在于唤醒日本民众对于日本本土文化的回望和反思,从开始系列日本民艺的复兴倡导,到建立日本民艺基础性研究、理论和民艺馆为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和现代设计、审美融合运用的系统、整体性民艺修复和运用工作框架。日本的民艺运动文化识别,并不限于少数民族文化类别,而是该民族在历史中留下的各类珍贵文化遗产,都成为民族艺术,作为大文化范畴中的民间艺术类别,对民族艺术类别做了“大文化”类别的整理和梳理,在民艺和风物中注重手工技艺类别的技术工艺收集和研究,并研究传统技艺和材料在现代产业中的运用和实践,大量传统风物和材料被使用,及手艺人以自身核心传统技术的修复和使用,参与到现代产业中的制作和生产链中,极大地激活传统技艺的活力。
可以说,日本的民艺运动从基础性研究开始,出版大量手艺人口述史文本,收集和整理大量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艺术,以出版和在设计“生活美学”形式重新回归到现代生活世界,在与现代时尚的结合中,输出大量现代化简洁实用的生活物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日本民艺运动和民艺的运用,有效地支持了日本现代设计产业和时尚品牌的生长,从文化系统、传统技术、风物、设计运用、品牌传播、推广和市场上系统性地融合到日本现代时尚产业中来。其间,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建立一个有机非盈利文化传承和盈利品牌的互动融合可持续发展模式,不断产生新的效应,成为支持民艺生长和民艺可持续发展参照范例。
中国语境中的“民艺”如何定义?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我们认为,每一项具有参照性的理论体系和可复制的模式的运用,都只在参照其可运用的技术模式,而文化的核心内容梳理和运用模式研究必须走在前面,作为指引性精神引导和可运用的内容参照。可复制的是做法,而传统智慧和精神价值永远是从自我的文化体系中生长出来的。因此,中国的民艺哲学范畴和文化内涵需要进行基础性研究和先导性梳理,而不是盲目引用“民艺运动”一词,用于文化产业中以“产品制作”为导向的新一轮“手作”为卖点的商业运作中来。
因此,我们认为,关于中国的民艺运动,需要在文化性和精神层面认知民艺的中国价值,梳理民艺的内涵和外延,从主流工艺美术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传习和发展等,逐步在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模式;发展民艺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并在手工制造的时间投入和情感附着中,发现民艺在快速消费时尚蕴藏的文化价值,建立民艺在中国快速发展中的现代性审美价值体系;倡导民艺手作者内生性自我发展体系,从价值倡导到精神共享的层面建立民艺的主体性文化认同,建立具有本土化实践和运用的民艺再生路径。
一、贵州非遗的“民艺”行动实践
以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内容的“民艺”行动为例,政府政策性支持和投入大量资金投入是前所未有的,但在制定政策之前对于文化传承的长远共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并未进入视野,并未建立民族手工产品的发展共识。民艺发展规划未先行,科学化系统化体系在大规模的公司化产品加工基础上未有意识上的长远考虑。支持大量微型文化企业建立有机会申请政府支持性项目无次序无规划制造民族性产品,而无序发展对于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一大危机。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完整珍贵的民艺资源库,只有在以文化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在发展策略中,进入市场和非遗的商业化在以非遗的文化传承为先导的基础上,才能在长远发展中实现永续利用,并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中走出独特的路径。
而此时,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表演性文化交流并鼓励传承人销售产品增加收入的外向型文化交流,这样的文化交流给传承人创造了售卖产品的机会,导致非遗传承人开始成立合作社、微型企业,加快步伐进入市场。而我们都知道,传统手艺人制作的生活用品是用于自身祭祀、婚丧嫁娶的重要仪式性活动的物件,或是用于日常生活穿戴的传统物件,是在祖辈流传的文化体系结构里,具有固定技艺和功能的物件承载了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符号型和技艺。
当面对现代城市生活世界对物件的诉求,这些传统社区的物件无法直接融入城市生活功能结构。除了少数收藏者可直接收藏作为文化艺术品的欣赏、研究和藏品,传统社区的文化艺术和生活用品无法直接满足多数城市人群消费的需求。非遗传承人摸索和试验制作各种迎合进入城市结构的功能性产品,而非专业化和非职业化的制造从人力投入和时间成本上都大大高于成熟的工业化生产体系。而且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不仅没有生产出可进入市场的产品,还极大地打扰和占用了完成“那一件小而美的手工艺术”的时间,从而降低文化传承的可能性,并在长时间的生产和生命时间中,丢失文化核心技艺的传承。
在未经过专业培训的技艺前,许多产品中完美的手工刺绣里,含有珍贵文化价值的符型与廉价的材料相结合,做成一些具有功能性的产品,以期能进入市场立刻增加现金收入。事实上,非遗传承人的核心技术是完美的手工和文化符号在各种民族技艺上的呈现,而不是花双倍的时间在制造一件完整的产品上,集中所有时间在手工文化技艺的制作上,先大大提升非遗传承人手工的附加值,在市场中占据独有的一席之地,从而在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和定位,而非盲目的都成为产品制作的公司。
目前,中国正在大规模介入的非遗保护和培训,以主流工艺美术和设计为理念,正在破坏民艺的生态环境,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倾向于制造市场认可度高的和技艺简化的图形,大量的苏绣运用到贵州苗绣丝巾的运用,极大地降低了苗绣技法的多样性,于长远来看,将在短期市场行为中破坏苗绣的传统技法和文化符型传承。地方政府推动的绣娘传承计划培训,亦在鼓励绣娘绣市场上流行的技法,比如在市场上运用较多的打籽绣,在黄平、雷山一带被培训公司大量鼓励绣娘使用,从而忽略了当地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唯一性苗绣技法,比如濒临失传的破线绣和双针绕线绣等比较复杂的古老技法,在苗绣中视为最珍贵的技法,所达至的工艺水平和讲述的上古时期符形非市场中几朵好看的简单花鸟图形和平绣能媲美。
因此,在民艺运动中当务之急,是要唤醒人们的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的觉醒和文化认同,以更多的基础性研究和故事文本来解读民艺的核心价值,去市场主体为导向的“什么好看绣什么,什么好卖绣什么”的单项做法。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市场和生计为主体的传承模式,事实上,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模式一直是我们倡导和行动的一个主体方向,但是,我们反对没有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可的唯一性的市场主导方向,盲目的市场指向磨灭文化的多元性价值,从而制造无差异性的标准化旅游商品。
以无序市场为推进的非遗生产性保护,缺失基础性研究、民艺故事、传统工艺调研、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材料融合的研发性项目推进,无研究如何运用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体系和发展模式,对于资源性短期运用和产业快速制造产品进入市场的发展运动,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传统技艺都将是一次替代性的发展运动,这对于未来民艺的发展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下一代人很难寻找到被我们这一代人“文化制造”和文化替代中的“文化原型”,从而无法识别古法文化智慧的原生性动力,在各民族璀璨的文化星河中无法拾起那一枚闪亮的符型,不能直达一种原生性文化的美,无法共享人类文明各个时期创造的文化遗产,无法享有并运用它们为自己带来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发展策略上无意制造的文化性的不公平。
文化扶贫和扶贫文化的悖论再一次出现,文化扶贫在降低文化持有者的古老文化性,而扶贫文化让文化无法植根于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基础之上,只是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和商业炒作的媒介和工具。文化成为一场公共的表演,成为一场视角性的表演,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和危机。事实上,我们所做的都立意于一次“更好的发展”,为我们传承更美好的文明,为每一代人能共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价值,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做更好的发展策略,用精细的发展哲学来建构一些好的发展模式,引领一个好的发展范式,建立一个精神共同体,认同文化的价值,认可民艺在中国文化中的组成部门,从政治结构、权利结构中解放民艺的自身,直达一种公正的审美,看到民艺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从而实现大众的文化认同,建立公正性的民艺发展模式。
随着贵州文化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回归文化的思潮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保存本土民族文化、向社会大众推广质朴的民艺之美,以及民艺运动所阐述的农舍市井日常用品之美,使地方上幸存的民间手工艺传统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对民间美术理论和保护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大量的珍贵民艺遗产,以多民族多元共生的文化性留存大量珍贵的生产生活民间艺术品,基础性研究和出版薄弱,以“口述史”视角出发,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讲述的民艺还未见出版。贵州民艺口述史系列丛书,旨在通过民艺的基础性研究,以传承人讲述为主体,重新搜集整理出版贵州山地生长出的丰富文化遗产,并以生活艺术和艺术生活为表达方式,在以人为主体的叙述中再发现贵州民艺的现代价值。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寨子里生长出来,从村寨里生发出来的祖先记忆和文化视像。寨子在中国的原始聚落中为最小单元,贵州寨子如一个小小区隔,在大山之间一方偏僻之处十几户到上百户人家,多民族聚集生活,与自然和谐共生,农耕劳作生长出祖先崇拜的神圣仪式,精微繁复的手工是手工者对神灵和祖先的敬畏,是自己和灵界对话的媒介,是看待世界的纯粹审美和公正对待世界的原初表达。
贵州多民族手工艺存留的符形直接承接上古时期的文明,对探寻中国文明之源具有重要价值。一直被视为贵州民间艺术不仅仅是民间艺术,而是上古新石器时代部族、方国的遗留,相当于国家这一级意义的遗产。一代代的民族迁徙史和保守性神灵文化使其得以传承,或者是祖先崇拜的需要以及族群定义的神学意义,使其在固执的仪式场域和生活场景得以传习,代代相传上万年。而贵州多民族手工艺所承载的文明起源的重要性,如果不被认知她对上古文明起源的伟大贡献,我们将永远不能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贵州多民族文化具有后现代主义审美的价值取向,民族手工保留上古文明的珍贵符型,留存的手工艺不仅属于中国,也是这块土地留给世界最宝贵的贡献。贵州的多民族文化不仅仅在中国是突出的文化多样性表达,在人类文明史的工艺美术史中含有非常重要的份额。我们相信,集聚具有文化使命感和创意精神的一群人,在一起带着对贵州多元文化价值的认知和认同,参与多学科多族群互动交融,城市和乡村交流互生,将引领手工记忆新的生命力,新的中国流行文化将生长起来,让手作之美为传统价值的媒介向世界表达中国,并代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中国文化与世界交流和对话。
二、贵州民艺基础性研究及“口述”文本
贵州民艺口述史系计划每年以1-2个艺术门类为基础,从村级田野工作为单元,采集仍活在村里从事民艺活动,按照传统仪式为自己制作仪式、生活用品,以及参与到市场中进行现代民艺旅游类商品再造的民间老中青民间手艺人,进行系统的艺术家口述史记录,图文并茂出版设计精美,能够传承贵州民艺文化遗产,又能为现代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做支撑性和指导性,协助城市和乡村“生活世界”彼此融合沟通,把传统文化仪式性的民族功能性民族艺术,带入具有现实关照性的现代城市生活世界,以开启基础性研究切实为文化旅游产业,为现代生活美学构建产生文化性认同为基础的发展哲学,并通过出版,当代艺术展览以及媒体文化传播互动,倡导民艺回到“生活世界”的现代生活美学艺术。
新近出版的《寨生—手上的记忆》是以行动为基础,以蜡染图形的故事解读和妇女发展叙事记述为文本,出版的深度文化故事书籍。在2009年到2011年的研究中,本书以榕江县塔石乡宰勇村乌吉苗寨的蜡染为载体,从当地两个苗族妇女的当代生活历程观察及图形故事口述中,对该支系的数百个图形进行蜡画、蜡染和绘画等载体上的解构式解读。
这些图形在以往的蜡染形态中,都是放在同一张画布上的,从来没有人对它们中每一个单独的图形进行分类解读。在近1年的“蓝花工作坊”中,两个苗族妇女在“小梅访谈”栏目工作室一边画画,一边解读图形上的故事,作者进行一一录音、记录和整理,3年后出版成书。书的出版对一个村落的蜡染进行系统的符号解构和故事性讲述,搜集进入书本的大量图形正在被一些文化产业公司广泛采用。
本项目定位于行动项目与研究结合,源于我们的几点认识:一是行动项目的时间短、重项目、轻研究,导致项目反思不足,对当地的文化了解不深,往往是参与项目的几个人草草操办几个活动,写几个报道向资助方交差了事;二是基础性研究成果为后来者深入了解某一个社区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而及时的反思将有助于项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持续效应;三是研究成果解决了社区长久存在的文化故事发掘、民族叙事的缺失,这对于民族文化产业走以文化为导向的产业化路径提供了可贵的参照。此外,粗浅的资料堆积,以专家学者为主导的文化解释已经不能满足外界的需求,也不符合当地发展诉求。故事发掘、梳理文化的肌理和细部,能让外界更多地了解本土文化,在贵州民族手工业产业走向国际化的探索中,为其增添国际性的符号。
当人类进入当代社会,永不停息的变化成为周遭世界最显著的特征。当我们的生活伴随着当代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的改变而开始出现趋同、类型化的时候,我们更加渴望与追求能够充分舒展自己个性、保留本土文化与传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理想。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渴望回到村落时光,通过行走、观察和触摸,通过听村子里的手工艺人讲述一个村落、一户人家或一朵蜡花的故事,让自己那些深埋在心底的古老情怀在当下得以唤醒。记录着自己民族古老文化与传统的记忆,一幅幅绽放在蓝色蜡染布上精妙的图案,就是一个个浓缩的美丽故事,在细细讲述着苗族人的历史、现状和对未来的期盼。
长期以来,蜡染作为传统艺术形态的研究,收藏界的粗线条地告知其来自哪个区域的出版物不少,而作为农耕民族仪式性符号和生活叙事的形态,被精英文化学者讲述,由文化持有者自己口述的生活叙事很少。作者深入思考贵州民族文化研究的历史状态,对于传统手工艺的研究多局限于出自哪个区域、哪个族群,采集资料多为图片和少量的文字作了改进和完善。
由于长期把贵州民族手工艺看成是民间艺术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在产业领域的时尚、现代性创意产业中的延伸和产品研发,从而产品形态还停留在民间艺术在城市里偶尔受到小众消费群体青睐的状态。这种认识,也极大地限制了研究人群和研究范围,从而使多年的民族手工艺信息停留在粗线条的勾勒和图片性展演上,基础性研究资料单一,信息比较粗,很多书籍简单复制以往出版物,很少有一手的原创作品。
这样的思考促成了作者对于“蓝花”系列的创新性研究。我们会问自己,那些民族手工艺的图形都很好看,可是她是如何而来的?她的历史细部在哪里被呈现过?她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基于这样思考,作者在近5年的时间里,从不同侧面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集中对丹寨县、榕江县7个村寨的人类学研究、参与行动项目中,逐步搜集当地人讲述的故事。作者认为,以本地人讲述的故事原真性地复原了历史的信息,即便是年轻人讲述的古老信息在减弱,也是从祖辈那里一代代传递下来的,至少比精英学者讲述的有些一知半解的故事要好。在基础性研究中,相信这些文化性符号能为文化产业服务,达成贵州多元民族文化从农耕文明时代,以文化符号进行故事解读、设计创意进入当代“生活世界”。这种立意让研究本身具有现实关照性,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处处留意对故事的发掘和对图形符号的解读。
在跟踪调研、访问榕江县塔石乡宰勇村乌吉苗寨的苗族妇女杨妹和李妹的过程中,在2年的田野工作中,发现蜡染作为苗族妇女从传统村落进入当代都市的交往媒介功能日渐明显。以此呈现的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商业文明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日益加快,对于这种农耕文明的产物—“手上的记忆”经历文化的变迁、技艺变更、传承人流动和城市的文化互动,让传统手工艺逐渐转变为过去的一种生活记忆和讲述。作者以两个苗族妇女的口述史为核心,系统地看文献,了解蜡染的研究成果;到她们生活的村寨去做田野工作,调研村寨基本情况、村寨发展状况、其他妇女蜡染活动等;连续1年多的时间,每月一次在贵阳进行口述实录,和两位苗族妇女坐下来讲述和记录蜡染图案故事;请两位妇女解构蜡染图形,并讲述每一个图形的故事。
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得出以下结论,从个人独特生命史中切入研究,从细部和微小处发现民族叙事,更能直观地表述蜡染作为仪式性符号在社区中的神话功能;口述史极好地尊重她们作为变迁的个体中讲述的真实性,留下一个蜡染符号的讲述的真实语境文本;“现代性适应”在她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从她们个人生活史出发的民族叙事,将可能从人物的独特经历中镜像这个族群在历史某个节点的宏大叙事;蜡染不仅仅是一门民间艺术,而是涵盖丰富内涵的族群神话功能和生活表达的媒介。
我们认为,在获取榕江系蜡染图案文化持有者——两个苗族妇女为主角的图语讲述,保存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供给年青一代学习和模仿;解读以神话学为基础的原始图语在历经文化变迁的传统村落中已经成为苗族妇女向往交往的一种重要工具,她们自身也在此重塑和再造蜡染文化符号的意义本身,以此为基础的符号讲述弱化了传统社区仪式的功能,作为神器的手工艺正逐渐演变为市场的商品,这极大地强化了作为文化持有者推动的“市场趋势”,使其完全可以作为当下政府和学界推动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对象,面向“过去记忆”简单呈现的“原生态”文化表达的启示和借鉴。
传统意义上,蜡染是与符型祭祀、仪式有关,用于婚姻、葬礼、出生、祭祖及重要节日活动,只有巫师知道这个知识体系。一般艺人只会画,后面的图形解释和说法都是“再造”的。她们目前画,有三个意向:画给神灵(也是护佑自己平安,去世后去到祖灵之地);为日常生活使用所画(打扮自己及表达对亲属的爱);还有就是为外来者的购买所画(为家庭生计所画)。三者都是为自我的生存之道和去世后的灵魂安顿问题。研究艺人为何画?画花对她们意味着什么?市场中的画花者,画花对她们的意义是什么?文化变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点。
贵州多元民族文化的传承在现代性语境下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以具有现实关照性的现代手段来解决。在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及其传承人的十几年的工作基础上,我们逐步建立以基础性研究、口述史、公益性文化项目为构架的工作推动模式,逐步寻找以实现生计和青年人文化认同和生计模式的传承模式。因此,研究方法为:行动项目+基础性研究——称为行动研究,应属应用人类学范畴。主要以民族志记录、开放式访谈、口述史采集、长期的公益性行动项目与村寨从事手工艺制作的人群交往。
三、民艺的公益实践:以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为例
贵州多民族手工艺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如果不被认知,我们将不能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建立文化的本土性认同与以文化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同等重要,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大力传播和传扬贵州多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建构以文化为基础的发展,在贵州省成为引领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公益性文化领航项目,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成为贵州推动民族手工艺传承和发展的一个核心项目。
我们认为,建立城市和乡村互动和交流的平台,让城市更多参与到本土乡土文化的认知和实践中来,城市支持乡村手工艺者共同参与协助进入市场,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一直以来,我们以艺术的眼光来审视民族手工艺,以乡村艺术家的身份来看待手工者和传承者,认为不断在城市的展览活动中,能增强乡村艺术家自身的能力,能让更多的城市人群认知到贵州多民族手工艺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叙事同等重要。
从2015年开始,花旗集团基金会持续支持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已5年。五年间,我们按照项目目标严格执行完成各项活动,大力传播和传扬贵州多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建构以文化为基础的发展,在省内认知度和国外交流上,均取得丰硕的成果。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在贵州省成为引领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公益性文化领航项目,得到贵州省委宣传部、贵阳市委宣传部、贵州省出版集团、贵州省新闻出版局、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重视,开始生长为贵州推动民族手工艺传承和发展的一个核心项目。
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注重展览和推广活动,建立城市和乡村互动和交流的平台,让城市更多参与到本土乡土文化的认知和实践中来,城市支持乡村手工艺者共同参与协助进入市场,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我们以艺术的眼光来审视民族手工艺,以乡村艺术家的身份来看待手工者和传承者,认为不断在城市的展览活动中,能增强乡村艺术家自身的能力,能让更多的城市人群认知到贵州多民族手工艺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叙事同等重要。
本着这样的基本价值认同,我们在项目几年时间,先后在贵阳成功举办3次展览活动,包括搁浅在时光村落里的蓝花: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百个苗族家庭的故事”慈善义卖活动、跨界·贵州公益艺术沙龙”《蓝花叙事》新书发布暨部分藏品展、跨界·民艺风物展/尘仪式等展览活动。
去年在北京的展览是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在2015年项目期的计划,将全面呈现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5年的项目成果,回顾展里将全面展现项目出版、基础性研究、设计、印刷的资料和作品。项目支持的3个县、十几个村寨的手工艺发展协会的蜡染、刺绣、织锦、手工纸的老物件和新产品数百件将参与展览。项目还邀请十几位青年艺术家用贞丰手工纸作画,以“再一起”呈现传统和当代的互动与“再生”。除此之外,项目衍生的贵州省首个文化公益品牌“蓝花叙事”和蓝花基金展示及长期的合作伙伴苗疆故事品牌和贵州盛华职业学院文化传承中心的作品,将彼此融入并相对独立地参与到展览中来。
“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始于2010年,旨在通过帮助贫困少数民族手工艺家庭作坊提高传统手工艺产品的生产和营销技巧,从而提高收入水平,传承并发展民族文化,保护和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与环境。该项目由花旗集团基金会资助,希望通过企业、民间组织、政府部门多方合作,积极探索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重目标有机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贵州省丹寨县、雷山县、贞丰县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县之一,村寨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低于1 196元。自2010年开始,由花旗集团基金会资助,贵州师范大学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和《贵州日报》“小梅访谈”栏目共同实施,在丹寨县11个苗族村实施扶贫项目。5年来,围绕蜡染、古法造纸、织锦、百鸟衣、锦鸡刺绣和米酒酿造等民族传统工艺,支持、建立了11个少数民族手工合作社,实施了大量生产技能和合作社能力培训,直接培养少数民族手工艺者近500人,提高了手工艺品的生产制作水平,并在不损害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提高了产量和质量;通过建立合作社产品销售点和在线销售,帮助手工业者与市场对接,增强手工艺者的谈判能力和定价话语权,并推动产品研发和销售。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使8 000户贫困少数民族家庭(近3 000人)平均年增收达30~40%以上。
在过去5年,贵州花旗手工业发展项目开展了以下的活动:支持、建立了11个少数民族手工合作社,通过出国访问、专家授课、参观和同伴技能等方式促进她们综合能力的提升;传授等能力建设活动,直接培养少数民族骨干(职业)手工艺人近500人;推动产品研发和产品销售;帮助手工业者与市场建立连接,在丹寨、西江、贵阳等地建立了5个合作社产品销售点,帮助8 000多户(30 000人)贫困少数民族家庭平均年增收30~40%以上;选择了100户苗族家庭搜集的125件代表作品,进行慈善竞拍、义卖,并在网上持续进行;邀请盛华技术职业学院和“绝对贵州设计师联盟”设计团队合作,推动合作社能力建设和产品设计;建立了一个产、学、研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及经济发展的平台;举办蜡染义卖、跨界、新书义卖和绝对贵州文化创意周展览等公众活动,在媒体的支持下,推动大众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和黔包、黔萃行等企业、贵州盛华职业技术学院、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合作,探索贫困社区民族手工产品在线销售的模式;建立了旨在帮助贫困少数民族妇女进行传统手工生产的“蓝花基金”,推出“蓝花叙事”公益品牌。
项目旨在支持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搭建手工艺者与产品市场的桥梁和平台,推动贵州民族手工艺文化机制认知和认同度,提高目标群体的生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协调资源分配,增强环保意识,实现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发掘文化故事,助推乡村艺术家参与创意文化产业,走小而美的精细发展路线,实现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建立城市艺术家和乡村手艺人互动和交流的平台,建构城市支持乡村手艺发展的支持系统;建立多群体支持网络系统,合作伙伴支持发展平台系统,促进跨学科跨群体互动参与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推出“蓝花叙事”公益文化品牌,助推“蓝花公益基金”持续支持乡村手艺人进行内生性的手工传承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实施项目的过程,也是一次为基础研究贵州传统手工艺蜡染技艺的故事文本开发历程,项目出版《蓝花叙事》《寨生:手上的记忆》等5本书籍,在对社区内部文化肌理的系统梳理中,发现社区内部自我发展的动力,在一次极具故事性的表述中重新发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价值。
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在贵州大力倡导文化强省、发展文化旅游为支柱性产业的背景下,这种尝试极有可能带我们走向一种以民族文化为导向的文化创意产业,走向社区内部为主导、外部多方支持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现代、时尚的视角,去全新解读、诠释和创意文化活动,不仅符合项目“文化互动、发掘故事 关注妇女”的价值,也最大化地推动了媒体参与到公益项目的实施活动中,实现了以本地公共媒体为主导的“文化影响力社会倡导”的最大化,在对于传统文化物件上图形的系统的深度解读,与现代设计、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的结合,将对产业的以文化为导向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手工艺开发,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花旗贵州手工发展项目团队积极建立跨学科、多团队协作,建立开放式志愿者工作平台,打通政府支持的公益性活动、文化深度发掘、故事开掘、基础性研发、现代设计、市场链等环节,积极探讨《蓝花叙事》公益性文化品牌。我们期待建立一套完整的、有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模式,对于中国都有效仿意义,甚至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一点贡献。
[1] 柳宗悦.工艺文化[M]. 徐艺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 潘鲁生,唐家路.民艺学概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
[3] 柳宗悦.民艺四十年[M].石建中,张 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 柳宗悦.日本手工艺[M].张 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5] 王小梅.寨生:手上的记忆[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5.
[6] 杨从明,任晓冬. 参与式发展 贵州的探索与实践[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蒲 涛]
“Chinese Metaphor” of Folk-CraftEstablish the Regeneration Way to the Localization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Folk-Craft
WANG Xiao-mei
(GuizhouDaily,Guiyang,Guizhou, 550001,China)
Based on the cases of Japanese folk-craft practice, the present study mainly illustrated the Chinese folk-craft activities. It wa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folk-craft based on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fields and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folk-craft. Furthermo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l model should be established related to mainstream arts and crafts, the heritage of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and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model could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values of folk-craft and its cultural values in modern society so that the modern aesthetic system and self-development system of folk-craft could be constructed. Eventually, the regeneration way to the localization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folk-craft could be established.
folk-craf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ocalization practice
2016-11-02
王小梅(1976-),女,贵州贵阳人,贵州日报高级记者,贵州省人类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G122
A
1674-621X(2016)04-013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