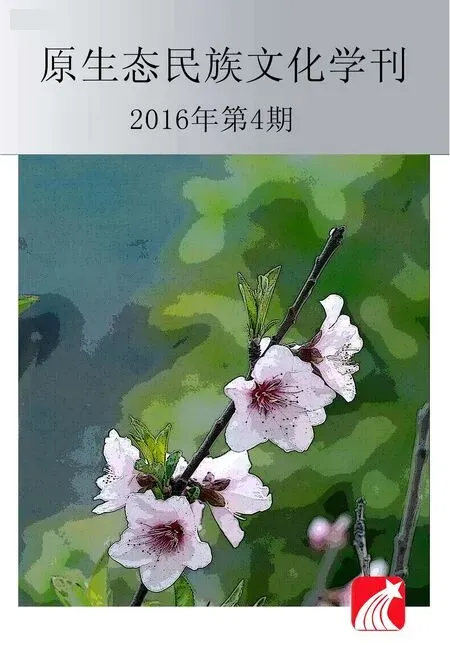村落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有机团结之耦合关系
——以绥宁上堡侗寨为例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1)
村落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有机团结之耦合关系
——以绥宁上堡侗寨为例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1)
上堡侗寨熟人社会中“礼”的馈赠体系、唇齿相依的生态格局与情感依恋产生共命运的社会心态,这与村落共同体的结构与功能共同构成寨民集体记忆之前提条件。英雄传说、历史遗迹、节日庆典与身体实践等延续和再造着集体记忆、族群身份与共同体的团结。集体记忆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符号和实践系统的各种表征之中,是确保集体身份和社会秩序连续性的重要条件。反记忆则代表着被边缘化个人和群体的抗争性叙述。集体记忆充塞着神圣仪式之外的世俗时间,起着类似于世俗道德的规范性整合功能。
历史英雄;仪式;共同体;集体记忆;社会团结
“社会团结”或“社会如何可能”是社会学领域中的基本主题,从迪尔凯姆对宗教仪式的探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等都围绕着这一经典命题而展开。1902年,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hal )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集体记忆”这一术语,迪尔凯姆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纪念仪式的论述和哈布瓦赫对记忆之社会框架的探讨等都是对集体记忆较早的论述。在仪式性的集体欢腾中,社会通过仪式和庆祝活动确保自身的更新并重新创造关于过去的集体形象。秉承迪尔凯姆的衣钵,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并非是主观心灵状态的反映,而是反映了心智如何在社会中相互协作、如何被社会设置结构化。然而,迪尔凯姆范式留下的问题在于:在世俗的、平静的和寻常的社会时期,集体记忆又如何保存?在日常生活中(也即在神圣仪式之外的时间)社会又是如何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本文认为,集体记忆储存于日常生活过程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实践之中;在了解湖南绥宁上堡侗寨村落结构的基础上,试图探讨集体记忆在村落共同体的团结中具有的整合功能及其表现形式。
一、上堡侗寨:“熟人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湖南省绥宁县的上堡侗寨历史悠久,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平民李天保组织万余西南边陲民众起义,在上堡称王封将,年号“武烈”,在上堡、界溪、赤坂等地建立中央、省、府、州、县各级政权,曾一度震动朝野,后被惨烈镇压。自明清以来,上堡村寨的格局与规模几经变迁,终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与外界沟通较少,至今仍发展相对滞后。上堡也因此得以保存相对完好的侗寨村落布局、社会结构和生活习俗。随着1998年上堡所在的黄桑坪乡成功申报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1年“上堡武烈王故城”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些年上堡在外界的知名度也迅速上升,慕名前来的游人络绎不绝。
上堡侗寨的经济结构相对简单,没有工业和服务业,旅游业尚处于筹划开发阶段。村寨的林业资源丰富,因此它的生业也与其息息相关。上堡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对林业保护方面的补贴。大多数寨民的家庭经济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缺乏商业意识。乡政府曾鼓励、动员寨民动手编竹篮盛土特产,以整篮出售给外地游客,但是始终难以成气候。寨民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通过一些重要的家族事件来维系,从而形成礼物流动的馈赠体系。在发生重要的红白喜事时,如房屋上梁、生子、丧葬、结婚和祝寿等,全村老小都要参加。以前寨民相互之间送粮食、牲畜等实物,现在都送红包,根据关系亲疏远近的不同,少则五六十元(外亲),多则五六百元(内亲)。受礼者在以后适当的场合必须回礼,回礼的价值往往超出赠礼,但回礼也意味着今后接受新馈赠的权利和机会。这种非市场方式的经济交换活动对于没有工资和商业收入的普通寨民而言具有重要经济和社会作用,它不仅可以作为家庭日常经济收入的补充形式,而且也为增加亲情提供了机会。全村寨的人们通过这种“礼”的流动从而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连带关系”。因此,上堡侗寨是典型的“沾亲带故”的熟人社会。一方面,这种“连带关系”是就房屋建筑等物理实体而言,村落中木结构的房屋鳞次栉比、紧密相连,从而形成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左邻右舍之间唇齿相依的彼此构建使得寨民肩负着共同的防火、防盗责任;另一方面,它也是就情感关系而言,这种“连带性”成为村寨治理和族群认同中的重要属性。连带性的社会关系和互依性的村落布局结构使寨民共享同一个生态圈,从而强化了集体认同感。全寨人们不仅在历史上荣辱与共,而且现实生活中亦息息相关。
在上堡的组织和管理体系中,除了由村长、支书等构成的官方行政系统外,还存在其他地方性的运作形式,较为典型的如“红白喜事理事会”。该理事会的成员一般3-5人,由村寨中的年长者或有威望者担任,现任的理事会成员包括村支书、村长、前村支书、妇女主任等,寨民凡操办红白喜事等都要由理事会负责。但是现在开销比较少的活动,尤其是只办两三桌的小规模红事大多由寨民自行操办,而不通过理事会进行。虽然该理事会在村寨中的实际功能已大不如前,但寨子里的白事仍然少不了理事会的张罗。在上堡的社会结构中,寨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寨老通常由全寨人选举产生,没有具体任期,但是倘若犯了严重错误则可以撤换,现任寨老已担任40余年。选择寨老的条件是要有威望(会看风水是获得威望的重要途径,而看风水的职业通常是继承的)、为人作风正派,并且已结婚生子。寨老兼管上堡的侗族和苗族,其职责和事务除了为寨民看风水之外,最主要的是主持一年四季重大节日的祭祀活动。他还参与地方管理事务的决策过程,村长、村支书若碰到重大事情都要和寨老进行磋商。
村委会、村党支部等这些实体组织和寨老这样的卡里斯玛型人物分别掌管着上堡侗寨的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寨民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共同遵守的“约定俗成”,也即所谓的“款约”,它在村寨的管理中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无形中制约和规训着寨民的日常生活。“上堡侗寨款约”共计8条,具体如下:
一、寨内树木不得砍伐,砍伐树木一株须补栽十株,娶亲生子做寿者、要栽种树木一颗。
二、不得打架斗殴、押宝、抽大烟、偷盗钱财,违者罚打更半年,男女间伤风败俗者驱赶出寨,终身不得上萨坛。
三、私人住房一天一小扫,一场(注:五天)一大扫,破坏寨子干净者,扫寨子一个月。
四、喂好自家牲畜,牲畜损坏庄稼的,主人秋收后赔偿稻谷。
五、金銮殿、忠勇祠、鼓楼、栓马树、萨坛、门楼、护林碑等古物,不得乱画乱刻、不得随意烧火、不得乱推杂物,凡损毁古物者要负责修复。
六、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柴草不得入户,睡前须熄灭明火,造成房屋失火殃及他人的“火头”要用一头牛、一头猪、十只鸡请全寨人吃饭。
七、拜萨大会、寨老会,各户均需参加,缺会一次,缴白米两升、香油一斤。
八、以上款约希寨民共同遵守。
该款约几乎包括了上堡寨民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重要方面,如护林、防盗、民风、卫生、牲畜与农作物、遗迹保护、防火和宗教仪式等。
近些年来,如同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形一样,上堡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村寨中留守的大多为老人和儿童,“空巢村寨”的趋势明显。这种现象对上堡侗族的价值观、民族传统、经济结构和人群组织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社会在遭遇现代文明时很难逃避被同化的命运,同化的关键路径之一便是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导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同质化。关于村寨传统文化之变迁一个实例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上堡寨民还实行“稻田养鱼养鸭”的生产模式,但是现在寨民的稻田里已经基本不养鱼,寨民认为食用在喷洒农药的稻田中生长的鱼对身体有害。因此,上堡侗族已没有“稻田养鱼”的传统。另一个实例是,侗族通常敬狗,素来有祭狗的传统习俗。然而,2010年上堡的寨民打死了村里所有的狗,“没狗干净,它们到处拉屎,还狂叫”,上堡的一位侗族老人如此对笔者说道。事实上,灭狗的真实原因是上堡有意打造旅游之村,乱吠之犬显然影响游客的观赏。现在的上堡侗族已不再敬狗,尽管仍会象征性地过狗节。
二、村落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形式
杰弗里·奥力克(Jeffrey K. Olick)区分了集体记忆研究中两种不同的范式或文化:一种是“集合记忆”(collected memory),它是被社会框架化的个体记忆之聚合,另一种则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即作为自成一体的集体现象[1]。这两种文化或观念分别是集体记忆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阐释取向,“集合记忆”是包含了神经学和认知性等因素的心理学取向,它认为将集体记忆视为超越个体的客观象征或深层结构可能会陷入集体心灵的形而上学之泥潭。从这种视角看来,社会框架确实形塑个体的记忆,但最终只有个体才能记忆,而共享的象征与深层结构只有当个体如此看待它们或付诸于实践时才是真实的。“集体记忆”取向认为社会性的某些模式和属性无法还原为个体性层次和心理过程,它强调公共的、个人的记忆之社会和文化的模式。诸如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理论明确反对弗洛伊德式的和其他心理学的阐释,由于存在记忆的社会框架,它使个体能够置身于这些框架内并回忆过去。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构成社会的各类群体在每时每刻都能重构其过去,尽管这个重构过程可能会出现歪曲、筛选等。在哈布瓦赫看来,个体在其所属的群体情境(group contexts)之外无法以任何连贯的、持久的方式进行记忆。事实上,这两种范式都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集合记忆”视角忽略了大脑之外的记忆术以及社会过程中认知性和神经学模式之外的记忆构成方式;而“集体记忆”视角忽略了这些过程中心理学动力机制的记忆构成方式。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范式都有助于理解集体记忆。对上堡侗族来说,明末的“武烈王”李天保以及他率领西南少数族群进行底层反抗的故事是真实的,并且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个体幸存者失败、屈辱的经历通过各种记忆术而逐渐结晶成今天上堡侗族的集体心灵创伤。个体性的创伤被外在化和客体化为各种表征形式,它不再是纯粹的个体心理问题。记忆的集体属性体现在神话传说、日常实践和话语叙述中,因此李天保及其事迹并不会因为亲历者与后代的逝世而消失,它作为民族文化与英雄符号会不断地得到延绵。家族的记忆、村庄的记忆甚至民族的记忆可以通过历史遗迹、口头传说、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等形式保留下来。这些记忆术的主体和承载者正是活生生的个体。个人从所处的时代、社会与家庭中获得某些记忆,从而形成个体的“心理构图”(schemata),并通过这种心理构图建立社会认同结构[2]403。王明珂认为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强化和凝聚族群认同是根基性的,因为族群以共同的过去来强调“同胞手足之情”。同时以集体记忆凝聚的族群认同也是工具性的,因为“共同的过去”可以被集体性地选择、遗忘、拾回甚至创造,从而在人群的互动中集体选择、重组、争辩“共同的历史记忆”,同时创造、保存共同的当代记忆[2]405。通过这些形式,个体记忆终汇聚升华为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
个体性记忆是破碎的、凌乱的,有时甚至会出现自相矛盾、时空错乱的现象。集体记忆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它也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是指向过去的记忆与指向当下的理性之间相互作用、协商和竞争的产物。这是一种历史的想象、现实的诉求之体现,它甚至是个人的表演或创造。集体记忆受到历史与现状的制约,也就是说,记忆的社会建构并非是任意的。社会群体所保持的记忆话语不仅能够策略性地解释过去,而且还可以被转换成一种当下可依赖的身份资源。神话传说、英雄故事、历史遗迹、节日庆典与日常实践等这些方式延续和再造着集体记忆、民族身份与共同体的团结。日常生活中的地点、纪念仪式和身体化的实践方式都起到维持集体记忆连续性的作用;换句话说,社会或族群的记忆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惯例化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40。除了口耳相传、文本书写与镌刻以及静态的历史建筑物来表现之外,记忆还包含在动态的身体化实践中。侗族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集体仪式和生活实践等方式来维持和强化集体记忆。在上堡侗寨,集体记忆的维系和强化方式包含了多种形式。从村落结构上看,全村寨的人都彼此相互认识,甚至可以说都是亲疏程度不同的亲戚。这样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礼”的馈赠系统勾勒出了身份认同的边界与轮廓,唇齿相依的生态布局与情感依恋产生一种共命运的社会心态。寨老与村委并行不悖的双重管理体制保证了村落共同体的稳定与延续,乡规民约则规制了寨民日常生活的具体运作。熟人社会的这些基本结构和功能是村落共同体中集体记忆运作的基本现实和前提。除了这种结构性条件之外,上堡还有着其特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在上堡,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萨坛祭祀等仪式,通常由德高望重的寨老主持,全寨男女老幼必须参加,这些集体仪式维系着寨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历史英雄李天保及其建立的武烈王国成为上堡集体记忆的关节点。直至今天,村寨仍保留着李天保起义时期金銮殿、忠勇祠、烟墩(烽火台)和旗杆石等遗址,并且当年义军的跑马场、点将台和练兵场等地至今仍然依稀可辨,很多寨民可以逼真地在现场还原李天保在其势力鼎盛时期风姿飒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壮观景象。作为少数族群的集体创伤,上堡一带还保留着反映当年义军被镇压后之惨烈状况的遗址,如臭人田、乱葬岗等,再现了集尸填谷、烽火狼烟、血流成河的悲壮场面。这些物质记忆形式在今天不断地得到复活并强化了上堡侗族的集体记忆。这些历史记忆中的悲壮与伤痛,告诫着人们勿忘民族的屈辱与异族的杀戮。侗族至今仍保留着一些传统的竞技项目,如走刀梯、滚刺床、爬藤绳竞技等。此外,集体记忆还可以表现为身体化的实践方式,如侗族的爬树藤竞赛,以及“四八姑娘节”时的背媳妇、摔跤等。
三、集体记忆、反记忆与社会秩序
在世俗社会中,取代宗教作为规范性整合之基础的是世俗道德;在某种意义上,集体记忆与世俗道德一样,也起着共同体的规范性整合功能。阿斯曼(J. Assmann)区别了4种记忆模式:模仿记忆,它维系着过去的实践知识;物质记忆,它是包含于物体中的历史;沟通记忆,指语言与沟通中关于过去的剩余物;文化记忆,它传递着关于过去明确的历史指涉与意识之意义[4]9。作为迪尔凯姆的弟子,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尽管他没有使用迪尔凯姆大写的“社会”(Society)而是采用“群体”(Group)的表述形式,哈布瓦赫仍然具有强烈的反个体主义倾向。为维持社会秩序与团结,社会必须消除和抹除那些导致个体彼此分离和群体相互疏远的记忆,社会在每一个时期需要以某种方式重整记忆,以适应社会均衡条件的变化[5]304。在哈布瓦赫那里,历史或过去不是被还原或恢复,而主要是由当下主体的信仰、旨趣和愿望所形塑。记忆与想象受历史与现实的形塑,记忆之间会产生相互替代、补充和竞争的现象。当记忆一旦开启反思进程它便不再是过去的简单重现和再生产,个体会通过推理、想象等方式来重构记忆。“正是理性或者说理智,按照一种符合我们此刻观念的秩序,在库存记忆中进行挑选,抹去其中一些,并对其余的加以排列”[5]304。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的集体属性受制于由指向过去的观念构成的框架,“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种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与现在的观念能够共存的原因”[5]312。
一个民族的历史创伤亦可以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作为共享的知识而集体建构一种想象的过去。现实的形态塑造着历史记忆及其表述方式,共享的文化创伤与自我认同追溯和确证着族群的渊源。社会记忆是社会之间或内部的联结组织形式,它包含的一些实践方式,诸如庆典、建筑遗迹以及传统、神话或身份等,正是这些现实文本中的符号表征促成了英雄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原迹再现,从而使历史英雄的故事结构被赋予日常生活的稳定形态。地域性的历史与认同通过这种方式被创造并在操演中得到延续,它甚至赋予民族主义以地域的想象力,进而成为整个村落共同体的集体历史表述形式,从而完成了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以确保村落共同体的团结。由于集体记忆是由当下的主体建构的关于过去的图像,其本身是主观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充满矛盾的,甚至是欺骗的、迷惑的和自私自利的。这表明了记忆的选择性和阐释的任意性,但是记忆并非可以任意塑造。历史的背后总会不可避免地残留着一些模糊性和不可理解性,对超越客观的、统一的和有序的历史之认知需要当下的主体参与互动,而这为主体的主观性认知建构创造了机会,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记忆是历史的他者”[6]56。
在绥宁县的历史档案中,关于李天保的记载只有轻蔑的寥寥数语,在官方的立场看来,他既不是王,也不是英雄,更不是神,只是妖言惑众的“妖贼”。可是,在上堡侗寨的民间记忆中,“武烈王”李天保却是为民请愿、勇于抗争的卡里斯玛式人物,他作为一种符号已经渗透在当地的神话传说、日常语言和生活实践之中。民间记忆与官方发明或编造的传统和记忆之对抗表明底层的人们能够自下而上地建构自身的反记忆或抗争性记忆,人们反抗与他们自身的回忆或感觉相抵触的叙事,从而与制度化的支配性官方叙事相抗衡,其背后隐含着历史叙述权的争夺。在关于集体记忆的宏大叙事中,非官方的民间阐释通常被忽略、篡改、错置和边缘化,反霸权的和颠覆性的记忆构成了反记忆形式。这种底层的反记忆对应于支配性记忆和公共话语,民间记忆作为底层反抗的重要形式将唤起正义、不畏强暴的自然情感,勾联起共同的信仰、传统以及英雄祖先。宏大叙事代表了政治精英对大写的历史之有意识的建构,而反记忆则代表着被边缘化个人和群体的抗争性叙述。民间记忆的选择、润饰过程亦形塑着记忆主体的替代性意识与身份。历史人物、场景和事件通过各种记忆方式得以重新复原,遗迹符号、身体化实践、习惯行为、口头传说以及节日庆典等唤醒了维系村落共同体历史的重要事件,通过它们锚定对过去的集体想象。这些生活和记忆实践能够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是保证集体身份和社会生活连续性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过去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符号与实践系统的表征之中。
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共同的历史构成的,因此,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可以说是一个“记忆的共同体”。为了不遗忘过去,共同体需要通过各种实践不断地重复、转述故事及其构成性叙述[7]。在这种意义上,关于英雄人物的记忆起到类似于宗教的功能,李天保在上堡已经成为一位民间的神,它表达和肯定了共享的信仰、命运和村落身份。任何社会都需要一种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连续感,过去能够赋予个体和族群以特定的身份,因此可以将集体记忆视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8],它赋予了社会的连续性以合法性,是创造集体仪式和社会团结的重要因素,它确保共享的道德和社会凝聚力,复苏族群的历史遗产,以重新肯定其纽带关系并巩固共同体的社会秩序。
四、总结与思考
本文重返古典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即社会秩序或社会团结是如何可能的?确切地说,探讨的是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社会团结何以可能?也即在世俗生活中,社会如何将人们整合到一起?神圣仪式之外的时间又是如何维系着人们对村落共同体之历史、文化以及归属感的认同?一言以蔽之,在行政组织、集体仪式和乡规民约之外,如何确保村落共同体的延续性和平稳运行?本文认为,正是集体记忆的建构性、连续性和自洽性确保了处于变迁过程中的村落共同体获得一种社会秩序,想象的、建构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确保了真实的共同体形式和族群认同。集体记忆充塞着仪式外的时间,一方面,共同体的社会团结由现实的社会结构及其互动机制来维持;另一方面则是想象的、不断建构着的集体记忆支持着共同体的身份与认同。现实与虚拟、真实与想象、显性与隐性、行动与思维等共同促进着社会团结与族群认同。它们回忆过去又指向未来,共同交汇于当下的现实,起着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在缺乏迪尔凯姆所谓的“集体欢腾”的社会情境中,集体记忆在日常秩序中充当着帮助人们回忆历史并将共同体聚合起来的功能,共享的集体记忆延续着传统与认同。
[1] Jeffrey K. Olick. Collective Memory: The Two Cul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1999, 17(3):337.
[2]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 1997.
[3] 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 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Jeffrey K. Olick & Joyce Robbins.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8(24):105-40.
[5]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毕 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2.
[6] Allan Megill. History, Memory, Identity.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98(3):37-62.
[7] Bellah, RN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153.
[8] Barbara A. Misztal. Durkheim on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2003(3):123-142.
[责任编辑:曾祥慧]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Memory and Social Solidarity: A Case Study of Shangbao Dong Village
WANG Qing-feng
(InstituteofGlobalEthnology&Anthropology,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
In Shangbao Dong village, the gift system, interdependent ecological arrangement and emotional attachment, together with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village community constitute the precondition of villagers’ collective memory. The forms of myths/legends, hero stories, historical sites, holiday celebrations and everyday practices persisted and reproduced collective memory, ethnical identity and community solidarity. Collective memory permeated i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everyday life symbols and practice system, those symbols and memory practices can preserve and pass on social memory, which guarantee the continua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life. Anti-memory represent as resistant discourses of marginalized individual and group. The social situation absent of Durkheimian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filled with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acts as the function of normative integration as mundane morale.
historical hero; ritual; community;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solidarity
2016-07-23
王晴锋(1982-),男,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与民族学。
C912
A
1674-621X(2016)04-009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