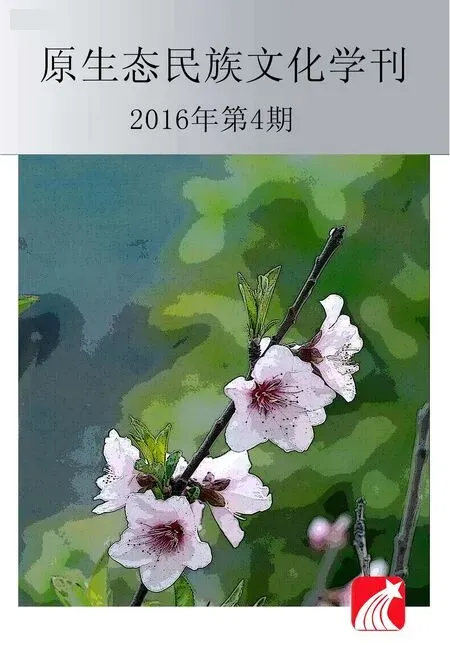农耕文明与传统村落保护
杨庭硕,耿中耀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农耕文明与传统村落保护
杨庭硕,耿中耀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当代的传统村落,大多定型于农耕类型文明,中国是世界上农耕类型文明最为发达的国度,致使其传统村落样式最为复杂和多样。有的是以农田的高度稳定而得以定型,有的则是以当地特殊产品的定型而形成了特殊的村寨结构,有的则是以古代交通道路的走向和集市定型而产生,也有的是因地方性政治中心的形成而造就了特殊政治色彩的村落。特定的文化生态特点和历史背景是传统村落得以稳定延续的灵魂所在,只有掌握其灵魂,传承与保护对策才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传承和保护的措施也才能落到实处。
农耕文明;文化生态;传统村落
一 、传统村落从无到有
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形态,被学者们称为狩猎采集文明。在该文明形态下,人类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需要跟随季节的变化在不同的地点,从事不同对象的狩猎采集活动,以获得生活和发展的物质需求。由于人类狩猎采集的对象在空间分布上各有其规律,而不可能相互重合。因而,随着季节的变化和狩猎采集对象的年季丰度的差异,相关人群还得不断的更换狩猎采集的地点和路线,才能获得理想的收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建立固定的村寨聚落,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过,所谓“居无定所”绝对不应当误解为随心所欲的四处搬迁。其理由在于,人们如果不掌握狩猎采集对象的生活规律及生物属性,有效的狩猎采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既然要随着狩猎采集对象的变化而调整人们的居处方式,因而这样的调整也是有规律可行的。这就意味着,村寨虽然不固定,但人们居处的方式却有规律。换句话说,当时的人们总是在最大限度的遵循规律的情况下,实施有计划、有目的四处搬迁,每到一地都需要建立临时的居住场所,或者说要建立临时性的村落。这些村落与当代所称的“传统村落”区别仅在于是否具有稳定性。但他们在什么地方定居多久,却有规律可寻,而不能曲解为他们仅是“随遇而安”,过着四处游荡的生活。一些学者将这一文明类型下的人们称为“混合狩猎队群”,显然有违实情,只能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一个比喻性的表述而已。既然在该类型文明形态下不能形成固定的村落,今天所执行的传村落保护,当然就不能将其涵盖在其中。
游耕类型文明是在狩猎采集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在这一类型文明中,人们不仅开始从事有目的的作物种植和动物驯化,而且其种植和驯化的物种开始相对集中到有限的某些物种之上。这就为人们深入认知和掌控这些物种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单位面积的产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社区所拥有的人口规模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生息地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稳定。然而,由于人类对自然风险的规避很难实现高度稳定和有效,因而其居住地同样需要做有规律的搬迁,以此规避不可测的自然风险,最终都会导致在该文明类型下的人们每建立一个村落,通常都只能定居一到数年不等。对于那些自然风险较少的地段,村落可以稳态延续的时间长待数十年之久,但一旦遭逢不测的风险或意外的社会打击,村落就得放弃,另外选择有利地段再建新居。就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所称的传统村落保护,当然也不应当把这一类型下的居民聚落纳入传承保护的对象。
对该文明类型下的居民聚落实情,历史学和民族学可以分别提供互有差别的资料,足以帮助当代的人们正确认识这一类型下的居民聚落特点。我国是一个文献大国,历代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凡属先秦文献都明确提及当时的王朝和诸侯王国,其都城都需要不断的搬迁。据传说,夏代的都城搬18次之多。商代从商汤建国到盘庚继位,直到盘庚迁都后,都城才基本定型。但与此同时,还拥有数量不等的陪都、临时都城,即令是国王的都城都还没有处于真正的稳定状态,普通居民的非稳定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周代以后,随着王权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都城才最终得以固定,但周朝也将都城从西安迁到洛阳,从而被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阶段1301。
当代的考古学发掘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记载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对夏朝都城的探寻和发掘工作已经历了一百年的努力。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认定,夏朝最早的都城地处陇西的“齐家文化”分布区内,晚期的都城则位于黄河南岸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通过发掘进一步表明,当时的都城内不仅具有王宫和居民住所,还拥有耕地,及临时放养牲畜的草地,当然也有各式各样的作坊。这就进一步表明,当时的国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聚落,它同时也作为生产聚落,生产区和生活区在都城内同样会发生相互置换的实例,都城尚且如此,普通居民聚落其可变程度之大就不难想象了。
安阳殷墟的考古遗址发掘报告表明殷朝的宫殿聚落已经高度稳定,然而城区内仍然拥有牧场、耕地,依然保持游耕类型文明的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王室墓葬还分布在皇宫附近的城内,当时土地使用的相互置换由此获得了一个铁证,表明城区结构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高度稳定。与此同时,先秦诸子的治国论著也多次提及,居民生活中有计划搬迁以及生产生活节律上的规律性搬迁。《孟子·梁惠王》中提到,国家遭逢灾难时国王要将居民从黄河西岸迁到黄河东岸,或者从东岸到西岸,这就是成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典故出处。《庄子》《荀子》《韩非子》诸书都同样提及当时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同的季节要从事不同的劳动,既要耕地、种桑养蚕,又要采伐木材、营建住房,还需要进入深山湖沼,从事狩猎、渔猎活动。这些生产和生活实情都与真正意义上的固定农耕不相同。事实上人们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定居在同一个村落之内,而是要有规律的迁徙生活场所。因而学者们将这样的生计方式称为“半定居式”生活。这样的结论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还获得了有利的历史证据。*①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1页。表明在游耕类型的文明之下,稳定的传统村落很难定型下来,因而今天讨论传统村落的保护时,对这样的“半定居”村落最好不纳入传承保护的对象去加以对待。
当代的民族学通过对游耕类型文明活态形式的田野调查表明。村落的搬迁不仅经常化,而且有规律可行。比如20世纪的田野调查中,很多苗寨都有新老寨之分,且共用一个地名,有的老宅废弃后,当地居民还要定时到老宅祭祖。至于具体搬迁的实情,有关资料的记录更其精准详实。还有一些资料表明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还要搬回祖先的居住地再次启用居住。类似情况不仅是苗族,还包括独龙族、傈僳族、瑶族等诸多民族。这就足以表明在游耕文明类型下,“迁徙无恒、迁徙无常”是其游耕类型文明居处生活习俗的常态。称为“无常”虽然不能贴近事实,但却可以提供一个启示,帮助人们认识到在这样的文明类型下,稳定的村落是很难传承下来的,当代实施活态的传承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了。
游牧类型文明是在综合狩猎采集文明和游耕文明的长处后,创新发展而来。在这一文明类型下,人们高效掌握了大型食草动物,也获得了物质生活上的富裕。但牲畜的觅食半径很大,为了获得稳定的生活物质,人们不得不随着畜群四处迁徙。据田野调查所知,山羊和绵羊一天内的觅食半径要达到30公里,黄牛要达到50公里,马则要达到80公里。当牧场的利用达到一定的限度后,人就必须和牲畜一并迁徙。因为,游牧文明下的人们显然不能建立固定的居民聚落,只能以帐篷为家,为的是方便随牲畜而迁徙。
进一步的田野调查表明,我国处于游牧类型下的蒙古族、哈斯克族、彝族和藏族等,通常都要实施随季节而迁徙的生活居处需求。蒙古族通常都要具备春、夏、秋、冬四季牧场,牧民的毡房需要在不同的季节到不同的地点去搭建。哈萨克族的季节性迁徙则更具特色,冬季要到戈壁滩搭建帐篷放牧牲畜,夏季则相反,要深入高山林区和草场去放牧牲畜,春秋两季则是在坡面草地上放牧。类似的习俗在彝族中也可以看到。因此,既然这些民族不能建构固定的住房,那么稳定的传统村落也就无从谈起,传统村落的当代传承和保护理应不能将其包括在内。
又据文献所记载,中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的游牧文明,其都城也具有鲜明的可移动性。历史上的辽朝是由契丹人所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该王朝名义上建立了东、南、西、北、中5个不同的都城。但辽国的皇帝并不会定居于某一个都城中,而是在不同都城之间轮流居住,而且还带领官僚、贵族和禁卫军等从事“捺钵”,也就是季节性的游牧和狩猎活动。当代考古证明,辽国都城的王宫殿羽建设也要仿效毡房的形式去修建,另从王宫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生产和生活遗物,也具有鲜明的轻便特色,为的是易于搬迁利用。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今天我们所说的传统村落显然不是上述三种文明形态的产物,而只能是固定农耕文明的产物。为此,要实现当代的传承和保护,关键就得弄清楚这些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归属,准确的区分其村落形成的样式差异,找准传统村落稳定延续的自然与社会基础,有效的传承和保护才能落到实处。
二、传统村落的样式差异
固定农耕文明的最大特色在于,实现了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因而不再需要不断的变换居住场所,这就为稳定村寨的最终定型奠定了文化生态基础。今天我们所能展开深入研究的传统村落也才因此而形成。然而,固定农耕类型文明,其内涵极为丰富。由于耕地的自然属性不同,作物种植的物种也各不相同,耕作体制和制度保障也将随之而异。这样一来,不仅在社区内人们出现了明显的分工,而且传统村落的生存基础也出现了分工,这就使得不同的传统村落其得以定型的社会和自然基础各不相同。为了加以准确的样式区分,显然需要将传统村落划分为各不相同的样式。以下仅就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实例展开深入探讨。
农田密集式的传统村寨。在固定农耕文明下,人们都要靠固定农田为生,一个家户的生计都被固定在小块的耕地上,以至于耕地总面积的大小直接决定着村寨规模的大小。其中只有那些连片耕地规模较大,自然与生态背景又相对稳定的村寨,才可能稳定延续数百年之久,从而成为传统村落的典型。比如,从江县的车江大坝,地势平缓、水源丰沛,非常适应于糯稻种植,当地侗族乡民凭借这一优越的地理环境,健全和完善了“稻鱼鸭共生式”农耕体系,而今这一体系被认定为“优秀的农业文化遗产”去加以保护。由此看来,要保护好这样的传统村落显然需要从该传统村寨的根基做起,不仅需要对传承下来的村寨加以保护,还需要对其伴生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这样一来,需要保护的就肯定要越出村寨的空间范围,要将该村寨所依托的稻田、森林和牧场等一并加以保护。否则,村寨所依托的文化生态一旦落空,该村寨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徒有躯壳,而不具有灵魂。这将意味着,要保护好这样的传统村落,不能见物不见人,只关注村寨建筑、村寨设施,而不关注人的生存基础。在这样的错位认识下,即便投入再多资金和人力、物力,能保存下来的仅是躯壳而已,而不具备灵性和稳态延续的活态传承根基。为此,正确的保护办法必须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统生计模式的创新利用捆绑起来,一并加以考量,才能形成有效的保护对策。只要方法正确,即令国家投入不多,不给予特殊的政策倾斜和待遇,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也可以落到实处。
具体做法应当凭借当地乡民所持有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提供当代人生活所急需的生态农牧产品,通过市场机制去获得稳定的、合理的报偿,使村民的生活有望,相对富足,他们也才能形成保护家园的冲动和激情,村落的传承与保护也才能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社会行动,真正做到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激情与创新的结合。这样的传统村落,才能做到既保持了传统,又创新利用了传统文化,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才可能得到有序的推进和落实,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
清水江流域在近6个世纪以来,随着杉树用材林产业的飞速发展,一大批苗族和侗族村寨也随之而定型,并传承至今。锦屏县的文斗、平鳌、加池、九寨都因此而定型。时至今日,这些村寨无一不拥有连片的人工杉树林,无一不拥有稳定的稻田,还拥有经果林、碳薪林和牧场,村寨的建设也古色古香,特色鲜明。但要做好类似传统村寨的传承保护,关键措施同样不在于保护村落建筑,而是需要振兴其传统产业,并使之与现代市场接轨。事实上,用材林业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产门类。世界上有不少工业文明的国度,至今还能够仰仗林业获得发展的空间和机遇,芬兰和加拿大就是其中的典型。葡萄牙则是仰仗栓皮栎产出的软木外销而获取巨额利润,林业种植也就成了该国经济支柱之一。中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代的中国人也不是简单的满足于胶合板家具使用,而是要追求“实木”装饰材料的运用。在这样的现代市场供求背景下,原木生产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有了这样的良好机遇,类似的传统村寨如果能够实现用材林产业的现代化创新,那么当地村民就可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了。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此类传统村落的保护同样可以与“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保护结合起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活态传承与保护。
除了用材林传统村寨外,桐油、生漆、樟脑等传统林化产品的产出,也造就了一大批传统村落。镇宁县的良田、弄泡、六马和三穗县的桐林等,历史上都因盛产桐油而富甲一方。赫章县的台神因盛产优质生漆而闻名遐迩,锦屏的小江、九寨因盛产樟脑粉也曾富甲一方。但问题在于,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化学涂料的兴起和化学防腐剂的滥用,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挤占了上述生态涂料和生态防腐剂的市场空间。上述村寨先后沦为贫困村寨,不要说保护传统村寨,就是普通乡民也会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这样的村寨,即令给再多的钱,再大的政策优惠,恐怕都无济于事。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得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在维护人民健康的需求面前,集合这些村寨所拥有的文化生态优势,实现现代化的产业创新。凭借这些生态产品的外销和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弦令张,这些村寨的乡民一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才能让这些村寨重建辉煌。这些村寨乡民一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他们也才会更加热爱自己的村寨,他们也才会拥有保护传承传统村寨的激情和冲动。这些村寨一旦获得这样的经济优势,传承与保护也就事半功倍了。
我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农耕文明大国,我国所拥有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不胜枚举。就以贵州来为例,茶叶、榨蚕丝、猪鬃等都曾是传统村寨外销获利的生态产品,由相关产业所此涉及到的传统村寨可达千余个。而时下最紧迫的任务恰好在于,如何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世界潮流,推动这些传统农林牧产品的现代化复兴。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传统村落的保护不仅可以获得物质保障,还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持,传统村落的保护也就可以落到实处。
商贸集散式的传统村寨。在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下,由于名特优产品的产出互有区别,为了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商贸活动在历史上从来没中断过。很多名特优产品不仅成了“宫廷”贡品,还成为国内市场的抢手货,甚至可与国际市场接轨,为国家获得巨额外汇收入。上文提及的桐油、生漆、蚕丝、茶叶就是如此,而这些产品得以外销,无一不是通过特殊的商业渠道去实现。于是,在比邻古代交通沿线的村寨,可以将农业畜牧视为副业,而将商贸视为主业,并在这样的商业基础上也形成了另一个样式的传统村落。比如,清水江林木贸易的繁盛造就了卦治、王村、三门塘、远口等众多的传统村寨,这些村寨本身种植杉树不多,但是所有的杉木原木外销都要从村下的清水江穿行而过,大宗的原木贸易要在这些村寨实施规模性的拍卖,还需要扎排外运。以至于在历史上上述村寨的存在,无论是村民当“水夫”、当经济人,甚至是参与饮食服务,也能获得巨额的财富。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这些财富还会很自然的用于村落建设,最终使得这些村寨不仅闻名遐迩,而且使得这些村寨建筑华贵辉煌,配套设施完善,居民生活的舒适程度也高于周边各村寨,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生活的高水准。当前,此类村寨需要面对的困境在于,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林木采伐锐减,贸易量也锐减,这些村寨不仅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而且乡民也沦为贫困人群,不少人为了谋生而外出打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即令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和人力,要保住这样的村寨恐怕终将于事无补。要保护和传承这一样式的传统村寨,关键是要正确的引导使传统林木贸易实效现代化转型,即令重新成为林木贸易中心不大可能,但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用材林产品的复兴,这样的村寨完全可以转型为生态旅游目的地,从而赢得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同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传承与保护思路。
关岭县花江镇,元明清三代曾在这里设置过暮役长官司。由于该长官司地处滇黔一路的要冲之地,同时又背靠优质的牧场。因而明代以降,这里一直是关岭黄牛、乌蒙马的集散之地,周边各村寨也因此而名噪一时、富甲一方,遗留下来的传统村落也多达十余处。当前,此类村寨的传承与保护需要面对的困境在于,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日新月异,马匹的销售已经淡出了市场,关岭黄牛的销售落到了中间商手中。再加上此前一段时间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畜牧业受到一定的窒息,花江各传统村寨也因此而落到低谷。不过,这些传统村寨并未走到末路,随着全国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对肉食的需求量巨增,黄牛、马头羊等畜牧产业必将迎来又一春。这样的畜牧产品集散地,同样会再次成为物流集散中心,只要这样的中心与现代化的方式得以确立,尽管交通路线有了改变,但集散地同样不可少,这些村寨的复兴照样存在着广阔的空间。
有鉴于此,保护此类传统村落不能把问题看死,而应当多一份预见,只要“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得以复兴,当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的传统集贸中心完全可以凭借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去实现大批量的拍卖和外销。这批传统村寨完全可以搭上现代化的便车,和时代潮流的推动而重现辉煌,只需要做到这一步,这些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同样可以获得物质、精神和制度的保障。
行政中心式的传统村寨。元明清3个王朝在大力开发西南地区的同时,也必然要在不同的地区分别建设各级各类的行政机构和军事设施,而这些因政治军事原因而确立起来的传统村寨同样为数不少,多达数百处。而今,时过境迁,行政和军事的建制无不陆续罢废,相关传统村寨及其地位也就江河日下、今非昔比。但往日的辉煌依然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相关的地上和地下文物也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认识,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纪念物不胜枚举。这样的遗产恰好是当地旅游目的地建设的资源宝藏,对这样的传统村寨,只要改变思路,将他们与旅游相结合,他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途径上获得理想的报偿,重现往日的辉煌。安龙县在明末之际,曾充当过永历王朝的临时国都之用。因而在当地的很多传统村寨之中,至今还保留着明代的众多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在清代设置南笼时虽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损,但流传至今的依然不少。今天将它作为历史名城去创新利用其文物古迹,使之形成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旅游目的地,不失为传统村落保护的可行措施。
贵阳市花溪区的高坡乡,在明清两代也是作为中曹长官司的衙门所在地。中曹长官司土司衙门至今尚存,但已多年无人问津。时下,如果将这样的文物加以创新利用,那么死的文物也就获得了现代意义的价值。相关传统村落的保护和传承也就不成问题了,类似的例子除了中曹长官司外,黔陶乡骑龙村的白蜡正副长官司留下的遗物遗迹也极为丰富,清代知名学者周玉皇的纪念地也在此地,同样可以一并加以传承保护。此外,还有岑巩县都素村在明代初时作为思州安抚司的衙门所在地,改土归流后又是田氏土司家族的世袭封地,田氏后裔长期充当为当地“土同知”。因而, 留下的文物极为丰富,将此开辟为土司遗址的旅游目的地,同样大有可为。
元明清三代的军事设施为数众多,其中一部分发育成了今天所见的传统村寨,比如明代建置的湖南靖州卫所辖的一个千户所,就位于今天天柱县县城,周边的雷寨、织云都是该千户所的设防区。明代后期将该千户所的设防区改建为天柱县之后,县城就一直发生争执,摇摆于两地之间,由此留下的遗物至今尚存,同样是可以实施旅游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再如,修文龙场驿故址是“奢香”九姨故址之一,同时也是王阳明的流放之地,目前该地已经成了旅游胜地,只需要作进一步的发掘和再认识,其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升。如此来看,只有做好和这样的配套工作,相关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同样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有鉴于上述,展开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显然需要分门别类,不能一概而论,显然需要针对其形成的根基去规划传承与保护对策,而不能仅保护其躯壳,而忽略其精神。望学界同仁多加留意,决不能见物不见人,决不能将文化与生态割裂起来,而应当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保护作为一个整体去对待,传承与保护才能具体化,精准化,成效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 结论与讨论
实施传统村落的保护理应是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传承与保护的原则必须确立为活态保护和传承,必须给被保护的传统村落赋予现代化的活力,使其文化经济处于可持续发展的活态运行状态,传统村落保护才能落到实处。必须牢记,仅仅保护建筑设施是远远不够的,理由在于,任何建筑都需要社会和相关民众去展开维护,去展开创新利用才是活的村寨,而不是博物馆中的古董。因此对不同样式的村落,理应使用不同的保护措施。需要将现代化的潮流和市场需求作为导向,去推动这些传统村落的现代化创新,传承与保护才能与现代社会接纳,乡民也才有激情。为此,以下三个原则值得借鉴。
其一是,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保护一并打包,实施整体性的规划整合,决不能见物不见人,不关注当地村民的实际和现代化要求。其二,任何传统村落都有他诞生和发扬光大的历史机遇和成长路径,这些传统村落的衰败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因而传统村落不能一概而论,要针对其衰败探寻其脱困的措施,无视历史传统,不发掘其历史底蕴,片面实施见物不见人的保护措施,肯定是一种保护与传承的失策。其三,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落同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由于他们诞生于前工业文明时代,这些传统村落的物质保障完全符合生态产品的要求,对维护现代人的身心健康也可以发挥直接的作用,其历史积淀也可以提供丰富的精神享受。因而,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要立足于生态文明的高度开展此项系统工程,需要赋予这些传统村落现代意义上的存在与延续的价值,需要将他们转化为服务于文化生态的财富,只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聚合村民的内生动力,使他们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和依赖力量,再加上政策优惠和舆论导向的支持,制度性的保障,传统村落的传统与保护就不再是一个难题,而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有机构成部分。
上述3项原则只要落到实处,传统村落就可以获得现代化的可利用价值,传承与保护就可以做到水到渠成。以上三大原则,实属必不可少,缺一不可,有关事宜,还望学者同仁深思。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 朱利安·斯特而徳.文化变迁论[M].谭卫华,罗康隆,译.杨庭硕,校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
[2] 郝 平,高建国.多学科视野下的华北灾荒与社会变迁研究[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432.
[3] 白寿彝,徐善辰,斯维至,等.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白寿彝,苏秉琦.中国通史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49.
[5]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委会.中国历史学年鉴2002-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577.
白寿彝,陈振.中国通史1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884.
[责任编辑:曾祥慧]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tection
YANG Ting-shuo,GENG Zhong-yao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China)
China, as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y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owns the complex and various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ome villages are formed by the stability of farmland; some are formed by local particular products. Additionally, ancient transportation and market could form a traditional village; some villages with particular political features are formed by the local political center. The reason why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could be passed down stably is the ecological cultural feature and their history background. Therefore, only in this way, coul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be effective and practicable.
farming civilization; cultural ecology; traditional villages
2016-11-12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采辑、研究与利用(批准号:16ZDA157)。
杨庭硕(1942-),男,贵州贵阳人,吉首大学终生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民族学;耿中耀(1989-),男,吉首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民族学。
TU982
A
1674-621X(2016)04-007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