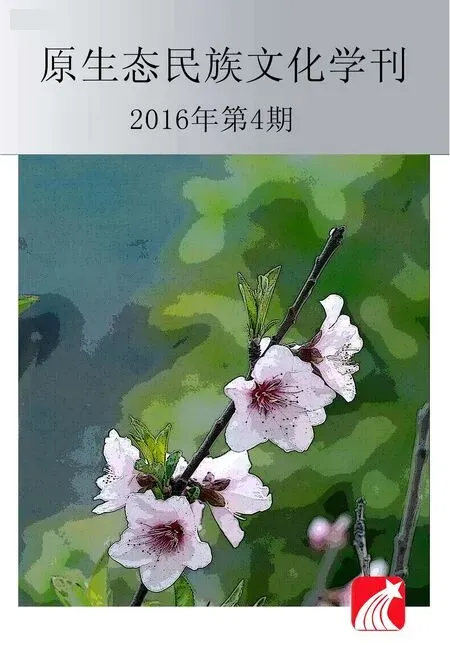论藏区司法权威的认同困境及其消解
——从赔命价的运作切入
王林敏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论藏区司法权威的认同困境及其消解
——从赔命价的运作切入
王林敏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藏区刑事司法中存在的赔命价现象表明,藏区司法权威存在认同危机。能否实现纠纷解决功能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控制,是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的有效渊源。藏区司法机关在实践中面临民间权威竞争导致权威流失,维稳思维掣肘、法治化转型尚未完成,是藏区司法权威面临的困境。消解上述困境的出路在于,司法机关需要贯彻法治思维、还原公仆角色,通过长期扎实的工作获得社会认同。
司法权威;社会认同;正当性;赔命价
国家司法机关*①基于本文论题,所称“司法机关”包含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参与刑事诉讼的公权力机关;因此,本文所谓“司法权威”的“司法”在外延上也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公权力机关的权威。对刑事案件具有排他性的司法管辖权,这是国家刑事法制的硬性规定,也是探讨藏区赔命价等刑事习惯法的现代化问题的制度前设。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并不是建立起司法机关,藏区群众就主动向其寻求帮助,更不是司法机关盖起大楼、摆好桌椅就能吸引藏区群众,纠纷当事人就会主动走进司法机关的大门。在藏区司法机关与藏区刑事案件纠纷中,存在一种法律规定之外的由藏区纠纷当事人用脚来决定的“司法管辖”关系。在既往的研究中,这层“司法管辖”关系被基于官方立场的治理思维作为一个官方制度否定的对象,将其置于一个被严重客体化的地位。藏区司法实践的现状要求理论研究者从“官方-民间”的互动结构入手,在理论研究中恢复民间各个因素的主体地位,从而揭示藏区命案当事人“用脚投票”背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即藏区司法权威的认同问题。
一、赔命价运作中的藏区司法权威
赔命价习惯法是藏区民间解决命案纠纷的传统做法。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赔命价案件中存在四方主体:双方当事人、司法机关、民间权威。我们往往能够看到国家司法机关对于藏区民间处理赔命价的方式有所期望,期待藏区民间社会以国家法律为依据处理命案纠纷,并且以正式制度作为评价依据;而基于这种官方立场的研究给出的问题解决方案都是制度设计性的,以关于藏区赔命价问题的立法建议为主要抓手,而看不到藏区司法机关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但从藏区民间角度来看,命案的双方当事人、民间权威乃至命案所在的整个地方村落或者部落,也都对藏区司法机关有所期待。对藏区司法机关而言,其实存在一个被民间评价、认可,进而被接受的问题。这个期望结构对藏区司法机关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民心”向来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司法机关工作的重心。
具体到藏区某些地方的命案纠纷处理中,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经常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藏民公开的话语“挑衅”。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济民在调研中发现青海藏区的杀人和伤害案件“除政法机关主动办理者外,一般很少诉讼至司法机关,习惯于采取‘赔命价’‘赔血价’的办法私下处理。这种沿袭旧制,索要“命价”的做法在藏族牧区还很盛行。‘你判你的,我赔我的’。甚至说:‘政法机关对被告人如何判,与我们无关,命价是绝对不能不赔的。’”[1]344青海省人大在调研中也发现:“政府判是政府的法,我们俩的事不给命价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1]151在某个案件中,当事人私自处理命案然后告诉司法机关:“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2]在一起群体性案件的处理中,当地群众认为“政府可以采用赔命价的方式解决纠纷,我们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1]151这种话语结构及其表达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表现形式不同,但是赔命价现象的广泛存在表明这种话语结构依然牢固。
站在司法机关的立场上来看,这些案件当事人的话语是很有刺激性的。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上述话语中得出的结论也大体不会出离如下框架:第一,赔命价是腐朽落后的东西。从“试论‘赔命价’‘赔血价’腐生的社会底蕴及其对策”[1]210“革除‘赔命价”陈规陋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225“青南藏区部落意识沉渣泛起”[1]340等文章报道的题目中我们就解读出这种信息。第二,藏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藏族群众中存在着大量的文盲加法盲,他们囿于按习惯方式解决纠纷,而不知道应该依照国家法律来处理。他们自认为按传统的方式解决纠纷是天经地义的,而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的”[3]。第三,藏区群众需要加强法制教育。“总之,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在各地政府和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依法治乡、依法治村活动,通过更多的文明村、法制村的实现,使广大牧民群众自觉地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运用法律手段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从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赔命价’和因此而酿成的违法犯罪案件”[4]。基于官方立场的赔命价研究背后的治理思维将赔命价完全视为一个客观化的治理对象,从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恰如一个手电筒,其强烈的光芒只能照亮自己前方的他人,但却照亮不了自己。
任何的话语都是一种思想意识的外部表达。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藏区命案中的部分当事人的上述表达的确能够反映出其法律意识淡薄。但站在藏区“官方-民间”的外部立场上考察二者互动关系时,上述话语背后其实蕴含着藏区民间社会对于司法机关及其权威的态度,即命案当事人对藏区司法机关的存在感以及尊重、信任和接受程度。藏区命案当事人对于赔命价的孜孜以求可以解读为对国家法律和司法机关的权威的质疑。有学者敏锐的指出,赔命价案件当事人行为后面的“潜台词”是“法院你管那么宽干什么?”[5]来自藏区司法实务工作人员对此的认知更为真切,针对一起赔命价案件的处理结果,“当地居民反映甚为强烈、纷纷质问国家法律的权威在哪里?人民司法机关的权威在哪里?”[3]这种“质问”事实上是司法工作人员借民众之口所表达的一种困惑,其实质是藏区民间对于藏区司法机关及其权威的质疑。
藏区社会对于官方司法权威的认同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对国家法律的认同;其二是对司法机关及其运作的认同。前一个层面常常被学界归结为“国家法律同民族习惯法的博弈”;后一个层面则被部分学者归结为藏区社会的“厌讼”现象。部分藏区的命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倾向于诉诸民间权威通过传统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选择司法机关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确是“厌讼”的一个表现。这个现象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加以证实。但笔者认为,“厌讼”只是一种表象,藏民不愿意到司法机关打官司,其背后隐藏的是藏区社会的权威认同问题。藏区群众“用脚投票”,基于自身意愿选择纠纷处理方式,表达的是对官方司法权威的不认同。民事领域的“厌讼”,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意思自治领域;而刑事领域的“厌讼”则是规避法律和司法机关,是对司法权威的无视。这对藏区司法机关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挑战。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何谓司法权威,形成司法权威认同的有效渊源是什么?
二、司法权威认同的有效渊源
“权威”一词,就其使用的场合来看,既指向拥有某种权力的实体;也指向此种权力实体与其治理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当权威被用来指代人或机构等实体时,该机构或个人的指令就成为受管治者行为的排他理由。当权威指一种关系时,权威者个人或机构就受到受治理者的尊重与服从”[6]。因此,权威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行为及其命运的能力[7]。 “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控制-服从”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司法权威就是由国家司法机关拥有的、通过审判影响公民与社会行为与命运的能力;作为主体的司法权威要求作为受众的公民与社会的服从。例如在命案纠纷解决中,司法者职责是裁判当事人之间纠纷,促使纠纷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在“法治中国”的条件下,当我们强调“司法权威”时,更加注重公民服从的主动性,而不是被迫的服从。只有在主动服从的条件下,才能衍生公民对司法权威的认同,由此引导的社会控制关系才能更加稳固;强制的服从并不能够必然导致公民的认同,由此引导的社会控制关系也极为脆弱。
在藏区,从国家司法机关的架构来看,藏区司法机关是单一制国家体制中的相应权力机关在藏区的延伸,其中,人民法院是国家法院系统的组成部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检察系统的组成部分、而藏区公安机关则是相应地方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藏区司法机关对命案的刑事司法管辖权来自于国家法律的正式授权。所以,从法律体系的内部构造来看,藏区司法机关的权威来自于法律、最终来自于宪法的授权。但这只是藏区司法权威的形式渊源,即所谓“语义证成的权威”或者“事实性权威”[8],并不能够直接形成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的有效渊源。无论是在藏区还是在内地,人们并不会因为国家法律规定了司法机关拥有排他性的司法管辖权就认为司法机关拥有“权威”,从而主动接受管辖并服从判决。司法权威,进而司法权威认同的有效渊源,是在法律的规定之外。我们的任务便是揭示司法权威认同的有效来源,并以此为圭臬引导赔命价现代化中的司法工作得到藏区社会的积极认同。
当我们在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中讨论藏区司法权威及其认同的有效渊源时,该论题的本质即司法权威的正当性问题。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契约论思想有效地证成了司法权的正当性。在社会契约论的论证框架中,作为前政治社会的自然状态存在种种缺陷,从而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所以人们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进入政治社会。就司法权而言,由于在自然状态中缺乏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人人都是自然法的维护者,人人都是自己事务的法官,因此无法有效的终止争议达成秩序,所以人们便放弃惩罚犯罪的权利,将惩罚犯罪的权利交给中立的政治共同体,从而形成刑事司法权。社会契约论显然是一种虚构的理论,但就司法权威的形成而言,其中有两个要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是社会契约论将司法权威的产生归于“人民”的同意,因此公民服从司法权威事实上就是服从自己;其二是社会契约论中的“承诺”思想,人民服从司法权威的前提是人民与司法权威之间的相互承诺,这样一来,社会契约论就把司法权威认同的有效渊源归于司法权威自身,即司法权威是否能够有效实现自身对人民的承诺是司法权威是否能够获得认同的真正渊源。所以,我们可以据此判断司法权威认同的实现程度。
以人民法院为例,司法权对人民的政治承诺乃是有效的处理纠纷,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知道,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因此司法权威的生命在于公正。质言之,司法是否公正是司法权威认同的最为核心的内在构成要件。司法公正的构成要素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是指审判过程的公正。“无救济即无权利”,所以,任何公民都有权就自身权利受到侵害而提起控诉,相关机构不得拒绝救济;“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因此,司法公开是程序公正的保障;“任何人不得做自己事务的法官”,所以,回避制度是司法公正的题中应有之义。实体公正是指裁判结果的公正,而裁判结果的公正的重要前提是实体法律制度的完善。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官方的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9]。根据法律作出裁判是法官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假如法院自身都不遵守法律,不按照法律进行裁决,司法权威及其认同便是无源之水。在通过程序实现实体公正的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理论素养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人民法院之外,中国的司法体系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相关的侦查、起诉,脱离法律的行动只能贬损其权威。
司法机关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水平高低还取决于其自身的能力。换言之,司法权威认同的外部条件是司法体系在整体政制架构中的地位,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对待司法机关的态度。司法机构的独立程度,特别是人民法院受行政机关的制约程度,是司法机关宪政地位的重要评价指标。在国家权力架构中,假如司法机关不能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平等对待,司法机关如何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认真对待呢?因此,在“法治”的语境中,司法机关需要与之政治功能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治话语权,惟其如此,司法部门才能更好的兑现自身的政治承诺,司法权威才能更好的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
所有上述因素都构成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在藏区还是在内地,司法权威认同的有效渊源不是司法机关说了什么,而是其做了什么;司法权威认同的形成,并不在于法律制度设定的如何完美,也不在于“立警为公”“司法为民”等政治口号喊得有多么响亮,而在于司法机关的行动对其承诺的兑现程度。当藏区司法机关声讨赔命价运作扰乱社会治安与司法秩序,苛责藏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之时,从赔命价的运作来看,藏区司法机关未能有效实现社会控制,不能有效保护辖区内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就是没有实现法律规定的职责、没有兑现社会契约的政治承诺。在这种情况下,藏区司法权威认同堪忧就在预料之中。因此,赔命价的存在仿佛是一道魔咒,也是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程度的一个指示符。
三、赔命价运作与司法权威的认同困境
“权威”既是规定性的,又是实践性的。规定性的权威是强制的,源自法律的设定。现代刑事法制中,规定性的权威由国家司法机关专享,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未经许可不得分享。而在现代刑事法制实践中,实践性的权威可能是分享的,司法机关无法通过强制性的规定进行垄断,因为认同来自于人们的内心,法律无从强制。赔命价的运作恰恰表明,藏区的某些民间权威分享了藏区群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10],从而造成藏区司法权威的流失。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认同、特别是人民法院的权威认同都不容乐观,只不过藏区因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地理环境而更加具有特殊性。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种特殊性,才能对藏区司法机关和藏区赔命价运作都进行“同情的理解”,而不是预先设定哪一方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
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一是趋向世俗化的社会的权威认同是如何可能的,这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困境,在这个过程中,神圣权威丧失,社会越来越世俗化、感性化、庸俗化;二是日益分裂和分化的社会的权威认同是如何可能的,这是世俗世界本身的社会性困境,这个困境主要表现为阶层的分化、利益的纷争[11]。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上述两方面的困境同时存在。但藏区的特殊之处在于,藏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而是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甚至保持着浓厚的传统色彩。在藏区特殊的社会结中,司法机构的权威认同有着不同于现代社会权威认同的特殊困境。
藏区司法权威认同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来自于传统权威的竞争。藏区传统权威有两方面。首先是藏区宗教权威的竞争。马克思·韦伯曾经预言:“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12]“祛魅”的世界中,神圣性的东西失去了号召力,无法构筑权威认同的基础;但藏区社会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其尚未“祛魅”。在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的藏区,宗教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宗教自身便是权威的代名词。许多司法机关都解决不了的赔命价案件,都是通过宗教领袖出面得到了彻底解决,宗教因素恰恰构成藏区社会认同的最为坚实的基础。其次是藏区民间世俗权威的竞争。在赔命价案件的解决中,民间权威始终是在场的,部分命案的当事人“习惯性的”寻求民间权威的帮助,而民间权威也乐于主动介入纠纷解决;当前藏区赔命价案件的纠纷解决中,民间世俗权威的介入已是常态。
此处,赔命价运作机制所展现出来的现象是,如果不借助于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那么很多赔命价案件的解决难度便很大,甚至解决不了;而借助这些传统权威,再难的赔命价纠纷也能顺利化解——并且是案结事了、永久解决。所以,很多司法机关便策略性的借助这些权威力量。但司法机关的困境在于,每当其解决不了的难题被藏区传统权威顺利化解时,藏区社会对传统权威的认同和信赖便巩固几分;而藏区司法机关在民间社会的威望和地位却可能因此受到轻视乃至贬损。也就是说,在面对和解决赔命价等司法难题时,司法机关借助传统权威越多,司法权威就流失和被分享地越多。这或许可以视为藏区司法机关策略性的借助传统权威时所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
藏区司法权威认同面临的第二重困境是藏区维稳思维的困扰。藏区法律精神的养成,并不只是藏区社会和藏区群众一个向度的知法、守法和认同法律。在社会治理的另一端,藏区地方政府尤其是藏区司法机关的法律意识、对待法律的态度,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不仅涉及藏区社会的规范认同,而且涉及藏区社会对司法机关的权威认同。藏法机关镶嵌在藏区总体的政制架构中,不能不遵循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和运作逻辑,当前对藏区司法运作影响最深的恐怕便是维稳思维,尤其是与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边疆治理思路结合在一起的维稳思维,更是对藏区司法运作产生深刻的束缚。
维稳思维以社会稳定为最高目标,其中不乏对政治认同的重视和追求。但在维稳思维的前提下,藏区司法机关往往陷入极端,或者是不惜一切代价息讼、消除涉诉上访等不安定因素;或者是为了稳定而任意突破法律底线,曲意迎合当事人的要求。这样,藏区司法机关便可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寻求认同而迎合当事人的要求,满足当事人对命价的诉求;但是对当事人诉求的满足却可能加强一种暗示,即当事人只要能“闹”,司法机关便可能妥协。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法律寻求纠纷解决,而是设法制造压力运用政治思维解决问题。如此以往,纠纷当事人所认同就不再是司法机关,司法权威认同便成为维稳思维的婢女。
第三重困境是藏区司法机关自身的法治化转型尚未完成。在藏区(乃至在整个当下中国)一个最为吊诡的事实是:司法权威有时在以法治之名进行运作并寻求认同,而在司法运作和寻求认同的过程中却未必行法治之实。在法治视野中,司法机关在本质上是为了公共福利而设置的公共服务机构。藏区司法机构在民众中之所以不受待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自身的衙门和官僚作风:门难进、脸难看。现代法治所提出的司法公信力要求,在藏区可能更成问题。所以,现代法治让藏区司法机关面临着一种新的困境:法治不仅是司法机关进行社会控制的正当性依据,也是对其自身的束缚。在赔命价案件中,藏区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法治原则声讨赔命价的参与各方目无法纪;而藏区社会与藏区群众同样也可以法治原则质疑藏区司法机关:你“法治”了吗?如果司法机关自身不严格依法办案,如何根据法治原则寻求辖区内的社会认同?按照法律的要求规范自己,先正己后正人,这是“法治中国”给藏区司法机关带来的新课题。
四、法治与藏区司法权威的生成
藏区司法机关嵌在藏区政治体制与藏区社会中,从而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的现状,不是某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在藏区命案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化视野中寻求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的生成路径时,需要综合考量,认真分析每一种可能性。而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讨论藏区司法权威认同问题,最坚实的理论基点是“法治中国”命题。文化人类学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深刻体认赔命价规则和藏区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生命力,以及其背后的藏区传统权威的纠纷解决能力,但是站在法制现代化的视角上,上述因素终究是被改造的对象,事实上的存在并不能证成其充分的正当性,当下的存在也不能证明其永远存在。藏区司法机关所能做的是面对困境,分析哪些因素是自身能够解决的,哪些因素是自身不能左右的,从而根据法治实践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有效解决赔命价案件中存在的纠纷,获得藏区社会的认同。
上述三重困境中,对司法机关而言,第一重困境属于纯粹的外部障碍。这个困境的解决不是司法机关所能决定的。去宗教化,即宗教不干预政治、宗教不干预司法是现代法制的一个基本特性,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区分公共领域、社会领域与私人领域,从而实现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私人的归私人,这是现代法制的另一个基本特征。上述两种区分是社会发育、发展和发达的结果。站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视野中,当下的藏区司法机关处于与藏区宗教权威、世俗权威相互竞争的态势中,无法通过道德劝说或者法律强制使后者退出命案纠纷的解决。法律可以逐步的限制和缩小藏区宗教权威、世俗权威参与纠纷解决的范围和程序;但是不能帮助司法机关自动获得藏区社会的认同。实践已经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命案当事人宁可不报案,也不寻求司法机关的公力救济。藏区司法机关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在竞争证明自己能力、兑现自己的政治承诺,惟其如此才能摆脱藏区传统权威竞争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关系结构中,我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藏区司法权威认同是一个历史的课题。当下藏区的司法机关在某些案件中的境遇和尴尬,是因为其正处于这个历史实践中。
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的第二重困境属于体制难题,相对司法机关而言也是一种外部障碍。这也不是司法机关本身所能解决的,但是“法治中国”条件下,当前已经具备了突破体制约束的部分条件。藏区法治社会的建设、藏区治理手段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赔命价治理去政治化、摒弃维稳思维、贯彻法治思维。包括赔命价治理在内的藏区社会治理是个实践课题,其中的各种复杂难题不是坐而论道式的清谈所能解决的。就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的生成而言,理论研究只能梳理出其大体脉络,其中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司法机关在地方政制架构的地位及其评价问题。赔命价案件往往都是牵动地方敏感神经、引发各方领导高度重视的大案要案,司法机关受各种条件的掣肘制约。司法机构被纳入到地方治理体系之中,就要受地方政府制约,接受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从而只能贯彻地方政府的意志。在这样一种体制下,藏区司法机关只能服从地方的“大局”,成为地方刑事纠纷解决体系的一个环节,甚至沦为次要的角色。“法治中国”呼唤法治思维,要求司法机关在赔命价治理中占主导地位,强调赔命价治理的法律效果优先。当下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突出地方司法的独立性,此种思路若贯彻到藏区司法系统,藏区司法机关就有可能摆脱地方干预,其被压抑的治理功能就会得到释放,从而在地方政制格局形成基于自身权威的社会认同。这是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生成的体制前提。
二是藏区司法机关与其上级司法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上级司法机关对藏区下级司法机关的评价问题。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法官按照法律的授权独立进行审判,但审级制度以及错案追究制度的存在,架空了地方法官的独立裁判权。在“法治中国”的语境下,藏区各级法院能否贯彻依法裁判,是其能否兑现其政治承诺、实现其社会治理功能的必要条件。赔命价案件是命案,因此,各级司法机关能否贯彻好刑法规定的命案处理规则,是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生成的规范前提。
藏区司法权威认同的第三重困境属于藏区司法权威生成的内部条件。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藏区司法机关不能控制制约其权威认同生成的外部条件,但是能够克服影响其权威认同的内部障碍。“法治中国”要求司法机关还原其“公仆”角色,藏区司法机关当然也不例外;“公仆”的角色定位要求藏区司法转换思维方式,从过去的治理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加强自身建设,首先把自己能够做好的工作做好做足,在此基础上结合藏区特殊的外部环境,尽力引导藏区社会的司法认同。
首先是藏区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建设。法制现代化最终是人的现代化,其中最根本的是司法从业人员的现代化,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司法服务能力。摆脱衙门作风其实是个意识问题,法官也好、检察官也罢,如果真的把自己当成“官”,便会自然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意识。在这种意识指引下的司法工作,只会导致司法权威的流失。因此,藏区司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应当从自身的服务意识做起,即使不放低姿态,也至少在工作态度上不让当事人厌弃。第二是司法技术能力,即娴熟运用法律规范和相应的法律方法解决纠纷的能力。在司法职业化的大潮下,藏区司法机关迫切需要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化水平。第三是司法理论能力,即司法工作人员在提高专业水平的同时,还需要提高理论素养,提高认识和分析问题的理论能力。较好的理论水平可以促使司法机关理性的对待赔命价等难题。虽然在当下的藏区司法实践中,并不十分需要冷冰冰的、理性的法律人,但理性的法律人是所有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地方的共同因素。并且从长远来看,藏区并不能脱离司法职业化的主流。所以,藏区司法机关有计划、有步骤的提高司法从业人员的理论水平是长久之计。
其次是司法公信力建设。“公信力”是生成司法权威认同的最为核心的要素,没有公信力的司法机关不可能拥有公共认同。在现代法治的条件下,对司法机关而言,形成公信力的锚点只能是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裁判。像赔命价这样严重的刑事案件的处理,司法机关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相似案件相似判决,即使照顾民族特点,也要通过充分论证使其获得法律上的可接受性。既要照顾民族特点,考虑赔命价案件的特殊因素,又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所以,公信力建设是考验藏区司法机关智慧的难题。赔命价案件的处理难度的确很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司法机关因为当事人的案外因素如闹事、缠讼、上访而妥协,突破法律底线追求个案效果的话,造成的示范效应便会损害其公信力,从而造成司法权威的流失。
权威认同的形成是实践性的。藏区司法机关的任务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藏区群众的认同,“驱逐”赔命价的运作,使规定性的权威获得实践性、使司法权威的形式与实质合一,从而成为藏区刑事法制中的唯一权威。司法权威认同的生成没有捷径。藏区司法机关唯有通过长期的、踏实的、耐心的乃至贴心的工作才能真正获得藏区群众的认同,藏区群众的脚才能自觉的踏入司法机关的大门,在纠纷解决中寻求司法机关的公力救济。
[1] 张济民.诸说求真——藏族习惯法专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344.
[2] 张济民.藏区部落习惯法对现行执法活动的影响及对策建议[J].青海民族研究,1999(4).
[3] 吴剑平.“赔命价”初析[J].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2).
[4] 张致弟.新时期藏族赔命价的方式及治理对策[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8(4).
[5] 杨鸿雁.在照顾民族特点与维护国家法律统一之间[M].贵州民族研究,2004(3).
[6] 李桂林.司法权威及其实现条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6).
[7] 拉 兹.法律的权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
[8] 罗杰·赛勒.法律制度与法律渊源[M].项 焱,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279.
[9] 富 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 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6.
[10]文 格.藏族习惯法在部分地区回潮的原因分析[M].青海民族研究,1999(3):76-77.
[11]路 杰.现代性与权威认同[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6):63-65.
[12]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48.
[责任编辑:吴 平]
The Dilemma and It’s Dissolu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Judicial Authority in Tibetan Area: Tak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Wergild as an Example
WANG Lin-min
(LawSchool,QufuNormalUniversity,Rizhao,Shandong, 276826,China)
The operation of the wergild in Tibetan criminal judiciary shows that there is a dilemma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judicial authority. Whether the dispute resolution can be realized is the efficient source of the Tibetan judicial authority.The judicial authority is facing the fact that the civil authority competition leads to the loss of authority in practice, thinking stability constraints, legal reform has not been completed, which is the dilemma. Tibetan judicial authority i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light of the way out, the judicial organs need to implement the rule of law thinking, reducing public servant role, obtain social identity through long-term solid work.
judicial authority; social identification; legitimacy; wergild
2016-11-25
王林敏(1968-),男,山东青岛人,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习惯法与法制现代化。
D92
A
1674-621X(2016)04-004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