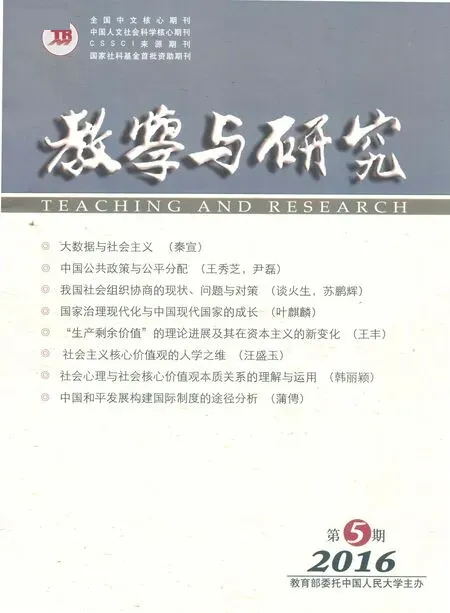阿尔都塞偶然相遇的唯物论思想研究*
经 理
阿尔都塞偶然相遇的唯物论思想研究*
经 理
阿尔都塞;偶然相遇的唯物论;再生产;政治哲学
阿尔都塞晚年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论,以便消除“辩证唯物论”的表述对法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不利影响。他并未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投向唯意志论的怀抱,而是反对“目的论”的唯物论;把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条件,认为无产阶级要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利用意识形态机器瘫痪的有利境遇,与其他团体实现联合,干预历史进程。他强调从“偶然性”视角重新理解历史唯物论强调意识形态的意义,但却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关系的连续性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社会的经济状况总体上趋于平稳,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并吸引大量海外移民进入到西欧社会之中,参与位于社会底层的生产活动。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的复杂性使阿尔都塞不再专注于如何凝聚无产阶级的整体意识,而是将政治实践的有生力量寄托在能够和无产阶级实现联合的移民、小资产阶级等团体上。[1](P240-241)但是,法国共产党(以下简称“法共”)没有对这些变化予以重视,而是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采取参与议会政治的方式使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针对“法共”的这种设想,阿尔都塞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论”。
在《论再生产》等晚期作品中,阿尔都塞注意到,事实本是客观对象向主体的呈现,是知识与呈现内容之间的一致关系。而在“经济决定论”语境中,它却转换为纯粹规律性的表现。于是,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维护社会再生产运行的前提出发,他认为意识形态以知识形式赋予了人们以虚假的“主体性”,使现有的生产关系以法律等形式渗入到日常实践活动之中,从而使人们丧失了追求自我解放的权利。但是,人们又有着追求自由的价值指向,渴望否定不利的生存现状。这就需要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以唯物论哲学为理论武器,反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利用社会政治事件冲击和动摇意识形态的有利机遇,占据现有意识形态结构之外的虚空,即在统治阶级保持沉默的地方,使个体之间重新联合起来,完成去意识形态化的任务,为实现自由而共同奋斗。本文力图从三个维度对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论加以考察,即反对目的论国家观、坚持唯物论的科学性和回归科学的政治实践理论。它们既是阿尔都塞晚年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也是他依靠政治实践实现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关键所在。
一、偶然相遇唯物论的理论背景
阿尔都塞认为,在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以“目的论”为导向的唯物论传统,它主张人们的实践活动需要服从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即服从于已被设定的事先安排。这是伪装成唯物论的唯心论,应该消除这种目的论的唯物论对人们实践活动的影响,把它改造成为人的能动实践活动的武器。
(一)反对“目的论”的国家观
所谓“目的论”的国家观就是把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视为一个连续的和自动的过程,认为人们的政治实践无法对“规律”进行干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国家观对政治实践的不利影响,阿尔都塞以“五月风暴”为背景作出了解释。1968年的“五月风暴”起初只是高校范围内的学生运动,然而,随着事件的不断升级,在不断调整过程中,他们的政治主张逐步拓展至家庭等各个领域,从而使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趋于瓦解,并出现了权力“真空”。在他看来,法共此时应当遵循马列主义的政治立场,利用党组织的意识形态机器,把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政治实践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向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宣战,[1](P210)然而,它的消极表现却令人失望。由此,他察觉到,造成此次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人们还没能摆脱经济决定论和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它基于线性时间观将历史解释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而人则一直处于“缺席”状态,历史表现为无“主体”的过程。实践主体的活动目的被诠释为使主体摆脱对象对自身的奴役性关系,而解除这种关系的唯一办法便是通过建构以占有知识为目的的实践活动,使自在的主体转变为自为的主体,即诉诸于实践中的智力活动来完成这项任务。这就使实践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转变为知识与对象的关系,劳动的过程变成了知识的实现过程。
如果我们把这种解释移入生产关系领域,那么,该观点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不谋而合。黑格尔认为,历史就是法及其现实化的过程,人类主体只有完全占有它的内容,即理念从部分回归到整体,才能到达共同生活的终点。只有扬弃对象实存的外观,从思维形式上占有对象,人才能脱离“自在”状态,成为“自为”存在。因此,在社会交往领域,国家法是联系市民社会的纽带,它的内容取决于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诸种矛盾。当国家法能够从形式上消除这种矛盾时,它便成为了包含普遍意志的行为准则,具有了普遍必然性。阿尔都塞认为,如果以这种立场看待政治实践活动,把国家视为随着经济交往关系而不断完善的政治实体,那么,历史便成为了与人们的价值追求完全无关的进程,这就如同“视人类的历史为宗教末世论的神话”[2](P182)一样。但是,与目的论的国家观相反,政治实践活动的能动作用突出表现为使原有生产关系瓦解,为了实现人们的共同理想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国家,实现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二)坚持唯物论的科学性
上述考察表明,阿尔都塞重新考察唯物论科学性不是想强调人们要从科学研究中获得普遍规律,并说明坚持它的必要性,而是要以它为理论武器反对目的论的国家观。因为这种国家观支配了“人们面对他们的社会和个人生存的实在对象和实在难题、面对他们的历史所采取的态度和具体立场”。[3]由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形态是建立在不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联合,这就取消了建构人类历史活动普遍有效性法则的可能性。[4](P278)因此,强调唯物论科学性的意义在于:(1)政治实践活动的结果取决于具体的政治形势,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状况的产物。(2)政治实践活动的对象不是相对于主体的客观存在物本身,而是人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就是确保这种关系得以维系和运行的实体。(3)政治实践干预的理论对象是从维系这种关系的物质存在入手,探索它的不合理性,从而否定现存交往关系,形成新的社会关系,这是政治实践活动追求的目标。可见,他是要反驳那些把国家的存在视为原因的观点,它使被建构的社会关系得以合理化。与之不同,政治实践活动的科学性则在于从国家合理化中找到盲点,即普遍与特殊利益的矛盾,并从否定生产关系入手去建立新的共同体。
因此,作为理论武器的唯物论哲学可以帮助人们指出支配人的知识与实践对象之间的矛盾,从而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依靠理论干预的力量来发挥其实践作用,即它不是要产生知识的效果,而是要改变“矛盾冲突所支配的某个领域内部的力量对比”,[5](P39)创造改变世界的机遇,进而在政治实践中实现人民的价值诉求。在他看来,统治阶级借助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使被统治者沦为特定生产关系的参与者,只有以批判的武器去意识形态化,被统治阶级才能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中撕开裂缝,形成有利于政治实践的“虚空”。
(三)回归科学的政治实践理论
阿尔都塞坚持唯物论科学性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应对经济决定论的“科学”主张,因为他认为经济决定论同历史唯心论一样,也是试图以特定的理论意图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施加外在影响,依据目的论解释人类历史。这种企图不仅无助于人民在历史实践活动中获得解放,还会使其深陷消极等待之中,放弃以实际行动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基于上述判断,从反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出发,他提出了回归科学的政治实践的任务。它的先决条件已经包含在坚持唯物论科学立场而产生的政治干预的效果之中。
其一,它为政治干预的理论预留了空间。在阿尔都塞看来,唯物论哲学的功能在于可以为政治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武器,反对科学中的教条,降低它们在借助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而发挥支配效果,改变各种支配性力量的实际比例关系。显然,如果能够以唯物论的哲学立场指出支配大众实践活动方式的虚假性,那么,原有的政治理论配置就会出现“缺位”,丧失维系原有社会关系的能力。这种理论“缺位”正好可以为无产阶级积极争取自由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之能够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游离于原有生产关系之外的个体或团体间建立紧密的政治联系。
其二,它为政治干预的实践预留了空间。阿尔都塞所理解的哲学并非致力于消除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实现思维与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实际上,他所关注的对象是人们的实践活动方式本身,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国家法使这种社会关系转变为物质性的存在,形成统治人民的力量。但是,它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政治实践方式。具体而言,意识形态控制的瓦解有利于无产阶级团结周围更多的人加入到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实践中。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要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核心,提出能够团结所有人的政治理想,为共同的目标而开展政治实践,进而为无产阶级历史创造性活动开辟空间。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依靠唯物论哲学反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支配,并在积极规划(否定既存的生产关系)过程中,确保政治实践基于实际处境,建构适合于政治形势发展需要的政治理论。
二、基于偶然相遇唯物论的政治实践理论
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经济决定论将人视为历史过程的“旁观者”,而唯心论历史哲学又忽视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强调人们的普遍意志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唯一动因。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能充分说明人们在历史过程中是如何摆脱必然性对自身的束缚的。在他看来,存在两种类型的历史,一种是从事后性反思完成的历史,它对历史进行目的论、决定论或起源论的解释;另一种是当下面向未来的政治实践活动,它是“不确定、不可预见和未完成的”。[4](P264)当然,这里的不可预见并不意味着共同的价值追求难以实现,而是指社会政治矛盾会随着事件的发生而产生变化。前者排除了偶然性的原因,将历史建立在已经完成的事实基础之上,对它进行揭示或反思,而不是从当前的政治实践活动本身(事件)去揭示人类历史进程。因此,从国家形成的角度突出“偶然性”的理论意图便在于:只有从否定偶然性的怪圈中挣脱出来,才能以历史的本来面目看待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才能反对目的论的唯物论扼制人民争取自由实现的机遇,建立科学的政治实践观。他从偶然性、相遇与唯物论等三个方面思考了如何实现上述目标的问题。
(一)“偶然”是政治实践的前提
“偶然性”在近代机械唯物论那里被视为关于对象的未知内容,某些机械论学者甚至主张根本不存在偶然性,认为它不过是未知的代名词,并坚信人们可以采用适当方法消除它。与之不同,阿尔都塞沿着马克思从实践活动考察人类历史的观点来考察它的意义。从意识形态发挥着维护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出发,“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含义被转换为意识形态支配的中断与延续,其中前者可以产生政治实践的“虚空”,即它的瓦解状态有利于形成新的政治联合。由此,他提出了不同于经济决定论的看法。
第一,生产关系的运行是在意识形态的参与下完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社会中的延续取决于生产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它保证了社会现有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运转。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个是政治—法律的(法律和国家),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各种不同的意识形式: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政治的等等)”。[5](P275)虽然两者都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但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是发挥维系社会生产关系作用的主要力量。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一,“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的想象关系”。[4](P296)也就是说,生存世界的异化使人们不自觉地接受了以话语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内容。其二,“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4](P298-299)它表现为国家机器要确定传播的控制范围,并借助话语形式使之在社会实践中得以显现。其三,意识形态把个体询唤为以整体形式参与到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因此,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不是一种机械的经济决定的运动,而是在“不在场的法”即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完成的。[6](P90)
第二,意识形态的支配效果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实际结果。法和一部分道德内容维系着现有生产关系的运行,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传播自身,并使个体成为社会生产体系的一份子。它有两个特征:其一,人与人之间的固定关系是意识形态支配的具体效果。在这里,阿尔都塞借用了列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即这种生产关系每时每刻都产生于商品生产的过程中。他认为,法和道德通过无形的、“不在场的”支配使个人参与到生产实践之中,保证了再生产过程的不断延续。其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能否顺利运转决定了它支配的效果。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散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各种社会机构以话语形式支配着被统治阶级。同时,被统治阶级也以各种方式减弱意识形态统治的实际效果。只有统治阶级力量压倒被统治阶级的力量,它才能发挥维护生产关系的作用,反之,人们便可以从中脱离出来。因此,它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两者的力量对比。
由于瓦解意识形态的支配便可以改变生产关系,这就为无产阶级联合其他被统治阶级依靠政治实践活动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开辟了空间。既然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压倒性的力量支配着社会成员,那么,被统治阶级应当积极介入到干预政治的理论实践中,以唯物论哲学反对意识形态对人的统治,制造意识形态统治的“空白区域”,为政治实践活动的展开创造有利条件。
(二)政治实践的方式——“相遇”
既然政治实践的前提是对意识形态统治退场的利用,那么,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主体应当采取怎样的实践方式联合分散的个体呢?结合他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阿尔都塞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要在坚持无产阶级对社会运动统治的前提下,找到一种“无等级制统治的、恰当的协调方式”,[1](241)只有“相遇”才是解决分散个体离散境遇的根本出路,它一旦发生,就会将彼此之间的联系固定下来。[5](P191)这样看来,只有以共同理想形式实现的相遇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他从三个方面做了具体阐释。
第一,“相遇”是政治实践活动的前提。在阿尔都塞看来,如果没有“相遇”,现实的一切都不会存在,仅有各种抽象的元素,缺少所有的连贯和存在。[5](P169)从政治实践的主体来看,政治实践活动是一种群体性活动,它能够在使意识形态机器瘫痪的斗争中发挥真正的功能,而不是单独个体的行为。这种看法与他对政治实践的理解密切联系。一方面,终结既存生产关系的力量只能来自阶级斗争,来自被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统治的对象的总体性政治实践的介入;另一方面,实践主体的总体性又不等同于独立个体的简单叠加,后者仅仅是政治实践的抽象理论要素,无法成为历史的实践主体。政治实践活动的承担者只有彼此之间以共同理想建立联系才能具有政治功能。这种总体性活动将有利于在政治斗争中形成压倒统治阶级力量的反抗斗争的合力,促使原有的生产关系结构走向解体。
第二,“相遇”需要政治干预理论的介入。阿尔都塞讲道:“显然,相遇本身并没有创造任何世界现实的一切,而仅仅是堆积的原子,在它们之上,相遇给予了他们以现实性。”[5](P169)从政治实践过程的一般特征来看,相遇后形成的联合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暂时性”,一种是“永久性”。暂时性联合是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实践目标而参与到实践过程之中,一旦目标达成,原有的政治联盟便会趋于解散。而永久性联合则是将参与共同政治理想的实践行动的个体集聚起来。与前者相比,后者虽然也要设定具体的实践目标,但它们只是共同理想的组成部分。
第三,“相遇”的完成状态是建立新国家。阿尔都塞认为,原子间相遇的过程必须持续。它不是短暂的,而是一个不断持续的状态。[5](P169)从政治实践的结果来看,实践主体参与政治实践活动的初衷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政治反抗,另一种是政治革命。前者是一种短暂的政治实践活动,取决于具体的政治目标、实践路径和达成目标的条件;后者则是一种持续的政治实践活动,它以变革现有的生产关系为目标。在他看来,如果政治干预理论能够通过政党组织的意识形态机器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政治实践之中,那么,它的最终目标便一定能够达成。
有鉴于此,无产阶级只有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转化为联合其他人的共同理想才能在实现自身价值追求的同时改变社会现状,即将具体的个人召唤为创造历史活动的实践主体。在他看来,既然政治干预理论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就具备说服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实践之中的条件。他既要保证理论与实践活动相符,又要在理论中兼顾无产阶级的价值追求。如果理论仅仅是对现实的反映,那么,它便不具备任何超越的内容,这样,就会失去对人们的吸引力。同样,如果理论的目的仅在服务于人们的价值追求,人们则会因不知道具体的行动方向而丧失对价值追求的信心。因而,持续的相遇正表明要积极利用“虚空”状态,使“相遇”发生的共同理想得以广泛传播,同时,要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制定阶段性政治目标,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从而实现永久的普遍联合。
(三)政治实践的基础——“唯物论”
阿尔都塞力图说明“唯物论”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意义。这里的“唯物论”是指在政治活动发生之前,原子化个体寓于世界之中的处境。这种处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原子化个体的生存处境是客观的和可以改变的。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论述中,阿尔都塞产生了思想共鸣,他认为,尽管海德格尔不是一个原子论者,但是,他也拒绝了对世界起源与意义问题的追问,而是将世界理解为被给定(be given)的存在,人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之中。世界的意义取决于人作为“存在”的超越性,是人的真实性和偶然性。[5](P261)一方面,在人进入到自己的生存环境之前,他无法为自己做出选择,而只能是这种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既然这种环境与人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那么,它又可以被人们自己的选择所改变,而促使生存世界发生转变的突破口便在于否定当下,使自己成为世界的支配者,但是,这种改变又要等待合适的机遇。这就表明政治实践环境是政治实践活动的客观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前提,政治实践活动便难以发生。
第二,原子化个体的思想处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能否发生。在《论偶然的唯物论》中,阿尔都塞指出,当人们在知道各种事物之后,这个起初还在以应答方式回应的人将以自学的方式终止这种状态,这正是唯心主义者通常忽略的一面。[3]政治实践意愿要以人们的思想处境为前提,他拒绝了将人理解为脱离现实条件而可以被随意塑造的观点,而是把人的思想状态和唯物论的哲学立场相联系,认为后者可以改变前者的看法,并视共同理想为人们团结的唯一途径。这就表明人们的思想状态绝非总是以观点林立、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形表现出来,而是可以为共同理想所塑造。
由于需要从主观条件出发考虑如何塑造统一的实践主体,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活动既要始终从唯物论立场出发考虑实现广泛联合的条件,又要反对那种认为社会是不可改变的错误立场,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改变它的有力境遇。这是他始终强调唯物论立场的根本初衷。
总之,从回归科学的实践观出发,阿尔都塞清除了目的论国家观对人们政治实践的束缚,说明了无产阶级可以从否定意识形态统治入手,基于政治实践的主客观条件,依靠共同理想实现和其他个体间的广泛联合,并凝聚为改变历史的实践主体,从而创造出符合无产阶级价值追求的政治国家。在他看来,现实世界存在着“机遇”,即实现无产阶级政治理想的虚空,只要能够抓住合适的机遇便能够实现自身的解放。
三、阿尔都塞偶然相遇的唯物论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唯物论要求回归到科学的政治实践方式,这种科学性始终贯穿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前提、方式和基础。它不仅为新时期欧洲无产阶级政党指明了争取解放的方向,也道出了实现自由的方法。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它的理论价值来看,首先,它注意到了西欧社会的新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新策略。随着西方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和全球市场化的逐步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结构日趋复杂,出现了许多非无产阶级的进步群体。面对新情况,资本主义统治不仅在国家范围内完善了暴力机器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大众的控制,还在大众文化层面加强了对大众的分化与瓦解。阿尔都塞敏锐地注意到:若想使无产阶级摆脱政治实践的困境,就必须联合这些新生力量共同加入到反对资本主义的阵营之中,然而,若按照经济决定论的主张,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这样,它的斗争力量不仅十分弱小,也很难在机遇到来的时刻实现政治有效的干预。因此,他试图以偶然相遇的唯物论来指导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反驳了和平过渡理论的观点。
其次,它从整个社会结构中探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在再生产中的作用。阿尔都塞在自己理论中期便已经注意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接合的关系,认为它们并非单纯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7](P74)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结构之中不是决定生产关系的唯一因素,而是表现出复杂性,即某种原属于次要地位的矛盾也会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上升为主要矛盾。“五月风暴”发生以后,他从再生产的角度重新思考了生产关系的存在和运行条件,认为意识形态是维护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前提,它依靠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以话语形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不仅使接受者能够在国家暴力机器的不在场的情况下,自觉地认可社会事实,还使他们主动从体现着虚假普遍利益的价值基础出发,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并使之不断进行再生产。然而,意识形态的支配关系一旦被改变,既存的生产关系便难以维系并趋于瓦解,这使他看到了无产阶级通过政治实践实现自身解放的希望。
最后,它试图通过强调偶然性的历史作用,将政治实践的科学性与人们对自由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阿尔都塞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活动一定要摆脱经济决定论强调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社会历史的进程绝非同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规律一样,与人的意志无关。从意识形态的功能出发,他认为无产阶级要从政治实践的具体要求出发,积极地利用突发事件产生的机遇,对社会历史的进程施加干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从具体的社会背景出发,充分考虑政治实践的主客观条件,在原有意识形态统治出现“虚空”的情况下,积极促成面向其他个人和群体的政治联合,并使它始终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这就回应了他对唯物论哲学的科学性理解,即正确的实践观要依靠正确的方法以恰当的方式表达理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8](P71-72)
阿尔都塞以意识形态为纽带联合其他团体的主张固然可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开辟新道路,但是,其潜在的政治分歧也会因政治实践对象的改变而暴露出来,致使政治联合面临着解体风险,这也是他不得不诉诸于不断“相遇”来解决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且,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也使他滑向了过分强调“偶然性”的一极。
首先,阿尔都塞把变革社会的焦点聚焦在唤醒大众和反对话语霸权的政治实践活动之中。由于他过分强调哲学的政治实践,即对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制度和法的理论干预,积极制造有利于人民群众追求自由的实践空间,这就使他过于强调唤醒大众和反对话语霸权,而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在他逝世之后,曾经受过其影响的学生,如普兰查斯、拉克劳等,彻底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转而以话语批判和公共政治活动作为其实现社会变革的生长点,由指导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理论退化为号召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话语反抗理论。这种理论立场的改变与其过分强调要以哲学的政治干预实现更多社会团体联合的政治主张有着密切关系。
其次,阿尔都塞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先在性,从而制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理论颠倒。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他为了实现政治实践转向而完全牺牲掉了历史活动的事后性解释,以致究竟是先产生新的法和国家制度,还是先产生新的经济条件,这成为其晚年政治哲学的理论难题。通过哲学实践的理论干预争取实现人民自由的机会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却将它与理解历史的理论建构活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根据他的观点,新社会的要素以元素的形式存在于旧社会之中,它的意义则有待人们去挖掘。但是,这种挖掘的意义并不一定等同于它在社会生产中的外在表现,因为在政治实践活动的背后,隐藏着为它创造条件的经济基础,只有尊重这个前提,那些推动人类历史变革的政治事件才能够获得成功。
最后,阿尔都塞在肯定新旧生产关系断裂的同时,否定了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他将生产关系理解为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参与下不断实现自身再生产的过程,这就使其将历史的变革理解为新旧生产关系之间的根本断裂。这有助于反对目的论的唯物论片面强调发展的连续性,断言新社会孕育在旧社会的框架之中,强调只有在政治事件降临的时候,人们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实现普遍联合,创建新的国家。但是,这就为新国家如何利用旧国家的物质性力量留下了难题。如果新国家没有继承旧国家的物质性力量,那么,新国家依靠什么力量保证自己的存在呢?
综上所述,阿尔都塞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角度对偶然性的深刻解读,是对历史唯物论的积极贡献。他之所以对纯粹的经济决定论进行反驳,这与他对无产阶级政治实践方式的关注密不可分。鉴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各种反抗资本主义的个人和群体力量的增加,使他提出通过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政治联合争取人的自由的实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偶然相遇的唯物论既是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批判,又是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行动策略。但是他未能合理解决历史的必然和偶然的关系。
[1] 路易·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Louis Althusser.Du Matérialism Aléatoire[J]. Assoc.Multitudes,2005,(2).
[4] 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下)[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5] Louis Althusser.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C]. Trans by G.M.Goshgarian.London:Verso,2006.
[6] Louis Althusser.Sur la Reproduction[M].Paris:PUF,1995.
[7] 王葳蕤.阿尔都塞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问题[J].教学与研究,2014,(12).
[8] 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上)[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孔 伟]
Research of Aleatory Materialism in Althusser
Jing Li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lthusser;the 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reproduction;political philosophy
It should replac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ith aleatory materialism in the declaration of Althusser’s later works for clearing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French communist. Althusser had never abandoned objective law of history and fell back on volitionism for underlying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of humanity. Obviously, his issue is to oppose materialism of teleology. He concentrated on the liberty of proletariat and thought the union with other progressive groups was good at intervene i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in the paralysation of state apparatus of ideology, when the unforeseeable event had arrived. It could help us examine profoundl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Marx. However, this theory resulted in abandonment of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by post-Marxist,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 and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 and discontinuation among productive relations.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认同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研究”(项目号:12&ZD006)的阶段性成果。
经理,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 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