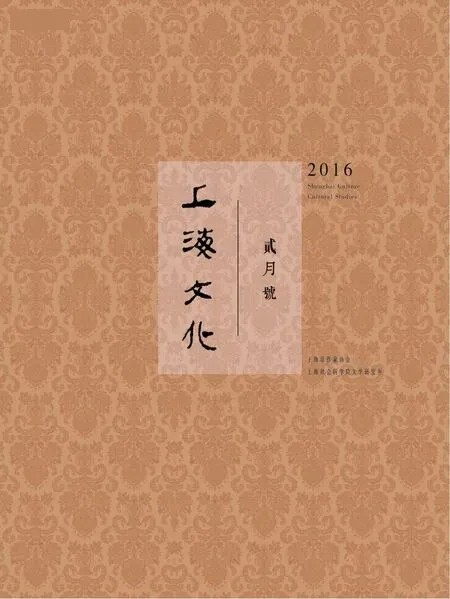“‘别现代’时期思想欠发达国家的学术策略”高端专题研讨会综述
潘黎勇
“‘别现代’时期思想欠发达国家的学术策略”高端专题
研讨会综述
潘黎勇
(上海师范大学)
2015年11月29日,“‘别现代’时期思想欠发达国家的学术策略”高端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知名教授、学者3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上海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所所长王建疆教授近期连续发表了一组以“别现代”命名的系列论文,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思想欠发达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缺乏原创的主义,人文学科处于弱势地位,学术话语和学术思想西方化,其后果便失去了在全球学术、思想和文化中的话语权,也与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潮流不相符合。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首先在学术上建构自己的主义,而“别现代”正是针对思想欠发达的事实所提出的一种主义的建构策略。它区别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而又同时包含三者的关于中国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的阐释概念。在别现代时期,多种社会形态既和谐相处,又相互纠结、相互砥砺,甚至相互冲突,处于同一个空间中,与西方的以时间断裂式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形成了很大的张力结构。但这种时间的空间化所带来的张力也构成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就如柏拉图所说的良马与劣马同时拉着一辆车,往哪个方向去,就需要高明的御手。因此,别现代就是别现代,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前现代,但同时兼具这三种时代的特征。“别现代”的“别”有“不要”、“告别”、“另外”、“别样”的多重含义,较之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生造的“differance”(延异)一词来,具有古今汉语的底蕴。“别现代”即指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关于社会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的中国式表达。在王建疆看来,依据“别现代”的思维立场,中国学术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性和主导性,而且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国学术能够在民族性与西方理念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此便能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有效地展开本土话语和主义建构。
与会学者就王建疆提出的“别现代”命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纷纷发表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别现代”是针对中国现实所提出的一个具有本体问题意识和阐释效力的思想概念。与会学者高度肯定了“别现代”命题的理论价值,赞赏其基于中国问题与现实所持有的学术立场和价值态度,认为该命题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黄海澄认为,“别现代”在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了一个聚焦点,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有效的阐释视角,具有学术新范式的质素,它的适用范围应该不止于美学和文艺学问题。张法认为,中国当代学术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如何有效地解释中国道路,“别现代”是从现代性话语发展出来的一种思想形式。它是利用一种本土化了的现代性话语来重新解释中国现实,藉之审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思想的功败垂成就看它对现代性话语的贡献怎么样。“别现代”是一种理论创造,其思想内容基本上是从美学层面来说的,这一方面可说是抓住了现代性的核心构件之一,也就是审美的现代性,但另一方面也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别现代”是否能够言说总体的现代性问题。秦维宪认为别现代理论实际上是对我们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激励。这个理论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乃至世界的文化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许明高度肯定“别现代”命题的思想价值和学术意义。“别现代”的说法使我们看到了某种可能性,它使学界以往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言说理论化、概念化、逻辑化了,为今后的思考者提供了一个抓住中国问题的把手,这对中国当代学术具有重要意义。周海敏认为,“别现代”是一种面向中国现实、与时俱进的真正的本土学术话语,同时,作为一个思想命题,它又具备前瞻性和全球性的特质。夏锦乾认为,“别现代”这个概念可以把过去很多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一些混乱、模糊的问题明晰地概括出来。“别现代”的思考路径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依照这个思路,是不是还可以提出“别封建”,“别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实际上,学界用来描述中国自鸦片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的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自己的创造。
二是“别现代”概念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并且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理论作为一种初创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话语,仍然处于建构过程当中,因此还需要从多方面完善其理论结构,充实其思想内涵,提升其学术品格。周宪指出,思想欠发达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了许久,钱学森之问,已经问了很久了,中国为什么缺少原创性东西?所谓当代中国为何缺乏自己的原创思想和理论这样的疑问其实反映出学界对本土原创思想缺乏的焦虑,这种焦虑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而要解决这样的焦虑自然是要实现我们自己的思想和理论的原创性。那么,此处就必然存在一个学术思想的原创性由谁来评价、评判标准谁来制订的问题,所以,在学术上完全摆脱西方话语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中国的学术要走向世界,首先还得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对西方人阐述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采用西方学术话语是不可避免的。自西学东渐以来,国人面对西方思想主要采取三种态度,分别是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和全盘西化,无论哪种态度,都包含了一种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别现代”力图寻求一种本土话语方式,这种努力值得赞赏,不过是否真的有必要将本土话语和西方理论对立起来呢?而即使是“别现代”这个概念,现代或现代性也仍是一个纯粹西方的表达,也仍是在用西方的框架来解释中国问题。吴炫提出,要全面认识“别现代”论题的意义,首先必须要理解什么是原创这个问题,而至于是思想、理论还是体系其实是次要的事情。原创必须在哲学层面上谈,所谓原创就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原创。立足当代中国,谈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和主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突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质而言之就是儒、道传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基本上是在儒道框架内发展起来并走向兴盛的,但这个框架没办法解释很多文学艺术现象,如苏轼的情诗,司空图的诗学,贾宝玉的文学形象等等。如果当代中国学术仍旧依附于儒家、道家来建构自己的主义,则中国永远不可能有现代主义,也谈不上创立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了。“别现代”如何落实到具体的理论创构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别”是和什么对象作区分呢?除了西方,是否还包括中国儒道传统。“别现代”是一个总体依附性的概念,能否突出自己作为哲学的“别”还值得研究。“别”容易接受,但是也很难完全与多样化的、独特的哲学接轨,这是“别现代”理论需进一步思考的地方。林少雄认为,就目前“别现代”所谈论的内容看,主要还是就美学和思维方式讲的,但它要作为一种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阐释力的学术话语,可能还需要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一一作出论述。程金城认为,我们可以把“别现代”看作是一种理论学说,乃至别现代主义,但在言说主义的时候,必须要把问题突出来。主义不是虚设的,也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别现代”的诉求及其指向的思想欠发达的判断,它到底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叶祝弟则认为,“别现代”在全球众多的现代性理论中如何彰显自己的合理性和思维优势、理论优势、话语优势、主义优势,需要展开学术争鸣,展开全球性的学术对话和思想碰撞,让中国学术在争鸣中走向世界。何云峰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有问题,后现代主义也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办?别现代就是一种对策和策略。别现代立意高远,具有超越性,理论指向是更高的时代。
三是基于“别现代”的延伸性思考。不少与会学者从“别现代”命题出发,对中国当代学术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夏中义从学术问题的提问方式来审视“别现代”的理论价值。他认为,就学术研究来说,能提出什么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提问题的方式同样关键,因为提问题的方式决定了问题的质量。夏中义将提问方式概括为两种:症候式提问和诊断式提问。依据这两种提问方式就可以发现,以往一直讨论的中国到底有没有美学、文艺理论这个问题,在王建疆那里表述为“崇无”、“尚有”,和“待有”。“待有”的问题超越了中国美学和文论有和无的问题,把问题引到了深处,尤其是引到了当下的现实中,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其实,沿着这种思路,还应该换一种提问思路,即中国的美学、文艺理论的表达形式是怎样的,和西方的有什么不同。由是可以说,中国在5世纪,存在刘勰《文心雕龙》这样相当成熟的美学和文艺思想,比同时代的西方要丰富、深刻和完备的多,而且更具有与现代美学的生命精神相贯通的元素。“别现代”可以帮助我们回到中国哲学、美学的思想现场,厘清思想事实,既能看到自身的优势,又能认识到缺陷。苏宏斌认同中国是一个思想欠发达国家这个事实,而对于如何改变思想欠发达状态,他提出了“弯道超车”的看法。就中国的当下学术环境来说,其主要对话者是西方学术,所以中国学术所谓弯道超车,超的是西方学术的弯道。而这里势必涉及另一个问题,西方学术有没有弯道,当前是不是处于弯道中。当代西方人文学术正处于一个低谷期,是处于弯道状态。中国学者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在这个学术弯道中实现超车的可能。这很大部分取决于学者自身的努力。在刘毅青看来,我们既回不到纯粹的传统,又无法用纯粹的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这就必然要求一种基于中西的学术化合,不管古典传统还是西方资源,都应该是基于某种问题意识而为我所用,这种取用过程实质就是在进行学术创造,是一种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照此而言,“别现代”正是这样一种值得肯定的“学术策略”。
在讨论会的最后,王建疆对与会学者的发言和提问作了回应。他认为,文化复兴要从学术复兴开始,要恢复学术公器的本来面目。只有学术的分析、甄别、批判,才能使传统文化的复兴走在健康的道路上。因此,人文学者要有担当,要进行原创性思想研究和理论建构、话语创新,做出不愧于时代的创造。同时他也坦诚,“别现代”理论正在建构中,其中的“跨越式停顿”、“自然发展观”、“时间空间化”等文章正在写作中。随着这些文章的发表,有些问题,诸如别现代有多大的涵盖性的问题,中西古今的关系问题,理论建构的标准问题等,都会得到进一步深入的解答。
在此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别现代”概念是中国学界近年来重要的学术创获之一,其论题的前沿性、话语的新颖性、思想的独创性在解释中国问题、构建中国本土学术话语方面必将产生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的其它文章
- “游泳”图释
- 殷商时代的巫乐考察
- A Song for Rosefinch with Passion and Tenderness: Bookview ofThe Wondering Man along Wu Chou River
- A Discussion on Jin Hong’s Syncretization and Variation and the Mondern Man’sConsciousness in the 1980s
- What is Shanghai Film: The History and Opportunities of ShanghaiFilm in View of Film Industry
-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Diplomacy: A Case Study of the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