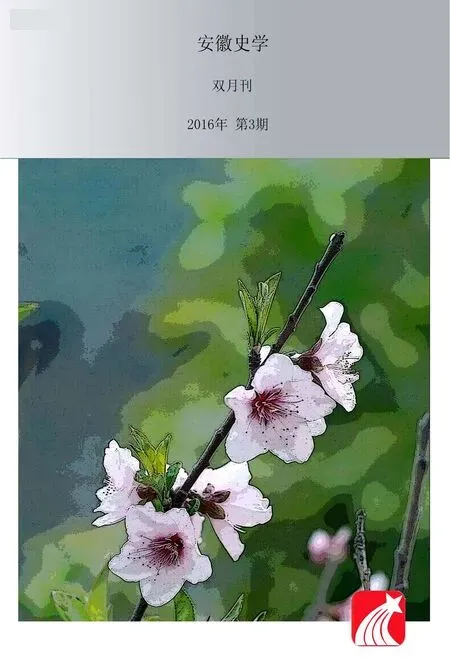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
王继平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
王继平
(湘潭大学历史系,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湘学在经历了元、明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进入了晚清繁盛时期。促成这一时期的繁盛现象,除了学术发展内在的规律及客观环境外,县域人文因素或曰县学的积淀,是重要的元素。新化邓显鹤于湖湘文献特别是船山遗书的收集整理、湘乡曾国藩经世理学士人群体的崛起、浏阳谭嗣同对中西学术的融通,促成了晚清湘学的发展与转型。
关键词:晚清;湘学;县学因素
作为一种区域学术的湘学,在经历了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短暂辉煌之后,陷入了元、明长达数百年的相对沉寂,到了晚清,进入了繁盛时期。学术发展自有其发展的脉络和自身的规律,但是,在这繁盛时期,有几个县的人文因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称之为县(府、州、县)学因素*本文所谓县学非传统官方儒学教育体系中供生员读书的学校,而是指县域中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即县域之学。可以特指县域某一著名学者之学术,如朱汉民先生谓谭嗣同之学为“浏阳之学”,但更多的是泛指一定时期一定县域有一定影响之学。其与学派也有区别,并非具有师承源流、学术谱系以及共同的学术旨趣。。本文拟以新化、湘乡、浏阳三地为例,探讨县学因素对晚清湘学繁盛的影响。
一
在晚清湘学复盛史上,新化是一个关键词。这首先表现在湖湘文献的汇集特别是船山遗书的猬集与刊行,其次是邹氏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型。
船山学的出现,既是清代湘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湘学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在明末清初的又一发展高峰,也是晚清湘学繁盛的重要标志。船山虽生当明末清初,其学说亦形成于斯时,代表着湘学发展的新阶段,但由于船山著作散佚未刊,其学说历两百余年不彰,而使船山学说显于世者,乃新化人邓显鹤。
邓显鹤,字子立,一字湘皋,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曾进乡试举人,然屡试礼部不第,大挑二等,任湖南宁乡县训导,因疾病归邵阳濂溪书院,卒于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梁启超称其为“湘学复兴之导师”*梁启超:《说方志》,《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湖湘后学称之为“楚南文献第一人”,可见他对晚清湘学繁盛的贡献。邓显鹤对晚清湘学复兴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关于新化人邓显鹤对湘学的贡献,夏剑钦在《邓显鹤弘扬湘学的成就与贡献》(《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一文中,对其文献整理、诗文创作均有论及,但就其与船山文献整理对晚清湘学发展的巨大意义,评价显然不足。,一是邓氏学术成就构成了晚清湘学的重要内容。邓显鹤一生致力于湖湘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他“以纂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二十五史》第12册《清史稿(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534页。,“搜讨掌故,不遗余力”、“岿然称楚南文献者,垂三十年云。”*易宗夔:《新世说》,“文学第四”,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曾国藩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
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饮食,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旁薄清绝,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君子惧焉。于是搜访滨资郡县名流佳什,辑《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东起漓源,西接黔中,北汇于江,全省之方舆略备,巨制零章,甄采略尽,为《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遍求周圣楷《楚宝》一书,匡谬拾遗,为《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绘《乡材经纬图》以诏地事。详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为《宝庆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三十四卷*《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24页。。
邓显鹤对湖湘文献的搜集整理,堪称在此之前规模最为宏大的工程,其价值正如同时代的思想家姚莹所说:
湘皋以诗鸣湖南数十年矣,乃其用心则尤在访罗遗轶,表章文献,……裒辑欧阳文公圭全集,与庐陵并行;编订《周子全书》,与《二程遗书》、《朱子全书》同垂天壤。其所为《宝庆府志》,先民、遗民、从臣、迁客及胜朝耆旧诸传,尤多可歌可泣,为史传所遗之人,盖楚故也,而天下之大文系也*姚莹:《南村草堂文钞序》,载湖湘文库版《南村草堂文钞》,岳麓书社2008年版。。
邓氏对湖南地方文献整理的贡献,是湘学发展史上重要的成果。湖广自康熙三年(1664年)分治,湖北、湖南两省建省,邓显鹤有感于作为一个行省的湖南文献的散佚,乃发奋搜集、整理,编辑成《沅湘耆旧集》,汇集了自晋宋至清道光年间湖南地区近2000余人的诗作,是湖南有史以来最系统的一部诗歌总集,对湖湘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梁启超曾将邓显鹤与李绂、全祖望相提并论,说:
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若何,间接影响于全国者若何,斯岂非明效大验耶?诗文之征,耆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5页。。
梁启超的评价,肯定了邓显鹤对晚清湘学发展的贡献。
然而,邓显鹤对晚清湘学的最大贡献是对船山遗书的搜集整理,使成为湘学标志性的船山学说得以彰显:
衡阳王夫之,明季遗老,国史儒林传列于册首,而邦人罕能举其姓名,乃旁求遗书,得五十余种,为校刊者百八十卷*《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24页。。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船山学说是湘学史上的重要发展形态。但船山生当明清鼎革之际,遭逢乱世,著述虽丰,但或藏之乡野,或散佚民间,使船山这一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湮灭山野而不彰。王船山生前,除青年时曾自刻一部诗集《漧涛园初集》外,其余著作全未刊布;他死后十余年,其子王敔曾选刻十数种,是为湘西草堂原刻本,流传甚少。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收书,对王夫之著作著录 6种、存目2种、查禁9种。邓显鹤经过艰苦的搜集,整理《船山遗书》150卷,于道光十九年在长沙开雕。不料,咸丰四年,由于太平军攻陷湘潭,“板竟毁于火”。湘皋先生对之汲汲不忘,多次寄书寄诗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督其印书。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由刘毓松等任校讎,在金陵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是为金陵刻本,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邓显鹤对船山遗书的搜集、整理功不可没,使隐没两百年的船山学术得以彰显于世,从而使王船山开始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并列为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船山之学才作为湘学的重要发展形态而名闻于世。正如姚莹、王先谦评价的,邓显鹤搜集整理刊刻湖南文献,“其大者尤莫如表彰衡阳王先生久晦之书,与顾、黄诸老并列”*姚莹:《南村草堂文钞序》,载湖湘文库版《南村草堂文钞》。;“今者船山先生竟与顾、黄两先生共垂不朽,刊书之功不可没。”*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批笺,光绪八年虚受堂刊行。正是邓显鹤对船山文献的整理,使得船山思想得以为湖湘学人所了解,而船山倡导的实学成为晚清湘学经世致用传统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奠定了晚清湘学的理论基础。
邓显鹤对湘学的第三个贡献是对湖湘后学的奖掖和影响,“奖宠后进,知之惟恐不尽,传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门庭日广。”最著名的是对魏源的影响,邓显鹤长魏源17岁,魏源一生以师礼事之,邓显鹤则对魏源寄予很高的期望,比之与蔺相如。还有邹汉勋,虽孜孜向学,但于乡间默默无名,邓显鹤邀请他一起校核、整理船山遗书,使其成为著名的舆地学家并开创了新化邹氏地理学家族。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说,邓显鹤对于湘学复兴的贡献是巨大的。湘学在经历了南宋湖湘学派的盛况后,一直处于沉寂阶段。邓显鹤的工作,不但使两晋以来湖南文献得以猬集,这就使湘学的统绪得以承接,尤使湮灭两百年的船山学说得见天日,也彰显了湘学在明末清初的巨大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船山学说为晚清湘学的繁荣提供了思想资料和学理传统。
新化为湘学做出贡献的,还有邹氏地理学。近代舆地学本质即为地理学,新化邹氏家族较有代表性,并形成舆地学上的新化派。其创始者为邹文苏之妻吴瑚珊,她曾协助其父撰《地理今释》10卷,邹文苏有6子分别为:汉纪、汉璜、汉勋、汉嘉、汉章、汉池,六兄弟在舆地学方面各有贡献,邹汉勋最为突出,于经学、音韵、地方史志编撰都较有成就,地理学方面,著有《六国春秋》及专论经纬度的《极高偏度说》和地图基本测绘方法的《宝庆疆里图说》。尤其是他总结了以经纬线测绘地图的经验,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它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可以说,邹汉勋是中国近代舆地学的奠基人之一。
邹汉勋之子邹代钧(1854—1908),字沅帆,又字甄伯。在地理学上的论著较多,如《上会典馆书》和《湖北测绘地图章程》,地理志及边防地理志主要有《光绪湖北地记》24卷、《蒙古地记》2卷、《日本地记》4卷、《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阿富汗、保路芝六国地记》8卷及《中外地理志略》、《中俄界记》、《中国海岸记》、《西域沿革考》等。邹氏在舆地学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成立了译图公会,另一个是建立了自己完善的测绘理论。1896年在好友陈三立、汪康年、吴达潇等人支持下,邹代钧于武昌成立了“译图公会”,后改名为“舆地学会”,计划出版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1897年首次出版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地图94幅,到1908年该会共出版地图13种,其中中国各地详图200余幅,加上国外地区共达600多幅,尤以《中外舆地全图》最为出名。
在测绘理论方面,邹代钧“不仅首次根据以地定尺的原则,以法国一米为三尺来制定中国之尺,而且将中西测绘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创立了自己系统的测绘理论”*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具体内容包括测量和绘图两个方面。测量方面,邹代钧主张通过测天度(经纬度)以定州县之部位,测地面以定州县所辖之各地。绘图方面,他认为绘制地图,首先要明确分率,即确定比例尺。分率既定,始布经纬。经纬画法上认为纬线曲经线直为最好。正是邹代钧的这一套完整的测绘理论,对《大清会典舆图》的测绘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依据该理论,邹代钧制作的《湖北舆图》和《湖南舆图》在当时各省测绘的地图中即属上乘。在邹代钧死后,1908年邹永萱筹资在武昌开办“亚新舆地学社”,后改名为“亚新地学社”,编辑出版各类教学、游览、历史地图,继承和发展了邹氏家族的舆地事业。
注重经世实学是湘学的传统,湖湘学者大多对舆地有极大兴趣,对山川形胜、舆图地理也多有研究。但使舆地学成为湘学的一部分,并俨然成为一学派,实自新化邹氏家族开始。此后,湖湘学者研究舆地学渐成风气。如严如熤撰《三省边防备览》,陶澍撰《蜀日记》,罗绕典撰《黔南世略》,尤其是魏源所撰《海国图志》,不仅是世界地理的集大成,而且其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更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思想之嚆矢。
二
在晚清湘学复兴过程中,湘乡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湘学繁盛的标志。湘乡因素的重要作用,就是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湘乡士人对经世之学的探求,使湘乡成为经世之学的重镇,并因为曾国藩及其所统率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事功而影响着晚清湘学的价值取向。
经世致用是嘉庆、道光之际学术的一种变向,是对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的反动,但它之所以成为晚清湘学的普遍价值取向,一方面,魏源受常州今文学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通经致用”的特色,陶澍、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对湖南学术界的经世之学的兴起起到了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曾国藩受到唐鉴的影响,崇奉“守道救时”,由此影响着湖南士人,形成了以湘军将领为主体的晚清经世理学士人群体,导致了晚清湖南经世派士人的聚集和崛起,引领着晚清学术发展并成为湘学的内核。
曾国藩是著名的理学家,但具有鲜明的经世色彩。曾国藩的学术,经历了“一宗宋儒”到“汉宋兼采”的转变,但都有经世的特征*参见拙文《论曾国藩的学术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只不过早期,其经世的诉求,主要“学礼”,所谓“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06页;而至后期,则从更多的方面来探求所谓经世之学了。他治宋学时,“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但于义理中探求经世之术;倡“汉宋兼采”时,更将经世之学的探求求诸于经、史、典制之中。下面的一段话可以说集中反映了他探求的经世之学的范畴: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弊,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第246页。。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经世之学研求的宏愿,举凡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均拟予以研究。其中关于“礼”的内容有四件,也可看出曾国藩的偏重。实际上,从“礼”中求经世之学,是曾国藩早年探求经世之学的特征,也是受其师唐鉴的影响所至。唐鉴认为“经济即在义理之中”,这是他认为“学问之途”只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的自然延伸。曾氏最初是接受这种分类法的,故云:“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以礼为经世之归,如郭嵩焘所评价的那样:“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郭嵩焘:《曾文正公墓志铭》,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4页。曾氏对《周礼》极为推崇,认为它“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稿、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06、152、206、152、206、410页。。他甚至以对礼的阐发与否来评价历代圣哲:“秦焚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06、152、206、152、206、410页。,“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06、152、206、152、206、410页。,“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06、152、206、152、206、410页。很显然,曾国藩对体现古代经世的礼学源流予以条理,其用意乃在于“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以弘扬经世之学。曾国藩审察历代经世书籍,“惜其食货稍缺”,故“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无所不赅,固如是也。”*《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06、152、206、152、206、410页。所以曾氏所列十四件可考究的“天下大事”,亦多为盐政、漕务、财用之类的“食货”内容。
因此,曾国藩求经世之学,一从“礼”中求之,也就是通过“学礼”,获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术。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06、152、206、152、206、410页。
在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而转向“汉宋兼采”之后,对经世之学的探讨扩大到历代典制史籍之中。他称经济之书从《会典》到《皇朝经世文编》,就是这种拓展。在读史方面,他历来喜读《史记》、《汉书》,而此时更有拓宽,不仅推崇杜佑之《通典》,且对司马氏之《资治通鉴》尤多推崇,以为是“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曾国藩对晚清湘学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他本人的学术成为湘学的一部分,而是他影响和集合了一批经世士人,造成了晚清经世理学的弘扬。首先,是对湘乡士人的影响,如刘蓉、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蒋易澧等等。刘蓉1834年与曾国藩相识,对于当时汉宋争讼的学风,他与曾国藩有着相同的见解。据云,他曾与曾国藩论学术,对汉宋之学多有所见。他说:“汉人诂经,各有专门,守师说”,而“近世所谓汉学家”,“异论歧出,其说千变”,“然则彼以汉学自鸣,非师古也,师心而已矣。其所为终由之而不厌者,非好学也,好异也已矣”,而“朱子于古今时务政治之宜,靡所不讲,而后世学朱子者,但守心性理气之辨,《太极》、《西铭》之说,闭关独坐,泥塑木雕”。刘蓉认为,汉宋之学“泯泯棼棼,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4—45、16—17页。。所以,他提出治学应“匡世济民”,经世致用。罗泽南在湘军创立之前虽未曾与曾国藩谋面,但二人却“神交”已久。罗泽南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表达了治学为经世的抱负,表示要“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著有《皇舆要览》若干卷,“百家述作,靡不研讨,而其本躬行以保四海”,被曾国藩推崇为邑之颜渊。罗泽南在家乡“假馆四方,穷年汲汲”*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4—45、16—17页。,很有一批门徒学生,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国华,李续宾、续宜兄弟,王鑫、王开仍兄弟,蒋益澧、刘腾鸿、钟近衡、易干良等等,都从学于罗泽南,受其影响颇深,具有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
其次,是对于湘学经世传统的弘扬。在曾国藩之前,唐鉴、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等人都是湖南经世致用之学的倡导者,曾国藩也受教于唐鉴。但是曾国藩通过湘军的事功,使经世之学成为湘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其对于湘学的贡献也就更为显著了。我们知道,在古代,除了南宋时湖湘学派曾名倾一时外,湖南学术沉寂不名,湖南人才亦属寥寥,湖南之于中国微不足道。自曾国藩湘军士人群体建立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事功之后,湖南才得以崛起,而这恰恰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士人群体所倡导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指引。
一是为后学指引了治学的方向,即以经世为目的,并因此而形成近代湖湘学风。作为文化史意义上的学风,是指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同时,它也是士人的一种学术心理积淀。在传统中国学术与政治紧密相联的社会环境中,学风不仅决定着学者们的学术价值取向,也决定其社会政治取向。因此,受同一种学风影响与制约的人,其社会态度、社会行为等方面,都有着基本一致或相似的趋向。一定时代和地区的学风对该时代的该地区的人才形成及其结构、素质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制约。湘军人物对经世之学的倡导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为湖南士子提供了一个仿效的榜样,这对湖湘学风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陶澍、魏源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近代湖湘学风,经过湘军人物的弘扬,已基本成为湖南士人的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成为一种定势的学术心理积淀。
二是影响了晚清以来湖南人才结构及素质。经世致用的传统与风格,使近代湖南人具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促使他们摆脱空谈义理、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传统路径,而强调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探求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并在现实政治中实现治国经邦的理想。因此,经世致用的学术与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是成为治国平天下之才。考诸近代湖南杰出人才成长的经历,大都是从小立下经世之志,刻苦钻研经世之学,养成了“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的经世情怀,承继了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的责任感,而这正来源于经世致用的学术与政治价值导向。近代湖南人才以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为主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经世致用之学强调的是对现实政治的参与,而不是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以适应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因此,它关注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经邦治国之术,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治国救民之道。在传统社会中,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与学术价值的理想实现形式,便是入仕从政。因此,经世之学的价值取向与近代社会现实相结合,使近代湖南士子走出书斋,在社会与政治转型与变革之中,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革命家,从而张扬着湘学的社会价值。
三
如果说在晚清湘学繁盛的过程中,新化之学开启了湘学复兴的帷幕,湘乡之学构建了湘学繁盛的基石,那么浏阳之学则成为湘学向近代转型的尝试。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伴随着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一系列西方器物开始了西学东渐的历程,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和研究西学,并试图寻求传统学术与西学的融合途径。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早期维新人士开始,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接受西学并力图融入中国传统学术的范畴,开始从学理的层面接纳西学,并形成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各种新的思想、理论、学说。到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就在较深的层面,糅合中西学术,形成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思想学说,开始了中国文化学术的近代转换。但是就湘学而言,特别是就学术内涵和价值指向而言,晚清湘学还是属于传统学术的范畴,是具有经世倾向的理学,也就是儒学的一个地域分支。同时,湘学还具有较为浓厚的保守色彩,甚至在戊戌维新时期,湘学的主流价值是保守的。一方面是理学家强调守道,讲求所谓正人心、端风俗,从本原上排斥所谓“奇技淫巧”,故而排斥西方的近代的观念、思想;另一方面,湘军的事功更造成了湘人特别是士人、士绅的强烈的保守闭拒的排外心理。当时有人描述这种情况说:
自咸丰以来,削平冠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陈宝箴奏,《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49页。。
湘人尚气,勇于有为,而气太盛,则不能虚衷受益*皮锡瑞:《伏师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
今人则评论说,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张朋园:《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页。。
这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既是湘学价值导向的结果,也影响着湘学的价值取向。即使到了维新运动时期,以叶德辉、王先谦为代表的主流学者,也是坚定地代表着保守势力对湖南维新运动进行攻击的。因此,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湘籍学者魏源以及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籍洋务派封疆大吏和士大夫,如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等等,他们或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或倡导中学西用,开展办实业、兴学堂、派留学的自强运动,但这并不标志着湘学的主流转型,而只是在理学的范围内扩大了经世的外延,即从传统的盐、漕、兵、农的经世扩展到西学的声、光、电、化以及坚船利炮,在学理的层面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试图融西学于湘学之中,重构湘学的学理基础,乃始于浏阳谭嗣同。
谭嗣同接触西学始于1893年。这年他与四川人吴樵订交,在吴樵的影响下,他对西学发生了兴趣,于是再次返乡时,他便购买了由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一些自然科学、外国史地和政治方面的书籍加以研究。从此,谭嗣同的兴趣逐渐转移到西学方面,企图从中探寻经世救国的路径。因此,他将以前研究旧学之得编辑为三本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莽苍苍斋诗》、《石菊影庐笔识》),开始了研习西学的道路。谭嗣同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7—168、128、293—295页。通过对西学的研究,谭嗣同开始了融西学于湘学的探索,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仁学》之中。
首先,谭嗣同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依据,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在宇宙万物起源和构成方面,谭嗣同早年继承了湖湘学者张载、王船山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主张气一元论,认为:“天以其混沌磅礴之气,充塞固结而成质,质立而人物生焉。”*《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7—168、128、293—295页。在接触西方自然科学以后,谭嗣同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解释的“质”,是指化学元素。而组成这些“质”的“气”,他以物理学的“以太”说明之,并用 “以太”概念代替了“气”,用以解释物质的本质。以太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一种物质。是物理学史上一种假想的物质观念,其内涵随物理学发展而演变。19世纪末,一些物理学家认为以太是传光热电磁的媒介,是一种密度比气体还要小的物质,但后来的实验和理论表明,没有任何观测证据表明“以太”存在,因此“以太”理论被科学界抛弃。以太这一概念被严复介绍到中国以后,赋予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内涵,因而规定了它的物质性。谭嗣同接触这个概念后,感到用它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物质构成更为直接,更能够使自己的仁学体系得到科学的支持,于是加以发挥,赋予它广泛的内涵。在《仁学》开篇第一章就写道:
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至于一滴水,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万而未已;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曰惟以太。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用,始可与言仁*《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7—168、128、293—295页。。
在此,谭嗣同说明了“以太”的物质性,并结合化学的“原质”概念,进一步说明了物质世界变化的根本原因:“原质犹有六十四之异,至于原质之原,则一以太而已矣”;世界上万物的差别变化,乃是其组成元素的不同:“质点不出乎六十四种之原质,某原质与某原质化合则成一某物之性;析而与他原质化合,或增某原质,减某原质,则又成一某物之性;即同数原质化合,而多寡主佐之少殊,又别成一某物之性。”*《谭嗣同全集》,第306、181、128、337、290页。
当然,囿于对自然科学的知识不足,谭嗣同的论证难免有错误的地方,但谭嗣同引入以太的目的,在于论证世界的物质性,在于说明世界发展的规律性,进而论证其“仁”的合理性。在谭嗣同看来,“夫仁,以太之用”,故“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用,始可与言仁。”
以太是体,仁是用,仁的主要内涵是“通”,“通”就是“平等”,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内外通,也就是人人平等。这样,谭嗣同通过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为他的变法维新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湘学带来了西学的因素。
此外,谭嗣同对数学也抱有极大的兴趣。据记载,谭嗣同阅读过当时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大部分数学著作,包括数学刊物《算学报》,也认真研读过一些数学著作,甚至演算过数学题。但是,谭嗣同并没有把数学作为个人的兴趣,而是将数学作为开民智的重要方法。因此,他在浏阳创办浏阳算学社,并建议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他认为算学实关系国家富强:
考西国学校课程,童子就傅,先授以几何、平三角术……故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兵农工贾,即未有通算而不出自学堂者。盖以西国兴盛之本,虽在议院、公会之互相联络,而其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不自测算而得。故无诸学无一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层台寸基,洪波纖受,势使然也*《谭嗣同全集》,第306、181、128、337、290页。。
可见,谭嗣同不但认识到科学对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也认识到了数学对于自然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足见其对数学及自然科学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谭嗣同在撰写《仁学》时,也应用到了数学。有研究者认为,谭嗣同在写作《仁学》时,应用了数学思维:一是《仁学》的结构几乎就是徐光启、李善兰所译《几何原本》的翻版;二是谭嗣同有意识地严格按照数学方式进行推理,例如对“平等”这一概念的论述*参见张祖贵:《谭嗣同与数学》,《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1期。。的确,翻开《仁学》“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赫然列出推理方程式。即如谭嗣同所说:“平等生万化,代数之方程式是也。”
谭嗣同对西方近代科学的研究之精深与应用之熟练、自觉,的确是此前湖湘学者未曾出现过的。这是湘学发生转变的迹象,是湘学转型的开始。
首先,谭嗣同在构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在阐释其宇宙观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作为其论据。湖湘学者张载、王船山认为元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强调世界的物质性,谭嗣同继承了他们的思想,认为“天以其浑饨磅礴之气,充塞固结为质,质立而人物生焉”*《谭嗣同全集》,第306、181、128、337、290页。。在研究和接受了西学之后,谭嗣同开始用“以太”来代替“气”,虽然以太是当时西方物理学的假设,也并未为后来的科学实验所证实。但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这就是谭嗣同提出了新的哲学范畴,不仅是传统中国哲学所无,尤为湘学中的湖湘哲学所无,拓展了湖湘哲学的范畴。
其次,谭嗣同的价值观,对传统湘学价值体系是一大冲击,对重构湘学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湘学的主流价值,乃是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封建的纲常伦理,所谓三纲五常。谭嗣同以冲决一切网罗的精神,对封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谭嗣同全集》,第306、181、128、337、290页。,是造成两千年来“惨祸烈毒”的根本,而封建的纲常伦理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要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谭嗣同全集》,第306、181、128、337、290页。从而根本否定了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传统的价值体系。谭嗣同还倡导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兴铁路、开矿山、办工厂,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也是对湘学传统义利观的否定。特别是他主张“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的“通”的思想,表达的是追求平等即“仁”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政治和伦理的所谓“正人心”、“端风俗”的政治伦理价值。
此外,谭嗣同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接纳,也是对湘学范畴的扩展。湘学是儒学的区域形态。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是以解经注经的经学为中心,其他的学科都只是经学的附庸。宋学的创始人程伊川论及古今学术的范围时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7页。清代学者姚鼐认为,学问之事有“三端’:“曰义理也,考据也,词章也。”*姚鼐:《述庵文钞序》,《惜抱轩文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46页。戴震也把学问分为三种:义理、制数、文章*《与方希原书》,《戴东原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4页。。曾国藩在鸦片战争以前,也把学术概括为“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一)》,第49页。由此可知,中国几千年来士人心目中的学问只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种,实际上也只有经学一种。自然科学被视为“奇技淫巧”,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所谓“凡推步(即天文数学)、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二十五史》第6册《新唐书·方技列传》,第619页。。在此之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等都在不同程度倡导向西方学习,也介绍甚至接受了某些西方学说,但大多为坚船利炮的技术层面或富国强兵的政治学说,对于自然科学则亟少接触和研究。作为受传统教育出身的谭嗣同,对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将其提高到变法图强的高度,他说:“盖以西国兴盛之本,虽在议院、公会之互相联络,互相贯通,而其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不自测算而得,故无诸学无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谭嗣同全集》,第181页。正因为如此,谭嗣同不但自己认真研究算学,而且在湖南兴算学,更重要的是将数学应用其《仁学》之中,进行了将其哲学思想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尝试。
因此,作为一部哲学著作的《仁学》,谭嗣同融传统学术与西方近代科学于一体,力图融合中西,并且构建了系统的体系,的确是湘学典籍中崭新的面貌,是湘学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当然,谭嗣同对于西学的研究与接受程度还不深,《仁学》也存在对西学的生吞活剥乃至曲解之处,但它是湘学转型的初步尝试。湘学近代转型的自觉,是随着20世纪一批留学生如杨昌济等人的回归才得以完成。
梁启超论及地方学术时说:“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且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04—305页。湘学作为区域学术,从整体而言是湖南这一区域学术的统称,代表这一区域学术的共同价值和取向。然就区域内部而言,由于经济文化传统有别,发展程度不同,县域的差别是存在的,故而县学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区域学术的发展。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湘学志”(12WTA3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方英
The Role of County Schoo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Hu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NG Ji-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After experiencing a phase of silence in Yuan and Mi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 in Hunan saw a cultural boo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o the inherent laws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 the factor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county humanity, or the accumulation and rising of County school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is prosperous period. The collections and arrangements made by Deng Xian-he (born in Xinhua, Hunan) in Hunan literature documents, especially the Chuan Shan’s Surviving Books, the rise of Practical Confucianism scholars, like Zeng Guo-fan (born in Xiangxiang, Hunan), efforts of Tan Si-tong (born in Liuyang, Hunan) made in Chinese-western academic bridge-all thes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Hu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Neo-Confucianism in Hunan;county schools factor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3-0018-09
作者简介:王继平(1957-),男,湖南双峰人,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