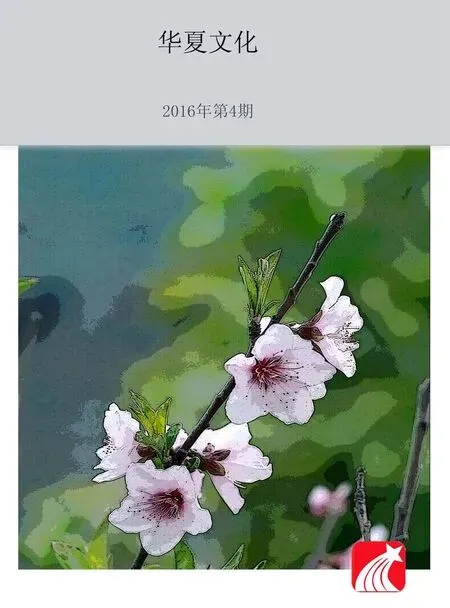情感、隐喻与周围世界:陶渊明的诗意“结庐”
□ 郝帅斌
情感、隐喻与周围世界:陶渊明的诗意“结庐”
□ 郝帅斌
刘小枫先生认为,中国的浪漫主义于魏晋时期形成气候。从思想渊源上讲,魏晋浪漫精神上法庄子,下取玄学。从社会根源来说,混乱颓丧的社会生活致使人们超形质而重精神,弃经世而倡逍遥,离尘世而取内心,求玄远和绝对,弃资生之相对。(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我们进一步说,陶渊明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极致。他的浪漫渗透到生活的一衣一饭,一山一水,一窗一隅,依凭他感知世界的卓越能力,在意志、理性、思辨、逻辑推演所不能抵达的地方,在权力、命名和秩序所不能管理的世界——死亡、沉迷、梦幻、情欲、伤感、迷惘和灵魂的领域——凭借性灵、情感、想象力和审美这些新工具去捕获世界,建立起世界的法则。
从这些新工具出发,平淡无奇的日常事物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有如笼罩着一层柔情、灵性而充满韵味的诗意光环。大道以诗的方式展现出来,诗被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从“林—鸟”到“人—庐”,陶渊明“结庐”在人境,完成了他诗意栖居的神奇飞跃:人不再以筑居者身份存在,而是以一种荷尔德林式的栖居者身份吟哦于大地之上。林、鸟和人建立起一种与大道谐和统一的关系。“吾庐”,这充满爱意的称谓,作为陶渊明对自我和人生进行透彻思考和再三确认后自觉选择的象征物,使世俗世界的生存居所,具有了肉身归宿地和心灵归宿地双重性质。
以“吾庐”为中心而展开的是一个被诗化的周围世界。在“斯晨斯夕,言息其庐” (《时运·其三》)的诗句里,我们看到“庐”被置身于魏晋人一向敏感的变动不居的时间之中。这让我们看到陶渊明的野心:超越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克服筑居本身所代表的劳作、种植、繁育、奔忙、休息和生老病死,将人直面自然,汲取大道所赐予的神性力量。
和17世纪的帕斯卡尔、18世纪的卢梭一样,公元4世纪的陶渊明也发现了爱的意义。当沉重的肉身沦陷在生存的困厄之中,只有爱才是唯一的安身立命的根据。“众鸟欣以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其一》)。在围绕“吾庐”而吟哦的日常世界中,陶渊明的诗意关照几乎无处不在。“霭霭堂前林”(《和郭主簿其一》),“幽兰生前庭”(《饮酒十七》),“荣荣窗下兰”(《拟古其一》),“榆柳荫后檐”(《归田园居》其一),“始雷发东隅”(《拟古其三》),“流目视西园”(《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咏贫士》) ……更有北牖、南畴、东篱、南村、南山、东郊、东林、东崖、西山、西阿等等命名,让这些司空见惯的日常方位、建筑构成,都为性情所染,显得温柔亲切,富有爱的味道。就连他的竹篱,都不再是一种隔离或禁闭,而是一种美的曲折。这种对空间的诗意描绘,也使得空间消融在大自然的呼吸之中,从而解除了它对我们人体的围困,构建起一个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周围世界。
作为人居建筑的必备——窗,在陶渊明这里尤其富有深意。窗本来就是天的投影地,风的游戏场所,窗里是一个内向而有限的空间,然而又并非封闭,与无限的外在世界有所沟通,与同样无限的内在世界同在。陶渊明把窗子与人的关系结合得更加紧密,其北窗、南窗和东轩所呈现的意义又各不相同。在陶诗中,北窗是快乐休憩之所,是劳动之后感触凉风的畅快之地,它隐蔽、私人而且快意。南窗则属于文人的寄傲之地,从南进行的一切活动多是正面、应俗、敞亮的,其内容则与理想、志向等基于士人身份而愿意公开展示的部分有关。钱钟书说,“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钱钟书:《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1991 年)。“依南窗而寄傲,审容膝而自安”,正是这样一种充满士人神韵的占有。
同样,新与夕(暮),这对规范时间的普通词汇,到了陶诗之中,成就一种炫目的辉煌。“新”是陶渊明应对时间中的沉重肉身,使之变得轻灵活泼的重要方式。诸如新苗、新诗、新酒、新畴、新月、新节、新制、新来燕、新秋夕、发新谣等词汇,都暗含更新、克服、净化、摆脱、提升、超越等非凡意义。孜孜于“新”的人总要付出“旧”所赐予的代价。与时光中的美好、温情、顺心、快意相比,往日的痼疾、习惯、情愫、失意都不是那么容易脱去,我们的生活常常因此而隐忍承受。这使得“新”笼罩着初生的美和希冀,就像是黑暗中所冥想的世界的早晨那样,欢喜和光明。
“夕”则是对早晨的回应。它在陶诗中常常与山气、归鸟、山林等意象相联系。“夕”是时间中的光的自现,却又绝不仅仅是太阳发出的一片简单的光芒。正如程抱一先生所说的那样,这种光芒可以使受它照亮的事物分外灿烂,天更蓝,树更绿,花朵更绚丽,墙上更金光灿灿,面容更容光焕发。夕阳依着山峰,周围是与之相衔接的次山丘、植被、山岩和远方空中冉冉飞升、旋转的小鸟。它们都披着落日的余晖,在黑夜即将吞噬这天最后光阴的时刻,改换了容颜(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于宇宙来说,这是一次不期而遇的相会,生命的目光捕捉了这永不重现的瞬间,而诗,凝固、传递了这一切。虽然传递的过程免不了损失,但更有增益。这增益,便是早晨所无法企及的生命终结时的虚空与饱满。
在超越有限与无限的过程中,陶渊明最为后人所称道的还是那句足以展现陶诗精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后世知己和发现者苏轼曾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为妙处”;又说一个“见”字有真意,“近岁俗人皆作望,神其索然”(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在苏轼评说的基础上,程抱一先生对此句中的自然之美做了进一步阐释(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他认为,中国的宇宙观建立在元气的基础上。美被元气激活,是一种在场或显现,遵循着隐现的原则。而山则是大自然的一种奇迹,是山让我们的世界没有变得像木板那么平坦和单调。山岭把生命提升到高处,大地之气和天上之气,可以在那里更好地交换。当云雾缓缓散开,山完全展现出它的美来,这美便是“天地大美”的自我显现。诗人在采菊的一刻,看到南山的行为正好与南山自身的显现形成一种令人欣喜的巧合。就如同人与自然在这时进行了一次不期而遇的对话,大自然在这一刻向它的知己倾诉了它最恒定的愿望,最不可言说的秘密。这是实的风景,同时也是人内心的风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风景,它永不再现,绝不重复,它成为人的生命中的唯一,也是瞬间的永恒。
东篱下欣然自开的“菊花”,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永恒的主题。其实关于陶渊明和菊花的关系,已是个古老的话题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陶渊明采菊嗅花的经典形象,让我们联想起晋人为汉语言贡献的一个高频成语:流芳百世。在刘义庆的名作《世说新语》中,戎马倥偬的大将军桓温躺在床上发表了一番独特的议论,他说人生在世,岂能寂寞无闻,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那就还不如遗臭万年。
流芳百世源自芳香存留不息的灵感,旨在把躯体和心灵相连的芳香变为灵魂本身的符号。倏忽而逝的植物通过芳香而得以无尽地存在,生命苦短的人则因美德而为后人所记忆。芳香能够在懂得它的人或嗅吻它的人心里激发出一种不可言喻的心醉神迷,并以某种更凌空、更浓缩、更持久的东西存在于接受者的记忆之中。一刹那间,我们不禁为“道”成万物而深深地惊喜与感激。
于是我们懂得芳香不再是菊花的附属品,而一跃成为它的本质。它使生命能够与始终孜孜于不可见的“道”延续相合。在这里,“道”之所以超越生死,不是经历了一个天堂,不在于永远地保持生命的恒在,而是要求生命像花朵那样,将它所负有的全部生命能量发动起来。此愿一旦达成,便是最高的圆满。芳香尽泄,元气淋漓,正如清人蒲松龄写陶生,“原是一段菊花的精魂化成”(张式铭点校《聊斋志异》,岳麓书社,1988 年版)。直到今天我们还将菊花和重阳意象叠加,意在长生久视。
与上面我们所熟悉的隐喻相比,在这个诗人“结庐”的诗意世界里,还有一个并不常为人提起的意象值得注意,即陶渊明的舟船意象。“船”在中国南方的家居生活中,几乎是必备之具。但在陶诗里,它是“吾庐”的延伸,极大地扩张了周围世界,为枯燥单一的隐逸生活带来了丰富的情感和多重的意味。
在《归去来兮辞》中,“船”的意象是欣悦和宁和,也是救赎,通往灵魂的安顿地——家园之甬道;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中,“船”又是痛苦的根由, “江湖风波恶,客愁焉有极”,“船”成了人在动荡不安的命运中无法主宰自我而任由其淹留、颠簸、困厄的象征(这种命运观更多地指向中国士大夫的仕途人生),沾染着悲伤的色彩,不仅与家园相隔相悖,更是孤独、疲倦和思念的情感寄托所在。此外,陶渊明还把船和月结合,开启了中国乃至日本的月船意象,启发了后来者“满船空载月明归”的纯粹、坦荡、无喜无悲,空空又满满的禅意人生。
在《桃花源记》中,“船”最终将有限的周围世界引向充满无限的彼岸境界。
“桃花源”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最后的也是终极的隐喻。在所有魏晋人创造的彼岸世界中,“桃花源”可以说最具现实色彩,影响也最大。这是一个儒道交缠的天地:在这里隐喻长生不老的“桃子”开始于周公开辟的黄金时代,此后短暂而分崩离析的秦帝国可以不计,汉魏却也不为人所知,鸡犬相闻的农耕生活仿佛回到老子的《道德经》时代。“存在”于此已跳出时间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被人类用来规限自身的时间失去了意义。这里只有绝对自由的天空,坚实、母性的大地,一切人世间的生老病死都在欢畅地劳作中隐匿。个人主义在这里终结,没有知识和记忆所带来的痛苦,没有一个你熟稔的历史人物生活在你周围,所有人都陌生且同一,没有个性而且忘我。于是万物静默,怡然自得。这几乎已是乌托邦的预显现,凭借“船”而抵达,深感其坚实的存在,又因“船”而恍然如梦,以为它已经失落,为人所遗弃,就如同一个令人惆怅的历史梦境或狂想。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寻觅—狂喜—再寻觅而迷失”的主题。可以说,桃花源代表一个抽象的最终存在,也代表着寻觅的过程,是一个关于寻觅的命题。
陶渊明最后“结庐”于这命题之中,并永居于此。
(作者:北京市北京广播电影电视研究中心, 邮编10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