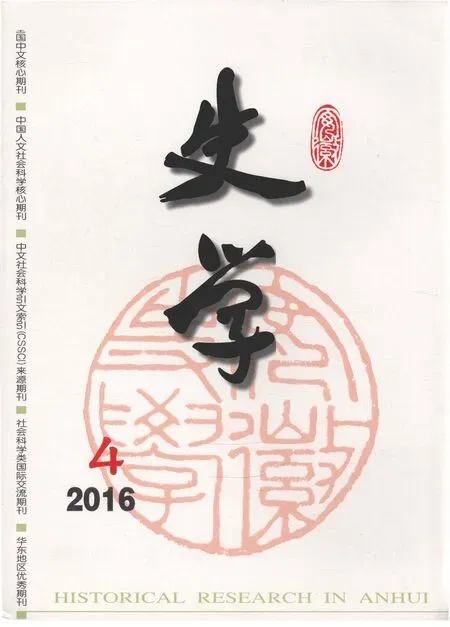商事如政事
——张元济“以政入商”下的文化运作
黄 剑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商事如政事
——张元济“以政入商”下的文化运作
黄剑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民元鼎革之际,中华书局以共和教科书为突破口,抢占商务教科书市场份额。面对危机,商务领导人张元济将其丰富从政经验与政治智慧导入商业模式,加之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高端人脉有年,故得以及时调整并挽回颓势。商务也适时利用其丰沛人脉,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年代夹缝中求生存,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无分新旧左右、禹内域外,效仿科举大举储才,将各方势力活成一片,使人脉在商务这个“变相之官场”的平台上,继续在政学商界良性延展,获得了自身历史上义利双赢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张元济;商务印书馆;以政入商;丰沛人脉;文化运作
满清亡于亲贵之手,是亲历过清季高层政治斗争的张元济的切身感悟。故在其执掌商务印书馆后,大刀阔斧地改革人事,慎用公司高层直系亲属在公司任职,清除管理层中尸位素餐之徒;运动政商学界各式各类人才在商务印书馆内外合理流动。张元济的“以政入商”——将政治智慧与丰沛人脉成功应用于商业运作,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不仅将商务打造成远东地区顶级出版巨擘,更被时人目为极重要之学术机关*胡适就张元济1926年辞商务经理一事致信论及,“……使这一个极重要的教育机关平稳地渡过这风浪的时期。”《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39页。1931年,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总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新闻报刊上,政学商三界许多头面人物纷纷独立或联合撰文,痛斥日寇摧毁我文化机关。,创造了行业历史上难以超越、义利双赢的辉煌局面。
学界对此问题,基本没有直接探讨,但也间接从某些侧面有所触及。孙惠敏认为,张元济的翰林从商,非一夕之变,而是长期积累经验、人脉的结果*孙惠敏:《翰林从商——张元济的资源与实践(1892—1926)》,《思与言》2005年第43卷第3期。。张元济终其之世不仅在积累单一面相上之人脉,而是随着时代变迁,与新旧左右的各方势力都有交集。叶宋曼瑛的研究最早注意到在“民国最初十年间,商务印书馆成为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可以愉快合作的场所——颇似众所周知在蔡元培任内(1917—1919)北京大学的局面”*叶宋曼瑛著,张人凤、邹振环译:《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实际上张元济在兼容并包的路上比蔡元培走的更远。该研究已经注意到张元济作为开明知识分子的那个面相,如果能更多的关注到张元济同时在政、商两界的面相,张元济的形象会更丰富和立体一些。杨扬对商务印书馆在1911年编印适合共和政体教科书问题上失误的事件进行分析,认为既有事件的突发性,也有公司困难;还有张元济本人倾向立宪,反对过激革命;及他对时局的判断来源于诸多友朋,如蔡元培、朱启钤、伍廷芳、郑孝胥等人,当时这些政坛人士都对武昌起义是否能迅速取胜,也无把握,所以影响到张元济的判断*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179页。。就作者举例而言的人物,分属不同阵营,显示出张元济人脉关系的复杂面相。
传统中国的宗法制社会,宗族与乡党在人脉构建中有天然之联系。张元济通过科举和婚姻进入了一个迅速上升的轨道,张元济在进士及第,续娶晚清兵部尚书许庚身之女后,人生开始了重要转折,由此衍生出的高端人脉为其在晚清民国年间呼风唤雨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地缘关系则成为他所构建人脉的重要基石。张元济身为浙人,通过科举及婚姻跻身上流,自然而然与政学商界的江浙头面人物发生联系。而晚清浙江、广东、湖南三地又是开化之士盛出之地*“盖我国开化之志士,广东、湖南而外,惟吾浙最盛。自康、梁被逐,谭、唐惨死,于是湘粤士气稍挫,独浙人尤激扬慷慨,志不少衰,其亦硕果之仅存耶。”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4页。,对时局影响极大,张元济凭此而建立的部分人脉的能量自是非同寻常。张元济少年时期在广东度过,故与岭南人物又有渊源,粤籍政学商上层人士自然也成为他人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元济在其一生的事功活动中,不断巩固与加强由业缘、姻缘及地缘产生的人脉关系,且将短暂政治生涯所获取的政治智慧及经验直接嫁接到商业运作之中,使商务印书馆得以不断扩张壮大。
一、教材与人脉
清末张元济虽与各方势力同时交往,在同一历史事件中,也尽可能的整合不同性质的人脉、共同参与、相互平衡,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因此获得长足发展,并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达到巅峰。同样,商务印书馆的兴衰,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张元济背后人脉势力的消长。这一特质,在商务教材的编辑与发行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发行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的初期业务重心和重要经济来源。民国肇兴,陆费逵成立中华书局,抢先出版与政体配合的共和教科书,企图改变商务独占鳌头的局面。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称:“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民国宗旨,前清学部所颁及民间通行教科书中有崇清及旧时官制避讳抬头等字样,应逐一更改,教员遇有书中有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并指报教育司,或教育会,通知书局更正。”*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戌编“教育杂录·第三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22页。办法从国家政策层面规定清代教材已不适合共和政体,而商务作为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此时还发行大量带有学部审定字样的前清教科书,必须作出修改。由于张元济自清季起就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高端人脉,尤其是政府中主导教育的资源,便及时调整出版方针挽回颓势,再上高峰。
在北京政府时期先后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汪大燮、严修、傅增湘、汤化龙、张一麐、汤尔和对商务都助力很大,当中非北洋系的蔡元培与商务关系最深。作为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的蔡元培,与张元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中,相互砥砺、共同成长。两人自登科起就交往甚密,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南来上海短暂主持南洋公学,蔡元培随之加入。1901年11月7日,醇亲王载沣视察南洋公学,沈曾植、费念慈、张元济、赵从蕃、蔡元培“迎送谒见。午公学宴醇邸及其参议员,随员与宴,座中凡三十余人,有地方官及道府以公事留上海者,又美国人五,皆公学教习。”当晚张元济与蔡元培更亲赴广学会,采购南洋公学备呈载沣之书籍*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面见醇亲王,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张元济偕蔡元培同往,可见二人关系非同泛泛。
1901年12月11日,张元济与蔡元培共同创办《外交报》*十一月朔,“菊生邀饮万年春,凡任《外交报》资本者,各先出银三百圆,由办事人出收据,即余与菊生、仲宣、钦甫也。”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1907年,孙宝琦出任驻德公使,蔡元培请孙宝琦之弟孙宝瑄及张元济等人关说,愿在公使馆兼充一名职员,半工半读。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三十两,而不用蔡元培服役。张元济也代向商务印书馆洽定,特约蔡元培为该馆编书,每月薪酬一百元,一部分汇往德国,一部分留给蔡元培在国内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67—568页。。蔡元培自此得以安心赴德留学。张元济也信守承诺,加以资助*1907年6月7日有:“甘单之款萧伯容寄来五百元已入尊账,收条附奉存詧。前汇之款已由京划奉,遵即转达粹翁,业已谈恰。”1909年6月5日有:“本月初七日寄上一函,内附一千马克汇票一纸。”《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452页。。直至辛亥革命成功,蔡元培出掌教育部,都受到张元济不少帮助。1912年6月27日,蔡元培致蒋维乔书:“所希望于菊公者,贷弟以千圆整数,俟弟南归后,陆续设法筹还耳。如公再晤菊公,务请代达此意为幸。”*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157页。蔡元培其后又数度执掌最高教育机关及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麾下教育资源极为庞大。张元济如此待人,蔡元培投桃报李之处亦多,为商务印书馆在教育上的垄断事业助力甚大。
汪家熔的研究认为,《北京大学丛书》、世界社的《世界丛书》、《北京大学月刊》都是蔡元培主持下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汪家熔:《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1页。。蔡元培从政之后,先后执掌教育部、北京大学、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等全国教育主管部门及高等学术机构,与商务关系密切到曾出任其董事会董事。两人之间,终其一生,互动频繁,相互倚仗之处多已。张元济与蔡元培的交往只是其众多关系脉络里的一个例子,但借此可以看出张元济的独到眼光。
凭借张元济掌握的丰沛人脉,商务印书馆应变迅速,从1912年1月开始,陆续出版系列教科书:《订正简明国文教科书》8册,戴克敦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4、16、35、35、35—36、36、85、17页。;《订正初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10册,蒋维乔、庄俞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4、16、35、35、35—36、36、85、17页。;《订正最新修身教科书》8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4、16、35、35、35—36、36、85、17页。;《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8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本书系辛亥革命后该馆编的第1套影响较深的教科书*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4、16、35、35、35—36、36、85、17页。;《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乙种)8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4、16、35、35、35—36、36、85、17页。;《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甲种)8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4、16、35、35、35—36、36、85、17页。;《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8册,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4、16、35、35、35—36、36、85、17页。;《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6册,姚祖义编纂,张元济、夏曾佑校订*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4、16、35、35、35—36、36、85、17页。;《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8册,沈颐、戴克敦编纂,高凤谦校订*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4、16、35、35、35—36、36、85、17页。等等。此种反应速度,与商务内部训练有素的编辑成员及领导人处惊不变的决断能力有密切的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张元济执掌的商务拥有政学商三界高层的丰沛人脉,尤其是政府内部主导教育的高官,如蔡元培等人的鼎力支持,因此才得以迅速摆脱颓势。
商务印书馆在积极修改教材的同时,也利用舆论进行造势。商务在《申报》上刊发广告向民众推荐曰:“民国成立,政体共和,教育方针随以变动。本馆前编各种教科书叠承海内教育家采用,许为最适用之本。今以时势移易,爰根据共和国教育之宗旨,先将小学用各种教科书分别修订。凡共和国民应具之知识与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详细叙入,以养成完全共和国民。兹将修订已成各书分列于下。”*《共和适用之教科书》,《申报》1912年2月23日,第3版。商务颇有技巧的强调了自身优势,姿态高调且富有底气。
由此观之,中华在民国建立之时,在教科书上的突袭打了商务一个措手不及。但商务凭借着政学商三界的丰沛人脉,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优秀管理与编辑团队,迅速扭转颓势,再度回到教科书出版的优势地位。中华书局的出现,使同业竞争开始加剧,直接导致民国初年教科书质量的上升,对一直居于垄断地位的商务来说也是一个向此努力的方向。
张元济在政学商界拥有庞大的人脉圈子,尤其是教育方面的资源,使得商务从晚清一直到国民政府建立的前期,多时能快人一步,及时出版与不断变化的教育方针所匹配的教科书。虽然此次由于商务决策者的原因,未能抓住共和教科书首发良机,但商务借此机会也越挫越勇,吸取经验教训,及时调整和进一步完善了企业架构。
张元济在中华书局崛起后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与政府内部,尤其是教育上掌权人物的沟通。张元济友朋之中,傅增湘与蔡元培一样都为其在教育界之大靠山。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四川江安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同年5月,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历官贵州学政、直隶道员。赴日考察教育归国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任直隶提学使,还曾充癸卯顺天乡试同考官,北洋大臣文案,直隶学务处会办,北洋女子公学、北洋女师范学堂、北洋高等女学堂总理,宪政编查馆一等咨议。宣统三年(1911年),与张元济同时出任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傅增湘随唐绍仪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中华民国成立后,任约法会议议员,1915年8月任肃政厅肃政史。
1915年元旦,张元济致信傅增湘,打听教育形势动态:“明年直隶发起省教育会联合会,江苏省教育会同人正在研究议案,其对于学制亦多不主张更改,惟于中学有仍取文实分科制之说。即使提出后多数通过,亦期以三年为实行期。从前改革学制每以颁布之日为施行之期,往往学校基础未定,而纷更已来,故永无良善之效果。此层似亦不可不虑。该联合举行在即,议定其事自必上诸政府。既议改革,何妨稍致须臾,参以众论,似于实际较有裨益。”*《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283页。1月6日,张元济得傅增湘复信,得悉“教育方针尚未定”*《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1页。。2月12日,再得傅增湘复信:“教育案已定,学制无大变更,但酌加读经耳。”*《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1页。同日,复傅增湘书:“教育案知已议定,无大变更。三学期实不便于社会,暑假、年假、寒假又春假,徒便于教员之躲懒,而失学生家庭之信仰。此实教育之一大障碍,想公等必已筹议及之矣。……。承询有人欲入本公司股数千,是否一户,抑系数人?向执何业?现司何事?能以姓字见示否?果与公甚相习者,必为设法也。……程树德条议令人沮丧,项城竟交部议,不知何意,公能知其内情否?”*《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283页。
此处“程树德条议令人沮丧,项城竟交部议”,乃指程树德1915年1月27日给袁世凯上条陈,提出停办小学,仍以私塾为主,并恢复科举的主张*《最近北京之趣闻》,《申报》1915年1月28日,第2版。。“条陈计分三大纲:(一)各省分放学宪县行考试;(二)与办科举集多士以推具才;(三)废去小学堂提倡私塾以复前清旧观。”*《北京近今注视之留学生》,《申报》1915年1月30日,第6版。《申报》对此评论曰:“近日北京中流以下社会纷纷谣传谓有留学生某君在某院占有最重要之位置,以前清覆亡全由于废科举兴学堂。民国成立,不应采取前清之亡国政策。因上书总统,呈请废止小学,提倡私塾,并恢复科举制度,总统阅呈颇为嘉许,即交教育部议覆。”*《最近北京之趣闻》,《申报》1915年1月28日,第2版。
袁世凯这个举动很明显是为帝制张目,试试舆情反映。张元济敏感察觉,故忧心忡忡致信傅增湘打听虚实。这也是为何商务一边发行共和教科书,一边仍沿用某些冠有学部审定字样的前清课本,直至袁世凯病逝*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农历3月25日,张元济才公开决定,“告傅卿,通告各馆,帝制取消,应推广共和书。并将普通书速即销去,勿退回”,“电告洛阳张,告同业,现非共和书不适用,勿再误会。”《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5页。。由此可见,直到民国建立四年后,商务才作出全面采用共和教科书的决定。文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分售的《小学笔算新教科书》甚至走得更远,在民国九年一套小学教科书廿七版的封面上还写着醒目的“学部”审定的字样*张景良:《学部审定·小学笔算新教科书》,文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分售,1920年第27版。。但是,商务保留的学部审定的帝制教材,与袁世凯称帝所用的帝制教材区别明显,商务的帝制教材是保留前清审定的内容,而非讨好袁世凯而编,多从市场需求的盈利角度出发而保留*许多偏僻的农村小学不仅在20世纪10年代沿用老式教材,在抗日战争的40年代也是如此。许多小学“挂着皇皇中心学校国民学校招牌,在教四书五经”。黄剑豪:《西江八县之国民教育》,《中山日报》(韶关版)1941年8月4日。。也正因同为帝制教材但内容不同,袁世凯称帝期间,商务课本备受排挤。商务的股东会议记录中,有如下记载:“本公司出版小学应用各书内容与国体有关者,去年‘帝制’发生之时,颇被排挤,办事人甚费周章,难免暗耗。幸事机即转,本馆旧存之共和书反而畅销,所得尽足以偿所失。”*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页。张元济在同时同事上交结各方人脉,也包含有企业夹缝中求生存之苦衷。
傅增湘早在1902年入袁世凯幕,在北洋同人眼中,被目为袁之私人。资深如徐世昌,谈洪宪逸闻时道:“就幕僚方面言,项城在北洋,有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徐世昌谈洪宪小史》,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殊不知,袁世凯的幕僚,虽首推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次为张一麐、沈兆祉、闵尔昌等,但这些故吏,多与冯国璋一样被蒙在鼓中,此时真正运作复辟之事的幕僚为夏寿田等人*《徐世昌谈洪宪小史》,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8—79页。。所以此次张元济打听对象错误。
1917年12月,傅增湘任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此后在第三次段祺瑞内阁、钱能训内阁留任教育总长,还曾任财政整理委员会督办。翌年10月,被时任总统徐世昌聘为总统府顾问。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因北洋政府罢免蔡元培北大校长,始辞教育总长一职。张元济在信中,除了与傅增湘谈论教育的话题外,对傅增湘介绍来购买商务股票的人士,并不是一味接受,也进行了调查,认为只有和他们“甚相习者”,才“必为设法也”。张元济善于利用这些社会关系,不仅给他个人积累了庞大的人脉圈子,也使得商务势力也随之壮大,在出版及新闻事业上的垄断地位日益稳固。
1917年是中国政局上颇为动荡的一年。年初,由于对德宣战问题演变成“府院之争”,进而发展到张勋复辟,最终引发“护法运动”。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并没有给商务造成太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虽然政坛的要角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张元济的旧雨新知还牢牢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教育主导权(如蔡元培年初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使得商务教科书在民国初年被中华短暂突袭成功之后,很快又再度牢牢占据了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对内没能出现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对外,列强又忙于一战,外国资本没有大举入华,反而使商务这种民族资本企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也正是这一年,曾经背弃商务的中华书局主事人陆费逵,由于时局变化非常,未能平衡各方人脉导致中华业务难以为继,请求商务领导人力促两家合并。中华书局自民元从商务印书馆脱离出来,就一直是商务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陆费逵对商务推销教材的手法非常熟悉,自立门户后多有效仿,但知易行难,在开业五年之后竟然落到主动要求合并的落魄地步。这当中有北洋政府内阁更迭频繁,教育部长随之变动,故而引发书业竞争的因素。吉少甫的研究注意到,出版企业与教育部长的亲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教科书竞争甚至书业竞争的格局。如范源濂任教育部长时,中华在与商务的竞争中就占上风;而与商务较深的汤尔和等人任教育部长时,商务在竞争中则反过来占了上风。至于运动各省教育首长采用各自教科书,也是两家惯用伎俩*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331页。。王建辉认为,两家企业相互比较,“中华具有更多的官方色彩,带一点官督民办的色彩,中华的股份,后来很注重走官方的路子。”*王建辉:《商务与中华:中国近代出版的冠军和亚军》,《中华读书报》2005年9月21日,第3版。然综合观之,虽然教育部长的更迭会引起市场份额发生一些变化,但商务牢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始终掌控有七成左右的教科书市场。而且因为其是老牌企业,资本雄厚,股权分散,所以看起来中华官方色彩稍浓。实则就商务历年董事会成员变动来看,除了创办人与重要高管外,不少董事多是在任或卸任高官。
吴燕在研究商务与中华合并这段历史时,认为陆费逵在1917年5月28日会见张元济,7月10日会晤过高梦旦之后,商务、中华的“联合之梦就这样彻底灰飞烟灭了”*吴燕:《民国初期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联合谈判始末》,《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但王震的研究指出商务、中华的联合是有数个阶段的,1917年7月1日,中华书局被史量才、唐绍仪、王仰先、贝润生等原中华的大股东所组成的新华公司承租。此后,两大出版社领导人张元济、高凤池、史量才、陆费逵等人,也多次商议转租中华,但都未能实现。同年11月下旬,陆费逵又将中华书局收回自办,两大出版社合并之事这才宣告结束*王震:《张元济先生愿商务与中华合并》,《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77页。。商务与中华合并之事,张元济一直是大力促成的,只是在遭到政治上、教育上的重要靠山傅增湘反对时,才戏剧化地暂停了与中华合并的动议。当年5月14日,王显华、孙壮来见张元济,对合并之事大加反对,王显华尤其激烈,张元济逐层剖析,“仙华言如此并无不可”*原文为仙华,指王显华,引用按原文不改。,总算同意了张元济力主合并的理由*《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203页。。但王显华又带来傅增湘、王季烈等人之信,表明均不赞成合并之事后,张元济态度改变,在午后参加商务印书馆第182次特别董事会上议定“中华合并问题因时局变动,即行停议”*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第467页。。张元济当天日记中也记载“以中央政局变动,不如停议”,并和高凤池约陆费逵面谈,告知停议之事*《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203页。。由此可见,张元济在两家合并一事上180度的大转弯直接原因就是收到傅增湘与王季烈的反对之信,信中内容虽无法得知,但马上停止,充分说明对即将出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意见之重视。两家出版巨头从中华的自立门户到请求合并,背后都是人脉消长的博弈,而最后未能合并成功,也是人脉作用使然。借助愈来愈根深叶茂的三界丰沛人脉,张元济往往在学制变更前夕,已知当中乾坤,使得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市场屡占先机,得以成为行业龙头,将一度有赶超之势的中华书局又抛于其后。
人脉的良性延展,一方面对外广结善缘,一方面向内储备人才,内外结合,方可期之大成。张元济在广结善缘的同时,充分借鉴了科举取士的可取之处,不断延揽各方人才,以适应社会大势并获得迅速发展之助力。
二、效仿科举之商务储才
张元济消化许多政治上的有益经验,应用于商业运作,如效仿科举制度,积极储备人才以备不时之需。民国元年,面对中华书局迅速崛起的挑战,商务加紧了储才的速度。由于商务编译国文部诸人,脱离学校即教育第一线多时,与当时的教学状况有所脱节,不得不延请相关教师,来充实教科书编辑人员阵容。
当时苏州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教师,如吴研因、范祥善等人,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先后编写了几部小学国文教材,不仅在本校推广成功,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广受好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分别把吴研因和范祥善聘请过去。后来世界书局的沈知方把范祥善从商务挖走;商务又用高薪将吴研因从中华书局撬走*谢菊曾:《涵芬楼往事》,《十里洋场的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60、61页。。谢菊曾回忆:“当时苏州一师附小的另一位教师俞子夷,编有新式小学算术教科书一部,用实物示教,内容新颖,趣味盎然,亦为商务印书馆以重金购下出版,我曾为此书校对过一部分。”*谢菊曾:《涵芬楼往事》,《十里洋场的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60、61页。
用人唯贤,不仅是非常时期的形势所逼,而且是张元济一直提倡的方针。这样不仅会让企业变得更有生命力,而且在商言商,也可以使得企业获得更大的利润。
张元济就储才一事也多次与公司主要股东和负责人进行探讨。1916年8月23日,张元济日记中记载与高凤池在这方面的交流:“翰言,闻人言,各部长言干涉太过,不能办事。余答言,甚不愿干涉,但不干涉则办事与否从何而知。”*《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00—101、97、103、104、105、106、108、109、109、110页。为了改变这种事必躬亲的状态,张元济加快了引进人才的步伐。8月16日,与庄俞、蒋维乔商量编译所人才事。张元济有云:“如有教育编辑之经验、学界之资格者,总宜收罗。”*《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00—101、97、103、104、105、106、108、109、109、110页。8月26日,约请张君劢担任杂志论说、德文书之校阅,又代撰紧要广告,月薪一百元*《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00—101、97、103、104、105、106、108、109、109、110页。。8月28日,午后在高凤谦寓所与陆尔奎、吴敬恒商谈业务发展之事*《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00—101、97、103、104、105、106、108、109、109、110页。。8月29日,张元济与黄炎培、郭秉文商量,拟聘蒋梦麟入馆一事*《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00—101、97、103、104、105、106、108、109、109、110页。。8月30日,致信郭秉文,“为延聘蒋梦麟事。即将昨日所谈详述办法。信留稿,存入延聘要人案内。”*《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00—101、97、103、104、105、106、108、109、109、110页。9月3日,访黄炎培,谈蒋梦麟之事*《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00—101、97、103、104、105、106、108、109、109、110页。。同日,梁启超推荐蒋百里。蒋欲在沪伴蔡锷疗养,不能不兼谋生计。欲月得二百元,张元济表示同意*《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00—101、97、103、104、105、106、108、109、109、110页。。9月4日,陈叔通介绍张仲仁。张元济与高凤池商定,“决定延请,每月薪二百元。”*《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00—101、97、103、104、105、106、108、109、109、110页。9月6日晚,张元济与高凤池、鲍咸昌、高梦旦、李拔可商议湘馆经理调动事。先生以为“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00—101、97、103、104、105、106、108、109、109、110页。。
不难看出,商务招揽知识较优的新人,目的就在于与学界、政界接洽。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营造的庞大高端人脉圈,必须如此方能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相匹配。而且,张元济为企业引进先进人才的同时,并没放弃公司元老中的有用之才,淘汰的多是些冗杂之辈。
张元济用人的新旧概念,他自己有明确阐释。1917年有信至高凤池书,“畅论用人政见之不同”。谓“……公司事业日繁,人才甚为缺乏,且旧人中之不能办事者甚复不少。若不推陈出新,将来败像已露,临渴掘井断来不及。”*《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102、103、103页。“且公主张用老人,弟主张用少年人;公主张用平素相识之人,弟以为范围太狭,宜不论识与不识,但取其已有之经验而试之。”*《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102、103、103页。后就此问题再度去信谈及:“本馆成立业逾廿载,不免稍有暮气。从前规模狭小,所有习惯不适于今日之用。欲专恃旧有之人才、昔时之制度以支此艰巨之局,其必终遭失败可以断言。弟等愚见,旧人固当重加倚畀,然才具平庸或敷衍了事成绩下劣者不能不严予裁汰。而素有劳绩年已衰迈者应另定酬给章程俾资退养,免致占居前方,俾新进不得迁擢。然一面裁汰,一面仍宜招徕。凡有新知识之人而宜于本公司之用者,仍当尽力罗致。更参以减额加饷之法,则支出亦不至滥增。至于公司规定规则,向来甚不完备。从前习惯足以为今日之障碍者,必当扫除,另行规定,俾昭整饬,庶治法治人同时可以并进,而公司亦可渐臻于光大巩固之域。否则冗员日多,人人趋避,徒保禄位,不负责任,弊病丛生,莫能防范。”*《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102、103、103页。
由此看来,张元济并未按加入商务的时间先后来定义新旧,而且在商言商,从企业发展出发,对原有员工中尸位素餐、再无贡献之人予以清退,以给新进才俊让开位置,让他们施展才华。张元济自从戊戌变法历练之后,对浪费资源、碌碌无为之辈是深恶痛绝。现今在自己手创企业中出现这一状况,就更不能容忍,急于除之而后快。所以,不免在此问题上,与商务另外的领导人高凤池、鲍氏兄弟等人产生摩擦。
商务的其他高层也纷纷就此问题发表看法。王亨统来言:“总务处现分两派,一新一旧。对于旧派从严,对于新派从宽。”张元济答:“新旧之见,就外面一看,却是有的。旧人当然日少,新人当然日多。至于旧人有能力者,仍然重用。如符干臣、陈培初均是。”*《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53、91、50页。张元济有感于清政府亡于亲贵之故,一直主张慎用高级员工子弟。因此也拒绝王亨统之子来公司任职。并借此约时任商务经理王显华谈,调解其与王亨统之间纠葛。张元济谓“用人之道,须令反对我者亦肯为我用,方能得人而用之”。王答“我无此量”。张元济又云“江海之量,何所不容”*《张元济全集·日记》第7卷,第82页。。从上述谈话可看出,张元济用人其实不分新旧、左右、支持或是反对,他反复主张用新人的着眼点,如同王朝开科取士一样,不过是储备人才,只要能为商务有所贡献,甚至是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人,也一概用之。
张元济将自晚清涉足政坛以来所积累的丰富阅历,成功导入商业模式中。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张元济等人通过编书、办报办刊等事功活动加强了与政学商三界不同性质人脉的联系,聘请各有所长的学者加入该馆编译所。张元济与当时“新”、“旧”、“中”、“西”、“激进”抑或“保守”的人物及相关势力都有密切联系,并同时参与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但如果简单地用后出观念,来比附、衡量张元济及与其交往人脉性质,其结果自然会离真相相去甚远。张元济虽标榜自己“喜新厌旧”,但其“喜新”,或是能够为商务印书馆直接创造价值,如编译所多数知识分子的引进;或是能够在不同层面上拓展人脉,如董事会股东的改选和扩大。商务在不断引进新人的同时也必须淘汰产生价值较少的冗员。正是如此,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不断扩充可利用资源、构建各方人脉,积极游走于体制内外、政学商三界之间,加之因缘巧合,通过变通非常之手段,既在政治之中,又在政治之外,获得了兼济天下的高度。
三、“变相之官场”
商务储才之众,流动之大,牵涉人脉之广,在晚清民国政学商界影响深远。茅盾甚至将其称为“变相之官场”,但恰恰因为张元济巧妙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将官场即政坛经验“变相”植入商业运作,才开创出一番“官场”外的新天新地。
庄俞在商务成立35年后回顾商务历史时有云:“故凡教育、工业、商业、文书、技术、事务之人才,在本馆均有献其特长之机会。返顾三十五年来之社会不稳定,事业不繁荣,人才湮没,岂可胜计;而本馆惨淡经营,日图向上,数千同人得长久委身于此项文化事业,各尽其才,共享甘苦,以贡献其服务成绩于社会”,“本馆更与社会上优秀人才随在有密切之情谊,有才高望重,已有建树,而后入本馆负荷其文化事业之使命者,亦有本馆尽力多年,而入社会主持政治、教育、文化、工商各种事业而成为一时俊彦者,此种关联,试一探索,颇饶兴味,稍知本馆情形者类能道之。”*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文集》第5册(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
茅盾则从另外角度观察到“编译所中有好多人月薪百元,但长年既不编,亦不译,只见他每天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或则与人(和他同样的高薪而无所事事者)咬耳朵说话;这些人都是有特别的后台,特殊社会背景,商务老板豢养这些人,是有特殊用心的。”*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前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45、145—146页。“这些内幕情况,使我不胜感慨;我的母亲写了极诚恳的信,请卢表叔不要把我弄到官场去,真料不到这个‘知识之府’的编译所也是个变相的官场。”*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前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45、145—146页。张元济所交结的人脉,不仅有蔡元培、高梦旦、郑贞文、茅盾等学术精英;也有王云五、孙壮等管理好手,甚至还有“特别的后台,特殊社会背景”的人物,例如陈叔通等人。就在茅盾进入商务前后,陈叔通将赴国会,来书请辞。张元济与其交换意见,让陈叔通开完国会再回商务,这段时间就算请假,并告诉他,之前陶葆霖*陶葆霖(1870—1920),字惺存,号景藏,浙江秀水(今嘉兴)县人,清两广总督陶模之子。1902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张元济延揽至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10年,被推举浙江咨议局议员,次年主编《法政杂志》。后北上为资政院议员。武昌起义时,因反对资政院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再度南归入商务印书馆。赴资政院也有领半薪的先例,陈叔通未允。张元济又道:“在京之日,公司亦有事相托,万不必却。叔仍未允。余云,即此可作定局。”*《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53、91、50页。陈叔通1914年离开《北京日报》进商务的时候,月薪两百元,但他本人说当时中华书局开出月薪三百元的高价,但由于张元济的关系而选择了商务*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36页。。在商务,陈叔通这种情况也绝非特例,除了他与陶葆霖之外,伍廷芳的情况也是如此。同年5月2日,当伍廷芳来信请辞商务印书馆董事一职时,商务同人均拟挽留。越明日,张元济亲自造访:“告以公司同人均愿借重,如嫌繁碎,董事会可不常到,有要事当趋前面商。”*《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53、91、50页。张元济之所以会采取这种低姿态对待上述人等,除本身有志趣相投外,诸人背后庞大人脉势力,也是其愿意放低姿态的一大因素。
实际上茅盾也深受“变相的官场”之恵,才能供职商务印书馆。1916年,茅盾北大预科毕业之后,其母陈爱珠托其表叔卢鉴泉找工作,要求不进官场,不进金融界。当时卢鉴泉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而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想承揽财政部公债券方面的业务,所以乐于推荐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也表示可以试办,并明确月薪24元,当时商务许多工人工资只有2元*钟桂松:《茅盾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7页。。商务当时养了大量“高薪而无所事事者”,存在各种复杂原因,既有政治上有所借重,也有金融方面需要支持,还有学界间的互为奥援。
这些如今看似吊诡,彼时并不鲜见的多面向人脉延展,使商务得以应付复杂社会之常情变态。个人与机构也通过人脉延展各取所需,皆大欢喜。所谓丰沛人脉,就张元济执掌下的商务印书馆具体而言,即遍布政商学界高端的亲朋故旧。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人脉关系,厚实之经济基础决定了其良性延展的松紧尺度;反过来,日益壮大丰沛的人脉又足以帮助商务应付世间之常情变态。中华书局在建立之初,发动了一场抢占教科书优势的突袭,但迅速被商务所击退,即反映出这一面向。
就算站在狭义的角度理解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也不仅仅在于依靠中央政府教育长官的青睐,同时在于其与发达地区的教育长官、各种性质的教育团体及有号召力的学界领袖都有密切联系;从广义的角度看,则是张元济与同时交往的政学商三界的实力人物共同主导的结果。这一时期北京政府,虽由分属不同阵营的派系相继执政,且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但由于张元济广结人脉,故多能预流而动,或积极应变以顺形势,创造出商务印书馆自身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张元济从政时间虽极短,但获得了不少政治智慧,并将之运用于企业管理,以至于在员工眼中,商务就是一个“变相的官场”。甚至商务鼓励职员从变相的官场进入正式官场。1917年3月17日,蒋维乔受蔡元培邀请,拟入京赴教育部供职,就此与张元济商量。张认为:“鹤处公私皆不宜,部事却有关系,似不宜却。”*《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72、85、86、87页。高级员工进入教育部,对商务印书馆所产生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其他如前文庄俞所说,由商务“而入社会主持政治、教育、文化、工商各种事业而成为一时俊彦者”不可胜数。
张元济在鼓励员工进入政学商界的同时,自己也与各方人物保持了密切联系。1916年7月24日,他在上海汇中饭店宴请北上新官及议员,赴宴者有范源濂、吴莲伯、殷铸夫等人*《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72、85、86、87页。。次日,“孙文偕其友廖仲恺、胡汉民、张溥泉、朱丁五人来观厂。又,唐少川、温钦甫同来作陪。”*《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72、85、86、87页。黄兴同日也有到厂参观。7月27日,宴请浙江省议员,到者褚慧僧、张霞雷、张申之等8人*《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172、85、86、87页。。由此可知张元济与政界人物来往频繁,交往人等也不以自身好恶为标准,既有与其堪称莫逆的蔡元培、傅增湘,也有与其关系紧张的孙文、胡汉民。他这种以企业发展为目的,兼容并包的人脉延展方式,直接促进了商务的迅速发展。
时人对商务亦学亦商社会身份的高度认同,主要是因为在张元济执掌商务印书馆后,通过编书、办报办刊等文化活动来加强与政学商三界不同性质人脉的联系所致。而此类事功活动得以开展,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商务是个“变相的官场”,得以储备有大量背景复杂的各类人才;同时鼓励员工从商务这个“变相的官场”转入政、学、商界,使人脉得以向政学商三界高端多面延展。商务这种高端人脉的延展方式,又直接受益于张元济有早年亲炙上层政治人物的经历,参与残酷斗争所得之经验。他将获得的政治智慧与经验成功运用于商业模式,通过文化事业一步步将商务推进到同业难以企及的空前高度。
结语
“学而优则仕”使得政学两界在传统意义上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商人身份则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四民之末发展到晚明的“士商异术而同志”*刘广京:《后序:近世制度与商人》,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53页。,再到张元济等士商同术亦同志的变化;从范蠡变陶朱公的传说演绎,发展到清末以降大量政学两界人士加入商界的历史阶段。政学商三界从未如此紧密地开始了相互渗透的态势。张元济等“以政入商”的有识之士,在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内夹缝中求生存,将从政所得之政治智慧与管理手段,及政学两界丰沛人脉导入文化产业,使商务印书馆此类民族资本企业获得奇迹般的扩张成长。
责任编辑:方英
中图分类号:K258;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89-08
作者简介:黄剑(1976-),男,江西大余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历史学博士。
Commercial Business Like Political Affair——Zhang Yuan-ji’s Culture Practice with His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Opinion
HUANG Jian
(School of Marxism,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The Chung Hua Book Company tried to occupy the market of the commercial textbooks through republican textbooks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The leader of the Commercial Press,Zhang Yuan-ji,who was of great political intelligence and abundant experience and was also well known among the political,business and education circles,resolved highly adaptive solutions to the crisis.Imitat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the Commercial Presss based on all kinds of cultural publication no matter the old or the new things,or the things in China or abroad.And the Commercial Presss was able to survive in the turbulent times also by extending its amp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o that it then developed well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Zhang Yuan-ji and maintained its position among political,business and education circles.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ercial Presss had been keeping great benefit and good reputation.
Key words:Zhang Yuan-ji;the Commercial Press;engaging in business based on political career;amp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cultural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