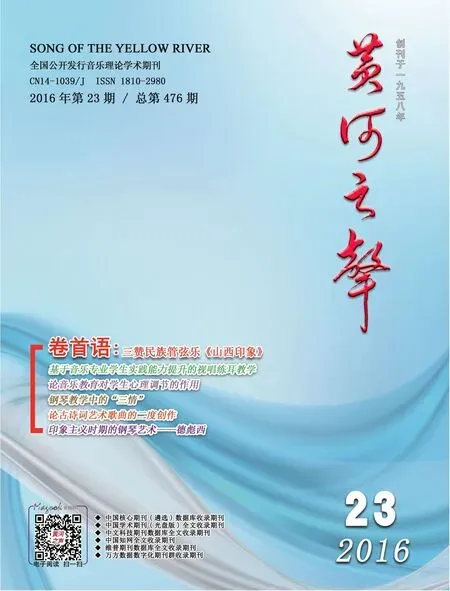鸣角一声当三声
——湘西土家族梯玛牛角号的音乐文化研究
向清全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100101)
鸣角一声当三声
——湘西土家族梯玛牛角号的音乐文化研究
向清全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100101)
牛角号,是用天然水牛角制成的吹奏乐器,早期用于狩猎、战争、祭祀等。它在湘西地区主要“存活”于土家族的祭祀、巫法等活动之中,为土家族梯玛(土家族法师)所“操控”。本文首先从乐器本身和音乐本体层面入手,探讨作为乐器的牛角号,所涉及到的形制、形象、曲调形态特征等方面的问题。其次从文化层面切入,探究作为法器的牛角号,它在仪式中被赋予的特殊功效和所达到的功能效应;以及作为身份象征的牛角号所涉及的一些性别“禁忌”问题。通过对两个层面、三个问题的探讨,试图展现湘西土家族梯玛牛角号的音乐文化全貌。
土家族;梯玛;牛角号;功能;身份象征;禁忌
牛角号是广泛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一件吹奏乐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牛角号除形制不同外,用途也有所不同。“在广西融江流域瑶族的牛角,以天然水牛角制作,瑶语称‘姜’,用于丧乐;贵州彝族牛角,叫‘孩过’,用于喜庆、丧乐;湘黔边界苗族牛角,发音悲壮,用于集会;布依族牛角发音低沉,用作集合信号。此外,还有的地区用铜、锡等金属仿制‘牛角’,用于宗教法事。”①
土家族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的部分地区。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土家族主要聚居地之一,湘西州与贵州省、重庆市、湖北省接壤,是湖南的西北门户,常被称为湖南的“盲肠”地带。较为闭塞的地理环境,为湘西增添了神秘色彩,巫楚文化影响着湘西地区的总体文化氛围,后由于各种原因,周边地区的汉族人口迁入,使得当地的巫楚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土家族人民在该地长期生活,并创造出自己独具特色的音乐文化,包括民歌、说唱、戏曲、器乐等多个类别。“土家族乐器分为吹奏乐和打击乐两种。吹奏乐器有咚咚奎,木叶、土笛、喷呐、牛角、莽号等。牛角,很早用于战争和狩猎,后来成为土老司的主要吹奏乐器。如摆手舞和铜铃舞都要吹牛角。”②而摆手舞和铜铃舞又与土家族的祭祀、巫法活动相关联。
综上可知,在湘西,牛角号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常作为沟通人神的法器,“存活”于土家族祭祀、巫法等活动之中,被仪式的执仪者梯玛(又称土老司,主要指土家族法师)所“操控”。还值得一提的是,苗族和土家族在湘西这片土地上长期共同生活,虽两者族属不同,但两族人民在生活习惯、风俗等方面并非完全“泾渭分明”,常有相互交融之处,这在他们进行的巫法活动中也有所体现。据笔者观察、了解,湘西地区苗族巴代(苗族法师),与土家族的梯玛在装扮、法器的使用上存在相似之处。除了司刀、铜铃外,牛角号则是他们在仪式中必备的法器。因此,需要说明的是,牛角号在湘西并不独属于土家族,而是土家族和苗族所共有。
一、作为乐器的牛角号
土家族梯玛常将牛角号称之为牛角,他们将其视为法器。而“局外人”要将作为乐器或响器的牛角与作为器物的牛角(不用来吹奏的牛角)相互区别开来,便把它称之为牛角号。从称谓上可知,牛角号常常被“局外人”视为一件能发音的吹奏乐器,将其作为一件乐器,就不得不涉及到它的形制、形象、发音、曲调等各方面问题。
牛角号主要用天然水牛角制成,由于直接取材于水牛角,所以形制的大小、长短各不相同,没有一定之规。由于现在水牛角越来越少,因此也出现了铜制的“牛角号”(与牛角号外形相同,只是制材不同)。
牛角号有一吹孔,无指孔。吹奏时发出类似“呜、呜、呜”的声音,声音较为粗狂,但具有穿透力,所以在某些地方或民族常将它作为集合信号。因为形制的不同,牛角号音域的宽窄也有所不同。吹奏牛角时,常用右手握住牛角号靠近吹孔处的位置,吹奏(图三)。
“玉皇角”、“老君角”是湘西土家族梯玛在进行仪式时,经常吹奏的曲调。笔者所采录的,湘西土家族梯玛周光交吹奏的曲调“玉皇角”主要是由两个呈近似大二度的音级构成。考虑到湖南湘西土家族的歌腔多为徵、羽调式,(《中国土家族民歌调查及其研究》中对湖南湘西土家族111首民歌进行了调式统计,得出:“湖南湘西土家族的民歌调式排列为:徵、羽、宫、角、商”③),因此,笔者将此呈近似大二度的音级用“sol”和“la”来表示(见谱例1)。
谱例1:
由谱例1可知,“玉皇角”全曲由“sol”和“la”两个音构成,最后以“la”音结束。吹奏时,“la”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sol”常常以“la”的倚音形式出现,呈现出前短后长的节奏型。值得一提的是,刘嵘老师在《土家族祭祀仪式音乐研究(下)—以家祭仪式“还土王愿”为例》一文中,对“玉皇角”、“老君角”的曲调进行了细致的记谱、分析,并得出:“两个曲调实际上就是一个曲调的变体形式,没有显著的区别,主要围绕一个基本音程进行反复。这个音程比纯四度略微偏窄一点,可以记作sol-do的进行。”④由此可以确定的是,土家族梯玛牛角号的曲调,主要由两个音级构成,但由于吹奏者(梯玛)的不同,两音级间呈现的度数也有所不同,如笔者采录的曲调为近似大二度;刘嵘老师所采录的曲调为“音程比纯四度略微偏窄一点。”
二、作为法器的牛角号
牛角号在梯玛的观念里,不仅仅是一件会发声的乐器或响器,它在梯玛仪式中常被视为一件具有特殊功效的重要法器。所以,对于牛角号在仪式中运用的方式和所产生的功能效应的探讨十分必要。“‘信仰体系’一个由‘信仰’、‘仪式’、‘仪式中的音声’组成的三合一整体,仪式的展现过程,其中一个重要有机因素是仪式展现过程中的各种‘音声’行为(其中包括一般用意的‘音乐’)。作为仪式行为的一部分,‘音声’对仪式的参与者来说是一个增强、延续、扶持和辅助的仪式行为及气氛的重要媒介和手段。我们对‘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从‘音声’切入,置‘音声’于仪式和环境中探寻其在信仰体系中的内涵和意义。”⑤
笔者曾亲历了一次梯玛所主持的“解洗”仪式。“解洗”仪式,是梯玛为一些所谓见到“鬼”以致于神经错乱的人解掉邪气的一种仪式,分三天进行。除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外,主要的仪式程序有:请师—开坛—早朝—踩碗—中朝—晚朝—过红山—上刀梯。梯玛主要在请师前和上到刀梯顶端唱完《送神》歌调后吹奏牛角号,虽然梯玛在请师时也手持牛角号跟随步伐晃动,但并没有进行吹奏。除牛角号外,梯玛仪式中还会出现一些在民俗活动中常用的乐器,如唢呐、锣、鼓、钹等。
唢呐、锣、鼓、钹主要作为梯玛歌唱时的伴奏乐器,在仪式中使用。唢呐伴奏有两种方式:其一,一直跟着曲调的旋律,如一些常用的歌腔,就有唢呐一直伴奏。其二,梯玛在演唱实词时不伴奏,而在实词结束后的拖腔时伴奏。唢呐伴奏时,一般要比演唱音域高一个八度,这与唢呐声音高亢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锣、鼓、钹(有头钹和二钹之分),则是一个组合,四件乐器相互配合,常在梯玛演唱的每一句歌腔间进行伴奏,根据歌腔的不同,锣、鼓、钹在伴奏时的打法和伴奏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据笔者观察,唢呐、锣、鼓、钹在仪式中的使用次数,要比牛角号更为频繁。虽然它们使用较为频繁,但这些“与民俗活动共享”的乐器与作为仪式法器的牛角号相比,功能效应却不相同。“认识仪式音乐功能的两种角度;一种角度是分析仪式音乐可能达到的功能;另一种角度是研究仪式行为者希望音乐达到的功能。这两种不同的认识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两种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前一种是从仪式局外人立场用‘客位观’去分析仪式音乐的功能效应;后一种是从仪式局内人立场用‘主位观’去理解仪式希望者对音乐的功能去向。”⑥唢呐、锣、鼓、钹作为梯玛歌唱时的伴奏乐器,在仪式中出现。梯玛认为,他们在做仪式时念唱的书卷较长,乐器的伴奏主要起到让自己换气休息的作用。笔者曾作为整个仪式的观察者,感受到唢呐、锣、鼓、钹在渲染和烘托歌腔的同时,也使得仪式音声更为“丰满”。因此,不管是在梯玛的观念中,还是笔者的观察感受中,这类“与民俗活动共享”的乐器都不具备一些特殊(沟通神灵)的功能。
但牛角号的使用,在梯玛的眼里却有不一样的功能效应。他们认为,在仪式前只要吹奏牛角号,神灵就会被请到他们做法的地方,来协助或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仪式结束后吹奏牛角号,可以将请来的神仙送回去。牛角号的这种特殊功效,不但体现在梯玛的口述文本当中,也体现在梯玛神歌的唱词当中。如梯玛在《请师》中唱到:“鸣角一声当三声,声声拜请请何神。”以及梯玛在上完刀梯后唱的《送神》(谱例2)。由谱例可见,《送神》为a、b上下句歌腔,反复五次,反复时歌腔变化不大,只是歌词按照“东、南、西、北、中”变化,主要用来拜送“东、南、西、北、中”五方神,后再接类似尾声的“最后一板”(局内人称谓)歌腔结束全曲。“la、do、re”和“la、do、mi”(或“la、do、re、mi”)构成歌腔旋律的基本语汇,“sol”除了作为结束音外,很少作为旋律的骨干音出现。a、b上下句的唱词几乎是一字一音或一字两音,总体唱词节奏较为密集,旋律主要围绕“la、do、re”三个音或“la、do”两个音展开,起伏不大,风格接近“朗诵性”;“最后一板”的歌腔,虽主要围绕“la、do、mi”三个音展开,但常有“sol”的加入,点缀旋律,并出现四度、五度小跳和八度大跳,旋律起伏相对较大,且唱词中的某些字的拖腔较长,旋律风格接近“咏唱性”。从谱例中还可以看到“最后一板”的唱词为:“道国今日现,鸣角走师神,大圣结界大天尊。”需要指出的是,《请师》、《送神》唱词中的“鸣角”二字,皆指的是吹牛角号,这说明牛角号在梯玛信仰体系中具有“请神”和“送神”的功能。
此外,这种特殊功能也体现在梯玛对于牛角号曲调的解读之上,梯玛周光交告诉笔者:“‘玉皇角’代表了24玉皇,主要向师傅报告去哪里做法。”在他用哼唱的方式为笔者解释这句话的时候,笔者发现,上述呈近似大二度的“sol”和“la”可分别代表“玉皇”二字,如(谱例3)。需要说明的是,“玉皇”二字并非该曲调的唱词,只是梯玛对这两个音背后含义的解读,然而从这些解读中不难发现,牛角号的曲调与梯玛信仰之间的关联。
谱例2:
谱例3:
相对而言,牛角号的曲调对于仪式参与者则更像一种“信号”。梯玛在仪式前吹响牛角号,仪式的帮助者或协助者(主要指仪式的帮手)和受仪者(主要指需要解决问题的事主),纷纷就位进入仪式状态,仪式的观看者(主要指事主家附近的一些民众,包括笔者)纷纷赶到仪式现场,这就充分体现了仪式参与者常将其视为仪式开始的“信号”。
综上所述,作为法器的牛角号,被梯玛赋予了沟通神灵的功能,在仪式中虽没有唢呐、锣、鼓、钹这些乐器使用频繁,但是可以说它对于仪式具有更特殊的意义。梯玛在仪式中吹牛角号“请神”、“送神”这种行为,同样也体现了梯玛对自己所信奉神灵的尊重。对于仪式的部分受仪者、观看者而言,牛角号的被吹响,宣告着仪式的开始或者结束,对仪式的起始和终止具有结构性的功能。同样,它也给受仪者、观看者一种心理暗示:接下来在该场域的活动要从世俗转向神圣。这就要求在场的人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怀揣着敬畏之心。可见,不管以何种角度去观察、分析、理解作为仪式中法器的牛角号,它的功能性意义都要远远大于它作为一件乐器的意义。
三、作为身份象征的牛角号及性别“禁忌”
乐器演奏者及他们的身份和性别常常是民族音乐学乐器学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布鲁诺·内特尔在《民族音乐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中,第26个论题“尤八的创造物:乐器”的开篇就谈到:“在民族音乐学中,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乐器是非常重要。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什么人演奏什么乐器,以及那样演奏一味着什么,这些一直是我们研究的内容。”⑦并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继续指出:“乐器对性别研究以及社会部分相互关系的其他研究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⑧可见,民族音乐学乐器学,不仅仅关注乐器的本身,还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视角,如对乐器演奏者的研究,这就涉及到了演奏者身份、性别等各方面的问题。
笔者上述已经提到,牛角号被土家族梯玛所“操控”,在仪式中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器。当然,梯玛与牛角号的关系,远远不止这么简单。梯玛周光交曾告诉笔者:“每一代梯玛死后,牛角号要和梯玛在一起,一并下葬。牛角号也可以传给下一代,有些梯玛使用的牛角号已有几代的历史。”牛角号与梯玛一起下葬或被代代相传,这都体现了牛角号与梯玛的密切关系,它逐渐成为梯玛的身份象征。众所周知,牛角号在古代的战争中,也被士兵所“操控”,号角声常被视为指挥战斗的信号。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卫星、无线电等先进通讯设备在军事当中的使用,现代战争已经不需要牛角号来传输战斗信号,士兵也不再是牛角号的主要“操控”者。但如今在湘西,牛角号仍被作为土家族梯玛的身份象征,笔者认为:
社会在发展,但牛角号作为梯玛的身份象征在湘西并无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牛角号的主要“操控”者仍然是土家族梯玛,而且这种“操控”和“被操控”的关系在不断地被强调和认可。土家族梯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虽受到过打压,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评定政策的出台;民族音乐学的引入对仪式音乐的关注;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湘西土家族梯玛可谓是“求大于供”,他们除了作为一些事主家的求助对象,也常被作为政策的保护对象、学者的研究对象、游客的“猎奇”对象。梯玛穿着法衣、吹着牛角号、唱着神歌进行各种仪式,不管是在事主面前展现“法力”,还是在学者面前展示文化或是在游客面前展演文化,他们在进行对外“表达”的同时也在“强调”着牛角号与梯玛或是与土家族巫法活动之间的关联。当然有时这种强调并非他们刻意去做,只是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进行仪式的。在对外的展现、展示、展演中无意识的不断“强调”,且不断被认可,都使得牛角号仍作为梯玛的身份象征而存在。
综上所述,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乐器“操控”者长期演奏着自己的乐器,使得乐器与“操控”者的身份产生关联,乐器“操控”者身份的变化也影响着乐器对于“操控”者身份的象征意义。
乐器不仅可以作为身份象征而存在,它还具有“性别”。这包括乐器制作者或演奏者赋予它的“性别”,如广西部分地区的铜鼓有“公母”之分;也包括乐器“操控”者的性别要求。因此,对乐器被赋予的“性别”及乐器“操控”者的性别要求的观察与阐释相当必要。湘西牛角号的“操控”者均为男性法师,这与土家族梯玛的传承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湘西土家族梯玛的承袭一般都是祖代相传,并只传本族宗亲的男丁,从不外传。有些梯玛班子在传承时可不受到本族的辈份限制,可父传子也可子传父,可兄传弟也可弟传兄,每一代梯玛都有自己相应的法号,法号辈份的高低由“入门”的先后而定。彭德荣在《梯玛与梯玛歌》一文中提到:“梯玛的传承一般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亲血缘系统家族递续。我们在采访中,凡梯玛,皆说是十代相传、九代师承之类。因此,做一场祭祀活动的梯玛群体,多是由亲血缘系统的父子几兄弟组成而由一位巫法大、辈份高、年龄长的梯玛作掌坛师。”⑨笔者的考察对象梯玛周光交,已是周氏梯玛第十二代传承人,在他梳理自己的传承谱系时,笔者同样发现周氏每一代的梯玛与他均有亲属关系,且都为男性。由此可见,在土家族的历史文化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些关于牛角号“操控”者性别的“明文规定”,但牛角号主要“操控”者在传承时对于性别的要求,造就了牛角号在湘西多为男性吹奏的“约定俗成”。这种隐性的性别“禁忌”,使得牛角号与男性法师关联起来。
四、结语
就乐器本身和音乐本体而言,牛角号在制作中的天然取材,以及曲调多以两个音级构成,使得它在乐器制作和音乐形态上不似某些乐器那样繁琐和复杂,但它所承载的文化却又是相当厚重。牛角号在仪式中被梯玛所“操控”,梯玛给予它音声,赋予它特殊意义,这样使得它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而这些文化内涵、象征意义与牛角号的本身及音乐的本体,共同“勾勒”出牛角号的音乐文化全貌。
注释:
①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10:286.
② 黄柏权.土家族乐器一览.民族艺术,1991,04:155.
③ 徐旸,齐柏平.中国土家族民歌调查及其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35.
④ 刘嵘.土家族祭祀仪式音乐研究(下)--以家祭仪式“还土王愿”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02:19.
⑤ 曹本冶.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11:44.
⑥ 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94.
⑦ [美]布鲁诺•内特尔著,闻涵卿,王辉,刘勇译.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8:328.
⑧ [美]布鲁诺•内特尔著,闻涵卿,王辉,刘勇译.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8:332.
⑨ 彭荣德.梯玛与梯玛歌.鄂西大学学报,1989,01:65.
[1]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2] [美]布鲁诺•内特尔著,闻涵卿,王辉,刘勇译.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8.
[3] 曹本冶.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11.
[4] 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5] 徐旸,齐柏平.中国土家族民歌调查及其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6] 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7] 彭荣德.梯玛与梯玛歌.鄂西大学学报,1989,01.
[8] 黄柏权.土家族乐器一览.民族艺术,1991,04.
[9] 刘嵘.土家族祭祀仪式音乐研究(下)--以家祭仪式“还土王愿”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