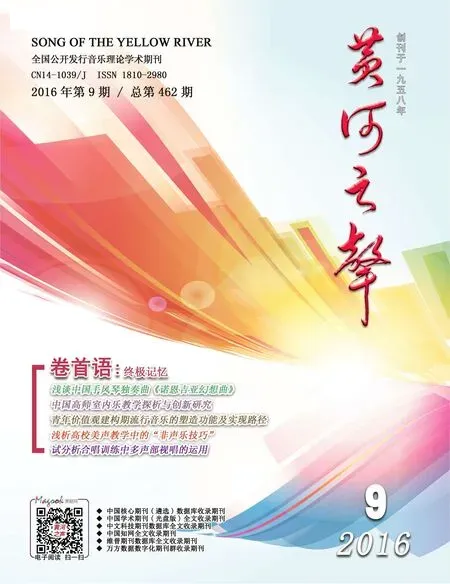上党梆子与民俗文化的探究
梁 奇
(中北大学艺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上党梆子与民俗文化的探究
梁奇
(中北大学艺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上党梆子是山西省的四大梆子(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之一。民间的音乐、曲艺和街头演出都哺育了上党梆子,使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茁壮成长起来。它和民俗文化紧密相连,活跃在民间的各种娱乐场合中,如庙会、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等。本文通过探讨上党梆子与民俗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发展,了解到上党梆子为民俗活动提供了服务,丰富的民俗活动也为上党梆子的生长、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上党梆子的传承必须与民俗文化的发展相呼应。
民间曲艺;上党梆子;民俗文化
上党梆子是山西的四大梆子(上党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蒲州梆子)之一。起源于笔者的家乡泽州县,流行于山西省东南部(古上党郡),于17-18世纪之交形成,俗称为“大戏”。上党梆子高亢激昂、朴素豪放,具有强烈的北方人的性格,其音乐的旋律曲调非常丰富,板式也多种多样。上党梆子在表演时最注重唱和念,它以版腔体为主,同时也注重曲牌体,与此同时还吸收了除梆子外的昆、罗、卷、黄。它零六年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上党梆子来自于人民,又传承于民俗文化,因此笔者针对上党梆子中的民俗文化进行了探究。
一、上党梆子的形成与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什么呢?它就是古时候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和其心理活动,在历史的岁月中,经过时间的锤炼形成了流传在民间对人民有约束性的一种文化[1]。山西省本就是个民俗文化很丰富的地区,晋城地区尤为丰富,应运而生的民间音乐也异彩纷呈,如上党八音会、花灯、高跷、旱船、狮子舞、泽州秧歌、竹马舞、泽州对鼓等等。每逢婚丧嫁娶都能看到上党梆子的演奏,在固定集会上还有大型的游街,包含着高跷、狮子舞和秧歌等各种民俗活动,简直是在看一场盛大的表演,人山人海,不亚于现在的演唱会。上党梆子普遍充斥在晋东南地区的各个村落中,大村仅集会就有两三个,其影响深入人心。它的历史有多久,无从查证。
(一)上党梆子与迎神赛社
在历史上,一些曾为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辞世后人民为其树碑立传,修神堂盖庙宇,供奉为神,子子孙孙,千秋万代传承至今,这些神话被运用在民俗文化中,把其写成书,编成戏剧,用上党梆子进行演绎,历经数千年数百年这种民俗文化在上党地区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每当人们提起神庙祭祀,就会联想到戏曲,二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这种思想使人们觉得宗教活动和戏曲演出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而用于表演这些迎神赛会的基本单位就是“社”,他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社会组织。笔者曾走访多个村落,采访当地的老人,他们见证了每个村镇搭建的属于自村的庙宇和戏台。这些庙宇和戏台专供百姓们祭祀和观看戏曲演出,而这样的迎神赛社的活动每年仅在村里庙会时方可祭祀观赏。在农村,对广大人民而言,庙会就像是过年,艺人们用戏曲、舞蹈等各种各样的表演来欢庆这一盛大的节日,众人可以一起感受艺人们精彩的演出,同时艺人们也在切磋武艺,进行更多地艺术交流。而在上党梆子逐渐没落的当时,庙会成为了上党梆子能够在当时社会继续存活的一条源泉。上党梆子得以流传到现在,就是因为受到上党地区丰富民俗文化的哺育。在农村,每个村子里都有庙宇。在笔者的老家泽州县鲁村村有个玉皇庙,在庙宇里就有戏台子,戏台子面对正殿,与其说是演戏酬神,不如说是人神共乐。在迎神赛社时表演的上党梆子的经典曲目有《秦香莲》、《打龙袍》、《三关排宴》等等。上党梆子的《三关排宴》说的是北宋时期,宋国与辽国交战,辽国大败,于是辽太后率将领到三关议和,佘太君向辽太后索要四子杨延辉,太后为大局着想,答应了佘太君的条件,不料最后却落了个儿女双双殉情的结果。其中佘太君怒斥其子的唱段相当精彩,成为上党梆子的经典唱段之一。
(二)上党梆子与婚丧嫁娶
红白事对所有人来说是人生必办大事,尤其是对农村而言。白事指丧葬,红事自然就是婚嫁。西方大多将婚礼办得庄重圣洁,而中国人图的就是喜庆、热闹。在上党地区民间的婚丧嫁娶是很重要的一项民俗活动,上党梆子跟这项民俗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婚丧嫁娶为上党梆子的发展丰富了内容,应运而生出了一些流传千古的唱腔和唱段。民间艺人刘土成说:“在农村除了神庙祭祀,对人们来说最大的是就是红白喜事,人们可以在这日子里可以尽情释放一下心情,同时也是加深邻里感情的重要日子。”
婚仪上演出的上党梆子折子戏是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内容以反映爱情、生活题材的为主。在晚上闹洞房之前总会唱上一段戏,经典的唱段有《小二黑结婚》,这是著名的文学艺术家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他对上党梆子的发展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即把这本著作演变为梆子戏。
在上党地区,葬礼举行的前夜总会唱上一晚的梆子戏,以此来告慰死者的魂灵。葬礼上的梆子唱段为上党梆子的发展提供了民俗文化环境资源。在葬礼演唱的经典曲目有《秦雪梅吊孝》、《杀妻》等。《杀妻》对于上党地区上党戏迷来说是人人皆知的,剧中王玉莲临死前唱的“窗前梅树是我友”这一脍灸人口的唱段,好多戏迷都学唱和表演这段唱段,其内容非常丰富,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杀妻》还被上党地区的民间艺人改编成了吹奏乐。
(三)上党梆子与节日庆典
民间艺人任香肉曾说:“每年各个村里都有庙会活动,那场面叫一个兴盛,人来人往,锣鼓喧天,邻村的人都会来到这里串亲走访,感受节日的气氛。”如:农历二月十五鲁村会、阳历的八月一号鲁村会、农历四月二十的水陆院庙会等,这些由祭祀活动发展而来的民间集会成了上党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每到集会时节人们常会以村为单位组织游行活动,在参加集会游行的队伍中,有独立的上党梆子表演队,也有以上党梆子为引领和伴奏的民间歌舞艺术表演队(包括高跷、狮子舞、秧歌、竹马舞等民俗活动)。为了配合队伍的表演,在演奏内容曲牌的选择上大都选取欢快、明朗的节奏型,用来烘托气氛。
上党梆子参加的主要节日庆典活动,还有元宵节的灯会、闹社火等。每一年的元宵节都会从正月的农历十四到十六三天时间进行庆演,举办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除此之外上党梆子还参加闹房、暖房、闹寿等小型民俗活动,它就是这样一种“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的音乐形式。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孕育着一方文化。各种各样的民俗文化丰富了上党梆子表演形式和表演内容,使其在更多地场合发挥其艺术魅力。上党梆子成为当时必不可少的文化载体,通过上党梆子各式各样的表演形式和丰富的表演内容,促使当时的人们了解历史,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们津津乐道。
二、上党梆子的现状与民俗文化
在采访民间艺人祁天生时,他边叹气变说道:“在前二十几年前,对上党梆子和民俗文化喜欢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更别提以后了。”其眼神中满是失望和无奈。在80年代时,上党梆子与民俗文化曾落入低谷,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不再把信奉神灵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是更多地依靠科学来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因此,迎神赛社活动虽然还有,但是上党梆子的神圣地位已经减弱;同时,婚丧嫁娶也面临着时代的考验,更多的西式婚礼形式,使通过上党梆子来烘托气氛的现象逐渐减少。葬礼也慢慢现代化,很少用搭棚唱戏来吊念逝者,即使有搭棚,唱的大多数也是流行歌曲和现代小品;节日活动更是受西方节日的冲击,更多地人在过西洋节日,传统的节日很少过,即使这样的节日也只是请上党梆子戏团在村子的戏台上表演,看的人大部分是50到80岁的老人。而且现在集会上游行的项目已经被取消,高跷、秧歌、旱船等这些民俗文化也被取消。
近几年来,我国各种文化积极、自由地在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延续一个剧种的生命。上党梆子自从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和进步。各项奖项不断,佳绩颂传,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对上党梆子的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晋城电视台开播的“我爱上党戏”和“上党戏票友大赛”使广大群众踊跃参与,老年人会聚集在广场和公园,和着乐队作为兴趣每天以戏会友。这样老一辈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传播,新一辈用自己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学习和传承。但是,还未形成一种持久的、系统的传承方式,因此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发展。
三、结语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上党梆子其实质就是与民俗文化融为一体贴近生活,贴近大众,雅俗共赏,不断创新的一种传播精神文明的文化载体。上党梆子是上党地区民俗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上党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因此,传承上党梆子必须与民俗文化的发展相呼应。■
[1]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1-63
[2] 冯双明.上党梆子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J].东方艺术,2011,2(1): 46-49.
[3] 贾明志.民间戏曲在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意义[J].湖南师报,2007,06(1):17-19.
[4] 路畅.民间戏曲的传承于保护问题--基于上党梆子的调查分析[J].文艺研究,2013,01(10):102-109.
[5] 栗守田,马天云.活跃在太行山区的上党梆子、山西剧种概说[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25-28.
[6] 黄涛.传统民间音乐传承的再思考[J].大众文艺,2011,08(2):46-48
[7] 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125-133
[8]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32.
[9]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13.
[10] 李梦华.菏泽枣梆与山西上党梆子的渊源[J].戏剧文学,2012,8: 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