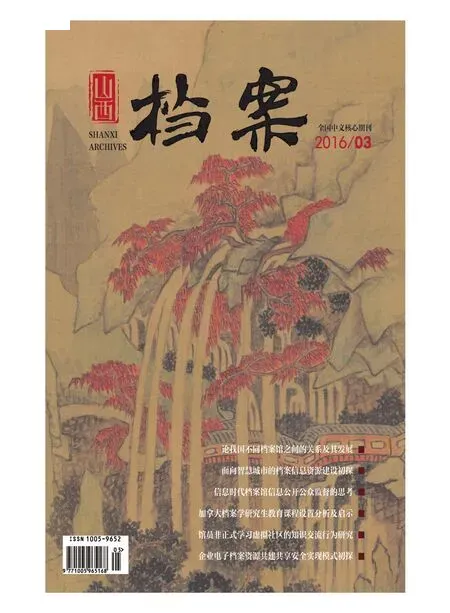论我国不同类型档案馆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
文/黄 超 Huang Chao
论我国不同类型档案馆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
文/黄 超 Huang Chao
摘要:我国不同类型档案馆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其中,国家综合档案馆与专业档案馆本是逻辑并列关系,但实践中专业档案馆的进馆范围在逐渐的让渡给国家综合档案馆;专业档案馆与专门档案馆实质上是部分包含、部分并列的关系;国家综合档案馆与公共档案馆则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实体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则将长期并存、互助发展。
关键词:国家综合档案馆;专业档案馆;专门档案馆;公共档案馆
我国的档案馆通常被划分为国家综合档案馆、专业档案馆、事业档案馆三大类。但在社会实践中,除了上述三种档案馆外,我们还有公共档案馆、专门档案馆、实体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等其他形式或称谓的档案馆。这些档案馆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势必会给档案馆的相关研究带来一定的混乱。因此,理清这些档案馆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有必要了。
一、国家综合档案馆与专业档案馆的关系及其发展
要想理清这二者的关系,先要搞清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国家综合档案馆和专业档案馆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我国档案馆按照进馆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产物。[1]国家综合档案馆是统一保管党和政府档案的管理部门,专业档案馆是国家为专门管理某一方面或某一特殊专业和技术活动中形成的档案而设置的档案馆。[2]
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在进馆范围上的差异,才会有国家综合档案馆和专业档案馆之分。因此,我们还需弄清二者在进馆范围上的关系。理论上,二者的进馆范围应该是逻辑并列或同位类的关系:可以有大小之别但互不包含。这就好比左右手:有惯用手和非惯用手的区别,但可以彼此协作;彼此协作的同时又互相独立,互不依附。综上所述,二者的关系应该是逻辑并列或同位类的关系。
但现实中要更复杂得多。2011年的《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国家综合档案馆和专业档案馆的进馆范围作了相应的规定。《规定》第二条指出国家综合档案馆以接收党和政府机构的档案为主,第五条指出专业档案馆“收集本行政区内某一专门领域或特定载体形态的专门档案或档案副本”。上述条款似乎恰好印证了国家综合档案馆和专业档案馆在进馆范围上逻辑并列的关系。但同时《规定》第三条指出:“涉及民生的专业档案列入综合档案馆收集范围。”这意味着专业档案馆的进馆范围并非涵盖所有的专业档案,而是不涉及民生的专业档案。与理论相比较,现实中专业档案馆的进馆范围是被缩小了的。同时,“民生”又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哪些专业档案涉及民生哪些又不涉及,根据不同的主张其结论可能会大不一样。那么在实际操作中,专业档案馆的进馆范围会有进一步被缩小的可能。正所谓理论引导实践,实践反映理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专业档案馆的进馆范围是在逐渐让渡给国家综合档案馆呢?
让我们拿《规定》比较一下2014年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先,在涉及专业档案馆时,《规定》有一定的篇幅,而《意见》则是一带而过。是因为专业档案馆发展完善无须赘述还是因为被进一步忽略?其次,在对国家综合档案馆进馆范围的表述上,《意见》显得更为笼统和概括:“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要依法集中接收保管本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各类档案。”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都可能产生专业档案,那“各类档案”包括这些专业档案吗?如果包括,又是否和《规定》中一样,涉及民生的专业档案列入综合档案馆收集范围呢?不管原因如何,《意见》中的这种表述无疑会进一步扩大国家综合档案馆的进馆范围,而相应的专业档案馆在进馆范围上就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渡。
因此,笔者相信存在这种趋势:专业档案馆的进馆范围在让渡给国家综合档案馆。而这种趋势使得二者的关系从理论上的逻辑并列关系逐渐转向现实中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因为随着进馆范围持续性的此消彼长,专业档案馆的馆藏资源会不断地被国家综合档案馆“蚕食”,到了一定程度,专业档案馆的馆藏资源将无法再维持其独立性与存在价值。最终专业档案馆将被国家综合档案馆“吸收”,成为其内部机构。
二、专业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的关系及其发展
这二者的关系,一般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第二种观点认为专门档案馆包含了专业档案馆[3];第三种观点认为专业档案馆包含了专门档案馆[4]。要想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要先弄清楚二者的出处。
“专业档案馆”出现于1980年《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和2014年《意见》中,“专门档案馆”出现于1992年《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与布局方案》和2011年《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规定》中。整两个概念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都没有在同一份文件中同时出现过。
《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指出专业档案馆是科学技术事业单位,并且规定:“国务院所属的各专业主管机关,根据需要建立专业档案馆,收集和保管本专业需要长期和永久保存的科技档案”,并且专业档案馆“根据需要可以兼管科技资料工作”。《意见》则写到“各级专业档案馆接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笔者认为这些表明了两点:第一,专业档案馆设立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满足科技档案管理的需要;第二,专业档案馆由专业主管机关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共同领导,归属于“条块结合”体制之中。
《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与布局方案》指出专门档案馆和综合档案馆一样,都是国家档案馆,都是归口中央或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直接管理的文化事业或科学技术事业机构。同时明确表明“专门档案馆指收集和管理某一专门领域或某种特殊载体形态档案的档案馆。”《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规定》则有规定:“各级专门档案馆,收集本行政区内某一专门领域或特定载体形态的专门档案或档案副本。”笔者认为这些也表明了两点:第一,专门档案馆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某些专门领域产生的或拥有特定载体形态的档案;第二,专门档案馆由中央或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领导。
虽然专业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都是科学技术事业单位,但二者的针对对象是一样的吗?专门领域产生的或拥有特定载体形态的档案就一定是科技档案吗?答案明显是否定的。所以认为专门档案馆就是专业档案馆的观点是错误的。
专业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在领导体制上存在差异。专门档案馆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领导,而专业档案馆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专业主管部门共同领导。如果专门档案馆包含专业档案馆,那么则可以推导出在领导体制上专业主管部门是隶属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或至少说要低一个级别,否则专门档案馆包含不了专业档案馆。但这就不符合我国“条块结合”体制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专业主管部门的现实关系。所以认为专门档案馆包含专业档案馆的观点是不对的。而反过来说,就因为专业档案馆比专门档案馆多了一个专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就意味着专业档案馆包含专门档案馆吗?
综上所述,二者所针对的档案,部分相同但并非全都一样;二者在领导体制上相似但不相同。专业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的关系类似一个相交圆,部分包含、部分并列。
三、国家综合档案馆和公共档案馆的关系及其发展
“公共档案馆”这一概念是舶来品,引入时间也不算太久。很多学者都对公共档案馆进行了研究与总结。[5]简而言之,公共档案馆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设立的,以保存公共档案资源为主体,并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档案馆。[6]公共档案馆具有开放与服务大众的“公共”属性。如果按照是否以普通公众为服务对象,是否有提供相应服务的法律保障,是否有满足公共需求的资源保障这三个标准来衡量[7],我国公共档案馆的建设还处于理论阶段。
为何要引入公共档案馆?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其“公共”二字。我国国家综合档案馆在社会实践中长期缺乏“公共性”,其服务对象大多是党政机关而非社会公众。进而造成我国以国家综合档案馆为主的档案馆体系长期缺乏“公共性”。因此我们才特别注重公共档案馆,因为其“公共性”可以弥补我国档案馆体系“公共性”不足的问题。
其实,国家综合档案馆一开始也被赋予了“公共性”,否则就不可能将国家综合档案馆定位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以及科学研究与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因此,笔者认为国家综合档案馆是在社会实践中由于多方因素的影响,其“公共性”被掩盖了,进而才让“公共档案馆”的引入有了“可趁之机”。试想,如果国家综合档案馆在社会实践中展现了其原本被赋予的“公共性”,那么国家综合档案馆实质上不就是公共档案馆吗?因此,公共档案馆的引入实质上是对综合档案馆的一种功能弥补,是针对国家综合档案馆“公共性”缺失的补救措施。
综上所述,“公共档案馆”本就是国家综合档案馆理念的一部分,只是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造成“公共档案馆”被国家综合档案馆遗失了。而随着国家综合档案馆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其“公共性”最终将会恢复,“公共档案馆”将再次成为国家综合档案馆的一部分。
四、实体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的关系及其发展
关于这二者的关系已有文章[8]进行过专门论述。数字档案馆实质上是利用电子网络远程获取档案文件信息的一种方式。[2]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数字档案馆建设中逐渐形成了集成模式和实体模式。[9]两种模式虽有差异,但都体现出数字档案馆是一种依附于实体档案馆的网络平台的事实。实体档案馆是数字档案馆的基础,二者会长期并存并互助发展。
(责任编辑:闻 道)
参考文献:
[1]杨继波.试论我国档案馆类型的划分[J].档案学研究,1988,(1).
[2]冯慧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李绍仁.论专门档案馆[J].安徽大学学报,1998,(2).
[4]邓荣华.浅议专业档案馆的性质、特点及其创新发展[J].北京档案,2010,(9).
[5]周林兴,邓晋芝.2003-2013年我国公共档案馆研究综述[J].档案,2015,(5).
[6]刘国能."以人为本"在档案馆的落实——上海市公共档案馆建设感议[J].新上海档案,2005(1).
[7]赵建功.公共档案馆琐议[J].山西档案,2003,(4).
[8]周庆,杨婵.数字档案馆与实体档案馆的关系研究[J].黑龙江史志,2011,(1).
[9]梁毅.对英美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分析与借鉴[J].档案学研究,2012,(3).
中图分类号:G27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16)03-0037-03
作者简介:
黄 超(1990—),男,四川绵阳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The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Archive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