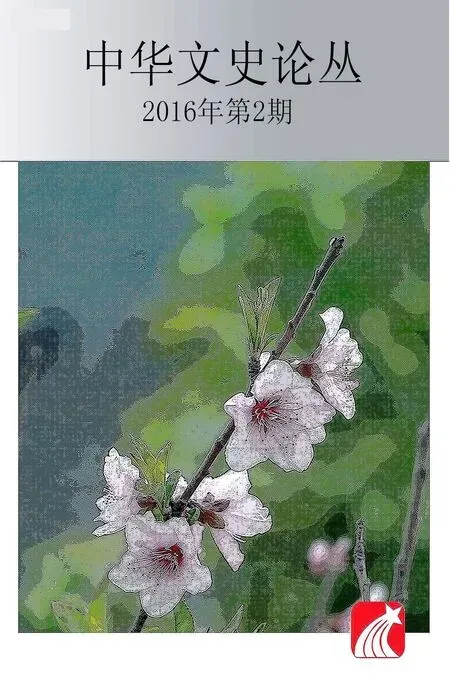道教神仙思想與韓國漢文小說的“仙遇”主題*
王雅靜 孫 遜
道教神仙思想與韓國漢文小說的“仙遇”主題*
王雅靜 孫 遜
中國道教思想的傳入和傳播促進了韓國漢文小說“仙遇”主題的產生,這些小說或狀仙界靈境,或寫仙人生活,或敍仙凡遇合,多側面地展現了道教神仙思想在古代朝鮮的存在狀態。而仙凡遇合中,無論是人神之戀,還是仙人周窮救濟,化解災難,都表現了韓國民衆的世俗願望。差不多與道教的傳入同時,古代朝鮮也較早接受了儒、佛二教的思想影響,並共同融匯於“花郎道”信仰。因此,韓國漢文小說有關“仙遇”題材的作品中,多有釋道身份合一,儒道思想互融的內容情節,呈現出鮮明的本土特色。
關鍵詞:道教神仙思想 韓國漢文小說 仙遇主題 本土特色
道教神仙思想是以神仙崇拜爲核心,旨在通過宣傳神仙的完美居所、長生不死和通天法術來吸引信衆的一種思想信仰,其淵源可追溯至中國古代先民對長生不老和自由生活的嚮往。《莊子·逍遙遊》中就有對神仙形象及能力的大致描述:“神人”居於“藐姑射之山”,“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①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一上,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28。此外如《山海經》之《海外南經》中的“不死民”,《大荒南經》中的“不死之國”,②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96,370。這些都是早期典籍中的神仙雛形。道教發展了這些典籍對於“神仙”養生、修煉、形貌、能力的描寫,認爲世人是可以通過服食等修煉方法而達到長生不老、隨意變化的神仙境界。如葛洪《抱朴子·論仙》說“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難也”,③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卷二《論仙》,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4。即表明神仙可通過服食養生等方法修煉而成。而得道後的“神仙”能夠“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太階。或化爲鳥獸,浮遊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④胡守爲《神仙傳校釋》卷一《彭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6。它的產生對中國古代小說影響深遠,魏晉六朝陶淵明《搜神後記》中的《桃花源記》,劉義慶《幽明録》中的《劉晨、阮肇天台遇仙》,唐傳奇中張鷟的《遊仙窟》,宋代類書《太平廣記》中的《玄怪録·古元子》,明代鄧志謨的《飛劍記》、清代李百川的《綠野仙蹤》等,都可見道教神仙思想的滲透。
道教神仙思想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小說創作,而且也波及包括韓國漢文小說在內的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小說面貌。本文擬就道教神仙思想與韓國漢文小說的“仙遇”主題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 道教思想在韓國的傳播與影響
古代朝鮮作爲中國的鄰邦,早在三國時期就受到道教思想的影響。高句麗是三國中與中國接壤的國家,所以較早引入了道教,記載也最爲明確。榮留王七年(624),唐高祖即“遣道士,送天尊像,來講《道德經》,王與國人聽之”。①一然《三國遺事》卷三《寶藏奉老、普德移庵》,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頁235。642年寶藏王即位後,也欲“並興三教”,其寵相蓋蘇文告王曰:“三教譬如鼎足,闕一不可。今儒釋並興,而道教未盛,非所謂備天下之道術者也。伏請遣使於唐,求道教以訓國人。”寶藏王深以爲然,於是向唐朝“奉表陳請,太宗遣道士叔達等八人,兼賜老子《道德經》。王喜,取僧寺館之”。②金富軾《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寶藏王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頁254,255。寶藏王有感於蓋蘇文的“惟有儒釋,無道教,故國危矣”的勸戒,向唐太宗陳請引入道教,且“以佛寺爲道觀,尊道士,坐儒士之上。道士等行鎮國內有名山川。古平壤城勢,新月城也,道士等咒敕南河龍,加築爲滿月城,因名龍堰城”。③一然《三國遺事》卷三《寶藏奉老、普德移庵》,頁236。道教後來居上,大有超越儒、釋之勢,可見高句麗對道教的尊崇。
道教傳入百濟雖未有直接的史料記載,但在近肖古王時,公元375年,“高句麗國岡王由親來侵,近肖古王遣太子拒之”。太子“大敗之,追奔逐北,至於水穀城之西北”時,莫古解勸誡太子適可而止,說“嘗聞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求多”。①金富軾《三國史記·百濟本紀·近仇首王》,頁295。又義慈王二十年(660),發現一龜背上有文曰:“百濟同月輪,新羅如月新。”巫對義慈王解釋說:“同月輪者滿也,滿則虧。如月新者未滿也,未滿則漸盈。”②金富軾《三國史記·百濟本紀·義慈王》,頁330。無論是莫古解勸誡太子時對道教思想的運用,還是巫師在解讀讖言時所化用的道教話語,都反映了道教思想在百濟的滲入與影響。
新羅位於朝鮮半島東南部,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道教傳入新羅的時間最晚。真平王(?—632)頗好田獵,大臣金後稷借用《道德經》及《尚書》中的話勸誡真平大王說:“今殿下日與狂夫獵士放鷹犬,逐雉兔,奔馳山野,不能自止。《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由是觀之,內則蕩心,外則亡國,不可不省也。”③金富軾《三國史記·金後稷傳》,頁516。可知新羅大臣對儒道等中國典籍的嫻熟運用。還有太宗大王第二子金仁問“幼兒就學,多讀儒家之書,兼涉莊老浮屠之說”,④金富軾《三國史記·金仁問傳》,頁508。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道教在新羅的傳播。
統一新羅時代(668—901),唐遣使赴新羅並贈送道教經典,促進了道教思想在當地的傳播。《三國史記》中記載:“唐玄宗聞聖德王薨,悼惜久之,遣左贊善大夫邢璹,以鴻臚少卿往弔祭。……夏四月,唐使臣邢璹以老子《道德經》等文書獻於王。”⑤金富軾《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孝成王》,頁121。新羅派遣的留學生在中國也學習道教的典籍與儀軌,如唐詩人章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就記録了新羅人金可紀入唐習道、修煉並一度返國的史實:“登唐科第語唐音,望日初生憶故林。鮫室夜眠陰火冷,蜃樓朝泊曉霞深。風高一葉飛魚背,潮淨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合夷樂,蟠桃花裏醉人參。”①《全唐詩》卷五〇六,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5753。《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有其小傳: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爲樂。博學强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退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念思,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卻入終南。②張君房編《雲笈七籤》,濟南,齊魯書社影印,1988年,頁628上。
這些資料反映了金可紀入唐學道的經歷。留唐學生崔致遠的《桂苑筆耕集》卷一五收録了道教齋醮時所使用的青詞,其中《中元齋詞》記“年月朔啓請如科儀。伏以道本强名,固絕琢磨之理;身爲大患,深驚寵辱之機。能審自然而然,必知無可不可。是以雕詞讚美,則乖妙音於混成;矯志求真,則爽奇功於積學。冀標玉籍,在守金科”。③崔致遠撰,党銀平《桂苑筆耕集校注》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98。反映了道教的齋醮儀式和所用的青詞特點。以上記載足以說明道教思想已被新羅的文人廣泛認可並接受。
高麗之時,道教發展最爲興盛。道教的經書總集《道藏》於此時傳進高麗,高麗國王睿宗六年(1110),即采納了曾赴宋習道的李仲若的建議,建立了朝鮮史上第一座道觀福源觀,並向宋徽宗請求派遣道士爲之培訓道徒。宋人徐兢出使高麗,曾對當地道教的情況作了一番描述:
臣聞高麗地濱東海,當與道山仙島相距不遠。其民非不知向慕長生久視之教,第中原前此多事征討,無以清淨無爲之道化之者。唐祚之興,尊事混元始祖。故武德間,高麗遣使,丐請道士至彼,講五千文,開釋玄微。高祖神堯奇之,悉從其請。自是之後,始崇道教,逾於釋典矣。大觀庚寅,天子眷彼遐方,願聞妙道,因遣信使,以羽流二人從行,遴擇通達教法者,以訓導之。王俁篤於信仰,政和中始立福源觀,以奉高真道士十餘人。①徐兢撰,朴慶輝標注《朝鮮文獻選輯·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一八,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37。
不但沿用中國道教的齋醮儀式,以作祈福禳災之用,而且效仿中國道教供奉神仙的做法,建立媽祖廟、八聖堂、城隍廟等道觀,以供奉媽祖、八仙、瘟神等諸神靈。正是由於高麗統治者的大力推崇與提倡以及與宋廷之間的密切交流,道教得以在當地長足發展。
李朝建立後,雖效仿明代施行崇儒抑佛的政策,連帶道教一并抑制,但道教仍在朝鮮傳播和盛行。李朝太宗十七年(1417),明成祖遣使將道教勸人行善的《陰騭文》贈予朝鮮。另外,道教對朝鮮的民間習俗影響至深,如“壬辰倭亂”時期明軍援朝時帶去的關帝信仰和道教的土地神、竈神、宅地神等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道教神等,都被朝鮮民衆接受並加以祭祀。道教的守庚申活動,李朝繼高麗朝之後也一直舉行。而且,李朝一代已有學者開始研究道教及老、莊哲學,如西山大師撰的《道家高擡貴手》,朴世堂寫的《新詮道德經》,韓源震著的《莊子新解》,徐命膺的《道德經指歸》等。②關於道教思想在韓國的傳播,楊昭全《中國——朝鮮·韓國文化交流史》(北京,昆侖出版社,2004年)和白銳譯《韓國哲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多有論及,本文參考了兩書論述的相關內容。
以上可見,道教自唐傳入高句麗、百濟、新羅後,經統一新羅時期留唐學生與統治者的推崇,高麗時期自上而下的崇信,道教思想已融入古代朝鮮的民衆生活和習俗中,並對古代朝鮮的文學、音樂、建築、醫學等諸多方面產生廣泛影響。其中,對漢文小說“仙遇”主題的影響尤其深遠。
二 道教神仙思想在韓國漢文小說中的多樣呈現
在韓國以“仙遇”爲主題的漢文小說創作中,無論是小說外部場景的描寫,還是具體情節的設置,都迎合了道教神仙思想影響下人們對於仙境及仙人生活的嚮往。韓國漢文小說對仙境、仙居、仙聚、仙修、仙術等仙人生活場景的建構,直接脫胎於道教的神仙思想。
《桓真人升仙記》是這樣形容仙境的:“有長年之光景,日月不夜之山川,寶蓋城臺,四時明媚。金壺盛不死之酒,琉璃藏延壽之丹。桃樹花芳,千年一謝;雲英珍結,萬載圓成。”①《道藏》(5),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513下。韓國漢文小說中的仙境描寫正是在道教典籍的基礎上加以渲染和誇飾。如《蔣都令授丹酬德》對仙境的描繪:
忽有翠苑彌亘數里,玉城嵯峨,金闕重疊,瓊樓綺閣,銀窗璧戶,縹緲輝映,於時洞天日曉,紅雲交影,珠貝金碧,玲瓏眩晃,乃歷重門,轉長廊,至一堂,窗欄階礎皆飾以雲母、水晶,琳筵珠帳,銀牀錦屏,瑩澈通明,令人骨冷神清,恍如羽化而登旋。有侍姬數十,花冠月珮,雲裳霞裾,各持銀箏玉簫,鸞笙鳳管,奏雲天霓裳之曲,樽設瓊漿玉醴,盤登火棗水桃,異香濃鬱,祥靄纈暈。又有衆仙驂麟駕鶴,乘雲馭風而迭相往來,洵是清都閬苑,真仙之攸居也。②鄭明基《原本東野彙輯》(上),首爾,寶庫社,1999年,頁513。
再如《陳學究指窟避禍》提到的天上仙宮:“近見有高門口圓如井,入則洞天光明,樓殿羅絡,階砌皆蒼玉,祥風微拂,彩雲如蒸,空中音樂嘹亮,異香撲鼻。庭有一樹,高數丈,開赤花,大如蓮。樹下一女子擣絳紗衣,豔麗無雙。”①鄭明基《原本東野彙輯》(上),頁520。
這裏,小說中的仙境大都由金玉珠寶、雲母水晶裝飾的宮殿,花容月貌、多才多藝的侍女,餘音繞梁的仙樂和芳香馥鬱的佳釀果品等要素組成。住在仙境中的人都雲冠霞衣,馭風駕鶴,法術高明。仙境不僅景色優美,植物異常,有諸如葉大如蓮的樹木、散發異香的瓜果、色澤如玉的酒水等,而且其珍禽異獸也爲人所用,與人和諧共處,體現着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
仙人的生活更是逍遙愜意的,他們住的是高樓,吃的是佳餚,飲的是美酒,不爲瑣事煩心,過着自在的日子,還時常組織聚會。如《攜客登嶽喚神將》中郭思漢少時蒙異人傳授秘書,能夠在自己家中製造出一個仙境,邀來諸仙友:“房中變成一大湖,水色清瀅,如鋪萬頃琉璃,紅荷綠柳,互映交蔭,珍禽遊鱗,翔泳其中。湖上有一彩閣縤戶,雕窗珠簾畫欄,玲瓏奪眼,不可名狀。其夫坐於樓上,方援琴鼓之,與五六羽衣者對坐而杯盤狼藉,又有雲裳霞裾之女,或吹彈或歌舞,其形貌聲音歷歷可辨。”②同上書,頁543—544。郭思漢用道術在房中變幻出一片湖光庭院,與其他仙人共享得道之樂,表現了作者運用道教的理念與思維方式,將對於仙境的想象移至人間,使之具象化。聚會中仙樂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道經裏仙家聚會時仙樂不可或缺一樣,《大洞真經》中就有上清西華紫妃及西王母在仙家的聚會上命各侍女演奏不同樂器的描寫。
正因爲仙人的居住環境和日常生活是如此美好,吸引着人們對於學道成仙的嚮往,因此,修仙就成了人生一件要事。修煉的首要之務是要斷食,所以學習辟穀就成了重要一環。《義兵肩挂匏竿》中抗擊倭寇的義兵領袖郭再佑就是通過辟穀得道成仙的:“或經月不食,惟日食松花小片,就鷲山滄巖爲棲息,地扁以忘憂,永謝煙火,多有異事。一日忽大雷雨震其房舍,公已化,異香滿室,傳仙去。”①鄭明基《原本東野彙輯》(上),頁186。把歷史上真實的抗倭英雄神仙化,表現了對英雄的崇敬和思念。再如《司印僧留客朝真》中的神僧傳授南宮斗“長生之方”時,就問:“第能絕穀否?”“對曰:‘何難之有?’斗本大嚼,未克遽斷哺啜。僧使之漸次減食,昨一簞而今一盂,過幾日,至廢食而不知肚餒。”②同上書,頁488。說明辟穀是可以實現的。
凡人經由適當的方法修煉,就可以得道,得道後的仙人自然就超凡脫俗。《曳杖翁引人成親》中的老人“龜形鶴狀,戌削清高,衣六銖碧紗袍,抱九節綠玉杖,洵是仙風道骨,迥出塵表”。③同上書,頁497。《蔣都令授丹酬德》中的蔣都令是上仙,即使他將自己裝扮成乞丐,蔭官還是能看出他“雖形鵠衣鶉,而狀貌有異”,“氣骨決非汩沒於流丐中者”,④同上書,頁509。說明得道成仙之人形貌的不同尋常。
成仙之人往往身懷絕術,會萬般變化。《授器換金試奇術》中的李士亭就在夫人面前演示了神奇的道術:“即就縫衣檉器中取其衆色錦,小小裁餘,握在手中,微作咒語,俄而散擲空中,蝴蝶紛然,滿室五色燦爛,各隨裁餘本色而成,翩翩飛舞,眩轉難測。”⑤同上書,頁50—51。《陳學究指窟避禍》中的陳學究則爲高玉成在園中變化出一場盛宴,將苦寒蕭瑟的冬日之況變爲暮春時的芳菲之景:“高牆粉壁,垂柳喬松,圍繞院宇。天氣和暢,異鳥成羣,亂弄髣髴,暮春時候。亭中几案皆鑲玉瑪瑙,鋪一水晶屏,瑩澈可鑑,中有花樹搖曳,白禽迴翔,以手撫之,殊無一物。”①鄭明基《原本東野彙輯》(上),頁518。仙術的神奇,可謂令人嘆爲觀止。
小說從道教神仙思想中汲取養分,詳細描繪了仙境的狀貌,以及仙人聚會的場景、修煉的方法、法術的神奇等,迎合了世人對於神仙世界及仙人生活的嚮往。在道教神仙思想的影響下,“仙遇”主題成爲韓國漢文小說中的一個普遍母題。
三 韓國漢文小說的“仙遇”主題及其本土特色
道教的神仙思想爲凡人經由一定的努力得道成仙,或憑藉一定的機遇偶遇仙人提供了理論依據,且道家成仙講究積累功德,《真誥》卷六南極夫人說:“夫學道者,行陰德莫大於施惠解救,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矣。”②《道藏》(20),頁524中—下。道教將積累功德作爲得道成仙的條件,創造出許多與凡人遇合的機會。韓國漢文小說中的“仙遇”主題包含了仙凡之戀、仙人周窮濟急和仙人預知吉凶等幾個方面。
“仙遇”小說中的主人公偶遇仙人大都是因爲深山失路,誤入其中。如《問異形洛江逢圖隱》,獵手日暮失路,闖入洞中。③《青邱野談》(下),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5年,頁300。由於仙人的居所較爲偏僻,溝通仙界與人世的橋樑多是重山疊嶂,主人公要跋山涉水纔能進入。又如《建碑書喻示大義》裏成承旨迷路後,“靡靡逾阡,轉入疊嶂,邃樾之間,四顧無人”。進退維谷時,又“過了幾曲灣,逾一嶺而入”,乘着月光,纔見“峽坼野開,村容櫛比,中有一大屋,魚緝鱗於碧瓦,雁列齒於花礎,髣髴朱門甲第”。①鄭明基《原本東野彙輯》(上),頁523—524。再如《覘天星深峽逢異人》中士人山行失路,“忽見大石中開若石門然,有大川自其中流出,菁葉時時隨流而下”,②《青邱野談》(下),頁290。浮水而入,方得遇仙人。
這類小說的結構因襲《桃花源記》的痕迹相當明顯,都以“誤入—交往—回歸”爲線索。以《麻衣對坐說天運》一文爲例:南師古遊覽白頭山時,“忽見巖石中開,有菑煙乍起,意謂人居,遂至其處,果有數家臨溪依巖,茅廬莆灑,地無纖塵。若非武陵仙源,便是天台隱居也”。果然迎面就碰見一位“衣冠古野,攜笻而出”的老翁,告訴他“此地深邃,不與人世通煙已百有餘年,世無知者”,並向他提供了“非煙火界所噉”的“酒食、山肴、野簌”,後南師古又重返人世。③鄭明基《原本東野彙輯》(上),頁380—381。
仙凡之戀的主人公進入仙境的方式與小說結構也不例外,且多呈現爲女仙與凡男的戀愛模式。如《曳杖翁引人成親》,咸永龜在前往關東的途中,僮奴和馬均暴死,進退維谷之際遇到了一老人,老人指引他來到“玄圃閬苑”處,並言說:“吾有拙女,久墮塵寰,未得良偶,知君有夙世赤繩,故引劉阮到天台耳。”直接化用劉、阮入天台的故事敷衍而來。咸永龜與女仙成婚後,未得袵席之歡,凡遇强就時,女仙就說“仙家夫婦只在神交”,頗類於道教的“偶景術”,變“黃赤之道”爲“人神雙修”。④同上書,頁499,503。故事沿襲魏晉六朝小說的仙凡之戀,將普通男性迎娶富家女以達富貴的願望繪製周詳。
小說中的凡男家境普遍清寒,因此除了希望與女仙愛戀外,還希冀仙人能幫助自己改善生活窘況。如《建碑書喻示大義》一文,成承旨因家庭貧窮,妹妹到了結婚的年齡無法成禮,便帶了一馬一僮,到海西尋找富裕的逋奴,希望得到幫助。抵達海西境時得遇仙人,初次見面,仙人便贈予一千兩銀子,助他脫貧致富。①鄭明基《原本東野彙輯》(上),頁523—529。《授器換金試奇術》中,仙人李士亭“周行四海,窮探幽奇,三入濟州,自爲商賈,以教民赤手贏生業,數年積穀鉅萬,盡散之貧民”,②同上書,頁48。表現了仙人周濟窮人的救世情懷。
小說中的仙人不但樂於救濟窮人,更能預知吉凶,幫人化解災難。如《授器換金試奇術》直言李士亭“未來之事皆預知,世稱以神人”。③同上書,頁48。《陳學究指窟避禍》中的仙人陳學究爲報答高玉成的悉心照料,帶他領略仙府後便令其墜入一窟,安排其觀看三老對弈,直至結束方教其御雲返家。後從其妻處得知,陳學究令其墮入窟穴的遇仙經歷,使之避開了二鬼的捉拿,挽救了他的性命。④同上書,頁515—522。再如《曳杖翁引人成親》中的咸永龜因思念親人離開仙境,女仙提前告知了“壬辰倭亂”的迹象,使其得以舉家遷移至女仙營造的“桃源避秦之所”。⑤同上書,頁506—507。這都反映了人類寄希望於神靈能護佑自己擺脫厄運的願望。
雖然中國魏晉六朝出現的遇仙小說如《桃花源記》、《劉晨、阮肇天台遇仙》等,已成爲一種普遍的模式,在韓國漢文小說中反覆出現。但韓國以“仙遇”爲主題的漢文小說在承襲魏晉六朝的遇仙模式的同時,也展示了同中之異,主要表現爲釋、道身份的合一,以及儒、道思想的互融兩個方面。
在韓國漢文小說中,僧人也可以承擔仙人的角色,擁有仙人的本領。如《教童攀繩摘仙桃》中的田禹治遇見的神仙,即是一位僧人。此僧是“道術者”,不僅能夠預知未來,隨意變化,“遊於六藝之門,演易義而通神”,還能帶領田禹治領略“上仙會讌之所”。①鄭明基《原本東野彙輯》(上),頁537—538。《設白帳避兵獲安》中的洪斯文遨遊山水時見到的僧人,也是“廣通道教”,會飛升之術,洪斯文腳力所不能抵達的地方,他就與之“偕行,從僻路升降”,至斷裂處,僧人“展兩袖據岸懸身而仰臥,令洪躍來,投其懷中”。虜兵將至時,洪斯文賴“僧之神術坐免兵禍”。②同上書,頁580,583。《司印僧留客朝真》中,傳授南宮斗延年益壽之法的也是僧人,此僧在雉裳山修行,是司印僧。他教南宮斗絕穀,傳長生之方,授《皇庭經》及內外丹秘訣,臨行又贈其鎖精之藥,③同上書,頁486—489。全然是一位披着僧衣的道士所爲。
小說將飛升之法、長生之方這些本是道教的內容賦予一名僧人,實現了釋、道身份的合一,其淵緣可以追溯到古代新羅的“花郎道”信仰上。“花郎道”又叫“風流道”,源於新羅真興王。真興王“天性風味,多尚神仙”,因此,“擇人家娘子美豔者,捧爲‘原花’”。“花郎道”選擇美豔女子爲“原花”,與道教對女仙的尊崇如出一轍。推選出的“原花”,負有領導徒衆修行的職責,並導引徒衆以“孝悌忠信”自勉。在道教中,女仙確實承擔教授有仙緣的凡間男子以長生之法,引導他們脫凡飛升的責任。正和“原花”所處的領導地位與引導作用相似,由此可知“花郎道”與道教神仙信仰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花郎道”信仰還將佛教彌勒奉爲“仙花”,稱爲“彌勒仙花”:“有興輪寺僧真慈,每就堂主彌勒像前,發願誓言:‘願我大聖化作花郎,出現於世,我常親近晬容,奉以周旋。’”彌勒被他的誠意所打動,便托夢使,真慈得以在水源寺見到“彌勒仙花”。新羅真智王聽說後即到處遍訪,最終於靈妙寺附近找到“彌勒仙花”,並將其奉爲“國仙”。①一然《三國遺事》卷三《彌勒仙花、未屍郎、真慈師》,頁291—292。這裏,“彌勒仙花”融佛教的彌勒信仰於“花郎道”之中,將釋、道身份合而歸一,反映了古代朝鮮小說“仙遇”主題獨特的一面。
韓國漢文小說的“仙遇”主題,不僅表現爲小說主人公釋、道身份的合一,還表現在內容上儒、道思想的互融。《曳杖翁引人成親》中的老翁,身爲女仙的父親,勸說咸永龜迎娶女仙。女仙如同凡間的女子一樣,依遵父命,與咸永龜結合,這是儒家倫理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再現;女仙不嫌棄咸永龜塵世中的妻子,並願意與之共同擁有一個丈夫,沒有嫉妒,體現了女子對儒家倫理觀念的自覺踐行。②鄭明基《原本東野彙輯》(上),頁499—507。《荷葉留詩贈寳墨》中仙女傾慕李澤堂的才藝,聽到他的朗讀聲後,便下降告以身份,即使被誤解,仍在臨行前贈他一硯一墨,並告知“用此硯墨必文思驟進,擢高第且顯官”,③同上書,頁309—310。將傳統儒家讀書人封妻蔭子、光耀門庭的願望,與道教中女仙來降、引導男子的方式完美結合。因此,其女仙形象也與魏晉六朝遇仙小說迥然有異,魏晉六朝小說中的女仙在兩性關係中往往處於主導地位,不容拒絕。如《弦超附智瓊》,女仙智瓊選擇弦超是因爲天帝的命令,倘若弦超拒絕智瓊,就會招致禍害,“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菑”。④干寶《搜神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7。與之相比,韓國漢文小說中的女仙少了一些淩厲與專橫,多了幾分約束與柔婉氣息,說明古代朝鮮在表現仙凡遇合等道教神仙思想時糅合了儒家的道德倫理。
小說中儒、道思想的融合,其原因也與“花郎道”密不可分。“花郎道”在推選“原花”時,要“聚徒選士,教之以孝悌忠信”,並將此視爲“理國之大要”,①一然《三國遺事》卷三《彌勒仙花、未屍郎、真慈師》,頁291。可見“花郎道”以儒家的“孝悌忠信”爲精神內核,與其日常生活的“遊娛山川”、“相悅以歌樂”的外在形態相結合,體現了儒家精神道義與道家行爲方式的有機融合。
古代朝鮮精神信仰的原型是“花郎道”,所謂“國有玄妙之道,曰風流,設教之源,備詳仙史,實乃包含三教,接化羣生。且如入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魯司寇之旨也。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②金富軾《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真興王》,頁56。由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花郎道”的源頭是道教神仙思想。所謂“設教之源,備述仙史”,實與道教一脈相承,故稱“玄妙之道”,又曰“風流”。但在發展演進過程中,吸納了儒、佛兩教的思想,形成了以“玄妙之道”爲基礎,實乃“包含三教,接化羣生”的“花郎道”信仰。正是由於獨特的“花郎道”信仰,形成了韓國漢文小說“仙遇”主題的本土特色。
綜上所述,道教的神仙思想產生於災難繁多的漢魏六朝,它所宣導的完美居所與長生不死之術,給飽受災難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理想世界。古代朝鮮與中國接壤,戰爭多發,災害頻現,朝鮮民衆自然也希冀有一個理想的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因此,道教神仙思想順理成章地被接受,韓國“仙遇”主題的小說應運而生。此類小說中無論是令人神往的仙境描寫,還是仙人生活的虚構描繪,或是仙凡遇合的浪漫想象,其目的都是爲了尋求亂世解脫,爲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們提供一種精神的寄托和慰藉。
(本文作者王雅靜係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孫遜係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本文係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東亞漢文小說文獻整理與研究”、上海市高峯學科“中國語言文學”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