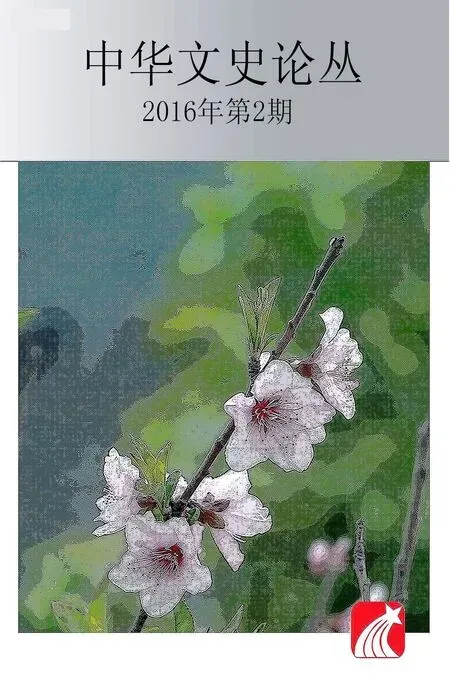士人流動與朝鮮鄉約頒行*
盧鳴東
士人流動與朝鮮鄉約頒行*
盧鳴東
朝鮮王朝在地方上通過監察制度和戶籍制度實行禮儀政策,由於在朝鮮半島上各地的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不同,加上地方官員管治不善和機制本身的模糊,導致未能產生成效。中宗十二年,朝鮮中央政府下令各地頒行《呂氏鄉約》,目的是使各地鄉人熟悉鄉約條文,繼而遵守鄉規,學懂儒家的禮義精神。當時的朝鮮士人在全國各地流動,對於鄉約的頒行和儒家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關鍵詞:留鄉所 五戶一統 士人流動 朝鮮鄉約
一 引 言
文化交流的發生,以至日後所以能夠起到深遠的影響,是文化輸出者和文化接受者的共同努力成果。自古中國與東亞各國在文化交流上,一直以强勢姿態出現,而由於中國處於儒家文化傳播的中心位置,因此,學者也集中研究中國對周邊鄰國所帶來的文化。但是,如果我們過於强調文化輸出者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文化接受者也是主導文化交流的其中一方,這可能會遺留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在歷代掌管朝鮮半島命脈的政權中,朝鮮王朝最能夠接受中國儒家文化,所以產生這種根深柢固的文化交流結果,朝鮮精英階層可謂居功厥偉。
朝鮮時期,從燕京購回國內的大量儒家典籍,在朝鮮的精英階層中得到廣泛流傳,這些由朝鮮王室成員和士人團體所組成的文化接受者,具備解讀儒家典籍的能力,也有經濟條件實踐禮儀制度,因此,中國儒家文化在朝鮮精英階層中的散播相當迅速。典籍是文化的主要載體,它在文化傳播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對於典籍的閱讀、注解和研究固然是文化接受者的首要工作,但在社會基層來說,他們不擅長從經典中解讀儒家文化,甚至不懂閱讀漢語,也沒有足夠條件遵行古禮儀式。所以,中國儒家文化在朝鮮社會基層中的傳播,比起精英階層來說,所要面對的困難更大。雖然,朝鮮王朝期望通過“留鄉所”和“五戶一統”的監察制度宣揚儒家文化,但是,基於戶籍人口和地理環境因素的限制,未能達到預期的成效。
儒家文化在朝鮮社會基層的播遷上,鄉約的作用可謂舉足輕重,而朝鮮士人擔當了重要的角色。文化傳播是一個動態的交流活動,它把文化從一個地方輸出至另一個地方,其中沒有固定路線可供追尋。但由於朝鮮士人是儒家文化的載體,因此,根據他們在地方基層上的流動,可以探索朝鮮鄉約頒行的地方分佈,聯繫起儒家文化傳播的訊息網絡,並刻畫出古禮在朝鮮境內的播遷。本文主要以朝鮮中宗、宣祖時期朝鮮鄉約頒行的情況,對朝鮮士人在京城內外,以及郡縣鄉洞的流動作出考察,分析中國儒家文化如何透過鄉約的形式滲透入朝鮮的社會基層中,並在古禮的傳播上取得一定成效。
二 設置地方監察機制
(一)設置“留鄉所”監察制度
朝鮮全國地方分爲八道,分別爲京畿道、忠清道、慶尚道、全羅道、黃海道、江原道、咸鏡道(咸吉道)和平安道,而各道之下,畫有府、大都護府、牧、都護府、郡、縣等地方行政組織。在地方官職制度上,各道置觀察使(監司)一人,是負責道內一切公務的最高統領。之下按照所屬的行政單位,設有府尹、大都護府使、牧使、都護府使、郡守、縣令、縣監、都事、判官、庶尹、察訪、教授、審藥、訓導、譯學和檢律等官職,這些地方官員可以通稱爲“守令”,分別掌管道內農桑、戶口、學校、軍政、財政、賦役、檢察等行政及司法等工作,而具體的行政實務仿照中央官制,分爲吏、戶、禮、兵、刑、工六房,交由各房幕僚、營吏、通引等鄉吏執行。
李氏王朝於全國實行郡縣制度,是中央集權體制的一種强化和體現。鄭道傳《朝鮮經國典上·州郡條》曰:“京邑,四方之本也。股肱之郡,供賦役,衛王室,京邑之輔也。遠而州郡,星羅碁布,皆出其力,以供公役,出其賦,以供公用,無非王室之藩屏也。”①〔韓〕鄭道傳《三峰集·朝鮮經國典上》,韓國文集叢刊編委會《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5),漢城,學民文化社,2003年,頁420。針對各地郡縣的本土風俗習慣,朝鮮中央政府設置“留鄉所”予以監管。朝鮮君臣認爲“留鄉所即前朝事審官也”,①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録》(10)成宗十五年五月七日,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頁590。它的設置是繼承高麗朝舊制而來。《東國文獻通考》謂高麗王朝於“國初以金傅爲慶州事審官,成宗定制五百丁以上州置四員,三百丁以上州置三員,以下二員,使本州舉望,忠肅王罷”。②〔韓〕洪鳳漢編《東國文獻通考》卷二三五,漢城,明文堂,1981年,頁743。事審官的工作負責“甄別流品”,“均平賦彼”,“表正風俗”,薦舉鄉中有名望的賢士赴京出仕。
朝鮮立國初年,留鄉所已經設置,當時“擇品官正直一二員,爲鄉有司,以正風俗,名曰‘留鄉所’”。③《朝鮮王朝實録》(11)成宗十九年三月二日,頁313。後來因爲世祖十三年(1468)咸鏡道吉州豪族李施愛假留鄉所散播謠言,率族黨囚殺地方守令,後更興兵謀亂,致被世祖革除。自成宗十三年(1482)開始,朝鮮君臣就留鄉所的復立問題展開了長達八年的議論,而在建議重置或否決的雙方爭持不休下,君臣們每次只能作出延後再議的決定。直至成宗二十年,儘管部分大臣的反對聲音依然不絕,朝鮮中央政府最終決定重置留鄉所,並備有官員常制。《東國文獻通考》記載:
國初置郡縣留鄉所,旋罷,尋復。成宗二十年立鄉正,稱座首、別監,推年德高者爲座首,其次爲別監,管一鄉風俗。州府五員、郡四員、縣三員,擇鄉中文學才行具備者爲之。④《東國文獻通考》,頁743。
當時建議復立留鄉所的朝中大臣,每以風俗敗壞,人心澆漓爲理由,上疏成宗允准他們的奏議。例如,《朝鮮王朝實録》於成宗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記曰:“自留鄉所革去以後,鄉風習俗,日就淆惡,漸不可長”;同年二月二日記曰“自留鄉所革去之後,鄉風習俗,日就澆薄,復立爲便”;十二月十六日記曰“請復留鄉所,糾察不正之人,使不得立於鄉曲”;十四年十月四日記曰“今革留鄉所,鄉風不美,正以此耳”;十五年五月七日記曰“請復建留鄉所,糾察鄉風”;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記曰“昔留鄉所不廢時,或有一人以孝順稱,則留鄉所必以孝順薦之;或有一人以惡行稱,則留鄉所亦必以惡行黜之”。①《朝鮮王朝實録》(10),頁292,294,419,529,590;(11),頁33。
設置留鄉所的其中一個重要意義,是檢舉鄉間違背倫常綱紀的事情,糾正地方風俗,避免鄉風薄惡,這是成宗時朝鮮京官大臣及各地儒生對它所寄予的厚望。《周禮·地官·大司徒》記載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②《周禮注疏》卷一〇,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707中,下。朝鮮儒生認爲,留鄉所繼承古制遺意,旨在發揮《周禮》中教化鄉民、匡正風俗的作用。權五福(1467—1498)《醴泉鄉社堂記》曰:
殿下即位之戊申,令所在復立留鄉所,……留鄉所即古黨正之遺意也。鄉有頑嚚自恣,不孝悌,不睦不姻,不任恤者,此堂得以議之。吏有包藏姦慝,憑假城社,侵漁百姓者,此堂得以議之,推《周官》三物之教行。③《東國文獻通考》,頁744。
金馹孫(1464—1498)在《金海會老堂記》曰:
己酉春,朝廷慮鄉俗之不古,特復留鄉所。……即古之鄉大夫“三物八刑”,所以教而糾者,自有其事,其或父而不父,子而不子,兄而不兄,弟而不弟,夫而不夫,婦而不婦,不睦者,不姻者,下訐上者,吏漁民者,皆在所察提撕焉,警覺焉,其甚者告於有司。④同上書。留鄉所屬於地方自治的一種檢舉制度,它通過所內鄉正官員所產生的監管功能,勸戒鄉人遵行儒家孝悌忠信之道,持守禮義廉恥,確保鄉鄰和睦相處,維持鄉間倫常正常化;當鄉人和守令有不合道德的行爲,違反法紀,所內官員就此進行議論,把犯人個案經由朝中京在所,轉送司憲府審理。
自成宗二十年復置留鄉所以後,歷經燕山君(1495—1506在位)、中宗(1506—1544在位)三朝,朝中大臣對它抨擊的輿論,甚囂塵上。原因是留鄉所采用的一種議論檢察制度,過於依賴品官的行政能力和個人操守誠信,而鄉內人物和守令的善惡一以所內品官議論爲依據,裁奪得失,若品官未能得人,便容易造成濫用職權的流弊。《朝鮮王朝實録》於成宗二十一年(1490)七月十七日,工曹判書成健啓曰:“設留鄉所,欲正風俗也,而其爲留鄉所者,非其人,互相毀謗,至於告狀,甚者與守令相抗,作弊於民,反致風俗不美。請罷之。”十一月二十日,司諫權景祐啓曰:“國家設立留鄉所者,欲使糾正鄉風也。今之留鄉品官,不務糾正風俗,徒事立威鄉曲,以濟其私,非徒無益,適足爲害,請革之。”又,特進官成俊啓曰:“留鄉品官,多行不義,一鄉之中,善人常少。”①《朝鮮王朝實録》(11),頁618,667。可見,成宗時品官的素質並不理想。更甚者有魚肉鄉民,大飽私囊,仇視地方官員等狀況出現,因此,留鄉所能否起到美化鄉風的功能,成效存疑。但大臣啓奏留鄉所的弊端,主張革除的倡議,卻因爲成宗以“設立未幾”爲理由,不獲接納。
在留鄉所外,朝鮮中央政府爲了篩選和委任所內品官人選,以及傳達鄉內不法犯案至中央審理,另於京城設置京在所,統領一切事務。成宗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記載:
鄉里之不孝不悌者,留鄉所可以糾之;鄉里之不睦不姻者,留鄉所可以繩之;騁姦謀而愚弄守令者,則可以制之;假官威而侵漁百姓者,則可以懲之。其有關風教大矣!……臣等伏望令京在所擇鄉中之謹厚公正者,以寄留鄉所之任,如有敗壞風俗,侵漁百姓者,移諸京在所,轉報憲府,推劾科罪。①《朝鮮王朝實録》(11)成宗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頁154。
可是,京在所的流弊也在留鄉所重置以後逐步浮現。燕山君六年(1500)九月二十八日,掌令申叔根曰:“各官設留鄉所,京中設京在所,以正風俗。今各官吏到京,則多辦食物,饋京在所人員,少不如意,輒加侵虐。”②《朝鮮王朝實録》(13)燕山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頁428。京在所官員執掌留鄉所官職委任權,就他們所屬籍貫的村內挑選賢達擔任品官職位,頤指進退,有很大影響力。此外,由留鄉所向中央呈報的地方犯案,亦必須經過京在所轉報司憲府,因此,他們操控着鄉民和守令的生殺大權,而地方官吏往往投鼠忌器,避免京在所官員寃枉是非,惡意彈劾,招徠禍患。
鄉在所和京在所在操作上存在不少漏洞,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機制本身欠缺清晰指引,在品評人物的標準上,品官既懸舉儒家德目作爲品評人物的憑據,但所內卻沒有具體規章條文提供鄉民恪守,犯罪之目的、原因以及刑罰輕重也沒有妥善交待,兼且當地鄉人不一定熟諳儒家人倫規範,偶爾觸犯,時所難免。鄉人不教而誅,是由於留鄉所未能同時發揮到地方教化的功能。中宗十二年(1517)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府下令全國八道監司頒布《呂氏鄉約》,宣揚禮義教化,匡正鄉風。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訓導崔淑澄上疏:“姑罷京在、留鄉所。”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殷霖奏議:“以鄉約中都約正、副約正,糾檢鄉風,而罷留鄉、京在等所。”③《朝鮮王朝實録》(15),頁297,369,544。雖然,兩所沒有因此被革除,但它們在鄉中所具有的監察作用,以及所內品官的職權也逐步受到威脅。中宗十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央政府令把《呂氏鄉約》分派給各地留鄉所和京城五部,由此促使朝鮮地方的監察機制發生了內部的根本變化。
(二)設置“五戶一統”戶籍制度
朝鮮王朝重視古禮在基層組織上的傳播,除了設置留鄉所外,成宗即位期間亦重新編定全國戶籍制度,在各地推行“五戶一統”制,通過鄰里互相監察,確保鄉人修身自治,從而美化鄉俗。
漢城府是朝鮮京城的所在地,府外分爲五部,包括東部十二坊,南部十一坊,西部八坊,北部十坊和中部八坊。世宗時期,朝鮮京城五部欲仿效中國“比長”和“里正”的戶籍編制,以五家設置比長一人,作用如各坊內的五家長,統領五家,而百戶則設置里正一人,如各坊的管領掌管百戶;另把京城內各面每三十里增置勸農官一人,分辨每家人數及長幼,避免人口流失。世宗十年(1428)史料記載:
城府啓:“丙午年版籍,迄今乃成。京城五部,戶一萬六千九百二十一,口十萬三千三百二十八,管領四十六,城底十里,戶一千六百一,口六千四十四,管領十五,其休養生聚,可謂盛矣。乞依周、唐之制,五部各坊五家爲比,置長一人;百家爲里,置正一人。城底各面三十家爲里,置勸農一人,每一里皆立標,以辨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凡征役之施舍、祭祀、婚姻、喪紀、農桑之勸懲,每當施令,家至戶諭,以時奉行,使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相保相守,以成禮俗。”命下吏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今之五家長即比長,管領即里正。各坊管領四十六,尙難擇定,若以一萬六千九百二十一戶,每百戶置一里正,加一百二十三人,何以充差?且城底各里,旣有管領,兼掌勸農,不必更設,宜仍其舊。”從之。①《朝鮮王朝實録》(3)世宗十年四月八日,頁128。世宗八年,漢城府對府內人口戶籍曾經進行點算,計算出府內戶籍有16 921戶,人口則有103 328人。按照原來的戶籍編制,漢城府內各坊管領人數總共四十六人,而世宗的建議是把原來的管領人數增加至一百六十九人,即是多增一百二十三人,達到每百戶設置一里正的指標。此外,他亦建議京城府內各面每三十家增置勸農官一人,而按照城內1 601戶計算,新聘的人手便需要五十三人。世宗的目的是藉着戶籍制的重新編定,加强制度本身的嚴密性,使比長、里正和勸農官發揮監察、勸懲的作用,保證居住在京城內外的所有人都能夠遵行禮義教化,沒有遺漏。但是,因漢城府內無法調配大量人手出任管領,兼且新增的勸農官與原來管領的職能又是重疊,最終漢城府收回成命。
在地方戶籍的重新編定上,朝鮮中央政府在全國郡縣以下的面、里地方基層組織內,設置統正、里主和勸農官。《經國大典·戶典·戶籍》記載:“京以外以五戶爲一統,有統主,外則每五統有里正,每一面有勸農官,京則每一坊有管領。”①朝鮮總督府中樞院調查課編《校注大典會通》,漢城,保景文化社,重印1939年版,頁205—206。根據“五戶一統”制規定,郡縣內五家聚衆成“統”,這是最小的地方行政單位,而每統設有統正;統以上有里,規定五統爲一里,設有里正,而由若干里聚衆成的面,則每面設有勸農官,由郡縣官員兼任。因此,“五戶一統”制是通過戶籍之間由下而上的層層監察,由統主告知里正,里正告勸農官,再由地方守令懲處犯法觸禁的鄉人。
成宗元年(1470),《經國大典》正式頒佈全國,而“五戶一統”制也開始在全國施行,但成效一直不如理想。成宗二十一年,特進官尹孝孫在經筵御講中指出:
《大典》內:“戶籍每五家爲一統,置統主,每五統爲一里,置里正,每一面置勸農官。”今外邑戶籍不如法,散亂無統,關係風俗事,無由檢舉,因此不孝不睦者多有之,誠非細故。請依《大典》,申明統主、里正、勸農官之法,統內如有罪犯綱常者,統主告里正,里正告勸農官,轉告守令,以治其罪,則風俗正矣。上顧問左右,知事李崇元對曰:“京中人家櫛比,可行此法,外方則山川相隔,人家遼絶,五家作統似難矣。”孝孫曰:“若人家稀少之地,則雖以三四家爲一統可矣。”①《朝鮮王朝實録》(11)成宗二十一年九月五日,頁647。
“五戶一統”制要求戶籍人口具有持久的穩定性,如果當地戶籍不穩定,人口容易流失,它便無法有效地運作,發揮不到預期的檢舉成效。李崇元分別了“京中人家櫛比”,“外方則山川相隔,人家遼絶”的差異情況,以及尹孝孫建議由五家一統改爲由三、四家一統的新規定,這正好反映出“五戶一統”制在施行上存在的隱憂。
京城戶籍人口稠密,朝鮮君臣憂慮的是管領人手不足,但京城以外人口數量分佈不均,擔心的是人口流失問題。若以平安道爲例,世宗十一年(1429)記載了當地情況:
上曰:“平安道境接上國,而民甚稀少,欲徙下三道之民實之,以備後患者,有年矣。……”右議政孟思誠對曰:“專以平民入居,則怨咨尤甚,若徙犯罪者,則庶無怨懟之弊。……”上曰:“罪囚幾人乎?”兵曹判書崔閏德曰:“犯罪者必不多,且遷徙,人情所難,未可遽行。平安道之民,雖曰‘稀少’,然今自平壤,北至江界,西至義州,城堡相望,鷄犬相聞,但近因年歉,流移他道者頗多。”②《朝鮮王朝實録》(3)世宗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頁195。
八道之中,平安道位處朝鮮西北部,接壤女真族的邊境,因此道人口稀少,人口流動性强。當時世宗曾考慮把下三道人口,包括南部的忠清道、全羅道和慶尚道平民,以及各道罪犯遷往此處,充實戶籍,防備女真犯境。世宗此舉反映朝鮮各道人口分佈不平均的情況,究其原因,在於各地的環境因素存在差異。在世宗十四年(1432)由朝鮮大臣尹淮、申檣編訂的《世宗實録地理志》中,便記録了當時朝鮮八道戶籍和人口的數量。①有關朝鮮八道的郡縣的戶籍人口數量,參考《世宗實録地理志》。朝鮮總督府中樞院編《校訂世宗實録地理志八卷》,《中國邊疆史地叢書·初篇》(10),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出版年份缺。

《世宗實録地理志》中朝鮮八道戶籍人口數量表
根據上表指示,平安道人口數量僅次慶尚道,總體人口超越十萬,這相對於各道人口來說,自然不算是稀少,但當中每戶平均人數僅高出京畿道,而與江原道相同。平安道累年歲收不佳,經濟生產不能提供道內居民足夠的生活需要,致使他們遷移外地謀生,這是造成人口流失的原因。就以平安道沿海和內陸郡縣比較爲例,西面靠近渤海的三和縣享有魚鹽之利,雖然縣內只有411戶,但人口卻高達3 105人之多,每戶平均人數爲7.6,遠高出於平安道中2.6的中位數。相對位於它東北面龍岡縣和江西縣來說,由於兩縣靠近內陸的緣故,每戶平均人數分別只得1.5和1.7,即每戶人口不足兩人,因此,我們推斷兩縣中應該有不少戶口是空置的。再以宣川郡和郭山郡爲例,兩郡西面靠近渤海,具有生產魚鹽的經濟條件,每戶平均人數便分別高達8.4(4 417人/528戶)和8.2(2 481人/ 302戶)。可見,平安道沿海郡縣享有海洋地利優勢,經濟生產力比一般依靠農業生產的內陸郡縣爲高,當遇到歲收不理想的時候,人口也不致於嚴重流失。
除了北道以外,世宗期間,朝鮮中部的京畿道和江原道的平民也有流動的迹象,他們流動的路線主要是自北方遷移到南方。《世宗實録地理志》記載京畿、江原兩道每戶平均人數只得2.4和2.6,可能與這次大規模的遷徙活動有關。世宗十三年,江原道監司指道內平民因農業失收,大規模地離開原居地:
江原道監司啓:“道內人民因去年失農,流移四散,故已令各官置防護所禁之。請令下三道各官,亦置防護所,如有流移者,隨卽論罪還本,其許接者,亦並治罪。”命依所啓,並諭京畿。①《朝鮮王朝實録》(3)世宗十三年三月二日,頁298。
江原道監司上啓中央下令三道官員嚴守邊防,足見下三道是江原道流民遷往的目的地,而中央把政令也傳遞到京畿,只是慎防少數流民遷入此道而已。事實上,根據後來中宗朝記載“京畿道內凶歉太甚,百姓窮乏,絶食之民頗多”,而“逃散者亦多”;②《朝鮮王朝實録》(16)中宗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頁271。而明宗時地方監司深感“道內旱甚”,曾上啓中央“下送香祝幣於京畿道,使之祈雨”。③《朝鮮王朝實録》(19)明宗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頁494。可見,京畿道經常發生旱災,農作收成極不穩定,而經濟條件也不及下三道。顯宗元年(1660),朝鮮全國發生饑荒,前吏曹判書趙絅上疏曰:
見北土饑民,流入畿甸,老幼攀牽,或五六八九爲羣,或十數爲羣,……京畿列邑,倉儲有限,本土之民,菜色亦多,雖盡棄倉實,烏能兼濟北民之急乎?……前年大無,八路同然,而關北爲最,赤地千里,十室九空。①《朝鮮王朝實録》(36)顯宗元年四月一日,頁241—242。
關北是咸吉道的地名別稱。當時朝鮮全國發生飢荒,其中以北方災情最嚴重,迫使大量咸吉道流民湧入京畿境內,但當時京畿道平民也是自顧不下,根本無力接濟自北方來的流民。由此來說,當朝鮮發生農業失守自然災禍時,人口的流動是呈現自北向南的趨勢,這是由於朝鮮北道和中部的經濟生產力偏低之故。
事實上,南方全羅道是朝鮮王朝的主要稅收來源,全國過半數的收入也由此地繳納。純祖十五年(1815),全羅監司金啓溫疏略曰:“國家之財賦經用,太半責之於湖南,而湖南之所以爲湖南者,以其有沿海諸邑也。”②《朝鮮王朝實録》(48)純祖十五年十月十二日,頁83。湖南屬全羅道,當地沿海郡縣西向黃海,南面東海,氣候和暖潮濕,適宜水稻栽培,例如面向東海的長興都護府、順天都護府和樂安郡,《世宗實録地理志》稱其“風氣暖”;③《校訂世宗實録地理志八卷》,頁210,214,218。而西靠黃海的沃溝、扶安、靈光、茂長、務安等諸縣,《世宗實録地理志》皆謂之“厥土肥”,④同上書,頁183,185,193,195,198。足見以上沿海數縣土壤肥沃,天氣和暖。比較北方平安道的地勢來說,正祖十七年(1793)江界府使申大年稱“本府幅圓廣大,素稱閑土最多,而嶺隘險阻,岡麓縈迴,殆不見數十里平原之野。農民恒言,願得平野爲農”。⑤《朝鮮王朝實録》(46)正祖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頁431。江界都護府包括理山、熙川、閭延、慈城、茂昌、虞芮和渭原七郡,按照申大年的說法,此府地勢險隘,不宜農耕,這說明了當地農產不佳的原因。
北方地緣氣候並不理想,加上地緣局勢緊張因素,都爲當地的農業生產帶來很多不利條件,在人口內聚力不足的情況下,當地人口流動漸趨頻密。實際上,中宗時期,朝鮮北道已不能遵行“五戶一統”制。中宗四年(1509)記載:
北道人潛賣人物於城底野人,已爲成風,吾民日漸減少,至爲可慮。前者各鎮城內居人,作爲五統,統有長,每月季點閱,雖闕一名,必罪統長。近來守令,不行此法,故賣人者尤爲恣行。①《朝鮮王朝實録》(14)中宗四年七月二十日,頁347。
人口販賣是北道人口流失的一個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五戶一統”制在北道已經無法繼續實行;之後在宣祖期間,朝鮮與倭人戰爭,全國人民逃難避禍;而顯宗時,朝鮮發生了全國饑荒,流民紛紛離開家園,這些因素都造成了人口戶籍嚴重流失,直接影響了“五戶一統”制的成效。
三 由禮儀化到鄉約教化
朝鮮中央政府在地方上采用的監察制度,不論是留鄉所抑或“五戶一統”制,它們在操作上都存在漏洞。制度本身過於依賴官員任命的得失,而客觀環境的制約也造成了不少阻礙,而且到了中宗時期,它們在施行上亦已出現困難。中宗十二年(1517)六月,慶尚道咸陽儒生金仁範上疏:“遵行《呂氏鄉約》,以變風俗。”②《朝鮮王朝實録》(15)中宗十二年六月三十日,頁284。七月,中宗下令八道監司廣佈《呂氏鄉約》。③同上書,中宗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頁297。此外,朝鮮王朝所謂的《呂氏鄉約》,主要是指朱熹的《增損呂氏鄉約》。這次頒令是朝鮮王朝在地方管治上的一次重要變革,是朝鮮中央政府采取原來的地方檢舉制度,通過留鄉所品官、統正、里正和勸農官監視鄉民,告發判刑,改由各道監司和守令頒行鄉約,使各地鄉人熟悉鄉約條文,遵守鄉規,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學懂儒家的禮義精神。中宗謂:“教化之行,當悠久以待,而亦不可繩之以法也。”①《朝鮮王朝實録》(15)中宗十三年九月十四日。朝鮮地方監察制度轉爲以鄉約形式實行,足見朝鮮王朝要求的是一種根深柢固的儒家文化植根,期望鄉人經過鄉約教化熏陶,守禮以常,持之以恒,徹底美化一地鄉風。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古禮傳播的舞臺上,朝鮮半島由禮儀化到鄉約教化的傳播歷程亦因此進一步呈現。
根據《朝鮮經國典》、《經國大典》和《國朝五禮儀》的記載,②朝鮮王朝編纂過不少國家法典,當中以《經國大典》最具代表性。《經國大典》參考了太祖朝的《朝鮮經國典》,太宗朝的《經濟元六典》和《續六典》,並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條文內容,經過憲宗和成宗兩朝校正後,頒佈全國。此後英祖朝的《續大典》、正祖朝的《大典通編》和高宗朝的《大典會通》都是沿此續寫而成。朝鮮中央政府向社會基層曾頒佈的禮儀制度,包括鄉飲酒禮、鄉射儀和冠、昏、喪、葬等儀式。《國朝五禮儀》是朝鮮王朝第一部的國家禮儀大典,自世宗命羣儒草創,歷經文宗、端宗、世祖、睿宗,直至成宗朝申叔舟(1417—1475)編訂成書。此書記録了鄉飲禮、鄉射禮等具體儀式給各地鄉人遵行,讓他們躬身修行,培養美好的品德。成宗二十一年(1490),尹孝孫指出:
國家行鄉飮、鄉射禮,鄉飮則每十月,鄉射則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行之。此法載《五禮儀》,所以厚風俗也。鄉飮則年高有德行者,鄉射則孝悌忠臣,好禮不亂者,乃得與焉;其與者恐有物議,不敢惰行,不與者皆欲勵行,固是美法。然才德兼備,忠信孝悌者,豈易得哉?有一才一行者,許令與焉,使留鄉所糾舉,非違幸甚。若觀察使盡心糾察,則守令,誰不勉勵乎?上曰:“然。”①《朝鮮王朝實録》(11)成宗二十一年九月五日,頁648。
尹孝孫認爲各道的留鄉所、觀察使和守令必須盡心鼓勵,薦舉有德行的鄉人行禮。此後成宗、中宗兩朝也曾多次申令各地奉行古禮儀式,但大多未能得到地方官員支持,成效不顯。②《朝鮮王朝實録》(9)記載成宗八年八月四日:“況斯禮之行,達於庶民,鄉飮之儀,亦所當講,所在監司守令,其體予意,迨此閑暇,以時舉行,同我大平之樂,以興禮讓之風,豈不美歟?”以此倡導各地行鄉射禮。此後成宗十年、十四年、十六年,先後多次申明。頁485。中宗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謂:“鄉飮酒禮,此大禮,不可廢也。”(14),頁624。此後在十一年、二十一年亦有申明,其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更下書於八道監司曰:“監司居承宣之地,所當敷民彝、敦禮俗,使一道,皆知孝悌之行;長幼之序。……且鄉飮酒之禮,乃尊高年、尙有德,仁孝,敬讓,無暴亂之萌者也。前已令申飭舉行,而旋又廢弛,卿亦詳考禮文以時行,使知尊卑、長幼之不可亂,以化民成俗。”(16),頁521。同時,即使守令悉心推行,但由於鄉人解讀儒家古籍文獻能力淺薄,行禮時根本無法掌握制度儀式中的意義。中宗十二年(1517)三月,執義柳溥指出:“今雖行鄉飲酒之禮,而皆爲糠秕之事,不知其蘊奧也。大抵古禮不能行於今也,且守令不能盡其責,徒爲虚文,故人心、風俗至薄,而至有不孝、不弟者矣。要須行之以實,可也。”③《朝鮮王朝實録》(15)中宗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頁266。如何使古禮行之有實,侍讀官趙光祖直言:
凡禮文之事不可以一日之間盡能之,又不可以難行而止之,亦不可徒爲文具而已。先須培養,使人心風俗醇美,然後鄉有善俗,朝廷須先行禮讓,可也。④同上。
遵行禮儀,則禮義明,這本來是對行禮者的合理要求。可是,這個合理性只適用在朝鮮精英階層上,因爲他們有閱讀漢文的能力,深受儒家文化熏陶,要解讀隱含在儀式中的禮義,並不困難。但對於朝鮮平民來說,儘管他們僥幸地被選中爲行禮者,但在儀式舉行過後,他們也許不明白其中奧義。因此,趙光祖認爲與其徒具形式,命鄉人勉强行禮,倒不如先改善鄉村風俗,這也是中宗命令各道監司頒行鄉約的一個原因。
自中宗頒令以後,《呂氏鄉約》成爲朝鮮各地奉行鄉約的典範。之後兩年,京城發生“己卯士禍”,與鄉約相關的政策一度終止,但對於鄉約在地方上的傳播沒有造成太大影響。在朝鮮鄉約的頒行上,朝鮮士人往往比起朝鮮中央政府的一道政令顯得更爲重要。中宗十三年(1518)九月十四日記載大司憲金淨曰:
臣於外方,見《呂氏鄉約》,大有關於教化。前此兄弟不和者,知悔而和;爲悖逆者,改而順人。皆知而行之,則厚倫成俗之道,豈小補哉?然鄉曲小民不知朝廷之意,而以爲監司一時之令,故皆曰:“今監司遞去,則止之云。”雖守令亦或莫之知也。當申諭此意,使知朝廷軫念之意,可也。上曰:“《呂氏鄉約》,行之則美矣。大抵教化之宣,皆在監司,而朝廷之意,亦豈不知乎?在監司盡力耳。”①《朝鮮王朝實録》(15),頁479。
雖然,中宗認爲頒行鄉約是各道監司的重要職責,他們有責任下令地方守令盡力宣揚。可是,擔當監司職務是有任期限定,當現任監司任期滿後,新官到位,推行鄉約的力度即有可能出現變化,兼且鄉人也認爲頒行鄉約只是個別監司的一時之令,不知道這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上推行的一貫政策。中宗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參贊官金淨曰:“若不立久任之法,則新舊監司,雖同是賢才,其設施相異,而民不蒙實惠矣。近者慶尙道觀察使金安國,盡心於興學校、厲風化等事,一道百廢,庶有俱興之理,民間顒望大治。而間有姦狡之徒,惡其詳明,於其遞期將迫,計箇滿之月,而相語曰‘金三月’。”②同上書,頁420。慶尚道觀察使金安國致力於地方宣揚風教,頒佈政令,風掣雷行,因而引起地方守令不滿,在他離任剩下三個月之前,地方官員嘲弄地稱他爲“金三月”。韓國學者李瑾明說:“鄉約的實施很大程度上依賴着監司或地方上官衙等行政力量。”①〔韓〕李瑾明《朱熹的〈增損呂氏鄉約〉和朝鮮社會》,《中國古代社會與思想文化研究論集》(二),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28。若是如此,鄉約的普遍性無疑受到很大局限。
但儒家文化在朝鮮半島的傳播,並非依賴朝鮮地方政策作爲文化交流的惟一途徑,它存在於社會羣體中,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一種傳播活動,而知識分子是文化的載體,他們所屬和所參與的社會組織和團體,以及個人的活動,都能夠起到文化傳播的交流作用。朝鮮士人有解讀儒家典籍的能力,具備實踐禮儀制度的文化知識,他們遍佈朝鮮全國各地,有條件向各道鄉民頒行《呂氏鄉約》,或據此整理各地的契約,融合朝鮮本土風俗,撰寫適合朝鮮社會發展的鄉約內容。事實上,在中宗下令各道頒行《呂氏鄉約》前,朝鮮士人已撰寫並在地方上頒行洞契和鄉約。根據朝鮮士人在地方上的流動,我們可以勾勒士人頒行鄉約的路線圖,掌握朝鮮各郡縣儒家文化植根的情況。由於朝鮮士人這種自覺性的傳播行爲是不規則地在朝鮮各地發生,兼且朝鮮王朝有長達五百多年歷史,無法按照年月日逐一檢視。因此,本文自中宗頒授《呂氏鄉約》爲時序起點,上下溯尋朝鮮各地頒行鄉約的情況,選取例子,對朝鮮士人的流動作三方面考察:(一)考察朝鮮士人在鄉間的流動;(二)考察士人自京城往返地方的流動;(三)考察告老京官的流動。
(一)考察士人在鄉間的流動
朝鮮士人有不少獲得“徵士”美譽,他們德行並高,誦讀經典,但志不出仕,不曾往京城赴考,對於這類儒生,我們主要考察他們在鄉間活動的情況。鄭介淸(1529—1590),宣祖徵士,日常勤於執禮,在羅州大安洞學舍“隱居教授”期間,曾率領衆弟子舉行鄉飮酒禮。①〔韓〕許穆《困齋先生傳》,鄭介淸《愚得録》,《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40),頁441。《困齋先生行狀》記載:
世居羅州錦城山下大谷洞。……其處鄉也,尊卑長幼之序,問訊慶吊之禮,無不曲當,溫諄款厚之誠,感動人心。其執喪也,式遵《朱文公家禮》,參用《禮記·士喪禮》,柴毁哀戚之容,人皆稱嘆。至於冠昏之禮,時俗專廢,而先生爲其子敏復,始行古禮,士大夫家多慕效之。……請授本州訓導,……間以《家禮》、《儀禮》、《禮記》,莫不各有次第,行之歲餘,孝悌禮義之風,日長於鄉黨之間。②《困齋先生行狀》,《愚得録》,頁438—439。
1582年,鄭介淸已五十四歲,因爲三次推辭不果,首次出任地方訓導,官從九品,掌握州內教育事務,開始教授弟子《呂氏鄉約》。《愚得録·困齋先生傳》記載:“州牧柳夢鼎,因薦其賢,州訓導。先生嚴師弟子之禮,施教一以《小學》、《藍田鄉約》,重冠、婚、喪、祭。”③《困齋先生傳》,《愚得録》,頁441。此外,生於慶尚道大丘府院北里的崔興遠(1705—1786),也因爲早有求道之志,以爲“名利之場,人情易喪”,遂終生“決意廢舉”;1739年,崔興遠於所居地“命書記諺翻《藍田呂氏鄉約》,增損約條”,④《年譜上》,〔韓〕崔興遠《百弗菴先生文集·附録》,《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222),頁231。頒行《夫仁洞洞約》。
羅州屬於朝鮮南部全羅道的一個郡縣,在這裏頒行鄉約除了大安洞外,還有平面南山村。羅世纘(1498—1551)生於羅州居平面南山村,“不待師教,淹貫經史,詞藻燁然”,①《年譜》,〔韓〕羅世纘《松齋遺稿》,《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28),頁107。久居鄉中,不曾赴京當官。中宗十八年(1523),羅世纘二十六歲,根據《呂氏鄉約》修訂鄉中洞契,並據此另立鄉約。1864年,禮官吏曹正郞鄭鍾學稱他“仿《藍田呂氏》遺規,修洞契,立鄉約,流風餘俗,至今猶存”。②同上書,頁108。這說明《呂氏鄉約》對當地風俗起到深遠影響,但同時也反映朝鮮士人撰寫鄉約,除了參照《呂氏鄉約》外,也根據朝鮮本土鄉中洞契而寫成。成汝信(1546—1632)生於慶尚道晉州東面代如村龜洞;1616年,七十一歲,於所居住的琴山洞撰成琴山洞約,“仿《呂氏鄉約》、《退溪洞約》,略加損益而行之”。③〔韓〕安鼎福《浮査先生文集·行狀》,《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230),頁329。《退溪洞約》即是李退溪(1501—1570)於朝鮮明宗十一年(1556)在慶尚道安東郡實施的《禮安鄉約》。由此可見,朝鮮鄉約不完全是仿照《呂氏鄉約》寫成,它是融合韓國傳統洞契和本土鄉約發展而成的。
在朝鮮的其他郡縣中,鄉約不一定受到當地鄉人歡迎。中宗期間,朝鮮中部京畿道曾頒行《呂氏鄉約》,但很快遭到廢止。南漢傑(1482—1529),京畿道南陽縣人,終生不曾赴京科舉;1519年,他被鄉人推舉爲副約正,負責頒行《呂氏鄉約》,但頒行不久,卻無疾而終。《有明朝鮮國南原房君墓碣銘并序》記載“歲己卯,《呂氏鄉約》行,時州士鼎盛,古制肇修,衆推君爲副約正,乃不久而罷,使其化不復見於世”。④〔韓〕盧守慎《穌齋集·有明朝鮮國南原房君墓碣銘并序》,《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35),頁276。同屬京畿道的利川縣,鄉人更嘗試以武力威脅,阻止朝鮮士人頒行《呂氏鄉約》。徐起(1523—1591),京畿道利川縣人,早年離鄉拜師“受《大學》,《中庸》等諸書”,因欲行《呂氏鄉約》而險遭性命之禍。《孤靑居士徐公墓碣銘并序》:“欲行《呂氏鄉約》,倡州之人作行約之所,名曰‘講信堂’,日習儀焉。里中惡少憚惡,潛火其室,公知鄉不可化,又恐有意外之禍,挈妻子入於智異山紅雲洞。”①〔韓〕朴枝華《守庵遺稿·孤靑居士徐公墓碣銘并序》,《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34),頁126。可見,地理位置不同,鄉約施行的力度也存在分別。
(二)考察調遷京官的流動
朝鮮王朝設有京官與地方官的調遷制度,京官出於調任、貶謫或個人意願,從京城派遣到地方當官,特別在後來朝鮮黨爭劇烈的政治環境中,京官被調配到地方的情況相當普遍。個別京官被調任到地方當官後,有宣揚儒家教化的使命感,每在其管轄地方頒行鄉約,使古禮的傳播深入朝鮮地方基層。文益成(1526—1580)生於慶尚道陝川郡泉谷里第,後遷入卜漱玉洞,好行古禮,其子舉行“冠禮亦遵古制”。②《玉洞文先生年譜》,〔韓〕文益成《玉洞集》,《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39),頁264。明宗四年(1549),在京城“中司馬兩試”,取得京官的入仕資格,後來在京中出任承文院正字、司贍寺正、司導寺正等職位,期間也曾調配到地方當洪原縣監、咸鏡道都事等。宣祖九年(1576),文益成從京中司諫院獻納,調配江原道,拜襄陽都護府使,到任後開始了禮義的傳播工作,“招境內子弟,諭以《鄉約》之文,申之以孝悌之方”。③同上書,頁264—265。
京官的個人意願也增加了京城與地方之間的士人流量。柳希春(1513—1577)生於全羅道南海縣,中宗三十八年(1543)出任京中弘文館修撰兼世子侍講院司書。後來爲了照顧家中母親崔夫人,辭去司書職位,中宗體恤其情,把他調配到全羅道茂長縣,當縣監。①〔韓〕李好閔《謚狀》,柳希春《眉巖集》,《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34),頁530。茂長縣是柳希春母親的家鄉,他在該地方施政一年,“設《鄉約》之科條,變俗導化之效,數年洽然,鄉井父老之所傳”,②〔韓〕林《示忠賢祠創立諸執事文》,柳希春《眉巖集》,頁542。致使當地具有禮義風教之美。後來,中宗病逝,他重返京城,幫助仁宗處理經筵職務;明宗即位以後,他出任司諫院正言。又如河受一(1553—1612),生於慶尚道晉州郡水谷里第,“壬辰倭亂”暴發前一年,於京城登第殿試丙科,因戰亂自京南歸尚州,直至1600年,“丁酉倭亂”以後,先後出任京城成均館典籍、昌樂道察訪、靈山縣監。不足一年,又棄官居尚州無量洞。1605年,再出任慶尙道都事,以《呂氏鄉約》作爲洞約的修定原則,頒行《水谷洞約》。③〔韓〕河謙鎮《年譜》,河受一《松亭先生續集·附録》,《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61),頁176。
京官調職在外方,也有些是因爲遭到貶謫。丁克仁(1401—1481),全羅道靈光郡人,1429年,赴京“捷司馬試”,獲得入仕資格。後因多年未能中舉,久居成均館。1437年,率領太學諸生上疏世宗,要求廢除僧侶試而遭到貶謫。南歸妻子家鄉泰仁縣,編成《泰仁鄉約契軸》,這是中宗頒布《呂氏鄉約》前,朝鮮士人撰寫的鄉約。《行狀》記載丁克仁“過泰仁縣西泰居川橋上也,公先已從婦家贅寓縣南之泰山古縣”。④〔韓〕黃胤錫《有明朝鮮國故通政大夫行司諫院正言不憂軒丁公行狀》,丁克仁《不憂軒集》,《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9),頁10。《泰仁鄉約契軸》記載:
人倫有五,朋友居一,並生斯世,號曰“難得”。矧同一鄉,從遊朝夕,以友輔仁,是謂“三益”。作契誠信,猶膠與漆,吉慶必賀,憂患必恤。回路管鮑,輝映簡策,山礪海帶,終始不忒。凡我同盟,取宜矜式,言不盡意,重爲之約。挾富挾貴,背憎面悅,多般巧詐,不恤其德,豈曰誠信,神明其殛,豈曰誠信,罪當黜伏。①〔韓〕丁克仁《不憂軒集·泰仁鄉約契軸》(9),頁19。
丁克仁認爲鄉人相處,益者三友,彼此當以誠信相待,有吉慶之事,必定道賀,這是他立契的重心思想。後來,丁克仁重返京中當官,至七十高壽解官南返全羅道,寫成《洞中鄉飲酒約》。此外,李滋(1466—1498)在出任京城弘文館博士期間,也因爲進諫時觸怒燕山君而遭到貶謫。《行狀》記載李滋“退輒擲帽叫憤,燕山嚴憚,出拜咸昌縣監,則《呂氏鄉約》,手書諭吏民,詩禮誨人不倦,期年而俗變”。②〔韓〕朴祥《訥齋集·博士李公墓碣銘并序》,《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19),頁90。咸昌縣是慶尚道郡縣,李滋當縣監期間,頒佈《呂氏鄉約》,使當地民風起了變化。
(三)考察告老京官的流動
京官告老解官回鄉是朝鮮士人的一個主要流動路線。琴蘭秀(1530—1604)生於慶尚道禮安縣浮羅里第;1590年,六十一歲,辭去京城掌隸院司評職務,解職告老回鄉。1597年“丁酉倭亂”期間,協助慶州收募軍糧,支持明兵;1598年八月,豐臣秀吉病死,戰事結束,當時琴蘭秀六十九歲,“秋講修鄉約於鄉序堂,刋揭先師約條,有《小識》”。③《年譜》,〔韓〕琴蘭秀《惺齋先生文集》,《韓國歷代文集叢書》(1732),漢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頁164。他認爲“鄉立約條與洞中族契,皆是良法美意,而自變亂以後,人心日益淆薄,不可以刑杖笞罰而爲勸懲也,故蘭秀於夫浦洞中,別立《約條》”。④〔韓〕琴蘭秀《惺齋先生文集·洞中約條小識》,《韓國歷代文集叢書》(1732),頁107。因戰亂後民風紊亂,他回鄉後修定《約條》,通行於鄉洞之中。1599年,琴蘭秀以七十歲高齡,欣然赴任奉化縣監,因奉化是他的籍貫。到任後,會集鄉老行鄉約,“一遵李先生所定,而參以呂氏舊規”,翌年八月呈辭解歸。
琴蘭秀當奉化縣令時,所行的是李退溪《禮安鄉約》和《呂氏鄉約》,而在其所居鄉中則另立《洞中約條小識》,以便鄉人履行。《約條》載曰:
順於父母,友於兄弟,和隣睦族,患難相救。
戒勿呈訴爭訟,戒勿割耕占畔,戒勿溝渠曲防,戒勿起伐禁陳山林。
已上上下通行事。
少遇長,必敬而行禮;少壯者,必代長者負戴;儕輩相敬,勿相鬥詰;
男女有別;勿相偷竊。
女人勃豀鬥詰者,奴婢橫逆不順者,洞中僉議治罪,已上下人勸懲事。①〔韓〕琴蘭秀《惺齋先生文集·洞中約條小識》,《韓國歷代文集叢書》(1732),頁107,108,109。
琴蘭秀的《約條》內容包含孝順父母,事兄睦鄰,能救患難,解決爭鬥,持禮相敬各目,這些均與《呂氏鄉約》的條目區別不大。但《約條》中另有勸導鄉人勤於農耕,切勿强占農田,獨霸水源,私伐林木等地方經濟民生各條;至於婆媳爭吵不和,奴婢橫蠻叛逆等諸條,是他另外增益的內容。事實上,朝鮮士人每於鄉約和洞契中加入與當地鄉風相關的項目,涉及的內容多是帶有針對性的。崔興遠在《夫仁洞洞約節目》中便示明:“寺刹近在咫尺,故村中之人與僧人不別,或僧與村家女同處一房,或褰裳衣,混役於田野之中。以至情慾相感,或有潛淫之弊,豈非尤可寒心者耶?此後切禁痛革。”②〔韓〕崔興遠《百弗菴先生文集·夫仁洞洞約節目》,《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180),頁387。防止僧人與鄉中民女有淫穢行爲,若有觸犯,規定上報守令,嚴正懲處。
中、朝地理歷史環境有別,鄉風迥異,朝鮮士人頒行地方鄉約時,每有獨特的措施,內容與《呂氏鄉約》不同。鄭琢(1526—1605),慶尚道安東府人,生於醴泉郡北金堂谷三九洞第。1601年,他自京城解官南返母鄉,到了慶尚道醴泉郡,寓居治東高坪坊,當時他參考《呂氏鄉約》,撰寫成《高坪洞契》。《高坪洞契更定約文序》記載:
四月,《高坪洞契》約文成。先生采《呂氏鄉約》可行於今者,與洞人條定式目,定名分,崇禮讓,勉忠孝,敦信義,恤喪救難。每春秋,洞會有司於座,講讀一遍。至於農商賤隸,譯以方言而曉解之,至今不廢,醴人揭於鄉堂而遵行焉。①〔韓〕錦堂《藥圃先生年譜》,〔韓〕鄭琢《藥圃集》,《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39),頁407。
《高坪洞契》載有禮義式目,每年春、秋兩季由洞中有司讀約一遍,並譯爲方言以供基層平民閱讀。在宣讀鄉約的形式上,《高坪洞契》與《呂氏鄉約》的不同地方,是在鄉約“主事”方面,由“約正”換成“有司”之名;在“聚會”方面,由年中每月聚會改爲春秋聚會各一次;在“罰式”方面,依據自輕至重的懲罰細則,逐由書籍、罰金、衆議、除籍各項,改爲酒罰、除籍兩項,有嚴重違約者,由有司以單子上報官方懲治。②〔韓〕鄭琢《藥圃集·書約條後》,《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39),頁480。
在鄉約的內容上,鄭琢指出謹就《呂氏鄉約》其中“拈出宜於今者十分之一二,務從簡易,便於設施,間或竄入俗例,所謂新舊條合録一紙”,③同上書,頁479。《高坪洞契》中的洞契約條,輯録如下。④同上書,頁479—480。
《洞契約條·勸勉條》:
盡忠事君,至誠事親,忘身殉國,倡義復讐。
貴貴尊尊,老老長長,睦鄰和族,先公後私。
愼納賦稅,勇於爲義,秘發陰私。
右條,契中以此相勸,使之遵奉勿失。
《洞契約條·禁制條》:
妄議朝廷是非,輕論州縣得失,以少淩長,以彊淩弱,親戚不睦,鄰里不和,違犯官令。侮慢長上,不救急難,擅伐禁林,擅樵丘墓,侵占田疆,放牧禾稼,攘奪人財。縱酒喧競,歐鬥駡詈,期會晩到,無緣不參。
右條,約中相戒,使勿犯之。
《呂氏鄉約》包括“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和“患難相恤”四條綱領,①朱熹《增損呂氏鄉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朱子全書》(24),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訂本,頁3595,3597,3601。而《高坪洞契》把這個四項目簡約爲“勸勉條”和“禁制條”兩項,當中還增設了一些細目:第一,“忘身殉國,倡義復讐”。《高坪洞契》寫成於宣祖三十四年(1601),當時朝鮮剛經歷了宣祖二十五年的“壬辰倭亂”和三十年的“丁酉倭亂”,漢城府在是次戰役中曾失守於倭人,宣祖落難義州,舉國震動,亦有不少儒生和僧侶組成義軍,爲國殉難。此細目是配合當時朝鮮國情,勸告鄉人不要忘記家仇國恨。第二,“秘發陰私”。這個細目是爲了發揮社會監察作用,鼓勵鄉人向地方守令檢舉犯過的鄉人,提高鄉約的監控能力。第三,“妄議朝廷是非,輕論州縣得失”。朝鮮中央在地方上設立留鄉所,方便鄉人監視地方官員操守,品評朝政得失,之後被革除,又於成宗二十年(1489)重置。這個細目是用來警惕鄉人,不要胡亂抨擊朝廷和地方官長,防止再次發生留鄉所的流弊。第四,“擅伐禁林”。朝鮮初年頒令松禁,禁止民間濫伐林木。宣祖六年,尹善道在《時弊四條疏》中指出這種情況:“況乎松禁極嚴,旣有山直巡審而察見,又有邊將搜討時擲姦,少有犯者,自水營或重加棍杖,或倍徵贖木。居民心寒膽慄,畏松如虎。”①〔韓〕尹善道《孤山遺稿·時弊四條疏》,《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91),頁322。此細目用來禁止鄉人私自盜取林木資源。
四 結 語
中國古禮文化在朝鮮基層的播遷,是通過國家政策和鄉間組織兩個途徑來實現的。前者所指的是“留鄉所”制度和“五戶一統”制,它是全國性的地方政治措施;後者是指由地方組織所頒行的鄉約,其實行除了依靠地方監司宣揚外,更重要的原動力是來自鄉間流動的士人。不同性質的文化傳播途徑,具有不一樣的文化傳播方式:“留鄉所”是通過品官的議論,搜查犯案,上呈京在所轉報司憲府審理;“五戶一統”是在鄰里之間的互相監察之下,由統正、里正、勸農官層層上告至地方守令,勸戒鄉民嚴守儒家禮義精神。兩者在性質上都是以地方管治爲前提達致文化傳播的實現,但由於它們過於依賴官員的任命和受制於地理環境的制約,在施行上存在不少困難。
鄉約是朝鮮基層組織所能夠承擔和接受的一種文化傳播方式。鄉約記載了各種規約條文和違約者的懲罰,目的是使鄉人在言行舉止上有所顧忌,遵行儒家禮義的要求,進而生活在儒家文化的氛圍中。按照朝鮮本土的實際情況,中國制度儀式和鄉約條目都作過不同程度的調整,但比較來說,制度儀式不能夠太過簡約,否則,禮義便難以在儀式舉行中獲得實現,兼且具備優良品德的鄉人,纔有資格被選爲儀式的參與者,尋常的婦孺百姓根本沒有親身體驗儀式的機會。雖然,鄉約也有儀式的規定,約正在宣讀鄉約時要遵行固定儀式。例如朱熹在“禮俗之交”的綱領下,增設“造請拜揖”、“請召送迎”和“慶弔贈遺”等細目,當中便包含了複雜的儀式內容。不過,由於鄉約主要采用讀約方式舉行,因此,儀式是可以盡量簡化,甚至删除。例如在《高坪洞契》中,所有記載在《呂氏鄉約》中的儀式都被取消,鄉人入約以後,不必爲了應付繁瑣禮節,背負沉重的負擔。金榦(1646—1732)任禮山縣監時,根據“正倫理,敦風俗,救患難,規過失”四條,向各洞頒行洞約約條,並示明“以上洞約四條,要皆删煩取簡,使上下可以通行”爲原則。①〔韓〕金榦《厚齋先生集·割鷄録·頒示各面洞契約條》,《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156),頁59。即使鄉人不會閱讀和聆聽漢文,約正透過韓文翻譯本和韓文誦讀的方法,也能夠讓他們參與鄉約儀式,從而具備掌握解讀鄉約意義的能力。
鄉約的包容面很廣,它能夠承接古韓國本土的傳統文化,顯示朝鮮社會當時具時代意義的課題。朝鮮中宗十二年(1517)向各道頒行《呂氏鄉約》,這是屬於官方性的頒授,但在此以前,韓國本土已存在含有聯誼性質的民間組織,士人在地方上亦有頒行洞契和鄉規。高麗時期,韓國發展了“契”的一種互助共濟的地方團體,直至儒家文化思想的傳入,立契人便把儒家思想納入契的條文之中。例如1437年丁克仁的《泰仁鄉約契軸》沿用了《論語》中“友直、友諒、友多聞”作爲契約的思想精神核心,②《論語注疏》卷一六,十三經注疏本,頁2521下。並合并使用“鄉約”和“契”來統稱。又如《高坪洞契》雖然根據《呂氏鄉約》修改了洞內契約內容,性質與鄉約相同,但它依然沿用“契”這個傳統名稱。在鄉約的細目上,朝鮮士人按照各地鄉間的風俗,以及朝鮮當時歷史環境和政局的發展,增加鄉約內容。例如琴蘭秀的《約條》有關於婆媳、奴婢和鄉間經濟民生的條目;鄭琢的《高坪洞契》增入爲國復仇、告發私隱、禁伐林木等約規。
由朝鮮士人的流動所刻畫出來的文化傳播網絡,是考察中國古禮在朝鮮基層植根中的一個重要方法。對於一些不曾赴京當官和告老解官的士人來說,他們頒行鄉約的主要場所是在其出生郡縣;一些自京城調配到地方當官的士人,每在其管治或出生地的郡縣鄉洞中頒行鄉約,據此,我們必須根據他們的《行狀》、《墓誌》和《年譜》的生平資料記載,勾勒出士人的流動路線,尋找他們頒行鄉約的地方。從本文附録所見,士人頒行鄉約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朝鮮南部,其中屬於全羅道的有羅州、茂長縣、泰仁縣;屬於慶尚道的有晉州郡、大丘府、咸昌縣、禮安縣、醴泉郡和陝川郡,在這些地方舉行的鄉約大多能夠獲得鄉人支持並有深遠的影響。比較朝鮮中部的郡縣來說,京畿道的利川縣和南陽縣雖然也曾頒行鄉約,但最後都無疾而終;而在江原道襄陽府和忠清道的禮山縣所頒行的鄉約,也是由剛調任到位的地方官員下令施行,當地士人未有主動地組織鄉約。而值得注意的是,朝鮮北道沒有一個郡縣頒行鄉約。
朝鮮的地理環境因素包含了經濟生產力和人口流動兩方面,二者關係緊密聯繫,而南北兩道的條件亦因此存在一定差異。北方天氣嚴寒,農業收成偏低,人口容易流失,導致平安道未能爲文化累積提供足夠的條件;南方天氣和暖,農產豐盛,人口凝聚力强,促使全羅道和慶尚道具有禮義植根的基礎。世宗時期,在朝鮮版圖中呈現出自北向南的人口流動趨勢,這個現象反映朝鮮南方的地理環境比北方優勝。同時,全羅道和慶尚道之所以具有禮義播遷的優勢,人才輩出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朝鮮王朝實録》記載中宗十三年(1518),朝鮮中央政府下令遣派觀察使到各道執行《呂氏鄉約》。中宗認爲“教官宜先擇遣,而不可盡擇。擇遣觀察使,則一道守令及爲士者皆化之”。當時執義尹自任便指“慶尙、全羅兩道,人材殷盛,其風俗宜先正之”。①《朝鮮王朝實録》(15)中宗十三年七月十六日,頁463。這說明在朝鮮八道中,慶尙道和全羅道盛產人才,推使朝鮮中央決意把這兩地作爲鄉約頒行的試點。這樣來說,全羅道和慶尚道可以推斷爲朝鮮基層古禮傳播的地理重心所在。
(本文作者係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附表 人物流動與朝鮮鄉約頒行

(續表)
*本文爲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優配研究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HKBU245913,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