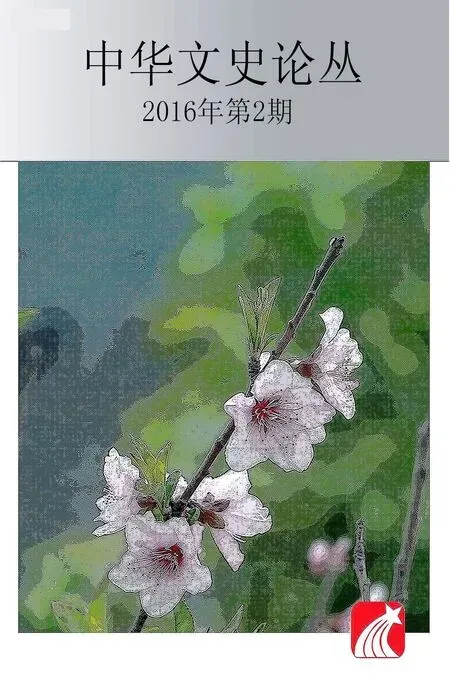從“胡亂”小說看古代朝鮮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
孫 萌
從“胡亂”小說看古代朝鮮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
孫 萌
李氏朝鮮王朝與明王朝維持着密切友好的宗藩關係,尊行共同的儒家華夷觀念,並在華夷框架下對周邊國家及民族進行了相應定位。因此,在明清交替之際乃至清朝建立很長時間之後,儒家華夷觀都深深影響着朝鮮對待明朝、清朝的立場,並在相關的“胡亂”小說中有大量體現。本文梳理不同時期“胡亂”小說的創作特點,由此探尋古代朝鮮社會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過程。
關鍵詞:“胡亂”小說 古代朝鮮 儒家華夷觀
朝鮮自建國以來,尊奉明朝爲正統,國王接受明朝册封,使用大明年號,連國名“朝鮮”亦是太祖李成桂向明朝請封而來。賜予國號,意味着對李成桂政權合法性的認可,也就此將朝鮮王朝的正統性與明朝的正統性連爲一體。因此,在十七世紀上半葉的明清交替之際,朝鮮堅守對明朝的忠誠,由此招致了後金和清朝軍隊的兩次進犯,史稱“丁卯胡亂”和“丙子胡亂”。隨後,朝鮮王朝奉爲正統的朱明王朝覆滅,而一直被視爲“蠻夷”的滿洲鐵騎入主中原,這使得華夷問題被推上了朝鮮思想界乃至政界的風口浪尖。
與此相應的,在很多朝鮮漢文小說中,有關明清易代和華夷分野的內容,或鮮明,或隱晦,或沉痛,或反思,均有所涉及。這些小說有直接反映兩次“胡亂”的,也有反映“胡亂”之後朝鮮各階層對明朝、清朝不同心態的,甚至還有看似與“胡亂”無關,實爲托言興寄、闡發作者華夷之論的。因這些小說的產生都與“胡亂”有關,在本文中,爲便於行文,借用朝鮮歷史上對這兩次戰爭的稱呼,將之統稱爲“胡亂”小說。
隨着時代的變遷,這些“胡亂”小說的創作主題與華夷思想也體現出階段性特點:直接反映“胡亂”始末的小說,重在歌頌“抗清斥和”派人物事迹,倡揚“尊周大義”;明亡之後的小說,則寄托着濃濃“故園之思”、“復國之志”,多以“小華”自任。
一 歌頌抗清殉國,倡揚“尊周大義”
最直接記録丙子胡亂中,朝鮮王朝“斥和派”大臣遵從義理之道,效忠明朝,不肯屈服於清軍之事迹的,是原載於《東野彙輯》卷三節義部的《三士成仁明大義》,①鄭明基編《東野彙輯》卷三,光州,國立全南大學圖書館藏本,頁216—227。講述了朝鮮王朝中“斥和派”三義士殉國的感人事迹,史稱“丙子斥和三學士”。“斥和三學士”的事迹在《李朝實録》中有記載,在正祖敕命編纂的尊周類書《尊周彙編》之《諸臣事實》中被列爲首篇。在小說中,作者將三人的形象塑造得更加鮮活,講述了“丙子之亂”中,朝鮮君臣在兵臨城下之際仍然盡力維護正統,但迫於無奈最終降清,世子爲人質,主戰派大臣慷慨就義的曲折感人經歷。
丙子年(明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三月,後金致書朝鮮,要求“共尊金汗爲帝”,否則便欲加兵。洪翼漢、校理吴達濟、吏曹正郎尹集,都主戰斥和。皇太極稱帝之後,於十二月初九日,率十萬清兵渡鴨綠江,十四日便至畿甸,朝鮮國王率世子百官入南漢山城避難。當此之際,清流斥和派仍堅持抵抗,金尚憲、鄭蘊曰:“軍士盡死,士夫盡死後,乞之未晚也。”但在清兵和主和派的壓力下,國王最終只能決定投降。金尚憲與鄭蘊皆殉節自裁。朝鮮世子自請出城爲質,並將斥和代表人物洪、吴、尹等公“出送虜陣”。洪公至瀋陽,清主朝夕設宴,“皆不受”。清主又以兵威示之,洪公“屹然特立,抗言不屈”,書下斥和之文曰:
大明朝鮮國累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歷可陳: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惟以直截爲風。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爲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況爾國之於朝鮮,新有交鄰之約,而先背之。大明之於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①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八,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年,頁153。
又大駡“清主”爲“天朝反賊”,終於被害。吴、尹二公於赴瀋陽途中寫下訣別詩數首,至瀋陽後,不屈赴難。
《東野彙輯》一書問世於1869年(清同治八年,朝鮮高宗己巳年),作者李源命(1807—1887),字穉明,號鍾山,曾以正使身份出使燕京。《東野彙輯》是他選取《於于野談》和《記聞叢話》中較可考信的一些篇章潤色增補輯録而成,並在每篇結尾加上自己的評論“外史氏曰”。在這篇小說結尾,作者評論道:
三學士之危忠大節,如文信國之柴市就禍。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皆文山之語,而三學士並有之。況以屬國之臣,爲天朝立節,則視文山尤難矣。我東之尊周大義,自斥和諸公而明張之,永有辭於天下萬世,其忠精烈氣,可與日月爭光矣。①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八,頁154—155。
從中可見,時至十九世紀後期,朝鮮文人對明清易代一事的評價依然是以清爲“胡”,以明爲“天朝”,以朝鮮爲大明屬國,朝臣爲大明陪臣,視斥和諸公之死如文天祥之赴難,通過贊頌“三學士之危忠大節”,闡發“我東之尊周大義”。
“丙子胡亂”中的朝鮮名將林慶業,同樣深受朝鮮人民的敬仰與愛戴,他死後甚至被民間神化爲民衆崇拜的偶像。記載他生平經歷的小說《林忠臣傳》,又名《林將軍傳》,有漢、韓兩種文本並行於世,版本較多,簡繁不一。筆者所見漢文本爲嶺南大學本《林將軍傳》與金起東本《林忠臣傳》,②《林將軍傳》,慶山,嶺南大學所藏寫本,每頁10行,每行20—23字,共65頁;《林忠臣傳》,金起東編《古典小說全集》,香港,亞細亞文化社影印,1980年,頁304—351。主要講述了林慶業受命援胡、丙子抗胡和暗通明朝、事敗遇害這幾個階段的故事,着重描寫了林慶業對明朝的友好感情和對“胡國”的鬥爭。文中同樣稱明朝皇帝爲“皇帝”、“天子”,而呼清朝統治者爲“胡王”、“胡皇”,表現了鮮明的尊明反清傾向。
《林忠臣傳》敍事較爲豐富,多細節描寫與傳說內容。書中,“胡王”被塑造成不念明朝恩德的忘恩負義之徒,明朝皇帝曾派遣林慶業援助胡國“擊滅加達”,但胡王自此“意氣日驕,有兼并之心,遂反江南,欲圖朝鮮”,林慶業因而大駡賊黨曰:
汝之主君,乃若禽獸者。南京天子以我爲大將,討滅加達,使安汝國,其恩其德,實難忘之,而反破中國,侵我東方。古今天下,豈有若是不義無道者乎?即欲盡殺汝等,以示大義。①《林忠臣傳》,金起東編《古典小說全集》,頁321—322。
《林將軍傳》與《林忠臣傳》雖在行文上有所差異,但主體情節與創作傾向基本一致,尊明貶清的立場闡發十分明確。如在講到林慶業(此本作林敬業)接受明朝派遣出兵援胡時,小說寫道:“敬業伏而白曰:‘小臣雖仕於偏邦,而仰事大國,犬馬之誠,豈有內外哉?’”②《林將軍傳》,頁10。而在潛通明朝事敗被虜之後,林慶業大駡“胡皇”曰:“彼如狗胡皇聽我言,汝何叛天子邪?厥罪無雙,而何乃雜言亂聒邪?”③《林將軍傳》,頁41—42。
小說中雖有一些虚構成分,但總體來說真實反映了林慶業的一生軌迹以及“丙子胡亂”的歷史事件。其中,仁祖避難於南漢山城、世子爲質,以及林慶業被迫出征明朝卻私下與明朝互通等大關節處均屬史實,真實地反映了明清交替之際朝鮮君臣尊明反清的心態以及被迫臣服於清廷的憤懣之情。
“丙子斥和三學士”和林慶業,因爲其抗清的英勇忠義,成爲朝鮮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還有柳夢寅的《於于野談》,④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八,頁335—428。雖刊行於“丁卯胡亂”尚未發生之時,⑤林明德《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八《本卷簡介》中曰其“在作者柳夢寅生前之西元一六二一年即已刊行”,頁7。但其中貫穿的“尊明貶清”的立場一以貫之。其中第一則便是萬曆年間朝鮮金應河將軍的一篇小傳,着重描述了金將軍在朝鮮協助明朝軍隊進攻後金的戰役中英勇死戰的壯烈事迹。
金將軍雖爲武將,卻深明義理,不附權貴,不畏生死。“秋,建州胡奴兒哈赤犯順。天朝徵我國兵,將軍以駐防將仍授宣州郡守”。臨行前,將軍對軍官吴憲說夢見自己“爲賊所斫”,已決意“多殺賊,不浪死”,於是佩戴了兩隻弓和百支箭,諸將“以爲怯”。“己未三月三日,天兵三萬,至虜地深河部落,全軍敗沒。我軍左右營亦相繼敗衄”。喬遊擊看到金將軍以步兵戰鐵騎的英勇情狀,也爲之嘆服。未幾敵軍打破我軍,“將軍下馬,獨倚柳樹下,射必洞札,賊皆應弦而倒,身被重鎧,矢集如蝟,猶不動。矢既盡,用長劍,所擊殺又無數。劍柄折,三易劍擊之”,最終壯烈戰死。後來聽被胡人俘虜又逃回來的人說,胡人都說:“柳樹下一將軍,雄勇無雙,朝鮮若更有此輩數人,不可敵也。”又聽說胡人打掃戰場時,時日已久,“尸皆爛”,“惟柳下一尸,顏色如生,右手握刀不可解,即將軍也”。①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八,頁355—356。
十六世紀末建州女真部在東北崛起,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與明朝對抗。朝鮮曾與明朝三次聯合出兵攻打建州,成爲掣肘後金南下攻明的重大威脅。這則小傳塑造了一個德行高潔、英勇義烈的將軍形象,用主要篇幅贊頌描寫金將軍在協助明朝攻打建州的戰役中勇冠三軍、死戰到底的忠勇事迹,實際上就是贊頌了朝鮮對明朝的忠誠。文中稱女真爲“建州胡”、“賊”,也體現了朝鮮一直以來鄙視女真爲“胡虜”的文化心態與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以上所列之小說,內容、風格、作者、時代均各不相同,但卻有一個突出的共同點:在這些小說中,都秉持鮮明的“尊明反清”立場,倡揚“尊周攘夷”的春秋大義。小說以文學的角度見證了朝鮮舉國在“義”、“利”之間所做出的抉擇。在這場戰爭中,對儒家春秋大義的堅守和華夷秩序的維護甚至一度超越了國家的現實利益。因其背後所包含的華夷問題,“胡亂”對朝鮮社會的影響較之戰爭本身更加巨大與深遠。戰爭災難加深了朝鮮人民對清朝的仇恨與反感,也就此奠定了此後幾百年間朝鮮對清朝表面臣服內心敵視的基本心態。
二 “思明情結”在明亡之後小說中的反覆流露
丙子戰敗之後,朝鮮向清朝稱臣納貢,成爲清朝屬國,派世子入清爲質,並斷絕與明朝的關係。但即使如此,朝鮮仍然潛通南明,並收留善待了大量明朝遺民。明亡之後,朝鮮雖也藩屬於清,但與對明朝的誠心事大相比,更多的還是迫於無奈的屈服。此種心態在思想界表現爲對儒家春秋大義、華夷正統等問題的熱烈探討。這一時期,有“海東朱子”之稱的大儒宋時烈,大談“尊周”,甚至倡議“北伐”。思明祭祀活動也長盛不衰,民間與朝廷都將之當作對明王朝“大恩”的報答,終其一朝未曾停息。①關於朝鮮朝思明問題,孫衛國教授親赴韓國實地考察,記録了大量實證材料,參看其專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99—225。朝鮮的漢文小說,也隨之開始頻繁地流露濃重的“思明情結”。
在十九世紀初期的短篇小說集《青邱野談》中,有這樣一篇講述漂海歷險故事的作品《赴南省張生漂大洋》:
濟州人張漢喆與友人金生及舟子二十四人登船航海赴京。途中遇到風浪,漂流到海島之上,等待路過船隻救援。不久,倭人的船隻路過,可是他們不但沒有搭救衆人,反而將衆人隨身物品劫掠一空而去。又過了幾日,衆人幸運地遇上了明亡後流落安南的明遺民的商船。張生與他們以筆談相問答交流,得知彼此身份後,明遺民搭救並熱情款待了他們。不料,在得知張生等均爲耽羅(濟州島古稱)人後,安南人因爲耽羅王曾殺死安南太子一事,想要殺掉張生等人報仇。在林遵等明人的大力調解之下,安南人放過了張生一行,但不再允許張生乘船。經歷了重重波折,最終張生到了都城,後幾年登科,官至高城郡守。①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八,頁100—107。另,《青邱野談》一般認爲作於十九世紀初期到中葉之間,小說中提到香俜島上有個朝鮮村,“村中有金太坤者,自言渠四世祖朝鮮人,作俘於清,流入南京,隨明人避世於此”,由此推斷,所記載的故事發生時間大致在兩次“胡亂”後百餘年,即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
該篇小說講述的雖是一個漂海歷險故事,與戰亂之事似不相關,但其中卻借張生與流落安南國的明遺民的對話,將彼時東人的思明情結抒發得淋漓盡致,感人至深:
有一人鬚髮不剪,頭戴圓巾,以書問曰:“爾是何國人?”對以朝鮮人,漂海到此,乞蒙慈悲,得返故國。著巾者復問曰:“爾國有中土人流落者,可數以對否?”張生疑是大明遺民,書答曰:“皇朝遺民,果多逃入我國者,我國莫不厚遇,録用其子孫,不可殫記。未知相公在何國?”答:“俺大明人,遷居安南國久矣。今因販豆,將往日本,爾欲還本國,須隨俺抵日本。”張生涕泣而書曰:“吾屬亦是皇明赤子也。壬辰,倭寇陷我朝鮮,魚肉我,塗炭我,其能拯我於水火之中,措我於袵席之上者,豈非皇明再造之恩乎!噫嘻痛矣!甲申三月崩天之變,尚何言哉!以我東忠臣義士之心,孰欲戴一天而生也!然而父母之亡,孝子不能殉從者,以其天命不同,存亡有異也。今於萬里萍水,幸逢相公,非徒四海之兄弟,同是一家之臣子。”①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八,頁102。
文中提到東人對明朝的情感主要有兩點:一是對壬辰(明萬曆二十年,1592)之亂中明朝出兵援救一事的感戴,視之爲“拯我於水火之中,措我於袵席之上”的“再造之恩”;二是一直以來對明朝與朝鮮之間君臣關係的深刻認同,以“皇明赤子”、“一家之臣子”、“忠臣義士”自居且自豪。這兩點其實也正指向了東人“尊明貶清”之由來的兩大層面:歷史原因與儒學思想淵源。可謂對朝鮮士子思明文化心態的極佳寫照。
同時,小說還從側面體現了東亞各國在朝鮮人心目中的不同形象:倭人在見到衆人求救時不僅不假以援手,反而將其劫掠一空,這當是朝鮮人在倭寇的常年侵犯之下形成的惡劣印象;而明遺民則給予了他們熱情幫助,並在安南人欲殺害衆人時從中保護,使衆人得以脫險。這顯然體現了明人對朝鮮人的友好態度以及朝鮮人對明朝的感懷孺慕。
作於十八世紀中葉的夢遊録小說《奈城志》,講述主人公無名子夜宿奈城,夢見明朝建文帝與朝鮮端宗及其所轄名臣聚會,借聚會衆人之議論,表達作者自己的政見與史論。文中多處表達出此種“海外遺臣”的“思明情結”:
無名子趨而進曰:“小臣生晚偏邦,雖未睹漢官之威儀,服事天朝,久蒙再造之聖恩,縱切衆星北拱之誠,奈此泥馬南渡之世,十五夜明月,不禁銀沉珠絕之淚,忍聽胡笳落梅之聲,曾作荒詩以寫臣志云:‘神州一統入滄桑,欲把三軍出鳳凰。萬曆皇恩嗟未報,寧陵志事實難忘。風泉此日懷周室,荆棘何時起漢光。願得貂裘身上著,驅馳遼薊禦邊霜。’”
皇帝(建文帝)再三興嘆曰:“卿不獨東藩之義士,亦皇朝之遺臣矣。其第二聯之意何謂也?”對曰:“往在壬辰,島夷寇我,舉國駭蕩。實蒙神皇之至仁,出師東征,再造藩邦。凡在血氣之倫者,鏤骨銘心之感爲如何哉!不幸時運所迫,至於丙子虜變,乃有所不忍言者。惟我孝宗大王憤發大有爲之志,與同德先正臣宋時烈幄對荆南,密贊北征之謨猷。志事未半,弓劍遂遺,此東土君臣之所以秪今忍痛含寃者也。”皇帝若曰:“大哉朝鮮,禮義之邦也!”①張孝玄等編校《校勘本韓國漢文小說·夢遊録》,首爾,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2007年,頁565。
假托元朝至正末年,實指明末清初的《金華寺夢遊録》,虚構了一個山東遊士成生(“名虚字子誕”)在遊覽金陵錦山金華寺時入夢,夢見中國歷史上從秦至明的著名君臣聚會一堂的故事。《金華寺夢遊録》采取的也是“入夢—夢中—夢醒”這一結構範式,主要通過夢中人物聚會上的語言行爲表達作者的某些觀點。
作爲一篇小說,《金華寺夢遊録》的文學成就或許並不高,無論從構思、人物描寫、情節設計上來看都無甚過人之處,其中借歷史人物之口發出的大量評論也多是舊論,並無太多特別見解。但正是這樣一篇文章,據金興圭、崔溶澈等所編《韓國漢文小說目録》記載,現存有抄本、合抄本二十餘種,還有刊本一種,可見其流傳之廣泛。這不能不讓我們推測,或許正是因爲這篇小說中抒發出的觀點,符合了當時特定歷史階段許多朝鮮士人的某種情感傾向,故不脛而走,有多種抄本、刊本傳世。
實際上,《金華寺夢遊録》雖沒有如前面幾篇小說一樣涉及明清交替之際的歷史事件,而是在評判中國歷史上諸君臣的功過。但不難看出,小說假托元末至正年間,實指明末。在這篇小說中,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著名君王基本都有出現,而又以漢、唐、宋、明的四位開國之君在文中出現最早,地位也最高。這實際上體現了作者所秉承的正是儒家正統觀,即只有漢族建立的統一政權纔是正統王朝。這其中又以漢皇與明皇爲白手建功,得天下最爲正大,是最完美的正統王朝。小說借劉邦之口說道:
尺劍布衣屈起豐沛,無一民一土,而幸賴羣臣之忠烈,終成大業,辛苦涉險,誰有如寡人之甚者乎?唐皇一戰而定關中,宋皇一夜取天下,然明皇之功業,猶勝於吾三人矣!①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三,頁23。
相比於同是白手起家的漢皇劉邦,明皇又因爲“受天明命,殲厥大凶,撥亂反正”而被推崇備至。小說通過對明皇的反覆稱頌,體現出對明朝正統地位的深刻認同與思念。
最後,作者在結尾處設計了一個元太祖率“諸蠻夷”來犯,被始皇、武帝“大破之”的情節,這顯然是對清軍的影射,也寄托了希望明朝能夠像中國歷史上兵威最盛之時的秦皇漢武一樣,驅逐蠻夷,復明正統的理想。
三 朝鮮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
朝鮮王朝建國之後,在思想領域內,一改高麗時期儒佛共存的狀況,展開了浩大的“排佛崇儒”運動,尊奉儒學爲思想界惟一統治理論。經過漫長的時代更迭,至明清交替之際,朝鮮儒學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作爲儒家政治理論核心的春秋義理觀念,已經深深融入朝鮮人的價值觀,成爲這一時期相關歷史事件與文學現象的思想淵藪。
春秋義理觀,是儒家政治理論的核心思想,它主要包括:如何區別華夷和處理華夷關係,如何評判一個王朝的正統性以及爲政者應如何施政等問題,即華夷之辨與尊周攘夷,春秋“大一統”觀以及“王道”政治。這幾個基本問題相互關聯,爲我們給出了一個儒家理想中的王朝所應符合的標準。
孔子自衛返魯,“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①《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943。《春秋》寄寓了孔子一生的政治理想,後人將《春秋》尊爲“經”而不僅僅以“史”視之,也正是以其中所蘊含之儒家政論思想。到了朱熹,由於南宋偏安一隅,不斷受到北方金元的侵擾,民族矛盾極度尖銳,故園之思、家國之感彌漫朝野。因此朱子在其義理思想中尤其强調尊王攘夷、華夷之辨,以及法《春秋》、立綱常的史學正統觀。歷仕朝鮮仁祖、孝宗、顯宗、肅宗四朝,被譽爲“海東朱子”的李朝大儒宋時烈,親歷了朝鮮對清軍兩次入侵從抵抗到被迫臣服的過程,目睹明朝的覆亡,曾輔佐孝宗積極謀畫“北伐”事宜,冀望恢復明朝。這正是他春秋義理觀的現實表現。
朝鮮所秉持的春秋義理觀,其源流大致便是孔子—朱熹—宋時烈這樣一脈相承的。“三夫子之生,天意最不偶然。周室東遷,不可以不生孔子。宋室南渡,不可以不生朱子。大明沒於腥膻,不可以不生宋子”。②《宋子大全》,《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111),漢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頁88。周末、宋末和明末,都是禮樂顛覆,天下失統之際,尤其明末,更是夷狄全盤侵占中華的大亂世,“在朝鮮儒學界看來,宋時烈乃上承孔子、朱子,在明清更替的時代裏,擔負起了孔子、朱子所曾擔負的重任,宣導‘尊周攘夷’的大一統觀念”。①關於“尊明貶清”與“尊周攘夷”理論關係及朝鮮儒學思想演變問題,孫衛國有專文詳細論述(《試論朝鮮王朝尊明貶清的理論基礎》,《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本文立足於小說研究,此處僅簡略言之。
體現在對待明清的態度問題上,春秋義理觀中最核心、最有力的理論武器便是“尊周攘夷”。以宋時烈爲代表的朝鮮君臣念念不忘明朝的恩德,對清廷極盡貶斥,這是因爲他們的尊周觀本於朱子,尊周問題不僅關係到倫理綱常,更是朝鮮立國之基礎。從評判標準上來說:只有漢族建立的穩定的大一統王朝纔是正統,纔應該予以尊崇;其他紛亂如三國,異族建立如北朝十六國,都不是正統王朝。從現實指向上來說,“尊周”以“尊明”,“攘夷”即“貶清”。
上文提及,李朝建國之初,本是高麗朝臣的李朝太祖李成桂向明太祖提請册封國號,並由此使李朝政權的正統性得以確立。可以說,李朝統治的正統性是建立在其宗主國明朝的正統性基礎上的,這就決定了明朝滅亡之後,李朝統治者決不會輕易地背棄賦予其正統性的宗主國而轉投他方。否則,以儒學立國的李朝政權就將面臨嚴重的理論窘境,還可能進而影響其國內統治的穩定性。
在明清交替之際,對朝鮮而言,對待明朝、清朝采取何種態度,不僅僅是簡單的政治或軍事利益問題,其背後更關涉朝鮮自身建國的正統性。這或許纔是朝鮮在對明、清態度問題上做出如此選擇的更深層原因。
然而,春秋義理觀是建立在以華夏民族爲本位的基礎之上立論的,因此,作爲非華夏民族的朝鮮,在接受和運用這一理論時,必然會遇到如何將外來理論運用於本土環境的問題。除了由“尊周攘夷”這一核心觀念派生出的“尊明貶清”基本立場,朝鮮的春秋義理觀還有其自身的民族特點。
春秋義理觀的朝鮮本土化所遇到的第一個難題便是:既然要“尊周攘夷”,那麽,朝鮮究竟是“華”還是“夷”呢?顯然,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自願接受一種自我貶抑的理論作爲本民族的統治理論,因此,解決朝鮮的“華”、“夷”身份歸屬是朝鮮春秋義理觀的一個重要問題。
孰爲華夏,孰爲夷狄,華夏與夷狄是以何種標準進行區分和認定的?這是華夷思想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在辨別華夷之後,乃能探討如何處理華夷之關係。
在孔子看來,華夏與夷狄的具體區別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禮樂教化程度上,“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①《論語注疏》卷三《八佾》,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2466上。夷狄缺乏禮樂教化,是蠻荒之地,有君主還不如諸夏沒有君主。對夷狄地區君主不合禮制的僭越行爲,“吴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對夷狄的輕視顯而易見。其二,頭髮服飾,孔子以“被髮左衽”爲夷狄的標誌。②《論語注疏》卷一四《憲問》,頁2512上。其三,地域上,夷狄散居於諸夏之間,華夏則居於天下之中,故曰中華。
若以服飾和地域來區分華夷,那麽朝鮮很難被歸爲中華。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朝鮮抓住了華夷之辨的核心標準以立論,即以文化爲分野:行周禮者爲華夏,不行周禮者爲夷狄,孔子辨別華夷的基本標準乃是文化而非血統與地域。也因此,華夷身份是可以轉化的。行周禮,則夷可變爲夏;不行周禮,雖夏可淪爲夷。在《春秋》中被貶稱爲“子”的吴楚之君,其始祖身份都是華夏族,“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①《史記》卷三一《吴太伯世家》,頁1445。楚王始祖鬻熊亦是事文王有功而被成王封於楚地。可是因爲他們長期處於蠻夷之地,行夷狄之禮,便淪爲了夷狄。反之,舜本爲東夷之人,文王本爲西夷之人,然而並不妨礙其居華夏正統的地位。這也正是韓愈在《原道》中所概括出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②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7。以文化爲標準畫分華夷,使得朝鮮得以在以華夏民族爲核心的儒家華夷體系中,爲自己找到了一個巧妙的定位——“小中華”。③關於朝鮮的“小中華”思想,參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頁34—50;劉喜濤在《文化視域下的朝鮮“小中華”思想研究:以〈小華外史〉爲中心》(《北華大學學報》2011年6月)一文中則以十九世紀朝鮮吴慶元所著《小華外史》爲研究中心,對朝鮮“小中華”思想的三種境界作出了歸納。
“小中華”之稱並非僅僅是朝鮮自謂,在《明史》中,朝鮮便被列在外國列傳之首,“雖稱屬國,而無異域內”。④《明史》卷三二〇《外國傳一·朝鮮》,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8307。在《朝鮮王朝實録》中就有關於建文帝四年(1402)二月己卯賜李芳遠冕服的記載:
帝遣鴻臚寺行人潘文奎來,錫王冕服,結山棚備儺禮,上率羣臣迎於郊,至闕受敕書冕服,出服冕服行禮。其敕書曰:“敕朝鮮國王李芳遠:日者陪臣來朝,屢以冕服爲請,事下有司,稽諸古制,以爲‘四夷之國,雖大曰子,且朝鮮本郡王爵,宜賜以五章或七章服’。朕惟《春秋》之義,遠人能自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朝鮮固遠郡也,而能自進於禮義,不得待以子男禮,且其地邇在海外,非恃中國之寵數,則無以令其臣民。兹特命賜以親王九章之服,遣使者往諭朕意。嗚呼!朕之於王,顯寵表飾,無異吾骨肉,所以示親愛也。王其篤慎忠孝,保乃寵命,世爲東藩,以補華夏,稱朕意焉。”①《朝鮮王朝實録·太宗大王實録》卷三太宗二年二月己卯條,奎章閣藏鼎足山本,葉11A;又見吴晗輯《朝鮮李朝實録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67—168。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②《明史》卷三二〇《外國傳一·朝鮮》,頁8279。自箕子時期開始,朝鮮便行八條之教,按照中華禮義教化人民,後接受周武王正式册封,這被朝鮮認爲是其“小中華”的開始而引以爲豪。李朝建立之初,向明太祖請封國號,朱元璋以爲“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③《朝鮮王朝實録·太祖大王實録》卷三太祖二年二月庚寅條,葉3A;又見吴晗輯《朝鮮李朝實録中的中國史料》,頁121。乃賜其國號爲朝鮮,正是因爲“朝鮮”之稱源於箕子,引發了對於朝鮮半島世行中華之教的溯源聯想,這被視作認可了李氏朝鮮在儒家華夷體系中的“小中華”地位,所以令李朝君臣上下感戴,引爲“大造之恩”。④英祖曾曰:“高皇有大造之恩,神皇有再造之恩,忘其大本,似爲未安。此予所以中夜怵惕者也。”後遂將明太祖、神宗、崇禎三帝崇祀於大報壇。見《朝鮮王朝實録·英宗大王實録》卷六九英祖二十五年三月辛未條,葉26B。在朝鮮漢文小說中就多有關於箕子朝鮮的記載。如李朝文人金時習《金鼇新話》中的《醉遊浮碧亭記》,⑤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七,頁81—91。小說開篇便回顧了箕子建古朝鮮國於平壤的歷史。“平壤,古朝鮮國也。周武王克商,訪箕子,陳洪範九疇之法。武王封於此地,而不臣也”。洪生醉遊浮碧亭,不禁生“麥秀殷墟之嘆”,吟詩六首,其中多是對箕子朝鮮的追思感懷,有“箕子廟庭喬木老,檀君祠壁女蘿緣”,“千年文物衣冠盡,萬古山河城郭非”等句。這就引來了一名仙娥前來,以仙饌設小宴招待之。女子亦做詩六首應和之,並說自己乃是“殷王之裔,箕氏之女”:“我先祖實封於此,禮樂典刑悉尊湯訓,以八條教民,文物鮮華,千有餘年。”①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七,頁86。
金時習效忠端宗,不肯與世祖合作,於世祖十年入金鼇山寫作《金鼇新話》,《醉遊浮碧亭記》主題雖是借對箕子朝鮮的追慕和衛滿竊國的痛恨,影射其對世祖篡位的不滿,但也從側面體現出作者對箕子朝鮮源自華夏、儒教興盛的自豪。
前面提到過的《赴南省張生漂大洋》,也有一個有趣的情節,體現出其時朝鮮在面對東亞儒家文化圈中其他國家時,因其“小中華”的地位而產生的優越心理:
林遵問我國俗人物衣冠山川地方,張生答曰:“我國襲箕子遺化,崇尚儒教,觸排異學,國以禮樂刑政爲治,人以孝悌忠信爲行,於是乎四百年培養之餘,人材蔚興,文章道德之士,史不勝書。衣冠則損益殷周之舊制,集成皇明之文章。山有萬二千峯之金剛,水有三浦五江之襟帶,地方不知幾千里。可得聞貴國(安南)之風土衣冠文章乎?”彼人輪看之,喧噪不已,竟無所答。自此彼人筆談,不曰爾國,必稱貴國;不曰爾們,必稱相公矣。②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卷八,頁104。
林遵向張生詢問朝鮮風土人情,張生介紹了朝鮮沿襲箕子遺化,世受華風熏陶、儒家教化的盛況,並轉而詢問安南國的風物。安南國人聽後無言以答,自慚鄙小,從此對朝鮮非常尊敬,“不曰爾國,必稱貴國;不曰爾們,必稱相公矣”。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張生在介紹朝鮮時着重强調並引以爲豪的正是朝鮮崇尚儒教的禮樂教化之風。
值得注意的是,“小中華”意識雖由來已久,但其高漲則反而在明亡之後。《奈城志》中作者假托建文帝之口說出的一段感慨,很好地解釋了當時東國士人的此種心態與論調:
皇帝(建文帝)忽垂淚而謂大王曰:“北望中原,神州陸沉,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家基安在?予雖遜位於燕王而社稷猶存,故每憑覽古都,庶以懷慰。而今靺羯喧騰,宗國永亡。徘徊宇宙,予將何歸?惟卿之國,寶祿綿綿,緒業不墜,千秋萬歲,以傳無窮,則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大王(端宗)亦感淚而對曰:“臣國服事天朝者久矣,今聞陛下之教,臣不勝慟隕之情矣。何幸藩邦則國脈綿綿,臣太祖、太宗、世宗、文宗之靈,世世享禴祠烝嘗,泉臺之下瞑目無憾而。”①張孝玄等編校《校勘本韓國漢文小說·夢遊録》,頁579—580。
中原陸沉、明朝覆滅,而孤懸海外的朝鮮反得以存續宗廟,綿延華夏一脈,“小中華”的使命感與自豪感也因之油然而生。
不過,隨着時代的發展,清朝統治日益穩固,明朝復國之夢漸成泡影。到了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前期,出現了主張利用厚生、北學清朝的“北學實學派”,其代表人物有洪大容、朴趾源、朴齊家等。這些學者多活動於京城,並有出使清朝之實際經歷,因此對當時朝鮮王朝以“小中華”自居,過於固守於華夷之防,排清自大的狹隘民族主義進行了批駁,表現出在華夷問題上的態度轉變,能夠比較公允地看到清朝先進的一面。雖然,終其一朝,朝鮮對清的態度並無根本變化,一直視之爲夷狄,從未如對明朝一般誠心事大,更多的還是迫於現實無奈的屈服和虚與委蛇。
(本文作者係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副教授)
*本文爲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東亞漢文小說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號: 13&ZD11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