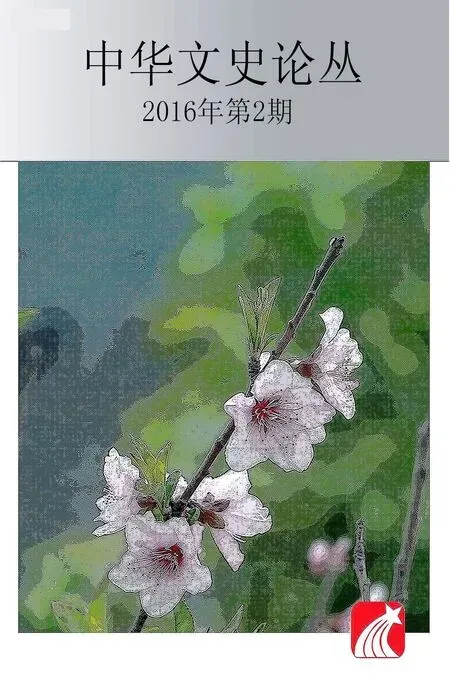“述毛”與“難鄭”
——王肅《詩經》學的語境還原及歷史建構
許佩鈴
“述毛”與“難鄭”
——王肅《詩經》學的語境還原及歷史建構
許佩鈴
王肅《詩經》注,全書已佚而集中存留於《毛詩正義》中。《正義》的解經系統對王注的取捨有內在的體例。通過還原佚文的引用語境,可以發現“述毛”是孔疏引用王注的預設前提。王肅對毛傳的墨守遠過鄭玄,其對未明言的傳意的補足和推測遵循一定的義例。“鄭王之異”是“王述毛”與“鄭異毛”衍生的間接結果。但王肅《詩經》學在後世的影像卻是圍繞着“鄭王之爭”的先在焦點拼接而成的,“難鄭”成爲核心。“述毛”的殘片與“難鄭”的影像都滲透了經學史發展的印迹。
關鍵詞:王肅《詩經》學 述毛 難鄭 《毛詩正義》
引 言
六朝南北分裂,經學亦隨之“好尚互有不同”,而“詩則並主於毛公”。①《隋書》卷七五《儒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705。《北史》卷八一《儒林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709。同宗《毛詩》,有鄭玄箋與王肅注之殊途。鄭玄“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②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之一,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上。陳澧對此數語十分推崇,稱其“字字精要”:“爲主者,凡經學必有所主。所主者之外,或可以爲輔,非必入主岀奴也。表明者,使其深者畢達,晦者易曉,古人所賴有後儒者惟在於此。若更爲深晦之語,則著書何爲哉?如有不同者,以毛義爲非也,然而不敢言其非;下己意使可識別者,易毛義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敬先儒也。讀者當字字奉以爲法。”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99。采三家《詩》說以補正毛傳。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③《三國志》卷一三《王肅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419。其《詩經》注可考者有:
1.《毛詩注》二十卷(見《釋文敍録》、《隋志》、《唐志》),另《隋志》又載鄭玄、王肅注《毛詩》二十卷,馬國翰謂爲“魏晉間人取肅注次鄭箋後,取便觀覽,非肅别有注也”。④馬國翰輯《毛詩王氏注》前序,《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一四,《續修四庫全書》,12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98下。
2.《毛詩問難》,《隋志》載“梁有二卷”。兩《唐志》亦載爲二卷。
3.《毛詩義駁》,《隋志》載八卷,兩《唐志》題爲《毛詩雜義駁》,亦八卷。
4.《毛詩奏事》,《隋志》載一卷。⑤王肅著述詳情,參郝佳敏《中古詩經文獻研究》附編《王肅著述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218—235;李振興《王肅之經學》之《緒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9—21。其《詩經》學著作,參孫啓治、陳建華等編《古佚書輯本目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7—28;洪湛侯《詩經學史》第四章《魏晉至唐的毛、鄭〈詩〉派》第一節《王肅的〈詩經〉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08—209;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臺灣,三民書局,1986年,頁220—223。
這些著述今俱亡佚,僅有後世輯本。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詩類》輯《毛詩王氏注》四卷,《毛詩問難》、《毛詩義駁》、《毛詩奏事》各一卷。黃奭《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亦輯《毛詩王肅注》一卷,將王肅對鄭箋的駁難亦一并收入,不另爲別本。二輯本互有參差。
“鄭、王之爭”是魏晉《詩經》學上的重要問題。之前學者對此多有探討,看法各異。①參郝虹《三重視角下的王肅反鄭:學術史、思想史和知識史》,《史學月刊》2012年第4期,頁14—24。而在研究路徑上大致可分兩種。一是考諸史籍,在思想史和政治環境的背景中論其時風與師承。據王肅本傳所載,肅“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②《三國志》卷一三,頁414。又《李譔傳》載譔“從司馬徽、宋忠等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③《三國志》卷四二,頁1027。由此,自湯用彤始,研究者多將王肅說經之異鄭歸因於以宋忠爲代表的荆州學派的影響。④湯用彤云:“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仲子之道固然也。譔、肅之學並由宋氏,故意歸多同。”《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載其《魏晉玄學論稿及其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61。又如唐長孺亦云:“就是經學中鄭玄、王肅的差異也由於鄭較近於漢儒家法,而王肅則年輕時曾從荆州學派的宋忠讀《太玄》,多少受新經學影響。”《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其《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頁364。然此說實可商榷,程元敏已有詳論。⑤詳參程元敏《季漢荆州經學(上)》,《漢學研究》1986年第1期,頁211—263。尤其頁258—260。《季漢荆州經學(下)》,《漢學研究》1987年第1期,頁229—262。尤其頁247—260。蓋王肅習鄭氏學覺其“義理不安”時,尚未師從宋忠。且以人才、著述、影響衡之,其時荆州之地亦未足當一學派。吴雁南則結合當時司馬氏與曹氏爭權的政治背景,指出“說明新政權需要新的學術權威以號令學術界”。①吴雁南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75。又參郝虹《王肅經學的歷史命運》,載葛志毅主編《中國古代社會與思想文化研究論集》(四),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56—58。此種觀點多舉《三國志》卷四《魏書·三少帝紀》高貴鄉公與朝臣論鄭、王之異同一事,頁136—138。
另一路徑則是比較王肅與鄭玄經說的內容,歸納其特點,往往利用輯本逐條比勘。如李振興在其研究王肅經學的專著中對今存王肅的七種經注均有列表,②李振興《王肅之經學》諸章。《詩經》注見於第三章《王肅之詩經學》第三節《鄭、王二家詩經注異同表》,頁500—568。並對現存的佚文進行逐條考釋(下簡稱李著)。史應勇探討鄭、王之爭,也有專章比勘現存鄭玄、王肅的六種經注(下簡稱史著)。③史應勇《鄭玄通學及鄭、王之爭研究》第十章《現存鄭玄、王肅經注比勘六種》,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頁231—367。《詩經》注見於頁249—323。郝佳敏在論述王肅反對鄭玄《詩》學的表現及其成因時,亦提及部分實例(下簡稱郝著)。④郝佳敏《中古詩經文獻研究》第一章《三國時期詩經文獻研究》第三節《王肅反對鄭玄〈詩〉學的表現及其成因》,頁31—44。
但王肅的《詩經》注之存佚實則有其特殊性。它不但在王肅的羣經注中現存最多,⑤李振興《王肅之經學》統計王肅經注“今可得而述”者,《詩經》注有三百三十則,遠高於位居其次的《尚書》注二百二十五則,見李著《緒論》,頁2。而參考馬、黃二氏的輯本,更可發見,現存佚文集中存留於《毛詩正義》(今本附《毛詩釋文》,下簡稱《正義》)中,⑥其他典籍中引録或轉述的王肅說《詩》佚文亦能爲《毛詩正義》所涵括,如常被稱引的歐陽修《詩本義》論《擊鼓》引述“王肅以爲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詩本義》卷二,四部叢刊三編本,2册,葉10A),《毛詩正義》卷二之一《擊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經疏引王肅說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頁155上,意正相同。不同於一般佚文的“散見各處”。與此同時,《正義》引用的前人詩說,亦以王注爲最多。⑦據韓宏韜《〈毛詩正義〉研究》上編第三章《〈毛詩正義〉的引書價值》所列《正義》引《詩》學文獻目録統計,合計引用王肅詩經著述二百八十七次,尚不包括 《毛詩音義》的引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 0 0 9年,頁1 2 4。《正義》兼主毛、鄭,形成“經—傳—箋—疏”四重結構,與十三經中其他注疏“經—傳—箋”三層結構相比可稱獨有。因此,除彙集衆說之外,它更是以“毛、鄭並宗”爲宗旨構建的嚴整的解經系統。其中對王注的取捨,自有內在的體例和剪裁規則。
因此,或許值得略作反思的是,之前研究往往利用輯本,全力關注王肅《詩經》注殘存之“形”,徑直進入了與研究存世文獻同樣的路徑,而有意無意間忽略了探問其來源:它從何處來?又是怎樣的機緣使之在整體亡佚後仍能殘存至今?
程蘇東針對“鈔本時代的經典研讀與存在的問題”的筆談似乎可以予人啓發:
傳統的輯佚學注意佚文的搜集與編排,但是對佚文所屬原書引書體例的研究,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視。事實上,所謂“佚文”,既然被納入了新的文本系統,不免會受到新文本語境的制約,因此,了解佚文所屬原書的引書體例,是我們評估佚文還原度的重要前提。①程蘇東《基於文本複雜形成過程的先唐文獻研究》,《求是學刊》2015年第4期,頁159。同期林曉光亦言及:“種種殘缺的佚文,本身是在不同歷史作用下保存下來的。總集、史傳、古注、類書各有不同的處理原則。”見其文《文獻重構與文學本位》,頁154—155。
試申言之,作爲輯佚資源的文獻典籍對佚文的保存,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自然或者偶然的存留,如古注、字書、廣收衆說的集解體等,或是旁及,或是廣收,這些存留在原書中是無意識的。另一種則是在一定的引書體例和目的下有意識的剪裁篩選,則“散”中仍有“整”。因此,對於後者中的佚文,不僅要探究原書的引書體例,更應該關注其引用的“語境”,②“語境”一詞在現代學術話語中是一個外延甚廣的泛化概念。本文所用 乃其狹義,即指字、詞、句等所在的可幫助確定其意義的上下文。這似乎是評估佚文相對於原貌之“代表性”的重要前提。而王肅的《詩經》注正屬於此類。
因此,倘忽視還原王注在《正義》中的引用語境,便不免舛訛和失實。此前的研究由此造成的缺失,綜論之,有以下數點:①三書中訛字等簡單錯誤自不計在內。如李著“碩大無朋”,“朋”誤作“明”(頁508)。史著“《國風·邶風》”誤作“國內”(頁252),郝著“胡承珙”俱誤作“洪承珙”(如頁35等)等等,皆略之不論。因僅據輯本、未核原文而襲誤者,如《采葛》“彼采蕭兮”,《毛詩正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卷四之一,頁314上),馬國翰輯本誤認“生民”爲“王氏”,采入此條(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一四,頁301下),李著遂亦列爲王肅說(頁506)。亦不論列。
一是僅録王說佚文。李著甚至未列毛傳,只將鄭、王列在一處。稱“比並排列,優劣自現,自不需多所辭費也”。②李振興《王肅之經學》第一章《王肅之周易學》第八節《周易王氏音比較表》,頁132。但即使同釋一句經文,也會因不明其說指向,而無法展開有效分析。如李著列《駟驖》“公之媚子”一句,箋云:“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據《正義》采王肅說:“卿大夫稱子。”③李振興《王肅之經學》,頁509。
核《正義》原文,實爲“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④《毛詩正義》卷六之三,頁482下。故《正義》所引王說實際是要解釋經中何以稱“媚子”,而鄭箋則是在串講詩義。彼此話題不同,自然談不上比較“同異”。
二是研究者往往懷着做過“具體內容的詳細比勘”的自矜,⑤史應勇特加說明云:“時下有些人士在具體的文獻問題尚未考量清楚的前提下就對鄭、王之爭做哲學史的評說,筆者對此不以爲然。”《鄭玄通學及鄭、王之爭研究》,頁232。尤其關注迥異於舊說“王、鄭對立”之外的“鄭、王之同”,每特加案語彰顯之。但因爲忽略它們在《正義》中出現的情境和《正義》的評述,僅從大意上評估孤立摘出的佚文,往往失之草率。如李著列出《桑柔》“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一句的王、鄭之說,備注“鄭、王義同”。①李振興《王肅之經學》,頁545。
此句毛無傳,鄭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正義》引王肅說云:“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
粗略看過,文字確實大體相似。但《正義》於後又評曰:
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爲不受之勢,故以爲假設拒己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爲君臣俱陷於禍難。②《毛詩正義》卷一八之二,頁1388上—下。字下點爲筆者所加,下同。
《正義》雖然認爲王說理可通,但“箋不然者”已經表明至少在其看來,鄭、王之說是不同的。細繹之,鄭、王之申說確實有別。王以此爲諫者自訴,嘆如今之政無望再返於善。而鄭則以爲是“假設拒己之辭”,“其何能淑”是聞諫者對“告教之言”的否定。文意顯然有別。
史著此例不誤,案語斷爲“鄭、王不同”。但同詩中“進退維谷”一句,卻又斷爲“鄭、王略同”。③史應勇《鄭玄通學及鄭、王之爭研究》,頁299,300。
此句毛傳只訓單字:“谷,窮也。”鄭箋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傳疏引王肅注:“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儘管鄭、王同申毛傳“谷,窮”之詁,但所指不同。正如《正義》隨後評曰:“箋不然者,以臣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爲二,故以施政本末爲進退。”④《毛詩正義》卷一八之二,頁1395上。
此兩例,《正義》均在引王說後接以“箋不然者”之申述,而李著、史著都僅憑自己理解的大意斷定鄭、王相同,失之眉睫。
三是忽視箋注在《正義》中着力於單字訓詁的特點,而從義理角度武斷大意。如史著舉《大雅·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鄭箋:“殷盛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王注:“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①《毛詩正義》卷一六之二,頁1143下。
史加按語云:“鄭、王大意略同,鄭則更强調周之有德而殷之爲天所棄。王則只强調其因衆叛而敗。”②史應勇《鄭玄通學及鄭、王之爭研究》,頁287。既斷其大意相同,又將其微異歸之義理。而實際上,其所以異實因鄭訓“予”字爲“給予”之義。而王述毛訓“予”爲“我”,故解説有別。正是單字的訓詁決定了詩義。
此句王注實輯自《正義》的傳疏:
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③《毛詩正義》卷一六之二,頁1143上—下。
可見《正義》引王說是要佐證其對毛傳解“予皆爲我”、“侯皆爲維”的推測,且所引王注只解“維予侯興”一句,並未及他句。史著未回歸其語境,故誤。
更有甚者,則將訓詁和大義分開討論。如郝著舉《齊風·南山》“既曰歸止,曷又懷止”爲例。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毛傳:“懷,思也。”鄭箋:“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於魯侯矣,何復來爲乎?非其來也。”①《毛詩正義》卷五之二,頁400上,401上。
郝著認爲王肅是“詞語訓詁從毛,詩句大義從鄭”。②郝桂敏《中古詩經文獻研究》,頁25。實則毛、鄭相異,而王注則是將毛傳帶入解經。解釋同一條經文,倘若大旨不異,語意自然相近,而比較訓詁之異同,自是判然有別。將訓詁與語意分開評其說經同異,邏輯上似已不通。
四是試圖通過對殘文的具體比勘直接概括總結王肅說《詩》的特點。③如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頁223—248;史應勇《鄭玄通學及鄭、王之爭研究》,頁231—232;郝桂敏《中古詩經文獻研究》,頁23—27。儘管因爲殘片與實際的總貌相差當不太遠,這一還原實貌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它仍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正義》引用的王說實是按照一定的體例剪裁後留下來的,對殘文的具體比勘展現的只是留在《正義》中的王注殘說的面貌。
由此可見,對王肅《詩》說進行語境還原,有利於更清楚地認識它的“殘形”及其與原貌的關係,並由此對經學史的習慣敍述作另一番思考。
一 解經系統與存録前提
《正義》實際是一個多層次的解經系統。它分章句解詩,在每節章句內部,都逐次疏解經文、毛傳、鄭箋(若無傳或無箋,則隨之省略)。因此每一章又可分爲經疏、傳疏和箋疏三個組成部分。
儘管《正義》總體呈現右鄭的傾向,④《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提要》:“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途。”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120上。但如《東方未明》正義云:“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强爲之辭。”《毛詩正義》卷五之一,頁397上。可見其基本態度還是實事求是的,並不强爲辯護。但因其兼宗毛、鄭,故疏文的傾向性實際決定於其所在的“位置”。所謂的“疏不破注”、“疏不破箋”似乎也要考慮到“位置”的導向作用。析而論之,傳疏自然要申說毛意,箋疏自然要闡述鄭箋。在不同的位置上,分申其說,各從其旨,義存兩解。①《十月之交》序疏曰:“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强爲與奪。”(《毛詩正義》卷一二之二,頁840上)又《東門之楊》箋疏曰:“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卷七之一,頁523下)可見其處理方式。
但以往對《正義》內部的結構體例的研究似乎都忽略了每章的經疏部分。而細察之,謹守傳、箋的《正義》在經疏中實際隱含了傾向和判斷。②關於《毛詩正義》的內部體例,郝桂敏《中古詩經文獻研究》第五章《〈毛詩正義〉研究》(頁110—112),韓宏韜《〈毛詩正義〉研究》第四章《〈毛詩正義〉的經學成就》(頁174—178)均有申說,但均未提及經疏中的“傾向性”。若還原其思考過程,則先是判斷此章毛、鄭之同異。若同,則合說。若不同,則分說:先以“毛以爲”串講毛之經義,再說鄭義,若其與毛僅略有不同,則指出其差異所在,時結以“餘同”。若差異較大,則以“鄭以爲”重新串講鄭義。舉例如次:
《谷風》“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章,毛、鄭同,經疏曰:“婦人既言君子苦己,又本己見薄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③《毛詩正義》卷二之二,頁174上,175上。
《行露》“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章,毛、鄭不同,經疏曰:“毛以爲……鄭以爲……”④《毛詩正義》卷一之四,頁94上,94下,95上。
《伯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章,毛、鄭略異,經疏曰:“毛以爲……鄭以‘願’爲‘念’爲異”。①《毛詩正義》卷三之三,頁287上,287上—下。
因此,其解經部分雖似六朝義疏體的串講,但因其所據之注有毛、鄭二家,故既表明了《正義》對毛、鄭經說的理解,也暗示着對二者同異的分析與判斷。
然則王注在這一解經系統中是如何呈現的呢?
《小雅·皇皇者華》“載馳載驅,周爰咨詢”一章箋疏似乎可見《正義》對王注的基本價值判斷。它在羅列鄭、王說《詩》之異後云:
《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②《毛詩正義》卷九之一,頁661下,663上。
疏中稱“鄭、王並是大儒”,可見《正義》撰寫之時雖以鄭箋爲本,但並不像後世那樣貶抑王說,是客觀地取王注以說經,這正合於其在序中所言“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③孔穎達《毛詩正義序》,《毛詩正義》卷首,頁4上。而其采録的王注究竟要起如何的作用呢?
前人對此早有論及,都認爲是以王申毛。馬國翰輯王注時即發現:“案鄭箋毛詩,而時參三家舊說,故傳箋互異者多,《正義》於毛、鄭皆分釋之,凡毛之所略而不可以鄭通之者,即取王注以爲傳意。”④馬國翰輯《毛詩王氏注》前序,《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一四,頁298下。郝佳敏言:“多采魏王肅《毛詩》注解釋毛傳義。”⑤郝佳敏《中古詩經文獻研究》,頁117。而其所以如此之緣故與程度,則尚未明言。
通觀之,不難發現,《正義》認爲,無論客觀效果如何,王肅《詩》說的主旨即在述毛。比如,毛無傳時,孔疏每用王注證明其對傳意的推測。如《鴟鴞》“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云:“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未解“勤”字之義。傳疏云:“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獉獉以勤爲惜。”故於解經述毛義時,亦云:“周公言己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①《毛詩正義》卷八之二,頁600下,602上,601上。
甚而用王肅之說作爲推定毛傳文本正誤的有力證據。如《行葦》“或歌或咢”,毛傳:“徒擊鼓曰咢。”傳疏云:“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誤耳。”②《毛詩正義》卷一七之二,頁1271上,1272上。案,《園有桃》“我歌且謠”,傳:“徒歌曰謠。”卷五之三,頁427下。遂定毛傳正本爲“徒擊鼓”。
又如《都人士》“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疏曰:
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③《毛詩正義》卷一五之二,頁1073上。
即使不認可王說,引而駁之,亦往往以“未得傳旨”作爲評語的落腳點(例參下文)。而所以如此,正是因爲將“述毛”作爲王說的主觀目的和主旨所在。因此,在《正義》的解經系統中,王說是爲了疏釋毛傳而引入的,“述毛”纔是《正義》所理解和篩選的王說。
而今本《毛詩正義》所附《釋文》,本爲陸德明《經典釋文》中的《毛詩音義》。學者考證,《正義》的成書與《釋文》並沒有必然的聯繫。《正義》附《釋文》是從南宋建刻十行本開始的。④參韓宏韜《〈毛詩正義〉研究》第三章《〈毛詩正義〉的引書價值》第二節《〈毛詩正義〉引書的學術認識價值》之《〈毛詩正義〉與〈毛詩釋文〉的關係》,頁143—159;曹詣珍《〈毛詩注疏〉版本流變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年第3期,頁70—72。陸氏其書有自述著述體例的《條例》,云:“若典籍常用,會理合時,便即遵承,標之於首。其音堪互用,義可並行,或字有多音,衆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各題姓氏,以相甄識,義乖於經,亦不悉記。”①陸德明撰,吴承仕《經典釋文序録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1。即“首標勝義,次列諸家”。②吴承仕疏語,見《經典釋文序録疏證》,頁12。因此,它雖然在引用次序上呈現了優劣評判,但收羅異說卻類於集解體,故可以認爲王注在其中是一種自然存留。另外,其“援引衆訓,讀者取其意義,亦不全寫舊文”,③《經典釋文序録疏證》,頁13。則引書但取大義,並不照録原文。
因此,在具體比勘鄭、王《詩經》學異同時,宜先考慮孔疏秉持的采録前提和毛傳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毛、鄭異同本身便是《正義》解經系統的重要樞機,因此,孔疏所判斷的毛、鄭異同實則設定了王注出現的具體語境。
二 毛、鄭異同與引用語境
以毛、鄭異同爲界標,分析孔疏對王注運用的不同情況,可以有效地還原其語境。兹分條詳析如下:
(一)毛、鄭異
若《正義》判定毛、鄭異,則常引王注以證毛傳。時是時非,或棄或取,皆以其是否“得傳旨”爲衡量標準。
1.襲而用之。襲用以貫通傳意,闡發傳旨。這一情況在全部的王注引用中是最多的。而其最常出現的位置是在傳疏中(若毛無傳,則移至箋疏末尾)。
相較於鄭箋,毛傳確實“隱略”。其略,皮錫瑞論“《詩》比他經尤難明者八”,其三有云:“三家亡而毛傳獨行,義亦簡略,猶申公傳《詩》,疑者則闕弗傳,未嘗字字解釋。後儒作疏,必欲求詳,毛所不言,多以意測。”①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經》,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頁1。其隱,似在於獨標興體,而往往不明說興義。②洪湛侯《詩經學史》結合朱自清《詩言志辨》的統計,認爲毛傳中標“興也”的詩有一百十六篇。而其中有說明文字的共二十六篇,其他九十篇,毛傳皆無說。參其書第二編第三章《詩經漢學》第三節《毛詩故訓傳》,頁183。
因此,毛無傳時,《正義》則用王注補詩訓。毛只訓單字時,則用王注串聯詩意。毛標興體而不言興理時,則引王注闡發興理。有時在引用後評其“傳意當然”、“傳意或然”或“言得傳旨”等。即簡博賢所云“故凡毛所不傳、或義有質略,則輒從肅說申義”。③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頁250。
補詩訓。如:
《彤弓》“受言藏之”。傳:“言,我也。”箋:“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傳疏:“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經疏述《毛詩》意亦用之:“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④《毛詩正義》卷一〇之上,頁731下、733上,732上。
串詩意。如: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傳疏: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享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⑤《毛詩正義》卷九之二,頁650上,651下—652上。
闡興理。如:
《白華》“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傳疏:“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經疏述《毛詩》意亦用之,云:“興婦人有德,已納以爲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絜白之謂。”①《毛詩正義》卷一五之二,頁1085上,下。
2.斥而改之。然而,《正義》有時雖然引王說,但並不全部認同和取用。皮錫瑞云:“唐作《正義》,兼主傳箋,毛無明文,而孔疏云毛以爲者大率本於王肅,名爲申毛,實則申王。”②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經》,頁2。似未見其全。斥之者,又往往因其所在位置不同,而情況有別。
在傳疏中,是因其“雖云述毛,而未得毛旨”,故另爲毛說。有時是另取別家之說。如:
《白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傳:“步,行。猶,可也。”箋:“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傳疏:“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爲毛說。”
毛、鄭訓“猶”字不同,故解詩亦當不同。王肅以爲此兩句是說“下國”,而侯苞以爲是自訴(指申后)。疏以上章“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是說“遠外我申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故此章亦當是說申后,因此評王說“與上章不類”,故取侯苞之解爲毛說。①《毛詩正義》卷一五之二,頁1086上,1087上,1085上。
或另作別解。如:
《瓠葉》“有兔斯首”。毛無傳。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傳疏:“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且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
王肅雖如字述毛,但孔疏不同意其“一兔頭”之解,而駁斥之。並於疏經時另爲說云:“毛以爲,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一兔。”②《毛詩正義》卷一五之三,頁1097上,下—1098上。
又在箋疏中,則是爲了申明鄭義,引王難鄭以申毛之說,然後反駁之,爲鄭辯護。如:
《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此經毛不爲傳。王肅解毛,以“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爲“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而箋以爲是成王“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孔疏在箋疏中串講毛義時,悉用王肅之解,並評以“傳意當然”。但在闡說箋意時,又引王難鄭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而詳駁其說云:
歷觀其次,粲然有敍,寧當於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廁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饟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①《毛詩正義》卷一四之一,頁985下,987上,987下—988上。
這裏卻反詰王注之非,次針對其駁難,逐條反駁。可謂詳矣備矣。
3.非而存之。當《正義》的傾向明顯是以鄭箋爲然時,本不甚認可毛傳之說,但格於體例,仍要疏證。這時在箋疏與傳疏中分別提及王注,便表現爲相互矛盾的態度。在傳疏中,會以王注證毛說。在箋疏中又不以其爲然,遂代鄭申說易傳之由,駁斥王說。相悖的觀點被安放在不同的位置中,從中又一次可見“位置”在《正義》解釋系統中的導向作用,不同的位置實際規定了不同的闡釋職任。前人所謂“疏不破注”的具體情形實則並非單一。如:
《大明》“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京,周國之
地,小別名也。”傳疏: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經疏中亦用爲毛說:“來嫁於周邦,既配王季爲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箋疏:“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②《毛詩正義》卷一六之二,頁1134上,下。
又如《漸漸之石》“武人東征,不皇朝矣”。毛無傳。箋:“武人,謂將率也。皇,正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箋疏:“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修禮而相朝。’此自王
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爲長矣。”①《毛詩正義》卷一五之三,頁1101上,1102上—下。
《正義》不以王之述毛爲然,且在箋疏中駁斥之。但因需解釋毛意,故仍“存以代毛”。
(二)毛、鄭同
若《正義》判定毛、鄭同,則在解經時合說毛、鄭。此時引用王注較判定毛、鄭異時爲少,析其語境,又可分爲四種。
1.引以證鄭。毛、鄭既同,則述毛亦即述鄭。故若毛無傳而《正義》以爲毛、鄭同,便會出現以王注證鄭箋的情況。此正是具體比勘經注的研究者們最爲關切的“王、鄭相同”。略舉數例以見:
《閟宮》“是生后稷,降之百福”。毛無傳。箋:“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予之福。”箋疏:“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爲與之福也。’”②《毛詩正義》卷二〇之二,頁1655下,1656上,1658上。
又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傳疏:“《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①《毛詩正義》卷一九之一,頁1509上,1509下—1510上。
乾嘉學者朱士端即以此爲例說明“按王肅申毛,有時從鄭”。②朱士端《彊識編》卷一“好是家嗇”附“王肅申毛從鄭”,《續修四庫全書》,1160册,頁443下。但此種情況在《正義》中非常少。或因已有“則更表明”的鄭箋解釋毛傳,故無需再復引王注爲證。
2.存王取鄭。毛傳質略時,《正義》若“無迹可尋”,即以鄭申毛,“同之鄭說”。徵引王注只是略備一解,在經疏中亦不取爲毛說。
如《桑柔》“念我土宇”。傳:“宇,居。”箋:“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箋疏:“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故於經疏中合解毛、鄭云:“其心殷殷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③《毛詩正義》卷一八之二,頁1386下,1387上。
又如《駉》“思馬斯徂”。毛無傳。箋:“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箋疏:“王肅云:‘徂,往
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④《毛詩正義》卷二〇之一,頁1638上。
3.斥王用鄭。《正義》以王注述毛非旨,故引而駁之,取鄭申毛。如:
《緜》“柞棫拔矣,行道兑矣”。傳:“兑,成蹊也。”箋:“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兑然,不有征伐之意。”傳疏:“《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棫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柞棫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經疏依鄭箋合解云:“於柞棫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兑然矣。言無征伐之心也。”①《毛詩正義》卷一六之二,頁1162下—1163上,下。
4.略王之鄭。鄭、王申毛雖不同,但疏以毛、鄭同,未引王說。在《釋文》中纔能見到隱而不彰的王注。如:
《椒聊》“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無朋,平均,不朋黨。”傳疏:“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也。”②《毛詩正義》卷六之一,頁451下,453上。與箋同。但從《釋文》中可知,“比”字,王“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③《毛詩正義》卷六之一,頁451下,亦見陸德明《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68上。與鄭不同,但《正義》略之未引。
三 補足傳意與說經義例
可見,毛、鄭之異和後學的“述”與“駁”在《正義》的解經系統中,已經超出了是非的意義界域,而是各處其位、各司其職地合成一個秩序井然、層次分明的系統。《正義》對引用的王注有棄有取,衡量的標準則是毛傳之意。
當《正義》作出毛、鄭異說的判斷時,其“補足傳意”實則遵循一些一貫的規則,並往往引王說來佐證自己的推斷,似乎也可以認爲,《正義》的推測可能是受了王說的影響,甚或是直接采自王說的。由此,可以發現王注的申說毛傳是依循甚至墨守一定的義例的。其中詳情,約而言之,略有數端:
(一)毛無破字
鄭箋每每改讀,若毛無傳,則王肅必以如字解之。《正義》也往往據毛如字而判斷其必與鄭異。
如《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傳:“丁,當也。”箋:“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傳疏:“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經疏亦用爲毛說:“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祐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土地之國,曾使正當我身有此旱乎?”①《毛詩正義》卷一八之二,頁1405上—下,1407上,1406上。
即使王注未被采入《正義》的推斷解說中,從《釋文》的記録中,也可見到王注是嚴循“如字”來述毛的。
如《七月》“田畯至喜”。毛無傳。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傳疏云:“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爲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②《毛詩正義》卷八之一,頁575上,578上。未引王說。而《釋文》引之云:“喜,王申毛如字。”③《毛詩正義》卷八之一,頁575上;亦見於《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中》,頁73上。
(二)同詩之傳
據同一篇詩中他章的毛傳發揮其未明言的傳意。
如《考槃》“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虚乏之色。”
傳未解“寬”義,故經疏云:“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薖’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①《毛詩正義》卷三之二,頁259下。
孔疏據卒章毛傳推測此章的傳意,引王說證之。又如上文所舉《駉》“思馬斯徂”一例,毛傳訓上章“思馬斯作”之“作”爲“始”,王注遂訓“徂”爲“往古”,以上章之訓合。《正義》雖以“無迹可尋”未采王說,但也肯定“此未必不如肅言”。
(三)全篇詩旨
毛、鄭解《詩》之旨不同時,王肅必依毛說。《正義》判斷毛、鄭異同,也往往以一首詩爲一個整體單位。如《雨無正》,小序以爲“大夫刺幽王”,而鄭以爲“亦當爲刺厲王”。解其中“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箋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於彘,無所安定也。”傳只云:“戾,定也。”傳疏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②《毛詩正義》卷一二之二,頁854上,855下,856上。
(四)訓詁通則
王注往往依據毛傳一貫的訓詁推測其未釋之字詞。如《商頌》中多次出現的“湯孫”一詞,因毛傳解《商頌》之首篇《那》“於赫湯孫”云:“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而鄭箋解“湯孫奏假”時云:“湯孫,太甲也。”①《毛詩正義》卷二〇之三,頁1686下,上。因此,以後各篇中出現的“湯孫”毛雖無傳,《正義》都據此推測傳意爲“湯爲人子孫”而異於鄭箋,且每次都引王注證之。如:
《那》“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來之意也。”箋疏云:“傳以湯爲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爲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②《毛詩正義》卷二〇之三,頁1687上,1690下。
又,《烈祖》“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箋疏云:“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③《毛詩正義》卷二〇之三,頁1693上,1696上。
又,《殷武》“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箋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敕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箋疏云:“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④《毛詩正義》卷二〇之四,頁1720上,1721上。
另將這一解詞方法推而廣之。《玄鳥》中“在武丁孫子”一句,傳只解“武丁”爲“高宗也”。箋解此句:“在高宗之孫子。”傳疏引王肅云“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並評曰:“毛以爲‘湯孫,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⑤《毛詩正義》卷二〇之三,頁1700上,1705上。
(五)一貫大義
《正義》往往據毛、鄭在大義上一貫的相異來推測其意不同,每得引王證之。
曾釗《詩毛鄭異同辨》列出毛、鄭異同大義有四,首列婚期。①參曾釗《詩毛鄭異同辨》卷上,《續修四庫全書》,73册,頁527下。毛傳以秋冬爲佳期,鄭箋以仲春之月爲正時。《正義》往往據此推斷毛與鄭異,亦引王說申毛。如:
《東山》“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毛無傳。箋:“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箋疏:“毛以秋冬爲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爲興。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經疏亦用以爲毛說:“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②《毛詩正義》卷八之二,頁613下,614上—下。
又如《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傳:“樗,惡木也。”箋:“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傳疏:“毛以秋冬爲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己適人遇惡夫也。’”經疏亦據之爲毛說:“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③《毛詩正義》卷一一之二,頁793下—794,793下。
此兩例毛傳均沒有明言詩意,而王注皆據“毛以秋冬爲昏”申說,《正義》采之。
(六)納傳入注
王注對毛傳的墨守遠甚於鄭箋。尤爲突出者,便是在串講詩意時幾乎將毛傳的訓詁原樣納入。
如《長發》“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傳云:“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爲內,諸夏爲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內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①《毛詩正義》卷二〇之四,頁1709上,1710上。
又如《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傳云:“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王肅云:“於乎美獉哉,武王之用衆也,率獉以取獉是昧。”②《毛詩正義》卷一九之四,頁1610下,1611上。都是添字將毛傳對單個字詞的解釋串聯起來,未漏一字。獉即使是毛、鄭意同,王肅的注釋也更加墨守傳意甚至傳文。
又如《東門之池》“可與晤歌”。傳:“晤,遇也。”箋:“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傳疏云:“《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③《毛詩正義》卷七之一,頁521上,下。
可見,鄭與毛意同,但用字不同,而王肅則將“遇”直接納入注中說經。
因此,王肅之述毛,頗類於兩漢經師對師法家法的恪守。在兩漢,守師法和家法都仍有自己闡述發揮的空間,④關於兩漢時期師法與家法之含義,參郭永吉《兩漢經學師法家法考》,載江林昌等主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與學術史——李學勤教授伉儷七十壽慶論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65—481。而王肅《詩》說的發揮正在其依據隱含的“規律”推測質略的毛傳之意,並補充申說,但述毛卻是發揮己意的前提。因此,其《詩》說的“異鄭”,也當從此角度理解。錢基博云:“獨太常東海王肅子雍灼知鄭箋之異毛,撰《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問難》二卷、《毛詩奏事》一卷以申毛難鄭;益闡毛義,撰《毛詩注》二十卷。”⑤錢基博《經學通志·詩志第四》,載《經學論稿》,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22。言中毛傳在鄭、王之異中的中介作用。這些從具體殘說中歸納出來的說經義例似亦可爲佐證。
但能否確定真實完整的王注也是如此嚴格地述毛呢?似不盡然。如經常作爲説明王注實事求是的例證——其釋《閟宮》“犧尊將將”之“犧尊”,傳云:“犧尊,有沙飾也。”鄭無箋。而王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利用新出土的實物改易毛說。疏引之而云:“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羲,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①《毛詩正義》卷二〇之二,頁1661下,1662上,1666下。研究者證明王肅反鄭有得時每引此爲例。如王志平《中國學術史·三國兩晉南北朝卷(上)》,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45;牟鍾鑒《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學》,載林慶彰編《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頁455;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遺籍考》,頁236等。徐中舒有《說尊彝》,證當以王肅所釋爲是,載《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640—646。
但這樣的異說只是偶一采之。顯然,即使王異毛的解釋實際還有很多,《正義》設定的“王注述毛”的剪裁機制或許也不會容下。若依上文所敍機制略作推測,則王注申毛未得其旨或可引而駁之,申毛未知孰是亦能姑且存之,但前提卻都是以“申毛”爲目的。通觀《正義》所引王注,只此一例顯與毛異。因此,還原到引書語境中的王注並不能完全代表其原本的全貌,而是經孔疏以“述毛”爲原則裁剪之後留下的殘片。但因王注本身即以“述毛”爲主,故雖是殘片,或許仍可大致近實。
四 王、鄭之爭與歷史建構
以上分析可見,與王肅《詩》注有最直接關係的是它在解經系統中服務的對象——毛傳。述毛既是王注進入《正義》解經系統的預設前提,又是它在其中擔當的最重要職責。即使寥寥幾條被輯入《毛詩問難》或《毛詩奏事》中的“難鄭”也服務於此。雖然由於《正義》主要在毛、鄭相異時,引用王注證成毛說,故鄭、王相異處甚多。但無論異同,王注與鄭箋的關係都是間接的。所謂的“王、鄭之異”似乎只是從“王述毛”與“鄭異毛”中衍生出來的。
但現有的殘片並不能等同於王肅《詩經》學在後世的影像。不能忽略的是,“鄭、王之爭”已經成爲先在的關注焦點,因此,這些殘片在後世的影像並不是對其原貌的還原,而是一種圍繞着先在焦點的拼接甚至變形。李振興在全面考察王肅《詩》注之後論斷說:“解毛多述傳意,觀夫今本《正義》所引,異說頗少。至毛不爲傳者,徵引闡發,則時與鄭不同。”①李振興《王肅之經學》第三章《王肅之詩經學》,頁318。亦可謂從微觀上得其真相。但他在結論中仍說:“王肅注經,在於與鄭氏爭名。”②李振興《王肅之經學》結論,頁780。就連贊王肅說詩“得毛意實多”的黃焯還是不忘强調其“雖有意與鄭立異”。③黃焯《毛詩鄭〈箋〉平議》序,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又言:“清儒師法鄭君,多喜掊擊王氏,實非持平之見。先從父季剛先生嘗稱王肅解詩時有勝義,所論郅允。以知孔疏往往以王義爲毛義,實非漫然從之也。”是承自黄侃。
可見,決定王肅經學之後世接受的實質上是不斷積澱的“建構性”歷史。王、鄭相異,史籍多有敍及。前引本傳明言“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但後世的漢學傳統中,鄭學地位甚高,與之立異的王學自然被置於反面,被斥爲“有意”甚或“惡意”反對鄭學。至樸學昌盛的清代尤其如此,並幾乎沿襲至今。周予同曾言:“王肅之學,過去一直爲經學家所非議,特別是清儒,不管是古文經學派、今文經學派,對他的‘混淆家法’,與‘鄭學’立異,都加責難。”④周予同《有關中國經學史的幾個問題》之《對王肅和“王學”的估價問題》,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8 3年,頁6 9 8。按,漢代經學分今文、古文兩派的觀念實則是由晚清以來逆推而强加的經學史敍述,兩漢經學實非 此般粗糙二分。參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載《錢賓四先生全集》(八)《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 9 9 8年,頁1 8 1—2 6 2。劉巍《中國學術之近代命運》第五章《經學的史學化:〈劉向歆父子年譜〉如何結束經學爭議》,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 0 1 3年,頁2 5 4—3 0 0。李學勤亦有《〈今古學考〉與〈五經異義〉》,收入氏著《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 9 9 6年,頁3 1 8—3 2 8。而下文引用前修之說時姑仍之,不復申說。
除此之外,似乎還應當加上“多造僞書”的印象。皮錫瑞《經學歷史》舉其“僞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共五書”。①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55。亦參孫欽善《中國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220—228。儘管今人通過研究和考古對此觀點有所質疑,②參王志平《中國學術史·三國兩晉南北朝卷(上)》第三章《三國時期的經學》(下)第二部分《王肅“多造僞書”考辨》,頁145—165,然尚未爲定論。但在其時,似乎是爲人公認的。
阮元手訂《詁經精舍文集》開篇所收十三篇同題之作《六朝經術流派論》,似乎可作爲反映時人對六朝經術的學術史敍述的一個窗口,徐雁平歸納了其主旨上的四點相同之處,如推崇漢學、表彰兩漢經學的師法與家法、貶斥六朝經學中的玄風與信口而談等。③參徐雁平《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上編第四章《詁經精舍的學術與文學:從阮元到俞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191。書中有對此十三篇文章的論點摘要,見頁187—191。若細化至對鄭玄、王肅的評價,則似乎也可以看到一條被衆口一詞的敍述濃墨重彩勾勒着的歷史線索:兩漢經學至鄭玄而極盛,至王肅逞其私說,與鄭相難,爲經學之一厄。兹略舉數例以見:
錢福林:“六籍之學,盛於漢代。宏敷經訓,鄭氏爲先。歲月既綿,其道用缺。此非傳世之易替,六代學士與有過焉……鄭氏沒後,王肅之徒,始與爲難。逞其邪說,多是臆造。若詞有所窒,說有不通,或妄改經文以見根據,或自爲一書以相左證。雖言繁而意達,實理疏而情漏。”①錢福林《六朝經術流派論》,《詁經精舍文集》卷一,《中國歷代書院志》(15),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16上。
胡敬:“當塗去漢未遠,師說尚存。大儒多出康成之門,羣籍未罹晉懷之亂。陸績述《易》,元本京房。王基說《詩》,義在申鄭。其最著者也。惜乎子雍無識,倡爲《聖證》之論。”②胡敬《六朝經術流派論》,《中國歷代書院志》(15),頁20上。
周中孚:“兩漢經學最重師法,各家流派,具詳於班范史傳,而鄭君康成集其大成。王肅後起,心忌其名,而欲與爭,因亦廣注羣經,力與鄭異,然其學終不足以勝之也。故自晉迄隨,王學仍不振焉。”③周中孚《六朝經術流派論》,《中國歷代書院志》(15),頁22下—23上。
洪震煊:“昔漢儒之經術,授受相承,淵源不隔。雖未盡合於微言,要亦自成爲古訓。北海鄭君出,由博返約,集其大成。竟委窮源,通於聖志。後有作者,蓋無得而加焉。自魏王肅逞欺詐之詞,張妖妄之論,暗造古文,私撰《家語》,歷誣經旨,顯斥鄭君,致學無心得者,易惑岐途。俾讀不甚解者,倒紊朱紫,餘焰至於晉代……且夫輔嗣注《易》,雖涉玄言。元凱注《左》,不無規失。要皆得自心裁,成一師說,瑕瑜不掩,疏密易見。惟習聞王肅之說者,但信其隱托聖言,不知其僞造古訓,淆亂舊章,擊排正義。明訓寖成暗室,萬古共爲長夜。罪深桀紂,竊謂不在弼而在肅矣。”④洪震煊《六朝經術流派論》,《中國歷代書院志》(15),頁26上—下。
嚴杰:“六朝以前,諸儒各守家法,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惟魏代王肅不守師承,好與高密鄭公爲難,造僞書而騰異說。”⑤嚴杰《六朝經術流派論》,《中國歷代書院志》(15),頁27上。
孫同元:“漢儒治經,各守家法,至北海鄭氏而集其成。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洎乎三國鼎峙,異說紛紜。王粲、虞翻迭有論難。然猶未能抉其藩籬也。惟魏王肅以姦人之子,氣焰方張,嫉鄭氏之名出己上,騁其才辨。僞造《家語》,又作《聖證論》以實其說,誠古今經籍之一厄矣。”①孫同元《六朝經術流派論》,《中國歷代書院志》(15),頁29下。
俞正燮亦以王肅等九人爲異端,稱其“蔑棄典文,幽沈仁義,遊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易》、《書》、《禮》、《春秋》、《論語》舊說盡亂”,且特意提出“而王肅最爲精悍,兼采馬融、賈逵之與鄭異者羅織之”。②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四“異端”條,《續修四庫全書》,1160册,頁182下。
諸人對王肅幾乎是全盤否定,認定鼎盛純正的漢代經學從他開始走下坡路。“與鄭立異”和“多造僞書”相輔相成,構成了王肅經學在經學史上的印象框架。③孫欽善總結王肅在古文獻學上特點有二:“一爲專與鄭學作對,得失兼有”,“二爲多造僞書”。《中國古文獻學史》,頁220。本來,《後漢書·鄭玄傳》說其“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④范曄《後漢書》卷三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207。但鄭玄箋《詩》卻改而宗毛,又被公認爲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正反映出他並不守專家師法。又如上文微觀所示,王肅墨守毛傳,鄭玄時有立異。但在經學史的敍述中,王肅卻成爲破壞家法的始作俑者。於是,上文列出的似可證明王肅墨守毛傳的種種“證據”被納入這樣的框架時都發生了微妙的逆轉。兹據所見,略舉數端:
1.“毛無改字”新解。
錢大昕云:“毛無破字,其說蓋出於王肅。肅欲與鄭立異,故於鄭所破之字,必別爲新義,雖自謂申毛,未必盡得毛旨也。”⑤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一五,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33。
王肅嚴格遵循的“毛無破字”的原則被認爲是爲與鄭立異,而故意自立新說,自定法則。但似乎可以對比的是,在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序》中依然提到了毛的這一原則:“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①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序》,《毛詩正義》,頁18下。
2.以三家說毛。沿用至今的例子是《小雅·車舝》“以慰我心”,《正義》本毛傳作“慰,安也”。《釋文》云:
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意。《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②《毛詩正義》卷一四之二,頁1023上。亦見《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中》,頁86下。
《正義》亦云:
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遍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③《毛詩正義》卷一四之二,頁1023上,1024上。
可見,《釋文》、王肅及孫毓所據本毛傳皆作“慰,怨也”,王肅於是“申爲怨恨之義”,仍是申毛。但因《韓詩》作“以慍我心”,“慍”與“怨”意同,故諸家遂認爲王肅是用《韓詩》與鄭立異。
朱士端云:“毛、鄭皆訓慰爲安,王肅用《韓詩》作‘以慍我心’,以違毛、鄭。凡此皆鄭所不取,而王肅獨取之,以故與鄭違。”並總結“王肅難鄭之法約有兩端:一則藉申毛傳以與鄭違;一則或用《韓詩》說以故與鄭異。《毛詩》多假借,毛無破字,鄭每破假借字讀之以易傳,鄭箋《詩》大旨宗毛,時以毛傳未安,間用三家《詩》以易傳義。然有時鄭亦不取三家說者,王肅則取三家駁鄭。”①朱士端《彊識編》卷一“鄭箋御馭通用”,頁442下。同卷“王肅《詩》注用《韓詩》”條詳述此例云:“毛傳訓慰爲安,康成申毛亦訓爲安。本繫馬融師說如此。《韓詩》云‘以慍我心’,慍,恚也。疏引孫毓、王肅皆訓慰爲怨,其意似主韓詩,王氏此條不獨難鄭,而兼難毛矣。”頁441上。《彊識編續》“王肅難鄭依舊說”條:“王肅所據以難鄭者,皆本韓、魯舊說也。”頁515上。
皮錫瑞《經學歷史》責王肅“故其駁鄭,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②皮錫瑞《經學歷史》五《經學中衰時代》,頁155。周予同注釋即舉此例作爲王肅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說之證,云:
鄭箋衍《毛詩》之古文說……但王肅從《韓詩》之今文說,改“慰”爲“慍”,云:“《韓詩》‘以慍我心’;慍,恚也。”即其一例。③皮錫瑞《經學歷史》,頁156—157。
李振興說法與周氏幾乎全同。云:
鄭箋衍《毛詩》之古文說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然王氏從《韓詩》之今文說,易“慰”爲“慍”,云:“《韓詩》‘以慍我心’,慍,恚也。”即其一例。④李振興《王肅之經學》結論,頁778—779。
且云“然而王氏若純爲駁鄭,而不顧詩義,則又謬之甚者也。宜乎《正義》之駁也。”⑤《王肅之經學》,頁415。
但回檢原文,《韓詩》云云,本是《釋文》所引,與王注無關。王注並未將經文中的“慰”從《韓詩》改爲“慍”。其解爲“怨恨”,自是據《釋文》本毛傳“怨也”申之,雖可能有參於《韓詩》,但並非以《韓詩》易毛駁鄭。
3.亂經。而謂王肅有意改竄《毛詩》之經傳以與鄭異,似始自臧琳《經義雜記》。此書雖撰成於康乾之際,爲閻若璩推重,但至其玄孫臧庸始刊行之,並廣請其時著名學者作序,乃爲世知重。①臧琳《經義雜記》卷前有《贈言校勘爵里姓氏》,列閻若璩、惠棟等三十餘位學者姓名。《續修四庫全書》,172册,頁38上—下。臧庸於全書之卷末識曰:“先考鐍藏遺稿甚固,教不孝等讀書,粗有知識,始啓篋校録,欲擇其要者付梓,由是當世學者甫知有玉林先生其人。”頁294下。
儘管是“偶有一得,隨筆記録”的“雜記”,②見臧琳《經義雜記》卷一前自序,頁39上。卻以駁王爲旨趣。臧氏自稱“驟以肅之說語學者,學者或疑爲鑿。然余閉户三十年,推勘肅之肺肝,瞭如指掌”。③臧琳《經義雜記》卷一〇“願言則疌”條,頁118上。案,卷十八,頁183完全相同,當是刻印之誤。每每情動於中,慨乎言之。
如卷一二“古之人無擇”條:
此傳的係王肅僞撰,故陸本無之。毛意當與鄭同,而《釋文》別爲毛作音,過矣。陸德明本既無此傳,孔仲達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蓋王肅既妄作此傳以與鄭相難,俗本遂承之,傳流以至今也。陸、孔在當日,必有先儒如王基、馬昭之徒辨及此者,故知此傳爲王肅語無疑。吁!舉一可以例百矣。毛詩傳先秦古書傳注中最可信者,而爲肅所亂。痛哉,痛哉!④臧琳《經義雜記》,頁133上。
卷三〇“《皇矣》傳考證”條:
據孔氏所言,知王肅既竄改《毛詩》,即私撰《家語》以合其所改。罪案見在,可覆審也。嗟乎!秦始皇焚書,賴漢初之儒而六經得如故。王肅注書,祗嫉鄭君之賢而欲岀其上,遂逞其庸妄之見,以顛倒六經。肅之罪甚於始皇,而晉唐以來儒者罕覺其謬,遂至轉相授受。多爲小人所欺,至余而灼見其弊。不得不大聲疾呼以救正之。惜余老矣,於《尙書》、《毛詩》、《禮記》三書甫啓端以折其謬,而精力未能全逮。後之人以余所考正者,類推及之,易易矣。區區開創之功,自負當步趨漢儒後,有明見卓識之士,當不以余言爲誣也。①臧琳《經義雜記》,頁280下—281上。案,阮元《校勘記》不以爲然,云:“以‘古之人’以下爲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經義雜記》不得其理,乃以《釋文》別爲毛作音爲過,又以爲《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皆非也。”《毛詩正義》卷一六之三,頁1191下。
卷二九“維此王季”條:
王肅注《毛詩》,亦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與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正經。使無識者見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及《左傳》合,鄭箋作“王季”爲誤矣。肅之伎倆心術,自唐以來無能知之者,我不得不痛切昌言之。②臧琳《經義雜記》,頁270下。按,江瀚《毛詩王氏注(嫏嬛館補校本)》提要批評“近儒佞鄭惡王成爲風氣,殆亦一偏之見也。”即舉此例駁之,其說云:“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詩毛氏傳疏》皆謂此經‘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亦云:‘此當以作文王爲正。’惟臧琳《經義雜記》,顓喜掊擊王氏,以爲‘肅好與鄭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正經’,而阮元《毛詩校勘記》遂從其說,疑誤後生。不知《禮記·樂記》引詩‘莫其德音’十句,鄭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是所見本亦作文王,何獨罪肅歟?”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詩類”,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305。
具體例子還有許多。如卷二〇“贈增也”條稱“蓋王肅改毛爲贈送以異鄭耳”;卷二九“勿士銜枚”條稱“王肅改銜爲行以與鄭異”;卷一二“曰予不戕”條稱“此必王肅妄改,以與箋義相難”;卷三〇“每懷靡及”條稱“然則‘每,雖;懷,和’之訓乃肅改《毛詩》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肅之罪,於是不可逭矣”。①依次見《經義雜記》,頁267下,275上,134下,286上—下。
通考這些論證,方式相似,結論亦一致。均是據《正義》和《釋文》中所載毛傳文字的不同版本,推定是王肅私改毛傳以合己說,與鄭相難。
臧庸校刻《經義雜記》,承其先祖之說,認爲王肅“名雖從毛,實欲異鄭”,爲“六經之蟊賊”。②臧庸《拜經日記》卷六“皇父卿士”條,《續修四庫全書》,1158册,頁99下。在其“思克紹先德”③臧庸《拜經日記自序》,頁52下。《拜經日記》前亦列有“贈言校勘里居姓氏”,遠多於乃祖。頁50上—52上。而作的《拜經日記》中分析王肅作僞的動機與過程云:
王肅好與鄭難,因改訓爲“養”以異鄭,而又恐學者致疑,復僞作毛傳以證之,使不知者見此,必以爲王得毛旨,箋失傳義矣。④臧庸《拜經日記》卷五“不我能慉”條,頁94上。
因此,也如法炮製數例。⑤臧庸《拜經日記》卷一“反予來赫”條,頁58下—59上;卷四“不吴不敖”條,頁79下—80上;“冥窈也”條,頁82上—下;卷六“曰予不臧”條,頁100上等。
從對《桑柔》“好是稼穡”一句的討論上,⑥《毛詩正義》卷一八之二,頁1388下,1389上,1391上。可略窺“王肅改《詩》說”在其時的承傳與擴大。鄭讀作“家嗇”,解爲“居家吝嗇”之人,王則申毛如字。《釋文》云:
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名(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⑦《毛詩正義》卷一八之二,頁1398上,亦見《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下》,頁97下。
如此,在《正義》中,本是毛、鄭相異,王申毛而與鄭異。但因《釋文》記載了原作“家嗇”的異文,因此,有斷定“禾”部爲王肅及從王肅之義者所加,原本毛傳與鄭相同。
臧琳云:
《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疑肅雖以“家嗇”爲“稼穡”,尚未敢遽改經字。殆後人又因肅義而改耳。①臧琳《經義雜記》卷二七“好是家嗇”條,頁258下。
朱士端亦同其說,云:
鄭於下文“稼穡卒痒”,始釋爲“耕種曰稼,收歛曰穡”,於“好是稼穡”不言耕種云者,則毛、鄭皆作“好是家嗇”可知王肅改“家嗇”爲“稼穡”,名爲申毛,實則難鄭,當依鄭說。②朱士端《彊識編》卷一“好是家嗇”條,頁443下。
段玉裁爲《經義雜記》作序,稱其“至如《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覺悟羣疑,宜百詩氏之贊嘆欲絶也”。③臧琳《經義雜記·敍録》段玉裁序,頁290上。故於所著《詩經小學》中亦承其說,云:
按鄭不云“稼穡”當作“家嗇”,則毛本作“家嗇”也。傳云:“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本,誤衍一“代”字,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也。”因曲爲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嗇”字从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祿”,語最無理,豈毛公而爲之乎?④段玉裁《詩經小學》卷三,《續修四庫全書》,64册,頁217下—218上。
段氏尚以“代”字爲王肅所見本誤衍,認爲王肅只是改“家嗇”字從禾。而臧庸爲段玉裁校刻《詩經小學》,⑤參虞萬里《段玉裁〈詩經小學〉研究》,《辭書研究》1985年第5期,頁43。卻又於旁加按語云:“鏞堂按,‘代’字即王肅所增。”⑥段玉裁《詩經小學》卷三,頁218上。更完善了王肅的“修改步驟”。
臧庸從盧文弨受學,盧氏亦認同其家學,於《龍城札記》開篇即云:
王肅不好鄭氏學,人之所見不同亦何害,乃必有意與鄭乖異。甚且不憚改經,改古人相傳之故訓,以伸其所獨見。前人固已有覺之者。近武進臧玉林著《經義雜記》摘辨尤多。其玄孫鏞堂從予學,爲予校《毛詩》、《釋文》,多本其祖之說,而其自爲說,別白是非,亦甚明確。
後舉“勿士行枚”一例則直接承自臧琳《經義雜記》之說,稱肅“今又破行爲‘行陳’,枚爲‘銜枚’。與‘樂道忘飢’語極相似,甚不可通,乃以之誣毛、鄭,不亦異乎”?①盧文弨《龍城札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後之泛化的論著每引此爲證,如辛旗《中國思想通史:魏晉南北朝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8。
暫不判斷這些說法的孰是孰非,卻不難從推理過程中看出他們都將“王與鄭難”作爲預設。又如《陟岵》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釋文》云:“王肅依《爾雅》。”《正義》認爲“當是轉寫誤也”。②《毛詩正義》卷五之三,頁430上—下,429下,431上;《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頁67上。而臧庸認爲《爾雅》誤,當從毛詩傳。於是自問自答曰:
王肅依《爾雅》者何也?好與鄭異也。鄭箋本毛傳,必與《爾雅》不同,故肅反從《爾雅》,據以難鄭,可斥鄭本之誤。唐人定本往往爲肅所誤而此獨不從肅改,亦可見肅依《爾雅》之非矣。③臧庸《拜經日記》卷五“岵兮屺兮”條,頁93下。
同樣的推理模式亦可見於朱士端之《彊識編》:
《爾雅》“倨牙”文上下必有錯簡,乃沿誤而莫之正也……然《毛詩》“六駮”傳已引《爾雅》“駮如馬,倨牙,食虎豹”之文,知其沿誤已久。惟鄭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正義》引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士端案:鄭氏亦不以毛引《爾雅》爲確,故易傳。則倨牙非即駮馬,鄭氏已疑之矣。及案《正義》引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蓋王肅自謂申毛,其實難鄭。毛傳引《爾雅》誤文乃王肅所加以難鄭,是其故智,非毛公之誤引也。①朱士端《彊識編》卷二“倨牙騶虞古叚耤通用”條,頁463上—下。
案,此指《秦風·晨風》“隰有六駮”,毛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所引爲《爾雅·釋畜》文。②《毛詩正義》卷六之四,頁503下,504上。朱氏既考證《爾雅》文字有誤,先是說見毛傳已引,知沿誤已久。但後見《正義》中引王肅之言,全申毛傳,遂改口斷定這一誤文乃王肅所加以難鄭,非毛傳原本之誤。儘管朱氏從具體經注的比較中發現了《正義》中實有鄭、王相同處,但在這裏,卻仍然以“王難鄭”作爲推理的依據,其先在的成見顯然。
由此可見,先定的印象框架決定了對王肅經學殘說的解讀傾向。無論這一印象框架是否與真實存在的王肅經學相合,是否符合當時“文獻的真實”,但它被闌入經學史,成爲後世“思想的真實”。王之有意難鄭,遂被作爲學風邪悖的象徵符號加以批判。
“自稱獨守鄭氏家法,於古今一切訓詁、一切議論,與鄭合者則然之,略有異同即黜之”的王鳴盛云:“肅於學術之中,行其忌忮,可謂小人。”③王鳴盛撰《蛾術編》卷五八迮鶴壽案語,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頁815;卷五九《鄭氏品藻》,頁848。
即使認爲“王肅之說,有是者,有非者,當分別觀之”的陳澧,①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六,頁103。仍要極力駁斥王肅:
吾之惡王肅,惡其人也,非惡其難鄭也。吾之惡王肅難鄭,惡其作僞也。若平心論辨,如鄭之駁許氏“異義”,吾豈惡之哉!江艮庭曰:“其人,小人也。”此定論矣。
又云:
王肅難鄭多矣,豈無鄭失而王得者?然王之居心爲可惡也。鄭之於毛則曰箋,於二鄭則曰贊而辨之。即使鄭有失,王但當爲之箋爲之贊辨,乃緣隙奮筆,遂欲奪席,此其居心可惡爲如何乎!然終以見惡於後世,甚矣,心術之不可揜也。朱子曰:“鄭康成畢竟是好人。”吾則曰:“王肅畢竟不是好人。”②陳澧《東塾讀書論學劄記》,《東塾讀書記》附,頁358—359。
於是自稱其著書“排王肅而尊鄭君者,欲救近時新說之弊也”。③《陳澧集·學思自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758。
當鄭、王經說異同的具體比勘化爲“王肅小人”的學風之弊,王肅經說的存佚或者所存之多少都已不復重要。是“王、鄭之爭”的框架建構了王肅《詩經》學在《詩經》學史上的具體樣貌。這一預設的框架來自於尊鄭斥王的立場,而其背後正反映了經學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
結 語
經過《毛詩正義》解經系統剪裁而存留的王肅《詩》說墨守毛傳,成爲孔疏述毛的重要參證。而在“王與鄭難”的預設框架中拼接而成的王肅《詩》說則是存心立異,敗亂家法,成爲清代經學家的集矢之的。“述毛”只是王肅《詩》說剪裁後留下的殘片,儘管這些殘片大體仍是接近原貌的。“難鄭”則是其在經學史敍述中呈現的影像。無論“殘片”還是“影像”,都滲透了經學史發展的印迹。
(本文作者係南京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