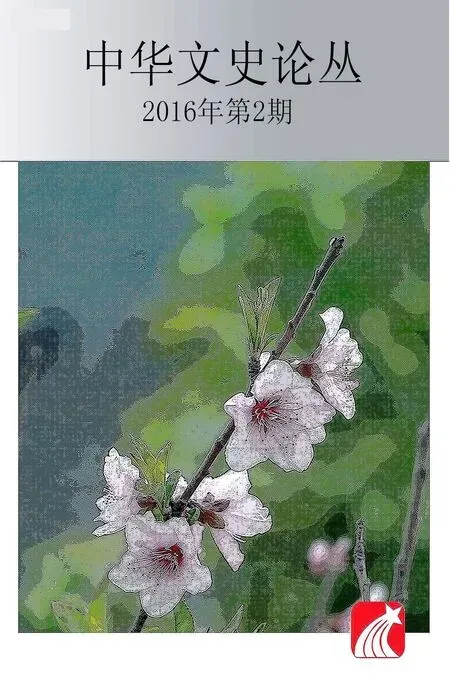《周易略例》的略例
——王弼思想再探討
劉康德
《周易略例》的略例
——王弼思想再探討
劉康德
魏晉玄學家王弼的《周易略例》一直被學界作二類理解。一類將《周易略例》作爲王弼對《周易》的若干體例的理解,可謂就易學而易學(如朱伯崑先生)。另一類將《周易略例》理解爲王弼掃除漢易象數學而提出的魏晉新易學,可謂對《周易略例》作哲學的分疏(如余敦康先生)。本文則對王弼的《周易略例》作別樣的理解,將《周易略例》置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考察,用魏晉時期的事例印證其觀點,指出理論學說——王弼《周易略例》中的若干觀點與時代背景是可以互相批注的。本文對《周易略例》的解釋,有別於作過實(就易學而易學)的疏理,也有別於作過虚(哲學上的疏理)的解釋。
關鍵詞:王弼 《周易略例》
一 王弼的《周易略例》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今河南焦作市)人。生於黃初七年(226),卒於嘉平元年(249)。爲魏晉玄學的創始人之一。
對於王弼的家族及學術淵源,余嘉錫先生的《世說新語箋疏》有敍述。《箋疏·文學》第6則引焦循《易餘籥録》一曰:“劉表以女妻王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凱爲王粲族兄,粲二子被誅,業爲粲嗣。然則王輔嗣爲劉表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也。劉表爲荆州牧,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宋衷等撰定《五經章句》。表撰《易章句》五卷,衷注《易》九卷,弼兄宏字正宗亦撰《易義》(原注見《釋文》)。王氏之於《易》,蓋淵源於劉表,而表則受學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劉表、王業皆山陽高平人。”①《世説新語箋疏》上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97—198。
王弼治《易》學,除注《周易》外,還撰有《周易略例》。潘雨廷先生認爲:“著此卷(《周易略例》)時,宜先於注《周易》,蓋爲注《易》之例也。今以(王弼)二十歲論,即廢帝乙丑(245)”。②潘雨廷《讀易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4。潘雨廷先生認爲王弼《周易略例》之先於《周易注》,“蓋爲注《易》之例”。但也有可能是王弼注了《周易》後,對《周易》的體例有了深刻的體會,再撰《周易略例》的。其後,唐邢璹對《周易略例》作注釋。③邢璹說:“王輔嗣《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順之理,應變情僞之端,用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神,匡濟邦家,推辟咎悔”(《周易略例》序)。對於邢璹其人,按潘雨廷先生說來:“璹,玄宗時人,始末不甚詳,自署爲四門助教,《唐書》以鴻臚少卿稱之。《太平廣記》載其曾奉使新羅,賊殺賈客百餘人,掠其珍貨,貢於朝。其人殊不足道,蓋媚上之佞臣也。”對其《周易略例》之注,潘雨廷先生又說:“邢氏之《注》,依文解之而已,無足輕重。”《讀易提要》,頁4 4—4 6。邢璹的《周易略例》注釋,我們能很方便地在樓宇烈先生的《王弼集校釋》一書中找到。
對於《周易略例》一書的性質,朱伯崑先生在《易學哲學史》一書中作如是說:王弼“《周易略例》一書,就是講他對《周易》體例的理解,實際上代表他的易學觀”。
基於這樣的判斷,朱伯崑先生在《易學哲學史》中對王弼的《周易略例》中的《明彖》、《明爻通變》、《明卦適變通爻》、《明象》、《辯位》等文作了一一梳理,得出其中王弼易學思想爲:“取義說”(得意忘象)、“一爻爲主說”、“爻變說”、“適時說”、“辯位說”等。①參閱朱伯崑先生《易學哲學史》上册第四章《魏晉玄學派的易學哲學》第一節王弼《周易注》和《周易略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236—270。同樣,朱伯崑先生的這種分析梳理離不開邢璹的注釋,留有邢璹的深刻影子。朱伯崑先生對於王弼《周易略例》的分析梳理,離不開其易學範圍,可謂就易學而易學。
可能出於對這樣的分析梳理的不滿意,余敦康先生在《漢宋易學解讀》一書中另闢新徑,認爲“王弼在這部著作中對《周易》的編纂體例、卦爻結構及其哲學功能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猛烈抨擊了漢易的象數學的思維模式,爲義理派的新易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基於此,余敦康先生在其著作中對這種“義理派”的學說作了哲學上的分疏、解釋。②參閱余敦康先生的《漢宋易學解讀》上篇《漢代易學》附録王弼的《周易略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頁103—125。
那麽,對《周易略例》的解釋,是不是還存在着別樣的途徑?因爲,按照一般學理來說,任何著作的產生,必定與其產生的時代存在着密切的關係,即理論學說與時代背景是可以相互批注的。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提到的若干看法、觀點必定是對當時時代環境的總結與概括。時代背景也必定可以爲王弼《周易略例》中的若干看法、觀點作注腳的。
以下讓我們舉若干例子爲其作注。故本文定名爲《〈周易略例〉的略例》。
二 《周易略例》的略例
本文敍述體例爲:先將王弼《周易略例》中的若干觀點、看法列出,然後舉時代事例爲其作注。因爲不是列出王弼的全部觀點,所以稱之爲“略”;舉時代事例印證其觀點、看法,所以稱之爲“例”,即“《周易略例》的略例”。
1.治衆者,至寡者也。①邢璹注曰:“萬物是衆,一是寡。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少以治之也。”樓宇烈先生按《易》理解釋爲:“衆,就卦象而言,指六爻;泛言之,則指萬事萬物,百姓庶民。至寡,就卦象而言,指起主導作用的那一爻;泛言之,則指萬事萬物之總根,最高統治者。”《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591,592。
東漢末年至魏晉,由於社會矛盾尖銳,伴隨着農民起義的發生,中央掌控州、郡的能力進一步削弱,各地掌握各種資源的刺史、郡守紛紛擁兵自立,形成割據狀態。這些擅兵的軍事集團爲了利益互相混戰。先是宦官(如蹇碩、段珪等),與外戚(何進)的鬥爭;繼而掌控西北軍的董卓進京。龐雜的西北軍進京後“淫略婦女,剽擄資物,謂之‘搜牢’”;②《後漢書·董卓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325。隨即袁紹聯合曹操起兵討伐董卓,董卓被王允所殺之後,董卓部將李傕、郭汜聯合發兵殺王允,並彼此間爲爭權奪利而互相殘殺,這些部將“放兵劫略,攻剽城邑”導致“人民飢困……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③《三國志·魏書·董卓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83。以後,曹操又以青州兵自立,與呂布、袁紹、袁術、劉備、孫權等軍事集團展開戰爭。
軍事集團之間的混戰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說:“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英雄記》又說:劉備“軍在廣陵,飢餓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①《三國志》卷一,頁14;卷三二,頁874。
伴隨着軍閥混戰的是,當時中原一帶還流傳着一種可怕的瘟疫,導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②《太平御覽》卷七四二引曹植《説疫氣》,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3294下。社會處於分崩離析之際。
對於諸多軍事集團混戰所帶來的社會苦難,王弼有所感受。作爲思想家的王弼首先想到的是要剷除“諸多”——只有剷除諸多不利於社會安定的集團,社會纔能太平安定。作爲哲學家的王弼又思辨地認爲要剷除“諸多”集團,絕對不能以“諸多”來剷除“諸多”,正所謂“存者不以存爲存”,“安者不以安爲安”。③王弼《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釋》,頁197。剷除“諸多”的只能是它的反面:“至寡(少)”,也即王弼在《老子指略》中的說法,“不忘亡者存”,“不忘危者安”。這也如同《周易·繫辭下》說的那樣:“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④《周易正義》卷八,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88中。以此類推,“治多者”必定是“至寡(少)”。據此,王弼希望社會中能出現少數能人、强者、精英(至寡者)來治理、剷除“諸多”不利社會安定的集團。於是,王弼提出“治衆(多)者,至寡者也”的想法。⑤《周易略例·明彖》,《王弼集校釋》,頁591。
對於“治衆(多)者,至寡(少)者”的想法,在當時還成爲社會的共識。如《世說新語·識鑑》說:“曹公(操)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亂世之英雄。’”①《世説新語箋疏》,頁382。換成《三國志》的說法是:“子(曹操)治世之能臣。”②《三國志》卷一,頁3。在王弼他們看來只有少數(至寡)英雄纔能剷除諸多利益集團,纔能治理動亂的社會。
王弼同時又將這種政治局面稱之爲“統之有宗,會之有元”。③王弼《周易略例·明彖》,頁591。樓宇烈先生解釋爲:“‘會’,合,亦即統制之意。‘元’,通‘原’,亦即‘宗’、‘主’之意。”頁593。《老子·四十七章》王弼《指略》:“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其歸同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王弼集校釋》,頁126。邢璹注:“統領之以宗主,會合之以元首。”頁593。而這種政治局面同樣又是當時人們所期盼的,就連名士龐統名統字士元,互爲表裏的名與字(統、元)期盼着社會能“統之有宗,會之有元”。
而“亂世之英雄”、“治世之能臣”的曹操確在這軍閥混戰中勝出。正如諸葛亮所說的那樣:“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④《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912。
以弱勝强的曹操在這過程中(如官渡之戰前後),做到了如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中說的那樣:“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⑤《周易略例》,頁6 0 4。“雖遠而可以動者……”下邢璹注:“上下雖遠,而動者有其應。《革》六二去五雖遠,陰陽相應。往者無咎也。雖險可以處者,得其時也。《需》上六居陰之上,不憂入穴之凶,得其時也。”頁6 0 6。“弱而不懼於敵 者……”下樓宇烈先生解釋爲:“‘據’,位。‘得所據’,指得其位。‘附’,依附。‘得所附’,指所依附者得當。”邢璹注:“《師》之六五,爲《師》之主。體是陰柔,禽來犯田,執言往討,處得尊位,所以不懼也。《遯》九五:‘嘉遯貞吉’,處遯之時,小人侵長,君子道消。逃遯於外,附著尊位率正,小人不敢爲亂也。”頁6 0 7。“柔而不憂於斷者……”下邢璹注:“體雖柔弱,不憂斷,制良由柔御於陽,終得剛勝,則《噬嗑》六五:‘噬乾肉得黃金’之例。”頁6 0 7。曹操將那些不利條件都轉化爲有利條件,最終完成“以弱爲强”、“挾天子而令諸侯”,所以諸葛亮說他“非惟天時,抑亦人謀”。
相對於“衆多”的“至寡”,王弼又將此(至寡)理解爲“一”。①這“一”,如《老子·二十二章》說:“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老子·三十九章》又說:“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老子道德經注》,《王弼集校釋》,頁56,106。《世說新語·言語》中有一段說法是對此最好的注腳:“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頁81。這“一”的功能與上述一樣,“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②《周易略例·明彖》,頁591。邢璹注:“天下之動,動則不能自制。制其動者,貞正之一者也。《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然則一爲君體。君體合道動,是衆由一制也。制衆歸一,故靜爲躁君,安爲動主。”頁593。王弼注解爲:“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也。”《老子道德經注》二十六章,《王弼集校釋》,頁69。“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③邢璹注:“統而推尋,萬物雖殊,一之以神道,百姓雖衆,御之以君主也。”《王弼集校釋》,頁594。這裏的“一”即至寡,從字理層面理解爲“宗”(道)、“元”(無),從(社會)實際層面理解爲“君”(主)。
這樣,這“至寡”、“宗”、“元”和“一”便被王弼處理成同一層面上的概念。這在王弼的《老子指略》中也有表現:“明侯王孤寡之義,而從道一以宣其始。”孤寡、侯王、君主是可以治衆(多)、制動(蕩)、御雜(亂)的。在此基礎上,青年才俊王弼用哲學的語言來表述:“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④《周易略例·明彖》,邢璹注:“明至少(至寡)者多之所主。”《王弼集校釋》,頁591,595。
有了這“至寡”、“宗”、“元”和“一”,王弼以爲可以“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①《周易略例·明彖》,頁591。邢璹注:“天地雖大,睹之以璇璣;六合雖廣,據之以要會。天地之運,不足怪其大,六合輻輳,不足稱其多。”樓宇烈先生解釋爲:“‘會要’,綱領,樞紐。‘方來’,指即將到來的變化。‘六合’,上、下、四方(東、南、西、北)稱六合,意指整個宇宙。‘輻輳’,向中心聚集。”頁595。正可謂社會再亂也不可怕。換成另一說法是:“品制萬變,宗主存焉”,邢璹注:“品變積萬,存之在一”。
這裏,王弼又將此與學理性質的《周易》相聯繫。因爲《周易》的《易傳》中的《彖》正好有此功能。於是王弼作《周易略例·明彖》來表述上述的觀點:“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這就是說,《彖》的功效就是總論一卦之意、斷定一卦之義。所以王弼斷言:“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即認爲看過《彖辭》,就能了解它的意思,掌握它的綱領。王弼認爲這是“以簡御繁”的關鍵:“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②《周易略例·明彖》,頁591,592。另,“簡約”也就成爲魏晉社會崇尚的原則。表現在“清談”上,强調“清辭簡旨”,“以簡應對之煩”……表現在“學問”上,强調“南人學問,清通簡要”。分見《世説新語箋疏》,頁498,100,216。王弼還煞有其事地闡述“衆多與至寡”即一與多的關係:“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 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③《周易略例·明彖》,頁591,邢璹注:“《同人》、《履》、《小畜》、《大有》之例是也。”如《同人》卦,六爻中六二爻爲陰爻,所以王弼說:“(六)二爲同人之主”,即是說,《同人》卦的“和同於人”之卦義是由六二爻所決定的。“(一卦)五陰而一陽,一陽爲之主矣”,邢璹注:“《師》、《比》、《謙》、《豫》、《復》、《剝》之例是也。”頁596。如《謙》卦,六爻中九三爻爲陽爻,所以王弼說(九三陽爻)爲“衆陰所宗,尊莫先焉”,即是說,《謙》卦的“勤勞謙虚”之卦義是由九三爻所決定的。“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④《周易略例·明彖》,頁591。“六爻相錯”,指爻,爻位與陰陽,剛柔互相間的關係。“可舉一以明也”,指可舉出六爻中的起主導意義的一爻來確定其卦的意義。
然而,這一切在我看來,王弼借《明彖》闡發的“衆多與至寡”即一與多的關係,其意向指向的還是他所處的魏晉社會,希望英雄、精英、能者(至寡)來治理這繁亂、動蕩的社會。這大概就是後人注意到的王弼著作中的“切人事,明義理”的部分。這就像皮錫瑞在《經學通論》中所說的那樣:“孔子之易,重在明義理,切人事。漢末易道猥雜,卦氣、爻辰、納甲、飛伏、世應之說,紛然並作,(王)弼乘其敝,掃而空之,頗有摧陷廓清之功。”①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5。
如此,則將王弼的《周易略例》只當成《周易》之體例來理解,可能是誤讀了《略例》,虧待了王弼。士大夫們均熟知的《周易》體例,王弼有必要喋喋不休地復述嗎?
2.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②《周易略例·明象》,頁609。原本乾卦(含義剛健),與馬(神彩俊健)對應;坤卦(含義柔順)與牛(神態柔順)對應。在王弼看來,只要合乎剛健之含義的,就不必拘泥於馬這一具體的物象;只要合乎柔順之含義的,就不必拘泥於牛這一具體的物象。
我們知道,在正常的社會下,倫理道德規範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必定一一對應,這就像“乾卦對應馬,坤卦對應牛”一樣,不容錯位。只有這樣,社會纔能維繫下去。
然而,漢魏期間的動亂,導致一切錯位,按名士孔融說,“古者敦庬,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末世淩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上失其道,民散久矣”。③《後漢書·孔融傳》,頁2266。這樣,導致社會政治倫理錯亂,不一致隨處可見。《世說新語·言語》就說到這一事例: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寔)。客有問元方(陳紀):“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④《世說新語箋疏》上卷上,頁59。這是說,“高明之君”不該“刑忠臣孝子”。現在刑了則說明社會政治倫理發生了錯位,即“善惡顛倒”、“好壞錯位”。這用漢魏名士邊文禮(邊讓)的話來說是:“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①《世說新語箋疏》上卷上,頁55。用魏晉名士阮籍的話來說:“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②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65。
社會政治倫理的錯位,導致士人言行放蕩。如路粹告孔融的罪狀是“不遵朝儀,秃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③《後漢書·孔融傳》,頁2278。
這種社會倫理道德錯位下的言行,給人帶來的只能是驚愕。耳聞目染這一切的王弼在驚愕之餘,從他的知識體系中提取出《周易》,修正了他原有的《周易》知識,將原本一一對應的“乾卦對應馬,乾卦對應牛”鬆綁,提出:“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何必坤乃爲牛”,“何必乾乃爲馬”。言下之意,“乾不必對應馬,坤不必對應牛”,乾既可對應馬,也可對應牛或其他,坤既可對應牛,也可對應馬或其他。理論上的鬆動是爲了適應現實上的變動,容忍現實中的怪事。原本儒家倫理中的父子、母子怎可比作父子是“情慾發耳”,母子是“寄物瓶中”的關係,現在既然理論上作了鬆動,那麽現實中也就不得不接受、容忍這樣的言行事實,並將這種道德變異比喻成“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④《世說新語箋疏·任誕》說:“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頁742。
漢魏動亂的社會激蕩世事多樣,奇事怪事層出不窮,所謂“魏晉風度”即如此。層出不窮的奇事怪事又進一步衝擊人們原有的倫理道德,固執於一一對應的倫理事項也就難以維繫下去了。正所謂“禮豈爲我輩設也”。①《世說新語箋疏·任誕》說:“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頁731。於是,人們紛紛改換門庭,奉行寬容度大的無規定性理念——老子“貴元”理論,導致老莊思想在魏晉期間的流行。
王弼還進一步修正他的《周易》思想。《周易》原本是這樣表述的:“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象生於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②《周易略例·明象》,頁609。這其中一一對應,環環相扣。而現在因政治倫理道德的錯位,必定不一一對應,於是出現了新事物、奇事理,接受、容忍新事物、奇事理,就必定要將這環環脫節,一一鬆綁,化解之間的邏輯關係。這樣,也就有了王弼的“忘象”、“忘言”說,即“得意忘象”;反過來“得象忘意”也成立,即原本思想意識形態下不允許出現的言行,現在出現了,每個人在這樣一種社會現象面前總得選擇:選擇原有意識形態,排斥新現象,意味着與社會發展相脫節,即“得意忘象”;選擇承認新現象,意味着與原有的意識形態相決裂,即“得象忘意”,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總之,不管是“得意忘象”還是“得象忘意”,不必一一對應的狀況出現,揭示了魏晉社會與以前社會的不一樣。
比如,棗子原本對應“食用”,現在卻可用來“塞鼻”。如“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③《世說新語箋疏·紕漏》,頁910。
又如,原本是“欣悅則肥,憂慘而瘦”,現在“無所憂”卻非但不肥,反而“清瘦”。按魏晉名士周顗說來:“吾無所憂,直是清虚日來,滓穢日去耳。”①《世說新語箋疏·言語》,頁92。
再如,名馬“的盧”害人,②《世說新語箋疏·德行》注引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頁33。但現在卻“救人”。《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松之注引《世語》說:“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躍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③《三國志》卷三二,頁876—877。
還有,酒醉誤事,現在卻酒醉成事。《世說新語·任誕》說:“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吴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④《世說新語箋疏·任誕》,頁745。
再有,半夜雞鳴原本被認定爲不祥之兆,現在則被素有大志的劉琨、祖逖視爲“非惡聲也”。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賞譽》注說:“《開元占經》百十五引京房曰:‘雞夜半鳴,有軍。’又曰:‘雞夜半鳴,流血滂沱。’蓋時人惡中夜雞鳴爲不祥。逖、琨素有大志,以兵起世亂,正英雄立功名之秋,故喜而相蹋。且曰:‘非惡聲也’。”⑤《世說新語箋疏·賞譽》,頁446。
諸如此類,均出現在不必一一對應的社會狀況之下。如此,則可以作這樣的界定和概括:一一對應(乾對應馬,坤對應牛),除了使社會規範、有章可循外,還必然導致社會僵化凝固;不必一一對應(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除了使社會失去規範、無章可循外,倒還可以使社會豐富多彩。魏晉風度的魅力亦表現在此。
不必一一對應的後果則是“無可無不可”。《世說新語·言語》說到:“王中郎(王坦之)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①《世說新語箋疏·言語》,頁132—133。
“無可無不可”的邏輯力量導致別樣的說法則是“什麽都是好的”,它的反面則是“什麽都是壞的”。《世說新語·言語》劉孝標注引《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鑑識,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諮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②《世說新語箋疏·言語》,頁67。什麽都是好的,不反映任何信息,實在是這種不必一一對應的社會現象下的語言表現。至此,魏晉風度的消極影響暴露無遺。
王弼借《周易》中的卦爻著《周易略例·明爻通變》和《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來言說魏晉社會的變化。但對於出自禮教家庭的名士王弼來說,其思想深處認爲社會儘管變化極大,但總有些穩定不變的東西存在着。這在他的《明卦適變通爻》中就有表述:“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③《周易略例》,頁604。邢璹注:“時有吉凶,不可越分輕犯也。”“動靜適時,不可過越而動。”頁608。“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①《周易略例》,頁604。邢璹注:“吉凶之始彰也,存乎微兆,悔吝纖介雖細,不可慢易而不慎也。”頁609。這“六不可”反映了王弼對封建社會穩定的嚮往。
3.用無常道,事無軌度。②《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頁604。它與“動靜屈伸,惟變所適”相聯繫。邢璹注:“卦既推移,道用無常;爻逐時變,故事無軌度。動出靜入,屈往伸來,惟變所適也。”頁606
王弼所處的魏晉時期,社會從未真正消停過動亂。《晉書·李重傳》說:“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事體駁錯,與古不同。”③《晉書》卷四六,頁1309—1310。戰爭還導致“家無完堵,地罕包桑”。④《隋書》卷二《高祖紀下》,頁35。如此社會,人之處世行事又怎會有“常道”、“軌度”?這社會又怎會有“典要”、“法制”及“度量”?所以,目睹耳聞這一切的王弼在《明爻通變》中總結說,“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巧歷(曆)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爲之典要”,⑤《周易略例》,頁597。在動亂的社會中,是難以產生“法制”和“度量”的。就是產生了所謂的“法制”和“度量”,也是難以消停這動亂的局面的,難以做到社會的“均和”和“齊一”。即使再聰明的人、再精密的(曆)法也是如此。對此,邢璹注:“萬物之情,動變多端,雖復巧歷(曆)聖明,不能定算其數,制典法、立要會也”,“雖復法制度量,不能均齊詐僞長短也。”頁599。故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人也只能“動靜屈伸,惟變所適”,導致善變多元,巧僞多端。阮籍借《獼猴賦》說:“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兮”,“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⑥陳伯君《阮籍集校注》,頁44。王弼將此歸爲“情僞”,即變化無定。這樣,我們也就能理解王弼所說的:“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⑦《周易略例·明爻通變》,頁597。
於是,社會的變化與人的變化處在互動中。社會急劇變化導致人之“情僞”產生,人之“情僞”,即善變多元,巧僞多端反過來使社會生態進一步變壞惡化。一部三國史就是人之計謀、權術的鬥爭史。
處於魏晉社會急劇變化這一現實中的王弼,感受到這變化的深刻,他將此與學理中的“變化”相結合,找到了傳統文化中言說變化的《周易》,將《周易》卦爻變化作爲其載體,寫就成《周易略例·明爻通變》和《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①如《周易略例·明爻通變》說:“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頁597。又如《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說:“爻者,適時之變者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頁604。真正完成理論與現實的結合,也因此使我們能將時代現實與理論學說作相互批注,從而使我們領悟:對於《周易略例》,就不能將它僅僅作爲論述《周易》體例的文章來解讀。
4.形躁好靜,質柔愛剛。②《周易略例·明爻通變》,頁597。邢璹注:“故《歸妹》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四體是震,是形躁也;愆期待時,是好靜也。《履》卦六三:‘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兑》體是陰,是質柔也:志懷剛武,爲於大君,是愛剛也。”頁599。
這大致是說,表現出來是躁動的,而其本性卻是好靜的;體質雖然柔順,而其志向卻是剛健的。引申開來說,是指人之內外表現不一致。
這在魏晉人物中就有例證。如袁紹,《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說:“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又如劉表,《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說:“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③《三國志》卷六,頁201,213。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動亂之際的魏晉人的善變多元,巧僞多端。
這種“形躁好靜,質柔愛剛”的多元性格在東晉名士郗鑒身上也有表現。《世說新語·品藻》說:卞壼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對此,劉孝標注曰:“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①《世說新語箋疏·品藻》,頁517。
5.合散屈伸,與體相乖。②《周易略例·明爻通變》,頁597。邢璹注:“《萃》卦六二:‘引吉無咎。’《萃》之爲體,貴相從就。六二志在靜退,不欲相就。人之多僻,己獨處正,其體雖合,志則不同,故曰‘合散’。《乾》之初九:‘潛龍勿用。’初九身雖潛屈,情無憂悶,其志則申,故曰‘屈伸’。”頁598。朱伯崑先生在《易學哲學史》上册第四章第一節王弼《周易注》和《周易略例》中解釋說:“‘合散屈伸’,指爻義的變化,有合有散,有屈有伸。‘體’,指一卦之體,即卦義。王弼認爲,爻義的變化,有時同其卦義相乖背。按邢璹注,如《萃》卦,兑上坤下,此卦之體,上悅下順,乃合順聚會之義。可是,六二爻辭說:‘引吉無咎。’……此是說,六二爻居下卦坤體之中位,而又當位,雖處聚會之體,但不願隨順別人,己獨處正,人雖多僻,而志在靜退。此即合中有散,與衆不同,所以說‘與體相乖’。又如,《乾》卦初九爻辭說:‘潛龍勿用。’……是說,‘潛龍勿用’,乃處於潛屈之時,可是並不因此而動搖自己的志向,按王弼的觀點,即屈中有伸,此亦是‘與體相乖’之義。”頁255—256。
按朱伯崑先生解釋:“體”爲卦體,即“卦義”;“合散屈伸”是指爻義之變化——“有合有散,有屈有伸”。如《萃》卦之義爲聚合,但《萃》之六二爻卻志在靜退,不欲相就,與衆相異,此謂“合中有散”。這說明一卦體(卦義)“有合有散,有屈有伸”之(爻)變化。引申開來說:一之本體,並不單一、純粹,它融“合散”、“屈伸”(多元)於一體,類似平時說的“一之雜多”。以此指向魏晉人物,也即表現多元多重,可融儉嗇、汰侈於一身(如殷仲堪),也可集貪、廉於一體(如王戎)。
又如殷仲堪,《世說新語·德行》說:“殷仲堪既爲荆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①《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42。如此儉嗇。然而,《晉書·殷仲堪傳》卻又說:“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②《晉書·殷仲堪傳》,頁2199。又是如此汰侈。所以余嘉錫先生說:殷仲堪“儉於自奉而侈於事神”。③《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43。正是集儉嗇與汰侈於一身。對於這種融多元(儉與侈)於一體自身,殷仲堪自己也認可,說:“乃得可盡,何必相同?”④《世說新語箋疏·文學》,頁241。認爲事體、物性並非單一、純粹,《齊物》未必真“齊物”,按王弼說來是“體質不必齊”。
又如王戎,《世說新語·德行》說:“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⑤《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23。其形象清廉得可愛。《世說新語·儉嗇》又說:“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劉孝標注引《晉陽秋》說:“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⑥《世說新語箋疏·儉嗇》,頁873,874。其形象又貪婪得可憎。正是集貪、廉於一體。
這種集諸多如貪與廉、儉與侈等於一體自身,在當時還成爲名士們的共識,表現在品評、賞譽人物時就是如此。如《世說新語·品藻》說:“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⑦《世說新語箋疏·品藻》,頁502。言下之意,龐統(龐士元)認爲自己能集世俗浮沉與王霸倚仗於一體。
《世說新語·品藻》又說:“明帝(司馬昭)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①《世說新語箋疏·品藻》,頁513。言下之意,謝鯤認爲自己既能穿朝服出入朝廷,也能脫朝服隱於山林(一丘一壑)。
《世說新語·品藻》還說:“明帝問周伯仁(周顗):‘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庾亮)?’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②《世說新語箋疏·品藻》,頁516。言下之意,周顗能集蕭條方外(隱居)與從容廊廟(從政)於一身。
“融多元於一體自身”的魏晉說法則是“兼有諸人之美”。如《世說新語·品藻》說:“時人道阮思曠(阮裕):‘骨氣不及右軍(王羲之),簡秀不如真長(劉惔),韶潤不如仲祖(王濛),思致不如淵源(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③《世說新語箋疏·品藻》,頁519—520。
又因爲“融諸多於一體自身”,所以東阿王曹植能將“融多元於一體”的大豆分解爲“豆、豆豉、豆秸”等而作成七步詩:“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④《世說新語箋疏·文學》,頁244。
6.體與情反,質與願違。⑤《周易略例·明爻通變》,頁597。對於“體與情反”,朱伯崑先生接邢璹的話頭說:“《歸妹》卦,震上兑下,上動下悅,其卦體爲悅而動。可是九四爻辭說:‘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是說,靜待婚期的到來,此即‘體與情反’。”對於“質與願違”,朱伯崑先生同樣接邢璹的話來說:“《履》卦,乾上兑下,按《彖》文義爲‘柔履剛’,乾爲剛,兑爲柔。可是六三爻辭說:‘武人爲於大君。’六三居柔兑之體,其志又在剛武。此即‘質與願違’。”《易學哲學史》,頁256。
此句大致是說,事體的本來與結果相反、相違。《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曰:“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爲所害。”①《三國志》卷一,頁3。這是說,靈帝建寧元年(168),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原本密謀誅殺閹官曹節、王甫等,不料密謀洩露,結果陳蕃被執,死於獄中,竇武兵敗自殺,整個東漢末期就是一個士大夫官僚、外戚、宦官不斷相互鬥爭、謀殺、擅政的時期。這就是“體與情反,質與願違”。
這種情形,與王弼的下一說法相似。
7.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②《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頁604。邢璹注:“一時有《大畜》之制,反有天衢之用。一時有《豐》亨之用,反有羈旅之凶也。”樓宇烈先生說:“‘制’,止。此句意爲,‘制’與‘用’,‘吉’與‘凶’,發展到一定時候會互相轉化。如椆《大畜》,從整個卦講是大止(制)之時,然而發展到上六,則變爲‘天之衢’,大通。……又如椫《豐》,……可是發展到它的反面椬《旅》,則有羈旅之凶。”頁605。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說:“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③《三國志》卷一,頁5。這就是一時以爲不錯的善的好的主意(召董卓進京),結果卻是惡的凶的(京城大亂)。所以王弼說是:“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對此,還是曹操認識清晰、正確,聞召董卓進京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④《三國志》卷一裴注引《魏志》,頁5。
魏晉時期就是這樣的活劇不斷上演。如三國建安十六年(211),益州劉璋原想引劉備入蜀來穩定益州政局及消滅五斗米道的張魯,結果非但沒有達到原來的目的,反而被劉備獲取了益州,劉璋自己做了劉備的俘虜。這正是“可反而用也”,“可反而凶也”。
西晉“八王之亂”之際,諸王在混戰中皆利用少數民族的貴族來爲自己服務,但結果往往是“反而用”,“反而凶”。如成都王司馬穎引匈奴劉淵爲外援,於是匈奴貴族長驅入鄴;東瀛公司馬騰引烏桓羯襲司馬穎,於是烏桓長驅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遼西鮮卑攻鄴,“鮮卑大掠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①《晉書·王沈傳子浚》,頁1147。中原大地成了匈奴、鮮卑貴族的統治世界。魏晉南北朝時期不斷上演着“反而用”,“反而凶”的活劇。
8.近不必比,遠不必乖。②《周易略例·明爻通變》,頁597。樓宇烈先生說:“‘比’,親。‘乖’,離。邢璹注‘近爻不必親比,遠爻不必乖離。《屯》六二、初九爻雖相近,守貞不從;九五雖遠,十年乃字,此例是也’。”王弼注《周易·屯卦》六二爲“志在乎五,不從於初”。故“六二”與“初九”,爻“近不必比”;而“六二”與“九五”,則爻“遠不必乖”。《王弼集校釋·周易注》,頁235。
這是說,靠得近的、關係密切的,卻未必相親相助;離得遠的、關係不密切的,卻未必相背相惡。《三國志·蜀書·劉封傳》說:“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劉)封、(孟)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這就是說,同屬一個利益集團,且相互間關係密切的劉備義子劉封,對處於危急時刻的關羽就是不施援手——“近不必比”。而劉封也因不救關羽,受先主劉備的責怪,加之“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③《三國志》卷四〇,頁991,994。“比”除在《周易》中有特定的含義外(如一卦六爻之比爲:初、二爲比,二、三爲比,三、四爲比,四、五爲比,五、上爲比。逐爻相連並列者爲“比”)。“比”在傳統文化中還有“比較”的意思。如《世說新語·品藻》說:“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方”爲“比”,引申爲“比方”,有“比如、比喻”之意。頁505。《品藻》又說:“王夷甫(王衍)以王東海(王承)比樂令(樂廣),故王中郎(王坦之)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頁510。
這種“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在魏晉時期還有表現。如《世說新語·黜免》說:“桓公(溫)坐有參軍椅(掎)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①《世說新語箋釋·黜免》,頁866。這是說,同類一桌人同盤共食,某人用筷子挾取(掎)食物有困難時,其他人也不相助,桓溫看不過去,發出“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這樣的感嘆,可謂與“近不必比”同調。
同樣,對於“遠不必乖”,《世說新語·識鑑》說:“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於時朝議遣(謝)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郗)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嘆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②《世說新語箋疏·識鑑》,頁403—404。這是說,郗超和謝玄關係不好(或許與他們父輩的恩怨有關),離得很遠,郗超完全可以借桓溫之手殺謝玄,但在謝玄北伐之際,郗超表現並不背乖,力排衆議,促謝玄北伐,成就其肥水戰爭之勝利,有“遠不必乖”意味。
9.應者,同志之象也。
此語邢璹注解得很通俗:“得應則志同相和。”③《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頁604,606。以史證之:“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④《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25—26。對此,顧榮“乃悟而嘆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虚言哉!’”⑤《世說新語箋疏·德行》注引《文士傳》,頁26。也可謂“志同相和而得應也”。
《周易》中的“應”,如具體說來,這“應”必與“位”相聯繫。我們知道,與一卦六爻相對稱的是“六位”:初、二、三、四、五、上。所以王弼說:“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有了這“六位”,處“六位”之上的“爻”就有了相對應的關係,其中“初、四相對應,二、五相對應,三、上相對應”。對應之爻爲一陰一陽(不同類)則交感相應,對應之爻均爲陽或均爲陰(同類)則無感應。也正因爲處於這樣一種“爻相應”(初、四,二、五,三、上),所以王弼說“應”(就空間而言)是“高下不必均”。①《周易略例·明爻通變》,頁597。邢璹注曰:“初四,二五,三上,同聲相應,不必均高下。”頁600。又因爲一卦六爻融時空於一體(初指時間,以概其終;上指空間,以括其下),所以“高下不必均”也必然隱含着(就時間而言)“遠近不必均”這一點。所以王弼說“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②《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頁604。邢璹注:“上下雖遠,而動者有其應。《革》六二去五雖遠,陰陽相應,往者無咎也。”頁606。“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③《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頁604。邢璹注:“初爻處下,有應於四者,即是體後而敢爲之先,則《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之例是也。”頁607。
如此,這“應”必定是在不同時空上的“應”。以此對照上述例證:“顧榮在洛陽”與“後遭亂渡江”是不同的時空,卻得到互相照應(顧榮施烤肉給炙者,受肉者——炙者後幫助顧榮渡江:志同相和),且又是不同類之間(顧榮爲尊者,炙者爲卑者)的“應”。④“應”,於常人處還有“報應”之義。《世說新語·德行》說:“吴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録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吴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頁49。
(本文作者係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