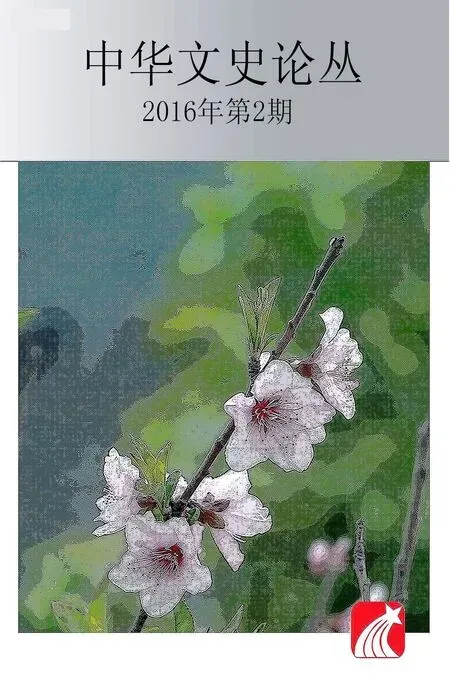詩讖入史:正史所載南北朝帝王詩讖的文學文獻學意義
李 猛 曹 旭
詩讖入史:正史所載南北朝帝王詩讖的文學文獻學意義
李 猛 曹 旭
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詩現僅存的兩首七言詩(殘句),都經歷了從“詩”到“讖”的被建構過程,這種現象在南北朝帝王詩歌中屢見不鮮,梁簡文帝、陳後主、周宣帝、隋文帝、隋煬帝等帝王之詩都有類似境遇。因製詩作讖的目的性與選擇性,這些帝王詩均以詩讖的形態保存於正史《五行志》和部分紀傳之中,且均爲殘篇,個別字句在建構過程中還被有意改動。這種詩歌存録方式,不僅保存了作爲詩和詩讖兩個面貌的帝王詩歌文本,也爲動態地考察每個文本的生成、傳播與接受提供了可能。這對於基本靠輯録的先唐詩歌而言,在文學、文獻學方面別有意義。
關鍵詞:製詩成讖 中古帝王詩歌 詩讖 五行志 存録方式
南北朝帝王,作爲特殊的文學羣體,其個人的文學創作及其圍繞他們展開的文人結集、文學唱和、詩文的編選整理等文學活動,歷來是這一時期文學研究的熱點,經過幾代學人的辛勤耕耘,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學界對這一時期的帝王詩歌的具體創作與傳播及其存録方式關注仍不理想。現存多位南北朝帝王的詩歌,是靠正史《五行志》以及部分紀傳所載“詩妖”一類官方史料纔得以保存和傳世的。而這種以“詩妖”“詩讖”形態存世的帝王詩歌,顯然是經過後代官方史臣依據搜集來的前朝帝王詩歌,尤其是其中的關鍵語句,刻意附會史實,進而將其詮釋甚至建構爲詩讖。也就是說,現存的相當一部分南北朝帝王詩歌有一個從“詩”到“讖”的被建構過程,而探索這一過程以及這種詩歌存録方式的文學、文獻學甚至歷史學意義,就顯得很有必要。
一 中古帝王詩讖的輯録與解讀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讖緯、陰陽災異,五德終始、天人感應等知識和理論的盛行與深入人心,帝王(尤其是末代帝王)這一特殊的羣體,其言行、起居等都因各類《起居注》等國史記載保存較爲完整;其詩文也因記録、整理乃至傳播的特殊性,在改朝換代前後,往往成爲政治對手以及後代官方史學關注、詮釋、書寫進而成爲政治宣傳的對象。這樣一來,帝王詩歌就成了其政治對手用以否定該帝王統治合法性的重要資源。由於這種宣傳方式的有效性與影響力,後代帝王在成爲繼任者前後,必然會授意相關人員對前代帝王詩歌進行一番搜集、閱讀、闡釋以及建構書寫,這樣,帝王詩歌就很難擺脫被利用、故意誤讀曲解,甚至被建構的命運。現存的這類帝王詩讖,大多保存在後代所修撰諸正史的《五行志》中,且大多被視爲“詩妖”。這種特殊的詩歌存録方式,爲探討帝王詩歌從詩到詩讖的轉化、帝王詩歌的傳播與接受、詩歌與政治的緊密關係等提供了可能。
在現存諸多南北朝帝王詩歌中,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的兩首七言詩(殘句),都是靠這種形式和形態存世的,故最爲典型。其中,《兩頭纖纖詩》本爲文惠太子的遊戲之作,①此詩逯欽立先生據《南史·沈覬傳》輯出“磊磊落落玉山崩”殘句,並擬題爲《擬古詩》(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381),但細核原文會發現“擬古詩”只是詩體,非其詩題,而《南齊書·五行志》所載之“兩頭纖纖詩”,方爲詩題。在箋注蕭長懋詩文之時,李猛又根據《藝文類聚》所載《古兩頭纖纖詩》、王融《代兩頭纖纖詩》,以及宋編《紺珠集》卷八所引《古樂府》等文獻,將文惠此詩題改作《兩頭纖纖詩》,並作了局部復原。見曹旭、陳路、李維立《齊梁蕭氏詩文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90—91。卻因詩中的“磊磊落落玉山崩”語,被先後詮釋成爲文惠預言諸長王(豫章王嶷、臨川王映、長沙王晃、始興王鑑、安城王暠),宰相(尚書令王儉、柳世隆),兩宮(齊武帝賾和太子長懋自己)相繼去世,甚至其子鬱林王昭業、海陵王昭文相繼被廢等亡齊之讖。而另一七言詩殘句,②文惠太子此七言詩爲佚詩,僅剩末句後三字,《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載:“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382;《南史》卷五《齊紀下·和帝》則曰:“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60。本是文惠太子與東宮才人共賦,其作意與內容本與佛教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但因後句“愁和諦”與“愁和帝”諧音,也被刻意附會齊和帝蕭寶融禪位於梁的史實,進而被蕭梁官方詮釋爲文惠預言齊和帝禪位之讖。③關於文惠太子兩首詩的輯佚、復原以及傳播與被刻意建構成爲詩讖的詳細論述,可參李猛《從“詩”到“讖”: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的詩歌創作、傳播與被建構》,待刊。
文惠太子之外,梁簡文帝蕭綱、陳後主陳叔寶、周宣帝宇文贇、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等帝王詩歌也有類似遭際。這些帝王詩讖多賴《隋書·五行志》、《南史·賊臣傳·侯景》等得以保存。尤其是《隋書·五行志上》“詩妖”一欄集中記載了陳後主、周宣帝、隋文帝、隋煬帝等幾位帝王之詩被詮釋、建構成詩讖的例子。其中,陳後主所作因屬樂府而被稱爲“歌讖”: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①《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637。
陳後主製樂府《玉樹後庭花》事,又見《陳書·皇后傳》、《隋書·音樂志上》,雖然二書對其製作過程的記載稍有不同,②《陳書》卷七《皇后傳》謂“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132。而《隋書》卷一三《音樂志上》則謂其“又於淸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頁309。但陳後主的作意應當就是爲“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曲成之後又於宮中“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哥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③《陳書》卷七《皇后傳》,頁132。其辭“綺豔相高,極於輕薄”,因“其音甚哀”,故後代多以“亡國之音”視之。因曲辭中有“花開不復久”語,與稍後陳的覆亡恰好相“徵應”,故被時人附會史實,並進一步解讀爲陳後主預言陳亡之歌讖。“亡國之音”與“亡國之讖”,是後代史臣運用時人熟知的兩種不同的知識和理論,從不同角度對同一事件的解釋,目的是要消解甚至否定陳後主皇權的合法性。這裏也可以看出唐初史臣有意將這兩種知識與理論融合:後主新歌“詞甚哀怨”,顯然與《隋書·音樂志上》所謂“其音甚哀”用意相同,而此音預示着亡國。從這個角度來講,詩讖纔具有一定的合理預見性。④吴承學認爲人們之所以把此詩句解釋爲陳後主即將覆亡的詩讖,是人們基於已知事物而對未來作出的合理推測。見《論謠讖與詩讖》,《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後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第二章《論謠讖與詩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5—41。鄔國平《讖言與詩學》也指出詩讖爲亡國之音找到了依據,《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3年第6期。
《隋書·五行志上·詩妖》所載另一詩讖是關於周宣帝宇文贇的: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蹀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帝卽位三年而崩。①《隋書》卷二二,頁639。
周宣帝與宮人“連臂蹋蹀而歌”同文惠太子與東宮才人共賦七言詩的情景尤爲相似,只是周宣帝所歌,屬於樂府,而“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也只是其中一句,或者一節,並非全部。其歌辭的內容與主題,應該源自《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②《文選》卷二九,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77年,頁412上。周宣帝所歌將及時行樂的思想體現得淋漓盡致,而這種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釋爲何他即位後即“彌復驕奢,躭酗於後宮,或旬日不出”。③《周書》卷七《宣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頁124。這種思想在北齊宮廷頗爲盛行。④《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載:“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高湛)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帝悅其言,彌加淫侈。”又載北齊武平中,韓長鸞勸北齊後主高緯毋須以陳人侵彭城爲意:“縱失河南,猶得爲龜兹國子。淮南今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爲樂,不須憂也。帝甚悅,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爲虞。”頁633。而“自知身命促”並不一定就是他在現實生活中真實的感受和預感,更多可能是一個昏君(更像是頑童)爲肆意玩樂找出的說辭。然而,周宣帝即位三年即告病亡,於是有人刻意附會這一史實,將他生前所歌“自知身命促”作爲不久即死去的讖兆,而這句樂府歌辭最終便被史臣解釋爲周宣帝預言自己命促之詩讖。
以上諸帝王之詩,都是被詮釋爲與自己的命運或國運相關的詩讖。《隋書·五行志上·詩妖》所載録的隋文帝詩則被解釋爲預言他人命運之讖:
開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爲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①《隋書》卷二二,頁639。此詩,馮惟訥《古詩紀》卷一三〇題作《宴秦孝王於并州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80册,頁433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從之,頁2627。此詩賴《隋書·五行志上》方得以保存,是隋文帝楊堅僅存的一首詩。
據《隋書·高祖紀下》,楊堅開皇十年(590)幸并州在二月至四月間,②《隋書》卷二《高祖紀下》載:“(開皇十年)二月庚申,幸并州。夏四月辛酉,至自并州。”頁35。卷六二《王韶傳》謂“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頁1474。按《北史》卷一一《隋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416)、《資治通鑑》卷一七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5526)均作開皇十年,故《隋書·王韶傳》之“一”字當爲衍字。故此詩當作於此間。王子相,即王韶,時爲并州總管秦王楊俊的長史,甚受隋文帝倚重,其時已六十六歲。隋文至并州,見其“鬚鬢漸白”,以爲“憂勞所致”,③《隋書》卷六二《王韶傳》,頁1474。故特加慰勞。看到王韶漸白的鬚鬢,楊堅也想到自己也已年届五十,白髮漸生,有感而發,遂作此詩。“明年後歲,誰有誰無”似即指白髮之有無,而此詩顯係隋文帝觸王韶之白髮而生情,慨嘆歲月無情。但作詩的第三年,即開皇十二年,王韶即病卒;④據《隋書》卷六二《王韶傳》,開皇十年隋文帝幸并州與王韶對話,王韶自謂六十六歲;又載王韶卒年六十八,可知道韶卒於開皇十二年(592)。頁1474。十年之後的開皇二十年,一同赴宴的秦王楊俊亦病亡。⑤《隋書》卷四五《楊俊傳》載楊俊死於開皇二十年六月,頁1240;而卷二《高祖紀下》則明確繫於二十年六月丁丑,頁45。這樣,隋文帝“明年後歲,誰有誰無”一句,即由原詩追問“鬚鬢”之有無,顯然被有意誤讀爲“二人之有無”,而他這首詩最終被唐初史臣刻意解釋爲預言王韶、秦王楊俊相繼死亡之詩讖。其實,王韶與秦王俊之卒年,都明顯遲於《五行志上》之讖言,從中我們依稀可以看到史臣刻意附會隋文帝詩句並强加闡釋的痕迹。
此次感官评价针对的是经过加工的凤尾鱼片的食用效果。评分小组由10位专业教师组成,他们都接受过感官评价的专业训练,评分标准采用10分制,取10位评分者分数的平均值[7]。选取质地、大小、色泽、厚度均相近的凤尾鱼片给10位评分者分别品尝,为了不相互影响评分结果,品尝时将10位评分者分别引入专业的感官评分实验室,不可有语言、目光等交流,品尝前后均采用绿茶水漱口,最大可能地做到客观、准确的感官评价。感官评价标准见表2。
《隋書·五行志上·詩妖》所載最後兩條詩讖是關於隋煬帝楊廣的,因這兩首詩歌的寫作時間、地點均不相同,特析作兩條: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飮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欷歔。
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弒,卽遭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①《隋書》卷二二,頁639。
據《隋書·煬帝紀下》,自大業十年(614)十月己丑(二十五)從東都洛陽還至西京長安,在西京僅月餘,即於十二月壬申(初九)啓程發往東都,戊子(二十五)日到東都,②《隋書》卷四《煬帝紀下》,頁88。此後再未能還西京。大業十一年五月,煬帝北上幸太原,避暑汾陽宮。八月乙丑(初五),巡北塞,得知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來襲,隨即於壬申(十二日)馳至雁門,次日即被突厥大軍圍城。至九月甲辰(十五日),方解圍;十月壬戌(初三),回到東都。在被突厥大軍圍城的一個月間,情況數度危急,雁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惟雁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門之時,矢及御前,煬帝大懼,以至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③參《隋書》卷四《煬帝紀下》,頁89;《資治通鑑》卷一八二,頁5697—5698。也只有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身爲皇帝的楊廣纔會詠出“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這樣感嘆欲歸而不得的詩句。④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煬帝已然脫離雁門被圍之險境,身處東都,美人再三吟詠此詩,令他想起那段刻骨銘心的往事,不禁潸然淚下。緣此,當宮中的美人再三吟詠此詩之時,他竟然“泣下霑襟”,這與他“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的情形恰好相應。
再回頭來看唐初史臣對此詩本事的描述,就會發現其中也留下了諸多刻意挑選、剪切甚至改寫史實的痕迹。如前所述,煬帝大業十年十二月至十一年十月的實際路線爲:長安(大業十年十二月初九)→東都(十二月二十五)→太原汾陽宮(大業十一年五月)→雁門(八月)→太原(九月)→東都(十月)。其中“自京師如東都”,實際上只有大業十年十二月初九至二十五這短短十六天時間。然而,長樂宮遠在大興城城外西北方向的長安故城,煬帝從京師去東都本不須經過長樂宮。這樣一來,《隋書·五行志上》所謂的賦詩時間(大業十一年)、地點(長樂宮)甚至詩意(欲歸不得)都與史實嚴重牴牾。所以,這裏的“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在時間上和路線的敍述上都有故意混淆之嫌:即將楊廣由雁門經太原入東都,也涵括在“自京師如東都”的敍述之中;而在時間的敍述上,則有意將起始放寬至大業十年底,並將楊廣北巡遇險、月餘方解圍、至十月纔返回東都等一連串史實故意略去。其用意無非就是欲將該詩卒章“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與煬帝後來在江都所作“求歸不得去”兩詩,一同詮釋爲隋煬帝“遂無還心”以致被殺之讖。
楊廣在江都所寫之詩描寫的是春景,而他於大業十二年(616)七月出幸江都,至義寧二年(618)三月被殺,故此詩當作於大業十三年春間無疑。①據《隋書》卷四《煬帝紀下》,頁91,93。大業十二年從東都出發之時,已然是七月;至618年早春三月,楊廣已被殺,故詩只能作於大業十三年春間。“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表達了詩人遭遇春景的喜悅,而“真成遭箇春”則流露出一絲“不得去”的慶幸。因詩中的“遭箇春”與“笑殺人”,恰好應驗了楊廣於次年三月在江都被殺的史實,遂被史臣解釋爲楊廣預言自己於春間被殺的詩讖。
除《隋書·五行志上》所載諸詩讖外,《南史·賊臣傳·侯景》也記載了簡文帝蕭綱的一條詩讖:
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蔕,冰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爲詩讖,謂無蔕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①《南史》卷八〇,頁2007。
值得注意的,《南史》所載蕭綱與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之詩讖,與《隋書·五行志上·詩妖》所載詩讖的性質、政治意涵甚至原始史料都大致相同,其原始史料主要是官方檔案。①游自勇《中古〈五行志〉的史料來源》認爲雖然前代編撰史書、筆記小說也是唐前《五行志》編撰的重要來源,但官方檔案是其中最重要的史料來源,《文史》2007年第4輯。而帝王詩讖,因基本上都是官方有意搜集相關詩歌並加以詮釋、建構,故其史料來源多爲官方檔案。文惠太子詩讖不見於《隋書·五行志》,當然是由“五代(梁、陳、後齊、後周、隋)史志”的編撰體例所致。而蕭綱詩讖不被載録,當然也不是唐初史臣對其詩讖性質的認定問題,而可能是史臣搜羅未備,李延壽《南史》後出,重加輯録,並將其置於《侯景傳》之篇末,作爲補充。
必須指出的是,從帝王詩歌到正史《五行志》所載之帝王詩讖,並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經歷了不同身份和層次的人所進行的多次甚至多重解讀和建構。期間有“識者”的初步解讀,②中古《五行志》在利用相關五行、天人感應等知識和理論解釋“詩妖”“服妖”“言之不從”等等之時,常冠以“識者曰”。“識者”這個羣體,目前鮮有學者注意,他們應當是有相關知識儲備又關心政治之人,並非史臣故意虚構。他們關注社會上的反常現象(包括反常之詩歌),並利用相關知識理論作出初步的解讀。如聽聞文惠太子“磊磊落落玉山崩”詩,即有“此讖言也”之嘆的沈顗,或可以“識者”視之。也有帝王的政治對手(或宗室、或異姓權臣)禪位前所展開的搜集、整理以及附會建構等一系列政治操作與宣傳,更有順利禪位之後利用官方權威對此前的解釋加以修正、定性,並作爲官方惟一正確解釋,最後纔是後代史臣選擇性地將其編撰並寫進入正史《五行志》或部分紀傳。
二 詩與詩讖轉換的內在機制與條件
帝王詩讖與正史《五行志》所載其他詩妖如童謠、謠讖等的詮釋方式有較爲明顯的不同,後者所利用的知識和理論不外乎傳統的讖緯、五行災異等,而前者則基本是根據詩句中偶一出現的關鍵敏感字句,利用諧音、離合、雙關、調序等手法故意附會相關史實,進而將其詮釋、建構成爲預言他人、自己甚至家國被殺(滅)之詩讖。由於輯録這些詩讖的往往是正史的帝王紀傳和《五行志》,而後者往往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反映,所以這些帝王詩讖的搜集、選擇、建構都具有强烈的目的性、選擇性。除了這種外在强加的目的性、選擇性之外,詩讖作爲一種頗具文學形式和意味的載體,與詩歌之間確實有某種內在的相通之處。
對此吴承學已有深入的論述,他發現自“詩妖”說產生之後,解詩者們就試圖用儒家傳統詩學對其進行闡釋。至鄭玄注《尚書大傳》,始以“詩之言志也”來闡釋“詩妖”,這正是以儒學的詩學理論來闡述“詩妖”出現的原因,詩讖形式上似乎異常,其實卻是百姓抒發自己的“情志”。這種以儒家的理性詩學來闡釋非理性“詩妖”現象,大大淡化了“詩妖”的神學色彩,“詩妖”理論與傳統的“詩言志”說的相通之處是它們都强調詩歌與政治的直接關係,其共通的理論基礎便是“詩可以觀”。①吴承學《論謠讖與詩讖》,頁29。孫蓉蓉《謠讖與詩學》則認爲謠讖的產生同《詩經》中“變風”“變雅”的詩作一樣,都是當時社會、政治現狀的反映和體現,其性質在於“詩之言志也”。《文學評論》2011年第6期。徐公持也認爲中國傳統詩學中的“神人以和”“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等觀念,還有“正變”等理論,也都支撑着“詩妖”説的存在。徐公持《“詩妖”之研究》,《國學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91—227。清人姚元之所謂“詩以道性靈,故往往有讖語”,②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0。可以說將這一點發揮到了極致。另外,中國傳統的“以意逆志”和“詩無達詁”的解詩方法,讀者可以隨意地、創作性地解讀詩句,甚至自由釋義,進而作出與作者原意完全不同的解釋。於是詩歌由詩人的無意創作到讀者的有意誤讀,成爲一種能夠預言和暗示詩人前途命運或事物發展的詩讖。①參孫蓉蓉《詩歌寫作與詩人的命運——論古代的詩讖》;鄔國平《讖言與詩學》。這些都是詩得以轉化成爲詩讖甚至詩妖的內在機制。
當然除了有內在相通之處外,詩與詩讖之間的轉換也需要具備一些必要條件,而二者之間的時空錯位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必要條件。②鄔國平認爲詩讖成立有兩個必要條件:存在被認爲帶有讖兆性質的詩歌、出現被認爲能夠證實這種詩歌隱含之意的生活事件。見《讖言與詩學》。《說文解字·言部》謂:“讖,驗也。有徵驗之書。”③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1年,頁90下。顧名思義,占與事逐一應驗纔可以稱讖,否則讖無從談起。故詩與詩讖之間必然存在着時空錯位,這是詩之所以能成爲詩讖的先決條件,即詩歌先於詩讖而存在。④〔日〕淺見洋二認爲“詩讖”大都是在作品完成之後,把作品搬到新的語境中去讀時纔成立,見《關於詩與“本事”、“本意”以及“詩讖”——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接受過程中的文本與語境之關係》,金程宇、岡田千穗譯,氏著《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67。“新的語境”,即詩讖已然應驗史實。孫蓉蓉亦謂作爲詩讖的某些詩句後來事情發展的契合、暗合之所以能夠形成,是由於讀者在閱讀此詩時,已經完全脫離了詩人創作時的特定語境,這種語境的轉移與變化,爲讀者的附會、誤讀、創造了條件。見《詩歌寫作與詩人的命運——論古代的詩讖》。前文所分析的諸多帝王詩讖(包括南齊文惠太子的兩個詩讖),無一不是如此。只是有些時間相去未遠,如文惠太子《兩頭纖纖詩》、陳後主、周宣帝以及隋文帝等詩;而有些則相去甚遠,甚至可以橫跨兩百餘年,如《隋書·五行志上·詩妖》所載王獻之(344—386)所作樂府《桃葉歌》,在隋滅陳後被詮釋成爲詩讖: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⑤《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頁637。《南史》卷一〇《陳紀下·後主》亦載此事,敍述稍簡:“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檝。但度無所苦,我自接迎汝。’及晉王廣軍於六合鎭,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度。”頁3 0 9。《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録》謂:“《桃葉歌》者,晉王子敬之所作也。桃葉,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歌之。”①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四五,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664。可知,此詩乃是王獻之(字子敬)爲其所篤愛之妾桃葉所作,《樂府詩集》録了其中三首,因其所唱均爲男女纏綿悱惻之情愛,故有《情人桃葉歌》之名。②《玉臺新詠箋注》卷一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71。按《玉臺新詠》僅録其中兩首。此歌在東晉南朝甚受歡迎,至陳代仍被“盛歌”。然而,因只有這一首歌辭中連續出現了“桃葉”“渡江”“迎接”等語,故楊廣率大軍滅陳後,就有人故意附會楊廣紥營桃葉山,③楊廣大軍駐紥之地,《隋書》卷二《高祖紀下》謂“六合”(頁32);而《南史》謂“六合鎮”,《資治通鑑》綜合《南史》、《隋書·五行志》之說謂“六合鎮桃葉山”(頁5504)。按《元和郡縣圖志》闕卷逸文卷二載:“桃葉山,在(六合)縣西南七十五里。隋文帝開皇三年,於此山置六合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073。可見,六合鎮之設置當爲伐陳作準備,後來楊廣大軍駐地當爲桃葉山。楊廣駐軍此處,除了地理位置因素的考慮外,或許還有意利用這首在江南廣爲傳唱的《桃葉歌》,爲己方宣傳造勢。晉武帝伐吴之前,曾利用東吴盛行的童謠“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有意加小字爲“阿童”的益州刺史王濬爲龍驤將軍,見《宋書》卷五一《五行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914;又據《晉書》卷三四《羊祜傳》,知發現並上表晉武帝利用此童謠,以及推薦王濬爲益州刺史、加龍驤將軍者,均爲羊祜,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017。參李曉紅《卞彬童謠與宋齊革易之歷史書寫》,《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2015年第5期。韓擒虎渡江任蠻奴接應等史實。而《南史》所載版本還根據歌中“渡江不用楫”句,附會任蠻奴接應南渡一事,刻意解釋作楊廣大軍“乘陳船而度”,藉此將其詮釋爲極具預言性質的詩讖。從王獻之作此歌的東晉中後期,到隋大舉南下滅陳,期間竟然已超過二百年。王獻之爲其愛妾所作的所作樂府詩的《桃葉歌》,在東晉南朝傳唱兩百年之後,終於被隋朝官方所利用並被詮釋爲詩讖,進而被唐初史臣所認可,最終以“詩妖”的形式定格在官修的《隋書·五行志》之中,詩讖轉換的時空錯位可以想見。
三 詩讖入史:作爲詩歌存録方式的文學文獻學意義
現存的帝王詩讖無一例外都保存在正史《五行志》(《南齊書·五行志》、《隋書·五行志上》)以及紀傳(《南史·齊和帝紀》、《南史·沈顗傳》、《南史·賊臣傳·侯景》)之中,而他們的史料來源又基本來自官方檔案。這些詩讖與史實和政治都有緊密的聯繫,因而具有很高的史學研究價值,近年來也頗受史學研究者的注目。但這些帝王詩讖的源頭和最初形態畢竟是詩歌,因官方的刻意詮釋、建構纔成爲詩讖,而且在一次甚至多次詮釋、建構的過程中,某些關鍵字句也被故意改換。所以被改動過的詩讖與原詩不僅在意涵上相去甚遠,在個別字句上也有差別,這樣就形成了兩種面貌不完全相同的詩歌文本。這種特殊的詩歌存録方式,對於基本靠後世輯録的魏晉南北朝詩歌,尤其是存量甚少的帝王詩歌而言,在文獻學和文學研究等方面很有意義。①關於存録方式對六朝詩歌的影響,參林曉光《論〈藝文類聚〉存録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學變貌》,《文學遺產》2014年第3期。首先,保存了部分帝王詩歌,雖然是經過刻意改動和再建構過的詩歌文本,藉着流傳有序的官方正史系統,得以代代相傳並廣泛傳播。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些史臣的輯録與整理,這些詩歌或許也會佚亡,至少不會有如此廣泛、深入的傳播範圍和接受羣體。其次,這兩個不同面貌的詩歌文本,除了有難得的版本校勘價值外,也爲進一步考察每個詩歌文本的生成、傳播與接受等問題提供了可能。
1.詩與讖,兩種不同性質與面貌的詩歌文本。
這裏所謂的兩種面貌的詩歌文本,不是單純指詩歌文本,而且包括作者和解詩者所賦予詩歌的諸種意涵。就詩歌文本而言,以文惠太子詩爲例,“愁和諦”是文惠詩歌原貌,而“愁和帝”則顯然是經過後代官方刻意改動過的版本。一字之差,其詩意、旨趣乃至性質就已有明顯不同,再加上後人刻意附會史實,將其建構成爲讖,因而導致原詩與詩讖在意涵層面上竟有天壤之別。而《隋書·五行志上》以及《南史》所載其他諸帝王詩讖,因其文獻載體的惟一性,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詩歌文本,都經過唐初史臣再整理、再建構過的詩讖,而非原詩,這種詩歌文本與原詩在文本上究竟有無差異、有多大的差異,已不得而知。但就其詩意而言,我們至少知道經過正史建構出的詩讖顯然與詩歌原意相去甚遠。有了這樣一個參照,我們對中古帝王詩歌的內容、體式、風格等或許會有更爲清晰的認識。這也爲“因讖求詩”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2.因“讖”求“詩”。
“因讖求詩”,簡言之,就是根據正史所載之帝王詩讖,向上逆推帝王詩歌的發生、發展以及原生態。以上所述帝王詩歌,大多作於宮中(包括皇宮、行宮和東宮),有些與宮人(才人、美人)共賦,有些樂府詩還曾在宮中廣爲傳唱。這些信息似乎表明這些作於宮中宴席上的詩歌與極富廟堂氣息的宮宴詩有明顯區別,似乎是帝王在廟堂之外的賦詩言志甚至自娛,故多是一時一地感情的真實流露。另外,在詩歌的傳播途徑和羣體上,因後宮女眷的參與,士人依禮鮮能參與其中,故而這些詩歌的傳播範圍似乎只限於皇帝身邊親近的宮人、內侍(可能還包括個別倖臣)。這些都使得帝王作詩時難免會犯下言語上的禁忌,①關於詩讖的“言語禁忌”問題,參孫蓉蓉《詩歌寫作與詩人的命運——論古代的詩讖》;鄔國平《讖言與詩學》。如“愁殺人”“玉山崩”“誰有誰無”“求歸不得去”等等。這種狀態之下,作出來和唱(誦)出來的詩歌,又很少經皇帝本人以及文士整理,即通過其他途徑傳出,被後人利用並製作成爲詩讖。由於詩讖的詮釋、製作甚至宣傳都由後代的官方主導,所以詩讖取代原詩成爲主要甚至惟一的詩歌文本。這樣,以詩讖的形態存世的帝王詩歌已基本淪爲官方進行政治宣傳的工具。
因爲後代在製作、建構詩讖的時候,只是將全詩之中那些涉及生死、吉凶的關鍵字句單獨析出,並利用相關的知識與理論加以詮釋,所以現存的以詩讖形式保存的帝王詩歌,鮮有完整詩篇,基本都是斷句殘篇,極端者如文惠太子的七言詩只存録了全詩的最後三個字。這當然是製作詩讖者所帶强烈的目的性和選擇性所致,這種整理和製作,一方面使得帝王所作全詩僅存片段,給今天的文學研究帶了諸多不便;另一方面卻爲我們根據所存片段,探索整理建構者的目的以及選擇的標準等問題提供了便利。
3.由詩讖推及“詩妖”。
前文所述之詩讖多載於正史以及正史《五行志》,基本都可以視作“詩妖”,所以從詩到詩讖這一被建構的過程中所體現的建構者的强烈的政治目的以及選擇的標準,同樣適用於那些被定格爲“詩妖”的樂府、民歌、甚至個別民謠。從這個角度出發,進而討論詩讖乃至“詩妖”之中的這些樂府、民歌,將被史臣詮釋和建構而成的“詩妖”逐一解構、還原,可以進一步探討甚至還原其原生態。明此,正史《五行志》所載“詩妖”,同樣可以從“詩”、“詩妖”、“從詩到詩妖”等三個層面展開動態的、全面的研究。而以往的研究多是孤立地研究其中的某兩個層面,這種研究顯然不能觸及“詩妖”文本生成及其傳播等深層次問題。
這些被定格爲“詩妖”的詩、樂府、民歌乃至個別民謠,首先是“詩”,兩宋以後的詩歌輯佚者也多以此視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古《五行志》所載録的“詩妖”是宋以後輯佚漢唐詩歌重要的淵藪。①《樂府詩集》、《古詩紀》、《古謠諺》、《古樂苑》等後出輯本中的很多詩、民歌、樂府、諺、謠等輯自正史《五行志》,至逯欽立編《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仍沿襲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古正史《五行志》也是魏晉南北朝詩輯佚的重要淵藪。但也正因爲此,這些“詩”在被輯佚者從正史《五行志》中逐一抽離的那一刻,“詩妖”之所以成爲“詩妖”的歷史語境、政治話語以及詩與“詩妖”之間的時空錯位也都被完全消解了。②即使如《樂府詩集》等書會將在其“解題”部分,將其詩歌的原載體——《五行志》予以說明,但沒有歷史場景及其史臣的相關詮釋、解讀,後來已經很難體會其“詩妖”的性質。所以,基於這些後出輯本的研究,只能停留在靜態的文學研究層面之上,只知“詩”而不知其與“詩妖”的淵源。而歷史學的研究則是完全是另一個方向,他們很少關注“詩妖”是由是後來人根據“詩”多次建構出來的,而只是關注作爲史料的“詩妖”所蘊含豐富的政治意涵及其史料價值。如前所述,“詩妖”的政治意涵畢竟多是後代官方和史臣强加詮釋的,故不能用來直接解釋歷史事件,更不能當作史實。③如胡祥琴即認爲“詩妖”是雜歌謠辭等此類文體在政治生活上的體現,並認爲“詩妖”撰述者爲證明某些論點而不惜采取牽强附會的方式。但卻將《宋書·五行志》所載《懊惱歌》、《兜鈴曹子》等“詩妖”直接當作史實,則明顯是誤解。參見胡祥琴《試論〈宋書·五行志〉“詩妖”的性質》,《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所以,打破學科畫分所帶來的約束,拋開各自研究領域的傲慢與偏見,全面地剖析作爲兩種形態和屬性的詩與詩妖、關注從詩到詩妖的動態變化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開展綜合研究就顯得很有必要。
(本文作者李猛係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曹旭係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