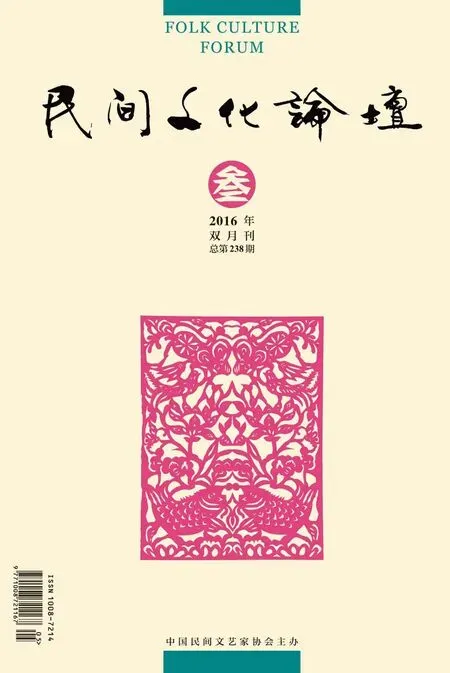论节日事项的“共有”“扩散”与“移借”诸问题—以端午节为例
宋 颖
论节日事项的“共有”“扩散”与“移借”诸问题—以端午节为例
宋 颖
我们可以用“共有”“扩散”与“移借”等几个概念,来探索节日事项之间的关联性,概括并解释节日事项的繁杂多样性。“共有”构成了节日事项在群体内世代共享的传承基础,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群体内部共同的记忆和文化情感,是构建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扩散”涵盖了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对同一个节日的文化元素的择用,精准性和模糊性同时存在。“移借”是指将系列文化符号成组搬移,不局限于某一节日,体现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惯性。节日事项的“共有”“扩散”与“移借”,有利于习俗的在地化,呈现出适应性的细节变化,为人类的实践和创新提供了可能性。
节日;共有;扩散;移借;端午
中国传统中的重大节日,像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均名列在2006年5月20日由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往往被称为“我们的节日”。其中,端午节于2009年10月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①参见东方网10月3日消息:2009年9月2 8日至1 0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开幕,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包括了中国申报的22个项目,中国端午节名列其中。,是中国节日中惟一入选的传统节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和生活智慧的代表。
从古至今,对于像端午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事项的记录和阐释,都不无巨细地要列举和描述当地过节方式。因此,我们能够大致勾勒和讲述一个节日“怎么过”,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在民众生活中,始终呈现着事项繁杂、变化多端的现实。因此无论哪个“共有”的传统节日,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在群体内有些地方或有些人声称“不过”或者“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的”。
尽管传统节日拥有特定的名称和相对固定的节期,并进入到国家层面的行政工作范围,但仍然非常明显地随着地域和人群的变化而呈现出纷杂的多样性,这使得某一共同体内“共有”的节日,往往成为一种概念上的文化想象。一方面,仅凭“共同的”或“我们的”笼统阐述,无法捕捉和交流具体的民俗细节;另一方面,倘若单凭某些标志性的事项来界定某个节日,就会发现其他区域或其他时间也出现相同或相近的事项,而陷入难以辨识的困境,更遑论厘清节日的源流。像端午节吃的粽子,用的艾草,划的龙舟,祭祀的神灵,人们发现在其他时间也有相似的使用。这些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民俗学者和节日研究者。
因此,对于传统节日的研究,除了收集、记录、描述和比较节日事项的具体形态,更需要具有学术阐释力的概念,能从根本上把握表面上多元化的复杂现象。笔者从对端午节跟踪近十年的事项研究中,尝试使用“共有”“扩散”和“移借”等几个概念,来探索节日事项的变动性和关联性。
一、“共有”:构建传承的基础并衡量群体的认同程度
节日事项的“共有”,形成了节日在群体内部共享并世代传承的基础,承载着一个民族群体内部共同的记忆和文化情感。这一方向的讨论涉及到值得关注的民俗国家化过程①参见宋颖:《“一国”的文化共享:〈中国年俗〉的民俗国家化过程探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7—117页;另见杰伊•梅克林著,宋颖译:《论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民俗共享与国民认同》,《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第250—256页。,对此的持续观察和深入分析另文专述。一个节日拥有独特的名称,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有所保持,还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能够在某些群体内世代传承,保持着在时间上流布和空间上散播的活力,这种文化流脉中具有某种“共有”的要素,从而构成了传承的基础。
从理念上来看,刘魁立曾强调,基质本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髓和灵魂。他指出,“非物质文化对于具体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来说具有本真性,而对其他人来说具有共享性。……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共享的可能性的差别”②参见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九次国学论坛上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6日;另见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中国民俗学会2009年年会论文》。。节日事项也具有“基质本真性”,使得人们能够“共有”某一个节日。从具体节日事项构成要素来看,节日中的“核心元素”③关于核心元素和变动元素的分析,参见宋颖:《端午节研究:传统、国家与文化表述》,第一章.中央民族大学2007届博士论文。是节日得以“共有”的基础,而对于节日诸多元素的使用和分享,是保持节日得以“共有”的表现方式。
在中国节日体系中,有的是法律规定的或人为设定的纪念日,有的是有着深厚生活积淀、跟随自然节律的变动而产生的传统节日。后者在历时关系和共时关系上都具有广泛的共有性。节日事项积淀着随时间推移而萌生又消失的种种细节,凝聚和连接着一方水土上的民众生活,蕴含着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中生活经验的精华,承载着人们对于自然、人生和社会的看法。节日事项通常是人们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在特定时刻的特殊讲究,往往是因为祖辈如此而世代传承下来,大多数人都在这一天做同样的(或相似的)事情,形成节日中“家家如是”④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7—350页。的情形。人们在同一时间采取共同的行为,在节日中出现的这些相同的民俗细节,构成了一个节日的“核心元素”,这让人们具备了彼此对话和相互交往的基础,形成一定范围内居住区域中的凝聚力,从而共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会遇到,由于地域不同、族群不同,生活环境和条件不同、观念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得某一地域的人们在这一天吃的、穿的、用的、讲究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就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知识”,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被人们使用、接受和理解,而呈现出一定的节日事项的适应性和由此产生的地域性。这些不同的生活细节,提供了具有差异性的节日文化“变动元素”,让人们之间充满着对彼此的兴趣和好奇,存在着分享、交流和移借、搬演的可能性。这些变动元素的多样化使用,会在后续的“扩散”和“移借”中详细讨论。
端午节的习俗事项也不例外①参见中国民俗学会编:《中国端午节丛书》(六卷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端午节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被认可为中华民族“共有”的一个传统节日。在韩国“江陵端午祭”于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在“共有”层面上引发了究竟是“我群的”还是“他者的”大讨论。一个节日的事项究竟在这一个或那一个群体内部“共有”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的差异能够大到什么程度,都值得分析。尽管人们共有着这一节日,但在具体的度过方式上,既有相通的内容,能够相互理解和接受,并用于个人的生活,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地域差异。
关于端午节事项的历史记载既久又多,时间上的事项层叠与沉积,以往梳理较多,暂且不谈。这里仅从湖北和湖南两地的地方志记载来看,主要有以下十项内容,如节期、角黍类、艾草类、五色丝类、采药、竞渡、屈原、祭祀类、送瘟、亲友往来等。对此,使用归类统计法②标明“类”是指,在该项下,还存在细节上变化了的其他类似元素。如供食用的角黍类,还包括馒头、粽等食品和物品。供使用的艾草类,还包括菖蒲、葛根等相似物。供佩戴的五色丝类,包括了香囊、蒜囊等。艾草类和五色丝等物都用于厌胜。采药,包含了斗百草以及用药草沐浴的习俗。祭祀类的神灵,包括了除屈原外对瘟神、水神、张天师、杨泗、伏波、城隍等神灵的拜祭。,来具体说明节日事项在空间上的共享程度。这十项内容的归纳基于地方志的记载,根据材料的详略而尽可能的合并类似物,但是对于记载较多的事项,尽管可能属于同一类文化符号,还是单列出来,以便进行较为细致的比较和对照。
以下的统计,一方面关注较为普遍的共有事项的记录,这将有助于了解端午节的大致形态;另一方面,对于特异的元素记录,如能体现出“变动元素”的适应性等内容,也适当予以关注。
这十项内容的比照,在有关湖北过端午的65种地方志③湖北65种地方志和湖南的60种地方志,均来自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记载中,节期上五日为端午的有65种,有4种将这天称为“天中节”,其中还要过“大端阳”的有9种,均在十五日,另有1种单记为十八日,1种记为从十五日到十八日。角黍类的记载,有38种用于食用,有23种用于赠送,其中6种记载赠送时配有盐蛋,1种记载用于祭祀屈原。艾草类的记载,有53种记载使用艾草,23种使用菖蒲,30种饮用菖蒲,52种用雄黄酒。五色丝类的记载中佩戴五色丝有11种,香囊有17种,其中有的混合佩戴着蒜枚、艾虎等。采药的记载19种。竞渡的记载有42种,2种记载提及“吊屈原”,2种提及丰年要持续3天,还有1种是初一到初六。提及屈原传说的有11种,其中1种记载当地有“三闾祠”。祭祀类有13种,祭祀张真人、水神、瘟神等,或者前往庙宇道观求取道符。送瘟的记载有10种,有迎船、送船、打龙船、祈神会、打醮等不同的称呼。记载亲友往来有13种。
在有关湖南过端午的60种地方志记载中,节期上五日为端午的有60种,6种称为“天中节”,2种称为“地腊”,2种称为“敬节”。其中还要在十五日过“大端阳”的有10种,另有1种记载为初十过节。角黍类的记载,有37种用于食用,有18种用于赠送,其中4种配有香囊,3种配有蒲扇,2种配有咸蛋,1种配有艾糕,1种配有鞋袜。艾草类的记载,有57种记载使用艾草,8种配有葛藤,1种配黄荆条,30种使用菖蒲,28种饮用菖蒲,52种用雄黄酒。五色丝类的记载,其中4种为五色丝,9种为香囊(有彩蛛、猕猴、葫芦、鸡心、瓜豆等样式),1种为雄黄囊,5种为蒜。采药的记载22种,拜“天医星”的记载有2种,3种记有“燃灯灸穴道”,6种记有沐浴或用来“澡洗”。竞渡的记载有43种,有2种提及初一到初五。提及屈原传说的有4种。祭祀类有7种,祭祀瘟神、伏波、关帝、城隍等,或使用朱书道符。送瘟的记载有1种,称为收瘟,不在十五日而在五日端阳进行。有4种记载亲友往来。
统计数据显示出①笔者梳理地方志材料时,发现的问题是,县志多袭用府志的说法。,两省普遍共有的事项是:食用角黍、悬挂蒲艾、洒涂雄黄酒、有龙舟竞渡等,局部地区除了过端午,还过“大端阳”。相比较而言,湖北重祭祀,除了吊屈原外,还有其他神灵,送瘟船活动较多;湖南则有“天医星”的说法,记载较多的事项是采药治病或沐浴;湖北亲友往来赠送角黍时配用盐蛋较多,湖南则更为多样些,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过同一节日时所存在的地域偏好、差异和特点。
从“共有”的概念入手,能够更好地分析某一群体内部长期传承的节日事项,把握节日的内核,即“核心元素”。正是节日当中所“共有的”这些核心元素,能够使得某一节日呈现出较为固定的形态,而得以整体把握,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上升为国家软实力和文化传统的象征,标明和区别“我群”与“他群”,获得在更大范围上“共有”的可能性。
二、“扩散”:在精准与模糊之间把握节日事项的多样形态
从上节的统计可以看出,端午节的节期主要是五月初五,节期可视为节日的“核心元素”,地方志记载中一般称这一天为“端午”或“端阳”,某些地方这天过节外,还另有以十五日为主的“大端阳”。在过大端阳的地域,五日会被称为是“小端阳”。有的地方还有二十五日为主的“末端阳”。
如《益阳县志》②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74页。(二十五卷,清同治十三年刻本)记载,除了龙舟竞渡外,“俗好祀鬼神,取肩舆舁神像,鼓吹相从,沿街往返,或装诸杂戏及种种鬼神,谓之‘迎会’……以初十夜为‘葛公会’,十六日为‘天符会’,二十六日为‘城隍会’。”
又如《恩施县志》③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437页。(十二卷,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记载,“清江龙舟竞渡,至十五日乃止。十五日,俗名‘大端阳’,悬门蒲艾始去之,饮食如前。二十七日,相传为‘城隍神生日’。邑人仗卫迎神于市。是月,乡农缚草为龙,钲鼓绕田,谓之‘趋(驱)虫’。”
再如《来凤县志》①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448页。(三十二卷,清同治五年刻本),记有,“五日,俗以是日为小端阳,十五日为大端阳,云始于马伏波。俱竞渡龙舟,十五日尤盛。……五六月间,雨殇不时,虫或伤稼,农人共延僧道,设坛诵经,编草为龙,从以金鼓,遍舞田间以禳之,亦迎猫祭虎之遗风也。”
这里简要举出的几个例子,是要说明节期上的“扩散”,一般表现为:初五的事项,有的也在初一到初五、初一到初六之间进行,主要是亲友往来,尤其是未定婚的、或者是姻亲的,在这几天之内都可以来往,赠送角黍等物,而不限于初五当天。十五日的大端阳,在某些地方是十六、十七或十八,主要举行迎船送瘟的仪式。有的地方是初一到十五,都可以择取日子来举行平安醮。过大端阳的某些地方因节期的跨越,或将十三日也纳入,一并祭祀关帝。而二十五日的末端阳,有的地方延至二十七、二十八,将“城隍日”②对于城隍的祭祀,与城隍的职能和端午节的文化意义有很大的关系。也一并纳入,由于城隍具有的一种职能是管鬼,而端午节有清理水域、去污驱邪的意义,因此特意要祭祀城隍。综合来看,节期的扩散主要有三段,由五日扩散到初一至初五,由十五日扩散到十四至十八,由二十五日扩散到二十八等。
由历史形成的节期,存在由点及线或由线及点的双向变化,引起了相关习俗事项的扩散形态,节期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在生活实践中所要求的(讲究的)过节方式的精准性和模糊性同时存在。节日事项的扩散,使得节日相关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在文化交往中,为习俗的在地化和适应性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为人类的实践和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可以说,“扩散”及由此引起的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重要的节日事项,限定在五日当天,甚至讲究具体在午时发生,如以午时水洗眼,午时来取药等;另一方面,某些节日事项,不限定在五日进行,可以在前后几天,或者十五左右、二十五左右,甚至模糊到“五六月”等,均有可能。
而节日习俗事项的扩散形态,主要是节日适应性而引起的地域性的“变动元素”的变化,既包括对于具体事项的类似选择,也包括对于这些文化元素的多种使用方式③参见宋颖:《从“少数民族过端午”模式看文化的涵化与误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1期,第 145—156页。。如上述的神灵祭祀,包括对于传说人物的祭祀,也存在择取屈原、伍子胥、曹娥、勾践、水神、瘟神、张真人、伏波、杨泗等人物符号上的变化。
以伏波故事的记载为例,与人们熟知的屈原传统对比来看,可以说明节日传说的扩散变化。如见于《溆浦县志》④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13页。(二十四卷,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的记载:
“俗以初五为‘小端午’,望日为‘大端午’。相传伏波征五溪蛮于五日进兵,士卒有难色。伏波曰:‘端午令节,蛮酋必醉,进可成功。今日乃小端阳也,后当与诸将过大端阳。’即进兵,诸蛮果醉,剿平之。乃于十五日大享士卒,遂名曰‘大端午’。至今仍之。”
五月举行的迎神形式也比较多样化,主要是祀鬼神,涉及的仪式和神灵较多样,如上述征引了其中的一部分。与“扩散”相伴随的是,出现了文化元素的“移借”现象。如《恩施县志》提及用草龙驱虫,不限定在端午日当天进行,也不在扩散的日期,而是不定期举行。这种模糊化,不仅表现了时间上的扩散性,也意味着这种节日事项可能会被移借到其他节日或平常日期来使用。而用草龙驱虫的事项在生活实践中亦确实如此,这种活动本身可以自由移借,为了发挥实际的功能,并不限于五月。
端午节日事项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所涉及的材料,往往具有地方性,也呈现出变动元素的扩散形态。角黍的用途主要是自己食用、亲戚之间赠送和祭祀祖先。而角黍制作中所使用的叶子,往往是就地取材,以当地常见的植物为主。湖南地方志记载用于包角黍的叶子就有6种,如箬叶、蒻叶、菰叶、楝叶、桧竹叶、竹籜(竹笋叶)等。人们用来保护家宅的草药,也有几种选择,如艾叶、菖蒲、葛根等,还有的地方用到雄黄、苍术、朱砂等。其中,艾草主要是插在门上,或制作成艾人、艾虎佩戴,有的地方用于沐浴。有关菖蒲的大多记载是做成酒饮用,少数是用来插在门上。制作的雄黄酒,主要是用来洒墙角,小儿涂额,有的在使用时配以朱砂。在对药草的使用上,也存在多种方式,较为细腻多样。仅以地方志中湖南一省用法为例,动词包括了如下种种:结、悬、挂、刻、切、拌、和、饮、煎、煮、洒、涂、酿、簪、系、刈、切、捣、研、杵、泛、劈、拳、燃、灸、馈、遗、送等。这些使用方法,也是地方特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三、“移借”:节日事项在生活实践中的创新
如果说 “扩散”主要体现在同一个节日当中的同一事项或同一文化元素的模糊化变动,那么“移借”中文化元素的使用则更为自由和多样化,常常不限定在同一个节日,表现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和实践性。在地方志中,正月、十二月等属于过年期间,时间段较长,各种节日民俗事项的记载最多,次之是五月事项的记载。其他月份的事项较少也相对简单。其中,端午节的一些具体事项,并不限于端午节这天出现;相应的,其他节日的一些事项,也会出现在端午节;不同节日之间分享相似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常是成组或成系列出现的),这样两种双向交错情形,都属于节日事项的“移借”。这样的移借现象,出现在“变动元素”的置换和实际应用的层面上。而节日事项中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背后的文化结构和思维结构在发挥着作用。有意或无意地将系列的文化符号成组搬移,这些文化符号背后固定的所指意义,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或者发挥实际的功能,具有社会交往的效用,体现出日常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行为惯性。
上文提过节期的扩散形态,提及的五日和十五日之间的事项,往往还会伴随移借现象。例如,
《岳州府志》①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481页。(三十卷,清乾隆十一年刻本)记有,“五日,沿门插艾,罢市竞渡,或编苇为船,肖龙形泛之,谓之送瘟。”
《续修永定县志》①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26—627页。(十二卷,清同治八年刻本)记有,“端午,……河内龙舟竞渡,钲鼓喧嘈。前二十年,具卤簿仪卫迎关帝至观音桥给竞渡者食物,谓之‘赏标’。竞渡者并力争先,上领食物,谓之‘抢标’。今因关帝祀典尊隆,寖不复迎。惟二十五、六日迎城隍神,一如当日。”
这里举出的例子,其中一则,十五日的送瘟在五日进行。另一则,把祭祀关帝的仪式移借到龙舟竞渡夺取胜利的程序中来。有些地方过节的日期跨过了五月十三的关帝诞辰,不但要一并祭拜关帝,还把这一祭祀仪式和其他节日活动融合在一起进行。像这段竞渡的记载,就提及迎关帝的仪式成为当地竞渡时“赏标”和“抢标”的重要环节。与一般竞渡在湖中争夺胜利不同的是,这里的竞渡是争夺来自神灵的护佑式的奖赏,神圣的意味显得更加浓厚。而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关帝祭祀愈发隆重起来,或许也是出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考量,就不再重复迎来观竞渡了。
更多的移借现象,表现在与正月、三月、六月等节日事项之间的相互移借。如亲友交往、避恶躲病、送瘟迎会等,其他节日也有类似的活动。其中,亲友来往,特别是姻亲之间和师生之间,在传统的重大节日均有类似的事项。一般而言,端午的亲友往来礼仪,大致像新年伊始的元旦那样进行。
如《通城县志》②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377—378页。(二十四卷,清同治六年活字本),“亲故以角黍、腌蛋相馈遗,盛者金花表礼,如‘正旦’。”
又如《安福县志》③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61页。(三十二卷,清道光三年刻本),“扎彩为龙舟,喧金鼓,往来波心,谓之‘竞渡’。……姻族拜庆,略如元旦,馆师尤有加礼。”
端午节使用植物清洁、避恶、祛灾、除病等仪式,在其他节日也有所借用。
如《保靖志稿辑要》④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43页。(四卷,清同治八年多文堂活字本),“正月十三夜,乡间老少妇女入城,在各寺庙观灯,谓之走百病。端午,角黍,蒲艾,雄黄酒,竞渡。”
又如《龙山县志》⑤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46页。(十六卷,清光绪四年刻本),记有, “三月,三日,女童摘地菜花簪首,曰辟疫气,或和作饭。清明,插柳叶于门,童男以柳圈首,亦曰辟疫。”
再如《直隶澧州志》⑥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56—657页。(二十六卷,清同治八年刻本)记有,“正月初三日,祛柏叶及女贞叶爆之,云辟蚤虫。卫生清洁事物。端午,禳毒,辟毒气。开聋,飞凫。除毒疾。取蟾蜍实墨于口,倒悬干之,磨以涂痈疖。六月,伏日,作汤饼,名辟恶。”
这里的几个例子,与端午插蒲艾于门首、小儿涂口鼻、佩香囊等行为来辟邪祛病大致类似。在正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等时节都可以进行这样的活动,只是变换使用了当季的植物,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些避恶祛病事项背后的思维结构和文化心理是一致的、共同的。发生“移借”的这些事项,集中在春夏,到了秋冬,便很少有祛病的记载了。
如迎神送瘟中像抬阁和送船等仪式,在地方志中也不少见,除了端午节,其他节日或不定期的某些日子也会举行,用祈禳仪式来祛除灾疫、求得平安。在关于湖北和湖南的地方志记载中,在民众生活中如此突出而重要的送瘟仪式往往会移借到其他时间段使用,种种记载可以与大端午的送瘟船相互映照,具体形式区别不大。例如,
《常德府志》①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49页。(二十卷,一九六四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记有,“正月,至十八日烧灯,以草为船,实以纸马,送至江浒焚之,谓之‘禳灾’。”
又如《慈利县志》②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64页。(十八卷,一九六四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万历本影印)记有,“正月,朔日,翌日,寺观僧道击铙鸣鼓,为各家收瘟,复作纸船,设忏悔以遣瘟。”
再如《永绥厅志》③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39页。(三十卷,清宣统元年铅印本)记载的大多为苗俗,其中有,“正月,秋千戏,延巫师,将五色纸禳之,十二日,民间共延巫师上刀梯以除瘟疫。”
例子中提及的正月习俗事项,借用了端午的五色符号所制作的五色纸,是用来除瘟疫的。正月的秋千戏,有时也移借到其他节日,端午习俗事项中至今还保留有秋千戏的活动。上述禳灾、收瘟等仪式,一般称为“打醮”,除了前引的正月外,在其他月份的事项中也时有所见。
《巴东县志》④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441页。(十六卷 ,清光绪六年刻本)记有,“平安醮 每岁三四月,邑民咸出金钱延黄冠诵经,分东西上下街,扬幡挂榜,市中贴过街幡,书‘解瘟释疫’、‘祈福迎祥’各四字。往年于设坛之三四日,装演杂剧、龙灯之属,名曰‘清醮’。近年无之,名曰‘素醮’。撤坛之日,以纸糊船送之江中,谓之‘放瘟船’。里中亦诵经二三日不等。”
《宁乡县志》⑤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680页。(四十四卷,清同治六年刻本),“端阳竞渡,以初一日划起。……以二十日为‘龙会’,二十五日为‘分龙会’。此二日有雨,谓可免旱灾。是月敛钱延僧道建坛,结彩张灯,鼓吹五七日,曰‘请水’,迎经曰‘游船’,以弭灾迓福,曰‘打清醮’。亦或以六月举行”。
《郧西县志》⑥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457页。(二十卷,清同治五年刻本)“旧于天河码头竞渡,于火星庙开坛作醮,扎舟送神,谓瘟火会。六月六日,是日为杨泗将军诞辰,沿河祀神演剧,各舟子赛会争胜。”
《保靖志稿辑要》记有,“三月三日,乡俗聚会,杀羊祭鬼,一说祭伏波将军。”
可见,祛疫送灾的祭祀仪式,人们根据需要常常移借而来搬演进行,内蕴意义相同,并不只限于端午。与大多数地方不同的是,后两种的记载中提及,祭祀伏波在三月三日出现,祭祀杨泗在六月六日出现。送瘟的活动不仅时间上可以有移借,地点上也可以变换,如例子中在码头边的火星庙举行,而竞渡争胜移借到六月六日祭祀杨泗时举行。六月六日,一般称为“过半年”,是端午—夏至由热转凉时节的另一节点,倘若不限于一个具体时间点,而从较大的时间段上去解读,也可归于与冬至—新年相对应的结构范畴内①关于“过半年”的讨论,参见宋颖:《端午节研究:传统、国家与文化表述》第三章,中央民族大学2007届博士论文。。在文献资料中,六月六日“过半年”中有不少民俗事项与五月五日“过端午”是完全相同的。
综上所述,节日事项在不同时间和场合中,出于近似的功能、使用目的和内涵意义而有可能出现相互挪移、叠加、借用等现象。在时间的纵轴上,同一年之内的不同月份之间,五月的节日事项与正月、三月、六月等相关事项之间还存在进一步比较和研究的可能性。
余 论
在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生活着多个族群,他们因地制宜而拥有着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李济从考古资料中提出过“多源中国”论,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苏秉齐“满天星斗”的文化阐述,无不指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在某种程度或某些层面上的共享与共有,并不能改变同时还存在着的多样性、多元性,甚至多源化的相互杂糅与整合的文化现实。
对于节日事项的研究,既不能以偏概全,又不能一叶障目。因此,上述讨论和例证使用“共有”“扩散”与“移借”等几个概念,来概括并解释节日事项的繁杂多样性。节日事项的“共有”,是建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了节日的整体性、延续性,不仅是某一群体的标志物,而且能够成为文明之间相互交往和对话的基础。而节日事项的“扩散”和“移借”恰恰是节日生命力的有效保障,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的智慧结晶,为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带着这几个概念去认识细碎的民俗生活细节,就能够透过现象看到节日的本质。
[责任编辑:冯 莉]
K890
A
1008-7214(2016)03-0093-09
宋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