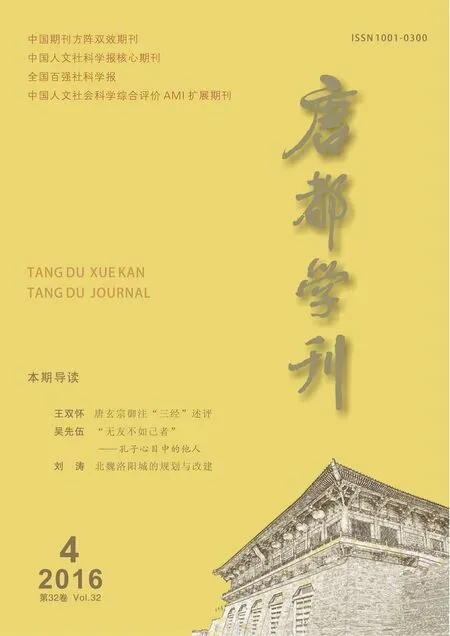价值观的制度化:何以必须与何以可能
张艳娥
(西安财经学院 思政部,西安 710100)
【博士论坛】
价值观的制度化:何以必须与何以可能
张艳娥
(西安财经学院 思政部,西安710100)
价值观的表现形态有制度化、知识化和生活化等多种形式,具有完整的制度化形态是核心价值观区别于一般价值观的基本表现。全面推进制度化建设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方向,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包含政治价值制度化和道德价值制度化的双重内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义性、加强具体制度和机制实施、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度化建设、推进道德的法律化及构建新型仪式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
在载体形式上,价值观的表现形态有制度化形态、知识化形态和生活化形态等多种形式,具有完整的制度化形态是核心价值观区别于一般价值观的基本表现,价值观的制度化能更有效地推进价值观的知识化和日常生活化。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十八大报告以“三个倡导”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性凝练,概括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虽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仍然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继续推进,但“三个倡导”的开放性表述无疑已经为此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当前一个时期,以“三个倡导”为方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就成为更紧迫的任务。全面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建设是培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工程的主导性方向。价值观的制度化为何必需?何以可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的科学内涵应如何把握?如何在实践中良性推进?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回答。
一、价值观为什么需要制度化
(一)制度化是价值观念获得统治地位的基本途径
制度化指的是从规则到行为等一系列社会范畴、现象实现规范化、常态化、通约化的过程,制度化既指的是制度的不断生成过程,也指的是制度获得普遍运行的结果。通过制度化的生成和运行,一种价值观念就可以从一种单纯的理论形态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物质性力量,从而获得核心和主导性地位,成为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建构是指通过由目标系统、规则系统、组织系统和评价系统等组成的体系,使主流价值观可操作化、可持续化,更好地获得实践运行的方式和流程。一个社会坚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就会要求相应的制度化规范来保障其实现。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所说:“宗教思想、道德思想、实践思想、美学思想也必须由强有力的社会集团承载,才能产生强大的社会作用。必须有人尊崇这些思想,鼓吹这些思想,捍卫这些思想,贯彻这些思想。要想在社会中不仅找到其在精神上的存在,而且找到其在物质上的存在,就必须将这些思想制度化。”[1]在传统中国社会,儒家价值观显然不单纯是一种观念化的存在,而是一种强大的制度化存在。仁、义、忠、孝等价值观通过科举制度、经学制度、氏族宗法制度等获得了一致而有效的存在运行支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平等的价值大旗,以价值启蒙和工业革命的双重力量共同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制度体系很好地承载和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追求。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2]从制度主义的角度看,制度化是价值观念获得统治地位的基本途径,核心价值观一定是能成功实现制度化确立并获得良好运行的价值观。
(二)价值观的制度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把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化”和“伦理化”两种不同的传统,而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历史实践为基础,在历史必然性与价值应然性的统一中来进行认识的。作为真理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166马恩正是立足于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出发来吁求更理想社会形态,这样就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要求在这一制度形态下要顺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要求采取相应的制度安排,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作为一种价值,社会主义内含着多方面的价值内容和价值诉求。在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总体价值目标下,既包括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物质丰裕的物质性价值追求,也包括能实现人们对高尚、文明、幸福、和谐等精神追求的精神价值,同时还包括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需求的政治性价值诉求。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由于历史局限和理解偏差,往往存在着将价值的社会主义与制度的社会主义相割裂的失误。这种割裂一方面表现为把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具体制度原则等同于社会主义,有意无意地忽略社会主义蕴含的丰富的价值关怀和价值要求;另一方面表现为将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割裂化为单一价值,要么片面强调物质价值,重蹈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覆辙;要么完全离开物质基础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从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中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全面发展,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基本路径。通过价值观的制度化,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等社会主义价值渗透进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和体制运行之中,获得坚实的支撑;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治理体系也在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的价值指引中,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体现出更强大的吸引力。
(三)价值观的制度化是复杂性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进入新的境界。国家治理是一个复杂性概念,从范围上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政党等多个领域;从参加主体上包括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多种类型治理主体;从治理方式上涉及政治制度、法律、价值观、伦理道德等多种治理手段。能在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轨道中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作用,将多个治理领域统合衔接,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手段,从而达到“善治”的效果是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方向。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高度重视制度治理体系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高度重视价值治理、道德治理的强大功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4]49价值治理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广义上的价值治理是指强化和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自觉与价值导向,充分发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等多种非正式制度因素的治理功能;狭义上的价值治理是对“价值失范”进行治理,解决价值问题、化解价值矛盾、提升价值信任[5]。价值治理的作用途径有软性和硬性两种机制,软性机制是以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自觉信念的养成来发挥作用的;硬性机制则主要是通过价值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来进行的。在社会面临利益大转型、大分化时期,价值多样化带来的复杂性及挑战尤为突出,这时更多借力价值观制度化、法律化的硬性机制来强化价值治理和国家治理就显得更为迫切。
二、价值观的制度化何以可能
(一)“价值—制度”互动转化的理论指导
价值观念在本质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制度作为一种政治法律规则和硬性权力存在,二者之间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转化的。对于价值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转化有大量的理论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制度经济学的奠基性人物诺斯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区分性研究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诺斯将以某种明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称为正式制度,将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不成文的限制称为非正式制度。诺斯认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系统中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价值观念可以转化为正式制度,这种转化表现为两种形式:诱致性正式制度的生成直接来源于各种非正式制度因素综合而成的自发秩序由“合理”到“合法”的演化;强制性正式制度的生成要想获得成效,必须考虑与道德文化、社会价值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保持契合性和互补性,并且通过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建构新制度。诺斯关于“正式—非正式”制度的相关研究揭示了“价值”与“制度”间互动转化的多重面向,从理论上回答了价值观制度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围绕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权力制度系统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呈现出清晰的理论脉络,‘意识形态—制度’的分析框架构成了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一个独特视角”[6]。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揭示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与其经济生产关系及制度上层建筑间的相互支撑性,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观念实质上是商品交换、商品流通的自由;所谓的“平等”实际上是保护资产阶级财产私有的平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过演化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形式,已经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制度上层建筑牢牢地融为一体。这些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分析,为研究和揭示不同制度形态与相应价值意识形态间的关联互动关系,确立了科学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基础。在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革命运动中,列宁系统思考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巩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相互支撑的理论问题。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思想突破了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观点,揭示了社会制度形态的建立可以具有相对优先性,在上层制度模式的相对优先建设中,先进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建设要同步跟上的内在规律。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对“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制度统治权”的关联、转化、支撑关系进行了更为系统全面的思考和回答,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制度”的分析框架更加成熟。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制度”互动转化的理论研究以及对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制度策略中的重要地位的理论揭示,为我们思考和解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中“价值的制度化”和“制度的价值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指导。
(二)价值观制度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将一种代表先进文化的思想观念体系转化为一种政治体制、宪法、法律或道德训诫等制度化形态的实践是一种新兴社会形态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常态性选择。中国传统思想异常丰富、复杂,有许多思想流派,但就总体性影响而言,没有哪种思想能超越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儒家思想影响的深远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不断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融合而渗透到方方面面的。儒家的制度化有许多形式,包括孔子的圣王化、儒家经典的经学化、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选举制度、儒生与权力的结合等[7]。同时,儒家观念在社会控制体系和制度设计中得以全面渗透和体现,上至朝廷的礼仪、宗庙的祭祀、国家的组织与法律,下至社会礼俗乃至乡规民俗,都灌注着儒家的精神与思维原则。从实践效果看,儒家的制度化是非常成功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探讨社会主义价值观制度化建设有很大的借鉴价值。近代西方十七八世纪的启蒙运动,通过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等观念的传播以及新兴资产阶级逐步获得生产力武器的主导权而被逐步落实为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而实现了启蒙思想“制度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制度化成为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的《独立宣言》《联邦宪法》《解放宣言》,核心宣扬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三个文件也是美国的开国之本、立国之本,在整个国家制度建构中起着主导作用。同时,爱国主义和美国传统教育的法规化,公民教育的系统化和组织化,政治教育和各种管理手段的紧密结合、与个体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与法律纪律手段的紧密结合,都是美国价值观教育和国家治理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新加坡从立国之后,非常重视文化价值重建在法治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努力建立既与西方市场经济相适应又富有东方文化优良传统的新型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将文化价值重建与青少年和整个社会的公民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在价值观的制度化上,道德的法律化是新加坡运用较多的方式,法律运用强制力来保护一切被认为良好的道德风尚,这一做法取得了良好的国家治理效果。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的双重内涵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主流价值观都包含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两个大的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政治价值观集中体现一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性的内容,是与特定阶级、特定制度形态紧密相连的;道德价值观是价值观念系统中社会公民层面的基本价值要求和行为准则,道德价值具有阶级性,但相较于政治价值,道德价值与特定制度形态间保持着相对较远的距离。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相接近的状态中,道德价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爱国、诚信、友善等道德价值几乎是所有现代国家对公民的一种普遍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包含政治价值观制度化和道德价值观制度化两层维度,二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内在统一。
(一)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制度化
在与不同社会形态、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区别的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价值。资本主义讲自由、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也讲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虽然他们之间具有相通性,但因为这些政治价值理念借以实现自身的具体制度安排不同,因而就具有了根本不同的内容实质,使得它们得以区别开来的正是政治价值观不同的制度化模式。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制度化,就是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平等、自由、公正、人本等价值全面渗透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之中,赋予社会主义制度正义性的实践过程。从本质上讲,制度表征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存在状态,随着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3]412,无产阶级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确立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利用国家政权确立和巩固新的制度形态模式,这使得原先建立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法等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价值观念所代表的内容扬弃了其局限性,变得更为真实、更为先进,并且具备了得以全面实现的坚实制度支撑。政治价值观的制度化首先是通过社会形态层面各项基本制度的建立来实现的,包括国体政体制度、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政党制度、民族制度等各项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基本制度安排的不同决定了制度形态间的差别,也为不同政治价值观提供了各自的实体支撑。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共同纲领》《五四宪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等陆续建立起来,从国家权力制度的层面保证了人民至上、平等、自由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落实和运行。其次,政治价值观的制度化,还离不开各项具体制度和体制的完善和良好运行来加以保障。如果没有完善、自洽、合理的具体制度和机制,再好的基本制度设计都会流于形式,其承载的政治价值也因不能在实践中发挥效力而发生变异。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而言,具体制度和机制层面的问题在当前更为突出。再次,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制度化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化建设,以制度化状态保障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在当前,主要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教育制度、学科制度、学习制度、宣传制度等环节在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体系”。
(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的制度化
社会治理从来都是以道德和法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使得简单伦理道德的正义说教显得软弱无力,道德价值的制度化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道德价值的制度化是指以系统化规则来建构和强化道德价值实践中的职权与责任关系,形成道德价值践行的约束与奖惩督促机制,形成某种稳定的规范体系,实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自觉与外部驱动相结合。道德价值制度化有多种实现形式,道德的礼仪化和法律化是两种最主要的方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成功实现了以“礼”为核心的道德制度化体系[8],“德政”为主,“礼”与“刑”为辅的社会治理格局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在今天的社会转型期,新型礼仪制度的建设不失为道德价值观制度化的重要选择。在现代社会,道德的法律化是道德价值制度化的最主要方式,许多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前列。通过道德立法、制度结构间的功能互补互济、社会赏罚的制度化、法规化,大大提高了道德价值的治理效果。如通过完备的公民诚信体系和行政伦理规范,把个人道德品行与个人的利益得失紧紧捆绑在一起,使道德价值的力量不再疲软的做法就具有普遍价值。
从联系性上看,政治价值观的制度化与道德价值观的制度化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是内在统一的。政治价值观的制度化要解决的都是关涉社会制度形态和国体阶级属性等的重大问题,会直接决定和影响公民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基本格局;道德价值观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群己边界的契约性问题,能有效激发公民的公共意识,促进理性的政治参与,道德价值观的制度化对政治价值观建设会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政治价值,既是制度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公民精神文明的成果,其建设不能仅仅停留于政府、行政层面的制度或机构等的重组及改革上,而应该同时着力于公民素质的提升和政治的实际参与上,其实行离不开公民道德制度化建设的支撑。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完善基本制度的正义性建设,用制度安排保障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立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制度化,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现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在当前阶段,由于制度建设仍然具有滞后性,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存在状态大多以宣传性的意识形态形式存在,在基本制度建构的纳入和体现上还很不充分,这大大影响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加强价值观的制度化建设首先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义性建设,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其制度载体间实现无缝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要更加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利平等。目前,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对公民民主权利落实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公民平等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等都有待更加全面落实;对特殊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还存在漏洞,特权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有待完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经济运行和分配秩序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合法的地方;在社会管理制度上,城乡分割、权利不均等的制度安排仍然发挥着作用;文化制度上,资本力量对精神、教育、文化的侵蚀现象值得高度警惕,如此等等,都是制度正义性不充足的集中体现,这些缺失都会对自由、平等、公正、诚信等价值观的落地生根产生致命的影响。长久缺乏基本制度安排支撑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在实践中流于形式。
(二)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用制度实施来约束和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
与基本制度安排相比较,一个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的变迁更新、落实运行更主要地依靠政策、体制、机制等非基本制度层面的制度支撑,这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尤其如此。一方面,具体制度较详细地规定了一定社会领域中若干具体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能使基本制度安排的理念和原则得到体现。如基本政体制度下包含着党政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选人用人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制度,这些具体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决定制度系统的实施运行情况。另一方面,对于价值观的培育而言,体制机制建设密切联系实际,直接在实践中运用和检验,是价值观制度化更集中的体现领域。在体制机制建设上,应将制度实施约束和规范价值观落实的重点放在社会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激励机制建设上;在动力和平衡机制上,重点是理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为社会倡导的创新、艰苦奋斗、自强等价值与公平、友善等价值达到有效统合提供现实有力的制度系统支撑;在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上,重点放在提高价值、道德失范行为的付出成本上机制建设上,形成保障“德福一致”及促进主流价值利益最大化的运行机制。
(三)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度化建设,形成制度化核心价值的教育传播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总纲和指南,不断推进它的制度化建设,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度化教育传播体系,必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的支撑基础。思维头脑中的革命与改变要真正变为物质世界中的革命与改变,制度是其中的决定性环节[9]。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化建设可以从三个环节着手: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科建设,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在学术研究和学科体制上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持续发展。作为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的时间还不长,还处于由大到强的发展阶段,尚未真正成为学科优势。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的启动实施,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达到“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的目的。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机制的规范化与大众化,在教育、宣传、普及制度上确保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常抓不懈。在市场化和深度全球化时代,来自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人心,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任务极为迫切。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管理规程、构筑全面的传播平台、健全引领、管控、评价的有效机制,激发多元传播主体的共同参与等都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宣传体制机制建设的有效路径。三是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机统一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和制度体系的三元互动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四)推进道德的法律化建设,以法律制度的硬约束保障道德价值的生成
道德法律化的正当性是来自于道德自身的非自洽性。从法的起源来说,法律是弥补道德自觉协调力的不足而产生的一种强制性的规则,“当道德对应受保障的利益无法维持,则就会诉求于法律形式,致使相关的道德理念和原则融入法律”[10]。道德诉求的是人心,良心、信念是其控制力的发生机制,当社会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复杂化后,光靠道德的内控力已经不足以推动人们实现从知到行的普遍转化,就需要在客观上借助法律外力的强力型塑。通过法律规范确定性、具体性信息,将可为与不可为界限明确规定,能普遍激发社会成员对规则的遵从。在今天,推进道德的法律化也是有效助力社会主义核心道德价值建设的可行性路径,可以从三个方向上进行:一是以立法形式尽可能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明确化、具体化,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如将家庭道德中的抚养、赡养等道德规范,职业道德中的诚信、公私分明、不收取贿赂等要求,公民道德领域的爱国等准则具体化、规则化,明确规定违反者的法律责任,使之便于操作。二是将抽象性的道德原则引入法典,通过立法规定准用性的道德规范,使得上升为法律规范的道德原则可以成为法庭审判的依据,达到既合法有合情的效果。三是对较高层次道德行为的法规激励。如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和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刑罚性规定等。在推进道德的法律化建设中,也要注意把握好合理界限,要区分层次,处于较低层次道德价值容易被法律化,而处于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不易被法律化,防止道德绑架行为的发生。同时,不能混淆法律和道德两种调节手段的互补性,要充分发挥道德的自律性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
(五)推进新型礼仪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供具象化载体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研究揭示的那样,人们的观念行为世界是由信仰(思想方面)和仪式(行为方面)两个层次范畴组成的,信仰、思想体系并不能单独地存在,唯有依赖于社会仪式才得以表现。特定仪式是集人、物、语言、符号、行为等多种要素于一体的特定意义的“综合表述”。一种主流价值观都需要借助一些独特的礼仪仪式来具象化体现自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新型仪式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的重要实现形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使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建立和规范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4]95推进社会主义新型礼仪制度建设,包含着以下几个层面任务:一是继承和改造一些传统仪式,中国传统仪式中很多体现孝道、感恩等价值观的仪式,应当很好地继承,同时,传统中存在的一些与现代法治、平等精神不符的仪式应当引导改造。二是创新仪式的形式和内涵,发挥重要节庆日和政治纪念日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中的独特优势。同时激活一些被遮蔽的仪式,如对中国二战胜利的相关纪念能激发人民对国家的责任感,增强民族凝聚力。三是制止和取缔一些落后非法仪式,在社会转型期,人群的价值失范在很多的婚丧嫁娶、邪教信仰的落后甚至非法仪式中表现得很典型,恶俗闹洞房、雇人哭丧、打着“灵修”名义的邪教集会仪式等需要加以引导和规范。通过仪式建设,使不同的承载主流价值诉求的礼仪在社会现实中转化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具象化规范实践,真切地融入大众生活中,就能在极大程度上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5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5]石永泽.以价值治理为文化强国提供精神动力[N].文汇报,2014-02-10.
[6]张艳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分析范式的三种理论图景:从列宁、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J].天府新论,2015(2):8-15.
[7]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
[8]郑文宝.道德制度化建设路径探微——基于孔子对“礼”的实用主义建构[J].道德与文明,2015(2):65-68.
[9]平飞.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化的中国经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7):68-76.
[10]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M].陈林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55.
[责任编辑王银娥]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for Values’ Institutionalization
ZHANG Yan-e
(Xi'a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Xi’an710100,China)
Values take on various forms such as institution alization, knowledge and life, the core values with a complete institutionalized form is its basic expression, separating it from the general values. Promotion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well as the intrinsic needs of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stitutionalization contains that of political values and moral values. The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value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re as follows: to perfect the justice of the basic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cret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ization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o boost the moral legalization and build a new service system.
values;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stitutionalization
B27
A
1001-0300(2016)04-0090-07
2016-03-08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新型礼仪制度建设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机制研究”(15JK1286);陕西省社科界2015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塑视角下的仪式制度建设问题研究”(2015Z009)的阶段性成果
张艳娥,女,陕西西安人,西安财经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