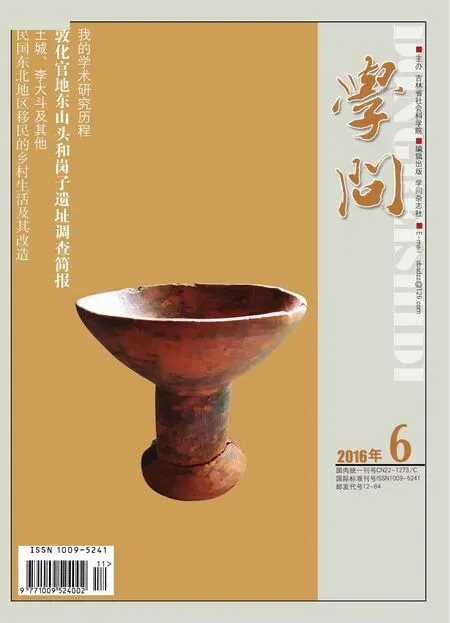张学良、中共与“抗日同志会”关系发微
刘东社
张学良、中共与“抗日同志会”关系发微
刘东社
[内容提要]“抗日同志会”既是张学良创建的联共抗日秘密组织,又是其“独立政党活动”的产物。它绝不能简单等同于东北军少壮派,但大体属于中共所称之“西安左派”的一部分。该组织在联共、抗日、捉蒋等方面虽有贡献,但其领导骨干却以极左面目反对中共与南京和解,反对释蒋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东北军东移,并一再拒绝中共指导,与中共的路线、主张背道而驰,最终以“二二”事件为契机,导致了其组织无形解体。
张学良“抗日同志会”少壮派西安左派“二二”事件
对于张学良创建的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以下简称“同志会”)的产生、发展、消亡过程及其性质、作用等问题,学界曾有少量论文做过一些探讨,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和张学良的传记著作一般也都有详略不等的介绍。然而,由于该组织当年处于秘密状态而文献资料甚少,以往的研究大多只能依据可信度参差不齐的口述回忆资料为主,遂使得该组织的幕后真实属性及发展趋势,张学良、中共与“同志会”的深层关系,“同志会”与东北军少壮派、“西安左派”的关系,“同志会”之极左派与“二二”事件的恩怨纠葛等问题,迄今尚难获得较为全面、准确的认识。笔者拟以档案资料为主,就上述问题再略予探讨。
一、“同志会”创建情况之若干辨正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首次肤施密谈前后,就已经考虑过要在东北军中建立自己的政治核心组织。在与中共交往的过程中,中共方面也屡次向张学良作过类似建议,并提醒张氏不能仅仅依赖或满足于部属对自己的个人信从。1936年夏,张学良曾约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刘鼎等人商量,提议东北军应有一个政治组织,可定名为“抗日同志会”。他要求以参与这次商谈的几个人组成筹备会,并要刘鼎拟定个章程①。7月末,筹建工作开始运转。②8月29日“艳晚事件”后,筹建步伐明显加快,不久即在西安张公馆会客厅宣告正式成立。不过,有关该组织创建的若干细节问题,在各种资料和论著中尚有种种不同说法,实有考辨的必要。
1.时间。“同志会”正式成立的时间,一般史书或笼统称在1936年9月,这自然不会有错。但究竟在9月何时?应德田回忆为9月初③,研究者或认为在9月初,或认为在9月中旬。1936年9月2日《朱理治给董威老兄并转钟哥的信》中称:“现在同志会已经开始”④,这或许是9月初说之档案依据。然通观朱理治报告全文,所谓“开始”显然指筹备创建工作之开始。另据1936年10月11日朱理治的报告称:同志会“成立二十多天了”⑤,依此前推20余天,则正式成立的时间无疑应在9月中旬。
2.首批会员人数与名单。“同志会”首批参加者即创建者究竟有多少人?或谓13人,或称15人。朱理治的报告称:“那天开成立会时,在到会的十三个人中,我们倒有七个是同学。”据此,则参加成立会者似乎应为13人。但朱理治又说:“而领导机关,亦是由张圈定的”,“但是圈定的结果,七个中央委员中,我们连一个都没有能够参加”⑥。7个中央委员再加上7个“同学”(即中共党员)和张学良,则正好是15人,但却与13人的总数相矛盾。因此,笔者颇怀疑朱理治报告中的数字有误。当然,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即创建者共15人,但当天到会者仅有13人,内情是否如此,因资料不足,现已难以确知。
至于首批参加的15个人究竟是谁?各种史书和回忆资料所列名单均不齐全,一般公认者有:张学良、应德田、孙铭九、刘鼎、苗剑秋、刘澜波、苗浡然、宋黎、解方(解如川)、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陶(贾国辅)等。另有回忆资料提及,栗又文曾参与过该会简章的起草⑦,高崇民亦曾修改过简章⑧,但此二人是否为“同志会”成员,尚须进一步研究,起码作为首批会员的可能性不大。⑨亦有人认为出席成立会的还有关时润(关沛苍)、杨心梅二人⑩,孙铭九也回忆关、杨为首批会员。⑪关、杨均为张学良随从参密室重要成员,参密室及其前身(总部副官处人事科特别人事股)先后受孙铭九、应德田直接领导,其成员(应德田回忆有11人)后来全是“同志会”会员,“同志会”秘密会议亦多在参秘人员居住的张公馆东楼会议室举行。以此观之,关、杨为首批会员之说较为近真。上述15人中,刘鼎、刘澜波、苗浡然、宋黎、解方、贾陶均系中共党员,即朱理治所说的“同学”,至于另一位“同学”究竟指谁,尚须进一步查证。
3.领导机构。一般史书和回忆材料多谓,还在筹备“同志会”时就内定张学良为主席(或称会长),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部长。正式成立时,另以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部长,车向忱为群众运动部部长,何镜华为军事部部长。1936年11月份又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长,刘鼎为教育部长,苗浡然为宣传部副部长。但此说法是否准确,实有待商榷。其实,朱理治报告里讲得很清楚,按“同志会”章程草案的规定,作为“抗日领袖”的张学良与其被称作主席或会长,还不如称作“总理”更为贴切准确。其他如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刘澜波、刘鼎等人的任职,大体上准确。至于车向忱担任部长的那个部,早在9月2日朱理治的报告中就提到,杰兄“有做同志会青年部(长)的希望”⑫。 10月11日的报告中亦称,同志会“自从成立之后,会也不开,各部工作也没有见到,除掉青年部因为我们有So参加,起了推动作用,做了一些工作之外。”⑬So即宋黎,宋黎曾回忆自己担任过“群众运动部部长助理”。可见从朱理治的屡次报告看,该部应称青年部而非群运部。
二、所谓“独立政党活动”及“第二党”倾向
据应德田回忆,在筹建“同志会”时张学良曾说过,建立这样一个核心组织就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中枢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⑭“同志会”吸收新会员时都要举行宣誓仪式,并有专门的誓词⑮。该会成立后,即侧重于在长安军官训练团中活动,虽组织发展缓慢,但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成员还是扩充到了七八十人,并在促进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接待和保护红军代表及往来人员,组织和发动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等。因此,一般论者多视“同志会”为联共抗日的秘密组织。此论固然正确,但却未必全面,“同志会”的属性恐怕还远不止于此。
《黎天才自传》曾言及,1936年夏季时,张学良“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我写具体方案”⑯。“同志会”成立时,几乎完全是模仿政党(尤其是国民党)形式,设立有中央委员会,由张学良亲自圈定了7个中央委员,11月后又吸收了两名中共党员为中央委员。据朱理治报告称:“最(有)趣的,那天开会的章程草案原由Y与LT起草,上面写着‘总理有最后决定一切之权’,事前C便用笔把这句勾掉了,但是到了开会时,草案上又写上了。C便提出:‘为什么我已经勾掉了,现在又添上来呢?’Y说:‘这是全体的意见。’结果,C便在‘总理有最后决定一切之权’之上加上‘暂时’二字。这种现象当然并不足奇,因为Nea今天还是刚由封建集团转变过来,并且它又是一种武装部队,集中多于民主,这‘暂时’也许不可免。”⑰可见,应德田和刘鼎起草的章程草案,无论是“总理”这一称谓,还是“总理有最后决定一切之权”的规定,无疑都是抄袭了中国国民党党章的旧文。至于上以领袖为“总理”,下设书记和各部部长与副部长(或部长助理),也都明显反映了其政党色彩。
此外,“同志会”发展新会员都要进行严格审核,加入者须进行庄严宣誓,组织又有明文的章程规范,都体现了其政党特色。现代政党在组织上的排他性,在该会章程中亦有明确规定。举行成立会时,“所通过的章程规定着,凡参加过其他任何政党活动的,必须在加入同志会之先报告出来”。以至于后来受“同志会”的影响,刘鼎曾两次向朱理治提出,张学良、孙铭九等人向他索要加入“同志会”的中共党员名单,“使他无法对付”,因为“人家对我们太好,什么都和他讲,使他不好拒绝人家的要求”。因此,朱理治在报告中一再强调:张学良“的组织CA,也正是他的形成第二党之意图”,主张中共应在“同志会”周围“发展各种群众组织,使其不至走到第二党的道路”。⑱显然,创建“同志会”既表露了张氏的第二党意图,且可视为其从事独立政党活动之产物。
三、“同志会”与东北军少壮派和“西安左派”
在不少回忆资料里,常常存在着一种将“同志会”等同于东北军少壮派的倾向,以至于影响到某些论者即径称:“抗日同志会,亦即东北军少壮派,其政治纲领是抗日、反蒋、联共。”⑲然而,事实可以证明,“同志会”与东北军少壮派之间显然难以简单、绝对地划上等号。
首先,西安事变前后的东北军少壮派,指1936年6月张学良开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后,“在王曲受训的东北军学员,年岁都比较轻,一般人呼之为少壮派,自此而有东北军少壮派之名”⑳。前述“同志会”虽然酝酿较早,但正式成立已晚至9月份。可见,仅从诞生时间的早晚而言,两者间就不宜划上等号。
其次,东北军内之少壮派,本身就不是一个精确、严谨的称谓,也并非什么成型的有规范性的组织或团体,更谈不上有较为统一的思想信仰、政治志趣,而且所指对象和范围在不同时期并不固定,如早在张作霖时代,奉系内部就有所谓元老派(旧派)与少壮派(新派)之别,新派内部还有陆大派与士官派之分。而所谓“少壮”,通常只表明他们较为年轻,血气方刚;一般思想上不太守旧,有一定的朝气;更主要的是他们多为团、营甚至更低的中下级军官、参谋、职员等;与军长、师长级的领兵官相对而言,他们处于暂时“无权”而又有上升趋势的状态。“同志会”则是一个极其规范的带有明显政党色彩的秘密组织,它有自己一整套的领导机构、组织章程、入会程式,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更有思想信仰或政治立场上的大体一致性。显然,少壮派只是对军中某一特殊人群的泛泛称呼,它与组织上严谨、成熟的“同志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最后,从人员构成及活动范围来看,东北军之少壮派当然以军人为限,也主要在军内活动。“同志会”成员固然绝大多数身负军职,但也有诸如东北大学秘书长周鲸文、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金锡如、东北中学校长孙一民等非军职人员,其活动范围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军内。
当然,由于“同志会”的主体多为青年军人,成立后又侧重于在军训团里活动,一般人常将“同志会”与少壮派混用,这本身并不难理解。中共高层也常用少壮派来指称“同志会”,有时也使用过“激烈分子”、“激烈派”这类称呼㉑;在很多当事人解放后所写的回忆材料中,“激烈派”或“激进派”这类称谓出现的频率甚高。但须指出,此际的少壮派或激烈派,只是特定场合或特殊语境下的临时指代称谓,并不意味着中共方面不知道“同志会”与少壮派之间的差别。其实,在1937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报告中,对“同志会”与少壮派的区别做了非常清晰的说明,即东北军“内部有少壮系及旧军官系的斗争。少壮系有抗日同志会,该会与我们合作,政治上表现左倾,有一部分师团长在该会影响下。另一方面为军长及总部各重要职员形成之旧军官系,他们对我们尚无恶感,对同志会有成见,政治上较差”。㉒
与此相类似的是,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亦屡次在特定场合下将“同志会”称呼为“左派”、“西安左派”、“西北左派”等。在当时,中共主要以对待抗日问题的立场、态度为标准,有时参考在联俄、联共等问题上的态度,将全国各地各阶级阶层、各社会组织、团体、各部队、各派系中的所有人群,都划分为左中右三派,或称之为抗日派、中间派、亲日派。“同志会”无疑属于左派,也是西安或西北左派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在西安或西北的地理范围内还存在着其他左派力量,因此,也就不能在一般意义上将“同志会”与西安左派简单等同起来。
四、“同志会”的严重弱点及与中共之关系
对于左中右三派,中共的基本方针和策略相当明确、稳定,即“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㉓。中共在不同场合下阐明其对左派的方针策略时,曾经使用过联合、赞助、扶助、援助、推动、团结、巩固、加强、领导等词汇;对中派显然以争取为主,有时也使用过分化、影响、吸收等词语;对右派则完全以反对、排除、打击、打倒为主旨。
既然对各派采取了这样的方针与策略,中共对属于左派的“同志会”的立场与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然而,“同志会”对中共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与态度?其与中共的关系又究竟如何?在此,我们必须结合“同志会”在政治立场上、领导体制上、组织上、工作作风上所存在的严重缺陷或弊端,才能够真正理清这些复杂问题。
1936年春夏间,随着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日渐密切,随着红军结束东征转而发起西征作战,“东北军内部在抗日与剿共问题上,发生了左右派的分化。一部分的先进份(分)子,主张违反南京的意志,停止内战,并和红军联合实行抗日;但另一部分则主张继续执行南京政府的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继续剿共”㉔。在此背景下,中共大力支持张学良筹备、组建左派的“抗日同志会”。不过,此际中共执行的是“抗日反蒋”的方针策略,受此影响,“同志会”骨干成员一直有着强烈的反蒋情绪。可是,8月中下旬后,中共转取“逼蒋抗日”的政策,其核心要旨在于争取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派,寻求国共之间的妥协和解以结束内战,通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开展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一旦国共两党能够达成妥协合作,该政策的前景无疑会走向联蒋甚至拥蒋以共同抗日。对此重大转变,中共的许多干部、党员一时都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而“同志会”的多数骨干成员则始终就未能适应或完成这一转变,他们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依旧停留在反蒋的偏激极左状态。
其具体表现是,西安事变前在政治上反对中共与国民党谋求合作,“反对我党争取南京抗日的策略”㉕。事变期间,所谓的左派领袖应德田、孙铭九辈,虽也曾积极参与了西安兵谏等行动,但“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㉖。在西北善后问题上,他们顽固“反对和平方针,坚决的主张内战,站在小团体的个人利益上,阻碍东北军内部的统一,他们在群众前反对甚至于辱骂我们党的主张”㉗。1937年春,东北军东调豫皖苏时,还有“一部分参加捉蒋杀王的同志会以及一部分左的群众及个别同志,曾经计划着反对移防,并欲将部队拉到红军中来”㉘。
在组织或领导体制方面,“同志会”的缺陷亦非常突出。前引朱理治报告曾谈及“同志会”内部“集中多于民主”,领袖个人独断色彩十分明显。好在作为“抗日领袖”的张学良既拥有崇高威望,又与中共关系极为密切,有他掌控,“同志会”尚不致在大方向上出错。然作为东北军的统帅,张氏事务繁杂,“同志会”的日常管理权力遂逐渐落到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手中,即由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小中心”㉙,实际控制着该组织。及至张学良送蒋回京后一去不返,“同志会”就变成了这些极左派推行其主战主张的重要工具。
另外,“同志会”自酝酿筹建之日起,即暴露出组织过于狭隘和对中共抱有极强戒备心理的特征。还在1936年9月2日,朱理治就已批评说:“现在同志会已经开始,只是这种组织与目前政治上的问题,犯了同一种毛病。DE把他看作比CP还要严密,认为假使有一个人泄露,最高负责人便不得了,便要误大事。”㉚举行成立会时,“所通过的章程规定着,凡参加过其他任何政党活动的,必须在加入同志会之先报告出来”。朱理治曾提议,“对CA,我们的策略,是将我们的同志全体参加,大量到下面开辟各处工作,发展各军、师的组织,使P在各单位起领导作用。并在P、L、CA之周围发展各种群众组织,使其不至走到第二党的道路。同时,对于中央委员会,采取善意的同志的帮助、劝导与批判。最近,LT、So对于S、Y在这种态度下,谈过几次,起了相当的作用。近来组织上已有相当的发展,吸收了我们的同志参加了各部的工作”㉛。虽说有此些微改变,但“同志会”依旧保持着“极端关门”及对中共戒备的立场。
如前述张学良、孙铭九曾转托刘鼎向朱理治索要加入“同志会”的中共党员名单;朱理治亦径言,张学良提拔、重用干部的原则是“以对他忠实,且他能把握住为条件”;张之提用中共党员,也“是在这种目的与意图之下,即希望他能放弃自己的立场,完全为张服务”,均是这种立场的反映。朱理治也承认,“东北军目前急迫的需要有一个本身的领导的组织,这在今天是不能由党来代替,而必须由东北军本身中的优秀与先进的左倾的分子组织起来,才能成功。同志会的各种工作,事实上非党的帮助与指导不能开展,但是他们对于我党的同志都是很大的戒备,而他们本身都不能使自己的工作发展起来,现在差不多还是停留在原有状态之下”㉜。
朱理治事后总结说,1936年秋末至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中间的分子以及过去右派的分子,都一致拥护张副司令的抗日主张……过去造成东北军内部分化的政治根源,一般的说是不存在了。所以党在那时单独组织与支持左派的策略,已是不适用当时的政治上的需要了,党在那时,应当迅速的(地)把左派转变为整个东北军的统一领导机关”㉝。而且张学良“在双一二事变前的一月,即有意把同志会转变过来,使同志会与李天民、王回波等各派共同造成东北军的统一的团体”㉞,为此“同志会”还制定“并通过了两个月内扩大百廿人的计划”㉟。
当时,朱理治曾向中共中央建议“党立刻的(地)领导这一转变”,即将“同志会”立即转变为“广泛的群众性质的组织”。似乎周恩来曾就“同志会的性质及其与救亡会之关系及党对他的策略”等问题复信西安,并不赞同过早转变。事变结束后,朱理治重提此事,也认为“可惜东委内个别领导同志不同意这种主张,不积极的(地)领导这一转变,结果这个统一的组织未能形成。虽是双一二之后,党在中央指示之后,曾为统一左派同志会及高级带兵官进行一些努力,但因为没有整个的计划,没有一致的动员,结果仍然不能消灭其内在之矛盾。没有及时的(地)把左派的组织转变为东北军统一的组织,是这次一切损失(指二二事件带来的损失)的祸根”㊱。姑勿论朱理治这一判断是否正确,它起码说明了“同志会”始终未能改变其独裁、包办、关门、狭隘等组织缺陷,所谓两月扩充120人的计划也自然泡汤。
“同志会”自成立后,不仅组织发展缓慢,工作进展不大,而且宣传空洞肤浅、行事偏激过左及夸夸其谈等作风也一直未有大的该观。如张学良出资创办的《西京民报》,无论在事变之前还是事变期间,都在大作反蒋文章,始终未能把蒋氏南京政府与亲日派真正区别开来。再如“东救”开成立会时,因为迁就应德田等人的意见,将东北军中国社党与国民党的基本群众排除在外,“也没有能够设法罗致东北名人参加或担当一定的名义”㊲,更是将“同志会”的褊狭作风带到了群众救亡组织之中。西北善后期间,“同志会”虽“坚主强硬,但少具体办法,对军事又少了解”,只是一味鼓噪主战、救张,却全然不考虑国内大局和抗日大计。
概括言之,中共始终大力支持、帮助“同志会”,并不时予以指导和善意的劝导、说服或批评;而在张学良掌控时,“同志会”对这些指导与批评也基本能予以接受或以较客气态度对待之。及至张学良离陕后,“同志会”在应德田等小团体控制下,完全站在宗派主义的个人利益的立场上,对中共的劝导与批评或以阳奉阴违的态度应付敷衍,或干脆公开拒绝甚至反对。他们不仅在群众中散布辱骂中共和平解决主张的言论,甚至为了逼迫红军参与对南京政府中央军作战,1937年1月27日晚,孙铭九等人还率领数十名少壮军官向红军代表团下跪请愿,企图胁迫周恩来等人同意其主战主张。1月末,在宁陕和平解决善后问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应德田等人又煽动东北军少壮军官召开所谓渭南会议,无端否定和平解决的议案。同时,这些极左派还秘密拟定了暗杀主和者的名单,其中既有东北军高级领兵官,亦有中共领导干部。至此,“同志会”的极左派已经彻底走到了与中共路线主张背道而驰的方向。
五、“同志会”的无形解散与中共的总结反省
继渭南会议之后,在西安王宅会议上,西北三方领导人还是坚持了接受“甲案”、和平解决善后问题的正确主张。随之1937年2月2日,在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的策划、指挥下,少壮军人发动了残杀王以哲、徐方、宋学礼、蒋斌等东北军将领的“二二”事件。
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1时,周恩来、博古即向陕北中央报告了这场东北军“内变”。次日凌晨,周、博又向中央报告:“我们严格批评杀王之错误”,但“少壮派犹未服,坚持主战,十七路军各旅长亦响应之”㊳。至2月3日下午,内有中共方面的严厉批评,外有东北军前线部队自行撤退,“东北军各将领均欲追究祸首”,“右派纷纷投降反攻,刘多荃甚至对西安警戒,对潼关接头,扣留少壮旅、团长”。眼见大局崩坏,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这才“悔过认罪”,在周恩来安排下,由刘鼎秘密带领他们潜赴苏区以“离队远避”。此际,中共的基本策略是东北军必须力求团结,认为何柱国、于学忠等人既无能力亦不可信任,须推出董英斌、高崇民、卢广绩等主持大局,“以造成新的中心”。为了东北军的团结,为了反对、分化右派,周恩来主张“少壮派须以取消组织,减少右派攻击目标,实际则秘密团结,徐图发展”㊴。可见,直到此时,中共仍未放弃支持左派“同志会”的基本立场。
当时,不仅西安地区东北军内和普通群众中盛传着共产党人参与杀王事件的流言,南京方面也进行着中共有意阻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枪杀王以哲之类的恶意宣传。中共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依旧坚持其保持东北军的完整与团结的政策,依旧对“同志会”的整体转变寄予希望。然而,应、孙、苗等到苏区不久,即坚持要离去;1937年3月初起东北军调往豫皖苏。面对着急遽变动的局势和东北军的新处境,中共决定在东北军内重新组织“东北民众救亡会”,并准备将来召集全国各东北救亡团体的联合会,“用群众的力量,来巩固内部的团结”。为此,须将东北流亡集团各实力派、各团体、派别都吸收进去,以这个组织作为东北系统团结的中心。这样,过去只是支持、团结左派“同志会”的策略显然已不适宜。1937年4月,中共决定,“同志会的组织,决定使其在无形中解散掉。其中好的分子,能加入党则吸收进来,不能,则用过去同志会的关系,和他们发生个别关系”㊵。至此,“同志会”遂宣告结束。
“同志会”的组织虽告终结,但围绕着“二二”杀王事件,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非恩怨却长期纠缠不清,一直延续至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当事人彼此指责、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在研究者中对某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亦感难以释解,甚或不无某些疑虑。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以下中共在事后的总结反省,当有助于今后展开更深一层的研究。
第一,关于单独组织和支持左派“同志会”的策略问题。前文已述及,这与中共对左中右三派的基本方针和立场有关。在那样的方针下,支持左派自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随着中共对蒋政策的转变与国共和解的日趋急迫,这种支持的限度和唯一性(尤其是在“同志会”坚持极左立场时)是否需要转变,在中共领导层中并非没有分歧。而事实是,直到1937年春,中共高层似乎一直并未改变这一策略。如果在国内政治大局发生转变时,即或是东北军内各派系政治立场出现转变时,旧有的策略方针未能适应这些转变或显得步履过于迟缓,则在实际的政治行为中产生错误的几率也会相应增大,“二二”这一痛心事件的爆发,恐怕就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关于转变“同志会”性质的计划挫败问题。朱理治在事变前和事变结束后,都反复向中央报告过这一问题,并认为当时张学良也曾有这样的设想。在他看来,1936年秋后,应该将“同志会”由单独左派组织转变为东北军内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党应该积极领导这一转变。我们已谈过,当时在西安的东北军内的“东工委”领导成员表示反对,但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周恩来也曾经写信不予赞同。结合后来的事实看,周恩来的书信应该是代表着中共中央或中央的“东工委”的意见。当然,这一转变在客观上能否实现或完成,恐怕会有很多阻力和障碍,但主观上能否意识到这种转变的迫切性,则无疑是思想和认识方面的问题。自然,朱理治的判断和建议是否就一定正确,可以进行分析研究,但这样的建议毕竟是有价值的,简单地予以反对或者拒绝的做法,则未必是明智之举。
第三,关于宣传方面空洞乏力以及脱离群众的问题。如前文所述,释蒋之前,西安的报纸、电台大多充斥着过多的反蒋偏激言论。释蒋之后,刘少奇在1937年元旦即总结说:“我们的宣传太无力,而且迟缓,我们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太不积极,不能超过法西(斯)派的讨伐运动,又因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的观点及一些幼稚的冲动,几乎有一时使我们在政治上在群众中处于困难地位,丧失一些阵地。”㊶周恩来也多次向中央报告过西安的宣传与实际行动,常有过左、机械死板有欠活泼以至外强内荏的现象;朱理治更具体指出西北三方宣传上有着脱离党的方针、内容口号陈旧、仅讲大原则而缺乏具体解释、步调过于迟缓等等弱点。当时,中共除了自身的宣传渠道之外,某些方针、政策和主张、决定往往借助于西安的媒体向外传达,而西安的舆论阵地却基本控制在左派手中(中共直接掌握的仅属少部分)。由于前述“同志会”的种种缺陷以及西北三角在宣传上的大量弱点,导致中共的某些主张、方案在群众中疑虑甚多,甚或遭致非议与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绪氛围下,“同志会”的极左派虽未必有多强的政治、军事实力,却能够煽惑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仗恃所谓军意、民意而敢于屡屡挑战中共的路线方针,甚至于胡做妄为而惨杀无辜和联共有功者。
第四,关于中共对“同志会”的温情主义错误问题。朱理治曾报告称,“同志会”的中心骨干是刘鼎、孙铭九、宋黎、应德田等人㊷,刘鼎、宋黎本系中共党员。“二二”事件后,张学良曾表态:“这些暴徒能够捉住正法顶好,如不能,给他们走远一些。”㊸洛甫、毛泽东也曾电告周恩来,“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从语气看,似乎参与杀王事件者中或许有中共党员。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困惑于那些首犯何以能逍遥法外,应德田、孙铭九等人何以后来当了汉奸却依旧能在新中国受到优待和重用。其实,纵观事后中共方面的总结,我们或许不难窥得内中端倪并会找到某些答案。
无须讳言,西安事变之前,中共对“同志会”是有着过多的支持、依仗甚或是溺爱。虽然“同志会”有着那么多的缺陷与弊病,中共依旧对其充满着善意、耐心和支持。和谈释蒋之后,“起初左派分子颇觉失望”,中共向共产国际报告称:“在详细解释力求国内和平促成一致抗日的方针后,均已同意。”㊹事实证明,“同志会”极左派的所谓“同意”,当属口是心非之类。此后一段时间,中共中央针对“左派及其群众对我们的怀疑”,主要以解释、劝导为主,并一再指示西安的周恩来等人应与“张、杨左派密切联系”,并在不少事务上看重和借助于“同志会”,同时亦欲极力促成少壮派与老派之间的团结与合作。1937年1月下旬后,由于“同志会”极左派主战甚力,不愿听从中共的劝告,中共中央这才逐渐改变态度,提醒周恩来、博古等人“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对极少数不能听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应反对少数过激分子的挑拨行为,“力争左派的一部或大部”。至1937年1月底2月初,中共也承认,“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随即便发生了“西安一部分激烈分子反对撤兵,不服劝说”而枪杀王以哲等人的事件。
“二二”事件后,中共虽对极左派予以强烈批评和斥责,然而语气间仍不无同情、惋惜之意。如刘少奇给洛甫的信中就说过:“西安二月二日那样暴动的事件,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了我们,在反对党的方针与号召之下,去进行暴动。”㊺即那些从事反对党的方针和号召的暴动者,过去却是“我们最亲近的人”。1937年3月初,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曾以孙铭九作为“极端的代表”,批评这些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但仍然认为“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㊻。4月下旬,朱理治在给中央的总结报告中提到,“最近在东北军内部不能立足的一部分左派,又都到了平津”㊼,主要指的就是不愿在苏区多待的应、孙、苗等人,即直到此时中共依旧视这些杀王首犯们为“左派”。
总之,如朱理治事后总结的那样,中共对于应德田、孙铭九辈极左派“肤浅的观感与行动,没有采取公开的批判与斗争”,仅靠说服与劝导根本就无法纠正其“盲动政策”。因而,不仅是西安的“东工委”,就是在中央层面,中共“对于左派以及其他的小集团的违反统一战线的行为与思想,没有能用足够的努力去纠正与批评,多少的带一些温情主义”㊽,这应该是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获得的最为主要的教训。如果进一步深究,对左派的偏爱以至过度宽容,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共基于阶级分析而对左中右各派制定的基本政策。由于中共视左派为自己的同路人或最可依靠的力量,加之战争年代党内普遍存在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反右容易纠左难等思想观念的影响,导致理论分析虽然精致细微,但实践行动中却极易将左派视为一个整体,忽视了左派不同团体、派别、个人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遂在支持左派的大原则下轻忽了极左派言行的巨大危害性,导致西安事变善后处理时出现了很多中共不愿看到的局面
[注释]
①《刘鼎札记》,引自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95页。
②③⑭⑮㉙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页,第65页,第67页,第67页,第66页。
④⑫㉚ 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33页,第734页,第733页。
⑤⑥⑬⑰⑱㉛㊲㊷《朱理治给董威并转钟兄的工作报告》(1936年10月11日),北京:中央档案馆存件。该报告末附列的代号对应单为:S—孙铭九,Y—应述寅(即应德田),CA—“抗日同志会”,BA—抗日兄弟会,L—烈君(即刘澜波),C—张学良,LT—刘鼎,Nea—东北军,So—宋(即宋黎),M—苗浡然,W—黄显声,一兄—老叶(即叶剑英),老吉—吉鸿昌。
⑦⑧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1页,第81页,第50页,第47页。
⑨ 虽有回忆资料称高崇民为“同志会”员,但高因编写《活路》遭通缉,1936年5月避往天津,8月被张、杨派人接回三原,至10月才秘密进居西安王维之家。8月份,栗又文已与董彦平奉张学良命赴新疆联络盛世才。“同志会”正式成立时,此二人均不在西安。
⑩ 高存信、白竟凡:《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⑪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5)《西安事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⑯《黎天才自传》,无文:《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⑲ 刘祖荫:《张学良与东北军少壮派》,《六十年文史吟》,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第640页。
㉑㉒㉓㉖㊳㊴㊶㊹㊻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367-373页,第340页,第244页,第387页,第366页,第370-371页,第298页,第341页,第387页。
㉔㉕㉗㉘㉝㉞㊱㊵㊸㊼㊽《朱理治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37年4月23日)附件《双一二事变过程中东北军中党的活动的教训》,北京:中央档案馆存件。
㉜《朱理治给周并转张、毛的报告》(1936年11月4日),北京:中央档案馆存件。
㉟《朱理治给恩来并转钟兄的信》(1936年12月3日),北京:中央档案馆存件。
㊺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总第22期)。
责任编辑:刘毅
K264.8
A
1009-5241(2016)06-0017-08
刘东社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副教授 陕西 西安 71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