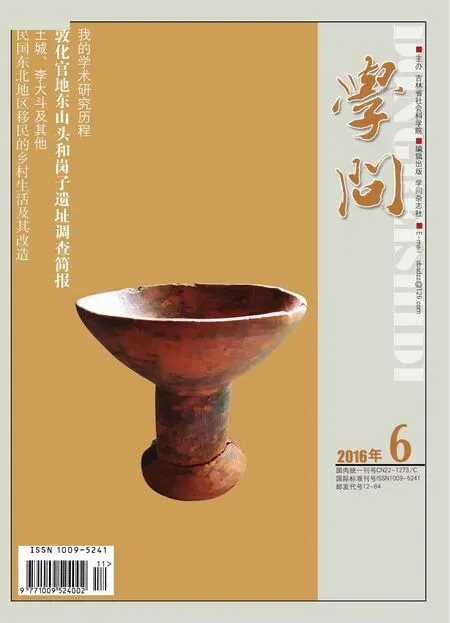民国东北地区移民的乡村生活及其改造——以辽宁村庙为路径的考察
刘扬
民国东北地区移民的乡村生活及其改造——以辽宁村庙为路径的考察
刘扬
[内容提要]近代大量汉族移民定居辽宁地区,同时将其家乡的信仰也带到了这里,村庙成为乡村大地不可或缺的景观,分布广泛。辽宁地区村庙承载着移民的乡村社会生活,移民的信仰、娱乐、公共事务几乎与村庙密不可分。民国肇兴,国民政府加快转型步伐,对民众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改造,村庙成为众矢之的,民国辽宁乡村地区的现代化有了很大起色。但民国辽宁地区的村庙已完全嵌入了移民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加之官方认识的误区,时局的限制,直至东北沦陷,这一改造彻底停滞。
民国 村庙 乡村生活 改造
一、民国辽宁移民社会与村庙的分布
村庙不仅是移民的信仰寄托,也满足了守护村落安全,保佑村民丰收等功利需求。搞清楚民国时期移民与村庙的关系,不能不追溯到清代移民潮时期村庙的状况。
(一)清代以来辽宁地区移民与民间信仰的传入
自清代顺治皇帝发布“辽东招垦令”以来,大批山东、河北、河南,甚至西北一带关内汉族移民迁入东北,光绪年间,由于东北的全面开放,封禁政策随之取消。辽宁地区①经历了招垦、封禁、再开禁的过程,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开垦,村落的形成,使农耕定居生活几乎成为该地区的主导,辽宁地区形成了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辽宁人口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国二十年(1931),除关东州外,辽宁地区中国籍贯人口已达到13088232人,城镇人口占11.57%,乡村人口占88.43%;民国三十年(1941),辽宁地区人口共计17168192人,其中乡村人口的比重为77.72%。②除原住民村落、驻兵或驿站发展起来的村落外,大部分为招垦或私垦的移民。辽宁地区是较早设立民治的府县,如复县、义县等处,人口大涨,庙宇的数量随之增多,大规模移民,不仅使乡村人口得到充实,也使得关内的民间信仰得到了传播。如下表所示:

表1清代辽宁部分县修庙状况表
可以说,移民的迁入,对民间信仰的崇祀掀起了高潮,是辽宁地区大规模复建重修庙宇的主要原因。其中,安东(今丹东地区)地区属东边道管辖,直到光绪二年(1876)才正式设县,移民陆续来此垦殖,安东的寺庙修建情况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仰传播与移民的直接关系。辽宁地区民间信仰的传播使得移民在定居之后开始修建村落的庙宇。
(二)移民与辽宁村庙分布
随着移民的到来,辽宁地区的村落渐渐星罗棋布。然而移民初到某地,“居若晨星,势若散沙,结合不易”,共同的信仰是整合移民的有力工具,“智者于是而为香火会……借以御侮减生危险”③。“香火会”正是移民利用共同的信仰而结成组织来凝聚力量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而,在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财神、菩萨、关公、虫王、社神、火神、五道、胡仙等被广泛祭祀,佛、道、俗神等共聚一堂,修庙护佑村落成为必需。辽宁地区的村庙既有村边用石板搭起的神龛小庙,也有由僧或道看护香火,由会首及普通村民管理,有的还有一定庙产的村落大庙。无论如何,这种村庙区别于僧道等出家修行的宗教场所,无严密的宗教组织、职能及教义,通常众神汇聚一堂无门派之争,近代辽宁乡村也形成了以村庙空间为标志的景观特色。
在广大的乡村地区,移民集体醵资兴建村庙的情况较为普遍,奉天省长公署档案中记录当时奉天全省学务公所总理世荣所对辽宁地区村庙的印象:“无无庙之村,亦无无产之庙。”④关于村庙的分布,辽宁地区全部村庙的统计数据并不易得,村庙往往规模各不相同,比较富裕的村落所建庙宇规模形制较为规范,而相对较弱的村落,仅仅用石块或是在树下搭建简易的庙宇保佑一方,很难准确地反映出各个村落的庙宇分布。
以民国时期寺庙调查记录清楚的海城县为例。海城县总面积为17200方里,统计九区共744村,640个庙宇,每26.88方里就有一处寺庙。⑤

表2海城县区村寺庙分布统计表⑥
当把寺庙的分布统计具体到区村时,我们发现基层社会村庙的分布密度是惊人的,其中三区、五区、八区、九区有庙1所以上,第三区每村平均有庙2所,按户数计算,平均每132.7户就有庙一所,可见庙宇分布密度之大。因而在地方志上常常能看见,“闲常周览城乡全境见夫穷乡委巷,莫不有祠宇在焉”⑦,“遍查开原境内城厢暨各区村屯莫不有庙宇在焉”⑧。这样的记录,十分普遍。日伪曾在东北乡村做过多次村落调查,几乎所有调查的村落地图上都清晰地标注着该村的庙宇所在⑨,因而村庙的广泛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时人的评论以及类似海城一样早期成为汉族移民定居的地区,就此来推断一下当时辽宁地区村庙的分布状况:“几乎村村有庙”,“无庙不村”的情况在民国时期的辽宁地区还是十分常见的。
二、民国时期辽宁民众生活与村落庙宇
古代社会的村庙不仅是信仰空间,同时也是政治空间,是传达皇帝圣谕,对社会下层进行教化和规训的主要场所。民国以来村庙这种政治空间功能淡化,更多展现的则是村民生活场景。民国辽宁地区移民源自华北平原,其生活方式绝大多数也被移植到了东北平原。村庙是联系和凝聚移民的一种特殊方式,从中可以窥见辽宁乡村地区移民的日常生活轨迹。
(一)笃信与狂欢——村落中的祭祀与娱乐生活
信仰是村庙得以存在的最初原因,而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点,使对神灵或祖先的祭祀已经无关乎“信”或“不信”,而是一种既定的行为,它以人们的欲求为原则,只要村民对某一神灵有所求,必然会有所祀。因而,村庙里的神灵可以不分教派、性别、功能,共聚一堂。马王、牛王、虫王、龙王、火王及天地、土地公、水神、柞树神等,这些是村民常祭拜的神灵⑩。村头的土地庙可以祭祖先也可以驱鬼神,村民的私祭是很平常的行为。村落中最为隆重的祭祀,一般是在神灵诞辰或是重要纪念日时的集体祭祀。据伪满时期乡村调查记载的村民集体祭祀状况,五月十三日或是五月二十三日祭祀关羽,根据经济状况好坏,由村民共同筹集,在敬神祈福后,由村民分食;六月六日为减少虫害,集体祭祀虫王;六月十三日是祭祀龙王,供奉整猪、馒头等,祈求龙王免除年内的旱魃、水害;六月二十三日为免火灾祭祀火神庙。⑪组织者及主祭人一般为当地有威望的士绅或会首,或是直接由村长组织并作为主祭人。祭祀前一定要摆放敬献给神灵的牢牲祭品,祭祀开始,全村人虔诚焚纸烧香叩拜神灵。众人祭拜后分享祭品,完成仪式。
祭祀仪式庄重而虔诚,但在仪式结束之后却是村民狂欢的到来,聚餐、看戏一般是村民少不了的程序。
祭祀神灵诞辰是村落中的大事,事毕,“宰猪治肴”,“村众齐至”,“众坐祠前顿食其余”⑫,也就是集体聚会,村民的娱乐时机开始了。“酬神演戏”只是一种噱头,娱乐狂欢才是民众共同的期待。“村中每演影戏数夜,于土地祠前,率为下流社会无稽之小说,亦有关于忠孝、邪正者,以供村众观听。”⑬这样的场合,“富农会向屯民提供酒水、舞蹈”⑭。有时富裕的人家会提供一些特别的娱乐费用。⑮此时,村民没有富贵贫穷的界限,人人可以借着“娱神”的机会,一展平日里的愁眉,大肆开怀一笑。
(二)聚合与公正——村落中的公共生活
村庙是村落神明的住所,在民众心中它更彰显公平和正义。村庙凝聚了村民,比起村中“井口”这种公共空间更适合作为处理乡村公共事务的场所。“村庙的宗教含义仅限于少数礼仪活动和偶尔的个人祈祷,此外,村庙的含义就只在凡俗的社会和法律方面了。”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民国时期辽宁村庙同样承载着旧村落重要的公共事务。
民国时期辽宁村庙多数由村民集资建成,以奉天省营口县石桥子村为例,我们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村庙的管理模式,“一个村子大概有一个或者两个寺庙,寺庙的管理有专门的老道。同时寺庙还有自己的田地大概20亩,其他的费用由村子支付”⑰。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村庙除建成的房产外,还有村民集资购买的“香火地”,支持寺庙的日常及宗教活动所需。村庙有时是村民自己看守,有时也招募僧道管理日常香火,但僧道对庙产无支配权力,而是公共的财产,“大家伙的”,通常村中设“会”管理,选举村中乡绅为会首来组织祭祀和管理庙宇相关事务,原则上他要代表全村落的男女老少的利益。
农事是乡村中的大事,商议看护青苗是集体共同的责任。祭祀虫王时“村董于是日齐集社庙,具猪羊酒馔致祭……订罚约,保禾稼”⑱。农户颇为重视。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选在村庙神像前商议农事,也是村民借用寺庙神灵权威性来监督世俗的一种考虑。村庙是被视为神圣庄严、权威性的圣堂,常常是村落的议事和调解空间。《盛京时报》就曾报道奉天城西四台子村住户马某与刘姓媪关于典当纠纷的事例,最后二人约定以共同赴庙发誓,以解决此事。⑲可见村庙在民户心中的地位,村庙成为了解决纠纷的场所。再者,民国时期村庙中常常被放置一些石碑,这些石碑往往是一些村落共同约定俗成的规则或是契约,作为乡村公众所遵守的习惯法。兴京县盘龙村因有人暗地侵占普护宫的林木,为解决此事,阖堡共议,达成一致,立石碑于寺庙中⑳。类似这样的碑文,很多记录在地方志中。将这些民间的和解条约、协定刻碑立于寺庙内,既可以不动用官府力量打官司,又可以处理乡间的民事纠纷。
近代以来,城市化的发展相当迅猛,然而相对于广大的乡村地区仍旧寥若星辰。即便城市生活在不断蔓延,但对于占人口总数绝对优势的乡村农民,以及那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社会下层民众来说,传统的生活方式仍旧是他们的主流,村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民国官方对辽宁村庙空间的改造
20世纪初是中国变革与转型最为激剧的时代,科学与民主是时代的主旋律,被视为“迷信温床”的乡村庙宇同其他宗教寺庙一样,成为需要改造的对象。但由于村庙分布的广泛,又与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官方的改造并非易事。虽未能彻底改造成功,但对村庙及民间信仰都是一种不小的冲击。
民国时期,官方对村庙空间形式进行了重塑,意图将其彻底改变为具有近代化意义的空间形式。首先是将村庙改为学堂,移风易俗。民国延续了清末的“改庙兴学”的做法,以教育兴国,将各村中基础较好的庙宇改设为新式学堂,“自改行新法以来,劝募巨资重修庙宇之事虽仍不能尽无,而借其地改设学校,暨作别项机关者,竟所在多有任守土之责者,能因势而利导之不难移风而易俗也”㉑。地方志记载当时地方庙宇状况,从中可见,官方的意图显而易见。官方对庙宇进行了较为激进的改造,有时甚至动用暴力手段,不顾民意强行拆毁。《盛京时报》对于官方强行拆毁庙宇的报道也时常出现,“南乡四台子镇长吴永升现已联合多人,提议将该镇倒塌之城隍庙及土地祠一律拆毁,改建乡镇小学堂”㉒。
官方还将寺庙改造为公所、警察所、慈善场所等用途的较多。在铁岭,院内设置消防队,“消防队设在中街关帝庙后院,凡有火警之家,无不登时扑救,城厢民居赖之”,还将“收容所设城隍庙院”,㉓神农庙内设自治所,“劝学总董刘东烺发起延聘讲员在南关农神庙内设自治传习所。”㉔,庇寒所则“假祖越寺地址及房屋,收容孤苦无依之老幼男妇”㉕;在凤城,寺庙被改造给图书馆、演讲所㉖;奉天省城将演讲所开到城隍庙内㉗。庙宇被改造成新式公共空间,乡村、城镇面貌为之一新,但“劝募巨资重修庙宇之事”,“仍不能尽无”,㉘仍是一种常态。
除了在空间形式上改造村庙外,对于庙宇中陋俗也进行了遏制和引导。中国人自古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对身后事十分的重视,希望选一块风水较好的墓地,常常不能立即下葬,因而将棺木寄存在庙内。然而,日久年新,无人照拂,一遇暑天,腐尸难闻,一旦风雨侵蚀难免会引发疫情。清末新政时期,卫生意识渐渐为官方所警醒,已经开始清理寺庙停棺的问题。《盛京时报》报道和传达了官方的说法:“总局因城关内外庙宇多有存放尸棺,年久无人管理,风打雨洒,骸骨暴露,大害公共卫生,随传知各局调查明白,以便分别办理,闻各局现已一律调查云。”㉙民国时期,对于庙宇停放棺材这种不卫生现象,官方同整治人畜同居、污水洒街、随地吐痰等卫生一样,多次下达命令予以禁止。对于在庙宇中聚赌、行骗的行为,官方严厉惩戒,“奉省行政公署训令略谓:各处有假庙宇配合药品名为神方即砒鸩,亦能服用殊与治安有碍,再加女巫医病,亦与风化有关,均应禁止以维治安云。”㉚
民国官方采取强制措施,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村庙存在的依据。官方往往以民众的上香拜神为迷信活动为借口,禁止祭拜活动,又有类似于“男女大防”,“有伤风化”为由,反对民众信仰行为,这种论调报纸上比比皆是。对于香火会这种集会形式,官方采取能制止便制止的态度,“督宪以此等集会事属迷信,且男女从聚集亦于风化有碍”,并且警务局严厉禁止,“一律查禁”。㉛甚至庙会期间演唱的曲目也在控制和禁止之内,民间的“蹦蹦戏”是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县署董监督以似此恶劣之习惯不但徒费金钱,且于地方风俗有碍,故特分令各区长及警甲所长等禁止演唱”㉜。一旦民意难违时,对村庙及民间信仰活动进行严密监管。因而庙会举办时,军警一般会到现场维持秩序。
官方改造村庙的行为,一定程度改变民众生活陋习,给新式教育的发展带来一定助力,而且丰富民众公共空间形式,大大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空间景观和生活秩序,在观念上给时人带来了冲击,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地方现代化的步伐。
近代以来,“立新必然破旧”的简单逻辑成为急于迈进现代国家行列而改造社会的思维方式。批判和打击迷信是社会上层的改良号角,乡村寺庙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权力与社会舆论的矛头指向。官方从公益事业出发,改造为新式学校、公所,改革陋俗,颁布新的寺庙损毁标准,但拆毁庙宇,搬走神像,却忽视民众的精神上的要求,结果带来的大量的诉讼案件,因村民为反抗官方拆庙而带来社会冲突骤然而起㉝。民国辽宁村庙空间承载了许多乡村社会的功能,有其存在的合理机制。官方改良基于一种对宗教、对村庙空间的不完整认识基础上,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被一些无良的劣绅所利用,对村庙的改造成为敛财的手段,使其改良措施大打折扣。此外,官方的行为打破了以往乡村社会传统生活空间,导致原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受到一定影响,国家在地方的形象也会受损。事实上村庙祭祀也仍在继续,每年的庙会照例举行,虽受到一定的阻拦,受到官方的监控,但民仍不改其乐。受民国时期政治局势混乱,国家力量相对弱化的限制,改造没有能达到应有效果。
[注 释]
① 清代以来辽宁地区先后有过盛京、奉天、辽宁省的称呼,本文一概以辽宁为称,同时兼顾不同历史时期辽宁地区的称谓。
②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人口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97页、第100页。
③ 周铁铮修,沈鸣诗等纂:《朝阳县志》,卷二十六,种族,民国十九年(1930年)铅印本。
④《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JC10,案卷1015,辽宁省档案馆藏。
⑤⑥ 廷瑞等修、张辅相纂:《海城县志》卷一,地理,疆域,卷二地理,区村,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
⑦ 裴焕星等修,白永贞等纂:《辽阳县志》,卷五,坛庙志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
⑧㉑㉘ 李毅,赵家语修,王毓琪纂:《开原县志》,卷二,坛庙,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⑨《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奉天省铁岭县),伪康德三年(1936),“关系屯附近略图”,第473页 。
⑩《农村实态调查一般调查报告书——安东省庄河县》,(伪)国务院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伪康德三年(1936),第368—369页。
⑪《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奉天省铁岭县》,(伪)国务院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伪康德三年(1936),第231页。
⑫⑬ 周铁铮修,沈鸣诗等纂:《朝阳县志》,卷二十五,风土,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
⑭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东北卷一),《锦州省盘山县农村自治及社会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⑮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东北卷一),《锦州省绥中县风俗习惯及宗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4-266页。
⑯[德]马克斯·韦伯:《储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6页。
⑰ 伪满洲国大同学院编:《满洲国乡村社会实态调查抄》,大同印书馆发行,伪康德元年(1934),第350页。
⑱ 田万生监修,张滋大纂修:《建平县志》,卷四政事,礼俗。1987年建平县志编委会据民国二十年(1931)抄本复印。
⑲《报应不爽》,《盛京时报》,1921年5月26日。
⑳ 张耀东修,李属春纂:《兴京县志》卷十,古迹,庙宇,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㉒ 奉天《拆毁庙宇》,《盛京时报》1912年9月17日。
㉓ 陈艺修;蒋龄益、郑沛纶纂:《铁岭县志》卷六,慈善志,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㉔ 陈艺修;蒋龄益、郑沛纶纂:《铁岭县志》卷四,自治志,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㉕ 杨宇齐修:《铁岭县续志》卷九,慈善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
㉖ 马龙潭,沈国冕等修;蒋龄益:《凤城县志》卷四,教育志,社会教育,民国十年(1921)石印本。
㉗《城隍庙内之演说大会》,《盛京时报》1917年2月7日。
㉙《调查庙宇停放灵柩》,《盛京时报》1909年1月17日。
㉚《禁止神方》,《盛京时报》1913年11月6日。
㉛《禁止举行盂兰会》,《盛京时报》1911年8月31日。
㉜《禁演蹦戏》,《盛京时报》1924年3月29日。
㉝ 参见拙文《民初国家对庙产问题的解决——以奉天省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5月。
K26
A
1009-5241(2016)06-0087-05
刘扬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吉林 长春 130033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ZS035)201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委托项目
责任编辑: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