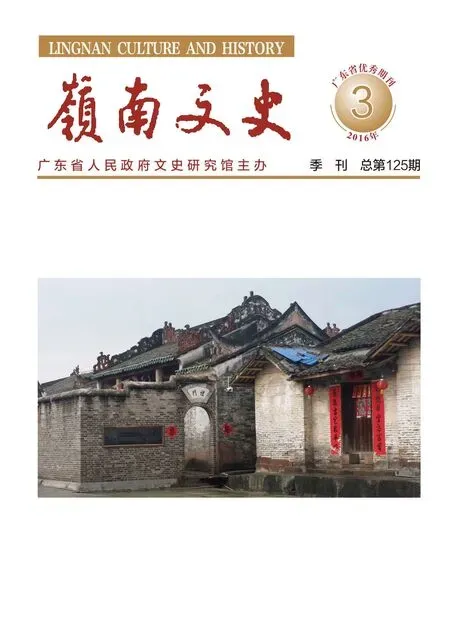“广府”与“广州”关系辨析
金峰
“广府”与“广州”关系辨析
金峰
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提出广东“三大民系”及“广府人”的概念。因潮汕和客家人在语言、价值观念及行为习俗等方面的文化特征十分显著,形成了自我认同感十分强烈的亚文化圈,加以“潮汕人”、“客家人”等概念范畴十分明晰,“潮学”、“客家学”研究得以在有明确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顺利展开。但“广府学”研究则迟至90年代才有重要成果出现,且“广府人”、“广府文化”等基本概念仍是歧义纷呈,“广府学”研究面临着研究对象缺乏严谨和普遍接受的定义,以及被界定为“广府人”的族群缺乏自我认同等问题。本文拟从有关“广府人”概念的界定入手,探讨广府与广府人、广府文化以及广州之间的关系。
一、“广府”界说
有论者指出在定义“广府人”时,面临着粤语与白话、广府与广州之间关系难以厘清,以及广府人概念多在通俗层面使用,但缺乏学术性细致界定等问题。理论上“广府”系指“广府人”生存活动的地理空间,“广府人”系指一个特定族群,而“广府文化”则是指一种亚文化圈,分别涉及地方学、民族学和文化学三个不同领域。有关“广府人”概念分歧的产生,实因上述三领域的“广府”未能和谐融通所致。
1.“广府”概念分歧
首先,关于“广府”的概念范畴,研究者往往根据需要各自界定。大多数研究者将“广府人”定义为生活在岭南地区、使用粤语的汉民族的一个民系。但因粤语在岭南地区分布极为广泛,[1]理论上被认为系属广府人的族群人口众多、分布零散,既超出广府行政区划范围,又存在地域文化差异性,使“广府人”概念能否包容如此大范围族群成为问题。因此陈泽泓即主张以明代广州府政区作为“广府”界限,甘于恩也将广府文化定义为“以广州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的粤语文化”。[2]由此造成“广府”概念出现了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的“广府”系粤语覆盖区,狭义的“广府”则是指明清广州府辖境,即以广州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为主体的地理空间。
第二个是“广府”古今名实的混淆。地理上的“广府”秦称“番禺”,三国时的孙吴黄武五年(226)始有“广州”之名。唐武德四年(621)设军事镇抚机构“广州总管府”(后改称“广州都督府”),唐人渐有“广府”称谓。10世纪时来华阿拉伯人也称广州为“广府”(khānfū),[3]说明唐称“广府”已极为常见。明清时置“广州府”,“广府人”的说法更是普遍流行。然须指出,古称“广府”或“广府人”,系政区概念或系代称此政区辖下居民,而罗香林袭用“广府”之名,但此“广府”已系文化地理概念,即被赋予文化学和民族学的内涵。即是说,古今“广府”名同实异,但颇有论者对之未能明辨而常有混淆。
第三是早被研究者所指出的“广府人”自我认同感的缺乏,[4]亦即在没有客观主体自我认同的情况下,如何界定“广府人”的问题。
2.“广府”界说
笔者支持采用粤语覆盖区界定“广府”的主张,原因如下:
其一,“粤语”及其他“文化核”的形成。尽管“广州话”具有特殊性且与其他片区粤语交流中时有障碍,但并不影响粤语作为更高层级方言的存在,各片区粤语虽有语音差异,但在语法、句法和词汇等方面的共性更加明显。更重要的是,由于语言在人类认知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操同一语言的族群能够形成相近的文化心理,使粤语人群在以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以及强烈的宗族和宗法观念、依托于水路交通的宗族聚居的村落形态、浓烈的民俗信仰等方面,都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正如客家人的活动空间虽小于广府人,但其范围更为广大,客家文化也存在诸多地方特色但共性特质并未削弱。由于粤语的纽带作用,粤语使用者的核心文化要素具有诸多共性,使得超出珠三角范围的粤语人群理应被纳入广府民系。
其二,基于基因技术的人类学考察。徐杰舜等指出,广府民系的父系血统汉族略超50%、母系越族超过80%。[5]此一比例显然与中原移民南迁史相符。而生物学基因技术也反映出岭南地区的广府人作为汉民族的一个亚群,在群体遗传学方面具有诸多共同特征,并且与潮汕人、客家人之间出现了符合历史学、文化学一般认知的遗传距离。[6]也就是说,“广府人”作为一个民系,其民族特质和生物学共性业已形成,这不仅是历史文化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生物遗传的结果。
其三,关于认同感问题。有论者指出:“某一民系的诞生传说或多或少都反映了该民系产生之际的背景及诞生的意义”。[7]“珠玑巷传说”无疑应当被视作“广府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开端。尽管这种认同不是对于文化共性,而是对于血统来源——“中原汉族”的认同。亦即广府人在自我意识产生之初,主要是关乎“来自中原”和“侨居于此”的共同信念。鸦片战争后,近代民族意识推动产生的地方意识,也使“我粤人”的地方认同取代了文化认同,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广东社会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同样更有助于强化 “粤人”意识而非“广府人”认同。还须指出,相对于潮汕人和客家人,广府人因迁徙至岭南地区较早,生存空间的自然地理条件优于后来者,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等各方面优势,因而明显自居于强势或主体的地位,也非常有利于“广东人”或“东莞人”意识的产生,即其心理体验已由最初的“外来客人”转而变成“本地主人”。也就是说,“广府人”作为独立群体的自我认同在“珠玑巷传说”以后即已产生,只是始终未能自认为是“广府人”而已。但缺乏自我意识并不代表广府人客观上不存在。如元代新会人与广府人合作生意的故事,即反映出周边的“他者”已有明确的“广府人”意识。民国时南番顺及中山被称为“上四府”,稍远的台山、开平、恩平、新会被称为“下四府”的习惯称呼,也是“广府人”自我认同的潜意识表现。因此,缺乏自我认同并不能否认“广府人”存在的事实,以及现代意义上“广府”概念的确立和传播。
二、“广府”与“广州”
府、州均系中国古代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在不同时期品级和辖区范围大小不一。汉代以后多行三级制,府州系省、县中间一级政区。狭义的“广府”,秦以南海郡下辖番禺县治其地,汉代南海郡辖区缩小而上以交州刺史部统领,三国时东吴将“海东四郡”(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并为“广州”,此后唐宋均有“广州”政区,元有“广州路”,明清有“广州府”。作为行政区划,“广府”大体同于“广州”。
然而“广府”的复杂性在于,历史时期其辖区始终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古称“番禺”、“南海”的县即今广州市区也往往是岭南省级机构治地,与一般“府县”大有不同,即不因行政上不能涵盖广义的“广府”而将之判然两别。此外,今称“广州市”的政区范围也与古“广府”有较大变化。因此“广府”与“广州”需要辨析者,一在“广府”能否代称粤语区,二在旧“广府”与新“广州”之间的关系。
1.岭南地域空间
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广府”,都处在地域范围更大且较为独立“岭南”地区之中。尽管广府人并未占据整个岭南,但其繁衍生存以此特定空间范围为基础,史料文献也无法将“广府”从“岭南”中剥离而加独立讨论。也就是说,整个岭南地区为广府人和广府文化的生成、发展及特质的形成,提供了相对独立、统一、共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其主要影响表现在:(1)因南岭阻隔,岭南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空间;(2)珠江河谷特别是三角洲优越的水、土、热条件,是广府稻作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基础;(3)珠江水系为广府先民的内外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水上交通;(4)岭南别有特产且面朝大海,广州更有开展外贸的区位优势,使广府文化别具海洋商贸文化特色。
2.“广府”核心地区的多维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的“广州府”所辖州县的地理范围,主要包括今广州、东莞、深圳、佛山、中山、珠海、江门等市所辖各区县,清远市辖各区及清新县、惠州市辖龙门县和港澳地区,即大珠三角地区,总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8]值得注意的是,广府政区地理沿革与岭南自然地理变迁和社会经济开发,是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相辅相成的发展过程。
自然地理上的珠三角,以西江的三榕峡、北江的飞来峡和东江的田螺峡为各江三角洲的顶点,历史上海潮曾到达上述地点,这是珠江成陆作用的起点。从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的分布情况,可大致判断出约6000年前珠三角海岸线,是从罗浮山南端西南至佛山、西樵山一线。[9]出土陶片证明汉代海岸线已推进至番禺、顺德一线,并维持至唐代。宋元以后因海平面降低及珠江堆积,海岸线不断向东南推进。唐宋时珠江中游的河谷地带基本成陆,宋以后主要在下游发展冲积平原。明清广州府的陆界与珠三角大致吻合,潜在的自然地理原因是当时珠江下游的成陆过程已基本完成,此后三角洲主要在海岸线发展。
与自然地理变迁相同,岭南社会经济开发也以唐宋为分野。宋代珠三角冲积平原大面积形成,同时开始大量修筑捍海及沿江堤坝,[10]不仅有利于防洪、灌溉,更使大量肥沃的湖沼和滨江低地变成易耕高产的“圩田”,加上掌握先进技术的北方移民大批南迁,以及统治者对岭南着力经营,更兼宋元时中国水稻种植技术趋于成熟,从选种、育秧到大田管理等精耕细作技术都基本成型,[11]并在岭南大面积推广,[12]使得宋以后岭南社会经济已从相对落后一跃而为较为发达。
岭南政区沿革与自然和经济地理的阶段性特征相一致,以唐宋为界,前此开发不足而统治者重在军事抚驭,后此则重在开发。其政区设置在此前系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拓展,[13]此后则以珠三角为核心向周边辐射。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新增县多系从旧县析出而非辟地新置,且所置县逐渐沿珠江向上游扩展。[14]
综上可知,“广府”政区是在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地域范围在自然地理上系位于岭南地区精华地带的珠江三角洲,在语言地理上大致相当于粤语广府片区,从文化学上可以视作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带,三者边界高度重叠,亦即是广府民系和广府文化孳息生长的核心地区。
3.“广府”的特殊地位
其一,在广义广府乃至在整个岭南地区,狭义“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最为先进发达,地位也最为重要。珠三角广府文化对周边具有强烈的向心吸引和辐射作用,如粤语广府片与其他片区及粤语周边方言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随距离远近而相似度、渗透程度不同的关系。[15]而在远离广州但与广州间交通便捷且农耕条件优越的岭南地区,星散出现使用广府粤语的亚文化区,并以之为亚中心向周边辐射,[16]充分说明广府片粤语在整个粤语区的核心地位,也从侧面证明了广府人和广府文化是在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孕育和成长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拓展。
其二,“广府”特别是广州在岭南交通地理中居于核心地位。历代中原政治中心通往岭南的交通,越南岭后往往以珠三角亦即广州为目的地,复以广州为核心辐射周边。如秦所凿通越“新道”均系溯湘江或赣江支流而上,越五岭后复顺北江支流而下者。[17]汉代越萌渚岭和都庞岭间谷地、沟通潇水和贺江的“潇贺古道”地位上升,[18]汉统辖岭南的交阯刺史部治设在广信,系因其居至广州干道之上。唐代大力疏通岭南与周边的交通,其东北向福建、西经广西至云南,以及南向粤西、海南岛等地的陆上通道均加经营。但上述地方均远离政治中心且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其与岭南核心地带联系的重要性及交通条件均远逊北路。[19]开元四年(716),较为平易的大庾岭梅关道经张九拓修后,成为南北往来的咽喉要道,此后历代王朝均将之定为中原通岭南的官道干线并沿途置驿,且不断加以修缮。[20]
岭南内部的交通也以广州为核心,但与北向中原的水陆兼施不同,岭南内部交通对珠江水系十分依赖,特别是唐以后,随着造船和航运技术的突飞猛进,珠江河运快速发展。[21]元代以广州为枢纽、通往珠江流域各地的水运网络趋于成型;[22]明清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珠江水系交通更显繁密,不断有大规模河道整治,[23]津渡和水陆驿站设置更加密集,沿河广府村落也大量出现。[24]两广各府县间铺驿、站线的设置不仅充分利用水道,珠江干支流所到之处的陆上驿道也基本沿江而修,[25]水路驿运极为发达便捷。[26]
其三,岭南地区的交通地理格局,对于中原文化传播和广府文化的扩散,特别是广府民系的地理空间分布,发挥着重要影响。汉以前湘江联西江一路最为重要,岭南文化即以广信最为发达。唐以后大庾岭路地位上升,粤北的曲江等县即成文教兴盛之区。宋代广府民系开始成型,三大民系的地域分野也渐有雏形。如有论者指出,“宋代广东……三大方言区已经形成,它们的分布区域与这时政区界线部分重合,其中粤语和客家语分界线北段和南段与宋代政区界线完全一致,……客家语和闽南语的分界线……跟梅州和潮州的政区分界线相吻合,不吻合部分界线则是后来移民的结果”。[27]三大民系地理分布表现上看是行政区划的规定,但实际隐含着自然地理因素的潜在作用。明清时珠江水系的交能孔道作用、沿珠江而设的水陆铺驿网络与广府族群地理分布的高度契合,与珠江水系稻作宜耕地带、粤语方言区,以及行政区划的广府地区的边界重叠,有着相互关联的内在成因。
4.广州的特殊地位
广州府城,即今广州中心市区或古代广东乃至岭南的省治所在,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汲取岭南大地及南海精华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当之无愧的岭南首府。
广州背山面海,处海陆交会之所。珠三角繁荣的农业经济及便利的内外交通,为其开展内外贸易提供了重要条件。如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灭南越国,焚番禺城,但仅仅20年后的《史记》中即指出番禺已复为汉19个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汉书》、《后汉书》均称广州物产丰富、贸易兴盛。三种史料在检讨岭南商业都会时均盛赞广州而不及广信。汉以后广州自然地发展成为岭南内外贸易的重镇,并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中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口岸。此外,除两汉三百年间统治者有意贬抑而将政治重心北移外,其他时候广州始终是岭南政治中心,如秦任嚣即称其“可以立国”。[28]行政中心的角色也不断地强化了广州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三、结论
其一,“广府”、“广府人”和“广府文化”所代表的学术领域不同,其内在一致性系以在共同地理空间的基础上形成,即粤语与广府族群的分布在自然地理方面依赖于珠江水系交通和适宜精耕稻作等条件,并在基础上形成广府文化的分布区。
其二,“广府”名词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小于广府地区,但因其在广府地区所处核心地位及在广府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约定俗成的情况下,以“广府”代称以粤语来界定的广府文化区是最为恰当的选择。
其三,今所称“广州”地理空间大于古称“番禺”或“南海”的县级行政辖区,但又小于古称“广府”。从地方学角度而言,“广州学”涵盖了地方历史、文化领域,其地理范围应以明清“广州府”范围为主,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超出此空间而以“岭南地区”为范围势不可免。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B13—B14页。
[2]甘于恩等:《20世纪90年代广府文化研究概述》,《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5页
[3](法)费瑯辑注,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4页。
[4]陈泽泓:《广府文化》,邱捷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5]徐杰舜:《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0页。
[6]李晓昀等:《潮汕人与广府、客家人母系遗传背景差异的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第6期,第664—668页;王琳凯:《基于15个STR基因座的广府、客家、潮汕族群遗传多态性研究和罕见嵌合体案例报道》,暨南大学2014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7]片山刚著,朱海滨译:《“广东人诞生之谜”——从传说和史实之间来考察》,《历史地理》2006第21辑,第417页。
[8]、[9]曾昭璇、曾宪红:《珠江三角洲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10]、[21]郎国华:《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暨南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1—44、41—51页。
[11]陈伟明:《宋元水稻栽培技术的发展与定型》,《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第31—35页。
[12]谢敏、李春华:《论北宋岭南谪宦对岭南农业的影响》,《农业考古》2007年第6期,第16—18页。
[13]许桂灵、司徒尚纪:《泛珠三角经济区政区建置沿革的空间关系演变透视》,《热带地理》2005第2期,第101页。
[14]王荣、吴宏岐:《.明清广州府土地开发特征研究》,《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7期,第145页。
[15]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方言》1987第3期,第161—162页;龙庆荣:《汉越语与粤语和平话语音对应关系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130—132页。
[16]粟春兵、王文胜:《梧州粤语和周边勾漏粤语词汇相似度的计量分析》,《梧州学院学报》2011第5期,第7—13页。
[17]余天炽:《秦通南越“新道”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104—108页;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第46—47页。
[18]韦浩明:《秦汉时期的“潇贺古道”》,《广西梧州师范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86—89页。
[19]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学术研究》1987年第1期,第53—58页。
[20]詹瑞祥:《韶关古道沿革考》,《九江师专学报》1988第1期,第95—99页。
[22]司徒尚纪:《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的历史变迁》,《热带地理》1991年第6期,第114页。
[23]蒋祖缘:《明代广东水陆交通建设及对商贸发展的作用》,《广东史志》2001年第3期,第3—6页。
[24]朱光文:《明清广府古村落文化景观初探》,《岭南文史》2001年第3期,第15—19页;冯志丰:《基于文化地理学的广州地区传统村落与民居研究》,华南理工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25]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25页。
[26]叶显恩《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27]司徒尚纪《广东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第23页。
[28](汉)司马迁:《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注释:
[1]陈泽泓即认为社会活动对“广府人”作出了各种诠释,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广府人,“真的是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参看陈泽泓:《纠结的“广府人”》,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3页。
[2]以粤语方言界定广府民系的研究者包括李权时、司徒尚纪、徐杰舜、王杰等人(参看李权时:《岭南文化·修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344页;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9—460页;王杰:《广府文化概念不断延伸》,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7日。
[3]陈泽泓:《广府文化》,叙言,第7—8页。当然,此后陈泽泓可能意识到这样就无法明确指称“广州府”以外的族群,因此他又修正上述见解,提出兼用使用粤语方言且有心理认同感,以及历史上的广州府地域范围两种界定方法,但他仍指出两种定义并不包容(参看陈泽泓:《纠结的“广府人”》,第33页)。
[4]沃尔夫的语言相对性假说主张,“我们所能具备的各种概念和知觉都受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影响”(见[美]R.L.Atkinson等著,车文博审订,孙名之等译:《心理学导论》上册,台北晓园出版社1994年版,第427页),认为话语通过理论、概念等,直接影响认知的方式和水平。乔纳森等还指出:“话语与行为、主体、社会过程……都是不可分割的。……话语实际有着种种行动取向时,话语的生产者就不仅仅是‘主体’(subjects),而且是‘行动者’(agents)。”(见[英]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著,肖文明等译《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即认为语言不仅构建成认知,而且会指导行动。由于语言对认知及文化构建提供了基本建材并直接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面貌,因此斯大林在定义“民族”的概念时即将语言列为四项基本条件之一。
[5]此传说称:“(梁之攀)壮岁服贾黔省,往来岁以为常。某年,之攀由粤赴黔,在乐昌舟中,与广府人共一舱,询其姓名为陈亮。”见同治《新会县续志》卷6《列传·人物》。
[6]其中明代广州府地域较大,北及今清远市除英德外的阳山、连州、连山各市县。参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元明时期第30—31页、清时期第44—45页。
[7]如宋祝穆引《海峤志》称:“中宿峡(即飞来峡)……二月、五月、八月,有潮上此峡,逐浪返五羊。”见[宋]祝穆撰,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06页。
[8]如明代《一统路程图记》即记京师至广州的官道亦即两地交通干道,至江西后系溯赣江而上至赣州、南安过大庾岭一线。参看[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1,上海图书馆藏明隆庆四年刻本影印本,史166,第486—487页。
(作者单位:广州大典研究中心)
——粤语·女独·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