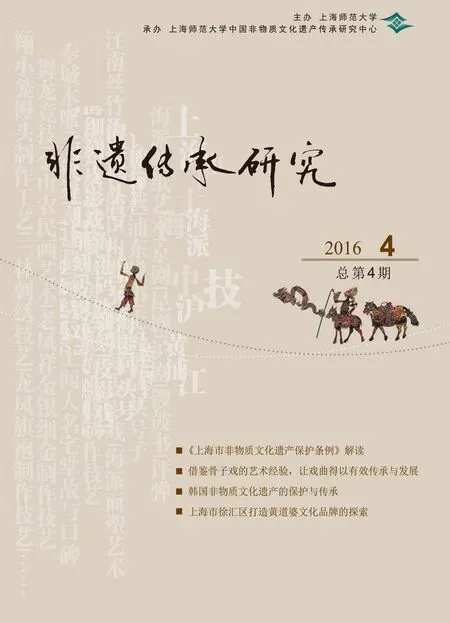吴宗锡与新中国评弹(下)
吴宗锡口述 王其康 毛信军整理
一、从陋室起步建设新中国评弹事业
1952年5月,我被派到评弹团工作。评弹团是一幢西式洋房,楼下是办公室,那时演员全部住在团里。楼房的底层有个客厅,大概30平方米左右,全团大会就在这里开。楼的外面有条走廊,走廊很宽,走廊的一半用玻璃窗隔开,里面放了三四张写字台,我和正、副团长,包括张鸿声就在这里办公,这就算团长室了。现在想想,我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开展工作了。在我到评弹团后的十年里,搞了不少创作的、整旧的精品长篇,及20多篇中篇、短篇,另外搞了很多开篇、选曲。这些开篇和选曲都成了经典性的流派唱腔代表作品。半个多世纪来,这些开篇和选曲是包括江苏和浙江在内的书场和演唱会中演出最多的节目。直至今日,这十年中创作的开篇还在评弹书台上演出。评弹团在这个陋室里搞创作、搞演出,打造了评弹有史以来的艺术高峰,超过了20世纪三十年代。
这十年是评弹最繁荣,也是艺术高度最高的时期。好多人问我,蒋月泉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响档相比艺术水准到底如何?我就讲,应该说是超过前人的,因为那时的演员只演一部传统的长篇,而蒋月泉、杨振雄等既演传统的,又演新的,像王孝和、白求恩等都演。另外,评弹曲调也有了发展,演出也有了发展。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书场,三四百个座位就算很大了,而到解放后,舞厅改成书场,书场大到了一二千人的规模。到五十年代末期,评弹走进了文化广场,评弹的听众大大超过了以往,培养了很多新的听众。实事求是说,解放后评弹繁荣昌盛,超过了以前,达到了艺术的高峰。
二、万事开头难:从个体到群体
我去评弹团后不是没有矛盾和困难的。当时,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党的工作,年纪轻没有社会经历,而这些评弹演员,过去都是单干的,以“档”为主,没有集体生活经历,没有现成的剧团可以学习评弹团怎样搞。评弹团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剧团。我去评弹团前,看了一些像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等剧团的书,另外还了解了一些部队文工团的做法,但那是不能照搬的。
还有就是以前评弹演员比较自由散漫,以“档”为主的,上面要求他们住在团里,星期一至星期五住团,星期六回家。评弹演员没有经历过集体生活,怎样过集体生活,对评弹演员来说,也是一个过渡。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每星期要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会上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位老艺人就提出来,你们不要批评我,我也不会自我批评的。现在觉得这样讲不对了,那时他觉得那样讲也没有什么错。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来到评弹团矛盾和困难还是不少的。
我到评弹团去时,有两个报社朋友对我讲:“你到评弹团去舒服啊,好去搞创作了。”因为他们想象中评弹演员都有自己的一部书,不要你另外操啥心的,各人有各人的书,你给他们安排好场子演出就是了,好像评弹团平时一点事情也没有的。当然这也是说笑话。实际上我到评弹团去,上面是有要求的,要做好实验示范,来带动整个评弹界,事情是不少的。
评弹团里的这些演员,他们从小就是这样一档一档书到书场去演出,谁也不服贴谁。卖座好的就是响档,你今天生意漂脱,你就不及人家。你年纪轻时红的,到了年纪大了,年老色衰了生意就落下来了。但是,评弹团就不一样了,有很多工作安排。譬如,要评级评薪了,干部都是习惯的,你是科级就是科级,处级就是处级,但是他们个个都是大亨。他们说笑话讲,有几个响档的牌子挂到典当铺里是可以当钱的。我的名气响,到典当铺里就是钱。谁生意好,谁就是艺术好。所以,要评级了谁也不服贴谁。有时候要做些安排,例如来了观摩票,一个团有20个演员,而上面分给观摩票只有四五张,你怎样分发观摩票?
当时有些剧团有主要演员,而评弹团是没有的。说谁是主要演员谁都不服的。别的戏曲剧团有主要演员,评弹团是没有的,我们上台都是主要演员。一个人单档我就是主要演员。所以在评弹团从开始到后来都碰到这样的问题,你要安排他什么事,都牵涉到他的名和利。例如排档子,谁做头档,谁做送客;要巡回演出了,谁去北京演出,谁去小码头,每一件事都牵涉到演员的名利。所以有几个与我关系比较好的演员对我说,你是派来的干部,你领导三四十个人(那时已发展到三四十人),就是领导三四十个剧团,我们是一个人一个剧团呀。这话讲得是比较实际的,因为人人以为自己是最好的。
再说拼档,现在说起来拼档简单,当时很不容易。例如蒋月泉、朱慧珍的拼档,现在听众都认为当时蒋月泉、朱慧珍的拼档是优化组合,培养了一对响档。而且有了这对拼档才有了《庵堂认母》这样的书,蒋月泉的蒋调和朱慧珍的俞调成为评弹一个典范的双档对唱。但是,当时要叫蒋月泉和朱慧珍拼档是拆掉夫妻档,吴剑秋和朱慧珍是夫妻档,你怎么跑过来把我们夫妻档拆掉呢。凡是拆档、拼档都会有矛盾,我愿意和他拼,我不愿意和他拼。现在看看有几对很好的拼档,开始拼前,两个人都说性格不合,我们不可以在一起的,这方面矛盾也是很多的。所以说从个体到集体,从来没有的评弹团到建立一个评弹团,事情是不少的。
评弹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评弹团的致命伤。当时上边成立评弹团是参考了其它剧团,包括文工团等,工资待遇是领导与演员协商的。协商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采取自报公议。自报每天收入多少。那时我们整个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所以报的工资是不高的,最高大概三四百元。但是1952年时这些响档在书场里自己演出,大概一个月有1500-2000元收入。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在书场里演出叫“拆签”的,单档我一个人说评话的,我拿一份签子。双档,如张鉴庭、张鉴国兄弟档,他们两人也只拿一份签子。这时候的拆签制度是这样的。单档拿一份签子,双档要拆账的,上手拿多少,下手拿多少,单档全部一个人拿。到了团里后又摆不平了,我单档拿一份工资,你们双档拿两份工资。相互间的差距,团外与团内的差距。而且外面照常在演出,我是演员,我也照常在外面演出,就是参加了国家团拿得少了。所以收入问题是很大的,尤其是后来评级评薪时。原先对演员讲以后要评工资的,评工资时工资会提高的。结果评级评薪时拿出来一张工资表,这是上面规定的。而且还具体规定,像赵丹这样的演员可以评一级,评弹演员是曲艺,不是电影演员,最高只能评三级。所以拿出工资标准一看,原先想评级时工资还可再加一点,结果评级后还是与当时拿的工资差不多。所以,工资的问题始终贯穿于评弹团,直到“文革”,一直是团里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会有演员要求离开评弹团,当然他提出要离开评弹团不会明讲是为了工资,总要寻些团里干部怎样对自己不好,或者寻些其它理由而走人的。最厉害时是有一批演员都想走。那时,演员是住在团里的,我和陈灵犀是可以回家的。晚上他们如何活动我一无所知,后来经过了做工作才平静了下来。现在讲是他们那时有思想波动,但我还是同情这些演员的。放在今天,倘若一个人在外面的收入可以拿到自己工资的六七倍甚至十几倍,我想任何人都是会动心的。
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的确很艰苦,他们的开销与我们一般的干部不一样。实事求是讲,有几个演员要负担两个家庭,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生活负担比较重。还有就是子女多,有的演员家里有四五个子女,有时要变卖家里的东西维持生计。刚解放时,家里还有西装等,后来拿到寄售店去卖掉。有些演员在团里休息时打康乐球,穿件汗背心都是有破洞的。他们有思想波动也是正常的,我也很同情他们。当时对有些事情的不满意有思想波动,往往就会流露到对干部、对工作安排的不接受。
三、治淮奠定了评弹团的思想基础
评弹团能够巩固下来,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评弹团一成立就去治淮,思想上打下了坚实基础。参加治淮到工人、农民中去,认识有所转变。他们过去比的是上海的响档,或者是有钱的人。现在眼前的是中国的穷人、苦人,他们对社会主义、对国家不知作出了多少贡献。因此,治淮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他们知道了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次治淮教育很重要,当时我和他们在一起,知道他们的一些思想实际,所以后来的工资等问题的解决,参加治淮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本来要走都留了下来,结果只走了两个。一个是严雪亭,后来又回来了;一个是谢毓菁,尽管离开了团,也并非完全为了工资,一直对评弹团非常好,也一直打电话来问候我。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即来去自由,出去不难为你,不批评你,一切从大局考虑。
上级对成立评弹团的目的和要求是在戏改上,也就是在艺术改革和提高上要起示范作用,包括创新、整旧都要做,要带动整个评弹界。当时整个评弹界都要成立评弹团,要以我们评弹团作为骨干力量,来带动评弹界。要改戏主要还是要改人。以前看足球赛,足球队教练有两个字,叫“调教”,这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调教演员很重要,改人即调教演员、培养演员。
四、树立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思想
那么,在培养演员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呢?一是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演员们以前都是单干,集体生活不习惯,有很多需要适应。刚才所说的主要演员等问题,渐渐地大家都接受了。后来我们也不叫主要演员,成立了艺委会,艺委会委员则更加名正言顺了。
一个人的人生目的要明确,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只是为了吃、穿、享受,还要为社会为人民服务。当然,也有些演员建立了人生的理想,要求入党,像朱慧珍就是解放后上海戏剧界、曲艺界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演员。
评弹团建立了很多规章制度。大家都遵守团规、团章,开民主生活会,相互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期间还搞了一次民主改革,这次民主改革是从工厂学来的。解放以后,许多工厂派了工作队进去搞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中发动工人忆苦思甜等。评弹演员和这些响档其实都是贫苦出身。所以解放后,都有翻身感。通过忆苦,每个人都联系了自己的身世,这对演员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五、成为响档都是不简单的——从提高演员文化素养抓起
成为评弹响档不是容易的,我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有关杨振雄的文章,文中写了杨振雄如何学本事,编辑给我改了题目为“杨振雄所以是杨振雄”,这句话倒是说明了响档所以成为响档是不简单的。杨振雄在编《长生殿》时,背包囊、走官塘,漂得来一塌糊涂,他们讲起来叫“看茶会”,没有生意,没有人睬他。杨振雄泡四年图书馆,学艺术,学昆曲等,经过了艰苦磨练才成为大响档,才有现在身上这点本事。
调教演员,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文化。进评弹团时,这些演员有的小学也没有读过。徐丽仙就是小学也没有读过,张鉴庭也是这样,看他是大响档,到了团里还学文化。我们利用一切机会给演员讲文化。评弹团刚成立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鼓动演员多看书。我还带着文学组的同志到书店去买书,买适合演员看的书。
我们还给演员上文化课。进团时这些演员不懂什么是文艺思想,一出节目要大家提意见,只会讲这只茶杯不该放在这里而要放在那里,只会提提这样的意见。到后来,什么是主题思想,什么是人物刻画,什么是矛盾悬念等都懂了。那时上面提出演员要学“斯丹尼”,我们评弹团也学了,这是有帮助的。斯丹尼讲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这对评弹演员也是有所促进的。
有时候,团里利用晚上乘风凉时间(因为都住在团里)读唐诗。我记得那时拿一块小黑板,上面抄了一些唐诗,有首唐诗是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一些演员是苏州人,这首诗是写唐朝时的姑苏,在苏州生活过的人非常感兴趣。从这里大家都知道了要读唐诗、读宋词,要增加文化知识。
除了学文化,还有就是组织观摩。那时上海的演出团体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外地来的演出团体或者自己的演出团体演出都要演观摩场。观摩场都放在上午,因为演员下午都有演出,观摩场的票子都发到每个团里。这些观摩场几乎每个演员都可去看,观摩戏曲、观摩话剧、观摩外来演出团体等,打开了演员的眼界。观摩后我们还组织讨论,大家看了有什么想法就讲。通过这些活动使得演员思想境界提高:感觉到我作为国家剧团的一个演员,我作为剧种的一个代表,我应该怎样做。
现在一直在说,剧团要有精品意识,要搞出自己的精品。实际上当时评弹团的演员都有精品意识。一个响档,他出去的身份是响档,一定要有听客欢迎的书的。后来我们上海评弹团在听众中建立了威信,成为了名牌,大家都不肯坍台的,希望每一场都演好。拿出去的新作品,都希望得到听众好的口碑。杨振雄说起来是:“要打胜仗。”当然他是把演出比喻为打仗。实际上每个演员都有高的品位和高的目标,那时评弹团演员的精品意识都是自觉的。我们上海人民评弹团的演员出去不好坍团里台的。
六、深入生活,获取创作源泉
从调教演员来说重要的是深入生活。评弹团一成立就去治淮工地,三个月回来,演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家感到下生活非常有必要。后来,团里创作一部《海上英雄》,蒋月泉编演的,他与周云瑞一起到海军部队下生活。排演《王孝和》,因在上海,全团去拜访忻玉英,并去王孝和墓凭吊。后来,这成为了评弹团的一个创作程序,如创作《江南春潮》到江南造船厂,《芦苇青青》去了太湖。蒋月泉排长篇《夺印》,从扬剧改编,排练之前带领一个小组到泗泾去深入生活。我当时还去泗泾看过他们,电影演员黄宗英也在那里深入生活,与他们在一起,所以说深入生活很重要。
评弹团把“谈道”变成了一种习惯,这也是继承了评弹演员的“坐茶会”,许多演员在一起讲书,讲评弹。每天上午在团里坐在一起谈艺术,交流各自经验,获得艺术养料。我觉得干部参加谈道有两点好处:第一自己做学生,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不懂评弹,在谈道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第二起指导作用,帮他们总结经验,把经验提高到新文艺理论层面。
七、良好的艺术氛围使精品迭出
当时评弹团的艺术气氛是很浓的。像蒋月泉等一些老同志到晚年还非常怀念评弹团当时的生活。每个节目到书场去听当然不大可能,因为大家都是演员,在团里排书、响排,都是演员们在听。演员排书时的精彩之处,也是其他演员相互学习的时机。有一段时间,杨振雄在团里排唐明皇一角,不少演员在路上走时都在模仿:“高力士……”当上楼梯时,“杨娘娘上楼啦”,年轻的演员常常模仿。徐丽仙唱《梨花落》,很多青年演员,包括团里新来的一位年轻干部住在团里,早晨起来就对着窗外唱梨花落。凡是艺术中有好的东西,大家都互相学习。
八、良性竞争促进评弹艺术发展
评弹团是一个集体,评弹艺术的发展,竞争是很重要的,我们团里形成了良性竞争。过去所谓的“敌档”,两档书大家在同一码头上谁说得好,当时码头上敌档牵涉到名和利。到了团里,大家都是团里的一员,但我觉得还是要有良性竞争。哪个演员今天演了一回好书,对其他演员都是一个促进。所以,后来不需要领导去布置,每个演员都会自己去搞些创造性的东西出来。在整理《玉蜻蜓》时,苏似荫、江文兰加了一回《智贞探儿》,这在《玉蜻蜓》原来的书里是没有的,他们在整理过程中谈人物、谈三师太人物、谈里面的矛盾,最后编成了一回书。作为领导,要在演员有积极性出来时加以肯定。有了一回好的书,就在全团演出,给他们表扬和鼓励,使每个演员都有激情要搞好的作品。
所以到后来,我们编长篇时,张如君、刘韵若写《李双双·补苗》,华士亭自己提出要搞《战地之花》,先是编中篇,后来编长篇。说明每个演员都在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有好的,领导一定要积极支持、表扬,以增强他的信心。当时演员认为,领导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比较准的,所以领导讲好,他们心里得到满足了。最近有两个演员在改编《三大亨》,见到我说,我们听别人讲好不在乎,只要老团长讲好,我们就满足了。
当时团里的改革,只要对评弹发展有利的,我们都予以支持。所以很多新唱腔、唱调都得以推出。有一次吴子安与张效声演《威震海外》,就是讲乒乓球的,在文化广场演,本来评话双档是用扇子的,他们想出来用乒乓球拍上台,结果效果非常好。老艺人是不会不懂评弹规律的,你支持了这些创新,其他演员也胆大了,敢于创新了。
九、有了实践才有了概念
我认为实践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只从概念出发。评弹创作的实践,整旧的实践,改革的实践,正是有了这些实践才有了概念。评弹现在用的名词,很多都是当时实践出来的。譬如“选回”,当时上海许多听众不可能每天都来听长篇,当时在仙乐书场办过一个星期演两回书,这个书是经过整理,演员懂得了人物,懂得了结构,使长篇更集中更精炼。叫什么名字呢?评弹不是戏,戏剧把它称为“折子”,评弹一周演两回的就叫“分回”。分回里再精炼选出来的,包括像《庵堂认母》,最早我们叫“精华”,叫长篇精华。后来觉得“精华”太高了,且范围小了,就想出来叫“选回”。长篇或中篇中的唱段,演员们都发扬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有些唱段在听众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是说每一回书里都最好有一两支比较好的唱段,这样听客也就比较满意了。那么这些好的唱段叫什么呢?一回回书叫“分回”,选出来好的我们叫“选回”,选出来好的唱段就叫“选曲”。开始评弹是没有演唱会的,后来我们就把评弹开篇放在一起,一只一只唱,叫它“演唱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评弹的流派如蒋调等,听客非常要听。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要回收人民币,卖“高价饼”。评弹听众多,可在这方面起点作用。于是我们想出来用各种风格的唱调来演出,那时蒋调就叫“蒋调”,陈调就叫“陈调”,没有人称之为“流派”,这是我想出来的。那时袁水拍到上海来讲到毛主席在双百方针中说科技上要发扬不同学派,文艺要发扬流派。袁水拍说我们讲流派,想不到评弹倒是有流派的。于是觉得“流派”两字很好,唱就叫“流派唱腔”。流派唱腔放在一起叫演唱会,放在上海音乐厅演出。票价卖到九角一张,那时九角就是高票价了,等于卖高价饼,可以回收人民币。流派演唱会很受欢迎。现在叫的一些流派唱腔,严格讲不能叫流派唱腔,所以杨德麟提了六条标准。有些只能叫“风格”,不能叫流派。严格地说流派在发声、唱法上都应有一套理论,才能成为流派。当时,我们在实践中还搞了很多新的形式,所以应该讲先有实践,才有概念。
十、提高演员审美情趣,发挥演员艺术激情
除了领导对演员讲这个作品好,我们还要对作品进行点评。不是说你今天好就好,要讲出好在什么地方,以提高演员的审美情趣。懂得什么是好,怎样才能好,也包括他的整个台风等。这样,演员对领导讲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好的,也非常信服。这些对推动和发展艺术是很有好处的。后来,整个评弹团搞成了一所大学堂。学习政治,学习艺术,大家得到提高。我说我们整个团像个大花园,每个演员都发挥积极性,都搞创作,都搞作品。到时候,好像你已施足了肥,自然而然,今天这档拿出一回书来,明天这个演员拿出个新的节目来,整个花园里用不着一个个去抓,一个个去推,它自然而然地焕发了出来。
我觉得搞艺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激情和灵感,演员你硬派他一个任务,叫他写个什么作品,激情出不来。而演员在谈道时,在谈创作计划时,这个是如何如何好,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演啥的,这很重要。他有了想法,你把它纳入演出计划,他搞出来的作品会比上面的命题作文好得多。因为文艺这个东西还是要有感情和激情的。评弹团的这批演员,往往在艺术上都是有激情的,要发挥他们艺术上的积极性。例如在搞《晴雯》时,杨振雄就说:“你来写,我来演。”他有这样的激情有几次杨振雄约朱雪琴演《挑帘》,他的《武松》书里有一回书,一个潘金莲,一个西门庆,杨振雄演西门庆非常有特色的,他吸收了川剧的角色,他叫朱雪琴演潘金莲,他们两个人来拼档。这种想象、这种激情是会促进好的节目产生。我们好多回书都是这样形成的,如刘天韵还要搞《阿Q正传》,他来演。当然有些想法没有做到,想到的多,做到的少,但是能够有想法,才会有做到,有很多好节目的诞生。
十一、科学的工作程序保证了节目的质量
我再讲一讲评弹团建立的一套工作程序,这一套工序保证了节目的质量。一般讲工序当然要有大家的激情和议论,创作的题材,还有深入生活。深入生活后回来,编出了剧本,剧本往往要进行集体讨论,如艺委会讨论等,讨论后修改,然后派给演员,这个我们叫二度创作。实际上原来的长篇也有二度创作的,演员也在不断修改加工。演员拿到剧本后人物应该怎样的,主题是什么,演员都要做案头工作。拿到了剧本,用演员的话说叫“拽书”。我们评弹团创造了几个术语,一个叫“切书”,切书就是把一回书的结构加以完整,啰嗦部分去掉。“拽书”就是等于把衣裳拽拽挺。剧本写好后要对每个人物的说表、动作,要想象出来、写出来,这叫“拽书”。拽书成了我们很重要的工作程序。拽好了书,排是一回一回排的,放在一起排叫“连排”,几回书一个中篇放在一起排,连排下来还要“响排”,在全团排,全团讨论。
再下来是评弹团演员很重视的叫“三度创作”。评弹演员很重视自己的节目一定要拿到听众中去演出,有很多听众的反应,促进了演员的发挥,促进了演员的灵感和创造性。当然也有听众帮助演员创造,听众提意见,听众写东西。实际上听众的反应,促进了演员的创造。以前的评弹形式也是这样,一部长篇要说不知多少遍才能成熟。我们把这叫“三度创作”。评弹演员有不少他们自己的名词,三度创作叫“磨刀”。一部新书出来要去磨磨刀,这个磨刀是指新刀要磨一磨把锋口磨出来。所以,评弹团新作品初演都不放在上海,先要找个小码头,一个小地方先去演,听听客反应,根据听客的反应,再进行修改,进行再加工。这个也可以叫三度创作。但是这个三度创作有一条,根据评弹演员的经验。在听众中演出叫“磨刀”,文雅的说法叫“出包桨”。搞玉石的人都知道,就是手里把玉石磨磨,会磨得发亮光出来,叫“出包桨”。这是玩玉石的术语,评弹演员把它引用到评弹中来。在听客中预演可以“出包桨”。根据评弹演员的经验,演半个月十五场左右,这个书是最最成熟的。于是由演员记录下来,合成定本,此后就不能随意改了。
评弹团的演出本一般在演了十五天左右,要把自己说的书记下来,然后再归纳到创作人员处,变成功一个定本。有了定本之后,再有演出要求演员不好再乱改。整理的旧书,如《怒碰粮船》《抛头自首》,后来有演员说《大红袍》,根据自己的习惯,根据自己的改编来演,我们团里就认为原来修改的意图、整理的意图被歪曲了,只讲台下效果好是不妥的。所以评弹团有一条规定也是很严格的,凡是定好的本子,不希望你在台上演出时随意乱改。
十二、评弹团必须密切联系群众
最后讲一点,我们评弹团搞评弹艺术等一定要联系群众,要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评弹界肯定都是我们的群众,要与他们联系。我们搞过几次培训班,邀请他们参加。评弹听众开座谈会,还有评弹爱好者也搞过几次活动。陆百湖告诉我,他参加过评弹团的培训班。我们还与业余评弹团和票友联系,特别是当初的工人文化宫评弹团,现在叫“茉莉花”,与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中有几个评弹积极分子,还编了书。他们编的书,我们觉得好的,我们评弹团拿过来演,这也是对他们的支持。他们有两回书,一回是《废品的报复》,根据匈牙利电影改编的;另一回是两位在邮局工作的人写的《投递员的荣誉》。他们搞了后,我们觉得这个节目不错,结果评弹团拿来排演。
那时评弹团经常到工厂去演出,像这样的节目我们拿到厂里去演,对业余评弹也是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评弹艺术要发展,必须要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做群众工作,总是强调一个团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