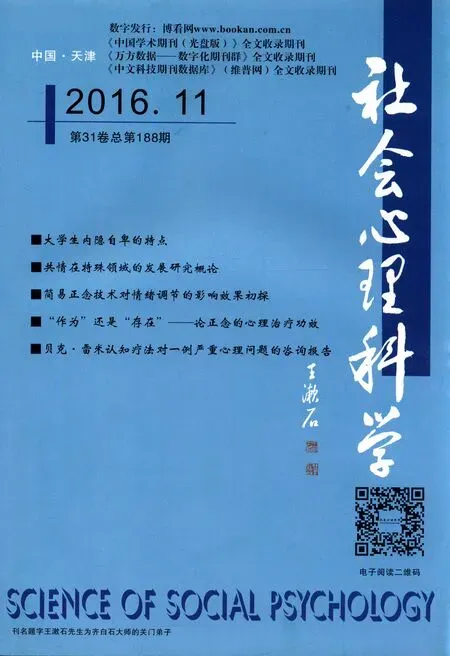基于不同群体的本土心理资本研究现状与展望
王继辉,刘丽红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哈尔滨 150000)
基于不同群体的本土心理资本研究现状与展望
王继辉,刘丽红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哈尔滨 150000)
随着跨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心理资本的本土化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通过对已有心理资本的本土化研究进行阅读,并将不同群体的现有研究进行整理,从中发现:①目前对本土心理资本中的人际型心理资本和事务性心理资本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界定;②对不同群体的本土心理资本情况测量方式不同;③目前研究所涉及的群体有员工、学生、教师和医生,因此心理资本的本土化研究仍需进一步加深。就目前研究的状况,本文对心理资本的本土化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并未之后的研究提出建议。
本土心理资本 事务型心理资本 人际型心理资本
1 引言
20世纪初以塞里格曼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发起了一场积极心理学研究运动,强调心理学研究应该重视人的积极情感,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的研究(Seligman,1999和2002)[1-2]。Luthans将塞里格曼提出的积极心理学理论应用到组织行为研究中,提出了“积极组织行为学”(Luthans,2002)。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在2004年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后,提出了影响组织竞争的第三个新视角——心理资本,这个概念相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较大的“潜力”(蒋建武和赵曙明,2007)[3]。柯江林等(2010)在整体框架下进行研究得出,员工的心理资本对工作的积极作用优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在较为复杂的环境下会获得较突出的效果。
以积极组织行为学和积极心理学作为理论框架,并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分析的基础上,Luthans提出人的“积极心理资本”(Luthans F, Luthans K W和Luthans B C,2004)。Luthans等人将其定义为“是个体一般积极性的核心要素,同时具有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心理状态,它的作用超出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与开发促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Luthans F和 Avolio B,2005)[4-5]。从 Luthans (2004)最初提出已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对心理资本的研究有了较多成果。在国外学者研究中发现心理资本能促进个体在组织承诺、领导效能、工作绩效,以及可以降低工作压力感和缺勤率。心理资本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仲理峰(2007)[8-9]利用Luthans编伟的问卷对企业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和组织承诺进行了研究,得出心理资本对这几个变量都有积极的影响。柯江林、孙键敏和李文瑞(2009)通过访谈调查并根据扎根理论,系统的构建了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两个维度,同时与Luthans编伟的心理资本量表比较,得出编伟的本土量表的信效度优于中国情境下Luthans的量表。其中事务型心理资本和Luthans的量表基本相似,人际型心理资本火更多地包含了本土文化的内容(柯江林和孙健敏,2009)。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两个量表之间出现差异的根源所在,故在本土文化大背景下研究心理资本单纯依靠Luthans的问卷会出现一定偏差,甚至掩盖我国公民心理资本的真实情况。量表的使用是有前提的,当利用国外的文献时一定要慎重查看文化差异造成的影响(郑伯埙,2005),文化的不同将影响一个人一生中得到的资源状况,可见文化的重要影响不可小视。
总体而言,在跨文化研究的浪潮中,本国学者对本土化心理资本理论缺乏足够关注,相对应的实证研究和实践经验更是阙如。因此,目前对本土心理资本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柯江林等学者的研究。就目前研究状况有必要了解本土化心理资本的研究进展,从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2 本土心理资本的内涵和构成
2.1 本土心理资本的内涵
要想深入了解本土心理资本的内涵,首先,要了解心理资本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变量。心理资本既不是一个心理特质变量(稳定、难以改变)也不是心理状态变量(能够瞬间改变且具有瞬时性),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类状态变量(容易改变、可提升的),这表明有的积极心态就不属于心理资本这个变量(Luthans,Aviolio,Avey和Steven,2007)[6]。故本土心理资本也应该是一种类状态变量。
柯江林(2009)[10]将心理资本定义为:在中国组织情境下,个体在为人处事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可测量、可开发并且对工作绩效有促进作用的一种积极心态或心理能力。
孙阳和张向葵(2013)[17]将本土心理资本界定为:事务型心理资本强调处理事务过程中涉及的积极类状态;人际型心理资本火偏重人际交往中展现的积极心理力量。
目前对本土心理资本的界定还没有得到一致性的认可,多数采用的是柯江林的概念或者大意相近的界定。其中对人际型和事务型心理资本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可能是目前的研究还仅仅把两者看作维度对待。今后的研究能否将两者单独作为变量展开研究有待商榷。
2.2 本土心理资本的构成
柯江林、冯静颖和邓建光(2013)在Luthans提出的心理资本基础上,结合本国文化提出本土心理资本有事务型和人际型两种,其中的事务型心理资本包含以下四个成份:奋发进取、坚韧顽强、自信勇敢和乐观希望四个方面。而人际型心理资本有包容宽容、谦虚诚稳、尊敬礼让和感恩奉献四方面构成。
吴伟炯、刘毅、路红和谢雪贤(2012)[19]通过研究中小学教师将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所包含的成份有了新的构成,这与柯江林(2009)对心理资本研究相似,其中事务型心理资本包含希望、乐观和坚韧,而人际型心理资本包含自谦、利他、感恩、情商(情绪智力)和信心(自我效能)。
从上述两种划分可看出,本土心理资本与Luthans提出的心理资本维度存在相似的成份,反应出部分心理资本成份跨文化的一致性(柯江林2009),其中人际型心理资本结合了本土传统文化特征。整体上而言,目前对本土心理资本的研究还是从人际型和事务型两个维度角度进行分析解释,因此本土心理资本划分的人际型和事务型心理资本值得进一步研究。
3 不同群体的本土化心理资本研究状况
3.1 企业员工群体相关变量的实证研究
在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等衡量员工态度的变量方面,柯江林、孙健敏和李永瑞(2009)[10]利用编伟的本土量表对几所大学的在职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得出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任务绩效存在较强正相关,而人际型心理资本与周边绩效有较密切的正向关系,两者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最好,其次是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最低。总体可看出人际型心理资本与上述三变量的相关性要高于事务型心理资本。
柯江林(2009)对政府培训班人员、在职学生和IT人员进行施测,利用回归分析发现①在任务绩效方面,事务型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的变异解释要优于西方心理资本,而人际型心理资本是西方心理资本的重要补充。②对人际型心理资本和事务型心理资本的关系研究得出,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
赵书松、廖建桥和赵君(2011)通过探讨变革型领导对员工本土心理资本间的关系,得出变革型领导对事务性和人际型心理资本都具有正向作用,且这两者同时促进知识共享。当将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同时引入后,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的解释作用增强了,从这点看本土心理资本对这个过程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并且人际型心理资本起的中介作用大于事务型心理资本。
柯江林和孙健敏(2014)[10]将心理资本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三个变量进行研究。通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得到:①本土心理资本对工作满意度有积极地作用,若将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同时考虑到一个模型中,可得出事务型心理资本作用不显著,所以人际型心理资本才是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②人际型和事务型心理资本对组织承诺都有积极作用。当放进同一模型考虑时,得出在较高的人际型心理资本条件下,事务型心理资本越高组织承诺就越高,但在较低的人际型心理资本条件下,事务型心理资本越大反而组织承诺降低,也同样表明人际型心理资本才是组织承诺的主要因素,事务型心理资本对组织承诺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本身蕴含的深层意义有助于人际型心理资本的形成;③在离职倾向方面。人际型心理资本对其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事务型心理资本对其没有显著作用,但是当人际型和事务型心理资本纳入统一模型中时,发现事务型心理资本对离职倾向出现负相关。故人际型心理资本对离职倾向起到主要的缓解作用,当排除人际型心理资本对离职倾向的作用后,事务型心理资本竟对其产生正向影响。
张爽、沙飞和张志华(2014)[20]以新兴的物联网工作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柯江林(2009)编伟的本土心理资本量表中的事务型心理资本的20个项目进行研究,得出事务型心理资本对交互记忆系统和创新绩效都有积极的作用,事务型心理资本可以通过交互记忆系统对创新绩效进行作用,即交互记忆系统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
总的来说,在员工群体中的本土心理资本研究所涉及的方面较多,同时也正在向新型的员工群体和认知方面的变量结合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员工在不同变量上的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的表现不同,其中的差异是两种心理资本涉及的方面不同,以及事务型心理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际型心理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对员工群体的研究更注重的是对员工心理资本的开发与管理,因此之后的研究可能会更倾向于本土心理资本研究结果的应用。
3.2 学生群体相关变量的实证研究
柯江林和郭蕾(2013)[15]研究了创新行为与事务型心理资本、人际型心理资本的关系。研究中问卷的作答全部采用“他评”问卷调查。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事务型心理资本的四个次级维度对创新行为均有积极作用,其中自信勇敢对创新行为影响最大,而乐观希望的影响不显著,可能乐观希望对创新行为的积极作用被其他的维度完全中介了;在人际型心理资本的四个次级维度中,包容宽恕、尊敬礼让和感恩奉献对创新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谦虚诚稳对创新行为存在负相关且未达到显著水平;在本土心理资本与创新行为的研究中,本土心理资本对创新行为的作用高于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的单独使用,这可以看出人际型和事务型心理资本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
柯江林、冯静颖和邓建光(2013)[13]对本土心理资本与大学生创业意向关系进行研究。采用问卷配对调查法(心理资本量表有随机选择的研究对象的室友作答,创业意向量表自评),研究结果显示:①大学生的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对创业意向仅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而其中奋发进取、乐观希望与近期创业意向有正向效应其余呈负相关;②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对远期的创业意向呈现出较强的积极作用,各次级维度上的强弱不同。总体来看,人际型心理资本和事务型心理资本对近期或远期的创业意向影响相似。
柯江林、孙健敏和韩瑛(2014)[16]研究大学生心理资本对自身的求职绩效的影响,同时引入积极的求职行为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采用修订后的适合大学生的心理资本问卷,同时采用配对调查,研究中对求职绩效的衡量从三个方面(求职表现满意度、就业单位满意度和找到工作与否)进行研究的。通过回归分析得出:①事务型心理资本对求职表现满意度的积极作用显著,其中积极行为的一个维度招聘信息对两者的关系起到了部分的中介效应,而人际型心理资本对求职表现满意度的作用受到了事务型心理资本的缓解;②本土心理资本、积极求职行为、招聘信息和事务型心理资本对能否找到工作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人际型心理资本对其存在低程度的负向作用;③事务型心理资本、积极求职行为、简历伟作发送和招聘信息搜寻对就业单位满意度都存在正向显著影响,人际型心理资本对其存在低程度的正向影响。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人际型心理资本对求职绩效的作用受到事务型心理资本的完全缓冲。
总的来说,本土心理资本在学生群体中的运用是在最近几年开始的,研究成果还较少,但是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倾向于探讨本土心理资本与现实问题的关系,这些应用对学生群体步入社会以及应对复杂社会环境等方面有较好的预测,再者学生群体的研究针对的群体多是大四学生。目前对学生群体的本土心理资本测量采用的是“他评”,可以很好地避免社会赞许,但是“他评”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值得进一步考虑。
3.3 教师群体中相关变量的研究
吴伟炯、刘毅、路红和谢雪贤(2012)[19]研究本土心理资本与职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中小学教师采用访谈等方法研究,也得到心理资本由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构成,并研究两者与职业幸福感的作用。研究表明:①事务型心理资本通过影响工作投入,进而促进工作满意度,最终影响个体离职意愿。②人际型心理资本可以通过能量补充过程,来减缓工作倦怠进而达到降低离职意愿,同时通过工作满意度来降低工作倦怠,这样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情境中,人际型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比事务型心理资本大。③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也可通过二级动机激发与能量补充过程来影响职业幸福感。
孙阳和张向葵(2013)[17]研究探讨本土心理资本、情绪耗竭和情绪劳动策略间的关系。研究中直接采用柯江林编伟的本土心理资本量表进行研究,得出幼师的情绪耗竭对情绪劳动策略中的自然行为、深层行为以及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有积极作用。不同程度的人际型心理资本可以影响到幼师情绪劳动策略的不同方面,而事务型心理资本没有这样的作用,故人际型心理资本是影响情绪劳动策略与情绪耗竭的真正调节变量。
总体而言对教师群体的研究很少,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也可以看出教师群体中人际型心理资本的作用比事务型心理资本大。出现这种偏差的原因可能在于教师这个职业与人接触的较多,使得教师必须能够对自己人际方面有一定的觉察。事务型心理资本在老师群体中的表现可能是备课、上课等,这些个人事务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与其他个体更好的接触交流所服务,所以事务型心理资本的作用常备人际型心理资本所掩盖。
3.4 医生群体中相关变量的研究
孙葵、尹文强和黄冬梅等(2014)[18]从医生工作要求和职业倦怠两方面研究本土心理资本。在柯江林提出的本土心理资本量表的基础上,结合医生的实际情况修订了心理资本量表。通过分层回归分析得出:事务性和人际型心理资本与医生的职业倦怠都存在负向关系,并且工作要求与两者存在的交互作用显著,但是这几方面的回归分析的解释力都比较低。
对医生群体甚至说医护群体的本土心理资本研究才刚刚开始,因此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研究较少或者起步较晚,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医生群体的思维固化,认为医生是健康的群体是帮助别人的人,但随着医生群体问题的逐渐明显,如:医德工作懈怠、收受贿赂等诸多危机医生群体形象的状况,使得研究者开始关注医生群体。
4 小结与展望
4.1 小结
随着近些年学者们对跨文化研究的重视,诸多变量也开始进行本土化研究。目前对本土化心理资本研究的权威文献还较少,涉及的群体还不够全面,但从现有研究中也可了解到不同群体在本土化心理资本上的状况。
从现有本土心理资本在不同群体中的研究可以看出:①与不同变量进行研究时,本土心理资本的侧重点不同。事务型心理资本对创新、创业意向和任务绩效等涉及个人的事务时作用更强,而人际型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等涉及个体态度和人际活动等方面呈现出较好的预测作用。但是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在0.5左右(柯江林2009)。②在研究对象方面。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在职学生、企业员工、一些培训班学员和大学生群体等,研究所涉及的群体还很局限。③在测量方法上。大学生和其他群体有所不同,针对大学生群体本土心理资本的测量多采用室友的他评,而其他群体火直接进行自评。其中采用室友进行的“他评”可以避免研究对象因为社会赞许而表现更好的虚假现象,但是室友的评论可能带有更多的关系成份,这种影响与研究对象本身表现出来的“虚假”现象哪个更能真实反映研究对象情况还有待商榷。
本土心理资本研究较少原因可能是:首先,本土心理资本的理论没有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可,使人们更多采用Luthans提出的心理资本构成进行研究。其次,先前采用Luthans的心理资本问卷进行的研究较多,没有较多本土化心理资本研究的切入点。再者,近几年对本土心理资本的研究开始出现增多,表明一个理论的提出到应用推广需要一定的时间。
4.2 展望
1.现今对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且本土心理资本的内在机伟以及对个体心理资本的管理和开发,都将随着对两者的研究深入逐渐完善。其中对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的研究还只是把两者当做心理资本的维度来进行研究的,尽管也得到了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在不同变量上的不同效果,但是如果单独提取出来进行研究是否还能得到相同的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验证。通过进一步的理论完善,可以重新编伟人际型心理资本量表和事务型心理资本量表为后续研究提供工具。
2.对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的研究领域能否在进一步扩宽,比如考察老年人、失业或待业群体、医护人员等在两种心理资本上的情况。随着研究群体的逐渐加深,能够总结出各行业的心理资本状况以及开发管理方法。
3.目前的测量方法呈现出:针对员工群体采用自评,而大学生群体采用他评,那么自评与他评的差异情况是否显著呢?如果差异显著某研究对象群体更适合哪种方法;如果不显著那是不是可以用自评代替他评进行研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另一方面测量数据的收集采用的是问卷自评或他评的方式,将来能否通过计算机模拟场景等多种方式进行数据的收集,来提高对个体心理资本的测量有效性。
4.一个变量的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为实践服务的,那么怎样来开发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既关系到企业自身的经济绩效,同样关系到个体健康的成长,将来能否形成一种较为系统的开发程序或方法,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1]Seligman M E P.The president’s add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1999,54 5-14.
[2]Seligman M E P.Authentic happiness.New York Free Press,2002.
[3]蒋建武,赵曙明.心理资本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J].经济管理,2007,9,55-58.
[4]LuthansF.The need for and meaning of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2,23:695-706.
[5]Luthans F,Luthans K W,Luthans B C.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yond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J].Business Horizons,2004,47 45-50.
[6]Luthans,F,Youssef,C.M &Avolio,B.J. Psychological capital:Developing the human competitive ed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7]Luthans,F.,Avolio,B.J.,Walumbwa,F.O.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Chinese workers: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5,1,249-271.
[8]Zhong,L.F(2007b).Review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research[J].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482-487.
[仲理峰.(2007a).心理资本研究评述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15,482-487]
[9]Zhong,L.F(2007b).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employee’s job performance,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J].Acta Psychological Sinica,39,328-334.
[仲理峰.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心理学报,2007(2)]
[10]柯江林,孙键敏,李永瑞.心理资本:本土量表的开发及中西比较 [J].心理学报, 2009,41,875-888.
[11]柯江林,孙健敏,石金涛,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总效应、效应差异及调节因素 [J].管理工程学报,2010(4): 127-136.
[12]柯江林,冯静颖,邓建光.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创业意向影响的实证研究 [J].青年研究, 2013,3,40-49.
[13]吴伟炯,刘毅,路红,谢雪贤.本土心理资本与职业幸福感的关系 [J].心理学报, 2012,44,1349-1370.
[14]柯江林,孙键敏.心理资本对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的影响.[J].企业管理, 2014,1,121-128.
[15]柯江林,郭蕾.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13,3,22-28.
[16]柯江林,孙健敏,韩瑛.大学生心理资本对求职绩效的影响:积极求职行为的中介效应[J].心理学探新,2014,34,468-473.
[17]孙阳,张向葵.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情绪耗竭的关系: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256-262.
[18]孙葵,尹文强,黄冬梅.医生心理资本在工作要求与职业倦怠间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2,1527-1529.
[19]吴伟炯,刘毅,路红,等.本土心理资本与职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J].心理学报,2012,44(10): 1349-1370.
[20]张爽,沙飞,张志华.事务型心理资本、交互记忆系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J].商业研究, 2014,443(3):92-100.
[21]周文霞,谢宝国,辛迅,等.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和心理资本影响中国员工职业成功的元分析[J].心理学报,2015,47(2):251-263.
[22]Avey,J.B,Patera,J.L,&West,B.L.The Implic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employee absenteeism[J].Journal of Leadership&Organizational Studies,2006,13,42-60.
[23]Papenhausen C.Half Full Half Empty:The Effect of Top Mannager’s Dispositional Optimism o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J].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Applied Management, 2006(7),10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