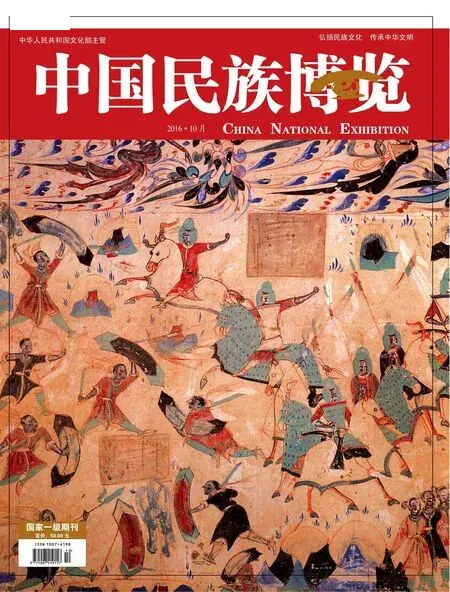文化变迁理论与民族节日研究
何马玉涓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文化变迁理论与民族节日研究
何马玉涓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关于民族节日现代化演变的研究不甚枚举,文化变迁理论被广泛运用。本文旨在对文化变迁视域下的民族节日进行研究,打破对节日现代特征深描的惯例,而将研究重心放到刀杆节成型过程中,通过追朔、推演,以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把握民族节日文化的发展规律。
文化变迁;民族节日;溯源
在人类学界,“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两个概念经常混同使用。有时又混为“社会和文化变迁”或“社会文化变迁”。从严格意义上来作区分,社会变迁的使用范围更为宽泛,可以指整体性的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也可以具体到社会形态或文化模式某一方面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变化,诸如食物、服装、工艺、技术以及习惯、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克莱德·伍兹就认为“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都是同一过程的重要部分,但在必要的时候,在概念上也可以区分,倘若文化可以理解为生活上的多种规则,社会就是指遵循这些规则的人们的有组织的聚合体。”[1]
研究之初,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前行。早期古典进化学派着力于说明文化变迁与发展的普遍作用,较少关注地域差异性和民族接触及其文化交流。传播学派的研究则将研究重心放在了文化的地理环境、空间变化和地方性演变,强调文化的散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进化学派的不足,但也忽视了内部因素,忽略了人类创造文化主观能动性,对文化变迁过程或传播时间顺序的解释缺乏说服力。功能学派强调文化变迁是以适应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为目的而发生的。在讨论文化变迁的动因上,人类学家通常把创新、传播、进化、涵化、冲突、适应、同化、融合和整合等都归在文化变迁这一动态的过程中予以分析和研究。[2]由历史学派发展的“文化区”理论,认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是由相似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构成,此区域内存在着文化中心,文化的变迁过程就是文化特质、文化丛由中心向外扩散的历史,“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被吸收、重造和向外辐射这个变迁的首要源泉,被称为文化顶峰或文化焦点。”[3]史徒华在《文化变迁的理论》中提到,关于文化演进的研究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重建或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与取向。他提出“对环境的适应”是文化生态的核心理念,借用了生物学上生态的意义,即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文化生态的适应才是文化变迁的动力。文化核心即是与生产和经济活动最为关联的各项特质的集合,与经济活动有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与宗教模式皆包括在文化核心之内。其他更多的特质则可能具备非常高的变异性。这些特质称为次要特质,主要受纯粹的文化-历史因素所决定的,如传播或无意的创新。正是这些次要特质使具备相同核心的文化显出各自的独特性。当然文化的确倾向于保持不变,人们的文化态度的确能够使得变迁的速度缓慢下来。但是在过去的数千年内,在不同环境中的各文化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极为剧烈的变迁,这些变迁基本上可归因于新旧技术交替与生产方式变化引发的新适应。即使偶尔有文化性的障碍出现,也阻碍不了因为需要、适应的步伐。[4]国内学者也倾向于文化变迁的动力研究。在王海龙、何勇的著作《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中对文化变迁动力因素做了详细表述:如果文化的供应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如果洞察到了,并且掌握了新的、进步的工具;如果能够作出必要的反应;如果新的事物比旧的事物看起来更令人满意;其他因素。如“中枢导向”或“强制文明”。[5]黄淑聘和龚佩华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要点,社会发展的合力可以看作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6]
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少数民族节日变迁研究成为了热点。学者们将目光聚焦于近30年民族节日的变化,而事实上,漫长的节日成型过程更加不容忽视的。在此,我以西南地区傈僳族刀杆节为个案,不难看出,文化变迁理论在民族节日溯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傈僳族刀杆节的研究放置于文化变迁背景之下,需要讨论的便不仅仅是现代社会近三十年内出现的问题。有关节日的一切因素,文化历史、民族发展、地理环境、社会适应等都受到文化变迁的影响。因此,浓墨重彩地从明代开始进行历史梳理才是研究刀杆节的文化演变过程的基础。
现在,学界对于社会变迁的动因达成一项共识,即社会文化变迁的具体动因在于新要素的产生。一般情况下,社会变迁新要素的出现的因素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积累为基础,从社会内部产生。二是从外部导入,从而对原来的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导入的外部要素与社会内因共同作用,推动社会变革的发生。
腾冲刀杆节的传说体系依附于明代三征麓川的将领王骥,而明代正是影响腾冲、乃至云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而这个时期,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成为影响云南社会变迁的明显的外部新要素。从根本上改变了云南人口的民族构成。来自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与不同地区的汉族移民,完成着他们自身的土著化转变,在与当地各民族的相互交融中,带入了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因子,为云南社会注入新的活力,逐渐影响和改变云南社会的发展面貌及民族关系,通过民族融合完成社会文化的变迁。民族融合是一个讨论起来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相互融合的民族先要拥有共同的生活地域。在其中,他们共同生产生活、文化交流、相互影响、逐渐融合。因此,民族杂居形成的共同地域是民族融合重要前提。从局部区域看,汉族移民的分布具有城镇、坝区、干线、要冲和开发新区相对聚居的特点,但是从全局看,汉族移民实际散处于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呈现出在滇中、滇东、滇西和滇南等广大地区与当地民族杂居的局面。汉族移民的散居分布,打破了云南当地民族原本存在的较为固定和完整的民族地域,切割了传统的民族聚居区,将在千百年历史中云南各民族相对稳定的地域,分离为一个个互有联系却分散的、较小的民族聚居区,使诸多民族失去了单独的领域,逐渐变成了汉夷杂居,推动了各民族大杂居趋势的发展。[7]民族融合与地主经济发展则是明代云南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内在动因。汉族移民在土著化过程中与云南各民族的不断融合,反过来推进了少数民族社会的变迁。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8月),朱元璋做好准备,“先给以布帛钞锭为衣装之具,凡二十四万九千一百人”,欲平定西南[8]。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征南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征南右副将军。根据朱元璋的部署,傅友德等率兵先至湖广,征集兵马,增加兵力,沿途又招引地方军伍,使征南大军人数达到了30万。九月,30万兵马的征南大军自南京出发,分兵两路,从北、从东两方大举向云南挺进北路,傅友德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等领兵万由四川南下,从永宁四川叙永县直趋乌撒云南镇雄县。东路,由傅友德、蓝玉和沐英等主将亲率主力从湖广西进,经辰沉(今沉陵)、芷江入普定(今安顺),进逼曲靖,据其要害。[9]之后,曲靖被明军攻下,奠定了全面攻取云南的基础。洪武十五年三月,明王朝“更置云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设云南、大理、永昌、姚安、楚雄、武定、腾冲、等五十余府,下辖州、县、千户所、蛮部等。[10]
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前后,麓川路“白夷”土官思任侵夺了南甸的罗卜思庄等村寨后,又“攻陷腾冲卫,云南震动”,更进一步“侵及金齿(今保山)”而“势甚猖撅”[11]。明王朝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三次派王骥发兵征讨麓川,即为历史上的“三征麓川”。在这三次军事行动中,腾冲成为了王骥军队征讨百夷土官的主要战场之一。第一次征讨,王骥与蒋贵一队,率军攻上江入腾冲。十一月初,王骥攻破上江寨,率兵渡下江,通高黎贡山道路,入腾冲,再由南甸(今梁河县东北九保)至罗卜思庄(今梁河西南之芒东)。与此同时,思任发率众二万于沙木笼(在今陇川县东北部)“据高山,立硬寨,连环七营”,抵御王骥军队,被王骥击败。第二次征讨,王骥派人前往缅甸宣慰司,檄缅甸宣慰司缚思任发父子来献,进兵腾冲。至腾冲,分兵两路,截断思机发逃往孟养(今缅甸克钦邦)的退路。[12]
明景泰《云南图经》载,腾冲疆域幅员东至泸江安抚司一百四十里,南至南甸宣抚司七十里,西至里麻长官司四百九十里,北至大理府云龙州三百五十里,东北至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二百七十五里,东南至南甸巡抚司大蒲窝寨一百里,西南至干崖宣抚司一百八十里,西北至茶山长官司五百里。《州志》载“吴志”云:“(腾越)诸夷接境,为远迩之喉襟,作西南之保障,边关要地,山河寸金,申画不严即为弃土。”[13]“腾冲处极边,缅甸掸人之所叩关而入贡者也,威弧不弦,乃无宁岁。”[14]腾冲地处滇西极边,为云南西出缅甸、印度的对外交通要冲。“三征麓川”之后,边患仍然存在,在滇西建立牢固的防卫体系,增兵镇守显得尤为重要。腾冲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屯重兵的据点,修城池加以固守,是确保滇西的重要措施。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将原来的腾冲千户所改设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腾冲筑城置卫成为明代中叶增兵云南,进行军事移民屯戍的重要契机。明王朝调重兵修筑了腾冲卫城。随后,调军腾冲,组织军卫,屯田固守。
正是这样特殊的疆域,影响着腾冲历史进程以及民族融合中本土文化的形成。明代收复西南边境的过程中,多有收编少数民族以补充兵力的情况。腾冲作为“江山阻绝,孤立西陲,四封之外,群夷猥集。”之地,少数民族被收编以制夷是征边的重要手段。明代吴宗尧作《腾越山川封土形势道里论》对收夷有专门记载:“永昌之上江十五喧,皆瘴区也,皆夷氓也,编之里甲,役之驿传,律以国法、官仪,不闻有违戾者。”[15]同时,列举了民族融合的成功案例,强调了少数民族融合的可行性,并大力推行:“为潞之计,虽夷其人,渐变其俗,……侵驯侵狎,潜消而默夺之。”[16]这些史料对应了腾冲傈僳族对其迁徙至腾的解释(随军驻守边关),古永(今猴桥镇)、滇滩均是腾冲地区傈僳族聚居区,也是历史上边境关隘。
腾冲自三征麓川设卫之后,大批汉人进入屯田镇戍,增加了人口,带来了先进技术,垦殖发展,成为滇西少数民族包围之中的文华荟萃、经济繁荣的特区,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积极带动作用。正因为腾冲丰饶的物资和“诸夷接境”的地理位置,清朝之后多有“缅人”、“野匪”来犯,“乾隆三十一年,缅人犯边”、“嘉庆十八年,野匪沿边焚掠”、“道光十七年,野匪余小老烧杀滇滩等处”……面对这些边乱,朝廷多次派兵征讨、剿办。在滇滩调查中,发现当地腾冲傈僳族的民族记忆虽然有零乱、重组的表现,但是主要历史线索与上述历史记载有诸多重合之处。当地50岁以上的傈僳族都认为他们是从北方迁徙而来,经过石月亮,再到腾冲。他们强调过去这里常有外族侵犯,抢夺物资,其先人因为有射弩的本事,被汉族征用,驻扎此地,抵御外敌。关于王骥的传说中,有腾冲建造石城的情节,也与史上明王朝调重兵修筑腾冲卫城相吻合。服从社会变迁大背景的腾冲戍边历史与傈僳族民族融合记忆的梳理为我们推演刀杆节演变过程的重要前提。
生计方式(戍边)在每一个环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而也导致不同社会性后果。环境不只是对生计方式有许可性与抑制性影响,地方性的环境特色甚至可能决定了某些有巨大影响的社会性适应。历史演进过程中,腾冲傈僳族与汉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日常的接触,使得彼此能够有机会接受对方的文化,民族相互融合,即使存在积极吸收或被动接受的情况。因此,同样是狩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腾冲傈僳族却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独特的意识,包括审美与精神。正如上文说述,极边的地理位置使其“盖自麓川之役(缅甸掸人)而还,干戈未戢,弓矢斯张,中朝分阃之心,亦勤至矣。”又“腾越徼外多野夷,素无管辖,自立头目,常为边患。”[17]长期边境内外的对峙关系使得傈僳族边民生出戍守边关的使命感,从而造成“军事”意象和“国家意识”在傈僳族刀杆节中的体现,展现出“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
得出了傈僳族刀杆节中“军事化”特征之后,不妨再大胆地推测一下史上刀杆节的发展过程,那就是刀杆节和“军傩”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据《腾冲县志稿》记载:“腾冲隘地尚有巫教之香僮,其术无师传,信之以为神附之,能跣足于炽炭之中,烧铁练缠于脖颈,空中借火,赤足履利刃,咬瓷瓦如嚼饼饵,所奉为三崇之神,每年二月八日演刀杆之剧,相传此种巫教乃明正统间王骥征麓川时设之以威服诸夷也。否欤?”[18]文中记载的刀杆仪式与傈僳族刀杆节核心仪式基本相同,并提出了刀杆仪式与“王骥三征麓川”的关联问题。这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明代的军傩。
军傩是在古代军队岁终或誓师等祭祀仪式中,戴面具的群体傩舞,兼具祭祀、实战、训练、娱乐的功能。军傩一词,在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书中首先出现,“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随着明代大军出征云南,军傩也就随着带来,并与当地民族文化交融,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傩戏。较为著名,并与明军出征云南相关联的当数安顺地戏。它的形成可以推演到明代边屯时期。“明朝初年,朱元璋的军队出征云南,曾在安顺建城屯兵,屯田的士兵和南迁的移民带来了古老的傩戏,并逐代流传”、[19]。
刀杆节中重要的的核心仪式是“上刀山”、“下火海”,其间香通们经过神授过程,完成蹬、跳、翻、腾空等动作;地戏的表演招式有抛枪、梭枪、架枪、压枪、挑枪、杀转枪、耍刀、顺刀、提刀、夹刀、飞刀、理三刀、围城刀、打黄金棍、打背板等刀、枪、棍技艺,以及徒手对打的空拳对、扭脖劲、鸡打架、左右栽花,等等。这些招式具备大量民间武术成分,也有对现实生产生活动作的模拟。[20]相比较而言,两者都有着强烈的军事化特征。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腾冲是“西南之保障,边关要地”,而安顺也是“黔之腹,滇之喉”,两者都属于军事要地。另外,明初的安顺,居住的主要是布依族、苗族、仡佬族居民。随着南征军屯居贵州,汉族人口大量南迁,改变了贵州历来“民夷杂处而夷居十八九”的居住情况和“溪洞山箐、内外隔离”的闭塞交通。为防范“诸蛮”叛乱,明王朝择地建城,在修建城池的同时,明军在安顺、平坝一带,设置屯、堡、卫、所驻扎人马。这也与腾冲的兵屯过程相类似。明军里盛行的融祭祀、操练、娱乐为一体的军傩随南征军进入贵州,与当地民俗风情结合,逐渐形成了以安顺为中心的贵州地戏。贵州地戏的传承路线,是沿着南征军的行军路线及屯田驻军分布的,呈现出明显的带状构架,其中心是贵州安顺,并一直延伸到云南澄江县阳宗小屯一带。[21]
安顺军傩演变可被借鉴,以来回答《腾冲县志稿》中“相传此种巫教乃明正统间王骥征麓川时设之以威服诸夷也。否欤?” 通过上述对腾冲社会变迁的梳理,军傩演变为刀杆节确实有相对应的历史条件。而且,由军傩转为刀杆节的演变过程一直延续到清代才逐渐固化为现代所呈现出的核心程式。刀杆架所设刀杆数量有明确要求并有所指,香通所要求的72把钢刀代表王骥三征麓川时候设立的72道关卡。腾冲72道关卡在历史上确有记载,但已经是清代之后的事情。“(胡启荣)嘉庆二十五年任腾越厅同知,在任六年,洞悉夷患,依苗疆案例,请于大吏,奏准择险要建石雕,筑坚堡。自古永隘美古、尖高山、蛮旦、槟榔江源,沿江扼设碉堡七十二卡,置买练田,收租给养练丁,以严防堵,边境肃然者六十余年。”[22]这明显受到后世文化的影响,将多个人的英雄事迹叠加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构建出现存的刀杆节口头叙事系统。
刀杆节的演变过程是整个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的产物,因为军事政治的需要带来的军傩被从军的民族运用,成为民族“军事历史”的符号化表现。由最初的军事操演、祭祀行为转变为占卜、祈福手段;由历史事件的复演转变为尚武精神的推崇。但核心没有改变,就是傈僳族文化适应下对自身民族精神与民族记忆的表达,关乎其坚毅品格、健硕体格和维护国家统一、服从总体利益的意识形态。当然,现代社会处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文化自新、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近30年刀杆节的复兴使节日本身发生了适应时代需求的演变,区域性的节日逐渐演变为整个民族的盛大节日,并得到了周边民族认同,迅速地产生出新的内涵与意义。
注释:
[1][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M].何端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2-6.
[2]刘明.环境变迁与文化适应研究述要[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2):56.
[3][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M].何端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4.
[4][美]朱利安·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恭启,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40-45.
[5]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234.
[6]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38.
7]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D].云南大学,1999:317.
[8]《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三八.
[9]《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三九、卷一四二.
[10]《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四三.
[11]《明史·麓川土司传》.
[12]尤中.明朝三征麓川叙论[J].思想战线,1987(4):61.
[13]李根源,刘楚湘.民国腾冲县志稿(点校本)[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87.
[14]李根源,刘楚湘.民国腾冲县志稿(点校本)[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491.
[15]傈僳族民歌中有《上江姑娘我领走》,与此地应该相同。
[16][明]陈宗海.腾越厅志(点校本)[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471.
[17]李根源,刘楚湘.民国腾冲县志稿(点校本)[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43.
[18]李根源,刘楚湘.民国腾冲县志稿(点校本)[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443.
[19]沈福馨.贵州安顺地戏和地戏脸子[J].贵州大学大学报,2003(1):1-9.
[20]桂梅.安顺地戏表演艺术探析[M].民族艺术,1990(1):36.
[21]庹修明.中国军傩——贵州地戏[J].民族艺术研究,2001(4):3-4.
[22]李根源,刘楚湘.民国腾冲县志稿(点校本)[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484.
[1][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M].何端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2]刘明.环境变迁与文化适应研究述要[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2).
[3][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M].何端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4][美]利安·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恭启,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5]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6]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李根源,刘楚湘.民国腾冲县志稿(点校本)[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
[8][明]陈宗海.腾越厅志(点校本)[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9]沈福馨.贵州安顺地戏和地戏脸子[J].贵州大学大学报,2003(1).
[10]庹修明.中国军傩——贵州地戏[J].民族艺术研究,2001(4).
G03
A
何马玉涓,副教授,现任教于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