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彼岸
张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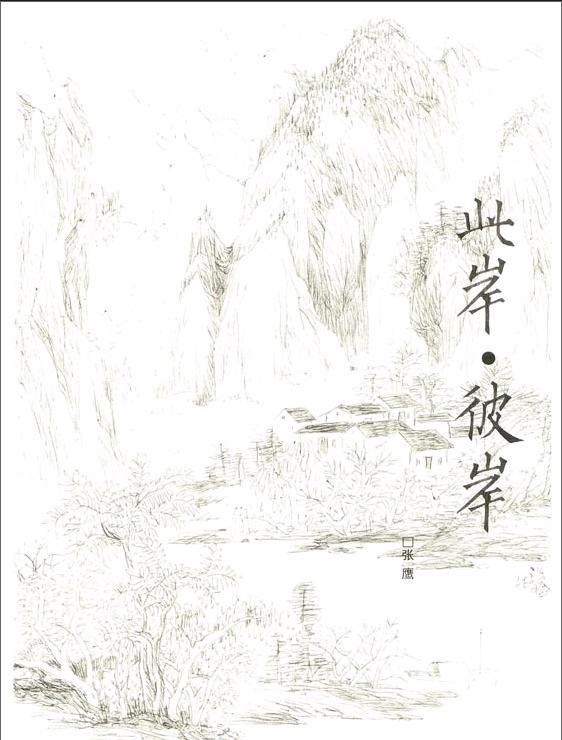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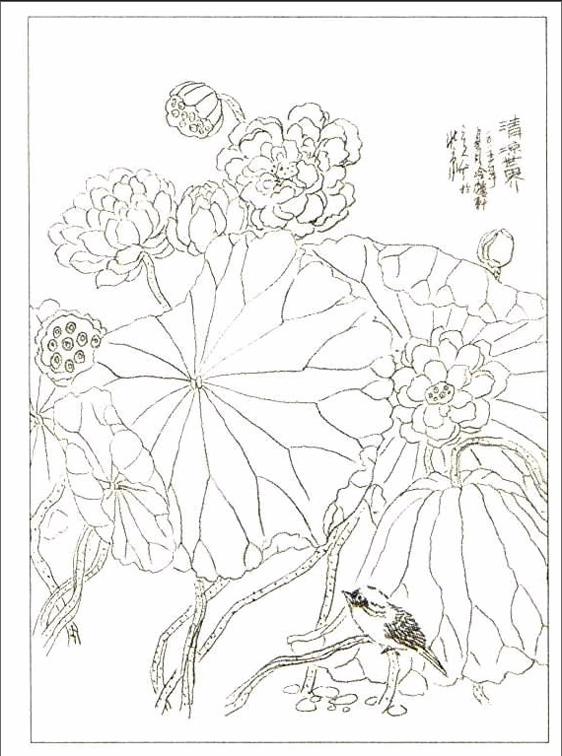
那天的太阳有点懒,没睡够似的,有气无力地挂在天边,遥遥地乜斜着她。她坐在女儿休休为她放在院子里的那把摇椅上,看着挂在天边的太阳,痴痴地想,许多年前的太阳,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一点儿也没错,许多年前的太阳就是这个样子——要不是太阳这么懒,路上的积雪不会那么厚,他们的路走得也就不会那么艰难了。
好多年后她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长途跋涉是在长征。
对于她来说,长征是一段快乐的日子。书上却说长征很苦,他们爬了雪山又过草地,有的人还过了三次草地,饿得实在没东西可吃了,就吃草根、树皮,草根、树皮也没有了,就吃皮带,实在没东西吃了,许多人饿死在草地上。草根、树皮、皮带她都吃过,还在草地上饿昏过好几次,可她一点都不觉得苦。她问强哥,我们那个时候苦吗?强哥摇了摇头,笑着说,苦什么苦?那个时候我们多快乐!
也许是他们只愿意记住快乐的事情,也许是有了强哥,有了强哥的歌声,她才没觉得长征有多么长。
强哥的歌声悠扬,在人头顶上飘。有一次,她都快要饿昏过去了,听见强哥的歌声,她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前走。
她一直以为,强哥的歌声带着她走完了长征路。
带她走完长征路的,除了强哥的歌声,还有一条红围巾,鲜艳艳的红围巾。红围巾的主人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文姝,文姝名字好听,人也漂亮。别人的脸上都冻出一道一道的血口子,她的脸却还足那么白,那么细,就像她刚刚见到她时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长征呢!
听说文姝是财主家的女儿,是上海来的大学生。
每次行军,文姝都走在她前面,长长的围巾随意地披在脖子里,远远看上一眼都让人感到暖和。山上风大,文姝的红围巾像鲜红的旗帜在风中飘。她深一脚,浅一脚,跟着招展的旗帜往前走,把厚厚的积雪踩得噗噗响。
休息时,她便挤到文姝身边,伸出冻得红肿的于,在红围巾上轻轻抚摩,红围巾摸起来柔柔的,软软的、把她的心血撩拨得痒痒的、酥酥的。
要是我也有这么一条围巾就好了、她想。
文姝娟姐好像看出了她的心思,把围巾摘下来围到她脖子里,笑着对人家说,你们快看,小碗围上这条围巾多漂亮!像不像个小新娘子?
那时她叫小碗——她还有一个名字叫诗伊、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他说小碗不好听,便给她取了这么个怪怪的名字。小碗是妈妈给她取的名字——生她的时候,她妈妈让爸爸给接生婆做了一碗荷包蛋,但接生婆没把那碗接住,碗摔在了地上。妈妈说、这孩子就叫小碗吧!
听文姝姐姐说她像个小新娘子,小碗的脸立即红了,赶紧把红围巾从脖子上摘下来,文姝姐姐又给她围上,手在她稀疏的头发上摩挲着说,你围上这条红围巾可真漂亮,这条围巾就送给你了。
小碗看看围巾,又看看文姝姐姐,文姝姐姐的目光正落在那条围巾上,从文妹姐姐的目光里她看到了不舍。她把围巾摘下来,戴回到文姝姐姐脖子早说:不,还是你戴着它吧、行军的时候我看到你的红围巾,就不会掉队了。
文姝姐姐将她紧紧搂到怀里,从文姝姐姐怀里抬起的瞬间,她发现有泪花在她眼睛里闪,接着便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都喘不上气来了。小碗的拳头使劲在文姝姐姐背上捶着,连声问:文姝姐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文姝姐姐含着眼泪摇了摇头说,没什么,没什么。过了很长时问,文姝姐姐轻声对她说:小碗、要是我死了,这条红围巾就归你了。
小碗趴在文姝姐姐膝盖卜快要睡着了、听她这么说,她惊恐地抬起头来,你说什么呢、文姝姐姐?围巾你戴着才漂亮,我不要红围巾、包不要你死!
文姝姐姐第二天就死了。
那天的太阳也像今天这样,懒懒地挂在天边。她恨死了那太阳,要是太阳不是那么懒、要是它再多发出一点热量,也许文姝姐姐就不会死。都快中午了,文姝姐姐的红围巾‘直在她眼前飘,她的脚步都有力了许多。可不知为什么,围巾飘着飘着就抖落到地上,等她赶过来,文姝姐姐已经死了。
文妹姐姐的睫毛湿湿的,苍白的脸颊上挂着泪珠,她想,义姝姐姐死前一定咳嗽了好长一阵、说不定她就是咳嗽憋死的。她已经咳嗽了很长一段时问了。每次咳嗽,都像是要憋得背过气去。
好多年后她才明白,文妹姐姐是患了慢性支气管炎,山上的空气人稀薄,她是喘不上气来才憋死的。
小腕哭了,她跪在文姝姐姐面前,用她胸前的柔柔软软的红围巾擦拭她脸上的泪水。小碗不忍心要文姝姐姐的红围巾,她要看着她暖暖和和地走。她用红围巾将文姝姐姐的脖了严严实实地围起来。她相信,不管多么大的风电吹不透文姝姐姐的脖子了,她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她,强哥,还有好几个红军战上用手扒开积雪,将文姝姐姐埋起来。
没有了文姝姐姐像旗帜一样在风中招展的红围巾,小碗的脚步也落寞了许多。要不是强哥一步也不放松地拉着她的手、她或许也和文姝姐姐一样倒在雪山上了。
小碗、你高兴些,爬过这座雪山就好了。
小碗不说话。
我知道,你一定足想文姝姐姐了吧?也许还有文妹姐姐的红围巾了吧?
小碗还是小说话。
强哥便说,小碗,你别难过,等革命胜利了,我给你买一条红围巾,和文姝姐姐的那条一模一样的红围巾。
小碗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他,真的,你说话算数?
当然,强哥笑着说,革命胜利了,我还要你当我的新娘子,给新娘了买条红围巾算什么?
小碗生气了,放在强哥手中的手使劲往外抽着,强哥却紧紧地抓住她,丝毫也没有将她放开的意思。她停下脚步,狠狠地瞪着强哥。
强哥说,对不起,小碗,我以后不再乱说话了还不行吗?
小碗不说话,手却不再往外抽了。
强哥说,小碗,我们唱歌吧,你不是最喜欢唱歌了吗?
小碗点』,点头,他们便唱起来。他们唱的是《国际歌》,唱着唱着,整支队伍都和他们一起唱起来。
小碗唱着唱着又流起了眼泪。这首歌还是文姝姐姐教她唱的,文姝姐姐告诉她,我们参加红军,不是为了报个人的私仇,也不是为了吃饱饭,我们是为了天下受苦人而革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文姝姐姐的话她并不完全明白,她却从文姝姐姐那里知道了什么叫革命。
破旧的木门“吱呀”响了一声,休休回来了。
她回过头去,瞥了休休一眼,仿佛责怿休休把她的思绪打断了似的。坐在摇椅上摇啊摇的,摇椅也和门一样,发出古老的“吱呀”声。
妈妈,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又到外面来了?休休埋怨着。
她不理休休、仍旧在摇椅上摇着。
妈妈,快回屋里去!
休休又说话了,她觉得休休今天有些哕唆。
妈妈,你快回屋里去,我有话要给你说!
休休的话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她从来都不这么对她说话。她看了休休一眼,休休的脸像是止被什么严肃而神秘的事情笼罩着。她从来没有看见休休这样过。
她还没说话,休休便将手伸给她,她也把手伸给休休,让休休把她拉回到屋子里。
休休扶她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说:妈妈,我有话要给你说,你千万别激动!
你还没说呢、我激动个什么?
她看着休休,觉得她今天真是怪异。
休休看了她一眼说:他死了
谁?
她的身体突然抖动了一下,但很快就遏止了自己。
就是……休休低下头说,就是那个人……
她缄默了,她知道那个人是谁,休休也知道那个人是谁这是她们家的规矩,提到那个人时从来不说他在这个家里该有的称谓,只是说那个人。
实际上,她们很少提到那个人、谁也不愿意提到他。
她面无表情,两只黑洞洞的眼睛盯着墙壁,仿佛能将墙壁穿透,望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但很远很远的地方又有什么呢?休休从她母亲的目光里看到的是一片空蒙。休休突然觉得那空蒙有些恐怖。
妈妈,你别这样,休休说,你要哭就哭吧,都这么多年了,别憋存心里!
准说我要哭了?她支撑着站起米,歇斯底里地对休休嚷,你要我哭什么?你说我该怎么样?
她说话的时候,像一头暴怒的母狮,休休低下头去,沉默了。
你出去,出去!别在眼跟前烦我!她仍旧对休休吼着。
休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听到厨房里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响声,她知道休休在准备她们母女的午饭了。
仿佛天空突然坍塌下来,沉甸甸地压在心上,把她压得都喘不过气米了。许多年前,她电有过这么一次,那时休休还没有出生,他在她面前哭着,她觉得是他的眼泪把她头顶的那片天空冲垮的。
她恨他,更恨她会在此刻想起那天的情景。
休休忙碌着,空气中弥漫着麻辣辣的气味,那气味直冲她肺腑,她觉得自己就要在那气味中窒息了。
她定了定神,摸起床头的拐杖同到院子里,麻辣辣的气味淡了许多,她重新坐回到摇椅上,摇啊摇……
太阳依旧慵懒,但她这会儿却觉得,太阳像极了那个人的眼睛。
几十年了,那个人的眼睛就像一个可怕的梦魇、总足小期而至地飘到她面前。今天,它又来了,在她最不愿意想它的时侯。
要不是那天她太累,也太饿了,或许她的生活中就不会有那双眼睛,她的一切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她觉得自己累得快要死了,强哥在唱歌,她却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歌声缥缥缈缈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米。四周是一片白皑皑的雪地、白得望不到边,她的眼睛都快要被那…望无际的白色刺得睁不开了。就在这个时候,她眼前亮了一下,有什么东西一闪,随即她便看到一束在洁白的雪地上战栗着的小粉红花。小粉红花就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她惊呼一声,挣脱开强哥的于,向小粉红花扑过去。
她重重地摔在一块大石头上,要不是那块石头阻挡,她就滑下万丈悬崖了。
哪里还有小粉红花,只剩下强哥那张暴怒的脸。
不想活了早点说!不想活你跑到雪山上受什么罪?早就该把你扔到山底下喂狼,把你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也好!还有脸哭?再哭,我不管你了!
她哪里敢哭,只是用泪汪汪的眼睛看着强哥、强忍着,不让泪花花掉出来。
小伙子,什么事情发这么人火?
声音在她身后响起,温温的,认人听了心里发暖。她回过头,看到了那双眼睛,他的眼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将满山的冰雪都融化了。
她的心被他的声音,还有他的眼睛烘烤得暖暖的,眼泪终于流下来。
首长,你不知道刚才有多险!她到处乱跑,要不是大石头挡住,她刚才就滚到万丈悬崖去了!
那人在她头上拍了拍,笑着说:小鬼,以后可要注意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不是故意的,她说,我是想采那边的小粉红花,可美了!
小粉红花在哪里?你告诉我小粉花在哪里?强哥仍旧对她吼。
她摇了摇头,小粉花确实没了踪影。
那人站在她面前,附下身去,笑眯眯地看着她问:小鬼,你一定是看到一朵小粉红才扑过去的、是吗?
她点了点头,泪水又流出来,要是强哥能像他这么和她说话就好了。
那人的脸严肃起来。幻觉,一定是幻觉,他说,小鬼,你一定有很长时间没吃东四了吧?
她点了点头。她已经三天三夜水米术沾了。
那人在灰布军装的衣袋里摸了半天,才摸出一块糖来递到她手中,说:小鬼,饿了就吃一块,这是一位朋友从苏联给我带来的,就剩下这一块了、我一直没舍得吃。
那人把糖递到她手中便拄着拐杖,踩着积雪一步步地往山上走去。
强哥凑上来看那块糖,糖纸上印着一个外国人的头像,包装很精致。她把包装精美的糖块送到鼻子边闻了闻,很香,也很甜,她又把糖放到强哥的鼻子下,强哥也不住地吸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