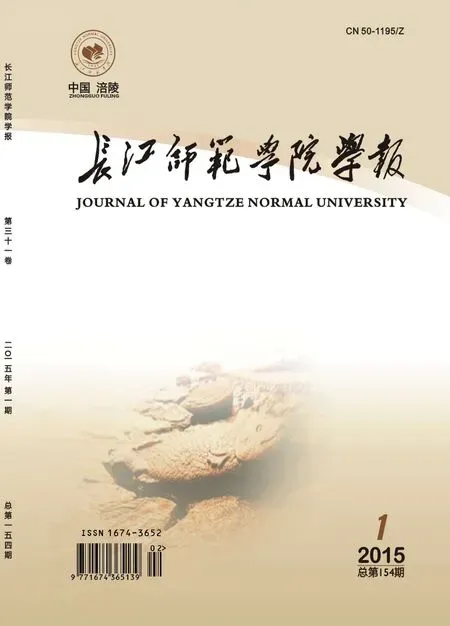论唐小说女侠形象塑造中的佛道文化渗透
论唐小说女侠形象塑造中的佛道文化渗透
方娟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在佛道二教走向融合的唐代,其教义无不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唐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是其中的一方面。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的塑造从女侠的练成、女侠的行动及女侠的最后归宿中都可得以一窥。佛道文化对唐小说的渗透,使得小说中女性走出闺阁,增添了女性形象的奇幻色彩,使女性形象在文化殿堂里更加多彩。
[关键词]唐小说;女侠形象;佛道文化;归宿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5)01-0079-04
[收稿日期]2014-11-28
[作者简介]方娟,女,湖北武汉人,主要从事先秦至隋文学研究。
一、引言
对“侠”的定义,莫衷一是。唐代对其释义,见于《史记集解序》中引司马贞“索隐”,云:“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游,从也,行也。侠,挟也,持也。言能相从游行挟持之事”[1] 3。又见《汉书·季布传》唐人颜师古注:“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2] 1975-1976。而今人所看唐小说中的女侠形象,似乎与这有不相符之处,因为二者的注释多站在“仁义”之角度,将目光更多地投射为“仁义”而舍生取义之人。唐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在这样的标准下自然不能称是。再看今人的释义,“所谓侠并不是单纯的社会身份或社会行为。我们认为侠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关系态度。其一,对人,顾朋友私义不顾朝廷公义,‘弃官宠交’,在野不在朝。其二,对物,轻财而重义,不为物所役,但在具体行为中常持义利统一观。其三,侠义道德讲究意气交合,‘同是非’,‘相与信’,以然诺诚信、趋人之急为务。其四,侠的欲望中心是‘立强于世’,有比一般人较强烈的自由意志和支配欲望”[3]。这样的定义更显恰当。唐代小说中的女侠,常常表现为有自己的目标,讲义气,不岌岌于物质,功成之后,淡然隐之。
“唐代的整个思想、学术界是在佛、道二教的笼罩之下的;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二教也从没有像唐代那样在知识阶层中广泛地普及过。就文学领域而言,几乎每一位作家都和佛、道二教发生一定的关系,受到它们的或深或浅的熏染,并在其创作中有所表现”[4] 512-513。在佛道文化交融的唐代,在唐代文人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女侠”形象又表现出特有的特点。
目前学界对唐小说中以女侠为题材的作品的界定,大致有13篇,分别为《聂隐娘》《湘媪》(《樊夫人》)、《红线》《贾人妻》《谢小娥传》《潘将军》《张季弘逢恶新妇传》《车中女子》《崔慎思》《荆十三娘》《马燧》《虬髯客传》《蜀人妇传》等[5]。对唐代女侠的研究主要有女侠形象的分类,如复仇形象、仗义形象、报恩形象、情侠形象等,以学者侯忠义[6]、程毅中[7]等为代表;有对女侠形象的具体阐释,其中包括女侠的产生、女侠的个性特点、女侠小说对后世的影响等,研究代表为胡丽的《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研究》[8]、杨萍的《从唐人女侠传奇到21世纪女性武侠》[5]等;也有对女侠的文化意蕴进行探析,如王立的《重读剑仙聂隐娘》[9]、韩达的《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10]、乔孝冬的《唐代女侠兴盛的文化阐释》[11]中所谈到的宗教文化等。儒道释在唐代社会呈现出高度的融汇,若单独说唐小说中的女侠形象的塑造受到佛教或道教的影响有失偏颇。在整个唐代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佛、道的普及,从上层社会的热衷直至走向民间,呈现的是世俗化、大众化的趋势。在这种普及的趋势下,供人消遣的小说不可能独树一帜。这里拟从唐小说中女侠的练成、女侠的行动及女侠的归宿等方面来探析
佛道文化在其中的渗透。
二、“侠”的练成
在唐小说中女性形象披上“侠”的色彩,其原因有唐代社会在思想上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佛道二教在唐代的盛行之风“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论难空有”[12] 7759。作为士族阶级的知识分子自然也在其中。女性形象身上的这种“侠”的底色对现实中深处闺门的女子而言,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在佛道文化的影响下,这类女性的出现,可以看作是自然之举。在具体作品中表现在女性身份及女性走出闺门、拜师学艺。
在《甘泽谣·红线》中红线作为薛嵩的女婢,在帮助他完成任务后,在向薛嵩吐露自己的身份时说:“某前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而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其三人。阴力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稟凡俚。”“轮回报应”说见于佛教经典,如佛教十二因缘说。慧远《三报论》说:“经世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13] 87。道教也说报应轮回。“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14] 741-743佛道二教文化在唐朝为之大盛,与其说这一契机给了士人宣传自己思想主张以托词,不如说是给唐代思想的经脉里注入了新的血液,这种血液也给了小说中的女性以新的形象。主人公在《红线》中“善谈阮咸,又通经史”,遣“掌牋表”,其号曰“内记室”,这些似乎只有男性才能胜任的角色,如果开始时有人抱着疑问的态度,那么,结尾处再回首,红线自述自己是男性转世之时,不仅为小说画上了句号,读者的疑问也就终于明了。佛道文化赋予这样的女性以男性的能力存在于世,惊人的本领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也不再“惊人”。
《聂隐娘》中的女性聂隐娘,本是“魏博大将聂锋之女”,这样的女性注定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却在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女尼,女尼向聂隐娘之父乞之,不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女尼盗之,使得聂隐娘最终走出深闺。女尼在唐代很普遍,“及安禄山反,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自两京陷落,民物耗蔽,天下肃然……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15] 1347跟着女尼出走的聂隐娘看似走上了学术之途,但是真正远离父母的她,接触到的则是“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的同门以及“初但读经念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匕首藏于脑中无所伤”“丹药化人、用丹药保人”等的神秘术。这样的聂隐娘“武技及其相关的飞行术……等,已经达到了超凡绝伦的地步,远非人间的侠与剑客可望其项背的了”[16] 329。既然人类无法实现,那么在宗教中寻找机缘也就盛行。在道家学术及佛家经典中飞檐走壁、轻功、神秘法术、剑术是需要修行的。聂隐娘用丹药,因仙丹是成仙飞天的必要,其说“若道术不可学得,则变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17] 46出神入化的神功在被道教奉为起源的道家,可得以上探于天,下揆于地,可与鹏鸟比肩,可与蝴蝶同化的“逍遥游”。剑术是道教的法宝,信奉者对铸剑非常痴迷,如陶弘景作《古今刀剑录》、许逊作《灵剑子》、吕洞兵作《述剑集》等。《庄子·说剑》载:“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下“作神剑法品”载:“凡是道学,当知作大剑法”,剑术也一直成为道教修炼之必备。同样,佛教经典《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王经》记载:“持明者,用华铁作剑”“行人得持明天,剑有烟焰,得隐身法。”[18]204聂隐娘的本领是在女尼的引导之下,揉杂佛道的本领。如此之类的“女侠”的练成还有谢小娥、湘媪等。
三、“女侠”的行动
女侠的形象在唐前有越女(春秋时女剑术家)为先导。唐代社会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使得这一形象的行动有合理的解释。而佛道文化在其中的影响便是让这类形象更为彰显。
唐小说中的“女侠”行为大都不是为了某种使命,而是被某种情感所驱使。如崔慎思之妾、贾人妻、谢小娥等是为了复仇。车中女子、聂隐娘、红线女、三鬟女子等是为了报恩。
在这样或复仇或感恩的情感驱动下,“女侠”的行动表现出非人的色彩。其一是,小说中的女性都有“飞人”的技能。《源化记·车中女子》中的“女人纵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剧谈录·潘将军》中的偷珠人“语讫而走,疾若飞鸟”;《集异记·贾人妻》中的女子“遂契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崔慎思》中的妾“逾
墙越舍”;《聂隐娘》中的聂隐娘“能于峭上飞走”等。其二是,这些女子大多有隐身的本领。红线在众目睽睽之下盗取金盒,“遁迹尘中”;《潘将军》中的女子盗取珠子游戏等。其三是,女性常用刀。《崔慎思》中的女侠“以白练缠身,其右手侍匕首”;《聂隐娘》中女侠将匕首藏于脑中;《红线》中红线的装扮“胸前佩龙文(纹)匕首”;《谢小娥》中的主角使用佩刀。这些“刀”正是她们行动的辅助工具。女侠称之为“侠”是因为她们在各自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诸如以上的本领和技巧。而这些技能很不常见,在今人看来都是虚诞,更何况于古人。但佛道文化给了这些行动以合理的解释。
佛家认可因果报应,认为“世界万物无一不由因缘合和而生,而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历然”[19] 155。因此,“复仇”“报恩”成为女侠行动的初因不足为怪。道家的飞行术、隐身术,在女侠的行动中我们不难看到(藏身、变为其他的东西等),这样的“女侠”同于佛道中的仙人的百般变化,如佛教中的关于观音的三十二应化身说等;道教说的“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而男女易形,为鹤为石,为虎为猿,为沙为鼋,又不少焉。至于高山为渊,深谷为陵,此亦大物之变化”(《抱朴子·黄白》)等为其特异功能作为诠译。女侠的行动与佛道的契合,借助佛道文化中不同于人类的灵验,加之于女侠之身,给“女侠”形象涂上了“仙人”的色彩。
四、“女侠”的归宿
女侠行动完成后的最终去向,如果只是嫁作人妻,过着平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只会将“女侠”的“侠”性消解在这些过于平常的事物上。而小说中“女侠”的非平常的归宿,也无疑是受到了佛道文化的影响。
“女侠”在完成自己行动后多“抛夫杀子”或与恩人相别。《崔慎思》《贾人妻》中的女子委身为妾室,在完成自己复仇的计划后,杀掉自己的孩子,离自己的丈夫而去。《聂隐娘》《红线》中的“女侠”完成自己的使命也是不辞而别。这些女侠最终的别离似乎没有任何的牵挂,跟世间的一切都没有“情”。佛道在其教义中宣传“修炼”的前提是去情去欲。佛家云:“学道人只怕一念有,即与道隔矣。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佛。学道人若欲成佛,一切佛法不用学,惟学无求无著,无求则心不生,无著则心不染,不生不染即是佛。”唐代诗人也曾叹“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没有“有”,“无求无著”即可成佛,佛家讲“缘”,诸多伤心事的“缘”自是情多。道家说不能成仙的原因是“爱习之情卒难遣,而绝俗之志未易果也”[17] 19。因为情欲在其中有这些妨碍,多为佛道果断弃之。“无情”成就了唐小说女侠形象的不食烟火!
做出了“情”的选择,在这类小说的结尾最为常见的是女侠的“不知去向”的归宿。其与人事的牵扯在小说的末尾多以“归隐”为最终归宿。粗略统计如表1。

表1 唐小说中“女侠”的归宿
小说中女侠大都选择“隐逸”作为自己的归宿。正史中对“隐逸”有记载,其云隐逸者是徘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隐逸者的身份大多与德才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以此来评价唐小说中的女侠,那么无一位符合男权社会中“隐逸”者的形象。女侠的不知所终的“隐”,这里可以理解为完成自身使命后的身退。佛教因果报应论认为,人是生死无常的、不自由的、痛苦的,而痛苦的根源是人类的无明和贪爱,在于人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万物纷纭,唯人最灵。”如悉达多·乔达摩抛弃王子的身份,最终成佛。世人抛却凡世间的名利欲望,自会自在。道教宣扬最多的是不死之术,它使人类达到永生的彼岸,因而道教神仙经常“遨游于世俗之外,寡情浅欲,不为尘世干扰”[20]。这些女侠的适时“隐”退,全身而退,是与世俗的告别,在消灾避祸的同时,又保持自身心性的自我追求,而这
些都是与佛道教义相吻合的。
五、佛道文化对唐小说女侠形象塑造的意义
(一)佛道文化的影响使女侠得以出现
佛教教义宣扬“众生平等”,在道教仙牌中有供奉女仙的状况,这些符合于唐代开放的社会现实,在民族高度融合的时代,佛道二教在社会上被广泛地接受,“从皇帝大臣以至市氓村妇,无所不深为所感。”[7] 350佛道文化的影响,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其侠义行动中,时常体现出“男性化”的色彩。
(二)佛道文化的影响使女侠形象的奇幻色彩增浓
唐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在佛道文化的影响下,其自长成之初,学习的多种技能已开始迥异于他人;到女侠初出江湖,快意恩仇的果敢行动,也显现出高出世俗的姿态;而女侠在江湖任逍遥后的退隐,是世人为其选择的最佳去处。女侠虽是女性,但是女侠注定是不平凡的人类,其行为充满着佛道中的奇幻色彩。
(三)丰富文学想象的殿堂,女性形象的多姿多彩化
唐代女侠小说的创作开创了我国武侠小说创作的新篇章,“从武侠小说发展史看,它是魏晋六朝武侠小说的集大成,也是唐代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全方位展示。它在唐代的创作及其繁荣,标志着我国武侠小说艺术的初步形成。唐人在表现内容、艺术技巧方面的独创,奠定了我国武侠小说发展的基础。”[21] 271在这样的风气的影响下,唐代小说在形象塑造的同时,脱于前代人的窠臼也在情理之中,佛道文化的渗透也给了唐代女侠形象超越前代的可能。佛道的教义宣讲、佛道的异域色彩、佛道的非人化特点、佛道的出入世的追求等使女性形象更为多彩。
佛道高度融合发展的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的塑造是其映射。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得以更加鲜明,特点更加突出。唐以后的女侠形象,如张训妻的超人法术、韦十一娘的剑侠之路、庚娘的复仇情深,是一脉相承的女侠形象,让女性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时代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韩云波.侠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模式[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91-96.
[4]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杨萍.从唐人女侠传奇到21世纪女性武侠[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7-41.
[6]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7]程毅中.唐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8]胡丽.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8.
[9]王立.重读剑仙聂隐娘——互文性、道教与通俗小说题材母题[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3):31-34.
[10]韩达.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61-65.
[11]乔孝冬.唐代女侠兴盛的文化阐释[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81-86.
[12]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3]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于平.道家十三经[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15]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王立.侠文学主题史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清]沈曾植.海日楼札丛[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9]方立天.佛教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20]罗立群.道教文化与明清剑侠小说[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85-93。
[21]汪聚应.唐代侠风与文学[D].陕西师范大学,2002.
[责任编辑:庆来]
□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