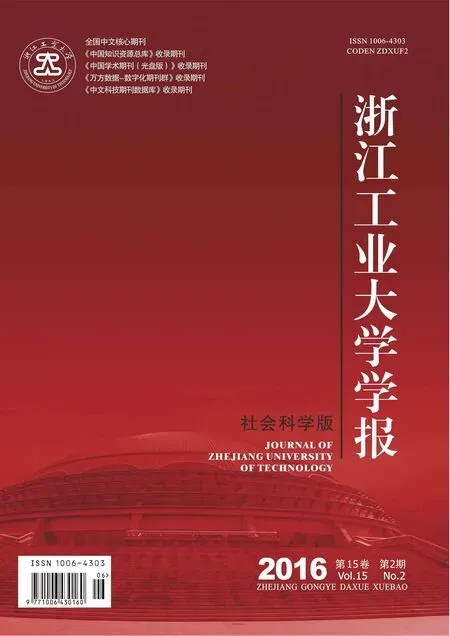睁眼看世界:中国比较文学的觉醒
王福和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睁眼看世界:中国比较文学的觉醒
王福和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鸦片战争的爆发,引爆了中西文化碰撞的导火索,把中国拖上近代历史的轨道。在冲进国门的西方文化面前,我们的民族不得不进行思考,我们的文化不得不作出抉择。于是,一批醒来的新人开始审视外面的世界,用不同于传统的思维撰写介绍域外风情的著作,用比较的视角剖析域外和中国的现实,既开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先河,也预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觉醒。
关键词:中国;比较文学;觉醒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基督教文化的肆虐,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古老神话,消解了中华帝国的天朝神威。不但引爆了中西文化碰撞的导火索,也把中国拖上了近代历史的轨道。面对凶悍的西方列强和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一批新人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惊醒、成长。他们在西方入侵所带来的白银外流和经济枯竭的情况下,在通商的社会背景中接触西学,走上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的人生道路。他们是醒来的中国人,是中国首次以比较视野从世界范围反观中国文化的一代新人。
一、睁眼看世界的先驱
魏源(1794—1857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率先放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先进人物之一”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驱”①李巨澜:《魏源与〈海国图志〉》,魏源著《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3页。。他一生著述颇丰,留有《书古微》、《诗古微》、《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圣武记》、《元史新编》和《海国图志》等诗文和著作。
《海国图志》受另一位“睁眼看世界”的先驱林则徐的嘱托而作。魏源曰:“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②(清)魏源:《〈海国图志〉原叙》, 魏源著《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于1842年完成。初刊50卷,57万字。日后10年间两次增补,1847年再刊60卷,60余万字;1852年又刊时达100卷,88万余字。“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②。随着两次增补,《海国图志》的内容不断丰富,影响逐年扩大,进而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亚洲的最完备的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的巨著①”和当时中国“最丰富完备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1],对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魏源认为,他的《海国图志》与昔人所作海图之书的差异,在于“彼皆以中士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而他作《海国图志》的宗旨则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因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共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①。鸦片战争的失败,除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外,闭关自守、对外面世界的一无所知以及夜郎自大的闭塞心理同样是不可无视的原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沉痛的反思,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口号”。因为只有了解西方,方能看到西方之优,我方之劣。只有看到我方之劣,方能懂得如何学习西方之优,强我中华。这种比较中看优劣,比较中求发展的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①李巨澜:《魏源与〈海国图志〉》,魏源著《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当时,不知道有多少麻木不仁之士, 在《海国图志》的启迪下, 睁开了沉睡之眼看世界。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上看,《海国图志》的价值在于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关注。在《大西洋各国总沿革》中,魏源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其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至十七八岁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学成,而本学之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在对欧洲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进行论述后,魏源得出结论:“五洲之内皆有文学,其技艺至备至精者,惟欧罗巴一州也。其外各州亦皆有之,但未能造至其极。”魏源认为,一个“古为卤莽之州”的欧罗巴,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文学成就,就在于“其地因近于厄日度,又连于亚细亚,故额力西国始得离暗就明,弃鄙归雅。且其民人才能敏慧,文艺、理学、政治、彝伦,靡弗攻修,以臻其至”②(清)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327页。。关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魏源通过比较后指出,英语“其语音与汉语大不相同,其音长,切字多,正字少,只二十六个字母,是以读书容易,数日间即可学之。故此学者无不通习文艺,如国史、天文、地理、算法,不晓者则不齿于人”②(清)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327页。。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能有这样宽广的世界视野和比较的意识,弥足珍贵。
徐继畬(1795—1873),清末高官,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近代中国‘发现’世界和西方的第一人”③王振峰:《近代中国发现世界的第一人——徐继畬再论》,《城市研究》,1994年第2期第52页。,在地理学、文学、历史和书法等方面多有成就。其《瀛寰志略》是“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历史的拓荒之作”④殷俊玲:《徐继畬和他的〈瀛寰志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启蒙作品,是“近代国人自著的开创性世界史地专书”⑤吴家勋:《近代睁眼看世又一人——论徐继畬与其〈瀛环志略〉》,《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第40页。,其地位和影响可以与魏源的《海国图志》相比肩。
《瀛寰志略》(1848)是徐继畬在遍访外国友人、传教士、领事,大量阅读外国地理和基督教书籍,广泛搜集外国历史资料以及中国文献,在经过缜密的考证、研究和整理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名著。为了完成此书,他广种博收,采多家之长,“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事实则多有可据,……亦有唔泰西人时得之口述者”[2]。在撰写过程中,他“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五阅寒暑,未尝一日辍也。……久之积成卷帙”[3]。作者站在世界高度,用寰宇视野,全画幅地介绍了亚洲、大洋洲、欧洲和美洲各个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政治、经济以及当时的社会现状,用当时国内外地理学上的最新成果和独特视角,为中华大地开启了一扇天窗,“使长期处于封闭、混沌状态中的中国人,通过这扇天窗开始把目光投向全世界”④。
开阔的全球视野,是《瀛寰志略》带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宝贵启示。徐继畬指出:“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里。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地球从东西直剖之,北极在上,南极在下,赤道横绕地球之中,日驭之所正照也”,而“中国在赤道之北,即最南滨海之闽、广,尚在北黄道限内外”[4]。这些在今人看来最起码的地理常识,当时却极具颠覆意义。他使人们明白,“古之言地球者,海外更有九州,今以图考,则不止九州”。他还使人们明白,“‘九州,天下八十一州之一’。今以图考,则无八十一州”[5]。换言之,世界之大,国人并不知;天地之广,国人也不知。而中国亦并非地球的中心,只是亚细亚之一大国也。这种立足全球,鸟瞰中国的视野,这种站得高,看得远的情怀,无论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还是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均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自觉的“比较”意识,是《瀛寰志略》带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又一宝贵启示。在论述欧罗巴的历史时,徐继畬多以中国历史为坐标比较之:
其地自夏以前,土人游猎为生,食肉寝皮,如北方蒙古之俗。有夏中叶,希腊各国初被东方之化,耕田造器,百务乃兴。汉初,意大里亚之罗马国,创业垂统,疆土四辟,成泰西一统之势,汉史所谓太秦国也。前五代之末,罗马衰乱,欧罗巴遂散为战国。唐、宋之间,西域回部方强,时侵扰欧罗巴诸国,苍黄自救,奔命不暇。先是,火炮之法创于中国,欧罗巴人不习也,元末有日耳曼人苏尔的斯始仿为之,犹未得运用之法。明洪武年间,元驸马帖木儿王撒马儿罕威行西域,欧罗巴人有投部下为兵弁者,携火药炮位以归,诸国讲求练习,尽得其秒,又变通其法,创为鸟枪,用以攻敌,百战百胜,以巨舰涉海巡行,西辟亚墨利加全土,东得印度、南洋诸岛国,声势遂从横于四海[6]。
这样的横向“比较”,在《瀛寰志略》中多有出现。它使读者透过中国的历史年代,在“比较”的坐标上对外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令人耳目一新。
自觉的“比较”意识,在对外国历史人物的介绍中也多有表现。论及美国时,徐继畬除了指出其“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外,还发出了“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①(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291、277、182页。的感叹: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①。
《瀛寰志略》中,徐继畬在介绍各国的历史地理时,也不时对所介绍国家的文学沿革和国事兴衰抒发自己的所感所思。论及希腊时指出“欧罗巴之开淳闷、通文学,实自希腊始”②(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卷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因为“雅典最讲文学,肄习之精,为泰西之邹鲁,凡西国文士,未游学于额里士,则以为未登大雅之堂也”①。论及瑞典时写道:“瑞国处穷发之北,在欧罗巴诸国中最为贫瘠,而能发奋自保,不为强邻所并兼。‘安乐者祸之萌,忧患者福之基’,虽荒裔亦如是也”②。论及丹麦时,作者认为该国在欧罗巴“壤地甚褊,未堪与诸大国比权量力也。而加的牙一港,扼波罗的海数千里之喉,……遂翘然为一方之杰。国之强弱,岂尽在乎疆土之广袤哉”②。
二、比较视域中的思考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清末外交官,清政府派往西欧的第一任公使,近代洋务思想家,“近代中国较早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先进士大夫”[7]和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他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养知书屋遗集》、《史记札记》、《礼记质疑》、《中庸质疑》、《使西纪程》、《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等,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过较大影响。
《使西纪程》是郭嵩焘出使英国途中撰写的从上海到伦敦共50天的日记。在日记中,郭嵩焘不但记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天文地理、风土人情,而且对所见之事,所闻之情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在比较的视野中,既肯定了西方文明的长处,也指出了中国社会的诟病,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郭嵩焘的直言快语和肺腑之言,饱受迂腐顽固派的诋毁,《使西纪程》也屡遭厄运。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困苦与艰辛。
从比较的角度上看,郭嵩焘对沿途的其景、其情、其事的描写和议论,都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展开的。在香港,他考察了当地的学馆后,感觉那里的学校“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相比之下,“中国师儒之失教,有愧多矣,为之慨然”[8]。在行进途中,他与随行人员谈及英国与荷兰在殖民地的赋税时,指出荷兰“专事苛敛,以济国用”,而英国则“地租税课取之其地,即于其地用之”。因此,“苏门答腊各小国,乐以其地献之英人,而不愿附属荷兰,亦以此故”①。行至赤道,论及宗教在世界各地的流传,郭嵩焘指出:“西洋主教,或君民共守之,或君民异教,各有所崇尚。”相比之下,“独中国圣人之教,广大精微,不立疆域;是以佛教、天主教、回教流行中国,礼信奉行,皆所不禁”[8]。行至埃及,论及不同民族的文字特征时,郭嵩焘指出:“文字之始,不越象形、会意。麦西始制之文字,与中国正同。中国正文行而六书之意隐。西洋二十六字母立,但知有谐声,而象形、会意之学亡矣”[8]。
除了以“比较”的思维对所见所闻进行评述外,郭嵩焘还在《使西纪程》强烈地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赞誉。如:“西洋以行商为治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肃,条理秩然。即在中国往来(内江),船主皆能举其职,而权亦重。所以能致富强,非无本也”[8]。再如:“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倐盛倐衰,情形绝异”[8]。又如:“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8]。言外之意,所表露的还是对当时中国社会落后现状的“比较”中的反思。
郑观应(1842——1921),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较早形成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较早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思想家,在实业、教育、文学和慈善等领域均有建树,著有《易言》和《盛世危言》等著作。
《盛世危言》(1894)是一部集中反映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著作,内容广泛涉及“哲学”、“教育”、“西学”、“藏书”、“政体”、“吏治”、“宗教”、“刑法”、“税负”、“财政”和“商务”等领域,“全面而系统地谈及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主张,是一部当时中国变法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和“维新变法大典”①苏全有:《〈盛世危言〉述略》,《兰台世界》,2008年第4期第52页。,在“中国的启蒙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地位,起到使国人由改良进到维新再到变革的中介作用”②陈志良:《〈盛世危言〉·编序》,(清)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时任清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称此书“皆时务切要之言”,感觉书中“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③(清)彭玉麟:《〈盛世危言〉·彭序》,(清)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早期改良主义者陈炽称此书“综贯中西,权量古今,……淹雅翔实,先得我心。世有此书,而余亦可以无作矣”④(清)陈炽:《〈盛世危言〉·陈序》,(清)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而郑观应则自谦“尝读史盱衡千古,穷究得失盛衰之故。方其厝火未燃,履霜始至,未尝无人焉。识微于未著,见机于将蒙,不惮大声疾呼,痛哭流涕而言之”⑤(清)郑观应:《〈盛世危言〉·郑序》,(清)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盛世危言》的价值在于对“西学”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究其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而“西学之强”的根本就在于其“强于学”,而不是“强于人”。因此,中国要与西方一样强大,重要的不仅仅是“枪炮战舰”的强大,而是强大中国的文化。而现实是“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篱?”他指出,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要分清事情的本末,切不能本末倒置。对中国人而言,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应该“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9]。换言之,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必须要先知此,方能知彼。必须要脚踏民族文化的土壤放眼世界,方能准确洞世界之变幻,察本土之优劣。
从比较文学的意义而言,《盛世危言》的价值还在于对教养的关注。而一个人的教养就来自于教育,来自于人才的培养。这一点上,郑观应表现出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比较”的意识。他指出:“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不但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认为“读书则智,不读书则愚;智则强,愚则弱”,而且以德国、美国和阿州为例,指出德国和美国之所以迅速富强起来,是因为“德国之民读书者百之九十五,美国之民无不读书”,而“阿州之民未闻读书,宜其全州为各国所分裂也”。在强调教育和读书重要性的同时,作者例举中国现状加以“比较”,指出“降及春秋,群雄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暴秦崛兴,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10]。
三、走向世界的尝试
黄遵宪(1848—1905),清末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享有“诗界革新导师”的美誉,被看作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留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作品和著作。
黄遵宪的一生,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亲眼目睹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等起义浪潮。动荡的社会现实,出使国外的切身体验,强烈的现实反差,令他痛心疾首,忧患顿生。于是,便“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朝夕编辑,甫创稿本,……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箧,重事编篡,又几阅两载,而后成书。”这就是“凡为类十二,为卷四十[11]”的《日本国志》。正所谓“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12]。
《日本国志》是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完善”、“在当时的时代,堪称是质量最上乘的日本史著作”[12]。全书共40卷,12志,分别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共50多万字。“作者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中专门叙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裁,从各个角度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介绍和研究,称得上是一部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尤其可贵的是,“在介绍总结明治维新经验的同时,黄遵宪还史论结合,与中国的现状进行多角度对照比较,提出一系列先进的改革主张”[12]。
《日本国志》是一部忧患之作,忧患之一就是国门的紧闭,国人视野的狭隘。这不仅表现在“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更严重地表现在“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因此,他便以此书“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11],既要唤醒陶醉在夜郎自大中的士大夫,也要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培养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
《日本国志》对比较文学的启示表现在对中学与西学不同命运的思考上。他指出:“日本之习汉学萌于魏,盛于唐中,衰于宋元,复起于明季,迨乎近日几废”[13]。而与此同时,则是日本的“西学有蒸蒸日上之势”[13]。这一衰一荣,究其缘由,就在于“中土开国最先,数千年前,环四海而居者,类皆蛮夷、戎狄、鹑居、蛾伏、混沌、芒昧。而吾中土既圣智辈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无不备其时儒者,能通天地、人、农夫、戍卒,能知天文、工执、艺事,得与坐而论其道,居六职之一。西人之学术未有能出入吾书之范围者也,西人每谓中土泥古不变,吾独以为变古太骤,三代以还。一坏于秦人之焚书;再坏于魏晋之清谈;三坏于宋明之性命至诋,工艺之末为卑无足道,而古人之实学益荒矣”[13]。
睁眼看世界,是中国雄狮苏醒的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认知世界、了解世界、学习世界,尝试走向世界的开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们在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触及比较文学,但他们广阔的环球视野,站在世界高度反思中国文化的情怀,为民族强盛而学习西方的欲望,以及无处不在的“比较”意识等,几乎都与欧洲比较文学在“孕育”的时间上相差不远,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诞生具有不容忽视的启蒙意义和举足轻重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梁通.从魏源到黄遵宪[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70.
[2] (清)徐继畬. 瀛寰志略·凡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
[3] (清)徐继畬. 瀛寰志略·自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6.
[4] (清)徐继畬. 瀛寰志略·卷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
[5] (清)徐继畬: 瀛寰志略·序[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
[6] (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卷四[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06-107.
[7] 刘国军.郭嵩焘与〈使西纪程〉[J].求是,1996(6):120.
[8] (清)郭嵩焘. 使西纪程[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15,31,19,23,39.
[9] (清)郑观应. 盛世危言·西学[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0.
[10]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教养[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69.
[11] (清)黄遵宪.黄遵宪集·下卷[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83.
[12] (清)黄遵宪.黄遵宪集·上卷[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70,6.
[13] (清)黄遵宪.日本国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38-342.
(责任编辑:王惠芳)
Opening eyes to see the world:the awakening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ANG Fu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China)
Abstract:The outbreak of the Opium War detonated the fuse of colli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and China was dragged on the track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face of Western culture that rushed into the country, our nation has to think about it before making a choice. Therefore, a group of pioneers who woke up and started to look at the outside world, wrote to introduce foreign customs in the way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pattern, analyzed the foreign and China’s reality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us not only setting up a precedent of “opening eyes to see the world” for our countrymen, but also indicating the awakening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words:Chin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wakening
收稿日期:2015-07-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51047)
作者简介:王福和(1954—),男,山东寿光人,教授,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303(2016)02-014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