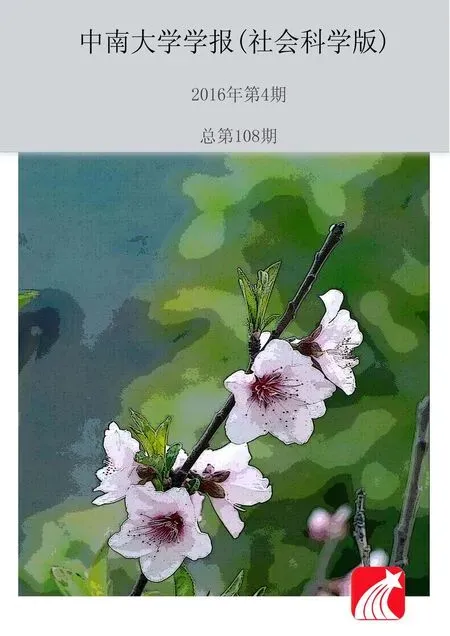论阎真创作的存在主义之维
晏杰雄,方佳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论阎真创作的存在主义之维
晏杰雄,方佳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阎真作品因反映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引起广泛关注,但少有人注意到其作品所蕴含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实际上,阎真创作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呈现;二是对“荒诞”的“孤独”存在的敞显;三是表达向死而在的存在之思。在对生活原生态刻写的基础上,作家对个体生存境遇的深描与对个体生存价值的追求,都彰显存在主义内涵,把其作品从人的生存推向人的存在。
阎真创作;生存境遇;存在之思;向死而在
在展示知识分子的内心博弈上,阎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他不仅把视线聚焦于揭示国内官场的黑暗,也把目光抛向了异域他乡的边缘化人物,除了对男性的个体发展的叙述之外,也展示了女性在婚姻和爱情中的地位,他对于艺术本位的执着追求,使他的作品拥有大批量的阅读群体。在已出版的四部长篇小说中,阎真一直站在人道的角度,把关切的目光放在了时代与社会,执着于挖掘在当下生活的人们的生存困境,尤其关注在生存困境当中喘着粗气挣扎的人,用细腻却又不失风趣的笔触向我们勾勒出个体无奈的生存状态,彰显出他的责任担当与普世情怀。就思想价值来说,阎真作品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所体现的普适人类性远超通俗文学。在阎真小说中,即便是那些看似寻常普通的故事情节中,也蕴涵着对个体生命价值和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潜隐着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根本性思考,既有强烈的当代意识,又有深厚的哲学意味。
存在主义出现之前,人们的生存方式就如同本质论中所设定的那般安逸恒定,不会对自身的生活时代、环境和生活需求做出过多的思考。但存在主义被提出之后,在认识到上帝已死之后,人们开始追寻生活的终极目的,力图找寻一种理想的世界,找到诗意的栖居地,在这种意义上,存在主义正是“代表着某种虔诚的努力”。[1]就这一点来说,阎真的小说处处浸透了存在主义哲学,无论是官场生态,还是学术场域,或者是异国他乡,抑或是两性婚姻,他都能深入到生命的本质,努力挖掘自由选择之后的深层含义,对复杂人性进行窥视,给生命意义以深邃的思考,并在思考中奋进,寻求真理,最终实现对人生价值与存在意义的深入探索。
一、呈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矛盾是人类在拥有空前富有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人性的异化日趋严重,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在使人类的创造性得以发挥的同时,却使人的尊严和自我坚守丧失,造成对物的依赖性,进入了一个迷惘困顿的生活环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作品普遍关注的是时代生活,大都揭露当下社会的不合理问题,但缺乏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叩问这一维度。阎真的小说在这一维度有较沉潜的探究,通过对都市文明的“恶之花”的透视来凸显生命异化的主题,展现荒诞畸形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以及现代人生存的焦虑和恐慌,从而探索现代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以及对生存空间与生活环境的拓展。
纵观阎真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中总是透着人生的无可奈何、现实的悲怆(《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均有体现),以及远飘异国他乡的孤独寂寞(《曾在天涯》中体现最明显)。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生存窘境,要么奋起反抗,与世界对峙到底,要么只能委屈求全,在命运面前忍气吞声。处于现实生存困境的他们,被命运推置于一个困顿且边缘化的境遇,对未来充满困惑与不解。阎真从始至终都是以一个负责任的文人视角去构建他所关注的生活世界,在那里涌现处于各种困境当中的人们,他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怀揣着人道主义的慈爱,关怀着芸芸众生。用悲慨沉郁的笔调去描绘人类生存困境——人们生活这堵大围墙之内挣扎的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勾心斗角、利益化的交往。
在展现生活的困境当中,阎真首先从情感的失落出发。阎真的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对情感这一人类最普适性因素的关注。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情感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的体验”[2]。情感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人基于客观事情上生成的主观印象与判断,是一种主观体验,因而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却又有普遍性的。人们以情感为内核驱动力,在情感的驱使下工作、学习和生活,但是并非每份情感都能让个体在体验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在情感低落沉重之时,个体难免会感到孤独。阎真的小说作品中,他时刻关注着不同时空背景之下的人的情感问题。在《沧浪之水》中,阎真以一个悬壶济世的医生为视角点来反思社会与我的关系,在浑浊的世界中试图坚守自我的那份情感。《活着之上》体现了历史学家聂致远在美好的人生理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纠结、冲突的情感。除了自我与社会之间那种完全相悖的激烈情感冲突之外,在这两部作品中,阎真也把关注点放在了作品中任务的情感的变迁上。这两部作品中的家庭中都有着爱情和亲情的维持,然而,亲情也可能包涵道德绑架。《活着之上》中的赵平平以给自己儿子提供优质的生活为由,不断向聂致远施压,试图改变现状,改变他内心的坚守,来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渴望,这何尝不是一种异化了的情感。《曾在天涯》是作者远在异域他乡,在加拿大的文化语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窥视和剖析,反观正在经历异质文化体验的华人,对他们的情感与命运进行言说,同时,对“我”的个人情感变迁也进行了关注。《因为女人》以柳依依为镜,表达的是两性之间相处的情感,提出了关于爱情与婚姻的现实问题。在阎真的作品中,无论是写有坚守的知识分子与残酷社会的博弈还是写异国他乡的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碰撞,阎真时刻刻画一个主题:情感的缺失。情感的匮乏和无尽的孤独的生存体验中,主人公内在的心理冲突与现实的重压必然会导致他们撕裂开来,呈现两种必然且极端的结局:要么顺应承受这种情感的失落,要么反抗到底,为忠实自己的情感坚持到最后。《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开始坚守着传统的价值观,对市场经济下以利益为风向标的人际关系极力反抗和抵制,然而在权钱的双重压迫下,只能放弃坚守,回到现实生活,妥协顺从时世。《曾在天涯》中的高立伟从最初的壮志凌云,试图在加拿大混出点名堂,到最终放弃学业,放弃绿卡,与所谓的家庭文化优越感抗争到底,独自启程回国。阎真试图展现的是一个生命存在的尴尬困境:已逝的传统价值观使当代存在个体的精神无所皈依,现代文明所暴露出的弊端和危机,使知识分子很难找到灵魂的安置圣地。
与情感关联,不应该忽略的是阎真作品对女性的关注。两性冲突中的家庭式逼迫也是阎真作品所重点呈现的人的困境。无论是《沧浪之水》中的董柳,还是《曾在天涯》中的林思文,抑或是《活着之上》中的赵平平,她们看似都是好女生、好妻子,恪守妇道,对丈夫也称得上体贴入微,如赵平平为了不让自己的母亲反对聂致远与她交往,三番五次在中间调和,多次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周旋。一开始,她们都是如此的体贴与美好,不趋炎附势,不唯利是图,但是实际上,她们本身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即本能扩张的物欲和内心传统女德之间的彼此斗争。她们一方面不想给丈夫压力,一方面又想改变现状,故而只能以自己作为扭转聂致远或池大为的逼迫者,不断用女性的特殊权利——嘟嘟囔囔的抱怨和倾诉,试图使自己的丈夫放弃坚守,获得物质上的收获,然而在有所收获之后,物欲愈发膨胀,不断推着自己的丈夫走上了与本真相反的道路。阎真在《因为女人》中所塑造的这一女性角色更是彰显了他对现代女性困境的关注。柳依依是市场经济下高级知识分子的女性代表,她从一个落后的小县城考入财经大学,怀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以爱情至上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开启了她的爱情生活。夏伟凯的身体启蒙让她对纯粹的校园爱情感到失望,这种最接近梦想的爱情给了她沉重一击;秦一星的社会启蒙让她在互相寻求中获得失落,这种失落感最终让柳依依的以爱为核心的价值观走向了破碎;宋旭升的婚姻启蒙,使她没有获得爱情,只能独自承受着来自理性婚姻的失落。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物化社会中,女性若获得独立的存在,比男性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阎真从性别角度出发,把女性安置在现代人中间,把女性的困境写的更加深邃——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天生就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为了追求情感,追求诗意,几经辛苦,然而诗意与宁静却早已沦为消费对象,因而获得的只是来自各个层面的失落,这恰巧使其笔下的女性更具有悲剧感。阎真写“女人”也是写人,实际上是对人进行更细微更极致的剖析。在两性世界中,女性是感情化类群和“弱小的人”,相对男性往往体现更丰富的人性和人的本真状态,从而体现人的本质性存在。通过对女性这个特殊的人的类群的透视,阎真实际书写了一部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人学之书,把对人性的观察推到一个无所逃遁的澄明境地。
此外,文化差异中的迷惘也是阎真作品中所表达的生存困境之一。阎真早年留学加拿大,在完全陌生且排外的生活环境中,亲身体验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困境以及华人在异域文化处境下的焦虑和苦恼。《曾在天涯》中,高立伟怀着远大的抱负与美好的希望,无论生活如何艰难,都义无反顾地去拼搏去努力,试图在异域他乡扎根,改变现状。然而在加拿大生活一段时间后,对这个国家也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所谓的自由、平等也并非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实际上,高立伟一直渴望平等的、心意相通的对话,不是林思文的咄咄逼人和家庭优越感,而是张小禾式的贴合心意,然而滑稽的是,这个对话的对象也是这个国家的边缘人。
二、敞显“荒诞”与“孤独”的存在境遇
“荒诞”和“孤独”在20世纪以来被人们普遍感知,而且感受是如此的深刻和强烈。人类追求永生而生命个体的生存是有限的;他们渴望完全理解这个世界,但是世界却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希望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实际上,人生却是虚无和无意义的,这些对立的矛盾产生了荒诞的境遇。中国作家从20世纪初就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萨特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那里获取了思想资源,以现代哲学眼光打量自已的时代生活,开始对个体存在的追问和人的价值的探求。现代文学开拓者鲁迅置身于“无物之阵”和“历史中间物”的尴尬处境当中,感知到被一种敌对势力包围了,空有满腔愤怒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振臂高呼反抗,却无从下手,“孤独者”便是鲁迅及其笔下的先觉者最为基本的生命存在体验。当代先锋作家余华也往往将人物置身于一种“极限境遇”当中去承受孤独的存在,主动或者被动地去询问存在的价值。阎真也把作品的人物置于一种荒诞的“两难境地”,进则忤逆了自己的良心,退则受到生活给予的重压,再现孤独个体面对荒诞的生活境遇时,生命本真的潜在可能性和矛盾性如何被激发。只有面对着充满偶然和不合理性的世界,经历着荒诞的命运的安排,经受人生的戏剧性转变以及对自己内心的质问,才能实现自我的坚守与裂变。
《活着之上》把笔触放在高校的腐败之上,试图以一个人文学科教育工作者的目光,去再现学术和教育体制的腐败与龌龊。聂致远把曹雪芹作为自己内心坚守的标杆,以曹雪芹的一生为出发点,反观自己坚如磐石的信念——对现世的自我感到惭愧。最开始的时候,他坚守自我,对公正公平充满了自信,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满是真诚,对一切都是顺眼的,自己也是懵懂的,然而在经历了考研、换导师、考博士、发论文、评职称这几件事情累加之后,对一切开始了质问,大家都从自我生存出发,以利益化作为交往的准则,这样缺乏公平与公正的社会,让聂致远对存在的意义进行反思。而他的同班同学兼室友的蒙天舒,在浮躁喧嚣的世界中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虽没有聂致远有才情,然而凭借他的“屁股中心论”倒也活得左右逢源,且蒸蒸日上。妻子赵平平是一个大学毕业的普通小学教师,工作兢兢业业,却因为没有“关系”的原因,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部作品中反复提到曹雪芹,以曹雪芹为开端,又以曹雪芹为结尾,每次当聂致远遇到两难选择的时候,曹雪芹就萦绕在他的心头,生活的逼迫与内心固执的坚守之间的较量,难免让人生出一种一个世界已经崩塌而另一个更为明朗的世界还未建成的焦虑与失落。在这样一个物化逐利的世界之中,人们彼此隔膜,无法沟通,没有着落、无依无靠,凡有精神坚守者不免陷入迷惘、困顿、孤独与虚无。如小说中对曹雪芹的评价一般:“可他生活得那样从容、淡定、自信、优雅,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阎真以一种调侃嘲弄的笔调叙述了一件滑稽可笑的闹剧——在聂致远对教授这个职称已经完全放弃的情况下,命运之神又开了个玩笑,最无希望评上教授的他却跨越众人当上了教授,情理之中而又意料之外的结果,呈现了人在命运的迷宫里茫然无措,原本被认为很有意义的事物,本质上却是无意义的,甚至是荒谬的。
《沧浪之水》叙述的是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当代知识分子试图坚守传统价值观而大众普遍的精神根基和价值观遭到解构的尴尬境遇。小说主人公池大为对传统文化信仰最初近乎执着眷念,但在现实的语境中,面对钱权的诱惑与生活的重压之时内心产生了矛盾冲突,不得不进行艰难的选择与挣扎。阎真直言:“我力图写出普通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迫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知识分子的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虚无主义者。”[3]《沧浪之水》围绕池大为仕途的发展而展开,池大为一心想要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寻医问道者。起初,他对那些不公正奋起反抗,对赤脚医生跪在卫生厅门口求助这一事情,也伸出了援手,对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反抗,他的苦闷成倍增加且无从排解,以致于要把自己撕裂开来,他对现实社会的反抗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让他们成为社会的“异类 ”。然而在现世生活中,生存环境的落魄,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小的昏暗的宿舍楼里,连厕所都在楼道尽头,而毫无才情只会点头哈腰的丁小槐却掌握了“马屁”精髓,一个大男人,竟细致到给领导洗袜子,十足的谄媚,而恰巧是这样,却一路攀升,房子轻而易举就有了。池大为本无心去争抢,也不想与社会同流合污,然而来自金钱方面的重压与妻子的苦口婆心,个体灵魂良知和俗世生活之间的矛盾使他内心感到撕裂的阵痛,各种客观外在物与本能的力量涌向生命个体,生命个体的主体存在受到压迫,逐渐被蚕食,人沦为外物的对象与客体的地位。于是只好选择一种相对更为舒适的、更为轻松的生存方式,生活在被普通人所认同的角色当中——池大为被迫地选择了适应与融合的这条道路,将世俗理念凌驾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上,远离个体生命的本真状态,自我“异化”。
加缪对生存的荒诞予以形象的描述:“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4]加缪所表达的荒谬只是一种理性的特殊存在,而在荒诞的世界中自由选择、积极探索,才是他的价值归宿。阎真惯于在黑暗无光、沉沦无望的现实世界中挖掘俗世的阴暗与罪恶,在荒谬的世界中探索生命的意义,寻求自我的价值归宿与灵魂的栖息地。金钱、欲望、权利这几个俗世的基本要素,并驾齐驱,使现世处于荒诞的自我否定当中。而阎真就是在自我否定当中去塑造人物,勾勒和敞显荒诞中孤独的个体存在。
三、表达向死而在的存在之思
存在主义出现在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之后,它得以产生的内在驱动力和动机来源就是“存在”的“焦虑”,认为个人的价值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体存在者在“异化”的实存状态中最为基本的情绪感受和心理体验就是焦虑。神学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利希在《存在的勇气》中对存在的“焦虑”如此评说:“关于焦虑的性质的第一个判言是:焦虑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存在物能意识到他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5]这就是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进行了解和认识。“焦虑”与“恐惧”不同,恐惧是对已知的实存物体的一种担忧和害怕,是可以随着威胁的解除而消除的,而“忧虑”不同,忧虑本身是无来由的,他是对非存在物的一种敏感的感知,发出威胁的对象也就是威胁本身,因而他不能被消除。在无神论存在主义那里,只有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说才为解除焦虑提供了途径。他认为:“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向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6]对于孤独个体而言,死亡是摆脱现实尴尬境遇、寻求自我价值的不二选择。只有死亡才能使人从庸碌世界中分离,与社会关系割裂,从日常的消极状态中解脱出来。阎真着力于描写那些在地狱般的生存境遇当中挣扎怒吼的人们,展现共同的现实困境,试图呈现一个生存重压下无可抗拒的悲剧命运,并对生与死这一对立的哲学命题进行思考。
《曾在天涯》以梦境为引子,梦中的我经历了生命的苦苦挣扎,死神也与我擦肩而过,在经历了“回光返照”之后,开始体会生命的意义:“这时我忽然想到世界上最重大的变化最重要的事件原来就是生命的悄然移动,逐渐泛开的凉意使我清晰地意识到了生命移动的这每一寸。”“我”在死亡中寻求生命本真,思考我与这个永恒世界的关系,原来“我”的存在不过是与世界的共同存在的一场邂逅,突然顿悟到一切人生挣扎都是徒然的没有意义的,现世的挣扎唯一的作用就是对生命路过的一个暂时的渺小的证明。不能强求人生的圆满结局,生命的存在意义在于对意义的追问过程。“向死而在”这种形而上的思考在阎真作品中并非只有这一处,《活着之上》开门见山就是叙述“死亡”:“小时候曾看到很多人离开这个世界,这在鱼尾镇总是一件大事,也是我们的节日。”鱼尾镇的葬礼,这只是死亡的一种形式,是与世界的一种告别仪式,正是这种告别仪式开始让聂致远开始对生命的存在进行追问,“对于那些离去的人,很少有人再提及,包括他们的亲人”,人生在世活七八十年,一点痕迹都不曾留下,那存在是为了什么呢?这不由得让聂致远觉得恐慌。爷爷的离去只是一个引起我内心震撼和思索的契机,把人物置身于生与死的对立中考察,正是他对生存意义的探寻的表现。通过人们在面对死亡之时所作出的自由选择来体现人对生存的畏惧与惶恐,对现实世界当中人物的生存和生命本真进行探索。他站在形而上的角度试图为我们指出一条通往生命本真的大道,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生存变得有价值。无独有偶,《活着之上》除了有对现世的人的死亡发出追问之外,对已逝的曹雪芹的祭奠也是一种对俗世人生的追问。对于曹雪芹生前死后的思考,让“我”不禁从一种曾经体验过的力量中让自己从俗世中超脱出来,对现世的自我有积极的引鉴作用。阎真不畏惧死亡,正视死亡,对人们必然要达到的终点不做任何回避,他正视死亡就是正视生存,从而实现了对死亡的超越。作者超越了对于某一种社会现象比如学术腐败,而对人类的一些本质问题作了哲学层面的拷问,因而使作品具有了相当的深度。《沧浪之水》直接以“父亲的死”开篇: “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父亲早年替同事说了几句公道话,因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划为右派,逐出了县中医院,受尽冷落。父亲在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后,吼了一声“苍天有眼”就倒地不起了,和范进中举一般有戏剧性。这样的死亡本身就很有戏剧性和荒诞性。父亲的死看似是一种偶然性,实际上也是父亲的自我选择,父亲本就是阎真笔下受压抑的、无奈存在的一个个体,因为保持一颗刚正的心而受到外部世界的压迫,一个愚昧的不合时宜的政治表现,就使他无处翻身,本身就活得歇斯底里和绝望,对人的存在充满了质疑,如果不愿采取行动,或者说根本跳不出这样的境遇的话,那就只能选择死亡。所以阎真设置了死亡的情节来完成父亲弃生求死的念头。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当此在作为这种可能性悬临于它自身之前时,它就被充分地指引向它最本己的能在了。”[6]死是必然的,并非存在的终结,而是走向存在终结的过程。向死而在指的并非是活着的人与等候在生命尽头的死亡之间的一种外在关系。人们不是走向未到场的死亡,而是在我们朝死亡走去的嘶吼,死亡早已在场。通过死亡或者是把人逼入绝境之后,探寻人的存在,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做出终极审问和思考。阎真深谙人生的终极虚无却仍然不懈地反抗,深知个体的孤独无助而执着地坚定自我,与群体做生存斗争,虽然难免也摆脱不了俗世的熏染,然而这种向死而在的形而上的思考正是阎真对个体存在的焦虑和群体存在的问题的一种关怀显现。
传统的哲学把人看作是孤立的主体,客观世界以及生存环境构成了主体,把人与环境割裂开来。康德把这种无法证明外部世界存在的哲学命题看作是一个“哲学和一般人类理性的耻辱”。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这种“哲学上的耻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明,而在于人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6]在他看来,把人生和世界等同是片面的,应当把人的认识和真理也视为整体,人生本就是一个呈现和揭示的过程,人生的展开过程也就是人的一个认识真理的过程,也就是事物得以“解蔽”的过程。阎真在创作中,阐述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是把人生置于死亡的格局中阐发,如池大为死亡的梦境、爷爷的死。在面对死亡,面对人生必然走向终结的这一事实,作者探寻的是超越死亡的意义,力图在绝境中寻求光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试图坚守住自己的精神世界,把生存的价值放置于追寻希望和目标的路途当中,借此去体现存在的价值。面对死亡的绝境,阎真探讨的不只是获得现实的物质、世俗的成功,而是从存在的意义上探寻真理和目标,试图以人生的展开,逐渐去认识真理,揭示事物的真相,只有当此在存在之时,存在者才被揭示、展开、得以解蔽,从而体现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即便身处绝境,在黑暗当中看到那一丝丝光明,正如悬崖上的那朵红花,遗世独立。阎真笔下的人物都怀揣着不屈服的精神,昂首阔步向真理迈进,即便没有光明,也要在追求的路途当中去反抗,这有些类似鲁迅所提出的 “铁屋子”情境:“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7]明知死亡只是徒然增加更多的苦痛,但是也要在呐喊中走向灭亡,在呐喊的过程中体现生命的价值。阎真试图告诉我们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认识到的,即便身处囹圄,处于封闭的现实黑暗,也只能朝前走,向着真理反抗到底,哪怕这是无意义的,但这才是生命存在的证实,这就是“真的人”的生存方式,被“处以自由之刑”[8]的存在主义者的生存方式。他们坚信在现实生活的世俗世界之后还有一个更为浩瀚更为深邃的真理世界等待着我们去揭示。
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阎真用他绵密的心理叙事,以生命自我体验为基础,把丰富、本真的人性剖析给众人,是对世俗生活与绝望的超越,实现了对人的关怀。无论是对知识分子情感失落的叙述,还是在对文化差异的迷惘的叙述中,抑或是对女性的整体关照当中,阎真无处不在的揭示那些“高知”的生存困境,面对荒诞现实与孤独个体的矛盾冲突与对立,把个体良知与存在境遇的对抗细腻鲜活地呈现出来。在极端的现代体验与深厚的现实关怀相冲突的情况下,阎真选择的是在死亡中或者是绝境中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把自已创作深入开掘到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寻上,与存在主义所代表的“某种虔诚的努力”相契合。
[1] 王晓华. 西方戏剧中的终极追问与荒诞意识[J]. 中文自学指导,2005(1): 16-20.
[2] 仇敌辉. 数理情感学[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7.
[3] 阎真. 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说说《沧浪之水》[J]. 理论与创作,2004(1): 60-64.
[4] 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
[5] 保罗·蒂利希. 存在的勇气[M]. 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33.
[6]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1999: 289.
[7]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41.
[8] 萨特. 存在主义为何物[M]. 北京: 人文书院,1955: 32.
[编辑: 胡兴华]
The dimension of existentialism in Yan Zhen’s writings
YAN Jiexiong,FANG Ji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By reflecting the general living status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Yan Zhen's works have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But,few have noticed the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inherent in them. In effect,there lie numerous affiliations between Yan Zhen's writings and existentialism,which can be ellaborated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presenting modern people's hellish struggle for survival,revealing the absurdity of their lonely existence,and reflecting on the existential philosophy of Being-towards-death.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people's original living situation,the novelist goes deeper to manifest the connotations of existentialism by sketching individuals' living circumstances and the pursuit for their life value,hence uplifting his works from survival to existence.
Yan Zhen's writings; living circumstances; philosophy of Being; Being-towards-death
I209
A
1672-3104(2016)04-0156-06
2016-03-20;
2016-06-12
2013 年度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健康发展理论研究”(13B026)
晏杰雄(1976-),男,湖南新化人,文学博士,美学博士后,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第五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