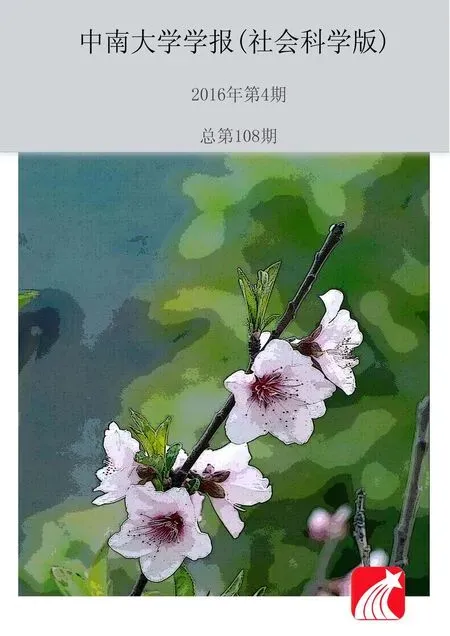论我国民族优惠的政策转向与话语重构
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论我国民族优惠的政策转向与话语重构
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我国是一个民族二元结构相对突出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实现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均衡协调的发展,我国实施了以“民族身份”作为社会资源倾斜性分配依据的民族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整体性发展。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嬗变,民族优惠政策的外溢效应渐趋凸显,民族优惠政策的存废也引发了学术界激烈而持久的思想交锋。事实上,由于我国民族二元结构在当前依然缺乏实质性改观,民族优惠政策仍然具有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过,鉴于民族优惠政策效力递减的客观现实,我国也应该逐渐以“区域主义”和“位差主义”的扶助政策替代“民族身份”取向的民族优惠政策,并通过重构“民族优惠”的话语体系,推动各民族形成“民族互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优惠;民族互惠;民族话语;区域主义;位差主义
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在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流变中形成了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非均衡发展的民族二元格局。为了实现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均衡协调发展,我国以民族优惠政策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在国家资源权威性分配过程中,给予少数民族以特别的倾斜性扶助,极大地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变迁,民族优惠政策的外溢效应开始凸显,民族优惠政策的价值正当性和现实效用性也引发了学术界旷日持久的理论诠辩与思想角力。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民族优惠政策是否依然具有生存的空间?民族优惠政策的外溢效应当如何消解?民族优惠理论又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地实现理论重铸和话语重构?这些都是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必须予以直面和回应的重大问题。
一、民族优惠政策的生成逻辑与理论价值
我国是一个民族发展历史源远流长的多民族国家。在王朝国家时期,受地理区位、自然资源、文化传统、族体规模和发展起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各民族非均衡发展的状况十分突出,尤其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发展鸿沟十分明显。然而,在民族事务治理历史中,民族发展鸿沟的矫正并不是王朝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焦点性议题,甚至没有纳入王朝国家的治理视野。由于地理上的区隔和文化上的异质,王朝统治者在“天下至中”的自傲心态之下想象边疆少数民族之时,往往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傲慢与偏见”;同时,也为了避免边疆民族政权的发展威胁中原王朝政权的安全,王朝统治者往往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持一种清静无为的态度,而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视为民族事务治理的终极价值追求[1]。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上民族不平等的理念得到彻底的纠正,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逐渐成为了党和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价值基石。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不但从价值理念和文化权利上反复强调各民族“理论上的平等”,而且矢志不渝地追求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追求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为了实现各民族的均衡发展和事实上的平等,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倾斜性照顾少数民族的民族优惠政策。民族优惠政策的价值正当性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普遍欢迎,也得到了主体民族的广泛理解,在随后的贯彻实施过程中收获了极为丰厚的政策绩效。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优惠政策是矫正民族二元结构的必然举措,也是我国民族国家建构向纵深推进的理性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主权意义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完成,并开始了政治制度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理性化的深入建构。在政治制度一体化方面,我国以大气磅礴而又润物无声的国家整合,通过民族精英的绥靖和行政权力的下沉,将民族地区政权吸纳进入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各民族地区都实现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形态演进。不过,国家政治制度一体化的建构虽然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但国家认同建构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实现,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之中,国家认同的建构是以各民族权益实现和幸福指数增长为前提的。而我国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社会鸿沟,以及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在横向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对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权益实现和幸福指数增长都是一种戕害。在我国民族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受制于各种先天和后天因素的综合性影响,少数民族仅仅凭借自身内源性发展动力的开发很难实现对主体民族的赶超型发展,从而导致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存在进一步的生存边缘化和弱势永久化的风险。少数民族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地位的持续下沉和不断走低,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党和国家向来主张和坚持的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成为一种梦幻泡影,并从深层次上妨害民族团结的推动,掣肘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型构,诱发他们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质疑,使得国家疆域存在裂变的风险。而国家疆域恰恰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得以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安身立命的前提,国家疆域的巩固统一也向来被视为民族事务治理的最高目标和核心利益。少数民族的边缘困境及由此产生的潜在风险无疑与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道德担当和终极追求相违,因此,为了矫正民族二元结构,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和维护国家疆域安全,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少数民族整体性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弱势地位进行集体救济。
作为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主要政策工具,民族优惠政策是有着特定的道德关怀和理论价值的。
第一,民族优惠政策是一种“补偿性正义”。它是对历史上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一种反动,是对社会正义和民族平等的执著性追求。在各民族长期的历史交往中,民族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多年来对不起少数民族”[2](48),“由于过去对不起人家,今后就应该多补贴、多支出一些,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2](152)。这是党和国家对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深刻反省和自我矫正,也是民族优惠政策创制的思想根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扶助、税收减免、对口支助、计划生育、高考加分、就业保障、人才培养和使用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差异化的保障政策。这种针对少数民族弱势地位而进行的差异化权利救济和特殊保护,并不是政府德性无节制的泛滥,而是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法则若然符节的。约翰·罗尔斯认为,社会正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3]。在各民族发展程度严重非均衡的状况下,如果单纯强调对社会基本价值在国家内部进行“平等分配”和“无差别对待”,那么根本无法保证民族发展机会公平和结果正义。因此,为纠正和消除少数民族由于非选择性境况而导致的族际发展结果的非正义而给予少数民族以合理的补偿机制和特殊的权利保护,乃是社会正义的客观要求。
第二,民族优惠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实质平等观”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4]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就必须“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5]。而在一个民族非均衡发展格局十分突出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经济地位的弱势必然会导致政治地位平等的失守、文化权利平等的失落和社会地位平等的失衡。即便西方一些国家通过“承认的政治”,确保少数民族各项权益能够得到普遍性尊重和包容性发展,但多数原则主导下的票决民主始终潜藏着多数暴政的风险,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很有可能面临着主流社会的集体性排斥,文化权利更是始终难以摆脱主流文化话语霸权挤压的风险。这就从根本上掣肘了民族政治生活由“承认的政治”走向“参与的政治”“对话的政治”和“协商的政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对西方国家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可能存在的多数暴政保持必要的清醒和警惕,在追求“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同时,必须通过多元举措对少数群体的正当权益进行特别保护。针对少数民族进行特殊的制度安排就成为了防止多数暴政,切实保障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平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第三,民族优惠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民族优惠政策的价值评判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哲学思辩和理论探讨,而更应当从事实层面反思和总结其实践效果。在民族优惠政策赞赏者看来,民族优惠政策自上个世纪50年代实行以来,党和国家从诸多方面对少数民族进行差异化授权、倾斜性的资源分配和特殊化的权利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整体性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中国政府系统地制定、实施民族优惠政策以来,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6]一些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方法,考察了少数民族城市化水平,也间接论证了“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正面影响”[7]。因此,民族优惠政策,不管是从主观感知还是实地调研,其政策红利和实践效力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更重要的是,民族优惠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形塑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民族优惠政策采取的是“以发展换忠诚”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权益的整体性增长,促进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民族优惠政策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弱势关怀”的底层立场和“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持续性追加,对于国家巩固和民族团结起到了极为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民族优惠政策的理论诠辩与潜在缺陷
在我国传统总体性社会时期,社会分化不明显,民众利益意识不强烈,信息流动相对缓慢,针对少数民族集体权利救济的民族优惠政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历史性成绩。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整个社会都兴起了一场“期望值的革命”,各民族的利益意识普遍觉醒,利益敏感度持续走高,民族优惠政策遭遇到了道德价值质疑和现实效力拷问的双重压力。在批评者看来,民族优惠政策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民族优惠政策的价值正当性在急遽的社会变迁中正在趋于衰颓。民族优惠政策的价值正当性源于民族发展的“补偿性正义”和国家政府的“道义担当”,是“基于公平的正义”在民族关系上的体现。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发生了极为严峻的社会分化,城乡、区域、行业、族际之间的发展差距日益凸显,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民族结构虽然依然存在,但是从社会分层视阈来看,民族内部也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分层现象,民族精英与普通民众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已然判若云泥。民族内部严重的社会分层现象,使得日益崛起的民族精英与传统意义的“最少受惠者”渐行渐远,传统针对少数民族弱势地位而进行的整体性扶助的道德正义性正在日益失去坚实的现实支撑。此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政治国家对市场社会的松梆,整个社会的活力急遽迸发,各民族民众在改变自身生存境遇的内在驱动之下,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跨区域大流动,并进一步形成了插花式的民族分布格局和互嵌式的民族居住格局,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然而,基于民族身份而进行资源倾斜性分配的民族优惠政策,并没有考虑各民族所处的区域发展程度差异和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导致边疆多民族贫困地区的主体民族享受不到民族优惠政策带来的附加利益,而生活在国家核心区域的少数民族在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充沛的社会资源之时却仍然享有民族身份带来的额外权益。民族优惠政策无法保证“反歧视行动政策真正地惠及最需要的人”[8],这就进一步解构了民族优惠政策的价值正当性。
第二,民族优惠政策并不能实现各民族“实质性平等”。我国民族优惠政策强调以民族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没有指出只有改变民族社会分层的结构性差距才可能达到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这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一些民众在与其他民族攀比时只看结果而不去分析原因,也不考虑个人之间的客观差异。这种政策实施的后果是民族优惠政策遭遇到了汉族成员和少数民族成员的双重不满[9]:汉族成员从个人角度考虑,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应有的不公平待遇(没有在法律或制度上得到平等的竞争机会);而在一些受到优待的少数民族精英看来,民族优惠政策往往意味着“承认被优待的族群命定地没有能力与其他非优待族群进行平等的竞争”[10],因此,民族优惠政策乃是一种强者的道德施舍与良心发现,是一种将“本属于我的东西”给予“他者”的德性怜悯。此种认知直接导致了一些少数民族精英因为所谓的“优惠政策”而产生浓厚的道德负重感,影响其竞争力的进一步开发。[11]同时,一些少数民族的普通成员往往又将本民族发展滞后简单而不恰当地归咎于主体民族扶助的不到位和民族优惠政策力度的欠缺,从而产生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追求更多特殊权益的内在冲动。
第三,民族优惠政策是对现代社会资源分配资格的背反。现代社会的资源分配是以个人成就为基础的;那些取得更高社会成就的个人——他们也往往被公认为具备更高的才能和职业水平,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这种分配方式的合理性在于这样一个假设,更高的社会成就意味着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12]因此,给社会成就杰出者匹配更多的社会资源,是整个社会正向激励逻辑的必然演绎,也是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客观要求。而民族优惠政策是身份导向的,其所主导的国家资源倾斜性分配是以民族身份作为特殊权益享有的唯一资格,本质上是对现代社会成就取向的逆向而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道德任意性”和对主体民族的“逆向歧视”。
第四,民族优惠政策在当代民族事务治理中的负向效应正在逐渐凸显。民族优惠政策以民族身份作为资源倾斜性分配的依据,客观上使得只是作为文化象征的民族身份具备了原初并不具备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民族形成了制度化的身份区隔,诱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刺激了少数民族关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强化了各民族关于稀缺性资源的竞争与博弈。而在当代民族国家纵深建构的过程中,形塑各民族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乃是各国民族事务治理一个核心命题。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但对于一些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认同的持续强化在某种程度上却有可能造成对国家认同的遮蔽与解构。中国民族优惠政策本意上是希望通过对少数民族倾斜性扶助换取各民族对国家的忠诚,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优惠政策外溢效应的凸显,民族优惠政策客观上却出现了刺激民族认同的负面效应。而民族认同的强化一方面使得各民族“我者”与“他者”边界意识的清晰,妨碍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推进;另一方面,民族认同的强化往往又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动员工具。在全球性国家主权神圣性逐渐褪色之后,民族认同已经成为抢占阶级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淡化之后精神空地的最汹涌的力量,如果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利用我国边疆地区民族认同持续性强化而进行反政府的社会动员,将给国家统一造成难以预料的风险。第五,民族优惠政策容易导致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非对称性相互依存”的错误认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一部厚重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并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并且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强的历史。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13](25)这也就是说,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各民族(包括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都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对称性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在当前民族优惠的话语体系中,我国往往侧重于论证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单向度扶助的道德价值性和实践效用性,一些宣传机构和部门也对党和国家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进行了全方位饱和式宣传,使得社会普罗大众对于党、国家、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扶助和优惠知之甚详。但不管是民族界的理论探讨,还是党政部门民族政策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对于国家和主体民族之重要意义,由此容易导致部分民众形成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非对称性相互依存”,甚至“偏害共生”①的错误思想。当年苏联解体的裂变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民族优惠政策导致俄罗斯族普遍形成“俄罗斯就是一头任人吮吸的奶牛”的观念,认为少数民族是俄罗斯族发展的负担,产生“甩包袱”想法。苏联解体,殷鉴不远,当前我们如果不警惕民族优惠政策的负面效应,反思民族优惠话语体系的缺陷,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巩固便始终存在着难以预知的不安定因子。
三、民族优惠政策的思路转向与话语重构
在民族优惠政策外溢效应不断凸显和价值争论趋于炽热的情境下,我国民族优惠政策到底应该何去何从,这是当前我们必须予以正面回应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优惠政策的存废之争,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正当性诠辩的问题,并不宜以某种普世价值作为逻辑起点进行纯粹主观的逻辑推演,而更应该直面当前民族事务治理的主要矛盾和核心议题,从民族事务治理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入手,反思和追问民族优惠政策的存废或修正。因此,在讨论民族优惠政策的存废或修正之前,民族优惠政策的赞赏者和批评者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最基本的共识,这是双方展开对话一个基本前提。其一,当前民族事务治理的终极目标或最高利益就是实现国家统一巩固和民族团结和谐,在何种程度上和采取何种方式对少数民族集体权利展开救济必须以国家最高利益为基本导向。其二,当前我国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非均衡性发展的二元结构依然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存在固化的可能,党和国家必须对少数民族集体权利展开救济,对少数民族的扶助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削弱。其三,为了规避民族优惠政策固有缺陷,当前针对少数民族集体权益救济必须转换帮扶思路,在不刺激民族意识、不加剧民族博弈、不固化民族界限的基础上去帮扶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当前民族优惠政策的修正或替代必须达到不谈民族优惠而实现民族优惠之目的。在以上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有如下认识。
第一,鉴于当前我国民族二元结构仍然十分明显,民族优惠政策依然具有一定生存空间。但随着民族优惠政策外溢效应的凸现,我们应该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审慎地确认民族优惠政策适用的时效与边界。民族优惠政策本身是基于中国非均衡发展的民族二元结构和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价值定位而做出的审慎抉择和精心规划,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有其存续之价值,但它是一种权宜性或暂时性的安排,而不是一种恒定的制度化安排,是在今后随着民族均衡发展格局逐渐实现而理应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一项政策。即便从国际反歧视法的角度来看,国际立法中关于少数群体的“优惠”政策也是作为一种特别措施或临时措施获得政治合法性的。而就民族优惠政策的适用边界而言,考虑到“基于公平的正义”法则、国家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民族事务治理绩效优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当前民族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应当主要集中和限定于边疆多民族地区双语使用困难的少数民族教育优惠与加分录取、民族医药优惠扶助发展、民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少数民族就业权宜性倾斜等方面。
第二,鉴于传统民族优惠政策以民族身份进行稀缺性资源倾斜分配导致民族认同强化和民族博弈加剧等外溢效应,当前民族优惠政策应该实现“民族身份取向”向“区域主义取向”的转化,即不再以“民族身份”作为是否倾斜性扶助之依据,而以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为标准进行区域性集体扶助发展,着重解决区域内各民族共同面对的公共问题,实现国家区域均衡性发展和区域内部各民族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聚居在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针对这样一些特定区域进行集体性扶助,既达到了不谈民族优惠而实现民族优惠之目的,又可以有效地规避民族身份认同强化和族际“逆向歧向”弊病之产生。这也正是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的,“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修订完善已有政策,还是研究出台新的政策,要逐步更多地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尽可能地减少同一地区中民族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要避免民族之间出现政策陡坡”,“防止因政策导向人为制造隔阂”。[13](67)
第三,鉴于当前我国深刻的社会转型和严峻的社会分化,传统针对少数民族集体权利进行的整体性救济并不足以确保惠及真正需要帮扶的底层民众,民族优惠政策扶助标准需要从“民族身份取向”转向“位差主义取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马太效应的彰显,我国传统总体性社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分化,各民族都出现了一批底层化和积弱化的弱势群体。“位差主义取向”的救济理念即为根据各民族成员在社会分化中生存境况,基于底层视角和人文关怀,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各民族成员进行普惠性救济。“位差主义取向”的价值底蕴在于,党和政府对各民族弱势成员的救济并不是因为其“民族身份”的缘故,而是因为其在“社会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缘故,[14]党和国家有责任保护其共享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之成果,保卫其追求幸福之权利。“位差主义取向”的权益救济,注重对各民族在社会分化中弱势群体的普惠型救济,是对“区域主义取向”的有力补充,它使得我国民族均衡发展的建构不仅注重地理区域协调发展的平面型思考,而且还注重社会分化与整合的纵向型思考,确保各民族均衡发展保障体系的立体化建构。
第四,鉴于当前我国在对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对口支援中存在建设“面子工程”的错误倾向,我国针对弱势区域和弱体群体进行集体性支援和帮扶还应该由“政绩取向”转向“民生取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治理的重心发生了重大转向,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不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治导向之下,很多地方政府出现了高度的发展饥渴和政绩需求,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领导干部提拔使用上都是“以GDP论英雄”“唯GDP论”。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我国对口支援工作中的支援方和受助方往往也受扭曲的政绩观之影响,倾向于建设一些贪大求洋、花团锦簇、易出政绩的面子工程,而并不着意于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的建设。这样一种做法事实上并不符合我国针对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进行对口帮扶的本意,而且在实践工作中也容易导致政府形象的集体蒙羞和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当前我们应该调整传统对口支援的一些偏差,树立“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民族福祉的普遍提升,切实把民生改善当作最大的政绩,建构覆盖各民族、全区域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安全网,在基本生活、基本养老、社会救助等方面为各民族群众生存条件的改善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第五,鉴于“民族优惠”话语本身容易不恰当地滋生大汉族主义情结和导致少数民族尊严受损,当前我国应该逐渐推动“民族优惠”话语体系逐渐转向“民族互惠”话语体系。“民族互惠”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修正民族优惠话语体系缺陷的努力尝试,也是我国民族理论自我成长的必然走向,更是从理论层面解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嵌互惠互利的客观需要。民族互惠的理论话语,强调的是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惠济,它潜藏的“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价值取向是对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非对称性相互依存”错误认知的深度矫正。同时,民族互惠理论的创制也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自我成长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建构起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与时俱进而又逻辑自洽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不过,以民族平等理论、民族团结理论、民族繁荣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侧重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基石和目标导向,而相对缺乏对各民族共生共存、互利互惠的历史和现实作学理性的解读和梳理。因此,为了实现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拾遗与补正,当前我国民族话语体系必须创制中国民族互惠理论,并从各民族经济上相互补充、发展上相互支持、文化上交相辉映、安全上互为保障等方面展开民族互惠的理论自证,更进一步推动各民族形成“相互依存、互惠共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释:
① “共生关系”原本是生物界的一个概念,是指动植物互相利用对方的特性和自己的特性共同生活相依为命的现象,它包括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偏害共生等多种形态。生物间彼此合作共赢则是互利共生,如果在两者共生的关系链中,只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毫无影响,则为偏利共生,而如果对一方没有影响,对另一方则有害,则为偏害共生。
[1] 朱碧波,王砚蒙. 论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转型与重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14,43(6): 30-34.
[2]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4.
[3]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47-448.
[5] 列宁全集·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 25.
[6] 纳日碧力戈.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132.
[7] 邓艾. 西部地区民族人口城市化差异实证分析[J]. 民族研究,2006(2): 30-38.
[8] 威尔·金里卡. 少数的权利: 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 邓红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3.
[9] 马戎. 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1.
[10] Horwitz,Donald L.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M].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657.
[11] 杜社会. 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渊源、法理与特征[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31(5): 5-9.
[12] 关凯. 族群政治[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104.
[1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4.
[14] 王砚蒙,朱碧波. 论我国边疆治理取向的调适与重构[J]. 云南社会科学,2015,206(4): 11-16.
[编辑: 颜关明]
Policy turn and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 minority preference in China
ZHU Bibo
(School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China boasts of multi ethnic minorities with remarkable binary structu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thnic minorities and majority,our country implements ethnic minority preferential policies with ethnic identity as the standard in allocating social resources inclinedly,which promotes their holistic development. However,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 and evolution of the society,the spillover effect of ethnic minority preferential policies began to highlight,arousing in academia heated and long-lasting controversy over its maintaining or abolishing. In fact,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such policies to survive and develop because there still lacks critical change in the binary structure in our ethinicity. But,in view of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ethnic minority preferential policies,we should turn gradually from the ethnicity-oriented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difference-oriented support policies such as regionalism and difference discipline,and re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national preference to promote the awareness of Chinese ethnic community that all ethnic groups form national reciprocity.
ethnic minority preference; national reciprocity; ethnic discourse; regionalism; difference principle
D562
A
1672-3104(2016)04-0137-06
2015-11-09;
2016-01-0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CZZ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15YJC810015)
朱碧波(1981-),男,湖北潜江人,法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边疆治理,民族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