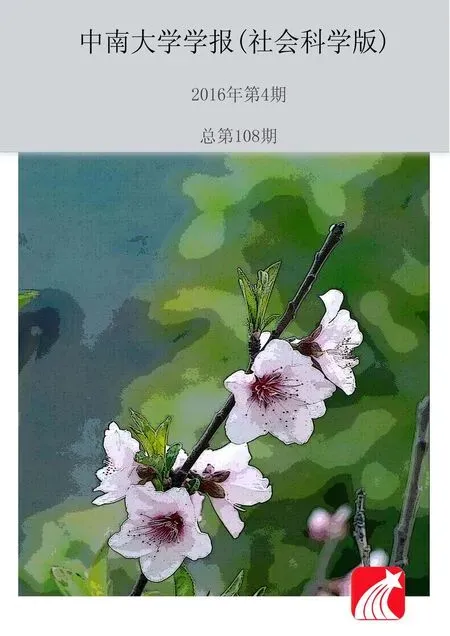被冻结的民主:政治道德的破产与绝对自由的悖论
——费赫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批判
温权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被冻结的民主:政治道德的破产与绝对自由的悖论
——费赫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批判
温权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因激进的政治主张和不成熟的民主实践,法国大革命为后世广为诟病。尤其以恐怖专制的雅各宾主义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下被反复批驳。费赫尔从国家政治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由“指券体系”所催生的国家干预政策与“德性共和国”的虚假预设,是大革命从民主走向专制的内在根源。他们将抽象的道德理想投射于具体的政治领域,并借助暴力手段使之进一步泛化到社会各个层面,从而强制营造出德性-国家-民主的蹩脚统一。当道德的衡量标准被肉身化为世俗的革命领导者时,政治民主就被道德专制所取代。其过程本质是哲学层面的绝对自由仓促应用于现实社会的结果。因此,大革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一场哲学实验的失败。而对大革命内涵的揭示,不是要脱离于它的历史区间以思辨的形式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是要通过展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缩短和减轻历史进程中不必要的“痛苦”。
费赫尔;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主义;民主;专制;德性共和国;绝对自由
虽然倡导平等与自由的法国大革命,伴随着雅各宾派独裁专政的瓦解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却在政治与哲学层面,为日后西方社会制度的发展留下了难解的谜团。原因在于,以启蒙主义为先导的激进民主制度,为何在政治上日趋保守集权?对此,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试图以大革命中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为出发点,通过分析雅各宾主义固有的内在张力,进而找到大革命失败的思想根源。
他认为,革命初衷的变质与恐怖专制的兴起,是一个从经济举措到政治运行,再到哲学预设,三者逐级异化的过程。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指券体系”为代表的经济政策,在后期强行摧毁了商品自由贸易的社会根基。作为“一个革命的措施,它将永久革命张力的不可避免的要素注入进连续的革命进程中”[1](42),从而在经济规律为政治指令所取代的同时,推行该政策的共和国也日趋成为剥削人民大众的权力机器。其次,由激进的政治制度所塑造的“德性共和国”,往往以公民监督人和道德净化器的身份出现。如此一来,执政党势必在模糊政治与道德界限的同时,凌驾于律法之上。而不断革命的意识形态最终则演化成非理性的宗教狂热。面对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极端的社会状况,它很容易蜕变为诉诸暴力以巩固政权的世俗神祗。再次,与其说大革命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体验,不如说它是一次仓促的哲学冒险。“德性共和国”的出现以及“救赎政治”的达成,毋宁以哲学上的绝对自由为主导。事实证明,后者“既不能产生任何肯定的事业,也不能作出任何肯定性的行动;它所能做的只是否定性的行动;它只是制造毁灭的狂暴”[2](118)。因此,革命后期雅各宾主义的恐怖专政,毋宁是将以上抽象的哲学理念付诸实践之后所造成的必然恶果。
以哲学的抽象自由为前提,进而在政治上对“德性共和国”的热衷,与启蒙主义的偏执情绪别无二致。而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张力,始终是困扰大革命民主进程的致命顽疾。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二者关系的曲解是大革命走向失败的直接诱因。
一、“指券体系”后遗症与行政指令常态化:经济逻辑还是政治逻辑
由大革命所缔造的共和国,从建立伊始就处在内忧外患的极端环境中。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其领导阶层为保卫自身的政权,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临时但颇具效力的行政举措。反映在经济层面,就是为平抑物价而强制施行的指券金融体系。当时的外在局势非常严峻:“1789年8月初,法国国库空虚,举债又连遭失败。社会动荡所导致的消费的畸形增长,使硬通货越来越短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行一种新货币的迫切性已被提上日程。”[3](161-162)鉴于此,由君主立宪派所组成的事务委员会,借助临时成立的特别银行,专门发行了价值4亿利弗尔的指券。凭借该措施,他们“一方面设想发行一种真正具有货币效能的指券,遏制商业萧条,恢复市场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剥夺教会对其财产的经营管理权”[3](163)。显然,指券发行的初衷,原本是想在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基础上,促成财政制度的良性改革。
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指券体系,不久之后就转化为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国债的单纯手段。而指券的不断贬值又造成新一轮的物价飞涨,一时间米珠薪桂,人民群众入不敷出。然而,之后的政府却“不提‘资本家投机集团’,更不提限价,强调的仍然是贸易自由和经济自由”[3](308)。于是,大规模的暴动和持续的社会动荡频频爆发。由此可见,经济上不健全的指券体系,隐含着国家与民众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费赫尔指出,在上述情形下,“国家要么从流通领域的大量货币中征用足够数量的货币单位以满足国家的需求,要么向所供应的货币中强制注入一定量新的贬值单位,以满足家庭的需求”,但无论如何,它“在理论抽象方面仍然与法国革命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1](53)换言之,发行指券作为大革命的应急方案之一,片面强调了国家政权之于公民生计的绝对优先性。而临时货币的贬值也“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破产,而是代表一条经济道路上,在这其中,数以万计的工薪族被迫遭受一个称为大革命的抽象物的剥削”[1](51)。费赫尔认为,后者无疑会产生以下两方面后果。
第一,以应急政策为先导的指券体系,几乎完全遮蔽了货币自身的运转功能,并以笼统的革命性质取而代之。如此一来,“货币体系的‘革命性质’意味着其内在规律不会表现出商品生产的水平和货币发行量之间的一致。”进而,“猛烈的通货膨胀扰乱了本已经脆弱的穷人的家庭预算,……其政治后果……只能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刺刀来解决。”[1](55)该现象尖锐地反映出,革命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普罗大众真实的角色转换。费赫尔认为,一旦君主制被推翻后,“群众被看做市民,那他们似乎就完全沉浸在诸如面包价格这样的庸俗问题之中,尤其在城市场景之中更为如此。”[4](8)况且,为大革命所建立的“自由国家事实上是与自由市场相连的,公民也是自私自利的人”[4](215)。因此,人民群众的生计问题与革命能否营造出良性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然而,随着经济政策向国家政权的明显倾斜,指券“持续不断的贬值承认了预算需要政治和时间的优先性,甚至不惜牺牲以工资为生计的人的利益”[1](50)。这无疑激化了人民与共和国之间固有的矛盾,从而导致革命政权持续的不稳定。
第二,指券体系的推行及其后续失败的赋税改革,又进一步促使国家政权对经济活动的粗暴干预,从而滋生出政治专制主义的端倪。一方面,“经济学被一种武断的方式政治化,同时,由于其自身不可避免的规律被宣称是‘自然的’。公民,他们所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都应该作为重要指导,却仍被边缘化,从未被咨询过。”[1](53)由此可见,实证的经济规律被政治的一厢情愿所取代后,公民基本的利益诉求也将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另一方面,面对群众的反弹与残酷的斗争环境,极端的政治手段在所难免。于是,“部队,甚至暴力,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被纳入到系统中来。……革命者只能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对民众强加新的赋税,另一种是强行临时实施各种‘革命的’经济政策。……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把革命引向自杀(破坏自由)的漩涡。”[1](54)经济体制的泛政治化,无形中把公民纳入不断革命的怪圈。随着暴力手段的介入,自由灵活的市场贸易被简化为国家的物质需求,原本独立的经济个体在服从行政命令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被视为彼此平等的集合体,并与抽象的国家相等同。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就“产生了对‘革命团结’的盲目依恋,失去了在客观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化时的应变能力。”[5](289)而他们自身作为具体政策的制定人,当然会以革命的名义,为维护教条的行政指令成为新的独裁者。
不难看出,由指券体系所引发的行政指令常态化,及其对经济规律的粗暴干预,突显了缔造共和国时,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之间深刻的内在矛盾。对此,费赫尔专门指出,“‘政治逻辑’,旨在创造一种‘自由社会’的动力,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当社会经济蓝图开始出现分歧,或是彼此之间互不相容的时候,这种常见的自定义在政治层面经常是同一的。”[1](20)换言之,经济举措的失当,与不成熟的政治指向不无关联。大革命的领导者旨在颠覆与旧制度相关的一切社会特征,这当然包括原先行将就木的经济体系。但其强有力的政令不能掩盖他们自身特有的阶级属性。指券体系的推行,从根本上来说,毋宁是扫除封建障碍,并刺激工业资本持续发展的政治行为。这与贫苦民众的根本需要大相径庭。因此,为应对“一种群众的情感:对工业资本主义潜在上升的一种怀疑的憎恨,工业资本主义发现了唯一的出路:一种教化的专政高于需要的远景”[1](106)。这表明,革命的自由只能是资本积累的自由。至于被这一目标所策动的大部分民众,则始终被排除在外。为弥补这种缺陷,革命者只能通过政治口号的形式,在宣扬理性的同时,一方面冠之以抽象的政治平等,另一方面又对其反对意见实施残酷镇压。尽管他们“通常都炫耀自己的理念具有‘最高的合理性’。但事实上,他们都是理性最差的学派。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国家干预论的主导精神”[4](204-205)。值得一提的是,脱离群众的行政指令逐渐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威。它在启蒙理性的包装下又引申为绝对平等的幻想。而盲目的“均权主义……既摧毁传统的等级制度,同时又使这种制度固定化,因为它在掏空等级制度内容的同时,又以法律的形式使之无限延续下去。”[6](116)
毋庸置疑,指券体系的失败是抽象的平等在经济层面掉入专制陷阱的开端。从主观上讲,大革命中的所有派别都以实现广大群众的自由与民主为己任,但狭隘的经济诉求,在客观上无法承载如此长远的政治理想。它势必演变成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角力,并以少数人的独裁专制宣告终结。革命者们不得不确信,“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经济规律’都不能抵制人类需要的动力,更进一步而言,他们是武断的、无拘无束的梦想家,对他们来说,绝对的平等高于自由。”[1](5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对抗造成了国家对广大民众经济平等与政治自由的双重否定。所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共和国宪法从来没有确实变做一个‘民主政体’;在‘自由’与‘平等’的假面具之下,暴虐和专制横行无阻。”[7](239)这无疑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共和国赖以为系的平等与自由理念,将蜕变为粗暴的政治教化。而领导者拥有这项权力的合法性也不取决于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可。为保证其政令的权威性,一种更为抽象的衡量标准势在必行。于是,愈加极端的政权形式呼之欲出。这无疑为雅各宾派“德性共和国”的执政理念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二、“政治道德”乌托邦与人民主权边缘化:道德预设还是政治预设
雅各宾主义的兴起,是大革命内部诸因素互相作用的产物。按费赫尔的理解,它是“意想不到的、不可预知的历史时刻三种趋势空前汇聚的结果,……这三种潮流分别是:山岳派左翼激进派的政治运动,愤激派对社会与经济的煽动,指券内部动力体制的呈现”[1](20)。可以肯定的是,雅各宾派的执政理念充斥着激进的革命诉求。后者试图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在平复所有困扰共和国问题的基础上,构筑完全正义的政治体制。用罗伯斯庇尔的话来说,该派别追求的目的就是使广大群众“和平地享受自由与平等”,并建立“永恒正义的王国”。[8](170)
然而,为罗伯斯庇尔所奉行的政治原则,在强调全民参与的同时,还隐含着一条先验的道德预设,即共和制度的良性运行与广大民众的善良意志并行不悖。因此,“这种共和政治可以用现实的完整形式达到公意,前提是所有参与者在道德上都是善的。同时,在一个腐朽文明当中道德的善只能通过一个正确的共和政治来获得。雅各宾派坚信,他们通过宣称道德政治和政治道德来达到目标。”[1](71-72)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如何看待政治与道德之间的铰合关系?而该设想被纳入民主实践后,能否真正兑现它的诺言?这些都是雅各宾派之于革命前景所必须回答的难题。历史证明,他们早已误入歧途。其中涉及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从宏观上来看,为政治道德所建构的“德性共和国”不啻为狭隘的复古主义幻想。它从来不具备稳固的现代政治基础,因为其合法性不以刚性的律法为必要条件,而是以柔性的道德意志为基本前提。所以,“在雅各宾派的解释中,‘共和国’包含两个实质性要素。首先,从与个人野心、贪婪和利己主义相比,它被看作是‘社会’时空扩展和集体意志。其次,与所有革命者中的政治敌人相比,它被看作美德的体现和协商,而这些政治敌人在教化的政治和政治化的道德中显现出‘腐败’和‘邪恶’。”[1](74)抽象的衡量标准,使国家在区分敌友时变得武断且随意。作为行政指导的公民德性,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解释,只能流于主观的肤浅直觉。反映在群众层面,就是民粹主义的舆论或意识形态;而它一旦为领导者所采纳,必然产生排它性的权威崇拜。上述两种情形,无一例外地出现在雅各宾派统治的共和国之中。因此,虽然“革命召唤了一个新的阶级(人民群众——笔者注)参与政治生活,……但舆论变成了一种力量,必须和它商量,并倚重它的协助,借以支持政府”[9]。它既是群众的公意,也构成领导者甄别善恶的直接来源。于是,在道德至高无上的口号下,“德性和恐怖盛极了一时;因为‘主观的德行’的势力既然只能建筑在意见之上,它就带来了最可怖的暴虐,它不经过任何法律的形式,随便行使权力。”[7](421)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由意见形成的道德暴力,最终的受害者却是产生它们的普通民众。
其次,从中观上来讲,由政治道德所引导的民主体制,实则是一元独裁专政对多元党派政治的无情压制。它既体现为雅各宾派对人民主权的践踏,也意味着政党之间的平等协商化为泡影。这是革命者对代议制民主进行片面理解所造成的恶果。尽管雅各宾派承认“政府的实际权力应该由选出的有能力处理国家事务的少数个体来执行”,但“他们也是卢梭的追随者,追随他对代议制的批判及其公意观念。……他们坚定地相信‘人民总体上不能管理自身’”。[1](99)如此一来,雅各宾派就切断了民主选举与行政权力之间的有机联系。并将对“德性共和国”的期许,转变成对人民与其它政党的双重敌视。在不确定公民是否具有他们所要求的高尚品德之前,为后者所选出的政治代言人显然不具有相应的合法性。况且,“在政治异常兴奋和‘狂热’的时候,……新的最高统治者通常都会膨胀得与所有部分都不相称,甚至在新的政治形而上学中得以神化”[4](211)。被神化的正是雅各宾派尤其是罗伯斯庇尔对自身执政理念的盲目自信。他们自认为是政治道德的代言人,且天然是衡量民众善恶与否的唯一权威。故而,“在政治上,雅各宾派不容忍任何竞争对手。……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中心、一个观念、一个主权是多么自然。……即在‘德性共和国’中只能有一种意志,导向中心的意志。”[1](116)在这点上,雅各宾派虽然是绝对平等主义的支持者,但他们自身却游离于这种平等之外,并成为高于乃至主导平等的世俗神祗。再次,从微观上来说,被政治道德所裹挟的普通公民与政策的执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藩篱。费赫尔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当雅各宾派“很少任用全权代理人和地方活动分子时,他们是雇佣官僚主义者而不是代表,这些官僚主义者既不是被选出来的也没有地方根源,他们直接依靠中央权威”[1](95)。这就使政府与公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脱节。作为领导者对群众的组织形式,它直接反映出雅各宾派对待人民群众的两面态度。革命者既期望他们的政治构想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得以实现,又担心后者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处于失控状态,从而危及自身的政权。由此可见,“革命精英对群众实行组织化的做法,突出地反映了他们对于群众的一种既爱又恨、既容又怕的复杂情感。”[5](306-307)这与政治道德所要求的一元政治不无关系。为罗伯斯庇尔所强调的公民道德优先性,实则是雅各宾派对民众实施教化的政治权威性。而该团体内的领导成员,自然就是高于普通民众的道德监护人。执政者与群众的差异化意在营造群众自身的同质化。经过教化的“‘人民’成为……善良意志的不加区别的总和:经此,代表制被排除了,革命意识于是以个人意志为名义,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构了一个想象的社会”[6](40)。显而易见,革命者与民众之间的隔阂,毋宁是抽象的道德理念应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时,必然遭遇的社会后果。
实际上,雅各宾派的“德性共和国”之所以沦为独裁专制的庇护所,根本上导源于它所奉行的政治道德理念曲解了平等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罗伯斯庇尔曾一再强调美德与平等之间的同一性。他指出,“我所说的是公共美德……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因为共和政体或民主政体的实质是平等,所以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热爱祖国必须包括热爱平等在内。”[8](171)但与共和政体相结合的平等,在革命者看来,还是人民群众摆脱王权达成普遍幸福的必要前提。因此在罗伯斯庇尔那里,较之于个体的自由,平等往往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这就使以平等为内核的政治道德成为实现公民幸福的手段。于是,道德自身下降为一般的幸福原则,并根据领导者的主观意愿,被强行投放于公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如此一来,必然在国家权力方面引起巨大的恶果。“正像它在道德方面所造成的一样,……主权者想根据自己的概念使人民幸福,于是就成了专制主义;人民想放弃自己追求自身幸福这一普遍的人类要求,于是就成了反叛者。”[10](209)不难看出,平等对自由的压制,意味着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雅各宾派在突显公民幸福的同时,又“把国家和社会、政治义务和道德义务混为一谈”,这毋宁是其“形而上学的国家论的主要错误”。[11]与之相反,正确的政治准则“绝不能从每一个国家只要加以遵守就可以期待到的那种福利或幸福出发……而是应该从权利义务的纯粹概念出发”[10](145),这就要求自由的个体对道德原则的自律性接纳。换言之,指引共和国前行的不是以绝对平等为标志的政治道德,而只能是彰显个体自由的道德政治。雅各宾派正是由于歪曲了道德之于政治的绝对优先性,才逐步否定了人民自由在政治实践当中的积极作用,进而以抽象的道德专制取而代之。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自由的消失与道德专制的出现,却是大革命向往自由的结果。这就涉及绝对自由的悖论,及其对大革命进程造成的深远且负面的影响。而后者毋宁构成大革命失败最为内在的哲学原因。
三、“绝对自由”大冒险与革命正义虚无化:哲学实验还是政治实验
将大革命只看做纯粹的政治事件,并不足以涵盖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在更为宽泛的层面上,它还是抽象的哲学自由遭遇现实的世俗权力时,带来的全新体验。可以认为,“大革命闯进了一个真空地带,或者不如说,它在直到昨天还属于禁绝地、但突然间被僭入的权力领域里迅速蔓延开了。……意思就是说,公民社会……正在摆脱象征性的国家权力,同时摆脱国家的法度。”[6](37)由此可见,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意在同之前传统的权力机制彻底决裂。这表明,象征王权的政治体系及其运用的封建法度,必然成为大革命所要清算的对象。反映在哲学领域,它包括形下与形上两个层次的内容。
一方面,大革命对封建专制的批判,要求彻底祛除王权之于自由的荼毒。因此,对后者的象征性代表——国王的审判与处决,在革命者(尤其是雅各宾派)看来,就显得尤为重要。费赫尔认为,该举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作为哲学的革命者,他们想监督君主政体原则象征性的葬礼,作为一种实现哲学承诺的行为……他们想在将要形成的新共和国德性和革命矛盾的过去之间划一条明确的区分界线,……国王的死刑看起来完美地为这两个目的服务”[1](129)。其中,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即审判并处决国王的正义性何在?能否妥善地回应该质疑,直接关系到革命运动的合法性地位。然而,在费赫尔看来,革命者的行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后者甚至只能被视为政治上消极的逃避。他曾尖锐地指出,“当我们为了反动地惩罚哲学的罪行而成为胜利者时,同意特赦是集体怯懦的行为,也是极其专制的基础,而不是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建构行为。最后,在政治上,哲学实践的血腥应用是通过斩除一个人而排除一个系统的象征,这是一次整体的失败。”[1](126)毋庸置疑,接受惩罚的国王只是抽象的封建专制象征性的牺牲品,而革命者对他的判决却将非理性的暴力因素引入法律当中。因此,专制的毒瘤并没有被根除,而是以审判的形式完成了由君主到革命者的让渡。之后雅各宾派的独裁政治在实践层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这一行为根本不具有它所宣扬的正义性,而革命的合法性也只能从法律之外的领域获得佐证。
另一方面,庶民对王权的战胜,最初表现为公民自由对之前法律制度的全面否定。故而,革命是超然于原先正义体系之外的全新体验。它意味着一种编年体上的断裂。鉴于此,“国家再生需要新人和新习惯,人民要在共和主义的模子里被重新锻造。因此,日常生活的所有犄角旮旯都要被检查,找出旧制度的腐化痕迹后彻底扫除,以做好迎接新制度的准备。”[12]但行之有效的重塑方案却没有被及时提出,反而以笼统的自由观念敷衍了事。其恶果毋宁是公民对自由的摈弃。这集中体现为,“在新的、由获胜的人民从君主那里借用的主权概念中,……它可能会陷入自相残杀的斗争之中,从而使国家难以控制。它可能蕴涵着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暴,从而使其成为自己的最坏敌人,并把民众带入到一种呼唤着‘我们不想要自由’的集体政治歇斯底里症之中。”[4](210)这在费赫尔看来,毋宁是关于自由的空洞说辞,向历史开出的空头支票。它必然伴随着理性的真空以及蹩脚的民主与专制思想的媾和。
自由的得而复失及其与正义之间的张力,实则是大革命在哲学层面遭遇危机的直接表现。或者更进一步来说,自由与正义各自的悖论,毋宁是作为哲学实验的大革命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从‘哲学’得到第一次推动。但是这种哲学起初只是抽象的‘思想’,不是绝对‘真理’的具体理解——两者之间有着一种不可测度的区别。所以,‘意志自由’的原则反抗着现行的‘权利’。”[7](417)换言之,催生大革命的自由理念,是与现实相分离的抽象的哲学设想,它本身并不具备健全的政治实践方案。内容的贫乏导致它在弃绝现行制度后,变为纯粹的否定力量,而不具备丝毫的建设性。由于自身的无规定性和破坏性,它只能表现为革命的狂热。后者“所希求的是抽象的东西,而不是任何有组织的东西,所以一看到差别出现,就感到这些差别违反了自己的无规定性而加以毁灭。因此之故,法国的革命人士把他们自己所建成的制度重新摧毁了”[13]。
在这样的情形下,以稳定的律法为前提的正义观,显然与大革命对正义的定位扞格不入。在以绝对平等和道德政治为目标的绝对自由中,“一切社会阶层,都消除了。……它的目的就是普遍的目的,它的语言就是普遍的法律,它的事业就是普遍的事业。”[14]于是,革命的正义只能表现为不断地清除与自由相背离的人与物,从而丧失了它对自由的规约作用。与此同时,“哲学的革命者……这种巨大的、对所有类型苦难的敏感,……使他成为绝对善的化身,……因此,在自由辩证法的旋转轴上,他自由地做任何事情。”[1](82)也就是说,一旦绝对的自由使普遍的律法转化为个体的情感,革命的正义也就因此抛弃了它的理性支撑。当原先的革命者成为善良意志的代言人,并再度走上神坛时,所谓的正义就只能充当他们在任意杀戮后,为其辩护的丑角了。所以,绝对的自由及其所彰显的革命正义,“所能作的唯一事业和行动就是死亡,而且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实质的死亡,因为被否定的东西乃是绝对自由的自我的无内容的点;它因而是最冷酷最平淡的死亡,比劈开一个菜头和吞下一口凉水没有更多的意义。”[2](120)绝对自由毁灭了正义的可能性,也从哲学层面说明了大革命走向专制的必然性。不被理性法则所制约的抽象观念,在现实层面的盲动,毋宁是一次哲学的冒险。而其代价,则是大革命失败后,继任者连续的专制统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革命是以启蒙主义为先声的政治实验。在它的背后,隐含了政治道德以及绝对平等的观念同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它不可避免地诱发了人民主权的缺失,并促使道德专制的形成。就这点上来看,大革命的失败作为政治实践的失败,无疑是以强权手段为先导的“救赎政治”的失败。然而,它还是以人类自由解放为目的的哲学实验。其中充满了对永恒正义和绝对自由的强烈期许。但抽象理念与具体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酝酿出更为极端的血腥杀戮。而这也造成了大革命对启蒙主义深刻的反启蒙回应。不得不说,“大革命的得失主要还不在于原因和结果如何,而在于一个社会向着它的所有可能性敞开了。大革命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和一种政治实践,从此我们不断地生活于其中。”[6](69)因此,当大革命遭遇政治和哲学的双重困境时,它所倡导的民主理想就伴随着行政指令的常态化而被革命自身所冻结。但它与启蒙主义割舍不了的特质,及其对自由和德性的浪漫追求,又为现代性的发展开启了新的道路。
四、结语:法国大革命失败了吗?
诚然,哲学上过于偏执的道德理想,与政治中亟待完善的社会实践,使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最终走向完结。但在现实维度,它只标志着一种特定民主模式的失败。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其巨大的社会意义是通过一种早熟的人类解放探索,为今后的民主实践提供更为稳健的操作方式。费赫尔只看到了大革命中抽象的道德诉求与具体的政治革命之间存在的张力与断裂,而忽视了二者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有机统一。虽然大革命(抑或雅各宾主义)在政治上走向了死亡,但从另一个侧面,它又为后人在哲学层面重新解读启蒙和现代性留下了无法回避但广袤无边的反思场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5]因此,当之前处在哲学构想层面的政治道德愿景,一旦获得相应的历史条件的支持,就必然会发生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进而实现它与政治实践的辩证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视为人类向往自由、平等的道路堵塞,而应将其视为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一个能动环节。其政治主张背后的哲学理念,既是指引后世继续斗争的积极乌托邦,又构成将其变为现实的激进需要。费赫尔的观点只停留在对大革命历程单纯的反思维度,而没有将它的精神实质进一步升华至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层面。套用马克思的话头,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性反思,将作为指导未来革命的理论坐标。它的积极作用不在于它以思辨的形式完成历史的跨越,而是通过展现正确的历史演进方向,为人类的最终解放提供以资借鉴的参考,并为其树立坚定的实践信心。而“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16]。
由此可见,对大革命历史意义的解读,应当以辩证的唯物史观为切入点,挖掘出它在人类社会的概念史演进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理论层面来说,对大革命内涵的揭示,决不是要脱离它的历史区间以思辨的形式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是要通过展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缩短和减轻历史进程中不必要的“痛苦”。[17]只有以史为鉴,在唯物史观的领域中,充分看到大革命历史性失败当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才能彰显人类解放这一崇高诉求之凤凰涅槃。
[1] 费伦茨·费赫尔. 被冻结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2]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3] 王养冲,王令愉. 法国大革命史[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07.
[4] 费伦茨·费赫尔. 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 高毅. 法兰西风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6] 弗朗索瓦·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7]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8] 罗伯斯比尔. 革命法制与审判[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9] 保尔·拉法格.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4: 45.
[10]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
[11] L. T. 霍布斯. 形而上学的国家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70.
[12] 林·亨特.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3.
[13]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 15.
[14]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116.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3.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57.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101.
[编辑: 颜关明]
The frozen democracy: bankruptcy of political morality and the paradox of absolute freedom
WEN Quan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for its radical political ideas and immature democratic practices. Especially in the system of western political,the terrorist autocracy Jacobinsism has been repeatedly refut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Feher considers that the state intervention policy born out of “the voucher system” and the false presuppos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virtue” are the inherent causes for the revolution to turn from democracy to autocracy. They project the abstract moral ideals to the specific political sphere,and further generalize it into all aspects of the society by means of violence,which enforce a poor unity of morality,nation and democracy. When moral standard is embodied as a secular revolutionary leader,political democracy is to be replaced by moral autocracy,which essentially results in that absolute freedom at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is applied to the real society. Therefore,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is,in the final analysis,a failure of the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 But the connotation of revolution reveals that revolution should not break away from its historical range to go beyond reality in the speculative form,but reduce and lesse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unnecessary pain by showing the laws of economic movement in modern society.
Feh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Jacobinsism; democracy; autocracy; virtue republic; absolute freedom
D091
A
1672-3104(2016)04-0124-07
2015-11-08;
2016-02-2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0AKS005);黑龙江省社科重大委托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08A-0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克尔凯郭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比较研究”(2015M580417)
温权(1987-),男,山西太原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布达佩斯学派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