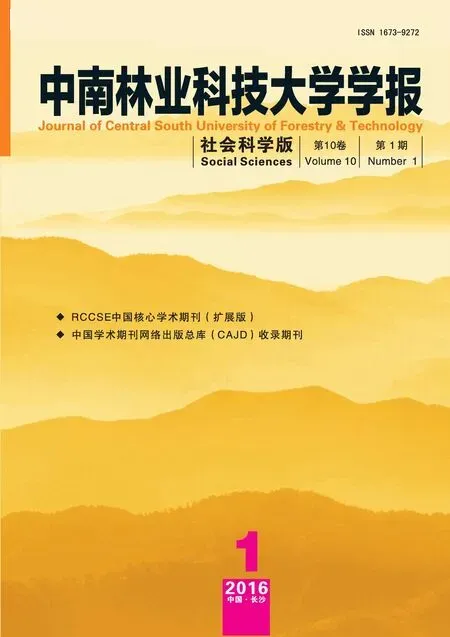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研究
——以湘西永顺地区为例
季轩民,喻文德
(吉首大学 哲学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研究
——以湘西永顺地区为例
季轩民,喻文德
(吉首大学 哲学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武陵山地区处于武陵山片区,主要以山区为主,人口大多是少数民族。由于其天然的自然条件,武陵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生态伦理观念。文章以湘西永顺地区为例,探讨了少数民族与植物、动物、水源、建筑的生态伦理表现,并通过其特征对少数民族中的生态伦理价值进行研究。
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湘西永顺
武陵山片区地处湘、鄂、川、贵四省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内居住苗族、土家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武陵山片区大多属于贫困山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少数民族人民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也就形成独有的生态伦理观。文章通过研究湘西永顺地区生态伦理观来探索整个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因此,对整个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湘西永顺地区的生态伦理表现
生态伦理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关于自然生态环境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人与自然在和谐相处的环节中蕴涵着伦理思想,包括人与植物、动物、水源、建筑等相处活动。其形成的生态伦理的最终旨趣是志向行动和实践,通过改造人类的内心、行为、生活方式使人类适应于自然,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1]
在我国武陵山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有的是受到宗教信仰影响、有的以禁忌习俗为标准、有的以乡规俗约为基准、有的收到生产劳动的影响等。湘西永顺地区属于土家族聚集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以及生态优势,因此形成了丰富的伦理思想观念。在土家族人民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体现不同的伦理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与植物的万物平等
我国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文明是一种农耕为主的文明,农耕又主要体现在人与植物的万物平等的相处过程中。在人与植物相处过程中尤其注重对森林树木的保护,其中蕴含了人与植物的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思想。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视,农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退耕还林”在湘西州永顺县如火如荼的开展。湘西州永顺县大山深处就存在着一处实验站——湘西州森林生态研究实验站。这是在湘西州政府的支持下建设的生态林实验站,主要以“林业研究”进行生态林的构建。生态林根据当地山势变化进行植物的种植,山脚主要以桃树、李树、油茶为主,山腰则以油桐、松树为主,山顶则以樟树为主。这里是国家油桐种质收集保存库,面积达52.6公顷,收集油桐种源213个品系。在湘西永顺土家族人眼中,森林对于他们来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他们经济、水源、环境等各方面来源,因此他们不乱砍乱伐、过度开垦、尽可能保护着每一棵树木,实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宫殿里,不仅可以感受到了浓厚的自然气息,还感受到了人与植物万物平等的情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这对加快生态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人与动物的平等共存
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动物的存在也有独特的认识。老子说过“圣人初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第二章)老子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随着“天道”运行的,顺道而行则可以发展,逆道而行则灭亡。而在人与自然相处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无为”,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礼记•祭义》中也曾记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所以,当地人们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要遵循这一法则,不滥捕滥杀,不对动物赶尽杀绝,要给动物足够的生存空间,以让其生存。有些民族甚至将动物视为自己民族的图腾、神灵,不准扑杀,要给予尊重、保护等,更体现了万物有灵的观点。
在湘西州永顺县的生态森林实验站还存在着这样一幅画面,在森林之中有很多的牛群和羊群在放养,山下有狗在四处张望,人们则坐在路边休闲、相互攀谈。这种人与动物平等共存的画面恰恰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这种尊重动物的做法不仅有利于调节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实现生物多样性发展,还可以推进少数民族的生态多样性建设。
(三)人与水源的良性互动
武陵山地区以山区为主,同时又离不开水。山水之间,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发展。老子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因此,少数民族对于水源的保护也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认为,水源是森林、土地、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如果没有良好的水源,整个生态系统不能健康发展。所以,在生态环境中,水源的保护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当地人们还崇拜天然的水资源,甚至直接引用由山中流出的水,他们认为那是天然的水,对于身体最有益处。这种人与水源的良性互动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
在距离湘西州永顺县清坪镇政府不远的地方存在着一条生态河流——洞坎河。洞坎河与张家界相通,有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以及生态优势。据说洞坎河是他们的母亲河,当地村民的水源也都来自这条河流。洞坎河水清澈见底,缓缓而流,两岸的的绿色植物更是争相开放。基于当地人们对于水源的保护,他们也就形成了适合土家族民族的道德意识和规范:禁止向河中抛扔垃圾;禁止在河中游泳;禁止随意开挖河流,堵塞水源等等。这种道德意识和规范有利于洞坎河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当地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促进作用。
(四)人与建筑的文化传承
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体现在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人与水源的相处上,还体现在人与建筑的相处上。建筑的建设不仅可以表达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还可以体现出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通过对少数民族建筑伦理的研究,有助于对整个武陵山区的生态伦理研究提供有效价值。
永顺是土家族聚集地之一,土家族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这里还存在着中国土家第一村——双凤村。因此,土家族人们把他们的文化都渗透到建筑中去。土家族的建筑以吊脚楼为主,其建材主要是树木,而吊脚楼的构建又与当地的环境十分的契合,依山而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种以建筑为主的文化传承为生态伦理观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并且不断丰富了土家族生态伦理观的内涵。
除此之外,永顺地区还存在着世界文化遗产遗址——永顺老司城遗址。老司城内有千年祖师殿、彭氏宗祠、摆手堂等文物建筑,这种文物建筑展现了土家族的文化制度。对于民族地区发展,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意义。
不仅如此,老司城的生态旅游发展也蒸蒸日上,这种人与建筑的文化传承对于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作用。
二、湘西永顺地区的生态伦理特征
从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现状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在与自然长期相处中逐渐形成了少数民族独有的生态伦理特征,以永顺土家族为例,湘西永顺地区的生态伦理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重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观
武陵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山多地少,虽然以农耕为主,但依靠的更多是山区森林带来的经济收入。俗语说“靠山吃山”,武陵山地区少数人民正是基于此条件上发展自己民族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并在开发森林的过程中尤其注意过犹不及的道理。森林不仅本身具有极大的木材价值,还可以防止山区水土流失,防止洪涝灾害等等。所以,“如何保护好森林,如何实现森林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便成为刀耕火种民族农耕文化传统的最本质和最有特色的内涵”[2]。武陵山地区的少数民族深谙这个道理,因此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不打破大自然本身所具备的生态系统,尽可能使生态系统自我完善、自我循环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在其他方面,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湘西永顺土家族在这方面体现尤为明显。土家族通过建设生态林,一方面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环境;另一方面,通过生态林所产生的果实来换取经济所需,而达到不用乱砍乱伐并保护树木的可持续发展观。除此之外,土家族还利用本身特有的条件开展生态旅游,例如芙蓉镇景区、猛洞河漂流、老司城遗址等等。通过将这些资源完善打造不仅可以有效保护,还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还可以为子孙后代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少数民族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观与其当地的生态模式以及文化形成了良性互动,体现着人与自然环境的融洽与和谐,更符合人类共同利益。[3]
(二)万物有灵的生态伦理观
由于自身条件约束,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经济类型基本属于摄取型经济,他们所从事的捕猎、伐木等活动都是依靠大自然的供给。所以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在原始生态观上形成了万物有灵的普遍信仰。他们认为不仅人有灵魂,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等都具备灵魂的。人类不仅要依靠他们生存,而且在死后还要归于山区土地本身,与万物平等,甚至说人与宇宙万物的灵魂是互通的,可以相互转化。万事万物也通过图腾崇拜、神灵崇拜、自然崇拜等形式在人类生活中有所表现。“人们敬畏自然就是对神的尊敬,破坏自然就是对神的冒犯”[4],因此,武陵山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这种万物有灵的生态伦理观念对与保护当地生态生态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通过对永顺地区土家族实际调查发现,土家族也有着万物有灵的说法。比如土家族信仰猎神,在打猎之前必须祭拜猎神,以获取猎神的恩准。在打猎过程中,会有所选择,对于刚生下的、幼小的、瘦小的动物给予放生。他们还认为如果过度打猎,得罪神灵就会受到报复。因此土家族人民通过将这种威胁寄托于“万物有灵”来为自身民族提供力量的帮助。土家族的这种生态伦理观虽不像专门法那样有明确的系统性规范,但对于人类的行为却起到了约束作用,这对维持当地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5]
(三)适应环境的生态消费观
武陵山地区地广人稀,生态资源有限,加之生存环境的不可选择性,少数民族只能依赖现实的自然条件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同时也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6]因此,这就决定了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消费观念——生态消费。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认识到自身环境资源的不足,要想在既能保证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不破坏自然环境,只能采取适应环境生态消费的伦理观念。生态消费也就决定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湘西永顺地区的土家族人民在这一点上体现尤为明显。土家族人民意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如果过度利用势必会导致大自然的报复,因此他们在于自然相处时采取“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的做法。在适时的节气砍伐树木,于此同时还要补充新的树苗;在狩猎的时节进行猎杀动物,并注重对小动物的保护;在冬季大雪覆盖季节,尽量不摄取资源等等。土家族人民的这种适时利用、适度消费、保持生态循环的消费观对武陵山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土家族人民的这一生态消费观有效保持了生物多样性,解决了大量自然资源。这种从民族生存与发展中形成的生态伦理观念有效防止了过度猎杀或摄取自然资源,从而避免动植物等物种灭绝,对维持人与自然平衡具有重大意义。[6]
(四)普遍约束的宗教信仰观
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在推崇“万物有灵”的生态伦理观同时离不开宗教观普遍的约束。少数民族在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所形成的尊敬自然、敬畏神灵的生态伦理观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规章制度,但其中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对于人们普遍还是有约束力的,有的通过非强制性观念和舆论的形式,有的是通过制度形式,用来约束和限制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7]
少数民族本身就是具备宗教信仰的民族,于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伦理思想大多都受到神灵法则的约束,这种超自然力的宗教禁忌成为民众行为的道德约束。[8]通过在湘西永顺的实地考察可以发现,土家族并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但他们依旧信奉多种神,大多把自己的祖先当作神灵,称为祖先神。所以土家族宗教信仰的生态伦理观一般都可以表现出土家族的原始社会的风貌,只有少数才反映着阶级分化以后的现象。永顺老司城还建有把部大神庙、摆手堂等。除此之外,在生产力及其低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土家族崇拜多神:“山神土地”管坡上五谷;“家先土地”管家禽家畜;“五谷神”管五谷的神祗;“阿密嫲妈”管保小孩的成长;“四官神”是致富神管六畜。[9]正是通过这种对神灵的崇拜体现在土家族人民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受到约束。虽然说宗教信仰及崇拜并不能为人们保护自然的必要性提供非常科学的依据,但是其敬畏自然的理念就是生态思想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对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10]土家族的这种宗教信仰生态伦理思想对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体现了宗教信仰生态伦理在保护生态中的价值。
三、湘西永顺地区的生态伦理价值
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难题,空气雾霾、土地沙化、频繁地震、洪涝灾害等,引发了进一步的生态危机。而生态伦理本身就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这就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伦理发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价值的作用,实现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伦理价值。
(一)发展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
生态环境是体现生态伦理价值的重要方面,生态环境好了,生态伦理也就具有发展的价值,如果生态环境差,也就意味着生态伦理价值的一无是处。所以,武陵山地区的生态环境一直处于非常优势的地位。武陵山地区大多具备崇山峻岭,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溪流,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也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巨大的贡献。武陵山地区的少数民族适应这种生态文化,并创造了独特的生态环境。少数民族这种遵循生态规律,“根据民族地区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得处理少数民族和自然的关系”,将民族发展与生态环境相结合,把伦理道德与生态有机统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健康、持续和稳定发展。[11]
这种发展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的生态伦理价值在土家族人民的生活中体现更为明显。在永顺地区,森林生态实验站、洞坎河流、不二门森林公园、老司城等都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发展,并带来了土家族人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一互动实现了良好的生态伦理价值。除此之外,土家族人们还合理开垦土地,促进农业发展。在调查中发现,永顺地区的整体环境非常优美,空气非常清新。由此可见,“民族生态意识浓厚的地区,生态就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护”,[12]实现生态伦理的价值蕴含。
(二)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①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2-11-8通过十八大报告可以看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对于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来说,既可以抓住机遇,促进社会发展,又可以进一步建设当地的生态文明。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我们应对生态系统退化、生态危机、资源紧缺等问题的重要资源。通过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价值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武陵山地区的生态伦理思想作为人类适应环境的独特方式和文化机制,还是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基础。[5]湘西永顺地区少数民族在建设自身生态文明的同时,必须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并与生态伦理价值层面相融合,最终贯彻和落实到社会发展中去。所以,要建设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发展就需要充分探寻和研究他们的生态文化传统,使其与生态文明建设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三)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处基础之上的道德规范,其中蕴含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形成民族团结、民族力量的重要因素。它对团结部族成员、增强安全感,维护民族心理整合凝聚起着重要作用。[13]所以,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生态伦理观对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团结稳定作出了巨大帮助,保护了民族繁衍生息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14]我们可以看出和谐社会就是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建设和发展武陵山地区的生态伦理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武陵山地区的生态伦理价值。不仅如此,民族生态伦理还是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谐社会评价生态伦理善恶的标准是看其是否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8]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伦理决定着人与自然相处的平衡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价值作用,维护民族团结,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建设。
四、结语
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虽然对促进武陵山地区发展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自身的不足以及局限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武陵山部分地区也陷入生态危机,武陵山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受到冲击和挑战。所以,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也是我们刻不容缓的责任。
[1] 何怀宏.生态伦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
[2] 江 帆.生态民族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90.
[3] 曾 易.和谐社会建设中民族伦理的价值意蕴[J].广西社会科学,2008,(5):44-49.
[4] 马宗保,杨文笔.视觉转换与人文生态价值的时代再造[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6):54-58.
[5] 王景华,刘东英.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研究述评[J].民族论坛,2013,(11):76-81.
[6] 李良品,彭福荣,吴冬梅.论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与生态环境[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3):139-145.
[7] 宴 辉.伦理生态论[J].广东社会科学, 1999,(5):71-76.
[8] 白葆莉,冯昆思.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J].大连大学学报, 2007,(2):99-102.
[9] 土家族:历史久远的毕兹卡[EB/OL].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40722752-1.htm,2014-07-09/2015-11-18.
[10] 刘俊宇,邹 巅. 湘西少数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态伦理学意义[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8(2):48-50.
[11] 贺金瑞,熊坤新,等.民族伦理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331.
[12] 李本书.善待自然:少数民族伦理的生态意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89-95.
[13] 陈 旭.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文化功能与现代价值[J].新疆社会科学,2010,(4):96-99.
[15] 胡锦涛.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厦门日报,2005-06-27(1).
A Study of Ecological Ethics of Ethnic Minorities of Wuling Mountain——A case study of Yongshun of Western Hunan area
JI Xuan-min, YU Wen-d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Hunan, China)
Wuling mountainous area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mainly mountainous areas, most of the population are ethnic minorities. Because of its natural conditions, natural Wuling mountain area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process of get along with nature for a long time to form the unique ecological ethics. Yongshun of Western Hunan area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inority with plants, animals, water,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an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ecological ethics value in research.
Wuling mountainous areas; ethnic minorities; ecological ethics; Yongshun of Western Hunan
F205;B82-058
A
1673-9272(2016)01-0011-05
10.14067/j.cnki.1673-9272.2016.01.003
2015-12-13
湖南省教育厅开放基金项目“和谐社会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生活化研究”(15K104)。
季轩民,硕士研究生。
喻文德,副教授,博士;E-mail:xuanminji1991@163.com。
季轩民,喻文德. 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研究——以湘西永顺地区为例[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10(1): 11-15.
[本文编校:罗 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