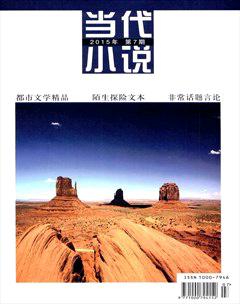看不见的伤疤
余和鲲
海浪好像一条绵延的白色丝带,撞击到岸上的那一刹那被撕裂成一块一块的碎片,就好像我的记忆一样,碎片化。
离开学校后,我每个夜晚都会做噩梦,我梦见许许多多的黑色的暗物质由远及近向我袭来,然后幻化成巨大的恐惧,直到这种恐惧把我惊醒。我醒来后常常回想母亲在一片吵闹中走远的情景。然后我又会睡去,直到小兰的面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清晰得不像是梦。
我回到老家的那片麦田,那里的血色的夕阳没有改变。我曾经在这片金黄色的麦田躺下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没入了地平线,然后一种刺骨的冷击打着我冰冷的心。我的汗和泪流淌在麦田里面,逐渐沉入到土地中。为了母亲的离去,我用手使劲捶干裂的麦田,然后又昏昏欲睡。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
母亲入狱后,我便辍学了。
我新来的这个城市经常阴雨绵绵,一点一滴直到天明,就好像情人眼里的泪。汽笛声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天空显得格外不明显。就好像我之于拥挤的人潮。
我能够感受到这里面的阴暗,每个矮小的出租屋都是这样,这一个出租屋也不例外。
有些记忆和伤痛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除,它就像生在脚上的冻疮,时不时在你温暖的时候提醒你的痛痒。这种痒,你无法用手准确地抠到,只能用心去感知它的折磨,而它也会逐渐逐渐把你奴役,就好像是被关在一座壁垒森严的监狱。
我和父亲在一起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搬家,我们不断地搬家。我们从老家出发,那个曾经鸡鸭成群、嬉笑怒骂的村子。现在因为人去楼空变得索然无味。曾经那些被村里的人争得死去活来的橘子树和柚子树都已经在岁月的颠簸中颠簸得只剩下孤零零的枯木。那些曾经油菜花灿烂无比的田地也已经长满杂草。我们村和大多数因为外出打工而人去楼空的村落一样荒芜,安静。
仿佛时间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地方凝固了。继续在这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方生活注定没有前途,父亲和我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离开这个叫做长沙村的地方的。
我们搬到了一个砖厂附近,盛夏,烈日会永远照耀着我们那间矮小又破旧的出租屋。父亲的身躯在烈日下暴晒,他的肌肤因为汗液的洗涤变得油亮油亮的,远远看上去就好像一尊古希腊铜像。
在这个烈日炎炎的盛夏,即使是一股细小的微风也会让我感到异常的兴奋和惬意。下班后,我在夕阳下享受着从后山来的微风。喝着几口家乡带来的凉茶,驱除疲惫和苦闷,和旁边的几个同事谈古论今,这种抱团取暖的舒适显得珍贵而温暖。
父亲认识一个叫做兰松的工人,他身材矮小,就好像患有侏儒症一样,但是他人很实在,很老实。
兰松有一个女儿诗柔,一个穿着粉红色裙子的女孩,微带着小麦色的皮肤看起来干练勤劳健康,乌黑的头发瀑布般垂直在肩上,瓜子型的脸蛋微微透着淡雅的红晕。清澈明亮的瞳孔,长短适中的睫毛微微地颤动着,薄薄的双唇如一朵淡雅的小红花。
这种女孩在我的记忆深处是一道明媚的渊薮,在她身上有一种意蕴无法缱绻。
她就好像一幅不受约束的山水画,也好像是一首音律绝美的歌。歌词里面有一种无法排解的抑郁,我想到的歌词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天空中琐碎的晚霞印照着她的美丽,绵延的秋色水天衔接。远处飞来的秋蝉在后山拥挤的绿色中隐藏,诗柔也喜欢后山的景致,只是因为在那翠绿的中间有一种叫做折耳根的东西,她非常喜欢这种学名叫做鱼腥草的植物。
后山的凉风吹动着她脸颊的发丝,也吹动了我。我们在一片翠绿中尽情挥洒着漫长的青春,她笑嘻嘻地用山涧的泉水浇灌得我全身都是。
我们从不曾提及自己的亲人,就好像彼此都有默契一样,从不触碰别人难以愈合的伤疤是一种关爱。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座城,它无声无息却也波澜壮阔。
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继续坐在那个地方,等待夕阳渐渐没入地平线。
那天,风吹着后山的森林,呼呼呼地响,月光照耀着孤寂,父亲辗转反侧。母亲的离开使得父亲疲倦了不少,父亲的皱纹好像一条一条虫子在额头翻滚,吞噬了他的精力。
即使母亲走之后,月光还是一段一段地照耀着我,照耀着父亲。她走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我的记忆便只是在这里最深刻了,她的目光有一种赭褐色的幽怨。
我那个时候只记得母亲坐着一辆警车,父亲在后面使劲地追逐。然后,我的脑海只是一片混乱。
我在无数个月光和冷风共舞的夜晚不能入眠,我总觉得母亲会突然出现在门口,然后向我述说她的冤屈。
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座城堡,里面满是幸福和鲜花。而诗柔就是我的城堡,我想她是喜欢我的,她明亮的瞳孔里面有一潭清澈洁净的水。
过了几个月,砖厂的老板改行做电子产品去了,砖厂倒闭,树倒猢狲散。
我惟一不舍的便是小兰,分别那天,后山的风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小兰不断地回头张望,我看着她明亮的瞳孔不断地黯淡,模糊,直到最后消失在我的视线。
我和父亲搬到了我大爸家里面,他家里面布置奢华,落地空调吹出的冷气格外凉爽,我忍不住站在那里让冷风吹个够。大爸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玻璃鱼池,那些花花绿绿的鱼儿在里面欢乐地摆动着尾鳍。大婶不是本地人,她独特的口音让我着实难以听清楚她的语言。她有些嫌弃父亲的邋遢,从她鄙夷的眼神,我看出来她对乡巴佬的深恶痛绝,就好像鱼儿对鱼缸的反感。毕竟大爸也只是一个上门女婿。 但是我尽力去讨好大婶,以至于我们在大爸家里面长治久安地住了接近半个月,父亲也算是在本地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父亲给别人开出租车,我们搬到了一个有众多出租屋的小胡同,这里住着许多外来务工的家属,更年期妇女的抱怨在这样一个小胡同里面屡见不鲜,有的是因为丈夫赌博输掉了一年的工资,有的是因为儿子和别人打架了。这个小胡同里面时常鸡飞狗跳,没有片刻安宁。那些没有事的婶婶娘娘会计较到因为24.5元的水费无法均摊而吵架结怨。常年的冷漠和计较、哭闹和死板把这个小胡同的气息凝固,化作一根冰冷的钢针刺进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且无法自拔,而且越陷越深。
我们出租屋对面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她一个人住,什么都和其他人分开。她见到我之后总是笑笑,那白里透黄、黄里透黑的牙齿让我毛骨悚然。
一天晚上,那个老太婆来到了我的出租房,她笑得皮开肉绽,仿佛是属于这个小胡同里面独特的笑容,让人受不了这样的笑。
她说她认识一个姑娘,想许配给我,父亲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我却极其反感,因为在我的心里面,小兰已经撑得起我的整个心扉,容不下其他的杂质,也装不下除小兰之外的女孩。她的气息已经形成了一种眷恋,我们的回忆已经在时间的洪流中凝固,就好像砖厂的砖一样已经被固定安放在某个角落。
那晚,老太婆把那个女子引来了,她看上去沉静美好而有一段风流隐藏心底,修长的身材使得她的衣服遮不住小肚子,若隐若现的肌肤以青春的名义给人以魅惑。我想起一首孟庭苇的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
她和小兰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一段相似的地方,就是有一种音韵美,她们的身上仿佛有一首歌,在你悄悄接近她时,歌声就开始响起。
她叫百合,她的话很少很少。她是一个孤儿,百合这个名字是孤儿院的院长取的,我也不想多问她的信息,因为我知道我们毕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喜欢的人是小兰。
百合我不熟悉,但是她的美丽却让我不得不为之叹服,如果说小兰是我手臂上的一抹蚊子血,那么她则可以算作是那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而永远不能成为我手臂上的一抹蚊子血。因为她的漂亮只能让我魂牵梦萦,而不敢有其它奢侈的想法。
但是,就在那晚,我的想法变了。百合主动约我到外面去,她羞答答的脸颊有些红润。百合修长的腿在那段白月光下显得更加白净,她缓缓向我走来,然后抱紧我。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左胸的跳动。
我可以闻到百合长发上的洗发水香味,还有她身上的一种淡淡的体香,若隐若现,如同百合花一样的。她紧紧抱着我,我的双手像触电一般将她抱住。我想我是要这样爱上我心口的那颗朱砂痣了,我只知道我是动心了,是不是移情别恋,我有些担心。小兰和我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我在暗示自己,百合的身体很柔弱,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她柔软身体的悸动。我们就这样的拥抱,在那个月光荒芜了美丽的夜晚。
从相识到结婚的那一天,我都感觉是迷迷糊糊的,而且我自始至终也没有想过和百合结婚。但是我们还是结婚了,并且是那样的自然。
那个媒婆笑得牙齿终于露了出来,父亲也很高兴。我说不上高兴也谈不上委屈,但是我感觉这一切都来得太快,让人猝不及防,就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来不及回味就已经成了事实。我不知道婚礼是怎么过来的,反正随便喊了几桌人,然后很随便地就完了。父亲照常一样开出租车,我和百合尴尬地笑笑。
百合是一个温婉得只剩下温婉的女生,她的声音很小很小,小得我几乎无法承受,但是我依旧对她很好,我相信缘分会让该遇见的人相遇,而爱情会让该幸福的人幸福。
那晚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应该给百合幸福。
后来,我搬出了那个怨愤的小胡同,我们一起搬到了另一个叫做萌心花园的地方,这里名不副实,没有我想象中的萌宠和花园。只有冰冷的建筑,我和百合搬到一个新的出租屋,这里通宵都有人打牌,他们的吵闹声和咳嗽声已经掩盖了月光的皎洁和夜晚的静谧。
我和百合在一起的时间,她从来不谈论什么,她总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我不敢触碰她,她身上仿佛有几千伏特的高压电。她也不碰我,我们有一种相敬如宾的感觉。
婚后,百合推荐我在附近一个修车洗车的地方当助手,没事洗洗车,递递零件什么的。洗车场的老板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有着半明半媚的忧伤,一张坏坏的笑脸,两道浓而不烈的眉毛也泛起了不易察觉的涟漪,他对我好像一直都带着笑意,弯弯的眉,像是夜空里皎洁的上弦月。健康的小麦色的皮肤衬托着他厚厚的嘴唇,魔鬼一样完美的五官,棱角分明脸型。
他的孩子很像他,是个男孩,喜欢扯着我的衣角要棉花糖吃,非常可爱。
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地平线的时候,我看见那个有道半明半媚忧伤的男人载着百合穿过曲曲折折的小路,百合紧紧抱着他,仿佛抱着一个身经百战身披铠甲的将军。我没有拆穿她,因为我知道,我自始至终都配不上她,她是百合花,开在我的心田,不会长在我的手心里。
百合回家后,她急急忙忙地洗了一个澡。她的脸很红润,兴许是那个男人给了她久违的幸福。他们就在远方的那条小路上交媾,小路旁幽森暗黑的竹林可以作证,小路旁叮咚的流水也不会视而无睹,男人的摩托车也不会撒谎。
而我只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我知道她没有错,我也没有错。只是命运错了。
百合给我说了那个男人是她的高中同学。他们从那个时候就相互爱慕。后来他把另一个女孩的肚子搞大了,才不得已结婚了。而在百合的心里面,那个男人永远是她心口上的朱砂痣,是那天上的一段白月光,而我只是她袖口的一粒饭粒子而已。她和我结婚只是为了让那个男人看,她介绍我到他的修车店工作也是为了让那个男人心痛。
我父亲知道了事实,他跑进我们的出租屋,将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全部甩在地上。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面是苦楚和疲惫,生计的艰难让他已经未老先衰,白发斑斑。
第二天,百合没有回来,我搬回了父亲的那个小胡同,我不想见到百合。小胡同的婶婶娘娘对我眉开眼笑,然后又私底讨论,发出一阵毛骨悚然、心惊胆寒的笑,夹杂着同情和怜惜。
百合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似乎是消失在了我的视线。
经过了一个月紧锣密鼓的搜索,百合的尸体在出租屋后面的那片草地的沟里面被发现了。
她的全身已经溃烂,我不忍直视,出租屋里面的许多人都蜂拥出来观看。他们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她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口里面的泡沫不断往下滴,原本美貌的百合花变成了粪窟泥沟里面冰冷肮脏的肉体。
过往的人听说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少女死了,都匆匆跑过来驻足观望,那一刻,天空变成了灰色,是一种死鱼眼一样的灰。我望着警戒线外庸庸碌碌的人群,似乎看见了那个洗车店的男人,他没有勇气走过来,然后消失在了我的视线。而且他的眼神很慌张,很害怕。
那晚,父亲收拾着东西,我们忘记了吃晚饭。出租屋的小胡同很安静,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安静,那些幽怨的老太婆知道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在谁身上。她们像往常一样尊敬比她们不幸的人,咒骂比她们幸福的人。
我和父亲处理好了百合的事情。那个夜晚,我将骨灰撒在了那个修理汽车的男人的店面附近,我不能让那个男人知道,因为他会害怕。我想百合的灵魂是系着他的,这样便也是她希望的归宿了。虽然出租屋里面的嘈杂还远没有结束,但是我和父亲打算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给予了我们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离开那天,称了几斤最贵的水果又去了大爸那里,我和父亲没有说我们的事情。因为父亲很理解大爸的难处,父亲知道大爸很忙。我们在这个豪华宽敞足有两百平米的房子里坐了十来分钟,父亲就向大爸告别。
大爸给我硬塞了三百块钱,他没有留我们,也没有再张罗什么工作。我看着大爸家里面那豪华的吊灯,好刺眼。大婶看着我,对我说道:“你要好好奋斗呀,多找些钱,光耀门楣。”
我淡然点了下头,父亲拉着我使劲走,一步都不停留。
我加快了步伐。
我们回到了原来那个砖厂附近,那个砖厂附近的出租房便宜,我和父亲便决定在这里落脚了。
我和父亲开始在这里附近的一个食品加工厂打工,早出晚归,创造的经济价值不高,工资也自然很低。食品加工厂里面有的是和我相仿年纪的人,一个个看上去身材魁梧。他们不喜欢我拼尽全力也不喜欢我优哉游哉,我只知道我是在嘈杂声中碌碌度过了半年,就好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直到那天我在下班路上遇见了小兰,她瘦了,高了,也白净漂亮了。她身边有一个男人,温文尔雅,接近四十岁,虽然不那么侃侃而谈却也看得出来是满腹诗书。至于兰松和父亲,他们久别重逢,要一醉方休。
我和小兰笑笑,很尴尬。
“这是你男朋友?”我故作大方地说道。
“鲲哥,有女朋友了吧。”她的笑还是那样清纯,清澈,如同夏季山涧里面的泉水一般透彻可人的笑。我没有告诉她我的故事,我轻轻摇头。
小兰身边的男人是她男朋友,他说要去上厕所,然后打电话说有事走了。估计是他从我的眼睛里面知道了我和小兰的关系,或许是不想尴尬,就走了。
我和小兰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些碎花生。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回忆当时的砖厂是如何的苦闷。
“其实我一直跟着你,跟了你很久。”小兰突然说道,她望着外面的车辆,来来往往。
小兰没有醉,她看到我和百合在月光下的约会,也是那次,我对百合动心了。而小兰则对我死心了。她知道我有幸福,她心满意足地离开。
“当初为什么不答应结婚?”
小兰的眼睛里面滚出了大滴的泪水。
“我是石女,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
我望着小兰,她的眼里没有任何光,只有暗淡的灰色。
我们沉默了片刻,突然手机响了,来电铃声是为了纪念百合的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
小兰很奇怪我的来电铃声,我本来想和她讲我和百合的故事,但是我没有。因为有些事只有自己经历才知道人情冷暖,别人口里面的恩恩怨怨和痛苦永远都只是隔靴搔痒。就好像我永远不知道小兰和他父亲兰松到底经历了什么一样。
第二天,那个男人接小兰走了,他喊我去玩耍。我本来是不打算去的,但是我不能忘记小兰,我想知道这个男人对她怎么样,我去了。我们经过了车水马龙的高速路,穿过了沿海的小路,走过了拥挤的菜市场。最后,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一座面朝大海的房子,旁边有一个马圈,还有一块菜地。
这就是我们的住所,那个男人说道。他很有信心,望着海滩,阳光,白浪。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够像海子的诗里面描述的一样,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每天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我们三个人在海滩上晒着太阳,踩着沙滩,远处的鸟蜂拥向了一棵大树。
走,带你们去一个地方。男人说道。
到了一个绿树环绕的地方,这里只有鸟儿的声音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我感叹这些古树盘虬卧龙一样的繁茂。
这是男人的住所,里面是一个别墅。住着他一个人,阴森森的四壁有几幅女人的画像,和小兰有几分相似,四周有几幅写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字幅。他看着墙上的那个女人,他的眼睛里面是怀念和悔恨、遗憾和不舍。
后来我从小兰那里知道,那些挂在别墅四壁的画像就是他的前妻,以前和他一起吃苦,他们从那个小村庄出发,卖过票,开过店,打过架,开过车,学手艺,吃过亏,上过当。后来他们走了出来,男人的前妻却因为那次大风死在了那片海上,那个男人的小屋就是为了纪念他的妻子。
我很钦佩他的才华,我们三个人在海边的小屋里面听那些年久违的老歌,旋律很伤感,至少我听是非常伤感的。中午的太阳照耀着海滩,男人高唱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小兰说他唱得难听,男人说这古诗词原本就是用来唱的。
我看着海鸥扑腾着翅膀飞向辽远的天边,有时候想想,觉得海鸥比人幸福多了。我正要告诉小兰我的这个观点,却发现她正和男人一起眺望着那些活泼的鸟儿飞往那绿树成阴的地方。我的心猛地被针尖刺痛,却不见有鲜红的血往外冒。只有隐隐的疼痛,却又痛入骨髓。
我和小兰道别,回到了我和父亲的出租屋。父亲在吃着花生,他对我说小兰为了我们的工作能够体面而且可以糊口,她向那个男人求情,把我们调到了一个丝绸厂做监工,一个月6000,但是她不惜做一个影子,做那个男人前妻的影子。她答应了那个男人,终身陪伴在他左右,那栋冰冷的别墅,那些繁茂的大树,那些飞去飞来的鸟。
我跑到了海边,看着涌上岸的海水冲击着软绵绵的海滩。我想哭,可是我没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在光鲜的背后不知道有着多少的故事,小兰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那样耀眼,我没有揭穿她,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座城,我们都习惯把伤痕卸妆装在城堡里面。
小兰对我情谊太重,我没有资格哭,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离开这里和父亲重新找一个工作还是应该在这里过舒适的生活。我不敢选择,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和父亲继续搬家,从一个矮小的出租屋搬向另一个矮小的出租屋。东奔西走已经让我觉得很累了,我想安顿下来,像海子那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想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想,我想投入那时而波澜不惊,时而惊涛骇浪的大海。或许海洋下面真的会有一所房子,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醒来的时候在医院,医生嘱咐我要多休息,今天就可以出院。我还是死不了,我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现实。父亲走了进来,他拿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还带来了那个老式的机器,已经布满了灰尘。父亲说多听音乐可以舒缓情绪,我望着外面的海滩,成群结队的鸟儿飞向那枝繁叶茂的树丛中。
我睡着了,我看见了很多很多的海鸥在茂密的丛林间飞翔,我梦见母亲在海鸥的背上向我挥舞着手臂。
责任编辑:李 菡
——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