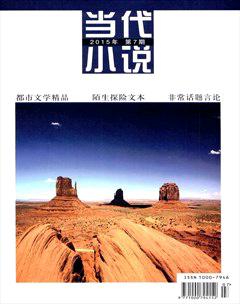父亲回去吧
黄万能
一
在锦城监狱门口,邢红扭头看见丈夫罗二胡还是怪里怪气地笑着,兄弟邢银还是漠然着。
邢红觉得真是,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那样。
邢红说,走呀,还愣着看哪样?说着就带头朝门卫处走去。
门卫要求登记,他们分别拿出身份证交给门卫。邢红说,我们是邢维余老人的亲属,特意从老家赶来。邢红和兄弟从老家赶来不假,罗二胡可是从福建的三明连夜坐火车赶来。
门卫听说邢红一行是邢维余的亲属,立即就进入了状态似的,板着的脸放松了一点,严谨的话语却不乏随和,你们来了啊,来了就好。门卫叫他们去办公室或监管科找人。
锦城监狱办公室的人听说邢红一行是邢维余的亲属,忽然就激灵了一般,请他们坐,给他们泡茶后语气谦和地说,你们来了啊——实在是很抱歉,邢维余去世这件事情我们也很感到意外……
邢红说人在哪里?我们想先看看他老人家。
监狱办公室的人说,我先把大概情况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邢红有点迫不及待想见到父亲。邢红是昨天上午接到监狱电话的,电话里的男中音问她是不是邢维余老人的亲属,待确认她是老人的女儿以后,男中音很遗憾地告诉她,她的在锦城监狱服刑的父亲不幸去世了。当时邢红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我父亲他去世了?你再说一遍!电话里的男中音重复说,确实是这样,你的父亲邢维余老人不幸在狱中去世了。邢红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在你们监狱服刑,怎么就去世了呢?你们是怎么搞的啊?竟然把一个服刑人员给弄死了!男中音说,邢女士,请你不要激动。对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确实很抱歉——希望你们亲属能来配合,把后事处理一下。
邢红随后就把消息告诉给了兄弟邢银。邢银表现得很生气,仿佛不是因为父亲在狱中去世他很生气,而是发生了死人这件事情,将耽搁他的活路他很生气。县里建园区,建到郊外的他们那儿去了,征地拆迁以后,邢银包着土建工程在做。
邢红本没打算急着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怕身体不好老态龙钟的母亲受到刺激。没想到她拐弯抹角地跟母亲提起父亲的时候,母亲竟然很有预感似的说,是你爹出事了吧?我昨晚上梦见他嘻嘻哈哈地在笑,怕也没得哪样好事情,做梦都是反的呢——是哪样事情你只管说,这些年我虽是说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其实已当没他这个人了。母亲这样豁达,邢红才告诉了实情。
母亲问邢红准备怎么办?母亲知道,邢红虽然出嫁多年,但自从父亲犯了案以后,娘家的事情多数是她在拿主意。因为邢银像是被父亲犯案的事情打击得昏了头一样,也像是在逃避家中的事情一样,尤其是与父亲有关的事情。邢红说还能怎么办呢?他死在监狱了,我和邢银只有去把他接回来——他毕竟是我们的父亲,是这邢家坝的人。母亲说应该的,你们去吧,不能让人说我们连尸都不给他收。
邢红在电话上把消息告诉给了远在福建三明打工的丈夫罗二胡,邢红用随意的口气说,毛儿家外公死哩,你要回来帮忙处理一下不?罗二胡用他惯常的孙悟空一般的声音说,他老人家死了?他老人家死了我就来看看吧——几十大岁了,也就这一回呢。邢红即使用随意的口吻跟丈夫说话,丈夫也会认真对待。为了死去的老人,丈夫舍得放下他百多两百块钱一天的活路,这就对了。邢红明白处理父亲的后事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她希望丈夫能跟她和兄弟一起参与,尽量做得圆满周全一点。也是要让人知道丈夫在参与她家的事情。
监狱办公室的人把他们带到了监管科。
监狱办公室的人又和监管科的人一起将他们领到停放老人的地方。像是一间单独的监号室。
邢红揭开盖着父亲的床单,两行泪水就下来了。穿着监号服的父亲面部惨不忍睹,眉毛稀稀的几根,眼睛像是被合上了却又没有合拢,鼻梁高高的,嘴巴也没有完全闭合,有牙龇在嘴唇边。整个脸部呈暴突状。邢红心想,父亲啊,你是怎么走到生命的尽头的啊?
邢银看父亲的脸色虽然漠然,可他说的话却很愤怒,你们是怎么把我父亲弄死的啊,你们!说着还要伸手去抓监管科人的衣领似的。
监管科的人和监狱办公室的人一边要邢银不要冲动,一边带他们三人到老人的住室,是一间集体监号室。监管科的人指着一张床铺说,老人去世的前一天,他的起居、饮食和劳动都是正常的,老人么,年龄大了,也做不了什么,分配给他的改造任务是打扫一下院落里的卫生——服刑对他来说也只是限制人身自由而已。因为他犯的那个罪使得其他犯人都有点小看他,所以平时他和其他犯人的关系都不是很好。那天晚上他一个人睡得早一点,大家睡的时候也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哪晓得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他没有动静,喊也没有喊答应,同号的人才向狱管报告。狱管经过检查,才怀疑他死了,再请狱医来看,确实已经死了。狱医确认他是突发脑溢血而死的。
邢银直戳戳地说,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们监狱说他是突发脑溢血他就是突发脑溢血吗?我们要求做医学鉴定!
狱管说我们定期给老年犯人做体检,老人确实患有高血压。说着便要狱医把老人的体检报告和尸检报告一起给三人看。
邢红和邢银看体检报告和尸检报告的时候,罗二胡说监狱都有监控录像的,我们想看一下老人死前几天的监控录像。
邢红觉得她要丈夫来参与这件事没有错,现在罗二胡提出的问题可以说点到了穴位。监狱的人有点迟疑而又犯难地说,我们这种小监狱,监控录像当然是有的,可我们条件有限,监控录像坏了没能及时修理,确实对不起,没法让你们看到老人死前几天的监控录像。
罗二胡说你们提供不了监控录像,就很难自圆其说。
邢银拿着体检报告,语气依然强硬地沿着他的思路提问题,你们发现他血压高的时候怎么没通知亲属?现在人死了就通知亲属了?
狱管说,你想说保外就医吧?我们这里当然也有保外就医,可是保外就医它也有规定,服刑犯人及其亲属得提出申请,尤其是他这个年龄完全可以,可是他没有申请。我们曾征求他的意见,他拒绝了,说他犯了罪,理应接受法律的惩罚,说他不想回去,说他没脸面对你们……
罗二胡说,那你们可以和亲属联系一下,征求一下亲属的意见啊。
狱管说这个,我们联系了的。电话是老太太接的,这里有记录,她好像不倾向接老人回去。她说儿子在包工程,忙,走不开;女婿在外面打工,要找钱来供一个小孩读大学,两个小孩读中学,也忙,走不开;女儿在城里的超市做工,照顾两个小孩读书,也忙,走不开。
邢红说这件事情我们亲属确实做得欠妥。邢红记得母亲说起过,监狱的人通知父亲有高血压的事。但是母亲坚决反对把他接回去,说他犯的事已经够臊皮了,要是他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又犯事就太臊皮了。邢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迅速站到了母亲一边。母亲说邢红,你硬要把他接回来,那他就和你去住,你给他吃给他穿给他洗衣服……邢红家中的房子虽然宽,可她在城里租的房子却不宽,也怕影响小孩读书,也怕罗二胡不同意,就打消了给父亲申请保外就医的念头。她和邢银都枉为儿女,愧对父亲啊。
狱管见没有监控录像和没申请保外就医几乎扯平,便将话题转入了另一个程序,说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犯人在监狱去世,监狱里会有一点补助,比如送到火葬场去火化的费用,回原籍的车费,还有就是规定时间和人数范围内亲属的误工费,也不多一点。
邢红提了一个很笨的问题,我们能把他弄回去土葬么?作为农村人,要是我们能把他弄回去土葬,他老人家在地下也会安心一点。
狱管说虽然你们把他弄回去土葬我们可以不负责任何费用,但是这个,还真不能。所有死者,必须就地火化,这是规定,我们只有遵照执行。
邢红又提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她想她必须据理力争,我们能给他换一身衣服后,才送他去火葬场么?这也是母亲的要求,不要穿着监狱里的衣服去火化。
狱管说这个,按规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犯人得穿着我们的服装,不过,想到他快八十岁的老人了,我们就破个例吧。
二
第二天一早,邢红、邢银和罗二胡再次进入锦城监狱,邢红让邢银去跟监狱的人办理离开监狱的手续。
邢红自己则提着个包和罗二胡一起来到停放老人的监号室,取出里面他们从家中带来或昨天晚上新买的帽子、衣服、裤子、袜子和鞋子。在给老人换衣服之前,邢红一下跪在老人跟前说,父亲,我们对不起你,让你死在了外面。现在,这也是没得办法的事情,我们给你换一下衣服,你不要见怪啊。邢红揭下老人在监号里戴的帽子,换上的是翻卷着毛的棉帽。脱下监号衣服以后,邢红接着把一件黑色呢子衣服的一只衣袖套上老人的手臂,在罗二胡抱着老人的遗体挪出空隙时把衣身穿过去,再把衣袖套上另一只手臂,理一理,扣了扣子,衣服就换好了。衣服换上以后,换裤子就轻松一点了,也是在罗二胡的协助下脱掉裤子以后,邢红把一条黑色布料裤子的两条裤腿一点一点地套上老人的腿,套到腿根以后,罗二胡伸手端起老人的臀部,邢红手中的裤子就套到老人的腰上了。也给老人系上了裤带,邢红特意系得紧一点,意思是希望老人到那边去后不要轻易松开自己的裤带。邢红给老人换上的袜子是厚厚的棉袜,鞋是里面有毛的皮鞋,相信老人穿着会暖和一点。全身换好以后,罗二胡还用手机给老人照了像。
邢银办好了手续加入进来,老人蒙了白布的遗体由三人一起抱上担架以后,是监狱工作人员抬上囚车的。锦城毕竟比县城大一点,不像县城那样,人死了有火葬场的车来运去火化。锦城监狱派出囚车把老人送去火葬场。锦城监狱原先在市郊,由于城市的扩容,它都位处市中了。坐在囚车里护送老人的邢红说纸钱呢?鞭炮呢?邢银恍然大悟似的说,买了呢,买了的,在这里,在这里。监狱工作人员说这城里不准放鞭炮,这车里也不能放鞭炮。火葬场那边有纸和鞭炮卖,去那边买安全些,从这边带过去也不安全。邢银说鞭炮不放就不放吧,这纸我买都买了,就扔在这车上也行——邢银于是就一路扔着纸钱,虽是扔在车上,可他依然像扔在地上一样隔一段就扔一点。
摆放老人遗体的担架被推到火葬场炉膛口的时候,邢红最后看了父亲一眼,噙着眼泪说,父亲,你一路走好啊。
邢银跟着站拢去说,爹吔,你原先也晓得的,城里的人走了得火葬,你走在城里就得火葬啊。
邢红听得出,邢银的话语仍有责怪老人的意思,谁叫你犯了罪被押到了城里?谁叫你没能坚持到刑满释放然后回去?当然,邢红也听得出,那话仿佛还有一层歉意,我们没有给你申请保外就医,我们也有责任。
罗二胡的表示则是象征性的,他看着蒙了白布的老人遗体,用背诵诗歌的语气说,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该咋的就咋的吧,我们会做到我们该做的一切。
在等待领骨灰盒的时候,邢红想起父亲从单位退休回家以后的生活。因是退休工人,父亲觉得,事实上也是,他的生活和当地其他人不同,穿,春冬四季,他有不同的穿着,冬天有棉大衣和呢子大衣,都有毛领,有翻卷着毛的帽子,有毛线衣毛线裤,有内层带毛的皮鞋;春秋时节,他有薄薄的外衣套衬衫,有轻便的黑皮鞋套白色的袜子;夏天呢,他有短袖衬衫,有塑料凉鞋,而当地像他一样年龄或比他年龄小的人,既没有他的衣装的质量,也没有他的衣装那样分得细、那样多。而吃呢,因为他有退休工资,隔个月把总要称肉打酒回家,还买水果罐头啊、麦乳精之类的东西回家吃。不论是吃或穿,无不体现出一种优越。住,他们家的房子早已透壁装修,板壁用红油漆漆过,柱头用黑油漆漆过,窗子安的玻璃,屋里经常是明晃晃的,热天有电扇吹凉,冬天烤铁炉子里的煤火,床上还有电热毯……
父亲过着优越的生活,却不大参加做农活,他说他都退休了,就是回家来休息的。当然,他说,家里硬是忙得很,他又心情好的时候,他是愿意帮忙搭把手的。可能就是这种状态,导致他的心思发了岔。而母亲当时,是想到他给家里带来了生活质量提高的好,就没有硬性要求他参加做农活。
父亲荷包里有几分钱,又不大帮忙家里做农活,就拿宽余的时间和附近跟他条件相当的老头们一起玩耍,除了经常进城,就是到周围人们爱去的地方玩耍,比如去钻麻池洞、千佛洞,去看石林,去看郝家湾民居,去看白号军的营盘,然后就和老头们一起打牌。他打着打着,邢银得知他打得密集,而且听说输了一些钱,就提醒他少打牌,说人老了,身体要紧,牌么,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可他没听,仍然固执地去打牌,意思好像是他输了,得去扳回来。可邢银又听说他输了钱,还借了债,邢银的火爆脾气就发了,说叫你少打牌少打牌,你不听,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在外面借了债,我可没钱给你还,大不了把你的棺材卖了抵债!邢银这一招倒是很灵,父亲确实少打牌了。可是这样一来,父亲就像没了着落似的,郁闷了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白天玩耍的父亲晚上要和白天劳碌的母亲说话,摆龙门阵,父亲往往才提起话头,母亲就打起瞌睡了。父亲说你怎么是这样呢,我们交谈一下嘛。母亲说你倒一天像老爷一样皮子都耍脱了,我忙得一点都没空闲,有点空闲瞌睡就来了。父亲从母亲那儿没得到他要的情趣,就常到村寨里公路边的小卖店去玩耍。他荷包里不是有几分钱么,他去店里买东西,买烟抽,打柜台酒喝,买零食吃,五香葵花啦,鱼皮花生啦,怪味胡豆啦,豆腐干啦,守店的妇女当然欢迎他,老主顾啊。兴许那时,他对守店的妇女产生了哪样想法也说不定。可人家守店的妇女只认卖货,只认收钱,哪会理睬他钱货关系之外的想法,再说他都是退休老头了,人家还年轻呢。没多久,公安人员就上门来把他带走了,说他强奸了村寨里和民哥的女儿!和民哥的女儿才几岁,不但同族同宗,而且还是父亲的孙辈。一家人全都不相信,可公安人员调查的结果却无法否定。臊皮啊,真是臊皮大极!不但臊了他自己的皮,还臊了母亲的皮,臊了他的儿女的皮,臊了他的儿女的儿女的皮……
殡仪馆真是想得周到,除了骨灰盒以外,还给老人的照片镶了镜框,还配有一束新鲜的菊花——当然是亲属付账。
邢红、邢银和罗二胡三人领了骨灰盒出来,监狱的人已不见踪影。邢红说,什么叫世态炎凉,这就是吧,监狱的人连把我们捎带下山的耐心都没有,人家怕我们还会缠住他们不放啊。罗二胡说人家连躲都躲不及,未必你还想人家请你吃了饭再走?
三人在殡仪馆外等了好一会儿才等到一辆的士车。
在客车站售票口买票的时候,邢红对邢银说买四张票。
邢银问为哪样呢,多花钱?
邢红说,我们来接他回去,自己花钱给他买个座位,不行啊?
邢银说只有你名堂多。
罗二胡这会儿站在邢红一边说,你姐儿这想法有创意,听她的吧。
上车以后,邢红捡他们四张票的位置中两张一排的坐下,说她和父亲坐在一起,叫邢银和罗二胡坐另外的位置。她把父亲的骨灰盒放在靠窗一边,自己坐靠过道一边。罗二胡说嗨,你还不挑呢,一个人占两个位置。邢红说你睁起眼睛说瞎话啊,我陪老人家坐,招呼他呢。要不你来招呼?罗二胡笑嘻嘻地说,你如不招呼,也该邢银招呼呀,还轮不到我呢。邢银则说,姐招呼,姐招呼得好,体贴周到,他老人家喜欢她呢,再说女儿又最疼父亲。
他们四张票的位置,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分开的,邢银坐的前面,罗二胡坐的后面。邢红觉得,这样也好,自己陪着老人家,兄弟在前面带路,丈夫在后面护送。
可是这样一来,邢红又感觉到,丈夫在后面怕是又有与女性挨挨擦擦粘粘糊糊的机会了。不过量他也不敢。男人是不是好东西,邢红都分不大清楚了。罗二胡有不轨的想法和行为后,爱努着嘴巴对邢红说,你老爹也爱那一杯啊,男人都爱那一杯呢,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男人真是怪物,是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怪物,他们总想鸠占鹊巢,扩大自己的领地,所以大多数女人们才简单而直截地表达——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罗二胡“没办法”,当初在酒厂上班的时候纠缠了那个照相的刘小四,后来买断了工龄又纠缠了好几个女人,邢红都烦了,也懒得管他了,他在外做工时要他每月交五千块钱工资,交了工资之外,他要去伙女人,去裹女人,只有另外创收才有可能,比如加班或节省烟钱,而回了家,没做工的时候,烟钱也是自理,其实也没多少余地顾及他的欲望了。邢红嘴上说你要怎样,最好不要让我看到,我烦。心里想的却是,由他吧,最好是他自己能够约束自己。
三
乘客陆续上车,差不多都到齐的时候,有人见邢红的身边有个空位,问有人坐没有?意思显然是没有的话,他来坐。邢红回答有,有人坐。邢红眼睛看着放在位置上的骨灰盒,还有老人的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问的人说,不就是个镜框么,你把它摆在边上,还可以坐一个人嘛。邢红说我给你说了,有人坐,你没听见?问的人便不好再说什么。
检票员检票的时候,坐在前面的邢银摸出四张票,分别向检票员点了四个位置。检票员说,还有一个人没来吗?邢红说来了,在这儿呢。检票员先是不解地看了邢红一眼,待看到镜框里的照片和照片跟前的骨灰盒时,仿佛被吓了一下,她似乎本不打算说什么,但停顿了一下还是说,你既然买了这个位置,别人应该也能理解,可你就不能把照片背过去么?免得吓着别人。邢红说坐车哪有面朝后面坐的呢?大家都是面朝前面,他也一样……
检票员下车以后,司机要让他的一个熟人坐前面第一排右边的机动位置,可那位置被人坐了,他把头歪过来发现邢红身边有个空位置,便说,大姐,可不可以商量一下啊?你旁边那个位置空着也是空着,让这位哥哥来坐一下。邢红说买了票的,本来就是要占个位置呢。司机站起身看见了镜框照片,说你买了票,有道理。可是,就像刚才检票员要求的那样,你可不可以把照片翻过去呢?邢银接话说,她刚才说了,坐车都是面朝前面,没有朝后面坐的。司机说,可是有人胆子小,还晕车,也想想别人啊。坐在邢红后面的罗二胡说,时间到了,开车啊,我们赶着回去呢。有乘客说,人家死了亲人,本来就难免悲伤,开车的坐车的都给个方便吧。司机说方便当然是可以给的,可是严格说起来呢,你带着骨灰盒上车,你给谁打招呼了吗?你征得乘客的谅解了吗?——我也是为大家着想呀,有人胆子小,害怕,还晕车呢。邢红说既然是这样,好吧,我用花把他的照片遮一下,该可以了吧。司机说大姐哩,我算是服了你了。
给父亲的骨灰盒买一张票哪里就能平静邢红的内心。
邢红实在是太愧疚。父亲因强奸幼女罪被判刑十五年,被送进锦城监狱劳动改造以后,母亲也不能原谅他,常愁苦着说从他犯案起,就当没他这个人。邢银也不能原谅他,常咬牙切齿地说他自身不谨,祸害别人,殃及家人,除了服刑,还会遭到报应!母亲坚持不到监狱看父亲,邢银当初不愿意到监狱看父亲,后来被他丈人劝说,才气冲冲地到监狱看过父亲。邢红自己呢,先是一年到监狱看望父亲一次,后来因为罗二胡外出做工,她照顾三个小孩读书,慢慢变成了两年三年到监狱看望父亲一次。对不住父亲啊。不管怎样,他毕竟是自己的父亲,用电视上的说法,父亲毕竟给了她生命,让她来到人世。现在,父亲已经走了,化成了一盒骨灰。在化成骨灰之前,她能想到并做到的,也只是给他换一身衣装;在这车上,她能想到并做到的,也只是给他买一个座位,让他像一个人而不是像一堆物品一样坐车回去。除此之外,她能想到的,就是父亲对她的好,作为一个父亲对她的好。邢红记得她小的时候,父亲每次从单位回来,除了给她买新衣服,还给她买礼物,不是玩具枪,就是玩具车。她记得父亲是很爱她的,她提出要电光鞋,父亲就给她买了电光鞋,她提出要红发夹,父亲就给她买了红发夹。父亲还给她好多好多的白色银毫——硬币零钱,说那是流到他手里的硬币零钱,他专门给她积存下来的。父亲还让她坐在他的肩膀上,“打马马肩”,在村寨里走来走去,邢红觉得很好玩。父亲亲她的脸的时候,那胡子戳得她脸上痒痒的——那美好的童年啊,要是时光一直停顿在那儿就好了……
在县城的长途车站下了车,三人又包了辆的士回家。
下车的时候,邢红说,回到家来了,邢银拿父亲的照片走前面,我拿父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罗二胡去小店里买鞭炮来放。
快要走进家的院落时,罗二胡在后面把鞭炮放得噼里叭啦响,白烟弥漫了好大一片,迟迟不肯散去。
老太太听见鞭炮声早就迎了出来,对她的一双儿女说,毛儿哩,妹哩,先把你们爹放在外面吧,他这也算回家了。
待姐弟俩把老人的相片和骨灰盒放在堂屋门前吞口的桌子上,老太太接着又小声说,毛儿哩,妹哩,在外面过世的人不能进屋。也不是我们亏待他,也不只是对他一个人这样,是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兴呢。他是晓得这个规矩的,相信他能够理解,你们也要能够理解才是。
父亲即使不能进屋,也还得按常规处理后事。邢红明白,虽然父亲死在外面,已先行火化,但他回来了,依然得把他送上山,让他入土为安。棺材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就是邢银威胁父亲要卖了替他还债的那副棺材,是早些年父亲自己准备的,没有麻烦邢银。请先生来安排,就是扎纸房,全龙幡伞,敲敲打打,唱唱跳跳。这个过程中,亲戚们都来了,来的人都念及父亲先前的好,或者看活人的面子,全都不提那犯案的事。大家都只有一个心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处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几乎都不涉及或评价,都是拣好的说,因为父亲再也不会置身人间了,他都走了。
邢红发现连母亲的态度也转变得不小。母亲看着邢银漠然的脸,劝说邢银,毛儿哩,你默起个脸做哪样啊,你爹他活了快八十岁,这回走了,你认为耽搁你的活路啦?傻大毛儿!人老了,早晚总有一回。你该做哪样要去做,为你爹做点事情啊,热情接待客人,也是为你爹做事情呢,也是做给活人看呢。你爹他再看不起你妈,再不把你妈放在眼里,你妈和他也是一世夫妻呢。他再不好,也是你爹呢,是他用他的工资给你买穿的,供你上学,让你从小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
和民是在夜黑的时候来到父亲的灵堂的,他像有点不大自在地出现在院坝边的时候,大家仿佛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似的。因为他是当初老人犯案那小女孩的父亲。当初,父亲被公安人员带走后,邢红和邢银曾去向和民求情,说和民哥同和民嫂要是能原谅他们父亲的卑鄙下流行为,他们可以补助一笔钱。和民说他们的女儿还那么小,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犯了法就该服法。邢红当时好尴尬。多年过去,那小女孩早已长大成人,读过初中就去外面打工了,一去就没大回来,听说已在外面结婚了。邢红反应快一点,立即站过去说,和民哥,你来了?来坐。邢红把“你”字的声音说得有点重。和民的声音有点生硬,坐——就不坐喽,我来看一下,有哪样活路需要帮忙的没有。邢红说和民哥,你能来我们很高兴,我父亲他,他作孽的事对不起你的女儿,对不起你们当父母的,也对不起邢家祖宗、邢家家族……和民叹了口气说,大伯他犯的案,已由国家的法律制裁了他。现在他人都走了,那件事就不提了吧。而我们,还是同族同宗啊,早不看见晚看见,初一不看见十五看见,还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啊。大伯虽然走了,可他还是大伯,我来,就是看一下有哪样活路要帮忙的没有。邢红说和民哥你能够这样想就太好了,这一时也没得哪样需要帮忙的,你先坐嘛,有哪样事情的时候你再帮忙搭把手也方便。
邢银把一包发给帮忙人的烟递过去说,和民哥,你先坐一会儿,有客人来的时候你帮忙放一下火炮吧。和民说行,这个活路不重。
老人的骨灰盒放在堂屋门口的时间,和民便负责鸣放欢迎客人的鞭炮。
棺材里只放着骨灰盒,抬着肯定比平常轻松得多,八大行的使用,仪式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抬八大行的人也做得像模像样,护在棺材两边的人也护得像模像样。整个队伍都像模像样,举遗像的,端灵盘的,执望山旗的,放鞭炮的。虽说不是很热闹,却也和别的丧事没什么两样,很有出殡的感觉。
邢红的母亲颤颤巍巍地把老人送到了房档头,虽然走不动了,也还看着出殡的队伍。
在预先挖好的坟地里,棺材合上之前,邢红和邢银都到棺材前去跟父亲作形式上的最后一别。
在邢红和邢银说话之前,放鞭炮的和民则站在十几米之外说,大伯,你以前做下了那样的事,不要怪我和小孩她妈不放过你啊,你自己也该承担后果。现在你走了,我来放火炮送你,你慢走啊!
邢银站到棺材跟前说,爹吔,我以前跟你作对,那是我不对。现在你去你该去的地方,就管好自己吧!
邢红看着棺材里的骨灰盒,那个她从锦城带回来的骨灰盒,眼泪汪汪地说,父亲,回去吧。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承担了责任。我们该做的,能做的,就是为你作一生中的最后一次送行——你一路走好啊,父亲!
曾经写过诗、自诩为打工诗人的罗二胡则站在棺材前念起了一首诗:来到这茫茫的人世间,我们匆匆地过每一天;在一分一秒的时间面前,贫富贵贱生命平等;每个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即使你的戴罪之身。你和我们不辞而别了,我们仍然把你悼念……
棺材合上之前,坟地四周早已响起了一片哭声。邢红也放声哭起来,哭声虽然并不是很激烈,但确实表达着她心中想表达的那个意思。在道士先生的忙乎中,在冷风的呼呼之中,邢红泪眼婆娑地看见坟前立起了一块墓碑——邢维余父亲老大人之墓。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