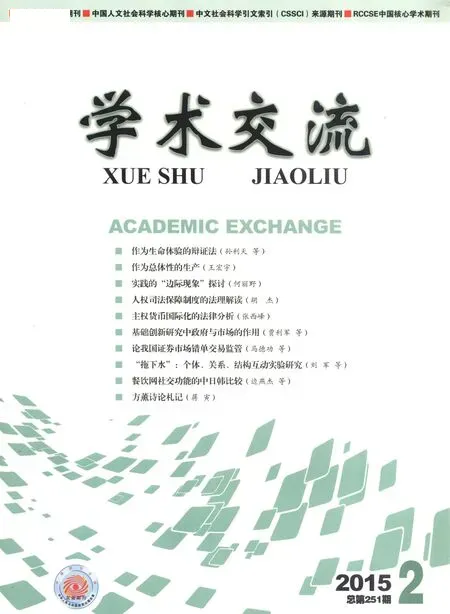餐饮网社交功能的中日韩比较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多学科理解的社会网络模型研究”(13&ZD177)
餐饮网社交功能的中日韩比较
边燕杰a,郭小弦b
(西安交通大学 a.社会学系;b.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西安 710049)
[摘要]餐饮聚会给人们提供了社会互动的机会和环境,促进了个体和社会的融合,由此产生了稳定的人际关系,被称之为社交餐饮网。基于东亚联合社会调查2012年数据,探讨餐饮网情感性功能和工具性功能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异同。通过社交餐饮人们加深沟通、增加信任、提升幸福感,是其情感性功能;而通过社交餐饮人们增加新的朋友,拓宽网络,提高跨阶层的资源整合能力和高层资源的获取能力,这是其工具性的功能。数据分析表明,三个国家中餐饮网的情感性功能从强到弱的排序是日本—韩国—中国,而工具性功能从强到弱的排序是日本—中国—韩国。可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儒家文化渗透程度来解释这些实证发现。
[关键词]社交餐饮网;情感性功能;工具性功能;中日韩比较
[收稿日期]2015-01-10
[作者简介]边燕杰(1955-),男,天津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关系社会学、实证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03;C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2-0154-06
餐饮聚会具有极强的社交功能,谓之为社交餐饮。比之其他的社交形式,餐饮提供了一个充分交流的环境,一个情义交换的场合,一个实现某种意向的机缘。为此,通过社交餐饮,一方面,参与人可以维持和加深已有的社会关系,发掘和运作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能结识新相识的朋友,拓宽社会联系,增加新的社会资源。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社交餐饮具有建构社会网络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功能,社会学研究上称之为社交餐饮网。本文依据东亚联合调查数据,从而比较社交餐饮网的情感性功能和工具性功能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异同。
一、社交餐饮网研究的发展
社交餐饮网(Social Eating Networks)是中国本土化的社会网络研究工具,1998年首次出现在中国城市消费者调查中。该调查询问受访居民外出餐饮的状况,发现“与他人聚餐”具有社会交往功能,这种功能包括情感性和工具性两个方面[1][2][3]。基于这次调查而提出的社交餐饮网这一研究工具,测量了每周社交餐饮的发生频率以及参与者的关系类型、个人特征和餐饮角色,借此研究个体与网络成员间的关系强度,以及他们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数据分析证明了社交餐饮网对于中国关系资本具有实证研究意义,并引发学者们去研究餐饮网对于企业绩效、关系消费、收入增加、社会信任、政府信任等方面的正负效应。
自首次研究之后,社交餐饮网曾在中国的两次问卷调查中被再度测量:一次是2009年的求职网调查(JSNET2009),另一次是2010年中国西部十二省的社会变迁调查(CSSC2010)。相较于其他更为成熟的社会网络测量方式(如讨论网、拜年网、求职网),餐饮网的测量稍显单薄。早期的调查中仅测量了外出餐饮的频次,即使区分了“请客”“被请”“陪吃”的不同情况,仍然仅仅是餐饮的频次测量。2012年东亚社会联合调查项目(EASS)对社交餐饮网作了新的探索,通过集体讨论研发了共同问卷,在中国、日本、韩国开展了包括餐饮网在内的东亚网络社会资本的研究。这三个东亚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餐饮的社交功能一脉相承,但其现代化发展水平却不尽相同,因而属于具有比较典型意义研究的范畴。
二、理论观点和研究假设
从理论上来研究,社交餐饮网具有情感性和工具性两大功能。情感性功能指的是,通过社交餐饮人们加强情感沟通、增进相互间的信任,从而提高幸福感;而工具性功能主要是指通过社交餐饮人们结识新友,从而增强了跨阶层的资源整合能力和高层资源的获取能力。基于EASS数据,关于情感性功能,本研究集中探讨了社交餐饮对于人们的信任水平和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关于工具性功能,本研究集中探讨社交餐饮对于阶层跨越、地位提升的推动作用。
(一)发展水平与社交餐饮网的情感性功能
东亚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平衡的,日本首先起飞,韩国随后,中国是三国中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化进程逐渐改变了社会关系模式,基于亲情的传统模式逐步式微,基于个人主义的关系模式日益强化。发展理论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越高,市场就越完善,个人需求就越能依靠市场得以满足。为此,经济越发达,社会网络的工具性功能越弱化;在发达经济体中生活,人们的社交网络是以情感性功能为主导的。这意味着,经济越发达,社交餐饮的情感性功能相对性越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1990年开始公布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HDI得分在0(最低)和1(最高)之间分布,用以衡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在2013年公布的数据中,日本的HDI得分为0.912,韩国为0.909,中国为0.699,所以发展水平的顺序是日本—韩国—中国。那么三国社交餐饮情感性功能的相对强度也符合这个序列吗?情感性功能在三国之间又有哪些共性呢?
社交餐饮是工具性功能和情感性功能的复合体[4]。情感性功能的本质是社会网络的维护和加强,其基础是互动行为,背后的含义是个体和整个社会的连接状况,互动行为越多的个体,与社会的连接状况就越好。人的社会属性需要个体和社会的融合,因而,一个人和社会的连接、融合状况越好,他就会越倾向于成为一个积极的人。这里“积极”的特质主要体现在主观情感方面,包括对他人的信任状况、自我的主观感受等。
信任具有促进社会稳定、加强社会合作、巩固社会团结的功能。研究证明,发达的社团组织和大量的中间组织都有利于信任的建立。在处于发展中的东亚儒家社会中,社团组织、自主的中间组织并不发达,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多地表现为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关于信任水平的研究大多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证明了社团参与、政府绩效对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近期有学者研究了社会网络在侵蚀信任水平上起到的正向作用:邹宇春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餐饮网社会资本对居委干部、警察等制度信任有降低作用[5]。另一研究发现,饮食社交通过信息传播和目标达成两种方式降低政治信任水平[6]。虽然对政治信任具有负向关系,但社交餐饮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作用还有待检验。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当物质条件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作为人们主观精神状态的重要指标,成为备受关注的多学科研究对象。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除健康状况、经济水平等之外,还包括婚姻关系、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工作状态、阶层分化等诸多社会学指标,当然,还有社会融合和群体归属[7]。社会网络作为个体和社会连接的重要纽带,是实现群体归属和社会融合的重要方式和渠道。
根据发展理论和上述讨论,我们得到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交餐饮网的情感性功能越强,则越有利于提高人际信任和个人幸福感,这种趋势的东亚三国排序是日本—韩国—中国。
(二)儒家文化与社交餐饮网的工具性功能
中、日、韩三国同属东亚地区,儒学曾是这些国家的主导文化和思想源泉。在最近一项关于世界价值观的调查中显示,英格哈特按照“传统——理性价值观”和“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两个维度描绘了文化世界地图,中、日、韩的地图位置接近,被归为“儒家文化圈”*资料来源:www.worldvaluessurvey.org.,因为儒家文化价值在这个圈内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东亚三国在儒家文化强度的得分排序为韩国——中国——日本。
儒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论点是伦理本位。所谓伦理本位,就是认为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定义和规范个人的利益、价值以及社会地位。为此,伦理本位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就是人们以关系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其行为后果,就是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有关系必有交换行为;若没有交换行为,则一切关系无从发生,一切人伦也无从建立。
交换行为可以分为对称性的经济交换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经济交换大多关注有价资源的短期交易,关注参与交换行为各方的相对得与失。而社会交换的特点则是交换周期的长期性和具体交换的非对称性。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交换行为往往是非对称的社会交换,这就需要行动者提早建立关系,并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加固和维持这种关系。魏昂德把关系说成是“特殊主义导向的工具性关系”[9],这样的关系是蕴含着情感色彩的,不是赤裸裸的交换,没有情感基础是不能完成交换的,但只有情感没有工具性的交换也不足以概括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关系。餐饮聚会就是社会生活中建立和维持关系的一种良好渠道,因为它为行动者提供了充分交流的环境,在一来二去的情义交换中,实现了工具性的目标。
从工具性目标的视角,社交餐饮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活动,蕴藏着关系运作的含义。无论请客方还是被请方,社交餐饮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普遍互惠行为。多次的、有来有往的社交餐饮更是重复互惠的过程。行动者通过参与社交餐饮、安排酒局、请客吃饭,个体可以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性行为构建网络并获取、动员其中的社会资源,或维持现有的社会资源。工具性的社交餐饮中亲属、朋友的比例相对较低,网络成员的稳定性低于其它的网络形式(如讨论网、拜年网),因而其蕴含的社会资源更有助于工具性目标的实现。
社交餐饮满足社会交换的非对称性和长期性两大特征。所以,人们并不是仅仅在具有确定性目标、需要动用资源时才设宴请客,而是通过设宴请客,或是参与他人的设宴,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网络,寻求并积累资源,以期在未来需要时可以从中获得资源,实现工具性的目的。通过社交餐饮形成的网络便成为个体可以动员的资源来源,该网络中的社会资源也成为了可以被“借取”、可以拿来使用的社会资源。无论参与社交餐饮是维持现有的网络资源还是发展新的网络资源,无论是设宴邀请方还是受邀赴宴方,我们都有理由相信这些经常参与社交餐饮的行动者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
资源动员能力的具体体现是什么?我们使用跨阶层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达高的资源获取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测量。跨阶层的资源整合能力指通过参与社交餐饮行为,网络能够帮助行动者接触到来自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从而获取和整合来自不同地位的社会资源。这里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指的是已经进入到日常接触中的网络成员,他们才是真正可以动员的社会资源。社交餐饮网并不测量具体的网络成员信息,它提供的只是发展个体社会网络、动员社会资源的渠道。我们通过行动者日常接触网的信息,计算跨阶层的资源整合状况和较高的资源获取状况。
地位差异大的网络可以克服地位资源的局限性、信息的重复性,提供更大的资源量[9]。日常接触的社会网络,有的网络中包含的阶层类别多,则网络的多样性强,网络中的人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阶层位置,其资源相异,影响所及呈互补性。同时,在日常接触的社会网络中,网络的多样性一致并不代表网络的达高性一致。社会网络的资源含量分布从高到低并非均质,越高地位的资源含量越高。因而,网络中的顶端代表了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至高资源的能力。能够接触到处于更高职业地位的社会成员,意味着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强。反之,日常接触中能接触到的最高职业地位的人地位越低,意味着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弱。
如果儒家文化越深入的社会其社交餐饮的工具性功能越强,即通过结识新友以提高跨阶层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地位达高能力,那么,我们得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儒家文化越深入的社会,社交餐饮网的工具性功能越强,人们通过餐饮网实现阶层跨越、地位达高的能力也就越强,这种趋势的东亚三国排序是韩国—中国—日本。
三、数据和方法
此次研究的数据来自“东亚社会调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EASS)2012年的调查,其中包括中国样本5819个、日本样本2335个、韩国样本1396个,总计9550个样本。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行了一系列描述性统计分析:
两大因变量的测量是通过问卷的若干指标得到的。情感性功能变量包括两个指标:一是普遍信任水平,由国际通用的问题“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陌生人?”而生成,是一个四点测量。统计结果显示,虽然信任水平的国家分布差异很大(p值趋于0),但是总的信任水平的三国排序是中—日—韩。二是主观幸福感(“您感到幸福吗?”),为五点测量。同样,幸福感的国家分布差异很大(p值趋于0),但是总的幸福水平(均值)是非常接近的。工具性功能变量也包括两个指标:一是跨阶层资源整合能力,被访者的社会交往在问卷给定的十个职业类别中越多,阶层跨越能力越强,最低为1,最高为10;二是地位达高能力,上述十种职业按照地位声望排列,交往者的职位地位越高,达高能力就越高。两个指标的三国排序都是韩—日—中,差异检验也都是统计显著的。
社交餐饮的参与频次和通过社交餐饮结识新友的频次是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这两个频次指标都是五点测量。社交餐饮的参与频次,中国最低,日本居中,韩国最高,国别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但是,通过餐饮结交新友的频次,中国最高,韩国次之,日本最低。
被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年限、职业类别是模型分析中使用的控制变量,而三国之间的差异也是比较大的。中国样本的性别持平,平均年龄约为49岁,而日本和韩国女性多于男性,平均年龄超过50岁。平均教育年限,日本接近13年,韩国接近11年,而中国只有8.35年。由于是户内成人代表性抽样,许多被访人是未就业者,中国最多,韩国次之,日本最少。
四、模型分析结果和解释
我们使用定序逻辑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去检验社交餐饮网的情感性功能和工具性功能。同时,为检验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使用了全交互模型,即将国家变量和基准模型中的每一个变量进行交互。全交互的做法等同于将总样本分成三个国家的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拟合,好处是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对子样本间的差异进行统计检验。
我们使用信任水平和主观幸福感来检验社交餐饮网的情感性功能。表1左列信任水平模型显示,参与社交餐饮的频次越高,则对他人的信任水平呈现出越高的趋势。虽然普遍信任水平中国高于日本和韩国(国别变量中国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但是通过社交餐饮提升信任水平的效应,三国的强度排序却是日—韩—中(通过互动项产生的排序)。表1右列主观幸福感模型显示,社交餐饮的参与频次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也就是说,社交餐饮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其强度的排序也是日—韩—中(也是通过互动项产生的排序)。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都支持本文第一个假设。
我们通过跨阶层资源整合能力和达高性资源获取能力两个维度来检验社交餐饮网的工具性功能。表2左列跨阶层资源整合能力模型显示:结识新友频次的系数是正向的,通过社交餐饮参与结识新友的频次越高,交往者的职业类别就越宽泛,跨阶层资源整合的能力就越强。这是社交餐饮的扩展社会资源的功能,在三个东亚国家中普遍存在。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呢?这可以通过模型最后部分的互动项来检验:日本通过社交餐饮而实现的跨阶层资源整合能力最强(参照项),中国略低(系数为负,但统计不显著),韩国最低。表2右列是检验社交餐饮对于达高性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通过社交餐饮结识新友的频次越高,能够结交的交往者的职业声望就越高,三国均有此效应。与前一个模型类似,日本通过社交餐饮结识新友而提升达高性资源获取能力的强度最高,中国略低,韩国最低(交互项及系数的统计检验)。这些结果与我们的第二个研究假设是不一致的。

表1 社交餐饮网的工具性功能分析
*p< 0.1,**p < 0.05,***p < 0.01
*由于表格长度限制,所有的控制变量均被省略。

表2 社交餐饮网的情感性功能分析
*p< 0.1,**p < 0.05,***p < 0.01
*由于表格长度限制,所有的控制变量均被省略。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社会被认为是一个关系社会,餐饮的社交功能广泛,而跨国比较可以帮助我们从实证数据中得到新的认知。本文运用中、日、韩三国联合调查数据,从情感性功能和工具性功能两个方面,检验社交餐饮网的社会功能及其国别差异,得到以下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从普遍信任水平和自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看社交餐饮网的情感性功能。东亚社会中社交餐饮对其他一般社会成员信任水平和对自我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具有提升作用,这一功能的发挥是通过参与社交餐饮行为的频次而实现的。国家间的排序大体是:日本、韩国较强,中国相对较弱。
第二,从推动日常交往的阶层跨越和地位达高能力看社交餐饮网的工具性功能。东亚社会的社交餐饮网对日常接触网络的多样性和达高性具有普遍的提升作用,这一作用使通过参与社交餐饮结识新朋友这一工具性行为得以实现。国家间的差异在于,日本社会社交餐饮网的工具性能力更强,中国次之,韩国最弱。
第三,社交餐饮网的情感性功能在东亚不同社会间的排序符合经济发展理论模型的假设。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社交餐饮网发挥的情感性功能就越强,反之则越弱。但其工具性功能却不完全符合儒家文化理论模型的假设。在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韩国社会,社交餐饮网的工具性功能却是最弱的。一方面,对于各国儒家文化影响程度的测量,来自单一调查的单一指标,不但其可靠性有待确证,而且多角度的测量是未来研究所期待的。另一方面,韩国社会的社交餐饮行为和个体网络也许存在不同于其他两国的特殊性,而这是我们目前的测量没有观测到的,需进一步地研究。
本文借助EASS数据讨论三个东亚国家社交餐饮网社会功能的异同,测量上受限于已有的变量,而理论解释主要是从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儒家伦理的社会嵌入程度来分析的。若干未获解释的数据结果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除了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儒家伦理的蔓延,我们必须从体制复杂性、文化多维性、生活方式多样性等更丰富的视角来发掘东亚国家在餐饮网反映出来的差异性。这样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因为本文分析证明,餐饮网在这些国家确实存在功能相同、结构相异的趋势。餐饮网对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和态度存在哪些影响,这也是我们期待未来研究者去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J].开放时代,2004,(2): 94-107.
[2]Yanjie Bian,Ken’ichi Ikeda.East Asian Social Networks[M]//Reda Alhajj,Jon Rokne.Th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Mining.Springer,2014.
[3]Yanjie Bian.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in Chinese Cit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M]//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2001: 275-295.
[4]Hwang Kwang-kuo.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92(4):944-974.
[5]邹宇春,敖丹,李建栋. 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5): 131-148.
[6]陈云松, 边燕杰.关系对政治信任的侵蚀: 城镇居民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及其差异分析[J].社会,2015,(1).
[7]Yanjie Bian, Lei Zhang, Jianke Yang, Xiaoxian Guo, Ming Lei.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People: A Multifaceted View[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4,(4).
[8]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 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9]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 清华社会学评论, 2000,(1):1-18.
〔责任编辑:崔家善徐雪野〕
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