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摆渡人
严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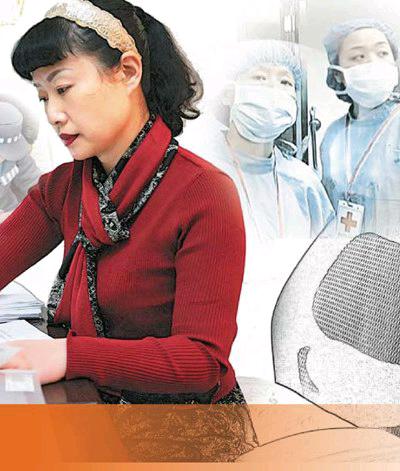
死亡与新生间只有几小时的距离。
大多数人对器官捐献的了解来自于影视作品。手术台上,病人各项生命体征消失,医生争分夺秒地取出脏器;等待移植器官的病人此时或躺在隔壁手术室,或躺在另一座城市的某间手术室,丝毫不知外面正进行着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接力赛。
人们敬佩医生,感念捐献者。但少有人知在二者间还有另一个隐形却极其重要的人。他们要解决捐献器官前所有错综复杂的情感、道德、法律问题。在官方报道中,他们叫“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一个诞生刚刚五年的新职业。
58岁的米智慧是其中之一。
一份新工作
55岁那年,这个前任护士刚办完退休手续就被领导叫住:有个新工作,你试试吧。
有亲和力、有责任感,又有医学背景,米智慧是这个新职业的不二人选。她没多想,一口答应下来,成了重庆首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但上岗后她很快发现,当协调员比当护士艰难许多倍。尽管医患关系紧张,可护士依然能收获尊重和感谢;协调员却基本只会遭遇冷漠和排斥。
上岗三年,米智慧已习惯睡得正酣时被电话铃声惊醒,她甚至期待这样的惊扰。会在深夜打来电话的通常是医院,“米老师,赶紧来,我们这里一个有捐献意愿的病人快不行了!”
期盼中的电话有时会好几周都没一个,有时一天好几个,每一个她都争分夺秒进行处理:几秒内恢复清醒,在电话里简单了解病人情况,判断是否符合捐献条件,如果医院距离较远还要联系红十字会派车。几分钟后她挂了电话,裹上外套,在出门前再检查一次充电宝、身份证、宣传资料、登记表格等是否都准备齐全。
同样习惯的还有希望的落空。深夜奔赴医院,常常半途中就会接到电话:病人已经离开人世,没法捐献了。
她的对手是“丧事一条龙”
干这一行,失败是常态。病人突然病情加重,医院嫌麻烦不配合,涉及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不及时……但家庭伦理情感是最主要的阻力。
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复杂滋味。你赶到了医院,进入抢救室,看到那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病人,他很年轻,却突发意外,属于条件最好的那类捐献者。你说服了他的亲人,捐出器官,让生命在别人的身体里延续。可突然,你的对手跳出来,就像新郎新娘正准备说“我愿意”,突然有人在门口大吼一声“我反对”一样,一切戛然而止。
米智慧的对手有时并不是捐献者的直系亲属。一个21岁的男孩因颅内出血脑死亡人,母亲和继父已经同意捐献,叔伯和姑姑们闻讯立刻全部赶到了医院,一部分人逼着母亲要和她算账,一部分人守在ICU门口不让医生动孩子。
母亲被逼得躲回了小出租屋,米智慧不想放弃,每天去一趟医院想和亲属们好好谈。跑了两天,她发现自己没法改变对方的想法。“你别和我谈,我们知道这是好事。”大张旗鼓对峙的背后,是两个家庭的斗争,“她一个改了嫁的女人,凭什么管我们家的事!”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可以救活好几人的希望,因一桩家庭矛盾破碎。
米智慧的对手还有做死亡生意的人。入行不久的一天傍晚,她接到电话,郊区发生一起车祸,车上一位男子当场死亡。这是另一类优秀的器官捐献者,发生意外的死者器官一般都是健康的,满足捐献条件。
同样在急救室,她离成功就差一步了,连登记表都递到了家属面前,程咬金又杀了出来。旁边一位神色闪烁的人把家属拉到一旁低语,很快对方的脸色就变得犹豫。那人自称是法医助理,称捐献器官会影响保险赔付。涉及到钱,家属反悔了。凌晨两点,米智慧无功而返。
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殡仪馆她又遇上了这个“法医助理”,一打听才知道上了当:“哎,什么法医,就是丧事一条龙的说客。”米智慧叹了口气,协调员有义务帮捐献者的家属处理后事,没想此举竟成了别人的眼中钉。
病房里最不受欢迎的人
跌过几跤,米智慧意识到面对捐献者家属,她得无所不能。要会和交警、监狱、医院打交道,要懂法律条款、保险赔付甚至殡葬礼仪。每一项都要从头学起。
付出了很多,工作的特殊性却决定她不一定能得到同等的理解。
护士是“白衣天使”,协调员更像是“死神的使者”,她走进病房,打破弥漫的悲伤,无情地宣告病床上的人再没有抢救价值。这是一个极其不受欢迎的角色,哪怕理智告诉家属们这个人所宣传和请求的并不是一件坏事,感情上一时也难以接受。
要说服他们很难,尤其是要说服老人。去年五月,一名中年男子因车祸脑死亡,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心脏随时可能停止跳动,如果要移植,必须马上手术。她找到了病人妻子,是她主动提出捐献丈夫器官。交谈时,病人70多岁的老母亲拄着拐杖过来,不耐烦地送客:“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走你走!”随即当着米智慧的面大骂媳妇。一个壮汉重重推开她,大声吼着:“你拿我弟的器官,要卖多少钱?”
器官=卖钱,所以觊觎器官的都不是好人,这是一些家属最直接的想法。还有人毫不客气地质问她:“你让我们捐,那你呢?”
现在,米智慧已经养成了把所有证件资料都装包的习惯。花花绿绿的证件里,有她签署的捐献所有健康器官的同意书,有协调员证、抢救证、心理咨询师证、捐献志愿者卡、佛教皈依证……“随身带着这些来证明我的清白。”
看到老人大声呵斥媳妇,米智慧感到有些愧疚,更感到心寒。也许老人的训斥会让濒死者的妻子此后再也提不起捐献器官的勇气,甚至影响到医院里其他旁观的人。要说服一个人容易,要改变一个群体的观念,何其难。
总有人会支持她走下去

摘取器官后,手术室里米智慧(左三)和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会向捐献人默哀,致以敬意。
一个人对抗一个群体,米智慧的生活频频被人打扰、威胁。拒绝捐献的家属因为气不过她对死者的“亵渎”,时常打来电话辱骂她。有人查到她家的地址,直接把威胁信送上门。去年她家的铁门就被邪教信徒贴了一张大字报:你这是在杀人,你会遭报应!
因为这件事,警方特地在她家门前装了摄像头。
可总有好人。从业五年,她最终只成功协调了57例捐献,成功率仅5%。可那些善良的捐献家庭和受捐者成为她坚持下去的理由。
2012年9月10日晚,20岁的山东女孩刘慧丽躺在手术台上,她已脑死亡。这是米智慧参与的第一次成功捐献,这段经历让她终生难忘。
那天早上,医院打来电话,才入行一个月的米智慧赶到病房前,看到哭得撕心裂肺的家属,她有点蒙。
母亲张瑞花是位质朴的农妇,几天前才把女儿送上开往学校的火车,没想到从此天人相隔。米智慧心里一阵酸楚,那一刻她甚至不知如何开口让家属签下同意书。她静静地陪在对方身边,过了很久,张瑞花抬头,问她:“是不是要签什么材料?”
协调员要见证器官摘除的全过程。晚上9点40分,捐献开始,已见惯手术的她没想到,这次器官摘取会让她失眠整整一周,闭上眼就会出现刘慧丽躺在手术台上的模样。之后的每年她都会寄给刘父一包麻花,“刘慧丽打的最后一通电话里,她告诉爸爸重庆的陈麻花很好吃。”
她感激每一个信任她的病人家属,看多了生死,她也渐渐学会如何帮助他们。三岁小女孩圆圆不慎从三楼摔下,抢救无效死亡。医院里,自责没有看好孩子的外婆跪在抢救室前哭得呼天抢地,孩子的母亲也哭得几欲晕死过去。
触景生情,米智慧早已泪流满面,可她还有工作。她只能尽自己所能为这对母女做点什么。家属不能进手术室,但协调员可以,米智慧替这位母亲为圆圆戴上最爱的小圆帽,用随身带的印泥给她涂了红嘴唇,“让孩子能漂亮地走。”化完妆,她用手机给孩子拍了照,“给她妈妈留个念想。”

米智慧已经养成了把所有证件资料都装包的习惯
有人能在支持工作时还能回馈她以善,这让米智慧终生难忘。
2014年9月1日晚,黔江区医院打来电话:“冉老师可能熬不下去了。”冉隆海是一名土家族小学教师,2004年检查出患有脑瘤,因十年来得到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冉老师在2014年7月签下器官捐献志愿书。
米智慧连夜驱车赶到黔江,当晚,冉老师被宣布死亡。依照土家族的传统,遗体必须完整,可他捐献了能捐的所有器官: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对角膜。而他的妻子在丈夫弥留时为了让器官还有被使用的可能性,忍着悲痛不停为他做心肺复苏,直到医生赶到。
捐献的肝和肾移植到了三人身上,一对角膜让两位患者重见光明。五个人得到新生。
即便是协调员,也不会知道受捐者是谁。五年里她参加过一次受捐者病友会,与自己常见到的悲苦不同,会场里一片欢声笑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健康的笑容。
仿佛一下从地狱飘到天堂,她亲眼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带着兴奋,米智慧认出了其中一位受捐者。“我知道为他捐肝的是谁,也陪伴捐献者家属一起哭过。如今见到受体这么健康,心里真的好开心。”
做不到的事
时至今日,米智慧已经连续三个春节,因为工作从团聚的饭桌中离开,三年来,为了避免错过捐献,她从不出远门旅游,“有一个能成的就太不容易了,恨不得马上飞到他身边。”她把这份事业排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缺席,成为了家庭的常态。
“他嘴上说着不支持我,但是把生活打理得很好。”丈夫深沉的包容让她欣慰,女儿虽然尊重她的选择,但更多的则是心疼。母亲忙碌了一辈子,如今家庭幸福衣食无忧,她本该安享晚年。
这份对家庭的亏欠在另一群人那里得到弥补。米智慧的手机通讯录里密密麻麻全是捐献者家属的电话,她编辑的名片一目了然:捐献者、病人或逝者姓名、亲人关系、亲人姓名(如“捐、张晓华、父、张伟”)。每一个成功捐献者的亲属都成为了她的好友。
因为把自己的联系电话留给了大大小小的医院,时常有人打电话找她出售自己的器官换钱,或者急迫地为家人寻找器官,更不乏向她抛来“合作意愿”的人。
她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话:“对不起,这件事我办不到。”
(除“米智慧”“刘慧丽”“冉隆海”外,文中其他人名均为化名)

